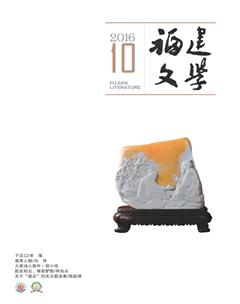蒲草人物
冯伟
三 舅
1977年的冬天,我和母亲回老家蒲草去奔丧。那一年我九岁。三舅四十七,死了。
米镇离蒲草五十里,那时没车,想去姥姥家一律都是步行。记得那一天刚下完一场大雪,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就和母亲从家里出来了,踩着积雪,行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随着脚踩雪的咯吱声和雪灌进鞋里的冰冷,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农村日子的艰辛。一路上母亲没话可说,绷着脸,脚步是急促的,也不顾及我的快慢,赶火车似的一个劲儿地往前走。我时不时地要跑上几步,撵上她,问啥时能到。母亲面无表情地回答:“快了,前面就是。”就这样,我和母亲整整走了四个小时。
我的姥姥、姥爷一共生养了十二个孩子,六丫六小儿。大舅李祥春、二舅李民春、三舅李会春、四舅李志春、五舅李和春、老舅李兰春;大姨李秀芸、二姨李秀琴、三姨李秀珍、五姨李秀芬、老姨李秀兰,母亲大排行老九,小排行老四,叫李秀英,也是他们十二个孩子当中唯一一个脱离了农村,嫁到城里的人。
在我众多的舅舅当中,开始给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三舅,是我的大舅李祥春。大舅虽是农民,但不务正业,不爱土地,爱赌博,成天鬼一样在村里游荡,白天睡大觉,晚上不着家,在蒲草一带是个有名的赌徒。那个年月,动不动就有人保组找到家里来,弄得全家人都胆战心惊的。自然大舅要比其他几个舅舅有“名气”。我的姥爷、姥姥自然对他也就操了不少的心。可要说生活过日子,几个舅舅加起来也没有大舅家殷实。这倒不是说大舅赌博赚了钱,日子好过,而是大舅的思维和那些弟弟不一样,不管输赢,该吃吃,该喝喝。照他的话说,有输的就得有吃的。
那时每家的日子过得都很紧,只有在大舅家的饭桌上能常见到大鱼大肉的影子。在我的记忆中,在大舅家的餐桌上,或是鸡蛋或是鸭蛋总是要有的。而别人家白菜、土豆都吃不上。我这几个舅舅和姨看了就生气,外面一屁股饥荒,家里吃得还这么好。可气归气,一个妈生出来的,哥兄弟、姐和妹还能怎么样?于是,在我的印象里,觉着大舅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更严重一些说,不是个什么好人。
在众多的舅当中,和大舅截然不同的是我的三舅——李会春。我的三舅是个大队长,还是个党员,是他们老李家在蒲草五十多户人家、几百口人当中唯一的一个党员。按当时大舅和三舅两个人的表现,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兄弟俩不仅在家里是死对头,在队里也是天敌。大舅的游手好闲,是出了名的,但他在全村的亲和力却好得出奇,连当大队长的三舅都不敢和他媲美。原因是他赌博交了不少朋友,公社里的一些领导、人保组的个别头头儿,自然就认识了不少。当然这些人不仅仅是认识关系,更主要的是“钱”的关系。谁家有个大事小情,请大舅通融一下好使。时间久了,村里人,只念大舅的好,对大舅的游手好闲和赌博成性也就忽略不计了。大舅不仅赌博成性,在村里的女人也没少划拉,大姑娘小媳妇,当然更多的是寡妇,好下手。要说这样的人应该是人见人烦,没人喜欢的,可大舅偏偏不那么招人嫌。说了也奇怪,赌博的人不管怎么输赢,手头儿总是有钱,你也说不清他是赢的还是偷的,是借的还是抢的。说是偷的没人报案,说是抢的又没人找。再加上大舅办事的能力极强,能说会道,出手又大方,也就在村里混了个好人缘。三舅却不同了,三舅是大队干部,待人接物都是有原则的,自然很多地方就是得罪人,特别是亲属。
从米镇到蒲草要经过分水、石棚、大岭、官屯、青山怀、火石岭、苇子沟、前窨后窨、前英后英,然后才能到姥姥家的蒲草。我牵着母亲的手,一跐一滑,深一脚浅一脚,经过半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到了姥姥家。
这时的姥姥家很乱,满屋满院子的人,哀号声不绝于耳。三舅死了,三舅是蒲草最大的官儿——大队长,在乡下算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死,在蒲草不能说不是件大事,自然前来吊唁和帮忙的人就不少,里出外进地帮着张罗、忙活。那时的冬天,也是出奇的冷。冬日里很少有人出出进进。特别是在乡下,在大雪封门的日子里,一个个都猫在屋里不想出来。只有哪家有了什么特殊的事情,通过队里的大喇叭,撇声辣气地喊上一通,这个冰冷的山沟才能活跃起来,村民们才肯走出家门。这一天的早上,还没等大队的广播放开始曲《东方红》,就听到哀乐声了。紧接着大喇叭就嚷上了,说他们的大队长李会春死了。开始村民们还没在意。在乡下死人是常有的事。在大喇叭嚷了三遍后,人们才明白过来,是他们的大队长死了,便在惊恐中纷纷地来到了三舅家。
在乡下,死人和结婚都属头等大事,无论是谁家,也无论是喜是丧,都要大吃大喝三天。特别是丧事,既表现了乡邻的热心帮忙,也能体现出主事人家的慷慨。也就是说,人死了,给活着的人一次吃饭的机会。特别是那个年代,吃是很重要的,属头等大事,怎么能不吃呢?三舅又是蒲草的人物,他死了,如同蒲草的天塌了,自然要比其他人过世显得紧张、沉痛和铺张。
我牵着母亲的手,风尘仆仆,急急忙忙地走进院子。第一眼就看见了支在院西北角的三口大锅,正冒着腾腾的热气准备着午饭。那热气在寒冷的冬日显得格外的温暖。我看了当时就有些饿了。
我和母亲进了屋,三舅的尸体就停在厨房靠北门的位置。母亲扔下我的手,一下子跪到三舅的灵前,说哭不哭、说叫不叫地边喊边哈哈地叫了三声哥。然后又扯过我,让我给三舅磕头。我跪在地上,糊里糊涂地磕了三个头。我觉着好玩儿,磕完头就和母亲进东屋见姥姥。母亲见了她的母亲才真正地哭了起来。她喊了一声妈,母女两个人就抱在了一起。母亲哭的时候,我没有哭,就在一边看着。我就是觉得奇怪,这么多人在,哭啥?!也不怕让人笑话。这时姥姥拉我上炕。我就坐到了姥姥的怀里。
三舅和姥姥住在一起。当时我也说不清是为什么。如果按乡下的规矩,姥姥是应该和老舅或大舅住在一起的,可我姥姥偏跟三舅住在了一起。后来我大了,听妈说,还不是因为你三舅是党员。我当时还小,不知道党员是干什么的。
我坐在姥姥的怀里。姥姥问我累不累,冷不冷。我看见一屋子的人,不敢说话,只觉着挺好奇,也挺兴奋。
姥姥家是五间草房,一明两暗的门,东面两间,西面两间。姥姥住东屋,三舅住西屋,中间隔着一个厨房。三舅的尸体就停在厨房的位置。
乡下每家的炕都很大,有些像大车店。每次来都能让我联想到我们小学校的篮球场。姥姥家的炕上坐了很多人,有大姨二姨和老姨,还有三舅妈和四舅妈,以及一些我不认识的邻居老头儿老太太,挤挤插插一炕。地上就是侄男和侄女在给死者裁黄表纸,打着纸钱。有蹲着的,也有跪着的。来来往往的人就从他们的身前身后走来走去。
三舅是躺在用条凳架着的一块门板上的。尸体上盖着拖地巾,是用黄色的缎子做成的,很鲜艳,上面还绣着两个小人儿。三舅的身上还放着一杯酒和一根葱。葱剥得很净,白白绿绿的,葱心部分是朝着死者胸前的左上角儿的,既表明死者是个男的,也意预着死者的晚辈们日后的多福。
母亲将我放到炕上,又回到厨房,在三舅的脚下开始烧纸。这时给三舅烧纸的不仅是三姨和五姨,还有一个哑巴。哑巴我认识,在她家还吃过大红枣儿。哑巴那年三十多岁了,始终没有嫁人。哑巴不是本村人,是三舅前些年,在村里山上树林里的一棵树上救下来的,也不知是哪儿的人。不会说话,还不会写字,想说话就那么“呀呀”的,有些像猫叫。更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后来三舅把她送到了公社,公社也没法处理,又是大活人,怕出其他意外,就让三舅暂时给安排到了他们大队的一个小型抽丝场干活儿。后来三舅见她怪可怜的,没住的地方,在公社的帮助下,在大队部的附近给她盖了间小小的茅草房,就算安顿下来了。两年以后,有知情的人,说哑巴是山西何家沟的人,父母都没了,闹饥荒,跑到这里来了,实在活不下去了,想自杀,遇见了三舅。三舅让她回老家山西,她说什么也不回,还比画着说,如果撵她走,她还去死。三舅怕出事儿,也就让她安居了下来,还给她取了个名字叫何兰香。
四个人烧纸,母亲和两个姨说话,也不背着哑巴,听着什么也无所谓。
母亲边烧着纸边问:“怎么样,三哥的棺材解决了?”
五姨说:“没有,上午研究了大半天,妈要把她的棺材让出来,这些人都没同意。”
姥姥有口棺材,是姥爷走后这几个舅凑钱给买的,准备着姥姥百年后用的。可万万没想到,三舅走到了姥姥的前面,又没有发送的棺材,姥姥就想让出来,几个舅和舅妈都不同意。
母亲问五姨,说:“老五,你啥意见?”
五姨说:“咱们当闺女的说话也不算。人家儿子给妈买的棺材,一旦给了三哥,将来母亲有那天怎么办?”
母亲又问:“他三舅妈是啥意思?”
三姨说:“就是一个哭。家穷得叮当乱响,别说棺材了,连多余的席子都拿不出来。一口一个嫁错了人,还埋怨三哥大队长当得不值。”
母亲又问:“大哥呢?”
五姨说:“你还不知道三哥和大哥的关系?大哥赌博被抓,三哥什么时候救过?不过表面上还说得过去。”
母亲说:“人都没了,就别那么较真儿了。”
五姨说:“大哥毕竟是场面上的人。不像二哥,一点面儿都不给。”
母亲又问:“二哥怎么了?”
五姨说:“他跟老三的劲儿比大哥还大,恨不得三哥早些死呢!”
母亲说:“不就是为了孩子当兵的事儿吗?都过去多少年了。”
三姨说:“你在城里,你不知道,在乡下孩子当兵比什么都重要,一旦当了兵,孩子就有出路了。你说三哥是不是糊涂,怎么能把那一年的当兵名额给了外姓人呢?这官儿当的,亲情都不讲了?”
母亲问:“后来谁去了?”
五姨说:“给那个孙洪章的老婆,孙寡妇了,说孙寡妇太困难了。”
母亲问:“三哥是不是跟孙寡妇……”
五姨小声说:“开始怀疑他们俩有事儿,后来又说没有,怀疑大哥有。谁知道?说不清。”五姨又说,“也是,那个孙寡妇家确实挺困难。你想啊,一个寡妇领四个孩子,怎么过?后来大的当兵了,还有三个。”
三姨说:“怎么不能过,我不是一个人啊?!谁家比她家富多少啊?我也是带着三个孩子,我怎么没有那些烂事儿?天生就是个骚货!”
母亲说:“要我说你也该找一个了。”
三姨守寡已经多少年了。她的丈夫,也就是我的三姨父是大炼钢铁的年代,炉倒了,砸死的。
“算了,我命硬,不找了。再找指不定还出什么事儿。”三姨又说,“要说孙寡妇也难,真要是没人照顾,她家那几个孩子还不知道怎么活呢。”
五姨说:“听说孙寡妇还要来吊唁。”
三姨说:“千万不能让她来。三哥的名声已经让她毁完了。来了我把她打出去。”
母亲说:“别那么认真,三哥都没了,有多大的仇,多大的怨,你也得忍着。人家是来吊丧的,又不是跟你打仗来的。”
三姨说:“那不行。这是败坏咱三哥的名声。她敢来,看我不把她撵出去!”
母亲又问:“四哥是什么态度?应该没什么意见吧?三哥一直对他不错。”
五姨小声说:“老四倒是没意见,可媳妇不行。人家说了,老人的棺材本儿已经拿了,棺材给谁用她不管,只是不想再出第二次钱。”
母亲说:“她怎么能这么说?三哥活着的时候,就数对他家最好。”
五姨说:“好也没用,老四在家说了不算。人心都让狼吃了。”
母亲又在盆里烧了一张纸,跪累了,站起身,直了直腰。五姨和三姨也站了起来。
五姨说:“晚上还得研究,明天就出了。”
母亲又回到屋中,和我的姥姥坐到一起。姥姥实在是老了,满目的苍凉。我坐在她的怀里,没有一点温暖感。姥姥用她那双皮包骨头的手摸着我的脚。母亲也不说话,用手给姥姥将一缕白发向后撩了撩。姥姥的身子好像是抖了一下,就把目光瞅向了窗外。我看着姥姥那苍老的双目死鱼般干干的发黄,缺少光芒。
这时有一群村民进了屋,给三舅吊唁。我的几个表哥给还了礼,并让到了三舅家的西间屋。这时院外突然有人喊:“吃饭了啊,赶紧吃完,下午送行。天儿冷,路远,时间长,都吃饱了啊,好干活儿!”
母亲对我说:“童童,咱吃饭去吧。走了大半天,一定是饿了。”
我真的饿了,一听吃饭,立马离开姥姥。
饭是在外面吃的,外面有大棚。那时乡下没有饭店,即便有,也不可能在饭店吃,吃不起。姥姥家的院子和乡下其他人家的院子一样都很大,在院子里用篷布搭的大棚,放上从学校借来的桌椅板凳,前来吊丧和帮忙干活的人就在大棚里吃。原本菜饭都是热的,可天儿太冷,上下这么一折腾也就都凉了。
我始终是兴奋的,没有一点悲伤感和沉痛感。我和大人们一样冒着寒风,耐着冰冷挤在一张大饭桌上吃饭。大棚里摆了十几张桌子,每张桌子都坐着十多个人。可能是饿的,或者是对饭菜的亲切,吃饭的人很少有说话的,都在低头吃饭,吃得忘我,吃得饕餮,吃得无我无人。我狠狠地吃了一顿饭,那顿饭可能是我一生中吃得最香、最多,也是最冷的一顿饭了。
吃完了饭,歇了一会儿,就到了给三舅送行的时辰。这已经是三舅死的第二天了,下午送完行,明天出殡。
送行前有个仪式,装车。装车就是把钱装在一个纸制的车上,给三舅带走。三舅的装车仪式是在姥姥家的院子里进行的,哥兄弟、姐和妹及所有的亲属都要参加。人们先是围成一个大大的圈子,圈子的中间是辆纸车,所有装车的人都要往纸车里扔钱。钱是假的,是打好的黄表纸钱,每个人都拿上一些。纸车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个窗口,前面有一头纸扎的驴拉着。装车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男左女右,男顺时针、女逆时针开始转,边转边往车里扔钱。装车的时候,手往车里装着钱,嘴还要不停地说着话。叫三姨父的就说,三姨父慢走,外甥给你装钱了;叫三叔的就说,三叔你慢走,侄儿给你装钱了;叫三哥的就说,三哥你慢走,小弟给你装钱了。男男女女各说各的,就显得有些乱。开始每个人的声音还挺大,渐渐地声音也就软了下来。在一旁围观的村民听了就像一群蚊子在嗡嗡地叫。我是三舅的外甥,也跟着装钱。只是我的个子矮,够不着车的窗口,每装一次钱,就得跳起来往车里扔,然后再说,三舅慢走,外甥给你装钱了。有人看了就觉着挺滑稽。我们装钱的每个人都绷着脸,或是哭丧着,或是面无表情。在我的前面是我四舅家的一个表哥。他的个子比我高,但比大人矮,也够不着车的窗口,他也是一扔一跳,跳完了就说,三大爷慢走,侄子给你装钱了。在我的后面还有一个比我个子还小的老舅家的表弟,也学我们的样子一跳一扔一说,可就是跳不高,把钱扔得里一半,外一半。就这样,表哥蹦完了,我蹦,我蹦完了,表弟蹦,有些像小丑儿。在一旁围观的人看着,憋着嘴,也不敢笑。每个人同样的话,同样的动作,要重复三遍。
车装完了,开始送行。
送行,不是送死人走,是送死人的灵魂先走。也是一种仪式,这时死者的肉身和灵魂是分开的。其实就是去土地庙那儿报到,然后路过奈何桥,再到阎王爷那里去。蒲草没什么奈何桥,那是阴间的东西,更看不见什么阎王爷。土地庙倒是有一个的,在离三舅家五里开外的一个山坳里。
正是天冷的季节,又刚刚下完了一场大雪,天上有明晃晃的太阳,很强烈地照在田野上、照在山冈上,亮得刺眼,看上去眼珠子发痛。阳光好像很足,其实一点暖意也没有。
送行的人从三舅家出来,稀稀拉拉地扯出好远,前头的队伍都要出村口了,三舅家的院子里还聚集着一大群亲属和村民等着出发。
蒲草到土地庙要经过两个村,甜水和香水,然后再拐过一个水库才能到达。送行的人无精打采,稀稀拉拉地在乡道上走着。打远看,在白雪的映衬下,一个个黑影像一个个正在滚动的羊粪蛋儿,稀稀落落的。我也在其中,跟着母亲,腰上系着条白孝带,慢腾腾地行走在队伍中。
我走着,不时地左顾右盼,想着孙寡妇能不能来,想着三姨打孙寡妇的样子。
在乡下,姥姥家的儿女可以说是众多的,六儿六女。六儿六女又繁衍出第三代人,每家最少四个孩子。不算女孩儿,晚辈儿被称为侄子的就有四十八个。送行队伍的前面一大截子,全是白衣白衫,披麻戴孝,和田野中的积雪融为一体。我和一些穿黑衣系孝带的,不属一家当族的人,还有很多村民,萎靡地跟在他们的身后,像一段肮脏的盲肠尾随着。
送行队伍的前头是打灵幡的人,灵幡的后面有人抬着纸活儿:有纸马纸车纸房纸猪纸羊,还有一男一女两个纸人儿,男的叫得用,女的叫随手;也不知是谁,知道三舅喜欢抽烟,还给做了个大大的“大前门”烟盒,抬着,也招摇。凡是三舅生前家里没有的东西,这里都有。我跟妈说:“人死了真好,什么都有。”妈打了我一下,不让我瞎说。我就不再说了。在抬纸活儿的后面,三舅最小的儿子还拿着一把纸制的镰刀,是三舅生前夏天看守庄稼总也不离手的武器。接着,是抬供桌的,供桌上摆着供品:有供菜,有馒头,还有供酒等。供桌的后面便是一个吹唢呐的人,我认识,叫二臊屄,也叫二埋汰,是蒲草本村的喇叭匠,一辈子就喜欢拿着喇叭挨家窜,恨不得谁家有点儿什么事儿,他好吹上一吹,喜事吹喜曲,丧事吹哀调,蹭吃蹭喝。二埋汰虽是个外姓人,也披着麻,戴着孝,以示对死者的尊重。
人们走着,听着哀哀怨怨、悲悲戚戚的唢呐声,像是在哭诉着一个故事,一个没头没尾的故事。听了让人心里难受。
吹唢呐的后面便是长长的送行队伍……
一行人来到一个山坳里,说是土地庙到了。我看了一眼,根本就没有什么庙。
土地庙原来是有的,到了三舅死的时候就没了。是三舅前些年带了一帮子人“破四旧”给破了。眼下用着了,庙没了,地儿还在。展现在眼前的是残垣断壁,是一个大坑。大坑夏天蓄有脏水,且发臭;到了冬天臭水冻成了冰,拜庙的人就跪在冰面上。
这时我看到了三姨,在寻找孙寡妇。
所有的孝儿孝女和一家当族来祭酒的亲戚,都跪到大坑的冰面上。首先由大劳忙振振有词地把三舅生前的所作所为流水账似的唠叨了一遍。也不知他唠叨的是真是假,都是些好事儿,什么一心为公,什么废寝忘食,什么先锋模范。有些我听得懂,有些我听不懂,反正都是好话,弄得三舅像个楷模,像个英雄,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意思。这么一唠叨,在场的人也就都被感染了,觉着这样的一个好人死了,白瞎了。便有人在人群中嘟囔:“那些作恶的坏人怎么不早些死,这么好的人却早早地走了。”在一旁跪着的大舅听了,瞥了那人一眼。
接下来开始正式祭酒。先是一家当族的平辈儿开始,然后是晚辈儿,一些外甥外女。每个人祭酒,少说也得三分钟,我是第七十六个祭的酒。
天依然是寒冷的,北风也刮得凛冽。可算轮到我祭酒了,我已经冻得不行了。我在起身的时候,险些栽倒在地上。我往远处瞅了一眼,突然看到了在离土地庙不远的一个山坡上,站着一个女人,领着三个孩子。我想,那一定是孙寡妇。
我是倒数第十七个祭的酒,也就是说我祭完还有十六个需要接着祭。祭完酒的可以站起来,没祭的就在冰面上跪着。每个人都盼着早些祭完。那时我就想,可别再死人了,跪不起。
我来到祭酒桌前,先是点燃三炷香,演戏一样,煞有介事地,左右上下地拜了拜,再插到供桌上的香炉里,然后又像模像样地磕了三个头。我有些冻麻木了,磕头的时候头碰到地上都不知道疼,后来才发现头已经磕破了。磕完头,又敬了三杯酒,学着前面的人哈哈哈哭了三声三舅,然后才能站起来。起身的时候,我摸了摸膝盖,由于跪的时间太长,已经冻得冰凉了。母亲心疼我,将我拉过去,小声地问我冷不冷。我看了眼母亲,想说冷,话却在喉咙里被封住了。
祭完酒,就是放鞭炮,同时把带来的纸活儿和装满了纸钱的纸车、花圈以及一些三舅生前的所用之物一起烧掉。三舅的灵魂就这样在熊熊的烈火和滚滚的浓烟中从人世间飘走了,骑着仙鹤,向着西方大路翩然而去。
这时我又往远处的山坡上看了一眼,孙寡妇还站在寒风中。
送完行,往回走的时候,我问母亲:“二舅为啥不哭,也不敬酒?”
妈说:“二舅家对三舅有意见。”
我问:“什么是意见?”
妈说:“就是两家不和。”
我问:“为啥不和?”
妈说:“二舅家的孩子想当兵,三舅没让。”
我问:“为啥不让?”
妈说:“当兵的名额被一个寡妇的儿子占去了。”
我又问:“什么是寡妇?”
妈不耐烦地说:“小孩子,别什么都问。”
我不再问了,又向庙后的山坡上看了一眼……
回来后,我问和三舅妈有矛盾的二舅妈:“什么是寡妇?”
二舅妈听我问,立刻瞪亮了两只眼睛,绘声绘色地告诉我,说:“寡妇就是没有男人了,没有了男人的女人就是寡妇,晚上睡觉独守空房,没人陪,外面刮风她就害怕,以为是鬼。你三舅妈就是寡妇。你三舅没了,她就成寡妇了。”说话的时候,二舅妈很得意,很是幸灾乐祸的样子。
送行完了,在姥姥家的大人们都忙自己的事。我闲不住,跑到了大舅家。大舅家我是来过几次的,就住在三舅家的左侧。大舅家的房子原先是和三舅家一样的草房,重新翻盖了,变成了五间大瓦房,还用红砖圈了个大大的院套儿,水泥的地面,气气派派,敞敞亮亮的,看上去有些像过去的大地主,把三舅家的草房显得有些像贫民窟。
我走进去,里面有人在说话,进屋一看是大舅、二舅,还有大大舅妈、小大舅妈和二舅妈。大舅一共两个老婆,听说小大舅妈是赢来的,怎么赢来的谁也说不清楚。为了这事儿,大舅还被判了一年半的徒刑。判完了刑,也就稀里糊涂在一起过了。大舅的两个老婆,大大舅妈和小大舅妈相处得还不错,不仅相敬如宾,还称姐道妹,难得的和谐。对大舅来讲,两个大舅妈不仅晚上睡觉用得着,每当大舅赌博的时候,也能用得着,派两个舅妈出去给站岗放哨。一个在河东公社的人保组门前盯着,一个在河西家门口等着。只要有人举报,人保组的人一出动,在河东的小大舅妈就向空中放一个钻天猴儿。钻天猴儿是一种鞭炮,点完后能飞得很高很高。只要钻天猴儿在空中一炸响,在河西家门口的大大舅妈或是能看见,或是能听见,立马给正在赌博的大舅等人报信儿,告诉他们人保组来了。大舅这边就散伙。工夫不大,人保组的人开着摩托车气势汹汹地到了,也就扑了个空。每每都是这样。这个故事我听了无数次,每次他们都讲得都有声有色,惟妙惟肖。
大大舅妈和小大舅妈我都认识,还都很喜欢我。我走进来,原本他们都是笑着的,为什么笑我不知道,反正这是我来奔丧第一次听到的笑声,而且笑得很肆无忌惮。他们见我进来,马上就不笑了。我本应该也是笑的,笑容刚刚绽开,见他们不笑了,我也就没有理由再笑了,这让我感觉很窘。人从笑变成不笑的过程很难,我想当时我的笑容一定很难看。大大舅妈看见我就问:“童童,怎么跑这来了?”我被大大舅妈问得有些发蒙,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本是瞎乱跑着玩儿的,没什么目的,大大舅妈这么一问我就没有理由了。小大舅妈见我不说话,就说:“快过来,舅妈给你鸡蛋吃。”我喜欢吃鸡蛋,就走了过去。只听二舅妈说:“装车的时候,一些孩子乱说乱叫,本应该叫三叔的,却喊成了爹,笑死我了。”
大舅说:“人多就是好,一跪一大片,像雪一样白。”大舅又问二舅,说:“你怎么不祭酒?点你的名字,你不答应。”
二舅说:“我不祭,死不死和我有什么相干?我一想起他活着的时候干的那些事,气就不打一处来。我能去送他就不错了。”又说,“大哥,你们说说,老三活着的时候哪件事是替咱老李家人说话的?”
大舅说:“二弟你不对,人都没了,死者为大,就不能再挑那么多了。什么对错,人一闭眼就没对没错了。”又说,“要说对老三有意见,我比你意见大。那一年我被县公安局的人抓去了,蹲了半个多月,老三看都没看我一眼。不仅不看,还对公社人保组的人说,好好教育教育我,省得给咱老李家丢人。你说这是亲兄弟该说的话吗?那次可把我气坏了。他县里有人能说上话,不说也罢了,你也别说坏话呀。还要好好教育教育我。我当时听了都想把他宰喽。可他现在没了,挑他还有什么用?”
大大舅妈说:“他还欠咱家的钱没还呢。”
大舅气道:“你找老三要去吧!尽说些屁话!”
大大舅妈说:“不要也成,但话得说。给老太太买棺材的时候,当儿子的人人都有份儿,老三当时没钱,是咱家给垫上的。谁曾想他走这么早,这钱管谁要去?一定得让大伙知道,这钱是咱拿的。老太太的棺材本儿,咱是出了双份钱,别以为他老三也拿钱了。”又说,“现在可倒好,人家一分钱没拿,却得到棺材了。你们说,上哪儿讲理去?”
大舅说:“你再说,别说我揍你!”
大舅这么一说,大大舅妈就不说话了。每每都是这样,一到关键的时候,大大舅妈就什么都说。说完了,大舅就要打大大舅妈,大大舅妈就不说话了,免得挨打。其实真打假打谁也没见过,反正大大舅妈的话该说的都说出去了。
小大舅妈把鸡蛋给我剥好了皮。我站在地上吃,吃了两口才知道是咸的。我就说:“这鸡蛋是咸的。”
小大舅妈猛地想起,说:“哎呀,我给你拿错了。”又说,“小鳖羔子,真精!”于是,就去了厨房,给我换鸡蛋。
我从大舅家出来,来到街上。乡野依旧是皑皑的白雪。村路上的雪早已被行走的人踩踏得板结了,脚走上去有些跐滑。我走在乡路上,迎面看到了老姨和大姨。大姨家不住在蒲草,住在后窨,离蒲草三里。大姨和老姨想去三姨家。
三姨家住蒲草的河东,三舅家住蒲草的河西,从三舅家出来到河东需要过一条河。这条河叫甜水河,是大清河的一条支流。夏天河水溪流涓涓,可以蹚着河水走人,也可以踩着摆在那里的几块大大的鹅卵石过河。冬天河水冻成了冰,水在冰下流,过河的人,无论大人孩子都从冰面上走。蹑足潜踪、小心翼翼,不摔倒了就行。老姨扶着大姨过河往三姨家走。我悄悄地跟在她们俩的身后,听他们说话。
老姨说:“三哥挺惨的,死了连口棺材都没有。”
大姨说:“老三这辈子,就是没把家当家,心都在外面了。”
老姨说:“二哥和五哥是让他得罪透了。”
大姨说:“关键是弟妹不行。三弟活着的时候没给他们办事,人没了,开始算总账。”
老姨说:“不是一家的人还是不行。”
大姨说:“是一家人也不行。平时老三对老五多好,还不知足。”
老姨说:“主要是五嫂操蛋!”
大姨说:“不怪媳妇,怪咱弟弟不行。老五媳妇跟老三种仇是在地震那会儿,老五媳妇管老三要集体的大柴取暖,老三没给,却把大柴分给了别的村民。老五媳妇生气了,说不给家人给外人,还是什么一家人。从此再没说过话。两家也不往来,跟仇人似的。后来听说老三在地震期间动用了集体物资,被公社给了个留党察看的处分,老五媳妇知道了,乐坏了!”
大姨说:“家里没得着好处,还为外人背了个处分,老三这是图啥?”
老姨说:“幸亏家里人没得着好处,不是损公肥私,真要是得着好处了,三哥的党票就没了。后来有人给三哥说情,说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集体和村民,才给了个留党察看半年。为这事儿,妈还大病一场呢。”又说,“咱家就三哥这么一个党员,真要是被开除了,咱老李家的脸往哪儿搁?”
我跟在两个姨的后面,正听得入神,“啪”的一声摔在冰面上。大姨和老姨回头看见了我,把我扶了起来。
我摔了一跤,就不想去三姨家了,又回到了姥姥家。这时的院子里有些安静,送行完了,哭喊声也没了,灶上的人在忙着做晚饭,大多的人都回家休息了,攒足精神,准备明天出殡。
三舅的尸体依然放在厨房的位置。我想起了有一年来姥姥家,偷吃了大队果园的苹果,被三舅发现了,他训斥了我,并在小河边罚站半小时。那时我有些委屈,还有些恨三舅,不就吃个苹果吗?有什么了不起。当天晚上我就不想在姥姥家待了,闹着回家。三舅知道了,给我拿来了几个苹果,说:“吃吧,这是咱自己家的。”我看了眼三舅,接过苹果。三舅又说:“以后记住,公家的东西咱不能动!”我吃着苹果,看着三舅。
我在三舅的灵前站了一会儿。有几个村民和那个哑巴何兰香在给三舅烧纸钱,边烧边将纸灰用黄表纸包好,然后放到三舅躺着的尸体的衣服里,说是留着明天三舅上路的时候用的。我也凑过去,装模作样地跟着胡乱地烧了几张。哑巴还跟我打了招呼,意思很想我。我也跟她做了手势,说也很想她。她看了很高兴。我烧了几张纸,然后就去了西屋,就是三舅一家人住的地方。
三舅住的房间和姥姥是对面屋。我走进去,三舅妈坐在炕上哭丧着脸,身旁有几个邻居老太太在劝说着。屋子里很冷,也很乱,炕上堆了乱糟糟的孝带和孝衫,还有一些刚刚砸过的纸钱。屋子里的房顶没有棚,能看到檩子、椽子和房梁及尖尖的棚顶,檩椽上悬挂着长长短短的塔灰,随着冷气在那儿飘荡着。由于他家死了人,墙上的镜子蒙上了黄表纸,钟也被停了摆。炕的对面是一个躺箱,已经旧得发黑了。躺箱上只有一个雪花膏瓶,还有一块被人用过埋汰汰的胰子,胰子的旁边放着条脏得辨不出颜色的擦脸的手巾;躺箱的右侧是一口酸菜缸,有酸菜在里面,被一块大石头压着,能闻到酸菜酸腐的味道。酸菜缸旁是条断了一条腿儿的凳子,上面放着几件肮脏不堪的衣服,既旧又破烂,我认识,是三舅穿过的,准备明天在坟上烧。屋内的墙已经不白了,是那种灰黑的颜色。冬天太冷,北墙上挂了好些霜,一块块的白,灯光一晃,白得耀眼,有些像白癜风;在炕西侧的山墙上,贴着一张毛主席的像,已经很旧了;像的两侧有三舅亲手写的对联: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字写得不怎么样,歪歪扭扭的难看。我看着毛主席,毛主席也看着我,他老人家和我慈祥地微笑着。
我在屋里转了一圈儿,又走了出来。这时我碰见了三姨正和大姨说话。只听大姨说:“我看见孙寡妇了。”
三姨忙问:“她在哪儿?”
大姨说:“在土地庙的北山上,领着孩子。”
三姨说:“她来我撕了她。贱货!”
大姨说:“这可不是打仗的时候。”
又到了晚上吃饭的时间,帮忙的外人和家里人,该吃饭的都吃完了饭。吃完了饭,大舅又给全家人开了一次会,会议的内容还是关于三舅的棺材问题。
姥姥家的屋里又换了一群人,都是舅舅和姨,姨父还有舅妈,站着的坐着的趄着的靠着的,满满的一屋子。这时,窗外一片漆黑。组织开会的自然是我的大舅。三舅没了,如果三舅活着,主持开会的一定是三舅。三舅是大队长,三舅是党员,无论在队里还是在家里永远是头把交椅,说话办事都要听他的指挥。三舅活着的时候,家里时常也是要开开会的。或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或是传达什么指示精神。三舅喜欢给人开会,更喜欢给家里人开会。在这个家只有开会是三舅唯一可以炫耀的了。他吃的赶不上大舅,穿的赶不上二舅,住的也就更不行了。只有开会是他最得意的。姥爷活着的时候,开会时三舅是要坐在姥爷和姥姥中间的,姥姥和姥爷就像两个大臣一样坐在左右,跟着自豪。特别是逢年过节,全家人总是要聚上一聚,做些好吃的在一起吃。这时的姥姥姥爷也一定是要把三舅夹在中间的,由三舅说上几句拜年的嗑儿,过年的话儿,然后开始吃,开始喝。三舅开会时还喜欢眼前放一张饭桌,左首是我的大舅、二舅、四舅、五舅、老舅;右首就是大姨、二姨、三姨、我的母亲、五姨、老姨。那些舅妈和姨父们只能是坐在其他什么位置了,或是蹲着,或是站着,随意。有些像水泊梁山按级别、分大小排的座位。这就是三舅的威风。三舅很喜欢这种威风,也更得意这种威风。开会的时候,三舅还喜欢在饭桌上放一个大茶缸子,茶缸子是他当县劳模时人家给发的奖品,上面还有个大大的“奖”字,奖字的后面还飘着一面革命红旗。茶缸里面没有茶,三舅喝不起茶,里面是用热水泡的面起子(小苏打)。三舅是得胃癌死的。家里人都知道他有严重的胃病,一喝面起子胃就不疼了。三舅还喜欢抽烟,满口的牙都是黄的,看上去他的嘴永远是脏的,而且脏得过分,像刚刚吃过屎。三舅讲话之前总是要卷上一袋旱烟抽,然后再喝上几口面起子水。如今三舅没了,那个大茶缸子就冷落在姥姥身旁的窗台上,里面的面起子水也已经是冰凉的了。取而代之的是大舅,大舅是老大,又有钱,父亲不在了,三舅不在了,长兄为父了。大舅是个瘦人,可他的瘦和乡下其他人的瘦不一样。我的二舅四舅五舅老舅都是瘦人,和乡下其他人的瘦法是一样的,是干瘦,黑瘦,而且瘦得萎靡,像霜打的草蔫蔫的,没有精神。由于生活的窘迫,穿不像穿,戴不像戴,瘦得土里土气,埋里埋汰,坐在那里,像一堆垃圾。大舅就不一样了,虽然也瘦,可瘦得白净,利落,有精神。他是一辈子没经过风雨,没干过农活儿的人,坐在炕上和那些跟土地打一辈子交道的舅舅们比就是不同。不仅穿戴不同,动作也不同,说出的话来也不一样。无论说什么都头头是道,条理分明,而且声音洪亮。坐在那里,有些像城里退下来的干部。
大舅说:“还是老三棺椁的事儿,明天就出了,总不能裹领席子走吧。都拿个主意,人死了不能总在家放着。”
大舅说话的时候,有人把目光瞅向炕上的姥姥。
大舅说完了,姥姥说:“看我干啥?你们不用研究了,把我的棺材给老三带走。”
二舅问:“你总是让,将来你有那天你用啥?”
姥姥说:“我到那天不用你们管。”说完,姥姥把干瘪的目光投向漆黑的窗外。
外面是黑的,屋里的人就被映到了玻璃上,有些像看幻灯片。
四舅说:“反正我不同意把妈的棺材给三哥。老太太这么大年岁了,到了连个棺材都没有,让人笑话。老太太,我可跟你说好了,你要是把棺材让给了你三儿子,到时候你有那天,别说没人管你。”
二舅妈说:“我们能拿一次钱,不能拿两次钱。再说,我们凭啥给他拿棺材本儿。老三活着的时候,对咱这个家有什么贡献?”
姥姥说:“怎么没有贡献?老三是党员,就凭这一点就是贡献。咱们老李家在蒲草,好几十户,几百口子人,还有谁是党员,不就咱家老三一个吗?他是咱家的顶梁柱。咱们李家这些年和东街的老王家都比个啥,是比人多吗?还不就比咱家比他家多一个党员吗?那就是贡献!光荣啊!咱家要不是老三这个党员在村里撑着,咱老李家这些年能这么硬气?”
二舅妈说:“有屁用,给咱办一个事儿了?哪次求他好使了?是咱家孩子当兵他同意了,还是地震时把大柴给咱们谁家烧了?”
老姨说:“我说二嫂,不能这么说。那大柴真要是咱老李家人烧着了,三哥这个党员还不得让人给开除啊。”
二舅妈说:“不为自己家办事儿,当官儿有屁用!”
姥姥突然说:“闭上你的臭嘴,我就不愿意听你说话。你只知道自己占便宜,什么时候替别人考虑过?”
姥姥的突然愤慨,让全家人有些吃惊,都去看姥姥。姥姥说完了话,嘴唇有些颤,手也有些抖。
四舅说:“这些都别说了。人都没了,说这些有什么用。怎么也得把人送走吧。就这么光身子走了,也让村里人笑话。”
五舅说:“老三这一辈子,除了对外人好,对家人哪好?”
大姨说:“老五,说话得凭良心,你家二丫蛋子掉水库里了,不是老三救的吗?!”
三舅妈哭着说:“你现在住的房子还是咱家的呢。那年地震,你家的房子震倒了,不是你三哥把咱家的房子让给你的吗?”
大姨说:“你家老五入团填表,政治面貌都是写他三大爷的名字。要不是因为他三大爷是党员,政治面貌好,你家的孩子怎么能入上团?”
五舅吐出嘴上的烟屁股,说:“谁让他是党员?咱们这一大家子,就他是党员,不写他写谁?别的光借不上,还不能借个名吗?”
五姨说:“借名也是借。我条件不行,要是行,我就送给三哥一口棺材。”
老姨说:“五姐,你别在那儿空嘴送人情。我还不知道你吗?铁公鸡一毛不拔。你问问在座的人,谁在你家吃过一顿饭?”
五姨说:“你们都有家,凭什么在我家吃饭?”
大舅听了生气,道:“你们还有完没完?说什么说,就是生你们这一群生多了。”
听了大舅的话,姥姥叹了一口气,用手抹了抹干瘪的眼睛。
大舅觉着话说过了,便低下了头。
老舅说:“知道你们这样,就应该把你们都掐死!”
大姨说:“要掐也得先掐死你,你是最小的,也是最多余的一个。”
老舅妈不爱听了,说:“掐死你,少掐死咱家人。”
大姨说:“你少参言!咱老李家的事,该你屁事儿!”
老舅妈说:“好,我不参言,咱们走!”说着,就拉老舅回家。老舅不动。
老舅妈又说:“你不跟我走是不是?那你跟你三哥走吧!以后你就别想回家!”
说着,一个人走了出去。在走到三舅灵位前的时候,一脚把正在烧纸的丧盆给踢翻了,顿时黑黑的纸灰飘了一屋子,也落了三舅尸体一身。正在给三舅烧纸的哑巴不干了,“嗷”的一声,蹿了上去,抓住老舅妈就开始打。老舅妈没有准备,两个人就撕扯在一起,滚在屋地上。屋里的人发现了,出来拉架。有恨老舅妈的,就拉偏仗,拽住老舅妈不放,让哑巴腾出手来打老舅妈。老舅妈的脸上就被挠了一道血槽,哑巴的头发也被老舅妈拽下了一大把。老舅妈见是哑巴打了她,又没法讲理,好汉不吃眼前亏,便叫嚣说:“你等着!我跟你没完!”也就落荒而逃了。
哑巴见老舅妈被打跑了,喘着粗气,又把被踢翻的丧盆重新摆好,继续给三舅烧纸。
众人又回了屋,坐下。
大舅说:“老弟,你的老婆你得管一管了。”
老姨说:“他管?他没女人根本就没法儿活!”
老舅说:“我就没法活,咋的?我没女人就活不成!有能耐你们都别娶老婆。”说着,一转身,也走了。
屋里又静了下来,房间里很冷清,只能闻到烧过纸的味道和一些呛人的抽烟味儿。
这时我母亲说:“咱们这么呛呛也没个头儿,我看还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吧。一口棺材多少钱,我出三分之一,剩下的大伙凑凑也就齐了。”
大大舅妈说:“她姑,你要拿你拿,别在那儿挤兑我们。老太太的那口棺材我们家已经拿双份了,替老三拿了一份儿。你是城里人,咱比不了,你们家像家,业像业,大人孩子吃穿不愁,咱不能比。咱家没钱!”
二姨说:“老四,你可别在这耍咱,这可是他们当儿子的事儿,咱当闺女的是嫁出去的人,泼出去的水,千万别蹚这浑水儿。你有钱拿行了,你拿了,我们这些姐妹拿不拿?搁什么拿?哪家不是等米下锅?谁家不是拖家带口的?你两三年不回来一次,回来一次你发善心,别说咱姐妹不给你这个面子。”
大大舅妈说:“就是,老四,你可别在这卖人情。就你三哥平时那表现,他死了,咱们能来都是给他面子。别的不说,前年地震,每家都在外搭简易房,老三把村里的架杆都给村里别人家分了,咱们谁得着了?我就没明白,你说他当这么个官儿咱得着什么好处了?不仅没得着好,还跟他吃了不少瓜唠。就说那个孙寡妇吧,咱也说不清他们俩是什么关系,可村里人都说他们俩怎么怎么的。你说他搞破鞋,关咱屁事儿?他舒服着了,咱还舒服着了?好光借不着,挨骂可不少。”
三姨“嗷”的一声,说:“别一口一个寡妇寡妇的,我不爱听。寡妇就得搞破鞋呀?”
大舅也跟着厉声道:“再说我揍你!”
大大舅妈也就不再说话了。
大姨看了眼三姨,却在背地里笑。
三舅妈突然说:“你别在那埋汰老三,他跟孙寡妇根本就没事儿。谁有事谁知道。”大伙就去瞅大舅。只听三舅妈又说,“再说,老三也不是那种人。他每次给孙寡妇东西,都是我亲自给送的。现在他没了,你们还在这说他的坏话,小心遭报应!”说着,便呜呜地哭起来。
四舅妈指着姥姥说:“老太太,你别以为你有个党员的儿子多么光彩。我跟你说,光都让别人家占去了,你得着啥了?临了,你那个宝贝儿子还不是跟你争棺材来了。”
姥姥听了也不说话,凌乱的白发在昏暗的灯光下颤动着。
大舅说:“你们说的都是小事儿。前年,咱爹走的时候,我想给爹找块好的坟茔地。老爷子一辈子辛辛苦苦不容易,我想给葬个好的地方,对咱们李家的后代也有好处。我相好了东山脚下的那块山坡地,正好是个杠子,后面是山,前面是河。还找阴阳先生给看了,说那是块好地儿,平杠,两沟夹一杠,辈辈出皇上。我就去找三弟要那块地,想把爹埋在那里。三弟听了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什么也不同意。说地是好地,要打粮食,做坟茔地白瞎了。你听他说的话,给咱爹做坟茔地白瞎了。这官儿是不是越当越糊涂?这儿子不白养了吗?老太太不是我说你,你不要以为咱家出了个当队长的你怎么光彩,不为自己家办事就是当了皇上也是没用!”
姥姥看了眼大舅,又一次把目光甩向漆黑的窗外。外面依旧是黑的,玻璃窗含含混混地映着屋子里的人。
母亲不再说话了。她搂着我,摸着我的脚,我的脚有些疼。
该说的话都说了,气氛一下子凝固下来,整个屋子也显得更加冷清了。我朦朦胧胧糊糊涂涂地听着,好像是在打架。
这时,姥姥叹了口气,说:“你们都别争了,我想好了,把我的棺材给三儿子,我走那天不用你们管。”
大舅说:“老太太你可别后悔。”
二舅说:“你是想让咱们背个不孝的名声。”
四舅说:“反正东西是你的,你爱给谁给谁。”
五舅不说话,在那冷冷地笑。
大姨不说话。
二姨不说话。
三姨五姨老姨也都不说话。
母亲就更没什么可说的了。
大大舅妈又不干了。她乜了眼大舅,又说:“老太太,咱可把丑话说在前头,万一你有那天,可别怪咱用席子把你裹走。”
二舅妈说:“这可都是你家儿子的事儿,既然你想这么做,咱们就立个字据。到时候让村里人看看,可不是咱们做媳妇的不孝顺。”
四舅妈说:“人家儿子是从人家肚子里爬出来的,当然心疼。”
五舅妈说:“你们都在这瞎嚷嚷,现在我是看明白了,这一群儿女,老太太最疼老三。人家是党员,是大队干部,你们是啥?都是土老冒!”
姥姥揩了揩眼睛,颤着声说:“当啥不当妈,都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谁都心疼。”
我母亲再没说话,含着泪走了出去。
母亲出去了。剩下的人也坐不住了。人们纷纷地离开了姥姥家。屋子里空空荡荡的,有些瘆人。
姥姥见人走了,下了地,驼着瘦弱的身子来到了三舅的灵前,抚摩着三舅的尸体,喃喃自语:“老三,别害怕,妈跟你一起走。”
母亲听到了,问:“妈你说啥?”
姥姥说:“老三走了,这个家我还待个啥意思,一起走算了,还能省口棺材不是?”
妈没说话,抱着母亲在三舅的灵前哭。
这一天的晚上,本应该是给三舅哭哭九场的,被棺材的事一闹,九场也没人哭了。
第二天是三舅出殡的日子,天没亮,我就被人们的忙碌声吵醒了。按当地的习俗,天不亮就该起灵。冬日的夜是漫长而寒冷的,晚上天早早地黑了,早上天又晚晚地亮。出殡要抢在太阳出来之前。亲属们和一些乡亲们早早地来到了三舅家。正在人们想把三舅放到姥姥的棺材里的时候,突然有唢呐声从外面传了进来。所有的人都把目光瞅向屋外。黑暗中,只见一个穿白挂素的女人领着一群村民,抬着一口白茬儿棺材,吹吹打打地走了进来。女人一脸的泪水来到了三舅的灵前,“扑通”一声跪下,哭诉道:“队长啊,我是代表四个孩子给你磕头的。你可一路走好啊!”
……
三舅走了。三舅就这么走了。三舅是躺在孙寡妇和一些村民们送的白茬儿棺材里走的。
这时太阳也出来了,带着一种光芒,照着出灵的队伍向东山的方向走去……
大 舅
三舅死后,因村里没有党员,蒲草村有一段时间没有大队长,所有的工作都是公社的一个副书记兼着的。按理大队长是不是党员也无所谓,可一个村没有一个党员坐镇还是不符合上级的规定和要求的。米镇公社为蒲草村没有适合的人选当大队长很是挠头。其实,想当大队长的也有那么几个,只是都不那么尽人意。河东的张三强,河西的吴柳,还有我的大舅李祥春,都算是蒲草村有头有脸的人物。张三强绰号“长头发”,做过几天小学的班主任教师,因为猥亵女学生被开除了。他的好色在蒲草是家喻户晓的,属于生活上有严重问题的人,人见人烦的东西。吴柳虽说没有张三强那么有文化,可也不像张三强那么不正派,就一个毛病——娘娘腔儿,走到哪里都是高抬腿轻落步,浑身上下没有二两肉,轻飘飘的,个子不小,走起路来两个膀子总是翘翘着,像是要飞,说话就更是燕语莺声了。属于女人见了恶心,男人见了肉麻的那么一种男人。这样的人当了大队长会是什么样?谁也不敢想象。要说有点儿男子汉气概的,大舅李祥春应该是首选。可大舅并不像死去的三舅那么让人信服,大舅的爱赌博在蒲草也是人人皆知的。这三个人要说有能力,在公社领导心目中有位置,还要说是张三强和我的大舅李祥春。公社的领导把张三强的好色和大舅的爱赌博进行了比较,哪个对社会的危害更大一些。有的领导说,张三强好色属作风问题,作风问题对家庭有影响,但对社会的危害不是很大。赌博就不一样了,输急了轻则借和偷,重则骗、抢和贪污,对社会影响极坏。可公社的一把手书记不那么看,他认为赌博属于游手好闲,金盆洗手不玩儿也就是了。有人说,赌博的爪儿,卖淫的胯儿,是改不了的。公社书记说,这两种人要改造就改造赌博的,这种人聪明,还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当个大队长应该没问题。如果李祥春能一年不赌博就让他当这个大队长,两年不赌博就培养他入党。公社的书记都这么说了,其他人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