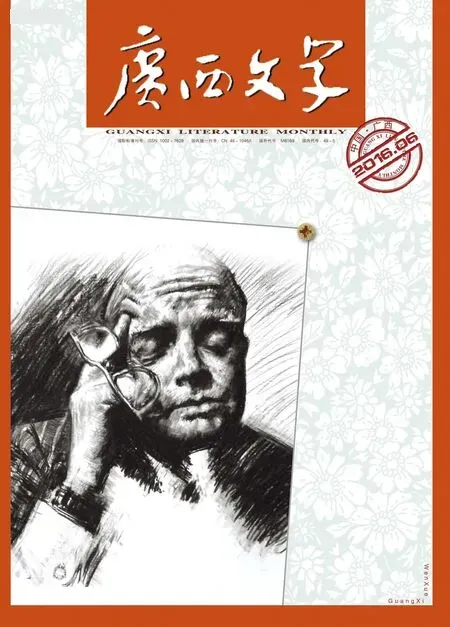黑老丘
短篇小说·王少龙/著
一
北街桥头橘色灯光映着河里悬浮的薄雾。
这一个寒冬的清晨即将来临。在这地处西部边陲名叫珍州的小镇,黑老丘摸索着起床,从挂在窝棚门破了的布洞探出头,借着橘色灯光往桥头瞅了瞅。
每一个清晨黑老丘探出头时都会打个哈欠。
有时候,黑老丘这一瞅,就会瞅到叫他干活的吆喝声。这吆喝声成了黑老丘每一个清晨最殷实的希望。这份殷实真是鼓舞人心的干劲,黑老丘会沉闷地应一声——唉!然后赶到桥头追向吆喝的背影,算是接到了一天里的第一桩活。有时候,黑老丘瞅了又瞅,眯着厚重眼袋的双眼,寻不到桥上的吆喝声,便把头缩回棚里坐在床沿瞅着妻子起床。如果这时你路过桥头,只要能听到桥下那黑漆漆的棚里发出碗瓢相碰的清脆声,还夹杂妇女在竭力抑制的咳嗽,这是黑老丘的妻子瘸着一条腿,正忙着给黑老丘准备早饭,好让黑老丘吃了出门。
黑老丘出门所带的揽活工具是一个背篼。背篼负着黑老丘的每一个日子,瞧它已经破烂不堪。
与往常一样,黑老丘赶赴北大街。商铺门一个个就像还没有睡醒的眼眶,没精打采地看着行色匆匆的路人。黑老丘穿过石板街,来到南大街的农贸市场,目送菜商贩匆忙搬运菜,一袋又一袋,黑老丘祈祷能有一个商贩能看到他的存在。
终于有一个商贩扛着一袋菜偏着头向黑老丘搭讪,说,黑老丘!你的门开着啦,你家里有没有人看屋?
黑老丘以为是叫他干活,便向前跨了两步。等他听清楚才停下脚步,说,有……我……媳妇在家呀。
那人喘着气,继续赶路,说,你的门真的开着呢,啊哈哈,小偷可多呢!
黑老丘跟上去说,哪会?我媳妇……她不走哪里,再说……没……没啥怕偷的。
那人停下转身看着黑老丘,哈哈笑,说,你看你,门真的大大地开着呢,看丢啥东西没有!
黑老丘低下头,看到自己的裤门敞开着,连忙把裤门捂上。黑老丘这才反应过来。黑老丘的脸这时也许真的成猪肝色了,可看不清黑老丘那黑黑的脸上有没有泛起一丝臊意,依然如故的黑,别的菜商贩抢着哈哈笑。
黑老丘的裤门根本就合不拢,纽扣老些天就没了。黑老丘在这阵笑声中只好把衣角使劲往裤裆拽了拽,离开了菜市,来到东大街。
这时成群在东大街上学的孩子看到黑老丘,打开嗓门儿起哄:黑老丘,背背篼,背篼烂,去要饭……
黑老丘瞪着这些孩子,涨红了眼球。到底该说什么,他没主张。
孩子们不敢对视这双涨红的眼球,突然畏惧了,一哄而散。实际上,这些小孩子更大的畏惧不是黑老丘本人,而是怕邻里说你长得真像黑老丘!
这句话会伤这些小孩子心的。这些小孩子知道,黑老丘这人与黑老丘这个名字,谁更可怕。
每一天,从珍州的北大街到南大街,再从南大街漫无目的走向东大街、西大街,黑老丘会默默往复多次。有时在某一次,会碰上一两桩活。今天的某一次是一个妇女吆喝着给他的。这妇女胖得像北街教场坝又圆又鼓的石凳。
妇女在街头拐角处叉着腿,大叫,黑老丘!过来。
黑老丘加快了脚步,小跑着去应答,我……来了。
妇女丢下一句话——背煤!扭着身躯走了。
黑老丘追着这句话,一丝不情愿匆匆替换了他脸上那份欣喜。但他依然尾随而去,追着这女人高跟鞋发出的乱了节奏的橐橐声,紧扭不放。
这是一个寡妇,黑老丘常常被她呼去干活。胖寡妇活多钱多,可每次干完活总会把黑老丘数落一通,责怪没有干好。每当这时,黑老丘也只能低着头不说话,觉得他是在虚心接受意见。
黑老丘一直没学会怎么争论,每次干完活,都没有讨价还价。这些挑剔的人都习惯了赚黑老丘的力气不说谢,且要送一句话给黑老丘,说下次不要你干了,说找别人可比你干得好!
但他们都知道,这珍州只有一个黑老丘。黑老丘似乎并没有意识到。
不过,胖寡妇的杂活,黑老丘还真有点不情愿干。这个胖寡妇不爱给工钱,黑老丘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脏话骂她。
可面对胖寡妇那硕大的一堆煤渣,黑老丘一下子忘记了自己的不情愿,抄起家伙就开工。煤尘滚滚,把胖寡妇逼着倒退了好几步。胖寡妇站稳,嘴里直叫,黑老丘,狗日背时黑老丘,轻点!给老娘轻点!
黑老丘这张脸不在乎煤尘扑打,这扑打仅仅是让黑脸更黑一点而已。他瞄了一眼胖寡妇,似笑非笑地埋下头,没有停下手中的家伙。
这胖寡妇远远地站在边上,看黑老丘一背一背把煤背到坎上的屋里。黑老丘那乱发根里渗出来的墨汁状的汗淌过脸庞,湿在衣襟。胖寡妇这样看着,没人读懂她心里到底在想啥。
也许,她啥想法也不会有,唯一有的可能还是一句话,还是怪黑老丘没有干好活。
在冬天,煤炭会送给人们温暖,可这把煤炭运进家门的黑老丘,谁也没有在意他会给这城镇的市民送来什么。
黑老丘没来得及洗洗那双和那煤炭一样黑的手,从胖寡妇手里接过钱,已经是黄昏上灯时分。这一次胖寡妇没有数落没有埋怨黑老丘,在没啥表情下给足了工钱。黑老丘也没有惦记她那数落的习惯,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沉默不语,提着背篼走了。
走着走着,黑老丘想起胖寡妇先前还欠自己清理垃圾的钱呢。黑老丘停下赶路,掏出钱仔细数了一遍,对!这只是这次背煤炭的工钱,黑老丘有点懊悔——刚才咋不一并收了呢?
黑老丘转念想,下次吧,下次一定要把这钱收了。
黑老丘回到北街桥下,女人已经煮了饭等他回来。
黑老丘女人借着拐起身,艰难地用一条独腿把持身体的平衡,为黑老丘张罗简单的晚饭。
累了一天的黑老丘,也许这时感到的的确是幸福。
或许是清闲。
二
可黑老丘这人怕清闲。
今天下雨了,黑老丘真应该清闲一天了,可他还是背上他的背篼,和往常一样出了门。其实人们没有留意这个道理,雨天的活可比晴天多着呢。黑老丘刚出门,就有人撑着伞迎上桥头来吆喝他。如果要对黑老丘说啥是幸福,有人吆喝他去干活,这才是黑老丘真正的幸福。
曾有人打趣问黑老丘——黑老丘,你图啥?一天只知道干活,图的是个啥?
黑老丘从没有回答过这个问题。也许他根本就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到底图啥?没人钻进黑老丘的脑袋想这事。就像春天的花儿绽放,图啥?就像北大街桥下清清的河水流向城外,图啥?就像人们对黑老丘一个劲地打趣取笑,图啥?就像旭日从清晨匆匆奔向黄昏,图啥?
也许,真没有图啥,在这地处西部边陲的珍州。
黑老丘没图啥,因为老实。老实又图个啥?也没图啥,只是本分。
怕清闲,图啥?没有图啥,这是黑老丘的生活习惯。
黑老丘的生活注定着他是一个勤快的劳动人。是呀,劳动人应该有自己劳动的岗位,农民的岗位在土地,工人的岗位在工厂,公务员的岗位在办公室,可黑老丘什么也没有,哪怕是一分地,他没有。在这个城镇里,他的岗位就在东南西北四条大街。四条大街每家的活都留有一份给他来干。但这个城镇的人们习惯了忽略,把黑老丘从自家的生活里忽略掉了。就算没有忽略的,会堂而皇之把黑老丘当作取笑的一份乐趣,仅此而已。
今天下雨了。
可人们是否还记得昨天的旱情?这旱情从夏天就开始了,干涸了整个秋天。其实,黑老丘和人们一样,是从旱情里熬到了这场雨里的。
几个月没有下雨了,图啥呀?今天下雨了,又图啥?
都知道,这啥也不图,是老天爷自个高兴!
走在这细柔的冬雨里,街上的人,只有黑老丘一人没有撑伞。这样一个地道的老实人,有人会认为黑老丘是在以这样别致的方式庆贺雨的降临呢。
其实是黑老丘舍不得买一把雨伞。
黑老丘走在湿湿的石板街上,脸埋得很低。还是这双破鞋,破鞋上方摇曳着的还是这身穿了一个秋天的衣服,这破衣服的领子上还是这头乱发,乱发下还是这张黑黑的脸。一个穿得时髦的苗条少妇打着伞走过黑老丘的身旁,她那珠光宝气的神采好像受到了某种侵蚀,她用手不停地扇她紧皱的鼻子,从黑老丘旁边逃了过去。
可没有逃多远,她转过身来,让伞低垂在地上,扭着脑袋抛过来一句话——黑老丘,背东西!
黑老丘也许知道自己身上的味道,远远地停下脚步,应了一声——嗯!然后远远地跟着这时髦的少妇。
这时黑老丘的脸埋得更低,因为这少妇滚圆的屁股左右摆动着在前面领路,真让人不好意思紧盯着不放。所以黑老丘埋着头,把视线系在这妇女的高跟鞋子上。这高跟鞋发出清脆的声音荡过大街,把雨丝抽得更稠密。一双双藏在伞下的眼睛,被这有节奏的清脆声拉出来。而这些眼睛刚看到这左右晃得厉害的屁股,然后看到低着头跟在其后的黑老丘,都觉得这场面有点滑稽。于是有人从细雨丝深处大笑,说,狗日黑老丘你想吃豆腐呀!
黑老丘也许感到委屈,因此他的头埋得更加低了,脚步放得更加慢了。
少妇让黑老丘在家门外站着。过了好一会,才拖着编织袋气喘吁吁地走到门口,说,把这个帮我丢了,这多少钱?
黑老丘没有答话。
妇女又说,这!钱,丢下一张零票,转身摔上门。
黑老丘捡起零票,用嘴吹了吹,放进口袋再用手轻轻拍了拍口袋,弯腰去整理地上的编织袋。他看到这袋子里不是别的,是一袋子腊肉呢。他有些纳闷。他取出一块,看到肉上爬满了霉霜。他用手在上面抹了抹,一丝微笑在黑黑的脸上泛了一下。微笑消失的时候,把袋子塞进背篼。
他一口气把编织袋背到了桥下的家里。
只听到黑老丘女人拉长了声音——黑老丘,哪个叫你偷别人的肉呀?你这背时的!
黑老丘涨红了眼,半晌才摊出一句,给的。
给?屋里一阵静默。
黑老丘女人从编织袋里把一块块的腊肉取出来,反复瞄了瞄,但她相信自己的男人是不会偷别人东西的。她把黑老丘的背篼清理好,让黑老丘又背着背篼出了门。
雨似乎停了会。
三
接连几天一直抽着小雨。抽着抽着,珍州的冬天就深了。
黑老丘白天在街上揽活,晚上没有睡在窝棚里。他在哪?他在帮别人家守灵。
这家的男人死了。用道士先生的话说,真是死得不是时候,一连七天都没有葬期。于是,这家人只能耐心地等待这个葬期的到来。
要命的遥遥的葬期迟迟不来,这设在单位大楼下的灵堂显得非常冷清。晚上只有黑老丘一个人守着一堆火苗,专注地守着空荡荡的灵堂。
对于守灵,黑老丘不知道这样守过多少次了。遇上天冷的时候,丧家会给黑老丘生一堆火才离开,天炎热的时候会给黑老丘准备一台风扇。其实那风扇大多时间是吹着灵柩。黑老丘守灵堂,是城镇的一个习惯,也是黑老丘生活的一部分。无论哪家死了人,不管有没有吆喝他去,晚上人们散去后的差事总会由黑老丘接管。黑老丘一到来,孝男孝女们就轻松多了,他们可以睡的睡觉,玩的尽情玩去,没有丝毫顾虑。
有时,孝男孝女不会离开灵堂,他们在灵堂边角摆上麻将桌,搓得麻将哗哗响。这时,黑老丘就远远站在一边看,看这些人自摸,看这些人放炮和牌,看这些人数票子出去收票子进口袋,看这些人手气不好的直往洗手间跑等,看这些人骂牌、骂运气、骂娘骂祖先。
这个时候,手气好的人把脸一转看到了黑老丘,得意地说,黑老丘你来搓两把?
黑老丘听了后退了两步。
这人又说,来嘛,我拿钱你搓搓……来!
黑老丘抖了抖嘴唇,转身不看了,人们也就不涮他了。
还有手气不好的,他们骂够了娘,就转过头来骂黑老丘。骂黑老丘真是你妈的黑煤粑。骂黑老丘滚远一点。
手气好的叫黑老丘,黑老丘无任何表情。手气差的人骂黑老丘,黑老丘会暗自偷笑一阵。或许,黑老丘这时的笑是一种幸灾乐祸。这是对骂黑老丘的人最大的报复。
这一次守灵,没有谁叫他搓两把,也没有谁骂他,因为只有他一人独守在灵堂。
孝男孝女在走的时候已经交接清楚电视机与影碟机的事。黑老丘盯着电视,再看看这影碟机,在这地处边陲的小镇,他心里感到满足。
可这影碟机不一会就停止工作了。这是碟片扫描完了,黑老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只会接受满屏幕的雪花和唰唰声。这给灵堂增添了不少阴森的气氛。
可黑老丘不怕这气氛。
这与真有没有鬼怪无关,黑老丘就是不怕。或许是因为黑老丘习惯了这种阴森森的场合。
其实,这时的电视对于黑老丘也没有多大的意义,这时黑老丘感兴趣的是睡上一觉。白天黑老丘帮城南的王胖子家搬运砖头,所有的砖头可以盖好王胖子家的三个大房间,真太劳累。所以这时,只有睡觉才是黑老丘最感兴趣的。
但黑老丘不能睡。这他知道。
可眼皮直往下掉,怎么办?黑老丘到灵堂外的食灶旁边瞎转悠了好一阵,抓了一把盐,往自己的头上搓。这手法就像搓麻将一样。于是,黑老丘的头发根上淀了白白的一层盐。
黑老丘以为这样可以提神,可最终黑老丘还是恍惚睡着了。
黑老丘的鼾声像雷鸣在灵堂回旋,一直旋到天亮,旋到孝男孝女来了,之后咒骂像暴雨一样到来,黑老丘才从板凳上弹起来。
孝子责备:黑老丘你干啥?不专心守灵,你来干什么?死人不会放过你的!你看你,只知道睡觉,油灯都熄了!你知道这灯熄了会咋样?熄了灵魂就找不到升天的路了,升不了天就永远待在人间!你负责呀?你负责得起吗?真是蠢猪一个!
孝子埋怨:我爹升不了天你负责!你知道香火断的后果是什么吗?你妈的不来就算了,来了就是这样守灵的?
这一骂,骂得黑老丘的瞌睡烟消云散了。黑老丘一脸真诚地自责。
接下来的夜里,黑老丘知道用盐不管用,就用扯头发来熬了一夜。直到出殡的清晨,黑老丘没敢在灵柩前打过瞌睡。黑老丘意识到,守灵打瞌睡真是不恭。
当黑老丘扛着出殡的大幡走在街上时,黑老丘在暗自决定,这次出殡后,下次不守了。谁知,黑老丘扛着的大幡触到了空中的电线,一团火花比出殡放了的烟花还亮丽。在黑老丘倒下直到瑟缩着从地上爬起来,所有孝子和抬丧的人的嘴巴一直张着没有合拢。
黑老丘就是黑老丘,电触了一下,爬起来还能扛着大幡在出殡队前开路。
黑老丘知道自己的使命,自己是什么人?自己这时候是领队的,任务可重了,后面这一长串的队伍,哭哭吹吹打打,全是自己带队前进呢。如果自己不起来,在珍州,这队伍就没有人带了。这时自己怎么能倒下呢?
但黑老丘知道,自己的掌心已经鼓起脓包,这是被电击的。电是什么概念?这对现在的黑老丘来说,可能只知道电这玩意杀伤力不小。
出殡结束,黑老丘也没有盘算好自己是不是应该从此告别守灵。
四
这个小镇如果出生了一个小孩,也许没有人打听过问,如果死了人,消息会跑遍每一条石板街。今天这死了人的消息就在街上来回跑着。
谁家死人了?就是那次叫黑老丘背腊肉去丢的少妇家。谁死了?时髦少妇的老公死了。
这黑老丘也知道。
到了天黑没有人守灵,人们才想到了黑老丘。此时黑老丘正蹲在北街桥下的窝棚里端着女人刚烧好的饭。
去叫黑老丘的人是珍州小镇的老牌二混混。
黑老丘不看他,也不哼一声,只关心自己碗里的饭。
这二混混怒了,瞪着眼,说,黑老丘!你不跟老子去可以,从此后你不要在珍州混!看老子怎样收拾你!
黑老丘不吃这一套,依然默默地吃着自己的饭。
着慌的是黑老丘女人。黑老丘女人凭单腿立起身子,声声应答。直到黑老丘把碗底弄光亮,还是不响一声,满脸的混沌。后来黑老丘二话没说就跟二混混走了。
这小镇死了人还真离不开黑老丘,不然这少妇家就不会去请他了。
其实黑老丘不怕二混混的狠话。黑老丘最明白,碗里那点肉味从哪里来的他最明白。
黑老丘跟往常一样,到了灵堂,首先来到灵堂遗体前,双手捧着三炷香举过头,作了三个揖,差事由此开始。
灵堂的人影按时散了。
这一夜黑老丘没有合眼,坐在灵堂旁边,眼睛盯着香火慢慢地化成灰烬。每次在香快灭时黑老丘就及时更换。尽管黑老丘内心深处是多么地厌倦守灵这活,但黑老丘知道,自己现在还是一个守灵的人。这是黑老丘的本分,也是大家放心让黑老丘守灵的原因。
第二天,黑老丘没有去上街揽活,依然守在这灵堂。
白天,黑老丘在灵堂真显得多余。
白天进出这灵堂的人们都是穿戴比较整洁的,黑老丘一身的脏衣服,反而有损灵堂的庄严肃穆。所以过去黑老丘守灵,白天就离开灵堂,免得有损灵堂的庄严与肃穆。可今天黑老丘没有离去,还像丧子的老人一样在灵堂里低着头一个劲的沮丧呢。
到这少妇家来吊唁的亲戚中有很多人不认识黑老丘,进了灵堂先看见黑老丘这穷酸样,并不知道是咋回事。有的就上前对黑老丘说——儿子走了……您节哀……
这话让唱着诵经的道士先生差点唱走调子。年轻的道士就忍不住偷笑。
黑老丘不应一声,好像接受了这句宽慰人心的话。
黑老丘以一脸的木讷来打发了这几个日日夜夜。
黑老丘没有离开半步,一直到出殡。
在出殡的这天,黑老丘依然扛着大幡,走在送葬队的最前列。
这时黑老丘那一脸的木讷显得庄重严肃。其实黑老丘的内心也是木讷的。这木讷的因素太多太多,道不明白。
黑老丘身后是灵柩。
灵柩在阵阵飞舞着的黄烟里浮动,在抬灵柩人的“起!起!起!”号声中缓缓前移,在男男女女的哀哭中拥向墓地。这种仪式很凄凉。在这样凄凉的仪式里,黑老丘想,灵守完了,也出殡了,也算从心里还了这少妇的一份情。但不能说还清,黑老丘想,要是哪天这少妇需要干丢垃圾搬运煤炭的事,绝不收一分一文。
这样想着,木讷的黑老丘心里倒有几分释然。
算了算,这守了几天灵,黑老丘就有好几天没有回家了。
黑老丘带着木讷的表情回到棚里,看到女人躺在床上,着实让黑老丘惊了一身汗。
黑老丘满脸的木讷瞬间消去,一下挂上的是黑黑的焦急。黑老丘瑟缩着手摸了摸女人这张白纸一样的脸,还有点热温,这才缓了缓他那直往脑门冲的热血。
黑老丘的女人病了。
女人在黑老丘这瑟缩的手掌下,一阵咳嗽,咳得棚顶痉挛,咳得桥下河水静止了抽动。
黑老丘慌忙去河里舀了水,边生火熬姜开水边对着柴火诅咒——还妈的……鸟人情!差点把女人……还到阴间去了!下次死个舅……老子也不去守灵了!老子再也不去了!狗日的……就算拿再多的钱,老子……也不去!
这次,黑老丘痛下决心。
五
黑老丘这几天都没有敢离开窝棚。
对于那些在桥头吆喝黑老丘的声音,黑老丘刻意不去理会。
这些来找黑老丘做事的叫不应黑老丘,又见黑老丘的棚门没有动静,就有了种种猜测。今天,这桥头不一会就聚集了好几个来找黑老丘的人。有人说,街上找不着他,这棚里也没有动静……有人说,怕不会是黑老丘这两口子走了。
议论下,有人顺着石级走下去,掀开了黑老丘的棚门布。只见黑老丘坐在床沿,黑老丘女人躺在床上,在昏暗的棚里脸色更煞白得刺眼。
这人定格了掀开棚门的手,质问,黑老丘!大伙在叫你呢,咋不应?
黑老丘没有吱声。
过了好一会,黑老丘女人才摸索着立起身子,说,去吧!我不大紧……
当黑老丘跟着这人走过西街,黑老丘傻眼了。这哪是西街?街上全是废弃物,昔日的楼房变成了一片废墟。两旁的房屋仅留下一地的碎瓦和几根东倒西歪的柱子。这些柱子就像森林发生火灾后的木桩一样,根根擎天。
这才几天没有出门,这个小镇拉开了旧城改造的帷幕。黑老丘不知道。
难怪去吆喝黑老丘的人特别多,人们是在忙着搬迁。黑老丘今天揽的所有活,全是帮人家搬家什。黑老丘一个人是搬不动大家伙的,于是,这些搬家的人,还请了别人,对于请黑老丘来,不过是打个下手。
这些搬家的人一下子多了。旧城改造就像一阵风,这些人是顺着这风来的。
黑老丘很想和这些搬家的伙计搭讪,但别人身上扛着沉重的活,没有工夫唠上一句话。
黑老丘干搬家的活一干就是三个月。白天搬完西家再搬东家,晚上回家照看女人。黑老丘女人时常三病两痛,十天半月就好了,这次也一样。
与以往不同,黑老丘的女人好之后,踮着一条腿,拄着棍子也去了废墟。黑老丘搬家卖力气,她去废墟是拾些破烂卖。似乎,这次蔓延来的城镇改造,另一个实惠就是黑老丘女人这样一个残疾人也出门忙个不停。
一天天,废墟在慢慢消失,废墟上拾废品的人在增多。黑老丘搬家也一样,搬一家少一家,一天天多起来的是街头闲着的搬家人。这些闲人比黑老丘年轻多了,且力气很大。黑老丘只能站在一旁,眼巴巴看着越来越少的雇主叫走的是身旁的力大气壮的伙计。
这些力大气壮的伙计从哪里来?黑老丘一直纳闷着呢。
这些是四川人。
以前只有黑老丘,大伙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个干苦力的黑老丘。而今,面对这些四川人组成的庞大的劳动队伍,不知应该呼啥好,于是,叫不出名,索性叫这些人为川军。这些川军干活可卖力嘞。
旧城彻底地换成了新城,他们的汗滴洒满了这片土地。
崭新的每一天,街上游荡着的川军,只要听到哪里一声吆喝,川军就蜂拥而上,把吆喝的雇主围得喘不过气来。川军随处可叫,人们也不再走很远的路去北街大桥下吆喝黑老丘了。
黑老丘夫妇的饭碗被掩埋在了旧城里。白天或者黑夜,黑老丘的生活更加寂静。已经暗示黑老丘不能在窝棚里瞅着等待那一声动人的吆喝了,只能到街上寻觅。有时候,真就从街的那一端飘来一丝吆喝声,川军闻风而去,黑老丘年迈的身躯也被卷在这风里。然后雇主会说,我叫的是川军,没叫你黑老丘呢!
黑老丘总是急,说,我也是四川……过来的!
雇主只带走少许川军,留下一大群。他们放下背篼,怒目瞪着黑老丘,咒骂道,你也配是四川来的?狗日杂皮黑老丘,你敢充我们四川人!老子洗白你!
黑老丘慌了神,说,我……真是……四川来的……川军!我们……是老乡呢,真是的……
还说!你再说你是川军,老子真洗白你!
黑老丘说,我真是川军,我……在四川……当过兵。说着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本,接着说,这……这是我……当年的证!
有川军在嘲笑,说,狗日杂皮黑老丘,牛皮客一个!你当过兵,老子还当过司令呢!
个别川军凑上前去想看个究竟。可这时黑老丘的手比说话利索,那双枯藤似的手一下子把小本子捂个严实。
你当过兵?川军里没谁相信黑老丘说的瞎话。川军里有人出了一个馊点子,指着广场上尹珍像问黑老丘,说,你知道那三个字念什么不?
黑老丘瞟了一眼,说,尹珍像!
那你知道尹珍是哪个不?
黑老丘这时显现出的是不骄不躁,捂了捂自己的口袋,说,一代汉儒!
这时,一群小学生路过广场,其中有一个学生说,看……黑老丘!哦——黑老丘,背背篼!背篼烂!去要饭……
这群川军跟着小学生起哄。
黑老丘眼涨得通红,背着背篼走了。
六
珍州这个小小的城镇,川军多过了需要帮忙的雇主。
川军个个身强力壮,黑老丘似乎没有输给对手,但真输给了岁月,就和女人一起拾荒去了。
黑老丘在废品里挑出来钢轴弹子帮女人钉到背篼底上,这样,女人每天出门不会因为背不动背篼而着慌了。日子总算平静了些。
可生活就是这样,你不能阻止任何一个人赶热闹。城里又来了一大批拾破烂的大人小孩。每天黑老丘出门得够早了,可还是会扑在别人之后,这又成了黑老丘生存的烦恼。
黑老丘现在有很多的时间默默守着女人。这天他们都没有出门,看着女人那带有滚轴弹子的背篼,突然想到了独轮鸡公车。可这独轮的车不好推。黑老丘许是真被生活逼开窍了,竟然想到了把这独轮鸡公车改成双轮车。如果这样推着,就可以驮些大家伙了,还能驮得更多。他合计合计,果真买了一副大轮子,把鸡公车加工成了板车。
这板车,预示着黑老丘又开始了一次新生活。
这天,女人跟在拖着板车的黑老丘的身后,走在这个欣欣向荣的城镇的大街上,正遇上米粮店搬家,老板正和川军讨价还价。老板看见黑老丘推着板车来了,心想,满屋子的米粮如果用黑老丘推的板车驮可能运得更快。
黑老丘从屋子里搬出来几袋大米,全放在板车上,然后弓着身,向街的那一头迈步而去。留下川军们目瞪口呆的神色。
黑老丘生平第一次有了乐趣。当年抢他饭碗的是川军,现在他又从川军手里把饭碗抢回来了,这让黑老丘的确高兴。女人单着腿拄着棍一跳一跳地跟在黑老丘的板车后。路过这条大街,留下的是这些川军的懊恼,这的确是黑老丘的乐趣。
黑老丘又开始每天清晨从窝棚里探出头来看看空中的启明星,再瞅瞅北大街桥头。这时,又有人在桥头吆喝黑老丘。女人的身体也硬朗了许多,早早地起来,为黑老丘准备早点,好让黑老丘吃饱点。
以前,黑老丘背着背篼走过的是石板街,现在拉着板车走过的可是混凝土铺成的大街。这样的日子有盼头。黑老丘在心里盘算。
现在黑老丘不再背着背篼在街上瞎转悠,每天只要把板车拉到广场边上,自己坐在板车上等一会,就会有活来找黑老丘了。需要用板车拉东西的,自己会到广场这里来叫。有时,黑老丘拉板车出去了,这些来找黑老丘的也会在广场旁边等黑老丘。
对于黑老丘,这是生活的另一种滋味。
这天黄昏,黑老丘拉着板车回他的北街桥下,路边一群人围着看热闹。
黑老丘停下板车,从人群缝里往里一瞧,大家正围着一个发了急病的老人议论纷纷。这老人是当年那个可恶的老牌二混混的老妈。黑老丘啥也没有想,拨开人群,吆喝着把二混混的妈妈弄上板车,直往医院奔去。闻讯赶来的二混子追上了黑老丘的板车,扶着车把,和黑老丘一起直奔医院。
黑老丘今天的做法真好,可运气不好,二混混的妈妈咽气了,在他的板车上。
黑老丘头一直深埋着,或许因为跑慢了而懊恼。好些时日没有守过灵了,黑老丘想以守灵来减轻心里的那份懊恼。不一会,有一大群川军来到了二混混的家门口,顿时热闹起来。
黑老丘扶起板车,默默地离开了。
黑老丘不知道,他走后,川军们在为守灵费讨价还价。
黑老丘远远落后于讨价还价的生活了,黑老丘只想拉好自己这快乐的板车。
七
今天清晨,桥上又有人来吆喝黑老丘。黑老丘从石级上到桥头时,才发现板车不见了。
桥下闻声而来的女人脸煞白。
吃饭的行头不见了,而那雇主一脸的幸灾乐祸,一阵干笑走了人。黑老丘狂奔找遍珍州的大街小巷,也没有找到他的板车。
好些天了,都没有板车的一点音讯,黑老丘夫妻俩在桥下的窝棚里坐对冷冷的四壁。
这天,一个好心的人来说,西街那里有一辆板车。
待黑老丘夫妇火急赶去,只见被砸成几大块的板车,轮子破一边,不忍直视。
黑老丘夫妇拖着板车的残肢碎体走过大街,才发觉满街都是板车。转眼之间,就像当年川军一样,冒出了阵容庞大的板车队。本来黑老丘打算马上去新买一辆,可这么多板车,买来又能怎样呢?
实际上,这几天,没有黑老丘的板车,居民们还是生活得非常幸福。那些需要雇板车的人,也不会因为黑老丘的车被偷了就得等黑老丘买来了再雇。生活的空缺总会被及时填补。
这就是生活。也许应该说,这就是生活的节奏。这个小小的县城,生活节奏之快就像匆匆的四季更迭。
黑老丘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黑老丘没有再去买板车。尽管女人一再说,生活就得靠板车撑着,必须买一辆,可黑老丘不想买。黑老丘没有向女人说太多的理由,以致一直很温柔的女人,这次对黑老丘怄气。
说实话,黑老丘唯一舒心的地方只有这个窝棚了。可现在这个窝棚里唯一能给自己温馨的人正在和自己怄气,黑老丘的脸更加地黑。
黑老丘以为第二天女人会消消气,可第二天到来,看女人那脸色,黑老丘只能又把希望寄托在第三天。可第三天女人还是没有和黑老丘说话,黑老丘又只能把和女人和好的希望寄托于下一天。
这样已经持续好多天了,无休止地耗着,耗着耗着新年就来了。
黑老丘起床了就烧洗脸水,黑老丘饿了就煮饭,黑老丘碗里的饭快刨光了接过碗加饭,总不哼一声。今天黑老丘刨着饭,心里有些急,可那黑黑的脸上,只是微微扭动了一下了黑黑的脸皮,依然没有发出一点声响。
他要是发出声响他就不是黑老丘了!女人在心底这样怨着黑老丘。黑老丘女人收拾好一切,自己背上背篼拄着棍出门去了。
在黑老丘的眼里,这一个新年没有什么不同于往年。
每一个新年到来之际,黑老丘都会在某一天待在棚里唱着一个川戏曲的台词,只唱一遍:人人有年我无年,提起猪头要现钱……
不同的是以往有女人听黑老丘这样唱,今天女人背着背篼上街去了没有人听了。黑老丘因此唱得更凄凉。今天黑老丘反复地唱着:人人有年我无年,提起猪头要现钱……
声泪俱下。
许是黑老丘女人在桥头就听到黑老丘的唱腔了,进窝棚时眼里含着泪水。
黑老丘女人立好棍子,用拄棍的手悄悄抹了一把泪,才把背上的背篼自个放下来。黑老丘也抹了一把泪,起身搀扶住单脚站立的女人,顿时,两行热泪滴答落在背篼里。
黑老丘扶着女人坐下,然后从背篼里拣出一小捆苕粉、一沓火纸、一把香烛、一块新鲜的豆腐、一捆小菜,另外就是一块肉,还有一双黑老丘穿的胶鞋。
这就是黑老丘家今年的年货了。
这么些天,黑老丘终于响了句,说,明天……二十八了,明天……我们……就去买一辆,二十九再勤勤地拉一天车,大年三十我们……再……添点年货过年,啊?
女人点头。
黑老丘女人弯腰从床板下取出所有的零票清点,黑老丘木讷地看着眼前这女人。
八
腊月二十八,准备过新年的人们把北大桥弄忙碌。
黑老丘夫妇俩被这忙碌的脚步声早早地揪起来。
早早地把黑老丘揪出窝棚来的,是一个在桥头上吆喝黑老丘的声音。这人对黑老丘的车被盗一事竟然不知道。由于黑老丘女人在窝棚里回应在桥头上听不清,黑老丘只能钻到窝棚外回了句——不拉,没车!
天还没有亮呢。
黑老丘钻进棚里一会,又有声音在桥头吆喝——黑老丘!黑老丘!
黑老丘不打算理,可这吆喝越来越急,黑老丘又得钻到窝棚外,大吼,不成!没有车!
有车有车!那人扶在桥栏上弯着身子探着头向黑老丘窝棚的方向俯身说,有车,你给多少钱?
这不是一个叫拉车的,是一个卖车的。
黑老丘摸不着头脑,说,我……我给多少钱?我告诉……我没有板车,真拉不了!
那人听明白黑老丘的话了,说,我这里有车,要卖,你给多少钱?
天没有亮,卖板车的上门来了。黑老丘身后跟着女人,上到了桥头。
价钱很便宜的,划算。黑老丘女人悄悄对黑老丘这样说。
黑老丘默默转身,下桥进棚里去拿钱。
黑老丘女人看着黑老丘回到桥下。忽地,她也扭身跟了下去,对数着钱的黑老丘说,这车不能买,哪晓得是不是偷来的!再说,要买就买新的,不要旧车!
黑老丘顿了顿,把手中的钱放回到床板下。
不一会,先后来了好几个要卖板车给黑老丘。黑老丘女人做的主,不买。
黑老丘女人说,这板车真不能买了。说,有一个卖自己板车的人这不出奇,如果有多个这样急着出售自己的板车就怪了。看来新板车我们也不能买了。
黑老丘点了点头,还是没有说话。
没有买板车,黑老丘没再添买年货。在城镇里别人的鞭炮声中,夫妇俩蹲在河边点上烛火烧了纸钱和香,然后回到窝棚里和女人默默吃着他们的年夜饭。
除夕夜在年夜饭结束的时候到来。烟花真美,映照着这个小城的每个角落。就连黑老丘这北大桥下的破棚旮旯,都沾到了烟花的七彩的色光。黑老丘沉默,黑老丘女人也沉默,他们在屋子里点着这盏只有过年过节才能点的油灯。昏暗的灯光映着这个棚里床上的破棉絮,映着简陋的餐具,映着空空的四壁,映着棚顶积满灰尘的破蜘蛛网,映着黑老丘夫妇俩苍老的面容,映着棚子里散发出来的霉味。
大年初一的到来并没有减少这棚里的霉味。
大年初一黑老丘又照了整整一宿的油灯。大年初二黑老丘女人又把油灯收藏到了床下的纸箱里。也许,要等到来年的除夕,这油灯才会再次点亮。也许油灯已经习惯了这种散发着霉味的阴暗的气息。
春节很快过去了。
黑老丘夫妇在这个窝棚子里如此打发了又一个春节。春节过后,春的气息也近了,黑老丘夫妇也习惯到棚外走走。其实,如果黑老丘的板车还在,黑老丘在新年里早就忙碌了。现在只好搀扶着女人到棚外瞧瞧,在大街上逛逛。但这远远不能消磨去一个习惯了劳动的人的时光。
黑老丘夫妇走过大街,看到那些遗留下来的川军,捂着春天的时光坐在自己的背篼上打盹。那些静静停靠在街边排着整齐队伍的板车,构成了一幅茫然落魄的图画。走过街的尽头,黑老丘是多么留恋这幅画里的板车。他忽然觉得,这些静静靠在那里的板车,它们就像自己一样成了失业的伙计。它们的两根手把,就像是伸给黑老丘似的。
九
能做什么呢?在这地处西部边陲的珍州。
这真成了黑老丘一个揪心的问题。
居民的心态已经跟随城镇旧城改造而改变。商家们不断变换花样来迎合着。
这不,南大街日杂货店改成了人力车行。店里专卖一种新玩意,前身像自行车,后身是两个轮子上加了一个有坐垫的车篷,这叫作人力车。可比旧上海那一伙人坐的人力车强多了。很多有钱的公子少爷都去瞧过了,很想买一辆回家玩玩。但这车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必须有人在前面踩,这车才能动。这些公子少爷生来就只能坐车哪能踩车?这车没有人拉肯定不行,总不能自己坐着拉自己。于是,这家卖人力车的门前看热闹的多,没有谁安心买一辆。
其实卖人力车的老板,他的初衷不是把车卖给这些有钱的公子哥儿,这些车的主人应该不是坐车的人。这个地方,街道上从没有出现过这玩意,有人真想买来经营经营这载人的事,可这些人都怕,怕啥?就是怕巴掌大的城镇,没有谁愿意出钱坐你的人力车消遣!
黑老丘打定主意,是接连瞅了好些日子。要是没有谁坐,那就让自己那苦命的女人来坐,没有客人拉那就拉自己的女人。黑老丘是这样想的。
黑老丘的人力车拉的第一个客真的就是他的女人,在城里风光地逛了一圈。大伙见到黑老丘拉着这玩意,都说,狗日黑老丘疯子!饭都吃不饱的人还有心思玩这个!真他妈的疯子一个!于是街上又有一则关于黑老丘的顺口溜——黑老丘的头发鬈鬈,买个车子屁股不冒烟烟,没谁来坐就拉着女人转圈圈……
接连几天,黑老丘始终没有拉到一个客人。这些人愿意跟在黑老丘的车后大骂大叫着制造热闹,没有谁愿意去坐坐试试。
这个商贩也是,最大的错就是把第一辆车出售给黑老丘。出售东西给别人,也是让别人给自己免费打广告呢。黑老丘何人?是这个城镇的名人,是这个城镇里人人皆知的穷人。穷就是晦气,谁愿意坐黑老丘的车?坐黑老丘的车这不是去惹晦气吗?所以,这人力车行的老板出售车给黑老丘,也是惹上了晦气!晦气惹上了,车行老板也许只能挨着日子等着车行关闭了。
任大家怎样取笑,黑老丘每天依然踩着车闲逛在街上,用手拽着系在前轮旁边那敲击铃子发出当当的声响的绳子。人们老远就知道,狗日黑老丘来了。
其实留意观察,还是有人想坐坐这人力车。只是,这些想坐着试试的人,他们看重的可是踩车的人。这踩车的人就是司机,黑老丘哪能当别人的司机!所以人们盼望着有一天踩这车的人不是黑老丘。如果永远是黑老丘,这些人将永远不愿意尝试。
这一天,一个小孩哭着嚷着要坐黑老丘的车。拽着这小孩的手强制离开的是一个女人。这女人正是那胖寡妇。这个胖寡妇现在穿着一双比以往更高的高跟鞋。强拽着小孩离开时这高跟鞋紧急地磕着街面发出的依然是急促而混乱的声。这寡妇恶狠狠地对小孩说,小孩子不能坐这车,坐了这车,今后不能考大学了。
这小孩子嚷着说,不让我坐我就是不考大学!不坐就不考!
黑老丘调转头,向母子俩踩着车赶过去,心里想试着说一句客套近乎的话。这话早就在黑老丘的心里排练多次了——坐坐吧!我免费拉一圈,让我拉着试试车……
可黑老丘张不了嘴。
胖寡妇侧身看见撵上来的黑老丘,瞪了瞪眼,说,黑老丘!你想诱导老子的孩子学坏是不是?
坐……坐车这……哪是学坏呀……话还没有说完,黑老丘慌忙调转车逃去。
只听胖寡妇在后面直嚷——黑老丘!把车停下——停下!站住!
黑老丘心里琢磨,又没有说话冒犯你,不坐就不坐,何必这样凶呀?
一个小孩的声音在身后嘻嘻笑,说,黑老丘,踩快点,我给你钱!
黑老丘扭头,看到刚才那小孩坐在自己的车上正咯咯地笑。
黑老丘不知道应该继续踩还是停下。这可是黑老丘拉的第二个客人呢。不能让胖寡妇就这样把自己的第二个客人带走!可叫停下的是孩子的妈呀,黑老丘没踩出几米,还是把车停住了。
胖寡妇很生气,喘着大气撵上来,一把揪住孩子,凶神恶煞地把孩子从车上拽了下来。
这一拽用力过猛,孩子重重地摔在地上,耳朵边上鲜血直冒。胖寡妇傻了眼。
黑老丘在责备声中真慌了神,慌得发呆,傻傻的。
胖寡妇抱着孩子跨上车,直骂,狗日的黑老丘!还愣啥?快送老子去医院啦!
黑老丘真的愣住了。这一骂,黑老丘回了点神,边踩车心里边琢磨——去医院,我应该收她多少钱,以前那次我帮她倒垃圾的钱是不是这次我一并收了。
黑老丘真想回过头来对胖寡妇挑明钱的事。起码也要说个明白,免得到时乱了套又拿不到钱。
但黑老丘始终就是扭不转头来。直到把母子俩送到医院大门口。这母子下了车,黑老丘还在琢磨着这老账新账一起收应该收多少钱的事。可这背时的黑老丘,就是不敢正眼看这母子一眼,更不说向这寡妇说多少车费的话了。
胖寡妇抱着孩子跳下车,招呼都不打一个就被医院的大门吞掉了。
黑老丘靠着车子在医院门口等胖寡妇出来,等了半晌也不见胖寡妇的人影。胖寡妇欠我两次工钱了,下次一定一并收了。黑老丘这样想着踩着车走了。
十
除了拉自己的女人,黑老丘终于拉了第一桩生意,那就是拉胖寡妇母子俩。
只是这第一桩生意没有收到工钱。
要是拉的是别人就好了,别的人给钱也许比胖寡妇耿直呢,说不定还会多给点……
第二天黑老丘还是踩着空车在街上转悠着。
停车!
黑老丘慌忙抓住刹车把,看到一个老人伸直两手和身体组成“大”字拦在车前,这老人又吼了一声——停车!
黑老丘看着这老人面熟,开始还以为是胖寡妇呢。可这老人比胖寡妇老。这老人是胖寡妇的娘。胖寡妇的娘?黑老丘琢磨着她娘有啥事叫停车,样子倒像是抢劫。
黑老丘心有点虚,没有根据的虚。
狗日的黑老丘!你撞了老子的孙儿,老子不会放你的!你赔老子的孙儿,你赔老子!寡妇的娘边骂着边上前来抓黑老丘。
黑老丘这才意识到,自己昨天真闯祸了。
黑老丘急忙从车上下来不让她抓。
不过黑老丘心里坚定,昨天自己并没有撞胖寡妇的小孩,是寡妇自己拽倒的。可黑老丘这话就是急了也说不出来。任老人抓着,还让老人的另一只手不停地捶打。瞬时,人们围住了老人和黑老丘。这时的老人和黑老丘就像是耍猴的,人们围着一圈观看热闹。虽然人老气衰,可老人不停地捶打,也着实让黑老丘招架不了。黑老丘就往外窜,老人便在后揪着黑老丘的衣襟,黑老丘挣不脱。
这阵势有些糟糕,有人大呼快报警。
老人就这样揪着黑老丘不停地捶打。
后来警察没有来,胖寡妇来了。
黑老丘更怕胖寡妇来揪着他打,所以黑老丘弃车而逃。一口气跑到北街桥下,钻进棚不敢出来。黑老丘女人握着菜刀切菜,见黑老丘慌张的样儿,没有猜出个子丑寅卯,可猜出了黑老丘一定生事了。女人的菜刀停在手中,眼睛盯着黑老丘——车呢?黑老丘我们的车呢?你说话!
车在……在街上,胖……胖寡妇打我……我才跑回来的。黑老丘词不达意。
哪个叫你去惹寡妇?你这背时的老丘!
我撞寡妇……不是!我撞寡妇的儿子……不是!我没有撞寡妇的儿子,是寡妇拽倒了自己的儿子——昨晚我不是向你都说了,寡妇的娘就打我呀!黑老丘怕得脸色惨白,那种黑老丘才有的黑这时被这种惨白掩住了。
黑老丘女人明白了。
可黑老丘不明白自己怎么就逃了,为啥就这样逃回来。没有撞人,拉了人还没有收到工钱,咋要逃回来?这样就不明不白地成了撞人了,这是咋回事呢!
黑老丘还没有明白这事时,胖寡妇找上门来了。
完了,背时的黑老丘,这下祸事撵上门来了!
可这事并没有黑老丘心里那般复杂。黑老丘本来就不应该明白什么,因为黑老丘本来就没有撞人。
胖寡妇掀开棚子的破布帘,黑老丘在屋子时像一只怕光的老鼠,吓得往女人身后躲。原来,胖寡妇的儿子失血过多,到医院时已经休克了。要是晚到几分钟,后果可想而知。这时胖寡妇会做什么?
胖寡妇走了,黑老丘脸色恢复了原来的表情,只是显得更黑。
许久,黑老丘才想起胖寡妇真的还欠自己两次工钱。黑老丘想,刚才真应该问她要。
黑老丘被寡妇的娘捶打的事传遍了大街小巷。人们都在说——狗日的黑老丘,被捶得真惨,全身是血跑回了家,车都被砸坏了,现在躺在家里出不了门了……
可这时看到踩着车的黑老丘,人们才知道自己在睁着眼睛说瞎话。
这瞎话其实很好。人们又从瞎话背后了解到了真相,那就是黑老丘被捶是真,但被捶得不严重。人们说,狗日的黑老丘,免费送人,真是活雷锋了。黑老丘又这样当了一次活雷锋。但黑老丘听着人们谈论他免费送寡妇这事,哭笑不得。
可这哭笑不得之后,人们都想免费坐一坐黑老丘的车。可人们坐在车上,黑老丘在前面弓着身子喘着大气踩,人们怎忍心这样免费坐?后来,生活改变着一切,人们走在街上,真的需要人力车来爱护爱护自己为生活奔波劳累的双脚了。
似乎从这天起,人们接受了人力三轮车,生活接受了人力三轮车,这个城镇接受了人力三轮车。
黑老丘熬出头了。
拉人力三轮车这行当熬出来了。
黑老丘的出头,那人力三轮车行也跟着出头了。
这时,黑老丘依然默默记着,胖寡妇还欠着他工钱。
十一
铛铛响的车铃声,是奏响生活的变奏曲。
黑老丘在这个变奏曲里,充当的是啥角色?人们习惯了忽略。
可黑老丘并没有在意这是一种怎样的忽略,只要拉着车上坐着的客人,这就是一份幸福。黑老丘和所有人力三轮车夫一样,忙碌在城镇的各条街道。黑老丘每次看到自己的三轮车当当的铃声弄醒了那些坐在背篼上打盹的川军,心里顿生一分自豪,美滋滋的。看着那些在街旁排着队等待吆喝的板车,心里忽地泛起一阵辛酸,酸溜溜的。黑老丘对生活的感触里,已经浸湿了沧桑。沧桑也成了人生成熟的标志了。可黑老丘在言辞的表达上,并没有因为沧桑而流利。那张苍老的脸,反而更加地黑。
这种黑已经沉淀了人生的另一种深沉的苦难。
黑老丘真不容易。这是老年人默默送给黑老丘的一句话。
黑老丘人力车的轮子,就像年轮一样,向着未来美好的明天驰去。
黑老丘女人现在每天晚上都点油灯,在深夜里等着黑老丘从桥头走下来。黑老丘还是住在这北大街的桥下棚里。这当当响的人力三轮车的铃声,虽然奏响了这个城镇的公共交通变奏曲,可要奏响黑老丘的生活变奏曲,这真还得需要黑老丘的加倍卖力。
虽然黑老丘不再听别人坐在街边的小吃店里涮他吃东西的吆喝声。黑老丘时常会亲自坐在这里吆喝着对卖小吃的人说——再煮一份,打……包!
但是,黑老丘还是只能活在人们的口角边,随时都可能被这一口唾沫带走。
黑老丘所踩的车,有些不务正业的年轻人坐了,总是耍横不给钱。遇上这事,不给钱也不能强要来,只能低着头踩车离开,寄希望于下桩生意。这些不给钱的人可比当年的二混混还要凶。当年二混混只耍横,现在这些人还会揍人。
城镇改造先是改造了住房,然后改造街道,再后来就改造河道。一次改造比一次更加细致周密了。黑老丘窝棚前的这北街的河道也得到了改造。河道改好了真好,河水清澈了。城镇里的小孩最爱到这河里游泳了。可这些来游泳的小孩,在离开北桥河时,总会把一些石子往黑老丘的破棚上扔。
每当这时,黑老丘女人会带着惊恐的、无奈的、祈怜的目光目睹着这些石子击打在窝棚顶。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目光?而这些可爱的、天真的扔石子的孩子,总会把这种眼神当成是一种作乐的奖赏。
黑老丘还没有夜夜点油灯的时候,人们便夜夜照电灯了。黑老丘夜夜点油灯的时候,人们天天张灯结彩了。这就好像是孩子们玩的捉迷藏,专门为黑老丘这样的人设计的一种生活的迷藏。
这天,黑老丘的车上又坐着老顾客胖寡妇。这个寡妇其实已经不是寡妇,嫁给了社区管事的儿子。这个顾客叫其他拉车的叫三轮,叫黑老丘拉车还是叫黑老丘,说明这胖寡妇还没有忽略黑老丘这名字。可这个胖寡妇彻底忽略了自己真的还欠着黑老丘两次工钱。黑老丘的脸上并没有浮现出自己还没有失去黑老丘这个名字而欣然,反而为自己开不了口讨回两次工钱而在心里窝火,只能反复铭记:胖寡妇还欠我两次工钱!
十二
清晨,黑老丘跟往常一样路过教场坝,一群人正在围观。黑老丘想,许是又有案件了。黑老丘停下三轮车凑上前去读公告的内容。黑老丘心里默记着这些内容转身离去的时候,脸是这平生以来最黑的一次了。
今天黑老丘踩三轮特别卖力,那已经佝偻身子左右摇摆着牵引着车身。
回到窝棚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女人正在扫地。
黑老丘叹了一口气,把自己慢慢平放在床上。
女人放下扫帚,凑过来问,是不是病了?
黑老丘没有答话。
女人用手去摸额头,没有什么不对,便继续扫她的地。但黑老丘病了,没有人知道,包括他的女人。
黑老丘这一卧床,就是三天。黑老丘女人记得,自己儿子去世时黑老丘就这样卧床一次,事隔这些年头了。黑老丘女人这样掂量着急忙出了门,拄着棍,没有半个主张。
黑老丘女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在街上摆地摊的医生。这个医生把手中那竹竿支着的写着“祖传秘方,妙手回春”的招牌斜立在黑老丘的床头,就开始给黑老丘看病了。
黑老丘女人看见这江湖郎中用右手掌竖立在胸前,闭目一会,口中不停地唠叨,念念有词。黑老丘女人便打住了郎中神秘的动作神态,问,医生,黑老丘怎么了?
这郎中皱了皱眉头,顿了顿,慢慢说,你夫君遇见血光灾星了,被三个死鬼缠着,一个是吊死的,一个是水淹死的,还有一个就是火烧死的……
哪有鬼!可别吓我。黑老丘女人说。
郎中忽用手向棚外一指,大吼一声,请看!淹死的鬼就还守在河里!
黑老丘女人打了一个寒战,顺郎中的手向外看去,只见河水面荡着一圈圈波浪。黑老丘女人小声说,没有鬼,别吓我。
黑老丘女人也忽然意识到,自己请回家来看病的原来是个江湖郎中。
这江湖郎中正要指着棚顶张口说话,被黑老丘女人止住了。黑老丘女人说,医生,你请吧,我们受不起你这高明的医术了,不耽误你的宝贵时间了,请便。
江湖郎中听了,收了收闪烁在他眼里的那份盎然的诡异,显出很遗憾的模样,握住他那招牌摆着头向棚外走去。到棚门口时,转身对黑老丘女人说,我是观世音菩萨派来的救苦救难……
请自便吧——医生大师!黑老丘女人打断了这个江湖郎中的话。
黑老丘女人转身看着床上长躺着的黑老丘,一下瘫坐在了地上。
时间就这样静默着。许久,从时间的边沿发出了一丝声音:娘……妈!娘妈,娘妈……水……水——水!
这嘶哑的声音,把黑老丘女人从地上提了起来。
十三
黑老丘的脸生平以来白了第一次,一白就是一个月。
女人坐在床沿上,看着黑老丘说,还是再去看看……把车卖了,啊?
黑老丘摆着头,伸手在床板下摸索一阵,终于拿到了那油纸裹着的一包东西递给女人。
女人接过黑老丘手里的东西,放回了原处,说,还是卖车吧。
黑老丘女人默默地拄着棍拿着东西来到街上,可不知道怎样开口叫卖。她路过一个收购旧时期钱币的地摊,她想,这一包可算是咱家的古董了。旧钱币商贩打开包,包里似乎像是一枚枚勋章,撒了一地。那黑老丘一直珍藏的小本,早已经被汗渍浸黄,没了一个字迹。
黑老丘这一个月来,对他女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哎呀,我没有病!
当时黑老丘在橱窗里看到的公告仅是整顿城里的人力三轮车公告。可黑老丘只能沉默,哪怕是面对自己的女人也没有提及。
禁令人力三轮车上街载客的日子就是在黑老丘不再卧床的第二天。从这一天起,人力三轮车禁止上街,退出生活的舞台。也难怪没有吃药打针的黑老丘,赶在这个日子结束卧床了。
这一天下起了毛毛细雨。黑老丘固执地把女人扶到桥头,安顿在自己的车上。黑老丘女人没有说话,就这样温顺地顺着黑老丘的意。
黑老丘女人看着男人认真地踩车的背影,手在颤抖。
雨丝不停地抽着。
黑老丘踩着车驮着女人,嘴角藏不住那一丝卑微的笑。
黑老丘竭尽全力地踩着车驮着黑老丘女人。
繁华的大街,默默地上演着生活的繁华。
天际边那一线温暖的阳光透过雨丝,照着俩人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