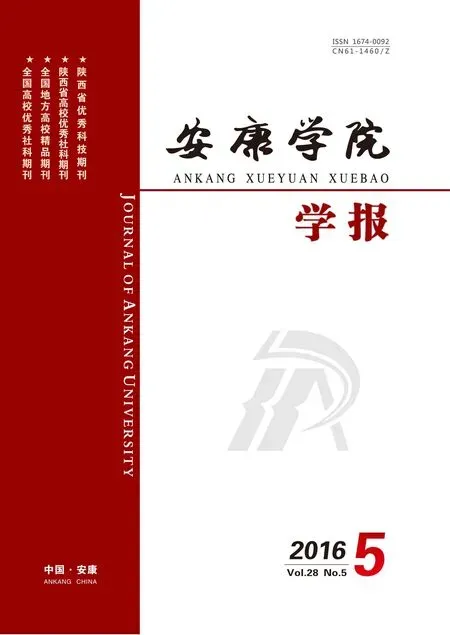群众教育价值取向的历史考察——以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为起点
王玉珏
(四川理工学院 法学院,四川 自贡 643000)
群众教育价值取向的历史考察——以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为起点
王玉珏
(四川理工学院 法学院,四川 自贡 643000)
基于价值取向视角考察群众教育活动可以发现,在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中,目的性价值取向不足,工具性价值取向显现;建国后到文革的群众教育主要通过群众运动进行,其特点在于目的性价值取向逐渐泯灭,工具性价值取向横行;文革后至今的群众教育呈现出工具性价值取向消退,目的性价值取向回归的特征。这一历史考察启示我们,持工具性价值取向,群众教育就会流于形式,甚至带来灾难;必须坚持目的性价值取向,以群众全面而自由发展为目标,方能取得教育实效,展现教育功能与价值。
群众教育;目的性价值取向;工具性价值取向;群众运动
群众教育的作用与意义是不证自明的命题,当前群众教育的效果差强人意也是有目共睹。切实有效提升群众教育的效能是亟待解决的时代重大课题,该问题的解决既需要实践工作的艰辛努力,也需要理论的反思与正确引领。理论的反思应该追根溯源,自然就该追问群众教育价值取向何在?这一问题的正本清源,意义重大,因为它决定了教育的内容、方法、途径等要素,必然也就决定了教育的成效。
群众教育价值取向可以简单类分为工具性价值取向和目的性价值取向。工具性价值取向是将受教育者视作工具,以实现教育者的目的为归属;而目的性价值取向则是将受教育者作为教育目的,以实现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现有理论研究对工具性价值取向强烈批判,研究者大多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学、人本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论证必须要坚持目的性价值取向,且将目的性价值的目的界定为“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内涵丰富,争议较多,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它的主体内容包括“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充分自由发展;人的才能和能力的多方面发展;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发展”[1]。
群众教育应该且必须以群众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教育目的本身,即在价值取向上坚守“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与之相对的是工具性价值取向,即将群众作为工具尤其是作为政治工具。群众教育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必须坚守目的性价值取向,因为党的宗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的全面自由发展就应该成为党工作的归属。同时,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共产党宣言》中描绘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2]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我们党奋斗的目标。可见,坚持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目的性价值取向,就是对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的秉承与践行,而工具性价值取向则是对其否定与扬弃。
知易行难,考察党的群众教育历史,可以清晰的看到,在教育实践中坚持目的性价值取向殊为不易,一部群众教育的历史,充满了曲折与艰辛,更凸显秉承此价值取向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一、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目的性价值取向不足,工具性价值取向显现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党在陕甘宁边区持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教育活动。社会教育是以群众为主体的教育活动,其对象是“不能脱离生产的文盲大众(儿童、青年、成人),不能脱离生产的‘半文盲大众’,不能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3]27。教育组织形式以冬学为主体,亦包括识字班、识字组、半日校、民众教育馆等。同时,各种文艺尤其是秧歌也成为重要的教育形式。教育内容包括以识字为主的文化教育、生产生活教育、军事教育和政治教育等。
结合当时边区群众实际,这些教育目标具有强烈的功利色彩,潜含工具性价值取向。当时边区生产力极其低下,群众生活十分困难,终年辛勤劳作而不得温饱,其现实迫切需要解决生产生活困难,维持生存。而教育者急需具有政治觉悟、抗战技能和文化知识的群众参与党的事业,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与矛盾。社会教育的目标设定在价值取向上存有严重偏误,只是单向度表达了教育者的现实需求,对受教育者的实际需要缺乏认可与关照,存在工具性价值取向明显,目的性价值取向不足的特质,这决定了社会教育的组织形式、内容、方法等必然出现失误与偏差,这也是社会教育在前期出现各种问题的根本缘由。
在社会教育的前期实践中,教育者按照既定目标强制推行教育活动,以冬学为例管窥。1937年,教育厅详细规定了冬学科目和课程(见表1)。按照此规定,学员每天从早到晚均要参加冬学学习,不得休息。学习的内容以军事、国语和政治为主,这些内容的学习达到每周37小时,比例高达88%。群众直接需要知识技能只有珠算,每周只有2小时,比例仅为4%,群众其它直接的教育需求被遮蔽。这样的课程设置和教育方式漠视受教育者发展需要,呈现鲜明的工具性价值取向,在各级社会教育工作者机械的强制推行之下,遭到群众的怀疑、抵制和规避。“吴旗一区三乡的冬学强迫动员学生,家长迫不得已只好送子弟入学,但不给学生送粮吃,学生每天吃不饱饭,喝稀米汤,不能安心学习。如让学生回去拿粮,就不再来了”“个别家长送子弟入学时痛哭流涕”[4]280。靖边贺家坬冬学,“第一天动员四个学生到校,第二天就跑了两个。群众反映说这是‘瞎胡闹’”[4]280“新城区三乡胶泥湾冬学,则规定不按期到校者,罚吃羊头会,或柴一百斤。由于这样,雇学生的事也发生了”[4]281。在新营湾的冬学,王爱民的婆姨有病,在家带孩子、煮饭没有去上冬学,遭到批评斗争,结果“老病加气又受寒”,很快就去世了[3]223。

表1 冬学科目与课程
实践中的困难和阻碍迫使教育者逐渐进行转向,满足群众的教育需求。1942年,教育厅指示,“兹根据实际需要,规定冬学课程为:新文字(或汉字)、卫生常识、珠算、时事、唱歌……教卫生常识和珠算各占全课程的五分之一”[4]176。而到了1944年则进一步明确要求,“既然根据地群众的生活基础是家庭和农村,我们的群众教育……就应该时时刻刻照顾到家庭和农村,家庭生活和农村生活中实际所需要的知识,就应该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或全部内容……”[5]。
这一转变落实在实践中,就是社会教育以群众实际需要和发展为出发点,以生产、卫生、纺织、牲畜治病、算账等群众急需知识为教育内容中心和重点,这些内容的学习,以解决群众迫切需要的生产生活知识与技能为直接指向,实实在在解决了群众现实困难,提高了群众的生活水平,这样的教育让群众成为了教育目的本身,是目的性价值取向的直接体现。如土佛寺妇女冬学开办之际,没有一个妇女主动参加。女教员李素本毫不气馁,认真进行调查,她发现在严冬中,村里的小孩子仍然穿着破旧的单裤,就连村长的婆姨都讲:“而今,惟穿的困难,布贵,自己又不会纺织”。李素本通过调查后认识到群众急需的是学会纺织,于是她确定教学方针为“纺线识字一揽子”。当李素本以纺织为教学切入点时,妇女们学习积极性极高,在学习纺织的同时,妇女们认识到教员是真心帮助关心她们,对于识字的抵触大大降低,一些妇女还主动要求识字,结果“有二十三个婆姨学会了纺线线,识字最多达到三百多字,最少的也识了五十多字”[4]338-341。
这样的目的性价值取向的教育解决了群众生产生活实际困难,自然受到群众的欢迎,使得他们自觉自愿投入到社会教育中。更重要的是,群众对这些知识的获取,在自身生活得到巨大改善的同时,深切认识到党和边区政府是他们利益的忠实代表,在心理上产生深深的认同。群众是朴实的,这种心理态势的生成,使得他们以饱满的热情响应党和边区政府的号召,支持和参与党和边区的各项工作,扫除文盲、战争动员、移风易俗、政治认同这些极难达成的教育目的也水到渠成的悄然实现。
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工作。社会教育各种组织形式与妇纺组、变工队、运输队等各种经济组织,民兵、自卫军、儿童团等各种军事组织密切配合,建立起了集体化、组织化和开放化的生产生活网络,将原来分散封闭的农民纳入各种组织构建的网络系统,这种集体生活关系网作用是巨大的。有学者认为,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不仅改变了乡村社会的关系网络,而且改变了人们的认知、情感和意识。农民生活的中心由此从自家的场院转移到党所期望的集体行动框架中,从而为党的政治动员奠定了最广泛的社会基础”[6]。但是,通过群众运动方式进行群众教育,本身背离了目的性价值取向。在社会教育构建的集体生产生活网域中,个人必须服从其内在的规则和规定,违背就可能会受到各种指责乃至惩罚,个人自主性极低,自由空间被挤压。就个人而言,身处群众运动构建的网络之中,即便得到发展,也不是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自然也不是目的性价值取向的体现和践行。
在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中,其目的性价值取向不足,工具性价值取向表现明显,但事出有因,无可厚非。因为社会教育的开展处于特殊战争时期,处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以群众运动方式发动群众参加抗战,勠力同心,共赴国难成为现实逻辑与必然选择,对个人关照不够实属无奈。但是,以群众运动方式进行群众教育,不自觉走向工具性价值取向道路,将群众作为政治工具,其结果危害无穷。
二、建国后到文革的群众教育:目的性价值取向逐渐泯灭,工具性价值取向横行
建国后到文革,群众教育主要通过群众运动方式进行。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的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华大地群众运动此起彼伏,土地改革运动、抗美援朝运动、三反五反运动、除四害运动、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风起云涌。“有学者统计,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大大小小的运动近70次。毫不夸张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无间断的运动中迎来‘而立之年’的。”[7]75群众运动成为了党执政的路径选择与特色范式,构建了在世界历史中也极为独特的社会政治生态,群众教育也在这些运动中不间断进行。
建国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群众运动成为了党执政的重要路径,也成为党开展群众教育的核心和主体渠道。此种历史事实的生成绝非偶然为之,而是其内在的历史逻辑必然。胡乔木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的过早成功,特别是几亿农民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参加了合作社,使连续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二十年以上的毛泽东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是万能的武器。”[8]学界研究则认为,群众运动成为被历史革命证明了的管用的法宝,当然要继续使用,且认识出现偏差,把群众运动等同于“人民民主”,作为了“群众路线”的同义词[7]75-76。
对于群众运动,有人对其开展模式做了系统的概括:开展群众运动程序是先明确目标,然后训练大量人员宣传贯彻这些目标,鼓动群众积极参与和实现这些目标;群众运动动员模式为通过集体的教学学习活动,用爱国主义等激发群众热情,提高群众认识,树立典型人物,让群众找到学习模仿的对象,通过舆论宣传氛围的营造,形成主流的价值观念并得到群众认同;群众运动由党主导,党的组织和社会各种组织相结合,将绝大多数群众纳入各种组织之中,通过组织将目标迅速贯彻到群众个体,通过群众的实践行动来达成目标[9]。在不间断进行的群众运动中,群众依附于各种组织,为实现各种目标而努力实践。与此同时,个体群众的主体性被悄然的弱化和遮蔽,群众个体变形为政治工具人。群众运动的持续生成,在事实上是工具性价值取向的一步步强化和目的性价值取向的渐渐枯萎。
倘若群众运动目标得当、方式合理,对群众而言,工具性价值取向危害不够显性,反之则危害无穷。随着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这些运动,目标失位,但群众基于历史的惯性、现实的权衡,被迫积极参与,尤其是“红卫兵”运动,让部分原本善良的个人沦为野兽,他们打砸抢烧,肆意横行,对他人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危害,更有甚者,父子夫妻兄弟之间反目告密,出卖迫害亲人。尤其值得反思的是,这些违背基本人伦的兽性行为是历史在场的正当之举,行为人认为自己的行动是正义的,个人的道德自律与价值判断在群众运动中消亡殆尽。可见,以群众运动开展群众教育,坚持工具性价值取向,让群众成为工具人,一旦目标方式错误,群众个体、社会、党和国家就成为同体受害者,群众教育走向了目的的反动,导致国家动荡,群众受苦,党的执政地位也受到严峻的挑战。
三、文革后至今的群众教育:工具性价值取向消退,目的性价值取向回归
文革刚结束,全国范围仍在开展大规模的批“四人帮”和批林彪的运动,对此,党及时果断结束了这些运动,把群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国家建设之中。这种转变的实现者和完成者就是邓小平同志。对于群众运动的弊端,邓小平同志早有认识。1961年他就指出,群众运动“如果一年到头搞运动就没有劲了,就变成浮夸、形式主义了,实际上违反了群众意志,脱离了群众”[10]。但在特定的历史境况中,这样具有真知灼见的声音被淹没了。1980年,他站在群众的立场上明确指出:“人民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大规模的运动厌烦了。凡是这样的运动都要伤害一批人,而且不是小量的。经常搞运动,实际上就安不下心来搞建设”[11]348。其后,他进一步总结到:“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和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问题,同革命时期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和对反动制度的破坏,本来是原则上根本不同的两回事”[11]336。从历史经验、群众运动的历史背景和群众的现实诉求等层面对在和平时期开展群众运动进行了彻底的否定,找到了和平时期群众教育的正确道路:与群众讨论说理,以制度的革新从而实现群众物质文化的满足来得到群众的认同与认可。从此,大规模群众运动被废止了,党带领群众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不断提高生产力,随着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的成就,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显著的提升,尤其是群众生活的政治环境得到质的改善,生活工作自由度明显提高,这就是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取向的具体践行。
其后,党的领导集体又提出和践行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归根结底,就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江泽民强调,“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12]。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直接明确地把群众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了价值取向,充分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群众成为发展本身而不是工具。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治国理政以来,先后在领导干部中进行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教育活动”,2016年即将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都是从对领导干部教育的角度体现出对群众的尊重,事实上是将群众作为工作目的,是实实在在践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取向。
这些理论是党治国理政的宏观理念,对党领导的群众教育活动一样具有指导作用,应该且必须引领群众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因此,从文革后到现在,我们对以群众运动方式开展群众教育予以废止,群众“集体人”的角色淡化,群众的个性得到极大解放,才能和能力得到全面发展,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强迫群众接受教育明显弱化,重视群众的主动性,目的性价值取向回归。
但我们也不无遗憾的看到,在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目的性价值取向依然不够。诸如通过政治学习等方式进行单向度的政治教育、宣传与号召;对群众现实生活情况不重视、不了解、不关注,只是进行政治宣讲,教育内容与群众实际脱节,形成“两张皮”现象等。这导致群众认为教育对其无用,在思想上反感,这是当下群众教育效果不够理想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我们在实践中必须不断扬弃工具性价值取向,坚持目的性价值取向的重要缘由。
四、结语
从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开始,以价值取向为视角分析群众教育可以看出,群众运动曾经是我们开
展群众教育的主渠道,而群众运动的实质就是通过严密组织体系的构建,将广大群众纳入其中,用集体化、群体化的方式开展群众教育,让群众的思想、行动和党的目标保持高度一致。这样的教育方式将群众作为政治工具,在本质上是工具性价值取向的体现,其恶果和贻害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展露无遗。而坚持目的性价值取向,将群众全面而自由发展作为目的本身,就会得到群众的积极拥护,让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实现共赢。这些启示要求我们在当下和今后的群众教育中,不能运用大规模的同质化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开展,必须坚守目的性价值取向,以群众的现实需要为出发点,通过群众体力和智力、才能和能力、社会关系、个性和主体性的充分自由全面的发展,建构和生成党和群众的命运共同体,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我们的“中国梦”而同心协力、共克时艰、努力奋斗,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众教育的价值与功效。
[1]宋秀红,郑洁.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及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J].探索,2004(3):93-94.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
[3]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4]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下)[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5]社论.教育要尊重对象的需要[N].解放日报,1944-04-07 (1).
[6]张孝芳.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J].山东社会科学,2008(8):137.
[7]赵智.王兆良.从“运动”到“活动”: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研究的新范式[J].山东社会科学,2012(6).
[8]胡乔木.胡乔木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62.
[9]龙太江.从动员模式到依法治国:共产党执政方式转变的一个视角[J].探索,2003(4):27.
[1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5.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925.
【责任编校龙霞】
A Historical Review of Value Orientation of Education for the M asses——Beginningwith Social Education in the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Area
WANG Yujue
(School ofLaw,Sichuan University ofScience and Engineering,Zigong643000,Sichuan,China)
A historical review of value orientation of education for the masses reveals that purpose-orientated values were not taken seriously in social education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area while instrumentality-orientated values were very overtly stressed;education for themasses was implemented mainly through masses’campaign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tspurpose-orientated valuesgradually disappeared and the instrumentality-orientated valuesspread through the whole country;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ill now the masses’education has been characterized by disappearance of instrumentality-orientated values and return of purpose-orientated values.The historical review shows us that if we hold instrumentality-orientated values,education for themasses will becomeamere formality and even bring about disaster.Wemust stick to purpose-orientated valuesand aim atthemasses’comprehensiveand freedevelopment.Only in thisway canweachieve desirable results in education and demonstrate the function and valueofeducation.
education for themasses;purpose-orientated values;instrumentality-orientated values;masses’campaign
D23
A
1674-0092(2016)05-0091-05
10.16858/j.issn.1674-0092.2016.05.020
2016-03-25
四川理工学院人才引进项目(2014R C24)
王玉珏,男,四川南江人,四川理工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党史党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