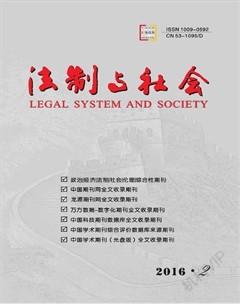空间碎片问题及相关规制
摘 要 空间碎片是人类在太阳系空间,尤其是地球外层空间的太空探索活动产生、遗弃的碎片和颗粒物质。它对运营中的航天器、有效载荷和航天员的生命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空间碎片问题得到广泛的关注与探讨,相关的法律实践也十分丰富,主要包括国际条约与国际习惯。
关键词 空间碎片 叶栅效应 外空委 《空间碎片减缓指南》
作者简介:詹陈朋,武汉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法。
中图分类号:D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2-277-02
一、空间碎片引述
(一)空间碎片(space debris)的定义
空间碎片的定义从文字上看来貌似很简单,但其在外层空间法中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在宽泛的意义上,空间碎片是指环绕在地球外空间自然形成的宇宙尘和人为活动的碎片。显然强大的宇宙力量难以受到人类的控制,在狭义上或学界通行的理解,空间碎片是指人类在太阳系空间,尤其是地球外层空间的太空探索活动产生、遗弃的碎片和颗粒物质,也称太空垃圾,主要由报废的空间装置、失效的载荷、绝热防护材料、分离装置以及因碰撞、风化产生的碎屑物质组成。
(二)空间碎片现状
总计,有大约9000块尺寸大于一米的空间碎片在对地静止轨道,而在低地球轨道也有同样数量的大于10厘米的碎片。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SA)承认,有大约11000块直径大于10厘米和几十万直径小于10厘米的碎片占据了地球轨道。2010年,SSN追踪在地球轨道中的21000个人造物体,它们都是10厘米以上的。在这些人造物体中,只有少于1000数量的正在使用的人造卫星,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减缓碎片的产生或对之进行清除,在50年之内估计这种碎片的数量会达到50000。1-10厘米的空间碎片在2003年被估测为11000块,大于1厘米的碎片总量估计有300000块。而更小一点的,尺寸在1毫米与1厘米之间的碎片估计有35000000块。美国大概要向其中一半的空间碎片负责任。
(三)空间碎片的“叶栅效应”
“叶栅效应”被用来描述一种现象——空间碎片的数量达到一个难以证实的临界值而使人类通向太空的活动成为不可能。这个假说是大型的空间碎片相互发生碰撞,产生越来越多较小的空间碎片。随着更多的空间碎片产生,碎片间的碰撞也愈来愈频繁,使得这个问题永远存续。如果没有减缓措施或类似的干预,一个护盾形空间碎片罩会笼罩在地球轨道,这个难以通行的碎片罩无疑会阻拦未来人类对外太空的探索。这种情形会使人类在几百年内不能通向宇宙,直到大部分的碎片脱离轨道到大气层中燃烧。所以,相关的减缓措施或碎片清理方案对于灾难的预防是必要且亟需的。
二、关于空间碎片规制的法律实践
(一)国际条约
1.《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简称《外层空间条约》:
《外层空间条约》是第一个规定各国从事外层空间活动基本法律原则的普遍性多边国际条约,是外层空间的基础性条约。《外层空间条约》被公认为外空宪章,它由序言和正文17条组成。其第九条与空间碎片规制直接相关,该条规定:在对于外太空的开发与利用过程中(包括月亮及其他天体),条约成员国须遵循协作与互助原则,并在外太空进行的一切活动中考虑到其他成员国的相应利益。条约成员国可从事对外太空的探索与开发,但同时应防止因引入外星物质致使的地球环境的有害污染及不良变化,并应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措施……
可为何在空间碎片问题上有相关法律架构的情境下,美俄等空间大国却无视条约的规定,屡屡进行各种造成大量空间碎片的活动、实验?这不能仅仅用国际法的“软法”特性来解释问题的出现。这也是由《外层空间条约》本身的特点决定的:(1)在条约的序言和第一条中,有“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所有国家谋福利与利益”等字样,这种原则性的字句对鼓励外空活动的环境保护有积极的作用,但太过笼统的字眼却缺乏实际的可执行性。且条约第一条规定了各国对太空探索、天体开发和利用的自由,可此自由却很难受到约束与控制,导致了空间碎片的大量存在,最终会让这种“自由”彻底失去意义。(2)条约对于缔约国外空行动产生环境污染的规制只集中于探索这一阶段,却未对天体的开发这一阶段做出任何表述。外空的探索,其目的就是为了天体的开发,这导致对天体的开发过程中造成任何空间碎片失去了条约的约束,也给予了缔约国将探索阶段产生的空间碎片推脱到开发阶段的现实可能性。(3)条约第6条虽规定了产生空间碎片的国际责任,但责任构成要素、责任方式以及责任的实现途径等方面都未能给出具体的、有实际操作可能的、有强制力保障实行的规定,且责任的承担没有有效的权力来保证,更不用说具体的执行程序和方式。因此,《外层空间条约》对于外空环境的保护和空间碎片的规制只是一个鼓励性大于操作性的国际条约,它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为将来更具体更具执行性的条约的形成奠定了基调,但对当下空间碎片的控制难以起到理想的作用。
2.《空间物体所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简称《责任公约》:
该条约首先规定了空间物体所造成的损害中的各个要件,如条约第一条详细规定了“损害”的含义、“发射”的意义、 “发射国”的概念以及 “空间物体”的含义。此条为确定空间碎片损害的责任主体、致害工具、损害表现等均提供了法律依据。空间碎片无疑是由于国家发射空间物体所造成的,且空间碎片会对其他国家或本国的航天器、轨道空间站造成损害,对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和健康造成损伤。所以空间碎片所造成的损害属于《责任条约》规定的损害类型,空间碎片所造成损害的责任应适用《责任条约》。此外,条约第二条与第三条根据受害对象的不同将空间碎片所致损害赔偿责任区分为绝对责任和过失赔偿责任。虽然空间碎片的产生难以避免,但是从几十年来空间碎片大量产生的历史告诉我们,大部分空间碎片的出现是因为人为的疏忽或实验造成的。故《责任条约》第三条规定的过失赔偿责任适用于空间碎片造成的损害。而且,《责任条约》对责任主体、责任类型、共同责任、损害赔偿、赔偿程序、赔偿时间等做出了详细地规定,对空间碎片的规制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但同《外层空间条约》一样,《责任条约》也有其局限性,虽然按照第一条第四款的规定可以做出空间碎片属于空间物体的范畴的法律解释,但这种推断不是严谨的,是容易被反驳的。因此可以认为《责任条约》并没有规定出“空间物体”的内涵与外延,也没有明确规定空间碎片与空间物体之间到底有无从属关系。显然这对于空间碎片造成损害的责任是否适用《责任条约》是一个难以越过的“槛”。其次,就算明确了空间碎片造成的损害适用《责任条约》,但空间碎片到底由谁造成从技术上来甄别具有相当难度,因为空间废物的数量十分庞大,碎片间的碰撞也是偶然发生的。这样就难以认定责任的主体,受害者因此也无法主张国际赔偿责任。最后,《责任公约》中尚未规定有关对空间碎片的预防措施,而是规定空间物体所造成损害的事后补救措施。这种规定并不能较好地在事前预防空间碎片的产生。
(二)国际习惯
国际习惯是各国在其实践中通过重复类似的行为而形成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行为规则,它必须包含通例和法律确信这两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是国际通例,虽然在空间碎片数量越来越庞大的现实面前,很多空间国家都或多或少表示了减缓空间碎片的愿景,但一方面缺乏具体的法律、计划,另一方面,各国还是乐此不疲地进行各种外空活动,制造更多的太空垃圾。所以,一个被广泛承认的国际惯例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形成。而第二个要素法律确信,显然也不能满足。2007年6月,联合国外空委发布指导方针彻底地解决了此问题。这份文件明确地阐明,《碎片减缓准则》不是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因此,具体调整空间碎片问题的国际习惯还远未形成。
但是一般的国际习惯或许能在规制空间碎片问题上做出一些努力。国际习惯法中存在关于环境保护的一般原则,该原则最初源于1941年的特雷尔治炼厂案。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形成了任何国家都无权以造成他国领土损害的方式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本国领土的法律原则。这条原则被世界各国广泛承认而成为国际习惯。虽然,这条原则中是对一国的管辖领域造成损害,似乎与空间碎片造成的损害泾渭分明,但发射国发生的航天器按照国际法仍属于国家的管辖领域,所以一国制造的空间碎片对另一国的航天器造成损害适用该国际习惯虽仍是值得商榷,但也不是没有任何可行性。此外,《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第21条原则规定:各国有根据自己的环境政策开发本国资源的主权;并且有责任保证在他们管辖或控制之内活动,不致损害其他国家的或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虽然该宣言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其原则被广泛承认为国际习惯。其包括了对任何国家管辖范围外的地区造成的损害。显然空间碎片在地球轨道所造成的损害是属于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
(三)联合国《空间碎片减缓指南》简称《指南》
联合国空间碎片工作组在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的第四十三届会议期间举行了非正式会议,在非正式会议的议论过程中,工作组审查了空间碎片减缓文件初稿,并提出了一份修订稿。在2006年2月28日举行的会议上,经工作组进一步审查后达成了协商一致文本,通过了《空间碎片减缓指南修订草案》,并于2007年正式通过了《空间碎片减缓指南》。该指南具体提出了诸多措施以实际减少空间碎片的产生,这些措施包括限制在正常运作期间释放碎片空间系统应当设计成不在正常运行中释放碎片、最大限度地减少操作阶段可能发生的解体、限制轨道中意外碰撞的可能性等。关于指南的适用性,《指南》规定会员国和国际组织应通过国家机制或各自适用的机制,自愿采取措施,确保通过空间碎片减缓的做法和程序,在切实可行的最大限度内执行这些指南。尽管《指南》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其在国际社会拥有广泛的政治影响力,它已经成为一项国际习惯法规范,并且国际社会的减缓空间碎片的国际实践也已经形成。如由12个国家组成了机构间空间碎片协调委员会,并通过《IADC空间碎片减缓指南》。
参考文献:
[1]李春来、欧阳自远、都亨.空间碎片与空间环境.第四纪研究.2002(6).
[2]贺其治.Space Law and the Environment.北京:中国空间法学会.2000.
[3]凌岩.国际空间法问题新论.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
[4]梁西.国际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5]尹玉海.国际空间立法概览.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
[6]李寿平、赵云.外层空间法专论.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7]邵沙平.国际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8]高国柱.外层空间法前沿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9]高国柱.空间碎片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河北法学.2006, 24(5).
[10]Gabrielle Hollingsworth. Space Junk: Why the United Nations Must Step in to Save Access to Space.Santa Clara L. Rev, 201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