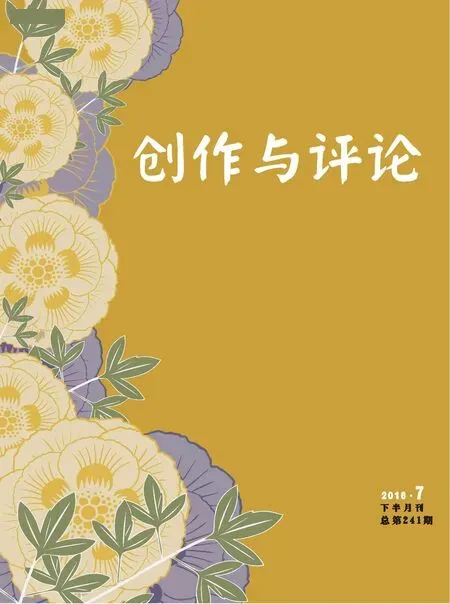“说”故事与讲“故事”
——话本传统在当代小说中的扬弃
○郭冰茹
“说”故事与讲“故事”
——话本传统在当代小说中的扬弃
○郭冰茹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研究中,给予话本很高的评价,他说:“这类作品,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①。鲁迅从文体、写法和语言三方面肯定了话本之于中国小说史的价值和意义。作为一种文体,严格意义上的话本虽然在清前期就已经衰亡了,但是其用于劝诫讽喻的社会功能,其围绕讲故事而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叙事成规,仍不同程度地显现在当代小说中,并为当代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叙事资源。
一
晚清“新小说”的兴起,是我们讨论“现代小说”与包括话本在内的诸种“旧小说”关系的起点。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在强调小说介入社会以改良群治、新国新民的同时,也一改轻视小说的文学传统,将小说置于经史、语录和律例之上,从而革新了小说观念和小说内容。“五四”新文化运动则以西方小说为范本,对小说这一文体进行了现代性预设:“现代小说”不仅应当用白话写成,更应当含有某种“现代性”,它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借助文学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终极形式。因此,在这一预设下,章回小说、笔记小说,甚至维新派曾大力倡导的“新小说”均被视为“旧文学”受到排斥和批判。不过,话本②并不在此列,这是因为与这些“旧文学”不同,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文体,话本早在中国社会进入现代之前,确切地说,早在乾嘉时期就已经衰亡了。
如果清理话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发展脉络,会发现这一文体的衰亡与乾嘉时期经世致用的社会风气及其自身的思想局限和艺术缺陷有很大关系,然而在新文学的倡导者看来,话本脱离了民间立场,失去了市井气息才是其衰亡的主因。郑振铎说,当话本由最初的“新鲜的、逼真的,具着多量的时代的与地方的色彩与背景”的“各地的新闻,社会的故实,当代的风光”转变为“枯涩无聊”“隔膜而不真实”的“古人之事”;当话本由“实际上的应用,而变作了非应用的拟作”,当话本由“娱悦听众”变成“文人学士们自己发泄牢骚不平或劝忠劝孝的工具”,“话本的制作遂正式告了结束,话本的作者也遂绝了踪影”③。郑振铎站在“平民”或“民间”的立场来重新认识话本这一“旧文学”,这在某种意义上为我们理解“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利用和改造话本提供了思路:当“民间”“大众”“通俗”等特征与革命文艺的目标相吻合时,早已衰亡的话本却被赋予了存在的合法性和时代意义。
对照“左联”时期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诸多讨论,我们会发现话本的许多特点非常符合批评家们对于“大众化”期许。比如冯乃超认为:“文学的大众化问题首先要有能使大众理解——看得懂——的作品,这不能不要求我们的作家在群众生活中认识他们的生活,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具体的表现出来。同时,文学的任务如果是民众的导师,它不能不负起改革民众生活的任务,就是说文学该有提高民众意识的责任”④。冯乃超提及的“群众生活”和文学作品的教化功能恰恰是话本所具备的,正如郑振铎对话本特点的概括:话本大多取材“闾巷新事”,说的是平头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对普通读者、听众而言,看书听书是为了消遣娱乐,可对写书说书人而言,话本则多了一层劝恶扬善的“道学心肠”⑤。此外,由于早期话本的传播媒介不是借助阅读而是通过书场,作为“说书的底本”,话本的可“说”性以及可“说”性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宣教优势也被左翼文人格外看重。瞿秋白明确指出:“旧式的大众文艺,在形式上有两个优点:一是它和口头文学的联系,二是它用的浅近的叙述方法。这两点都于革命的大众文艺应当注意的。说书式的小说可以普及到不识字的群众,这对于革命文艺是很重要的。有头有脑的叙述,——不像新文艺那样‘颠颠倒倒无头脑的’写法,——也是现在的群众最容易了解的。因此,革命的大众文艺,应当运用说书滩簧等类的形式。”⑥左翼批评家对话本文体的意识形态再阐释,为这一文体的激活做了一定的理论铺垫,或者,反言之,正是话本的这些文体特征为左翼批评家建设“文艺大众化”理论提供了文本参照,使他们在“新内容”与“旧形式”之间找到了关联点。
当然,尽管话本自身的特点契合文艺大众化的某些要求,左翼文人对“旧形式”的批判态度始终如一,正如周扬高屋建瓴般地强调:“我们一方面要对这些封建的毒害斗争,而一方面必须暂时利用这种大众文学的旧形式,来创造革命的大众文学。不过我们不要忘记劳苦大众是应该享受比小调,唱本,说书,文明戏等等,更好的文艺生活的”⑦。换言之,话本可利用的部分仅仅是其形式而已。文艺需要大众化,旧形式应该被改造,不过,关于如何改造、如何利用等等操作性的问题在“文艺大众化”以及随后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中都没能获得进一步的讨论。事实上,如果只是在理论上赋予话本以存在合理性,而没有将对其的改造和利用纳入新文学的创作,这一文体仍然是“僵死”的。
二
真正有意识地在创作中利用并革新了话本这一文体的作家是赵树理。在赵树理关于创作的各种表述中,他广泛地使用了“说书”这一概念。从某种意义上看,“说书”与“话本”同源,如果细究,“话本”强调的是“底本”这一文字体现,更接近文学;而“说书”强调的是“说”这一表现形式,更接近曲艺。事实上,赵树理吸收的正是话本能够被表演的可“说”性,而在诸种“旧形式”中,赵树理之所以会对话本情有独钟则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很大关系。长期农村生活的浸淫使赵树理对评书、秧歌、地方戏这些北方农民喜闻乐见的消遣形式更有感情,而这些艺术形式中最接近文学/小说的可能就是评书/说书。赵树理曾在他的父老乡亲中传递过新文学的讯息,但这些最初的文学实践屡遭挫折,因此,赵树理对新文学无法深入农村的问题最感同身受,也最主动自觉地抛弃了从新文学中习得的表现方式,转而从评书话本中汲取资源。
细读赵树理的文本序列,我们会清楚地看到,他对话本的吸收并没有停留在新文学倡导者们所大力强调的“形式”的层面,相反,他从一开始就摈弃了话本小说中入话诗、头回、正话、篇尾等僵化的程式套语,而将利用旧形式的侧重点放在话本的传播效果上——事实上,无论是19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还是《讲话》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首先强调的恰恰是文艺的传播效果而非艺术特色。如果将赵树理的文本序列与同样利用“旧形式”、套用章回体书写新内容的《吕梁英雄传》《烈火金钢》《新儿女英雄传》等相对照,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周扬就对《吕梁英雄传》“旧瓶装新酒”的尝试置若罔闻,茅盾认为它虽然对“章回体”进行了扬弃,但功力不够。⑧而赵树理只在形式上分段,列出小标题,看上不不怎么像“旧形式”的作品,比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反而得到了周扬、茅盾、郭沫若这些文艺界领导的肯定,认为“他所创造出来的绝不是旧形式,而是真正的新形式,民族新形式”。⑨
从某种意义上说,赵树理所创造出来的“新形式”正是借鉴了话本的特点,在小说的可“说”性或曰能“听”懂方面做足了文章。赵树理的努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故事有头有尾,且完全依照时间顺序展开。话本里正话的开头往往首先交代人物、地点,以便听众/读者迅速进入故事,跟着说书人经历人物的各种遭际。赵树理深谙说书人的套路,也往往开门见山,起笔就点出人物和地点。诸如“刘家峧有两个神仙,邻近各村无人不晓:一个是前庄上的二诸葛,一个是后庄上的三仙姑”(《小二黑结婚》)这样的开头比比皆是,几乎涵盖了赵树理的文本序列。随后,赵树理的故事按照时间顺序逐步展开,“这天晌午”“这天晚上”“第二天吃过早饭”“隔了两天”“选举完了”“吃过了饼”这样的时间标识随处可见,如果遇到插叙中断了之前的讲述,类似的时间提示便以重复之前情节的形式出现,比如《卖烟叶》写李老师听完电话回来,贾鸿年便大哭起来,叙事人接着向读者解释贾大哭的原因,讲完之后为了接上这段被插叙所中断了的叙述,马上重申“李老师接罢电话回来,贾鸿年一见,不是就放声大哭起来了吗?”赵树理开门见山式的开篇方式和对时间不厌其烦地交代,主要是为了达到能让听众“听懂”的目的,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通过一条条明晰的时间线索,帮助读者/听众始终跟上叙述人的节奏。
二是普遍使用结构简单、缺少修饰语的短句。在赵树理的文本序列中,类似“这人现在有五十多岁,没有地,给村里人放牛,夏秋两季捎带看守村里的庄稼”(《李有才板话》)这样的句子构成了文本的主体。赵树理在语言的使用上表现出一种充分的自觉,他认为“作品语言的选择,首先要看读者对象。写给农村干部看,用农村干部能懂的语言;写给一般农民看,用一般农民能懂的语言”⑩,而为了让书面表达的语言能被一般农民听懂,则要“设法把知识分子的话翻译成他们的话来说”⑪。在《<三里湾>写作前后》中,赵树理对比了两种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一种是“她(王玉梅)知道西墙根杈枒凌乱的一排黑影是集中起来的板凳”,一种是“她知道板凳都集中在西墙根”,并且以农村人听书的习惯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给农村人写的文章要用后一种。两者对照,显然,后者这种句法简单、主谓宾紧凑、修饰语少、短小精练的句子,便于听众抓住叙事人想要表达的意思,更适合于“听”。
三是书场情境的营造。赵树理了解北方农村喜爱听书的文化习惯,因而在小说创作中也极力模仿书场的情境。书场有效地拉近了全知叙事人与读者/听众之间的距离,一方面容易引起受众的共鸣,另一方面也方便受众的情感带入。话本对书场情境的模仿,主要是通过让第一人称的全知叙述人⑫现出原身实现的,所以我们常常在话本小说中读到类似“看官,今日听我说桩奇事”这样的句子。赵树理的文本序列中有不少这种第一人称的全知叙事人,“诸位朋友,今天让我来说个新故事”(《登记》)这样的起笔方式也屡见不鲜。相对于小说的艺术创新,赵树理更看重其宣传效果,书场情境对小说可“说”性的强化,更有效增强了文本的传播效果。
赵树理是在话本自身具有良好的传播性能这一基础上,接受并创造性地发展了其可“说”的特征。这一努力不仅使他本人的文学书写确立起鲜明的个性风格,帮助他实现了小说既能“看懂”又能“听懂”的通俗化目的,同时也为新文学的“民族形式”探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而他的话本实践也因此具有了文学史意义。
不过,赵树理虽然被誉为“方向”,但他对话本传统的利用和改造倡导并没有引起一场大至文学观念,小至创作技巧的文学变革,甚至也没能真正起到“方向”的作用。这一方面与新文学作家对北方通俗曲艺的隔膜有关。新文学作家大多出生于江浙、福建、四川、湖南一带,文化积淀和文人传统的浸淫以及学识与才情的养成使他们无法像赵树理那样天然地靠近北方农村的艺术形式,更不用说学习和改造了。另一方面则与话本本身的艺术局限有关。在“现代小说”的概念中,人物形象往往是“现代性”的重要生长点,人物的成长经历、性格变化都承载着重要的意识形态训导功能,而话本小说重情节轻人物,人物虽然经历悲欢离合,但性格没有发展,也从未体现出人作为“主体”的“主体性”。事实上,赵树理的小说一开始就面临这样的批评,比如认为《李有才板话》中“新人”形象模糊,有些人物只不过“是尽了仅能给人以模糊印象的‘跑龙套’的任务”⑬;《三里湾》也存在“新人”形象不清晰,“典型化”程度不够的问题⑭。此外,诉诸于口头和听觉的艺术形式与诉诸于书面和视觉的艺术形式有着不同的审美要求,一旦用来阅读的小说迁就了听觉,读者势必会对小说松散的结构、无法得到聚焦的主人公以及触目惊心的闲言碎语⑮失去阅读的兴趣。
三
赵树理之后,仍有不少作家或多或少、自觉不自觉地在其创作中呈现出话本元素,不过,与赵树理不同的是,他们普遍抛弃了赵树理所强调的小说的可“说”性,转而在故事的可“读”性上做文章,更关心故事怎么“讲”,或者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与1980年代初许多颇有影响的著名作品相比,方之的短篇小说《内奸》被认为是最接近话本形式的文本。署名海笑的推荐文章中这样评价:“《内奸》在艺术风格上也做了大胆的探索,采用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故事生动,结构紧凑,形象鲜明,语言辛辣。小说一开头,就如说书人的开场白,然后紧扣着榆面商人的命运慢慢说来,……通篇文章笔锋犀利,嬉笑怒骂,妙趣横生,听评话、读杂文时的效果,在读《内奸》时兼而有之了。读后掩卷深思,不禁使人想起了唐宋传奇、明清小说,也会想起鲁迅的《阿Q正传》和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这原是一种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民族化群众化的小说”⑯。
《内奸》一开篇就凸显出非常鲜明的话本特征,开头即交代参与故事的人物:“这个故事的时间前后长达四十年之久,涉及的人物有两个将军,一个女同志和她的两个孩子,杨伪县长,土匪头子,日本鬼子的特务,美国教会医院的医生……就让我从那个不干不净的商人田玉堂谈起吧”⑰这种开头符合话本小说落笔在人,情节的演进史往往是人物遭际史的叙述特征。
不仅如此,方之进一步继承了话本小说第一人称全知叙述的特点,并有所创新。这种继承和创新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缩短叙事人与读者的距离。比如讲述告一段落后,叙事人说:“按说,本篇早该收场,再啰嗦下去,便有混稿费之嫌了。幸亏,来了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波壮浪阔,惊天动地,是个见灵魂、出文学的时代……像田玉堂这样的人物,自然少不了一段传奇式的的遭遇,这才使本篇得以续写下去”⑱。第二,发表议论,表达观点。比如“读者也许会奇怪,这个处理不伦不类,算个什么名堂?既未查清,怎能处理?既曰决定,哪有‘最后’?季头头官不官,民不民,怎能代表专政机关?——是的,不要说读者奇怪,连我作者也感到奇怪。然而,当那位‘永远健康’的赫赫尊神在位时,无奇不有,这又有什么可怪呢?”⑲第三,调整叙事时序,重新结构故事。比如“读者看到此处,不知有何感想?好动感情的也许会拍桌子,大骂那个‘白大褂’。好动理智的则会说:这要怪田老板自己不知趣……作者要请诸君且慢议论,我还得补叙一段资料。原来……”⑳。显然,方之对叙事人的这种处理方式不仅达到了让读者身临其境的叙事效果,而且也方便叙事人/作家自身的感情带入和观点表达。
方之在自叙中曾提及《内奸》两投不中的一个原因是“这篇作品又像小说,又像评话,作者还夹了不少议论,不大像小说的写法”,并针对这一指摘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评话是下里巴人爱听的,吸收点评话的手法,我看也不至辱没小说的高雅”。至于议论,他说:“本来《内奸》光叙不议也行,但是我意有未尽,想骂骂那些该骂者,并对‘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之类的先生开点小小的玩笑,所以夹带几句杂文,违反了‘小说作法’”,而作家本来就应该顽强地表达其所爱所憎,敢于表现自己的个性棱角,而不应该囿于所谓的“小说作法”㉑。于话本形式中融入杂文式的批判是方之对话本小说这一古典小说文体批判地继承。除此之外,《内奸》的语言表达通俗简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赵树理语言风格的继承。其实,除了方之,新时期初期不少作家,比如高晓声、古华等,他们的语言风格也都或多或少地显现出赵树理的影响,这或许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话本传统的隐形呈现。
不过,从方之的回应来看,《内奸》显现出话本小说的特征并非他的自觉选择,而是一种不自觉的创作惯性使然,这与他的小说创作受赵树理的影响有关㉒,也与他在“文革”结束后急于发表议论,表达观点的写作态度有关,毕竟,话本小说第一人称全知叙事对文本的直接介入令方之的直抒胸臆显得更为便捷和顺畅。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19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知识界普遍表达出一种现代性的焦虑,为了回应西方文学的现代性,中国作家祭起“寻根”的大旗,希望从民族传统中找到文学文化之“根”。虽然对传统的强调逐渐成为日后文化认同和小说创作的路向,但是包括话本在内的古典小说的文体意义在当时仍是盲点。直到1989年,先锋作家苏童写出了一个地道的“中国故事”《妻妾成群》,“力图在此篇中摆脱以往惯用的形式圈套,以一种古典精神和生活原貌填塞小说空间”,并且“尝试了细腻的写实手法,写人物、人物关系和与之相应的故事”。㉓
苏童在写作中也自觉地有意识地借鉴话本传统,只不过,他看重的是话本的“故事”性。话本原是在勾栏瓦肆中表演用的底本,为了吸引听众,故事往往取材于市井生活。妻妾争宠、夫妻怄气、逆子出走、金屋藏娇、恩客绝情……这些话本小说中常见的主题为苏童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而苏童也表现出对这些沉淀在中国人集体记忆中的故事元素某种“虚构的热情”。他的《妻妾成群》《红粉》《妇女生活》《园艺》等中短篇小说常常是对这些古老的中国故事进行剪辑、拼贴和重组之后的“旧貌换新颜”。苏童将短篇小说视为成年人的夜间故事:“每天入睡前读一篇,玩味三五分钟,或者被感动,或者会心一笑,或者怅怅然的,如有骨鲠在喉……培养这样的习惯使一天的生活始于平庸而终止于辉煌,多么好”㉔,正因如此,他的写作不以载道为己任,而是更为关注小说/“故事”自身。话本小说中活跃的都是些市井里的小人物,苏童笔下的也是。如果说说书人还存有一片“劝诫”的“道学心肠”,苏童则完全放弃了这个立场。他说:“文学中也有一个政治正确和道德正确的红线。我一直偷偷地钻过这条红线,钻出去写。判断好小说坏小说,公共文学道德在我这里不是一个判断系统。我所有的作品都在试图脱离这个公共的文学观,或者我刚才所说的社会进步观、崇高观”㉕。这种放弃使苏童的文本得以浸淫于世俗生活,在凡人琐事中抒发诗性。阿城在为中国古典小说溯源时认为,世俗性才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主要特征㉖。或许,正是在对世俗生活的描摹上,苏童接通了古典小说,尤其是话本小说的叙事传统,从而使他的小说具有了某种“古典”精神。
为了讲好这些“中国故事”,苏童借鉴了许多话本小说的叙事技巧,并有所创新,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文体风格。在情节设计方面,苏童突出了话本“常中见奇”的特点。他的中短篇小说或者是以一个平淡无奇的场景开头,经过处心积虑的铺垫和煞有介事的渲染,最终走向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比如《园艺》和《樱桃》;或者相反,让一个耸人听闻的开头,经过一惊一乍的铺排,换来一个平静如水的结局,比如《美人归来》;或者设置几个各自独立的叙述空间,通过人物关系和空间的转换实现波澜起伏的叙事效果,比如《另一种妇女生活》。情节设计中的巧妙构思使苏童小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在结构安排方面,苏童创造性地发展了话本小说的固定体制,将入话、头回、正话、篇尾诗发展成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叙事单元。在几乎每篇小说的排版行文上,这些叙事单元都以空行间隔,单元与单元之间基本以时间顺序连缀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由于每个叙事单元都由一、两个相对完整的情节构成,使得苏童得以在这些更小的彼此独立的叙事单位中尝试以不同的叙事人、叙事时间、叙事视角、聚焦点推动整个故事的发展。换言之,苏童将一部不断变换叙事人、叙事时间和视角的带有形式实验特点的现代小说,分割成若干个小的叙事单元,而每一个单元却分别由一、两个以传统的表达方式呈现出来的完整情节构成。由于排版行文上的空间间隔,叙事单元之间的转换也变得自然起来。这样的布局一方面便于叙事人轻而易举地调动叙述过程中的人物、情节和叙事时间,避免了平铺直叙的平淡无奇;另一方面则兼顾了读者的阅读习惯,便于读者跟上叙事节奏的变化,降低了阅读难度。
在语言风格方面,苏童赋予了话本小说的白描技法以工笔和色彩。同样是以形传神,苏童的文字并不像话本小说那样简洁节制。以《妻妾成群》描写颂莲初入陈家为例:“仆人们正在井边洗旧毛线,看见那顶轿子悄悄地从月亮门里挤进来,下来一个白衣黑裙的女学生。仆人们以为是在北平读书的大小姐回家了,迎上去一看不是,是一个满脸尘土疲惫不堪的女学生。那一年颂莲留着齐耳的短发,用一条天蓝色的缎带箍住。她的脸是圆圆的,不施脂粉,但显得有点苍白。颂莲钻出轿子,站在草地上茫然环顾,黑裙下面横着一只藤条箱子。在秋日的阳光下颂莲的身影单薄纤细,散发出纸人一样呆板的气息”㉗。这段文字将颂莲的衣着、发型、动作、表情一一展现,即不失白描的线条干净,下笔传神,又兼具工笔的精描细画,错落有致。除此之外,秋日的草地、傍晚的阳光、蓝色的缎带、苍白的面孔、单薄的身影……这样的描述令整段文字充盈着色彩。细致的线条和饱满的色彩很容易被读者还原成一幅充满质感的图画,虽然画中的元素并不复杂,其“象”外之意却颇令读者回味。王干将苏童的语言风格概括为“意象化的白描”,认为“苏童大胆地把意象的审美机制引入白描操作之中,白描艺术便改变了原先较为单调的方式,出现了现代小说具有的弹性和张力”㉘。无论是意象的审美机制还是白描的具体操作,都与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相关,苏童藉此确立起的叙述风格也成了他的个性标志。
在一次访谈中,苏童如此描述自己的写作转型:“打破故事,分裂故事,零碎的、不整合的故事,都曾经是我的叙述上的乐趣,但后来我渐渐地认为那么些没有出路,写作也是要改革开放的,要吸收外资,也不能丢了内资。从《妻妾成群》开始,我突然有一种讲故事的欲望。从创作心态上讲,我早早告别了青年时代,从写作手段上说,我往后退了两步,而不是再往前进。我对小说形式上的探索失去热情,也意味着我对前卫先锋失去了热情。而往后走是走到传统民间的大房子里,不是礼仪性的拜访,是有所图。别人看来你是向传统回归,甚至是投降。而我觉得这是一次腾挪,人们常说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不仅仅是人生观的问题,也是解决写作困境的一个方法。”㉙由此可见,对话本传统的借鉴是苏童摆脱创作瓶颈的自觉选择,同时也契合了他的创作态度和创作观念。
詹姆逊关于“文化变革”的研究包含这样一个观点:“每种艺术形式都负载着特定生产方式及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意义。当过去时代的形式因素被后起的文化体系重新构入新的文本时,它们的初始信息并没有被消灭,而是与后继的各种其他信息形成新的搭配关系,与它们构成全新的意义整体”㉚。因此,传统叙事元素能否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被激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人的取舍决断,以及这个全新的“意义整体”融入现代小说文体的方式。从赵树理到苏童,从“说”故事,到讲“故事”,不同历史时期作家对话本资源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汲取,一方面反映出不同时代文学观念的历时性变化,另一方面也激活了这一古老的文体形式,并赋予了其新的文学史意义。
注释:
①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四讲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中国小说史略·附录》,崇文书局2015年版。
②通常意义上的话本指的是说话人的底本,“话”即口头讲述的故事。当说话这种口头文学向书面形式转变,由供给说话艺人使用的底本变成供给读者阅读欣赏的文本时,它才成为文学意义上的小说。这种转变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书坊出于牟利,将话本汇集刊行;再是文人的润色加工大大加强了话本的可读性。本文使用的“话本”概念指的是其经文人润色后供给读者阅读的“文学意义上的小说”。相关论述见罗小东:《话本小说叙事研究》(第一章话本小说的文体生成),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
③郑振铎:《明清二代的平话集》,《郑振铎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334页。
④乃超:《大众化的问题》,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⑤凌濛初曾借说书人之口直言:“从来说的书不过谈些风月,述些异闻,图个好听。最有益的,论些世情,说些因果。等听了的,触着心里,把平日邪路念头,化将转来。这个就是说书的一片道学心肠,却从不曾讲着道学。”凌濛初:《三言二拍·二刻拍案惊奇(第12卷)》,齐豫生、夏于全主编:《三言二拍》,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
⑥宋阳:《大众文艺的问题》,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
⑦起应:《关于文学大众化》,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页。
⑧茅盾:《关于<吕梁英雄传>》,高捷等编:《马峰西戎研究资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⑨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56-166页。
⑩赵树理:《做生活的主人》,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45页。
⑪赵树理:《也算经验》,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98页。
⑫依照西方叙事学关于叙事视角的理论,第一人称叙事人参与故事,因而只可能是限知视角;不参与故事,没有固定观察位置的全知视角只能是第三人称。在现代小说中,第一人称且全知视角只能通过有意识地视角越界才能实现。然而中国古代话本小说借助模拟的书场情境,很自然地实现了。
⑬冯牧:《人民文艺的杰出成就——推荐<李有才板话>》,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75页。
⑭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⑮以赵树理的小说为例,类似于“第二天”“隔了两天”“离吃午饭还有一阵子”这样的时间提示,“正炕后墙”“柜子里上一格”“靠盒子前边”等等方位描摹对于听众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些提示能够帮助听众在脑海里串联起事件的发展过程,建构起清晰的空间方位。可是一旦用来阅读,这些篇幅巨大的琐碎交代就显得多余而难以忍受。
⑯海笑:《向读者推荐<内奸>》,方之:《内奸》,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8页。
⑰⑱⑲⑳方之:《内奸》,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页、第36页、第49-50页、第60页。
㉑方之:《“高抬贵手”及其他》,《内奸》,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9-81页。
㉒叶至诚:《曲折的道路》,《方之作品选·代序》,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㉓苏童:《寻找灯绳》,《纸上的美女:苏童随笔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页。
㉔苏童:《短篇小说,一些元素》,《苏童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
㉕苏童、张学昕:《回忆·想象·叙述·写作的发生》,《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6期。
㉖阿城:《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
㉗苏童:《妻妾成群》,《妻妾成群苏童代表作》,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㉘王干:《诉讼意象》,《花城》1992年第5期。
㉙周新民、苏童:《打开人性的皱折——苏童访谈录》,《小说评论》2004年第2期。
㉚伍晓明、孟悦:《历史—本文—解释:杰姆逊的文艺理论》,《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詹姆逊相关论述见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王逢振、陈永国译:《政治无意识》(第一章论阐释:文学是社会的象征性行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