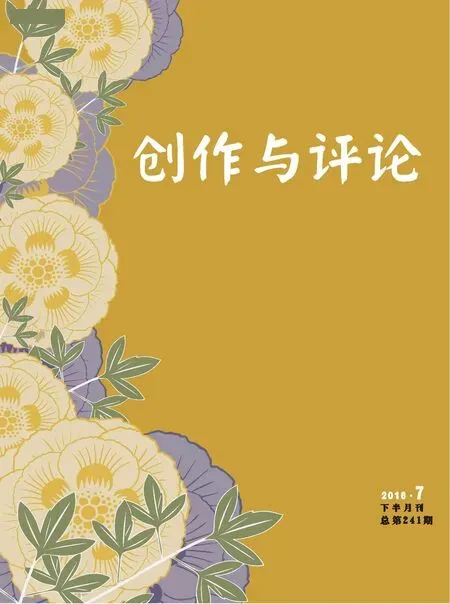中国新诗写作难度的缺失与重置
○罗小凤
中国新诗写作难度的缺失与重置
○罗小凤
放眼望去,当下诗歌界群魔乱舞,大量粗俗不堪、平庸至极的“伪诗”被奉为经典,许多追随者争相模仿,严重扰乱了诗坛的审美秩序和艺术标准,误导了中国新诗的发展方向,以至谢冕曾不无痛心地感叹:“新诗正在离我们远去”①。虽然马永波、马知遥、霍俊明、刘波等学者、诗人反复呼吁提高写作的难度,但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甚至遭来一些被批判者的抗议与谩骂。可以说,中国新诗的发展已经陷入困境,正如马知遥说:“目前是中国诗歌最黑暗的时间,面对一个个小丑和戏子以诗歌的名义表演,我以为是要写点文字了。”②而中国新诗之所以会陷入困境和“最黑暗的时间”,究其根源便在于诗歌写作难度的缺失。
一
诗歌写作难度的缺失,主要表现在诗歌立意、主题、选材上缺少难度,造成当下许多诗在内涵上呈现不可承受之“轻”;诗歌艺术上缺少难度,使诗歌陷入不堪入目之“平”的尴尬;诗歌语言上缺少难度,使诗歌陷入不忍卒读之“白”,由此,当下诗歌患上“轻”“平”“白”的“不良综合症”。
1.不可承受之轻
2010年初,韩少功在《文艺报》上指出,我们的文学正步入一个“无深度”“无高度”“无核心”及“没有方向”感的“扁平时代”,“文化成了一地碎片和自由落体”③。韩少功所针砭的文学弊病在当下诗歌躯体上的症状显现尤为突出,当代新诗在内涵上追求“躲避崇高”的境界,因而剥离了诗之灵魂与内涵,致使当下诗歌被逼入一方缺少深度、厚度、高度的死角,承受着不可承受之“轻”。
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躲避崇高的“零度写作”“个人化写作”等诗歌形态竭尽所能地发挥“私语”功能,结果导致诗歌写作陷入琐碎、破裂、阴柔、絮絮叨叨的泥淖不可自拔,出现了“崇俗”“崇私”或曰“祛魅”的诗歌倾向,其影响扩延至今。诗人们竞相沉浸于个人狭小的生活天地,彼此抄袭盗版着自恋与矫情的“小我”情绪,絮叨日常琐碎、俗事,暴露个人生活隐秘、鸡零狗碎,美其名曰“原生态”“新写实”,众多所谓之“诗”纯属日常生活琐碎的流水账式日志,或是新闻化叙述,成为原生态生活的“拍摄”与“放映”,未经过任何诗意的提炼、升华,毫无内涵与重量,“轻”不可耐。如一些诗句:“穿短裤/穿汗衣/穿长裤/穿拖鞋/解手/挤牙膏/含水/喷水/洗脸/看镜子/抹润肤霜/梳头/换皮鞋”(《零档案·起床》),只是简单地线性铺陈起床后鸡毛蒜皮的流水帐琐事,完全成为日常生活的文字放映,未传达任何诗的感觉或情感内涵;“毫无疑问/我烙的馅饼/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一个人到田纳西》)、“一只蚂蚁/另一只蚂蚁/一群蚂蚁/可能还有更多的蚂蚁”(《我终于在一棵树下发现》)、“天上的白云真白啊/真的,很白很白/非常白/非常非常十分白/特别白特白/极其白/贼白/简直白死了/啊——”(《对白云的赞美》)等完全是将随意的一句废话分行排列,毫无诗意可言,轻浅琐碎,遑论思想性、境界、情怀等审美价值。
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崇低”诗歌。“躲避崇高”的诗歌姿态彻底解构了诗歌的内涵诉求,伦理、道德、人性的底线一再被践踏和僭越,以“著名诗人”标榜自居的“码字工匠们”高举反文化、审丑审恶、虚无主义等诗歌幌子,把诗歌的门槛踩得一低再低,整个诗歌界完全呈现群魔乱舞、低俗不堪的景象,比如《我的垃圾人生》《你们把我干掉算了》《拉屎是一种享受》完全解构了“诗”的高雅性,充斥着的是不良不雅情绪;至于《每天,我们面对便池》《沈浩波与韩国情人的性爱之后16首》(组诗)《为什么不再舒服一点》《肉体》《压死在床上》《奸情败露》《为什么把我弄醒》《爱情是一种化学》等冠以“诗”之名的“杰作”简直恶俗难耐,一入眼便觉误吞死苍蝇,其轻其俗实在让人无法承受,难怪马知遥呼吁“诗人穿上裤子,请不要随地吐痰”。
然而,针对这类无高度、无内涵、无核心的“崇俗”“崇低”诗歌,竟有人大言不惭:“真正意义上的减法从此开始。减掉了什么呢?……(减掉的就是)意义(包括哲理),以及诗意(包括抒情)。当取消了意义的表达,诗意的流露,还剩下什么呢?……我回答说,剩下的就是‘诗’。”④这类“减法”逻辑导演的诗取消了生活与诗的界限,彻底瓦解深度,取消意义,形成了意义的空白,决不可能剩下的只是“诗”,而是无法承受之轻。
2.不堪入目之平
诗之为诗,主要面临“写什么”与“怎么写”的问题,后者于诗至关重要,但当下许多诗人都对诗歌技巧与艺术手法置若罔闻,一味地平面铺陈、流水账式记录,只是把日常生活语言分行排列,过于平庸化、平面化,根本无法抵达波德莱尔所言的“将奇异的诗艺铸造”的境界。
当下许多诗由于根本不讲究任何诗歌艺术,拒绝隐喻、象征、通感等诗歌表现艺术,而让物体仅仅成为物体,事件成为事件,诗被还原为生活本身,回到作为日常生活形态的本真状态,消解了诗的象征、隐喻蕴涵,平常、散淡而又随便地把日常口语分行排列,诗的传统审美特性却屡遭责难与贬斥,支离破碎,完全消解了诗歌作为艺术的审美特质,诗性特征模糊甚至完全消失,陷入“不堪入目之平”的泥淖,诗性缺失。如林混的《羊》:“每次回家/我都要给妈妈喂养的七只羊/添草/饮水/最近一次回家/羊圈空空如也/只剩下一些羊粪豆儿/上面盖着稀薄的小雪//妈妈说:/黑城建了个屠宰厂/羊涨价了/一律卖了”抛却了所有诗歌艺术手法与技巧,完全成为一小段日记的分行排列;沈浩波的《原谅》:“朋友中岛/在网上给我留言/说他又没工作了/让我再帮他找/我一下子感到有点绝望/这年头/到他妈哪儿/找去啊”则纯属分行排列日常生活细节的平面叙述。这些诗以及李伟《章子怡漂不漂亮》、春树的《漂亮朋友》、伊沙的《崆峒山小记》等诗均只是把日常生活中的某一事件或细节或感触以文字“传译”出来然后分行排列,不使用任何诗歌技巧,不讲究任何艺术手法,自身诗性消解溃败殆尽,如何成诗?
3.不忍卒读之白
口语诗歌的泛化,让诗歌话语失去了语言维度的最低限度,陷落于直白、低俗的不忍卒读之境,与诗之为诗的本体诉求相去甚远。
有人讽刺当下诗歌时认为只要学会使用回车键即可写诗甚至一夜走红为“著名诗人”,此情形确实并非耸人听闻。当下许多诗虽采取了分行形式,却完全是日常语言的复制,沦为大白话、自来水的口水诗、废话诗,用词简易、直白、随意,毫无诗性自律与难度,纯属文字游戏、语言垃圾。许多诗人笔下大量运用口语、大白话、方言、土语甚至俗语,解构了诗的审美特性,使诗成为了失去灵魂的粗鄙化、滥俗化语言。在他们眼中,无事不可入诗,无人不可入诗,无细节不可入诗,诗流泻成毫无节制的口语表达,如张进步的《有病》:“大街上的人都怎么啦/有人卖油炸臭豆腐/有人买油炸臭豆腐/有人卖夹馍/有人买夹馍/有人卖甘蔗/有人买甘蔗/有人卖水果/有人买水果/有人卖衣服/有人买衣服/有人开车/有人坐车/有人走路/有人走路还勾肩搭背……这些人是怎么了/有病啊”,简直不知所云,完全为揪住某个字眼而组词造句式地梦呓和胡言乱语。乌青的《对不起》、张小云的《憋吧》等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完全解构了诗歌语言的洁净、高雅、优美、含蓄等语言特质。如此诗歌语言,根本毫无诗性可言,正如评论家何言宏曾指出的,将一句大白话分几行来写,根本就不能算诗,即便硬要称之为诗,也只能是“口水诗”:“这些口水诗虽然你多读几遍,也能读出一点味道,但这已经完全没有了诗的美感。”
二
毋庸置疑,中国新诗病了,那么,如何为她治病呢?笔者认为,只有提高诗歌的写作难度,通过书写大情怀、大境界提升诗歌高度,增加文化蕴涵以增进诗歌厚度,锻炼诗歌技巧与语言以增加诗歌密度,让诗回归诗的本质属性,才能解决当下诗歌的“轻”“平”“白”等病症。
1.大情怀、大境界:诗歌高度的提升
诗,如何拒绝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呻吟,如何拒绝小女人、老太太的絮絮叨叨拉拉扯扯(杨匡汉语),如何拒绝心胸的阴暗与狭隘,从而让日常情感升华到大情怀大境界,让自己的作品直击当下的生存意义与生命意义,使诗承担起灵魂言说的本职责任,这是当下诗歌自我救赎的主要路径。虽然当下诗歌中出现了一些轻俗难耐、不堪入目、不忍卒读的作品,但历史的河流终将淹没这些诗歌渣滓,而一些在寂寞中坚守内心纯粹、守望人类精神家园的诗人必将迎纳诗歌史的青睐。笔者认为散文诗中近年来涌现了一批具有大情怀、大境界的作品,如一直在寻求诗歌艺术和诗歌精神“突围”的灵焚,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创作了思考人类生存命运以及人类生存与文化悖论反思的《飘移》《房子》《异乡人》等组章,而他近年发表的《女神》《生命》《冲动》《第一个女人》等诗里引入了神性维度和史性目光,试图抵达人类灵魂深处与人类存在本源之终极的思考。他还积极大力地倡导“意义化写作”⑤,多次在其诗论文章中传达如何让诗超越一般性的日常叙述或小感触的抒发,而抵达神性力量与终极意义的超验之境,显示了极为自觉的诗性自律与追求。耿林莽、刘虔、周庆荣、黄恩鹏、爱斐儿等诗人近年来的散文诗作品亦都抛却了日常小情感、小感触的抒发,而呈现出大境界、大情怀的开阔气象。自由诗中柏桦、欧阳江河、吉狄马加、蓝蓝、王小妮、李轻松、路也等诗人近年来自觉坚守诗之为诗的纯净领地,善于把个体经验提升为人类普遍经验的表达,显然这种诗歌新质值得继续发掘。如欧阳江河的《凤凰》“以神话叙述整合与重塑当代图景,反思了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生存境遇,揭示了当代世界具有的多层次、多维度、多侧面的立体化格局”,“获得了当代诗歌前所未有的包容性和扩展性”,被称为“当代史诗”:“具有史诗品质的《凤凰》也具有宏大叙事的特征,表现出立体化描绘当代世界,进而整体性诠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的努力”,“蕴含了一种世纪性以及全球化的使命意识”⑥,显然,《凤凰》在情怀、境界上显然是磅礴宏大的,超越了国别、民族、地域,而抵达全人类的“普遍价值”层面,然而,这种诗在当代诗歌版图上太少了。聊可安慰的是,“70后”诗人高世现的《酒魂》亦在做着这种努力,他试图创作《魂魄九歌》,而一万行的长诗《酒魂》是第一部,陈仲义认为此诗“上天入地,纵横捭阖”,“几达‘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境地”,“超强的主体人格建构,恍若苍茫寥廓中的大鹏扶摇,茕茕然独倨于珠峰之顶。精气神之丰沛,蔚然奇观。是屈骚大气长虹,太白翻江倒海之集合,凌虚高蹈而根系地气。因情志披沥、良爱侵透,故价值伦理视域胸怀,高屋建瓴”“峭拔自负,荡气回肠。大千世界之人、事、物驱遣裕如;乱世尘相之长嗥短啸,转手为云覆手为雨”“在为中国诗歌的阳刚登场,重新涅槃”,并以“旷世杰作,百年雄起”⑦八字概括,评价虽然有些过誉,却显示出高世现的诗已完全超越小情绪、小自我抒发的层面,呈现了大情怀、大境界。这些诗中大情怀的呈现,大境界的营构,无疑极大地提升了诗歌的高度,是当代诗歌努力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2.文化蕴涵:诗歌厚度的增进
中国当下的诗都是自我、个人情绪的发泄,是个人生活的流水账,很少将文化糅入诗行,因而当下诗歌在整体上是缺乏重量和厚度的。事实上,中国新诗要想在世界文学的场域里获得尊重与推崇,就必须拥有“中国品格”,而“中国品格”的形成主要便在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独特的文化蕴涵。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若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之河中撷取文化片段,将之写进诗歌,或以之作为诗歌底蕴或主核,必然能增进诗歌的厚度与重量,真正获得“中国品格”。
具体而言,一方面是历史文化。中国历史五千余年,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记忆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因而处处掩埋着历史,处处隐藏着文化。宇文所安认为“场景和典籍是回忆得以藏身和施展身手的地方,它们是有一定疆界的空间,人的历史充仞其间,人性在其中错综交织,构成一个复杂的混合体”⑧。若诗人们能在历史的场景和典籍中驰骋历史想象,深入历史与文化深处探寻历史遗迹,让回忆“施展身手”,追寻历史记忆,必然能增加诗歌的厚度。欧阳江河的《凤凰》便深入历史文化,“频繁指涉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中的凤凰主题,从庄子、李贺到李白、韩愈,捕捉了中国古人与凤凰聚合的一个个瞬间”⑨,呈现了中国文化传统中与凤凰主题相关的文化底蕴;高世现的《酒魂》亦成为“中华文化复兴立传立碑立铭之壮举”⑩,他在回答著名诗评家徐敬亚的问题时表示是“借酒还魂”“聆听历史”,全诗涉及历史人物超过1000个以上,文化底蕴深厚的地名、天文名词等都不计其数,都呈现出丰厚的历史文化蕴涵。只有让诗承载起渊深的历史文化,才能构塑出超越国别、民族、地域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中国品格”。
另一方面是民族民俗文化。这是指诗中要突出民族品格。中国品格是由民族品格汇聚而成的,各民族的文化品格积聚起来,构成中华民族这个大的民族的整体民族品格,因而,民族品格的彰显与“中国品格”的构塑是同声相应、相得益彰的。吉狄马加、扎西才让、鲁若迪基等诗人在这方面都做得不错,将自己民族的文化注入诗歌,构筑了“民族品格”,呈现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图景。
3.艺术技巧与语言:诗歌密度的加强
诗之成其为诗,诗的隐喻、象征、通感、夸张等艺术手法的运行显然是诗与其他文体的重要区别。诗是各种艺术因子立体聚合爆发的力量,优秀的诗作如戴望舒的《雨巷》、卞之琳的《断章》、顾城的《夜》、舒婷的《神女峰》、海子的《九月》等诗之所以令人反复咀嚼玩味而不厌,原因在于它们全面调动了系列意象的组合及象征、隐喻、通感、夸张等各种艺术手法,极力拓展开诗的语言空间与语意空间,尽意驰骋想象与感觉,从而展开灵魂话语的广度、深度、厚度与高度,达到诗歌的立体审美效应。有别于当下摈弃崇高、拒绝隐喻等弊病之诗,一些诗人自觉地探求诗的艺术。李轻松对诗歌艺术进行了多式样的尝试,她曾表明自己的诗歌艺术观念:“写诗是为了创造一段距离。与现实/我保持着一贯的疏离”(《写诗是一件美丽与苍凉得无法言说的事》)。她在其诗中调动各种诗歌艺术手法的力量创造诗与现实的距离,如她在诗中糅入戏剧因素,或尝试诗剧的创作与表演等,均是她为探索诗艺所作的努力。她的诗从不拒绝意象的隐喻或象征意义,“火”是其着墨颇多的一个意象,但决非停留于物理学意义的“火”,而是上升到了形而上层面。法国著名学者巴什拉认为“对火的凝视把我们带回到哲学思考的渊源”⑪,他说火“能解释一切的特殊现象”“一切迅速变化的东西就可用火来解释,火是超生命的”⑫。李轻松亦深谙“火”的力量,在她笔下,身体是一把火,精神是一把火,铁是火,血是火,语言是火,爱情是火,生命是火,死也是火,如《意外之美》中的“一页纸里的火”,《铁的幸存者》中“那些形而上的火,是你的另一种表情”,《铁这位老朋友》中“亲爱的铁,‘我火焰中的一部分’”,《还有多少铁可以重打?》中的“我的每一个毛孔都已张开/我的炉火蔓延成灾”,这些诗中“火”意象均携带着丰富的哲学蕴涵和深刻的精神暗指。李轻松对诗歌意象、隐喻、象征等艺术手法的“调兵遣将”促使其诗从不堪入目之平的尴尬中突围而出,显示了默默坚守的一批诗人们对诗歌艺术自觉探索的努力。
诗化语言的锤炼亦是增加诗歌内在密度的一条重要路径。虽然新诗是以言文一致的现代汉语入诗,但诗的语言与散文的语言并非毫无二致,遑论日常会话之语。诚如瓦雷里区分诗与散文时曾指出,如果散文的语言是走路,诗歌的语言就像跳舞。众所周知,跳舞讲究舞姿与步法,体态与风貌,需优美、艺术化,诗的语言亦如此,需要“诗化”,惟其如此,方能成为诗人传达灵魂话语的言说方式,成为灵魂话语的诗意载体。当下诗歌以口语入诗,这是无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但口语作为诗歌语言,并非真如日常说话的口语般直白随意。欧阳江河曾敏锐地指出,如何处理这种口语,如何使之水乳交融地渗透到各种视觉的、知觉的、幻觉的书面语言之中,如何使之经过诗人的生命、灵魂的智慧时带出更多样的语言光芒,投射出更多复杂的语言境界,形成更有力的语言气候——这也许是完成现代汉语诗歌革命的一个关键。因此,无论粗细精芜都入诗,将口语理解为俗语、土语、大白话,只能建构虚假的诗歌语言,让诗歌沦落溃散。2002年,阿毛的《当哥哥有了外遇》一诗曾引发中国诗坛的“阿毛现象”,并引起诗歌界有关“新诗有无传统”“口语诗是不是诗”的激烈讨论,被列为“2004年最重要的诗歌事件之一”。在此“现象”和“事件”中,《当哥哥有了外遇》被列为阿毛口语诗的代表作,并几乎成为阿毛的注册商标。但事实上,阿毛的诗歌语言并非如那些不可卒读之白的作品中所铺陈的口语,她对语言拥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并善于把这种敏感转化成一种创造性话语,通过单纯质朴而深入浅出的语言拓展诗歌的可能性,在张力性语言中挖掘生活本质,虽平白如话却极具陌生化效果和感染力。阿毛的语言充满悖论的张力,如“一群被割了耳朵的听众”“丝绸的喉咙”(《诗朗诵》)、“一出生就老了”(《引力》)、“一个是天使,一个是天使一样好看的魔鬼”(《早春的唯美》)、“我出发,我返回,/我是自己的他乡”(《春天来了》)等都是从普通的日常生活择取事件和场景、细节、感觉,却以非常状态呈现于诗行,把读者的感觉从习惯式的“嗜眠症”中唤醒。阿毛的诗歌语言讲究大词小用,虚词实用,化深为浅,化难为简,以语词新的、突兀的结合糅合矛盾的语义,表现平常事物的不平常,达到陌生化效果。反讽、隐喻修辞等语言技巧亦为阿毛之所擅长,其诗由此呈现出丰富的内在张力,显示了以口语入诗却抵达诗化语言的可能性。
诗既为诗,必然有其诗歌语言的语言特质,如跳跃性、非逻辑性、写意性,以及含蓄、凝练、雅致等,诗语是生活语言的淘洗、提炼、升华,需要在不断的锤炼、锻造和打磨中形成。
窃以为,中国当下诗歌的发展只有提升写作难度,增加诗的高度、厚度、密度,方能彻底治疗当下诗歌的“轻”“平”“白”等顽固性、高难度“综合症”。
注释:
①转引自南帆等:《新诗的现状与功能》,《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1期。
②马知遥:《诗人穿上裤子,不要随地吐痰》,《艺术广角》2010年第3期。
③韩少功:《扁平时代的写作》,《文艺报》2010年1月20日。
④何小竹:《加法与减法》,《6个动词,或苹果》,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⑤灵焚:《意义化写作——论周庆荣的创作》,《诗刊》2010年5月上半月刊。
⑥⑨吴晓东:《后工业时代的全景式文化表征——评欧阳江河的〈凤凰〉》,《东吴学术》2013年第3期。
⑦⑩陈仲义语:http://www.poemlife.com/revshow-68897 -958.htm
⑧[美]宇文所安著,郑学勤译:《追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2页。
⑪⑫[法]安德列·巴利诺著,顾嘉琛、杜小真译:《巴什拉传》,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119页、第116页。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