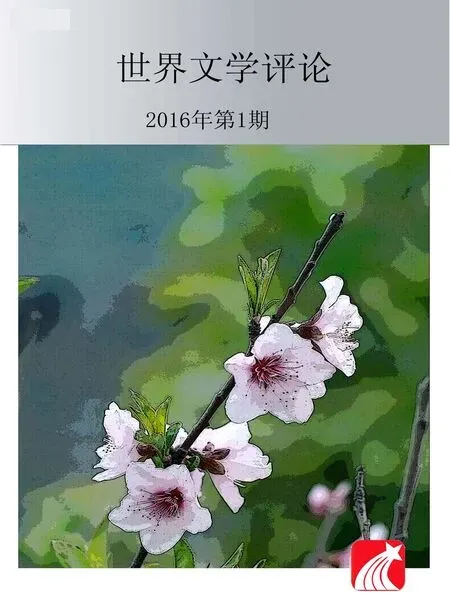现代人的生存历险与信仰追寻之路
——再探勒克莱齐奥《诉讼笔录》
彭云涛
现代人的生存历险与信仰追寻之路
——再探勒克莱齐奥《诉讼笔录》
彭云涛
前人对勒克莱齐奥长篇小说《诉讼笔录》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对西方现代文明批判的主题阐释上。本文则从文本的细节入手,围绕主人公亚当在物质生活中的生命感受和生存历险以及精神生活中无意识之下的自我异化,来展开对他信仰追寻之路的剖析,由此挖掘文本之下的深层内涵。这一全新视角的解读将为《诉讼笔录》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发。
勒克莱齐奥 《诉讼笔录》 生存 异化 信仰
Author:Peng Yuntao is from the faculty of arts inWuhan University,research area isWorld Literature.
《诉讼笔录》是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让·马里·古斯塔夫·勒克莱齐奥(Jean Marie Gustave Le Clézio,1940-)在23岁时发表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这部作品1963年发表,当年即获得了法国重要文学奖——勒诺多文学奖,并很快被视为堪与加缪的《局外人》相提并论的作品。有学者从中看到了方兴未艾的“新小说”的影子,而其中疯狂、梦幻的意象,则让人感受到行将结束的超现实主义的余波(1966年,超现实主义之父布勒东去世)。一个23岁的名不见经传的尼斯小伙子的作品可以让人同时联想到法国最重要的三大文学思潮,勒克莱齐奥确实可以说一步登天,一下子进入了经典文学的殿堂。[1]
该小说讲述了一个被视为疯子的现代知识青年亚当·波洛的日常生活、所见所闻、行为方式和处事态度。初读之下,旋即被扑面而来的无聊、颓废、失落乃至绝望的气息所感染、触犯,这也正符合了勒克莱齐奥的创作初衷:“依鄙人之见,所谓写作与交流,就是有办法能让任何人相信任何事。而只有通过连续不断的,一连串的冒昧之笔触,方能动摇读者冷漠的城墙。”①(勒克莱齐奥 II)但倘若耐下性子读上第三遍、第四遍,便慢慢感到凌乱芜杂的情节、看似戏谑的语言正在从眼前退去,我们会被作者对待主人公的生存历险和信仰追寻之路所表现出的严肃态度所感动。
前人对这部作品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对现代西方文明批判的主题阐释上,具有代表性的如柳鸣九附在《诉讼笔录》中文译本之后的介绍性文章——《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极端厌弃》;紧随其后,不少文章专门探讨西方现代文明对人的异化、物化等问题;还有学者从勒克莱齐奥小说的寓言性、生态性、人道主义等方面着手。也有文章反弹琵琶,客观指出这部小说的不足之处,如张公善的《洞见与盲视:勒克莱齐奥〈诉讼笔录〉简论》。好的作品都具有多维阐释的张力,不同时代也会有不同的解读,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丰富着作品的内涵。关于这部小说隐约透露出的现代人精神的无可寄托以及信仰追寻的艰辛和苦涩至今还鲜有人提及。在此,笔者从文本细节入手,围绕主人公亚当·波洛的在物质生活中的生命感受和生存历险以及精神生活中无意识之下的自我异化,来展开对他信仰追寻之路的剖析。
一、恐惧与逃避:亚当·波洛的生命感受与生存历险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任何时代的所有小说都关注自我之谜。”[2]勒克莱齐奥的《诉讼笔录》也不例外。小说正文一开篇就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名叫亚当·波洛的生动而典型的“nobody(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形象,“他像是个乞丐,四处寻找阳光,有时坐在墙角,几乎不挪身子,一呆就是几个钟头。他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双臂派何用场,通常让它们顺着躯干晃动,尽可能不碰一下。他好似那些染病的动物,动作挺灵巧,藏在洞穴里,严密戒备着危险,戒备着来自地面的危险,它们以自己的皮毛为掩护,几乎与地面浑为一体,难以分辨”(勒克莱齐奥 1)。在这短短几行字里,作者便用一种夸张的感觉化书写向我们勾勒出一个精神萎靡、肢体慵懒、缺乏生气的现代人形象,这不禁让人想起乔伊斯笔下的布卢姆、加缪笔下的默尔索等文学形象。虽然作家用这种状态来概括现代人略显片面,但用与古典文学作品中独立张扬、英勇不羁的英雄们相比,他们仍具现代人所独有的代表性。现代文学中为何会出现这一奇观?这种精神状态到底源自什么?它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生存历险呢?
人类从为自己不穿衣服而感到羞耻的那一刻起就赤条条地从大自然中分离了出来。孤独,便成了每个人的宿命。现代科学技术在看似便利高效的表面下制造出人与人触手可及的亲密假象,实则是无情地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而每个人又好似依附在现代社会网络之上的一只蚂蚁,根本无法脱离这个社会,这就产生了不同于古典作品的“自我之谜”,它常以个体在社会中无立锥之地而感到荒诞、恐惧为反映。作为一个敏感的知识青年,亚当对这种分裂状态的感受力远比大众庸人要深刻得多,在他看来,“生活不是逻辑,它也许就像某种意识的无规律现象。一种细胞疾病”(勒克莱齐奥51),他时常幻想出阵阵莫名的害怕和恐惧,如在给米雪尔的信中,他写道:“对我来说,地球已变得一片混沌,我害怕恐兽,直立猿人,尼安德特人(吃人的),更不用说恐龙,迷龙,翼指龙,等等。我害怕山丘变成火山。或者北极的积水融化,导致海水上涨,将我淹死。我害怕下面海滩上的人。沙滩正变成流沙,太阳正变成蜘蛛,孩童正变成龙虾。”(勒克莱齐奥 10)这些臆想的恐惧感将他团团围住,他甚至在恐惧感中找到了让他镇静的力量。
在恐惧感的催使下,他孤独一人躲避到被弃的山顶小屋中,他“喜欢恐惧、慵懒和奇异的情调,憋不住去挖地穴,并忍辱负重,悄悄地藏到洞穴里去,就像儿时那样,钻进两片破旧雨布里”(勒克莱齐奥12),“他没有一天不来创造这番奇迹:他的神话感被激发到了极点,常常用石块和瓦砾把自己埋起来;他恨不得倾尽世上的碎石和垃圾,将自己掩埋其内,占据物质、灰烬、卵石的中心,渐渐地化为一尊雕塑……它就像一粒种子,好似一颗树籽,深藏在土缝里,等待着天赐鸿福,吸水发芽”(勒克莱齐奥55)。所以有论者说,在亚当身上体现出“人不仅仅异化成一种物体,更是异化成更为本源的东西——物质。一个是物体化,一个是物质化,虽然都可以称为‘物化’,但却大相径庭。前者形象地表达出现代文明对人的扭曲变形,后者则是对现代文明的极端弃绝”[3]。该论不无灼见。可以说,与勒克莱齐奥笔下诸如妓女、失学儿童、黑奴等社会边缘人不同,亚当的逃避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自我边缘化”,他是在深感生活无意义时,主动选择逃离这个“文明世界”,试图斩断与现代社会的种种联系,以求获得内心平衡。
亚当的尝试无形中夸大了现代社会生活的无意义,人毕竟是社会性的动物,况且,从一开始与米雪尔保持书信往来就已经暗示了他并非真正渴望与世隔绝的孤独,而是在冥冥之中寻找一种更加真挚、热烈的交流。他去动物园,看到的是被饿瘦、被压抑、被戏弄的野兽;他在河边偶遇淹死的男人,只感受到民众们冷漠的眼光;他与米雪尔做爱,没有感受到生命融合的快乐,只有解释不清的隔阂;他真诚地同医学生谈话,却被视为精神病患者,医生的诊断更是简单粗暴……这种茫然而无望的寻找与发现,不断加剧着他与外部环境之间的隔离感。“他突然感到厌倦,也许是为活着而厌倦,为不得不时刻提防这形形色色的危险而厌倦。与其说是他的结局,倒不如说是他下决心去死的时刻。他为这迟早有一天总要发生的奇特变化而恐惧,这一变化将迫使他再也不去想任何东西”(勒克莱齐奥119)。逃避现实的极致便是奔向死亡,当死亡的念头占据他,对死亡的预期和想象必将导致对当下生活的遗忘。所以,多数论者认为亚当是对现代文明的绝对厌弃,这看似不无道理。但故事的最后,当他与医学生辩论无解时,“他喉咙里连一声也哼不出”,在生无可恋的世界里,他无处可逃,尽管他也曾等待着一个“猝不及防的末日”,做一个彻彻底底的逃脱,但他更“在拼命地活着”,规划着接下来的生活,体味着眼下的平和,“他被长久地固定在这张床上,固守着这四壁、窗条,固守着明亮的金属和鲜艳的油漆所构成的这份和谐”(勒克莱齐奥 271)。克尔凯郭尔说,恐惧与精神的觉醒有关,他认为恐惧是很重要的宗教现象。精神越少,恐惧越少。同时,恐惧还是堕落的结果。只要还有罪,就不可能没有恐惧,这是面对上帝的恐惧,面对最高审判的恐惧。但是恐惧应该被克服,完善的爱就能驱赶恐惧。[4]因而,仅仅将亚当的逃避视为对现代文明的绝对厌弃恐怕是不准确的。
二、禁闭与反叛:无意识之下的自我异化
任何对于外部环境的反应,都是人物心理状态的显现;任何心理状态的显现也都反映于人物的行为方式之中并作用于人物所处的外部环境。亚当的消极倦怠自然引发他对外部环境的避让、退却。但他的逃避与一般意义上的逃离有所不同,我们且看下面的话:“亚当似乎独一无二,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像这样死去,真正地死,悄悄地死;他仿佛是时间唯一的一个生者,在不知不觉地死亡,不是死亡肉体的堕落与腐烂,而是消亡在矿物的冻结之中。”(勒克莱齐奥 56)“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等待着这一时刻,而他,亚当·波洛,他来到了,他突然来到了,成了世间万事万物的神圣的拥有者;他无疑是他所属种类的最后一位幸存者,确实如此,因为这一种类已近末日。”(勒克莱齐奥 66)可见,亚当·波洛的逃避看似消极、孱弱,实则蕴含着觉醒者的力量,这种力量让他成为这个世界茕茕孑立的“唯一的一个生者”、“最后一位幸存者”,促使他担起寻找超越人与人之间互动的一种全新的生存路径的重任,这种生存路径以逃避和禁闭为形式,内蕴着有力的反叛。
在自我禁闭的凝视中,他“成了青苔,成了地衣。差不多就要成了细菌和化石”(勒克莱齐奥56)。他也能潜心“加入了最微不足道的笼中部落,与蜥蜴、老鼠、鞘翅目动物或鹈鹕打成一片,消受午后剩余的时光”(勒克莱齐奥 62),当游客为绒猴好坏争论不休时,亚当道出令人不快的真实:“这不漂亮也不坏,这是只狨猴。”可以说,动物园是现代文明的一大景观,人们为满足自己的畸趣,将原本自由生活于大自然中的飞禽走兽关押在局促的空间中供己观赏,更将驯服它们视为人类的智慧,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式的傲慢,使人类将自己与动物视为主客关系,忘却了用一种平等的眼光去看待动物,忘却了动物不因为人的爱憎而改变自身是动物的事实,亚当的话正是一个冷峻的警示,也是对人类常识的反叛。
现代文明把人从前现代的血缘共同体和地域共同体中抽离出来,还原为由工具理性和物质欲望主宰的原子式个人[5]。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日益淡漠。当亚当在充斥着戴墨镜行走的路人身上寻不见温暖时,他选择跟踪一只狗以摆脱他所属的那个可恨的人类,当现代人“准备在那摆满花束和果篮的橡木餐桌、丝绒窗帘、双人床和印象派复制画之间度过人生”(勒克莱齐奥 85)时,他却想象着某天可以像狗一样在漫天的灰尘中做爱。相比之下,狗自在宽广的生活空间和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远比人类建造的与自然相隔离、充满局限的天堂要有吸引力得多。动物叙事的根本宗旨无疑是扩展人的生命体验,促使人类生命与动物生命之间能够更自如地交流,至少使人不要继续对动物生命存在物种歧视,并自觉地从对动物生命的无限制的蛮横和暴力中撤退出来,使动物生命有可能从人类造成的漫无边际的苦海中挣脱出来,使人与动物生命之间恢复较为亲密的关系。[6]当亚当·波洛与一只老鼠共处一室,他嘲笑老鼠的处境:“首先,你是一只老鼠,落到了人的世界中,世上到处都是人居住的破房子,有陷阱,有枪支,要的是老鼠的性命。其次,在老鼠普遍为黑色的世界中,你却是一只白鼠。这样一来,你就滑稽可笑了,又是一条死罪。”(勒克莱齐奥 91—92)老鼠这种异物般存在于世的状态不也是亚当自身处境的一个写照吗?在对抗白鼠的过程中他莫名其妙地咒骂道:“该死的,该死的猫!”这话从未有人冲着这类动物咒骂过,笔者也深以为奇。实际上,亚当·波洛此时已无意识地将自己分裂成肉身残暴的人与虚弱胆怯的老鼠,当意识处在两个深渊之间便会产生道德和个性的分裂,他的咒骂既是对自己作为残暴的人类如同捕鼠的猫的咒骂,又是化身老鼠后对强者不卑不亢的对峙。这只受虐的白鼠,“它就要去天堂,带着神奇的欢乐,部分路程靠游泳,部分路程靠飞翔。它将在地球上留下赤条条的身子,让体内的血一滴滴流尽,让这血成为地板上那一神圣蒙难地的永久标志”(勒克莱齐奥 96)。此时,死亡于白鼠而言已然不是折磨、痛苦,反而成为一种解脱和不屈的骨气。白鼠的死有了和道成肉身的耶稣为承负人类罪恶的牺牲同样的不朽色彩,这是对世间公义问题的一种象征性解决,更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有力反叛。
既然人的物化不因个体的否定而消逝,那么,人应当怎样面对这种物化呢?亚当想到一条“物质沉醉之路”,以求采用物质的同一动力来战胜物质,“他以自我创造达到自我毁灭。他在演奏一种交响诗,最终的结局不是美,丑,理想,幸福,而是忘性,虚无。他不久将不复存在。他不再是他自己”(勒克莱齐奥 171—172)。可见,亚当的感觉方式已经超出了柳鸣九所说的原始化、降格化、非人化、物化,更达到了一种无我化状态。事实上,对现代文明中包括自己肉身的绝对弃绝说到底是一种近乎病态的自我保护,但这条“物质沉醉之路”毕竟只是将问题推上极致的一种可能的思考,细读之下,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亚当·波洛对现实有着自己的期许。
三、批判与呼唤:信仰追寻之路永恒
在小说序言中,勒克莱齐奥称其所运用的语言是由冒牌的现实主义对话体渐变为古董学究式的夸张笔触,这是因为在他看来,现实不是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作家们用简单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所能概括的,它比我们看到的要复杂得多。因而,揭示和解释人类存在的全部现实仅靠现实主义的平铺直叙、心理描写是不够的,有必要利用各种知识、各种手段去帮助我们认识和表现真实的世界。他所谓的“冒牌的现实主义”破除了现实主义所倡导的社会决定论,使小说主人翁与社会环境呈现出一种格格不入的关系。亚当是人类始祖,作者借此之名,正是为了突出基本人性与现代文明有冲突的地方。②作品后半部分以亚当的公众演说和医患交谈两件事为主线,亚当古板的学究式语言看似疯癫、毫无逻辑,实则隐含着作者当时渴望介入社会、改变现实的迫切心理。③亚当与加缪《局外人》中墨尔索的不同之处在于加缪以一种哲理化的手法,通过对墨尔索杀人过程和动因的冷静追述,揭示现代人存在荒诞的事实;而《诉讼笔录》则是以一种荒诞的手法,通过叙述亚当的游荡和疯癫,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现代理性社会,具有深刻的反讽意味。那么,《诉讼笔录》深刻的反讽是否仅是导向反讽本身,还是另有期许?难道处于现代社会生存困境之中的人就只能任其沉沦,看不到一点光了吗?
逃避现实、向往不可预知的事物本身就是虚妄,它们除了增加对生活的厌倦情绪并不能解决实际的困苦。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说:“一个不成熟的理想主义者会为理想悲壮地死去,而一个成熟的理想主义者则愿意为理想苟且地活着。”事实上,亚当在自我植物化、动物化乃至无我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否定现实生活,他对现代文明心存恐惧,但不厌恶,他渴望看到摘下墨镜后人与人之间温情的对视,他喜爱海滨遛狗的女郎、动物园贩卖零食的老妇,甚至在与米雪尔谈论战争时,他说:“我,亚当,说到底,我还处在战争之中。我不愿走出战争。”(勒克莱齐奥 46)可以说,亚当怪诞行为的背后是对这个日益符号化、同质化的社会现实的批判。因为在这个人口过剩的世界,已经没有人会真正去在意一件细小的事情、一个具体的个人,“更重要得多的是整个宇宙。二十亿男女同心协力,创建事业,建设城市,制造炸弹,征服空间”(勒克莱齐奥 150)。人们在一个炼就统一的熔炉中经受煎熬,为着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伟大事业而劳碌终生,属于每个人的时间被物质世界夺走,个体生命的意义被抹去。当每一个人的面孔变得愈发模糊成为一个个无名的符号,当真实的生存环境被眼花缭乱的物质所遮蔽,由此构成了一个德波所谓的“景观”社会和波德里亚所谓的“类像”世界。它们共同构筑了一个自我衍生的封闭体系,封堵了我们与现实的通路,人生活在这个物化和符号化的虚拟世界里,就丧失了与世界本性和自我本真的联系[7]。而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个性和价值,是拥有自然之心的人,文明的生命力也存在于这参差多态之中。亚当·波洛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疯癫者,他拒斥同一,自成差异一体,反而成了“世间万事万物的神圣拥有者”、“最后的一位幸存者”,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确是一个“成熟的理想主义者”。
现代社会的同质化倾向直接导致了自我的丧失,而这又必然伴随着道德的沦丧。因为真正的道德,必须也只能建立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之上。众人围观淹死的男人并将之视为难得的消遣,这其中潜藏的精神暴力欲望即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道德沦丧。亚当街头的演讲正是对道德沦丧带来的人际关系冷漠的批判和反思。他控诉现代化科技发明的电视之类的“魔鬼”,尽管它们为人类创造却控制着人类,使人类“永远处在分隔的境地”,忘记了“我们大家都一样,都是兄弟”;他呼唤着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真挚交流,要学着在一个人的世界里说话,他说:“去吧,讲一讲,到处去讲。宣传福音。”(勒克莱齐奥 209)因为那些讲述出来的最美丽的福音才是每个人内心深处渴求的甘霖;他渴望看到“我们最终又合抱起双手,低声祈求无情的神祗”,永远保持对大自然的谦卑以及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情谊。人生苦短,智慧无涯,苏格拉底在两千多年前就慨叹“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而现代人却傲慢地宣称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在与医生谈话中,亚当以自己一个聪明同学的遭遇为例,指出现代人认知感受能力的严重缺陷,根本不能理解真正智者的精神境界,有很多事物实际上都是在现代人的悟性之外的,对此,现代人不仅不认识自己的局限,反而把这种局限与偏狭视为当然的真理与谬误的分界线,把自己悟性之外的事物斥为荒唐。(勒克莱齐奥 283)由此,呼唤敬畏之心的回归。亚当的话不仅仅是一篇篇尖刻抨击现代人类和工业化社会的檄文,更欲为人类心路指明方向——真诚、善良、美好,这是我们来时的路,未来也必然沿着它走下去。
在一个外在决定性具有极大摧毁力的现代社会,能勇敢地提出质疑,站到社会的对立面去看待问题,寻求人的可能性还能是些什么,这本身已经十分可贵,但勒克莱齐奥不满足于此,他还要在怀疑主义的土壤上开出一支信仰的花朵。他曾批判道:“西方文化太过专横。它最大限度地强调了自己的城市和科技文明,并且压抑着其他形式的发展,例如宗教虔诚和对于自然的感知。在理性主义的名义下,人类文明这一未知的部分被严重压抑着。”[8]信仰的缺失使现代人成了精神的漂泊者。亚当在这一背景下体验到爱与恨的茫然、目的和手段的悖论,他在逃避现实的同时也在自我戕害,禁闭之中体验绝对的孤独和恐惧,蕴含着英雄献祭的冲动;他曾想过自杀却又放弃,因为自杀是容易的但对减轻现实的苦难毫无裨益,也不可能换得上帝的出场,因而他选择一种自我下沉的方式以分担现实的苦难。在给米雪尔的信中亚当曾这样写道:“我并不自豪,可我希望他们判我一点什么罪,以便我能以自己整个躯体去赎生活的过错;倘若他们侮辱我,鞭笞我,往我脸上吐唾沫,那我总算有了个归宿,我最终将信仰上帝。”(勒克莱齐奥103)别尔嘉耶夫在《论人的使命》中指出:对生命的精神理解总是有一个前提,即不但要有人的生命,而且还要有神的生命。精神生命总是以另外一个最高的东西为前提,生命向它运动,向它上升。最高的善和价值不仅仅是生命,而是精神生命,是向上帝上升的生命,不是生命的量,而是生命的质。精神生命根本不与心理和肉体生命对立,根本不否定后者。精神生命意味着心理和肉体生命进入另外一个意义上的存在之中,意味着它们获得更高的质,意味着它们向高处的运动,向超生命、超自然、超存在、超神的东西运动。“生命”对我们而言可以成为最高价值、最高善的象征,价值自身、善自身是真正存在的象征,而存在自身则只不过是终极秘密的象征。[9]
在与医生的辩驳中,亚当指出,作为造物主的上帝并不是他感兴趣的所在,但对他而言,上帝填补了一个“可怖的、难以承受的空白。介乎于生命层次之间……介乎于两个层次、两个时间之间”(勒克莱齐奥 255),这是一种妙不可言也无须多言的层次。他在生命中体味与上帝建立起的联系,对信徒而言,“重要的不是知道,而是知道自己已知”(勒克莱齐奥 256),以自身的存在而存在。有论者认为,“以存在而存在”是对人类极端功利化生活的彻底否决与悬置。作者对人类的这种拯救意图还是那条还原之路。本来在人身上共存着物性—人性—神性,它们是一种递进关系。人类作为有意识的物种,理应将自己逐步提升,而不是退化到物的地步。[10]然而,亚当·波洛所谓的“存在”并非止于完全意义上的自然的、物质的存在,它更是一种不去强求证实上帝是否存在而呼唤心存上帝的思维上、精神上的存在,他在失落之时低吟的两句诗歌:"Tis ye",tis your estrangéd faces,That miss the many-splendoured thing.(这是弗朗西斯·汤普森《天国》中的诗句,喻指基督教信仰,可译为:正是你们,正因为你们别过脸去,才看不见那五光十色的宝贝。)(勒克莱齐奥 154)正是对内心不灭的信仰之光的召唤。抑或说,这种退化和堕落本质上是从存在向非存在的复归,就如前文所引别尔嘉耶夫的话那样:“存在本身则只不过是终极秘密的象征。”重要的不是物质存在本身,也不是返回自然,而是要直面人性内在矛盾,找到每个人内心中不死的信仰。况且,当我们习惯于个体命运、自我意义被贬低、被忽视,有意识地关怀并强调每一个具体个人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信仰的立足点。真实的信仰不正是从一个个无可寄托的内心世界中产生的吗?亚当向我们传递出这样一个真谛:人就是这样一种对自己不满,并且有能力超越自己的存在物。
注解【Notes】
①勒克莱齐奥:《诉讼笔录》,许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页码,不再一一做注。
②许钧、张洁在答《楚天都市报》(2008年11月10日C40版)记者问时讲述了勒克莱齐奥的创作初衷:他写这部书,看似是对主人公的诉讼,实际上是对现代文明所隐含的某种疯狂性的诉讼。
③勒克莱齐奥在与中国译者许钧交谈时曾说:“写作这样一部书,与当时法国的政治与社会状况有关,也与我个人的经历有关。当时法国正经历阿尔及利亚战争。作为一个青年,随时都有可能被征召入伍。我对自己的前途、对社会的前途,感到迷茫,从心理上说,也有些害怕和不安。写这样一部作品,当然也涉及我对社会的一些看法。在某种意义上看,也是一种政治介入与社会介入。”(许钧:《勒克莱齐奥的文学创作与思想追踪——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载《反叛、历险与超越——勒克莱齐奥在中国的理解与阐释》,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72—373页。)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董强:《勒克莱齐奥的世界视野》,载《反叛、历险与超越——勒克莱齐奥在中国的理解与阐释》,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页。
[2]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
[3]张公善:《洞见与盲视:勒克莱齐奥〈诉讼笔录〉简论》,载《反叛、历险与超越——勒克莱齐奥在中国的理解与阐释》,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4页。
[4]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神与人的生存辩证法》,张百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5—46页。
[5]汪树东:《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6]汪树东:《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8页。
[7]卢志博:《物质的遮蔽和反物质主义的“战争”——勒克莱齐奥“战争”评析》,载《反叛、历险与超越——勒克莱齐奥在中国的理解与阐释》,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4页。
[8]卢志博:《物质的遮蔽和反物质主义的“战争”——勒克莱齐奥“战争”评析》,载《反叛、历险与超越——勒克莱齐奥在中国的理解与阐释》,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7页。
[9]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神与人的生存辩证法》,张百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6页。
[10]张公善:《洞见与盲视:勒克莱齐奥〈诉讼笔录〉简论》,载《反叛、历险与超越——勒克莱齐奥在中国的理解与阐释》,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3页。
[11]梁工主编:《圣经与欧美作家作品》,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
The studies of Le Clézio's Novel Le procès-verbal were focused on the criticism of westernmodern civilization.Revolving around the hero Adam'sexperience of life,survivaladventure inmaterial life and the unconscious self-alienation in spiritual life,thisarticle expand the analysis of hisway to faith from the detailsof the text,so as to dig up the profoundmeaning of this novel.Review ing Le procès-verbal in this innovative perspectivew ill provide beneficial guidance and inspiration to the study of thisnovel.
Le Clézio Le procès-verbal survival alienation faith
彭云涛,武汉大学文学院,主要研究世界文学。
Title:Adventures in Surviving and the Pursuitof Faith forModern People—A Review of Le Clézio's Novel Le procès-verb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