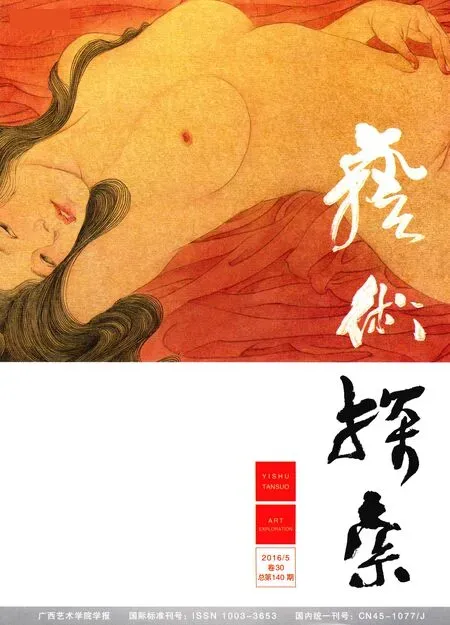清代平阳府地方音乐活动考述
孙豪
(文化部 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北京100012)
清代平阳府地方音乐活动考述
孙豪
(文化部 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北京100012)
地处中原腹地的山西平阳府自古有深厚的礼乐传统,有关地方音乐的记载见于明清以来的各类方志。通过对此类史料的勾稽,可以管窥清代平阳府地方音乐的基本面貌。其形式多样,内涵丰富,大体分为两类:一是各级官府举办的各种国家祀典礼乐活动,如文庙释奠、关帝庙祭、文昌庙祭、乡饮酒礼、救护礼等。二是由民间社会自发组织的各类民俗音乐活动,如婚嫁、丧葬、社祭、迎春、庙会及其他节庆等。两类活动中包含有乐舞、鼓吹、笙歌、戏曲等音乐表演形式,它们在有益互动中呈现了既鲜明对立又高度融合的形态特征,共同组成了清代平阳府地方音乐文化的整体。
平阳府;方志;官方祀典音乐;民间礼俗音乐
清代平阳府是地处山西南部的中级行政区划。其拥有深厚的礼乐传统和丰富的音乐文化,可视为清代中国北方音乐文化的代表。对其进行综合研究具有认识清代中国地方音乐文化的典型意义。目前,学界尚未对清代平阳府地方音乐活动作体系化的整理与描述,仅有个别研究对其有关内容进行了零星记录。
笔者考察了平阳府地境现存的祠庙、寺观、戏台、碑刻等音乐文物以及地方志、笔记、小说等文献中有关音乐活动的历史资料,重点是清代及民国时期成书的平阳府及其境内各州、县的志书,如(康熙)《平阳府志》等,共计30余种。通过对大量析出史料的整理分析,本文将清代平阳府地方音乐活动概括为文庙释奠、关帝庙祭、文昌庙祭、乡饮酒礼、宾兴、救护、婚嫁、社祭、迎春、庙会及其他节庆等类型。按照社会性质和表演形态的不同,它们又分属官方祀典和民间礼俗音乐活动两大类。
一、官方祀典音乐活动
官方祀典音乐活动,是指由官方主导的包含音乐表演在内的各种祭祀、典礼活动。此类活动主要以国家机关执行、国家礼法约束、国家财政支撑为基本特征。清代平阳府所设府、州、县三级行政机构,具备完成各类官方祀典活动的资格与义务。由其主导完成的各类祀典音乐活动,在清代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如按性质与功能属性划分,官方祀典音乐活动可分为祭祀与庆典两大类。其中,祭祀又主要是指为“神”举办的各类仪式;而庆典则主要以“人”为主题。
(一)文庙释奠
文庙释奠,亦称“丁祭”,是清代全国各府、州、县学校每年都要按期举办的祭祀“先师孔圣”的礼仪活动。在国家礼典系统中,文庙释奠活动属吉礼范畴。清廷颁布《大清通礼》有《春秋释奠先师孔子之礼》一章,规定了各地庙学释奠礼仪规程,平阳府连同其境内各州、县学均须按制执行该礼。
释奠活动时间为每年“春秋二仲月上丁日”[1]227,地点在平阳府及其境内各州、县学文庙。受祭者主要为孔子及其弟子、后人,其神主分列大成殿正配位、东西十哲位及东西庑先贤、先儒位。执事人员有献官、执事官、乐舞生等,由供职于府、州、县衙的“长官”及在各学校肄业的“学弟子员”来充当。[2]197
据《大清通礼》及《平阳府志》等典志所载,释奠活动的行礼规格为“三跪九叩”,主要包括“戒誓”“省牲”“习礼演乐”“瘗毛血”“迎神”“三献礼”“饮福受胙”“撤馔”“辞神”“望瘗”“燕飨”“旅酬”等仪节,[1]224-231
且大多仪节均包含一定的音乐表演。
文庙释奠活动中的音乐表演主要有乐舞、鼓吹、钟鼓、笙歌四个类型,其中又以乐舞表演为核心内容。表演者均为熟习祭孔雅乐的学弟子员,其大多受过严格的礼仪及音乐培训。
乐舞是歌唱、舞蹈、器乐三位一体的综合性表演艺术。文庙释奠乐舞是由歌工登歌、乐生奏乐、舞生佾舞三类音乐表演共同组成的有机体。另外,乐舞可以分为“文舞”与“武舞”两类。舞队的排列也曾先后出现“六佾”与“八佾”两种方式。[3]2538乐章先后出现过《大成乐》与《中和韶乐》两套,均由六个乐章组成,分别在迎神、初献、亚献、终献、撤馔、送神等仪节中唱、奏。其中,《中和韶乐》为清廷所颁国家祀典用乐,其规定地方各府、州、县文庙释奠乐章为《昭平》《宣平》《秩平》《叙平》《懿平》《德平》。[4]60乐舞表演所用到的乐器有麾、金钟、玉罄、鼓、搏拊、柷、敔、琴、瑟、排箫、笙、箫、笛、埙、篪、鼗鼓等,舞器有节、羽、籥、干、戚等;每类数件,按规定的方式排列使用。[5]81-84
鼓吹乐,也称“导引乐”,是释奠活动中“张榜”“戒誓”“迎牲”“迎神”“送神”等环节的音乐表演,主要作引导、仪仗之用。①(光绪)《山西通志》卷七五《学制略上·释奠》:“戒誓生捧神牌置案,舁起引导,乐鸣钟鼓,设誓牌于戟门外。”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点校本,第5193页。鼓吹乐的表演以器乐为主,在队列行进时演奏,有时也加入歌唱,所用乐器为“笙、笛、籥、管、箫、鼓、板各二”,所奏器乐曲目为《朝元歌》②(光绪)《山西通志》载:“《朝元歌》,盖燕乐之流。按其声字,则太簇之羽,俗称中吕调者也。其器则笙、笛、籥、管、箫、鼓、板各二,未祥所自。祭日迎神、送神用之。至祭前乙丙日送祝、迎牺牲、粢盛及省牲、视馔别用《迎凤辇曲》。今《迎凤辇曲》久废,凡导引并用《朝元歌》。”第5234页。。
钟鼓乐,是由悬挂于大成门两侧的大成钟、大成鼓(也称晋鼓)及摆放在大成殿中庭前的建鼓单独演奏或相互组合演奏的音乐,在仪式中起警戒、发令等作用。在表演方式上,其又可细分为晋鼓独奏、转班鼓独奏和钟鼓齐奏三种,按清廷所颁《转班鼓谱》击奏。
笙歌乐,是在释奠活动中“燕享”与“旅酬”两个环节的音乐,主要为琴、瑟、笙、箫、编钟等乐器的组合表演形式,表演曲目多为《鹿鸣》《鱼丽》《南山》等乐章。[6]50-52
释奠活动中所有音乐演奏均需遵循国家礼典对乐律、乐调、乐谱及乐器的各项规定。其中,乐制、律制由康熙皇帝钦定,乐器、舞器等由雍正皇帝颁定,乐章乐谱由乾隆皇帝御制,三者并载于《大清会典》等清代政书。
(二)关帝庙祭
关帝庙祭,全称作“关圣帝君庙祭”,是清代全国上下各级官府每年举办的祭祀“关圣帝君”关羽的礼仪活动。如同文庙释奠,清代平阳府地方关帝庙祭属于吉礼范畴,其礼仪亦须遵循清廷中央的各项规定。
关帝庙祭的时间为“春、秋仲月”(农历二、八月),具体日期由承祭者“择吉”后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核并批准决定。此外,农历五月十三日为关帝圣诞日,各级官府也要在每年此日举行祭祀关帝仪式,称为“特祭”③(光绪)《山西通志》卷七二《秩祀略上·中祀》载:“关圣大帝庙,府、厅、州、县岁以春秋仲月致祭。又五月十三日特祭。祭时并祭三代。其解州庙及祖墓,亦同日祭。”第5039页。。
祭祀关帝的地点为各地关帝庙。清代,全国范围内关帝庙建置颇多,众多关庙中首推平阳府解州关庙,因其所处之地山西解州(今山西省运城市)为关帝祖籍,故此庙祭祀活动受到相当重视。雍正二年(1724年)以前,解州隶属平阳府,故该地区关帝庙祭在平阳府地方祀典音乐活动中具特殊意义。
参加关帝庙祭活动的主祭、承祭、陪祭等人员均由地方官员来担任,礼生及乐舞生由地方各学弟子员来充当。依典制,其祭礼规格与文庙、社稷同,皆为“三跪九叩”礼,祭品、祭仪与京师略同。《清史稿·吉礼·文昌帝君》及(民国)《乡宁县志·秩祀考·关帝庙》均有相关记载。
直省关帝庙亦一岁三祭,用太牢。先期承祭官致斋,不理刑名,前殿印官,后殿丞、史,陈设礼仪,略如京师。[3]2542
关帝庙,在城内中街,旧日察院基址。春秋仲月,部颁吉日致祭,又五月十三日特祭,均用太牢。[7]91
关帝庙祭的具体仪节在清《通礼》《会典》等及平阳府地方志书中均有记载,主要有“致斋”“眂割牲”“备器”“迎神”“初献”“亚献”“终献”“撤馔”“送神”“望瞭”等。除宣读祝文内容不同之外,其余环节与文庙释奠礼基本相同。[2]237-238
关帝庙祭音乐表演的核心内容为乐舞,由各省府州县遵照清廷所颁礼典具体施行。除此之外,还应当有鼓吹及其他音乐表演的参与。④按:虽然文献资料没有显示关帝庙祭是否用及鼓吹等乐,但依文庙释奠例推论,应当存在此类音乐的表演活动。关帝庙祭乐舞为“干戚
之舞”,属“武舞”性质,舞队规格为“六佾”①《清会典》卷三六《礼部》载:“唯关帝庙乐舞,京师用八佾,直省用六佾。”北京:中华书局,据光绪二十五年石印本影印,1991年,第316页。,六列排列。
乐曲为《中和韶乐》,咸丰四年(1854年)颁于各府、州、县,②(光绪)《山西通志》载:“咸丰四年,加封‘护国保民’四字封号,升入中祀,颁发祝文乐章,舞用干戚,余仪并同文庙。”第5039页。共六乐章,分别在迎神、初献、亚献、终献、撤馔、送神等仪节中唱、奏。(光绪)《山西通志》载其乐章具体为:迎神,奏《格平之章》,无舞;初献,奏《翊平之章》,有舞;亚献,奏《恢平之章》,有舞;终献,奏《靖平之章》,有舞;彻馔,奏《彝平之章》,无舞;送神,奏《康平之章》,无舞。[8]5039-5042
关帝庙祭音乐表演所用乐谱、乐器、乐律、乐调等均同文庙释奠,遵循清廷御制相关礼典。
关帝庙祭作为一种官方祀典,在清代平阳府地方官方祀典音乐活动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其仪节、陈设、人员及音乐等多方面与文庙释奠有所相似,故可与之相互参考。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官方举办关帝庙祭以外,民间举行关帝祭祀活动也非常普遍,二者在活动内容及形式上均构成鲜明对比。
(三)文昌庙祭
文昌庙祭,全称为“文昌帝君庙祭”。其与文庙释奠、关帝庙祭相同,是清代平阳府及其境内各州、县官府每年如期按制举办的祀典活动,属吉礼范畴。
所谓“文昌”,最初是指天上文昌宫六星,并无“帝君”称号。后来所谓神人“文昌帝君”,实指东晋张育。张育为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374年)蜀王,为抗击前秦苻坚而战死。后人为纪念他,在梓潼郡七曲山建祠,将其尊奉为“雷泽龙王”。因张育祠所在之地梓潼郡七曲山本有梓潼神亚子祠,所以后来人们又将张育祠与同山的梓潼神亚子祠合称为“梓潼神张亚子祠”③《明史》卷五〇《礼四·诸神祠》载:“梓潼帝君,姓张,名亚子,居蜀七曲山,仕晋战殁,人为立庙祀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08页。。由此,张育被称为“张亚子”。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张亚子”被敕封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3]2542-2543专司文事,主科举考试。于是,后人又将其简称为“文昌帝君”,与天宫文昌六星同名。
文昌帝君庙祭每年共有三次,春、秋仲月各择日致祭一次,二月初三日(文昌帝君诞辰日)特祭一次。(光绪)《山西通志·中祀》载:
文昌帝君庙,府、厅、州、县岁以春秋仲月致祭,又二月初三日特祭。同日并祭后殿三代,仪同关帝。[8]5044
致祭地点一般是当地文昌帝君庙,特殊情况可以例外。《清史稿·礼志三·文昌帝君》载:
直省文昌庙有司以时飨祀,无祠庙者,设位公所祭之。[3]2543
文昌帝君庙祭在祭器、祭仪、人员组织等方面与文庙释奠和关帝庙祭相类,唯在祝文、乐舞表演等方面有差异。
文昌帝君庙祭祀音乐表演亦以乐舞表演为核心。其乐舞规格为“乐六奏,文舞八佾”[3]2543,所奏乐曲为《中和韶乐》,共六乐章,时有舞蹈与之相配,具体曲目为:迎神,奏《丕平之章》,无舞;初献,奏《俶平之章》,有舞;亚献,奏《焕平之章》,有舞;终献,奏《煜平之章》,有舞;彻馔,奏《懿平之章》,无舞;送神,奏《蔚平之章》,无舞;望瞭,奏《蔚平之章》,无舞。[8]5044
同关帝庙祭一样,文昌帝君庙祭不仅是官方祀典音乐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民间普遍存在的礼俗音乐活动。文昌帝君在民间不仅被认为是掌管“文运”的尊神,而且还被认为是可以助人升官发财的“禄星”。信仰体系下的多重功能促使民间对文昌帝君庙的祭祀活动更加繁盛。
(四)乡饮酒
乡饮酒是清代在全国范围内,由各府、州、县官府每年举办的一种宴饮礼仪活动,属嘉礼范畴。乡饮酒礼发端于上古时期的民俗。在周代时,其已被确立为一种具有“明长幼之序”功能的典礼,④《礼记·射义》载:“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参见(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卷六〇,《十三经清人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438页。并成为历朝实施礼教的重要手段之一。清廷对乡饮酒礼非常重视。《清史稿·礼志八》载:
乡饮酒礼:顺治初元,沿明旧制,令京府暨直省府、州、县,岁以孟春望日、孟冬朔日,举行学宫……雍正初元,谕:“乡饮酒礼所以敬老尊是非曲直,厥制甚古,顺天府行礼日,礼部长官监视以为常。 ”[3]2655
乡饮酒礼的仪程在清初时沿明旧制。后来到乾隆年间,清廷曾对其仪节及乐章等活动内容有过重新整顿。《清史稿·礼志八》载:
乾隆八年,以各省乡饮制不画一,或频年阙略不行……五十年,命岁时举乡饮毋旷。每行
礼,奏《御制补笙诗》六章。[3]2655

图1 乡饮酒礼图
乡饮酒礼的举办时间为每年孟春望日(正月十五日)、孟冬朔日(十月初一日),地点在平阳府及其境内州、县所有学校的明伦堂。届时,由各地官员宴请当地较有威望的民间人士。(光绪)《翼城县志·风俗·乡饮酒礼》载:
每正月望、十月朔,儒学斋长择荐绅士有齿德者为耆宾,署其名而举之学,学详之县。先期下启。至日,则令尉论训,皆诣明伦堂宴饮焉。扬觯、读法、酬酢、拜跪,一遵典礼,亦古尊高年、重有德之遗意也。[9]438
在乡饮酒活动中,所有被邀请的宾客均须具有一定的社会身份,并经过官方审核。参加宴会的人员均须按规定的位置就坐(图1),①清廷颁发《乡饮酒礼图式》及相关规定,并载于(道光)《太平县志》卷六《典礼·乡饮酒》:“主:知县,如无正官,佐二官代位于东南;大宾:以致仕官为之,位于西北;僎(耆宾):择于里年高有德之人,位于东北;介(介宾):以次长,位于西南;三宾:以宾之次者为之,位于宾、主、介、僎之后;除宾、僎外,众宾序齿列坐,其僚属则序爵;司正:以教职为之,主扬觯;礼生:以老成生员为之。”凤凰出版社编选《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52),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影印本,第333页。不同身份的宾客由不同等级的官员招待,②(乾隆)《蒲县志》卷四《学校·乡饮仪注》载:“大宾一人以乡大夫致仕有德行者为之,介宾一人以庠生文行兼茂者为之;耆宾一人以耆民有德望终身、不入公府、不犯刑科者为之。先期,儒学议定,上其名于县,县报可,卜吉,肃启明伦堂设宴几筵。百执事者咸在,考钟击鼓。大宾,正官主之;介宾,教官主之;耆宾,佐僚主之。”成文出版社编选《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四二九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影印本,第242-244页。执事人员由教谕及学弟子员来充当。
乡饮酒礼主要包括“迎宾”“读律诰”“供馔案”“献宾”“宾酬主”“撤馔案”“谢恩”“送宾”等仪节,各仪节中均有一定的音乐表演,表演者为学弟子员充任的乐舞生。
乡饮酒礼仪式中的音乐表演主要有三个类型:钟鼓乐、笙歌乐和鼓吹乐,分别在读律诰、宴饮和送宾三个环节中表演。表演形式与文庙释奠中的钟鼓乐、笙歌乐和鼓吹乐(导引乐)相同。③关于钟鼓乐、笙歌乐和鼓吹乐的表演形式,参见本文第一章第一节“文庙释奠”部分。整个表演中,以“笙歌乐”为核心。曲目有《鹿鸣》《南陔》《鱼丽》《关雎》等,由国家统一颁布。所有音乐技术均遵循《律吕正义》,乐谱为《御制补笙诗乐谱》。《清史稿·礼志八》中《乡饮酒礼》条载:
其制,献宾,宾酢主人后,酒数行。工升,鼓瑟,歌《鹿鸣》。宾主以下酒三行,司馔供羹,笙磬作,奏《南陔》,间歌《鱼丽》,笙由庚。司爵以次酌酒。司馔供羹者三,乃合乐,歌《关雎》。[3]2655
清代平阳府各地官方对乡饮酒礼非常重视,并以常办此盛会为荣。这种情形可从各方志文献的详细记载中略见一斑。如(乾隆)《续修曲沃县志》有《乡饮》一卷记录了该县历任“大宾”“介宾”“耆宾”姓名及出身,多达数百人;[10]462-465(乾隆)《乡宁县志·礼俗·乡饮仪注》云:“乡宁治万山之中,风俗淳朴,秀者肄诗书,朴者勤稼穑,如乡饮酒礼,岁岁举行。”[11]78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清代平阳府地方乡饮酒活动的盛行情况。
(五)宾兴
宾兴,是清代各地官方为当地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举办的宴会礼仪活动。这种宴会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乾隆)《蒲县志·学校·宾兴》载:“《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后世宾兴之名昉此。”[12]242
宾兴礼与乡饮酒礼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乾隆)《乡宁县志·礼俗·宾兴》认为:“以乡饮酒之礼,礼而宾之是宾兴,即乡礼酒,无二也。后世乡举里选之法不行而以士子科举为宾兴,遂岐④据文意,疑为“歧”字。。”[11]80据有关学者
考证,清代,全国范围内,各府、州、县举办宾兴礼的活动非常普遍。①参看毛晓阳《清代宾兴礼考述》中对清代全国范围地方志中相关“宾兴”文献的搜集整理。《清史研究》2007年第3期。当然,平阳府也不例外。
宾兴活动大多在有科考之年才会举办,具体日期由举办者根据科考时间商卜决定,地点一般在县学公堂,由各级地方官员宴请科考士子。(道光)《太平县志·典礼·宾兴》载:
每遇乡试年七月初旬,择吉延科试,取录入围生员赴公堂。设宴演剧,酒数行且起,各有馈赆。[13]332
宾兴活动举办时,宴饮场所一般会张灯结彩,大堂门外要设仪门,搭“天桥”“月宫”。宴饮之后,考生们会随同官员一起“登龙门”,到“月宫”折桂,以祝愿科考成功。这些仪式后,官员会送考生到东门外,饮饯酒揖别。(乾隆)《乡宁县志》载:
在大堂悬灯,结彩设宴,仪门外搭蟾宫,大门外搭天桥、龙门。席毕,各生折桂,官送至东门外,饮饯酒三杯而别。[11]80
在宾兴活动的整个过程中,有两种音乐表演形式:鼓吹乐与戏曲音乐,分别用于引导和宴饮。(乾隆)《蒲县志·学校志·宾兴》载:
每岁当大比博士弟子员、高等应举者。县官卜期开宴,鼓乐导送,彩旗前引,县官率僚属肩舆送出东郭门外。[12]242
又(道光)《太平县志》载:
每遇乡试年七月初旬,择吉延科试,取录入围生员赴公堂。设宴演剧,酒数行且起,各有馈赆。为步月桥于仪门内,乐引诸生折桂枝而上,至大门揖别。[13]342
宾兴活动举行的主要目的是“崇隆士子之心”[13]342,体现国家对文教的重视。如(乾隆)《乡宁县志》所说:
以乡饮酒之礼,礼而宾之,是宾兴,即乡礼酒,无二也。后世乡举里选之法不行而以士子科举为宾兴,遂岐。其礼于乡饮酒之外所谓“龙门”“月宫”,皆谐俗以美观耳,然其崇隆士子之心,非有异也,故于乡饮酒外另叙宾兴礼。[11]80
宾兴活动的举办既有官方的推动主导,又有官方的财力支撑,它显然应当属于官方祀典音乐活动的范畴。但是,令人颇为不解的是,在地方盛行的官方庆典,竟没有被记录在清代国家礼典之中,这种现象耐人寻味。没有国家礼典强制执行的礼仪活动却得到地方官员的普遍认同,里面有深层的原因有待挖掘。或许真如《乡宁县志》所言:宾兴礼是乡饮酒礼衍生的产物,故国家礼典仅以乡饮酒礼记之。然而,方志中既然将乡饮酒与宾兴分别列述,则反映出二者之间的差异,其中众多微妙有待深究。
(六)救护
救护,是清代官方在日食、月食发生时组织举办的祭祀日、月的仪式,属于军礼范畴。救护礼为顺治元年(1644年)国家定制,康熙十四年(1675年)又经调整。《清史稿·礼志九》载:
日食救护:顺治元年,定制,遇日食,京朝文武百官俱赴礼部救护。康熙十四年,改由钦天监推算时刻分秒,礼部会同验准,行知各省官司。[3]2671
救护活动的举办时间要由精通天文的钦天监人员预测,并及时通知将遇日、月食的地方官府。参加仪式的人员主要为地方各级官员、阴阳官及执礼学弟子员。《清史稿》载:
直省遇日、月食,各按钦天监推定时刻分秒,随地救护。省会行之督、抚署,府、州、县行之各公署,并以教职纠仪,学弟子员赞引,阴阳官报时。至领班行礼,则以督抚及正官一人主之。上香、伐鼓、祗跪,与京师救护同。[3]2671
平阳府地方部分州、县志书亦有对救护礼仪节的相关记载。(道光)《太平县志·典礼·宾兴》载:
日食预行,所属官司前期设香案于露台,金鼓列仪门,乐人列台下;设拜位于露台上,俱向日。至期,阴阳生报:日初亏,各官衣便服,行三跪九叩首礼,班首官上香毕,正官击鼓三声,众鼓齐鸣。及报“圆”,鼓声止,各官衣朝衣,行三跪九叩首礼。月食救护同前仪。[13]332
救护礼的仪节较为简单,时间同日食、月食持续时间,所以一般不会太长,次数也不会多。但它仍是平阳府官方祀典礼的组成部分,其中单纯的鼓乐表演也是官方祀典音乐的一种样态。
二、民间礼俗音乐活动
民间礼俗音乐,是平阳府地方各种民间礼俗活动中所表演的音乐。本文所谓“民间礼俗”,主要指“民俗”事项中有关“人生仪礼”和“岁时民俗”两方面的内
容;①民俗,是指“产生并传承于民间的、具有世代相袭特点的文化事项”。民俗事项可分为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人生仪礼、信仰民俗、岁时民俗、社会组织民俗、民间文学七类。参见苑利、顾军《中国民俗学教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年,第1页,第15-16页。而“礼俗”一词,是沿用平阳府部分地方志书中“礼俗略”“礼俗”的提法,②(民国)《永和县志》卷五为《礼俗略》,(乾隆)《乡宁县志》卷十二为《礼俗》。用以同民俗事项中非人生仪礼及岁时节令民俗的部分相区别。民间礼俗活动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民间大众主导、民间习俗约束及民间财力支撑三个方面。清代平阳府地方民间礼俗活动非常丰富,其中不乏包含音乐表演的活动事项。
(一)婚嫁
婚礼,是为婚龄男女结合而举办的人生仪礼,在国家礼制层面,属嘉礼范畴。虽然历代官方都对社会各阶层婚礼有礼法约束,但民间婚礼主要是受民间习俗的影响,凸显“俗”的性质。
所谓婚礼仪式,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婚礼应当包含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项仪节,在古代称为“六礼”。狭义的婚礼,则单指亲迎之后的“拜堂”(也称“合卺礼”)仪式。拜堂是整个婚礼的核心环节,一般在黄昏吉时举行,“昏礼”之名由此而生。
清代平阳府地方民间婚礼仪节与古代婚礼大体相同,但有一些出入,主要体现在“六礼”不完备上。(康熙)《平阳府志·风俗·昏礼》载:
昏礼各处不同,大约六礼之中,仅存其四:问名、纳采、请期、亲迎而已,亦有不亲迎者。[14]726
又(乾隆)《临汾县志·风俗·昏礼》:
婚礼有六,临邑仅存其四,问名、纳采、请期、亲迎而已。[15]33
问名、纳采、请期、亲迎仍是清代平阳府地方民间婚礼的主要环节,但缺少了“六礼”中的纳吉与纳征两个部分。在剩下的四个仪节中,亲迎最为核心。至婚礼当日,男方家需有年长者陪同新郎前往女方家迎娶新娘,女家设宴款待,男方将新娘迎回自家后即可拜堂成亲。第二日,新娘拜见公婆,新郎还要到女家谢亲。至此,婚礼可算完成。(乾隆)《乡宁县志·礼俗·昏礼》:
至期,父醮其子加之冠,邀年长亲戚同往迎。女家设筵款待。奠雁毕,赠婿花红。导妇归,同拜天地、祖先。次日,拜舅姑及诸尊长。男家诣女家,曰“谢亲”,用陪客引新郎拜丈翁母。[11]82
音乐在清代平阳府地方民间婚礼中的使用较为普遍,并且非常重要。据(民国)《永和县志·礼俗略·昏礼》,该地方民间婚礼中“若无音乐,女家间有不允其迎娶者”[16]278。
民间婚礼中表演的音乐主要有鼓吹和戏曲两种形式。前者一般用于亲迎,起导引、仪仗作用,也有用于宴飨、催妆的情况。(民国)《襄陵县新志·礼俗·昏礼》载:
迎亲之日,以昏为期,婿坐肩舆。亦有乘马、坐车者。鼓乐导引诣女家。至则拜谒岳父母暨妇党之尊长者,依次行礼毕,登筵,作乐催妆。宴毕,婿先归,俟于门;妇坐彩轿,鼓乐导引至门,随婿入,同拜天地,行合卺礼。[17]128
而后者则主要用于宴会,为宾客娱乐、为宴会助兴之用。(康熙)《平阳府志》载:
(昏礼,)张延演剧,富家率以为常,无复古者昏不举乐之意。[14]726
清代平阳府地方民间婚礼音乐的表演者为吹鼓手、戏班等民间艺人。从当下的民俗遗存来推断,清代平阳府地方民间婚礼中音乐表演所用曲目、剧目应当比较丰富,表演方式一般比较灵活。
(二)丧葬
丧礼是以家庭为核心的亲友组织为亡人举办的仪式活动。在礼制层面,其属凶礼范畴;在民间,其为传统习俗。
民间丧礼的举办一般在死亡事件发生后三个月之内,具体日期由丧主请阴阳生“卜期”而定。丧礼仪式大多在丧主自家庭院内外临时搭建的“灵堂”举行。参加丧礼活动的人员主要包括亡者或丧主的亲友、乡邻以及其他执事人员。
清代平阳府地方民间丧礼仪节主要包括初终、袭殓、成服、祭灵、出殡、至葬、虞祭、祥襢等,但平阳府及其境内各州、县在这些仪节的称谓上会略有差异。在整个丧礼仪节中,祭灵、出殡是较为重要的部分。(道光)《赵城县志·风俗·丧礼》载:
人死,迁尸于床,沐浴更衣,不紟不绞。即卒奉尸夷于堂,棺实以棉,并柏叶纸裹之,属死者之齿及爪皆实之(生时所脱落者)。次日,设灵床,成服,主人斩衰苴杖,奠无算,哭无时,赙者
以米饭。七日,主人复设奠,鼓于门,亲属皆至,曰“做七”。每七皆如此,四十九日乃止。将葬,择启期、营兆宅。葬之前日,主人设奠,亲属各至祭,主人哭踊无数,伤举柩也。明,迁柩就舆,吊者皆执绋,妇人哭送于路。致圹,瘗刍马纸衣,乃窆。主人哭踊无数,哀亲之在外也。既窆,反祭于殡宫,即古虞祭礼。墓成,祀后亲属皆拜墓,庆地魂之得所归也。嗣是而练、而祥、而禫,皆如制。居丧之日,不饮酒,不食肉,不御内,哭必尽哀,孝之至也。[18]79-81
平阳府民间丧礼中音乐表演大多在祭灵、出殡、宴会等环节,主要有鼓吹乐、戏曲音乐、僧道法乐等形式,表演者为吹鼓手、戏班、僧人、道士等民间艺人。在所有表演形式中,以鼓吹乐的表演为最普遍且最重要。(道光)《赵城县志》载:
葬日必多延客,奠物取丰恶非,送殡必以鼓乐;非是谓之“黑葬”,为不孝。贫者力不能给,多停葬者。[18]80
据(道光)《直隶霍州志·风俗·丧礼》云,此类鼓吹乐的表演形式与婚礼并无不同:
赵邑喜庆者,置鼓于门,遇父母丧亦如之。[19]121
除了鼓吹乐,还有部分家庭会请民间戏班表演戏曲音乐,目的在于“愉尸”。(康熙)《平阳府志·风俗·丧礼》载:
扮剧愉尸,牢不可破。至于出殡之日,幢幡遍野,百戏具陈。力不能备,则以为耻,宁停柩焉。[14]726
僧道法乐也是丧礼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光)《太平县志·坊里·丧礼》载:
以至逢七斋僧,朝祖作乐,饰为美观。倘力不能备,有十余年停柩者。[13]293
又,(雍正)《临汾县志·风俗·丧礼》载:
亲丧,逢七日,或诵经,或致祭不等。富家每七必举,过七犹有,五十日、六十日,以及百日后始已。中户首七、尽七致祭,三七延道,五七延僧,率以为常。[20]687
僧道不仅表演诵经音乐,甚至还有“佛剧”的表演。(道光)《赵城县志》载:
他若延僧道诵经、演佛剧,犹失礼,当尽摈之。[18]79
作为一种传统习俗,平阳府地方民间丧礼在仪式的主要环节上和国家礼制没有矛盾,但在许多细节方面同国家礼典发生冲突。这体现了民间与官方两个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文化差异。
(三)社祭
社祭,是以“社”为单位的民间组织所举办的祭神活动,是一种历史久远的民间风俗。“社”在古代是指土地神,社祭多与祭祀土地、祈福禳灾有关。
清代平阳府民间社祭活动较为普遍。时间一般在夏、冬两季“社日”,由村社人员参加。其主要活动事项是陈牲醴祭神,目的在春为“祈”,在秋为“报”。在祭祀活动中,一般都有戏曲、鼓吹等音乐表演。一方面为了娱神,同时也为了娱人。(康熙)《平阳府志·风俗》载:
岁时社祭,夏冬两举,率多演剧为乐,随其村聚大小隆杀有差,盖犹报啬之遗云。[14]727
又(光绪)《山西通志》:
秋获后,飨赛最盛,弦管之声,盈于四境。[8]7075
此外,临汾、太平等平阳府境内各州、县皆如是。这种在社祭活动中表演音乐的活动称为“社火”,也称“香火会”。其主要是为民众祈福求安而设,但同时也有物资交流的功用。(康熙)《平阳府志》载:
乡镇立香火会,扮社火,演杂剧,招集贩鬻人,甚便之。然男女聚观,识者恨焉。[14]728
又(光绪)《汾西县志·风俗》:
岁时社祭,春祈秋报,率多演戏宰牲。随其村落大小隆杀,大抵多失之俭。平时市无屠肆,亦其地瘠民贫,有以使之然也。汾邑地处山僻,商贾不通,市场匪易。每岁三八两月城中会期,邻封霍、赵、洪等处有铺来县贸易花布、货物,邑素称便。[21]65
民间戏班与吹鼓手是平阳府地方民间社祭音乐表演的主体。他们为获得一定的劳动报酬而表演,而民间社会集体出资又是支付这些花费的主要方式。
(四)迎春
迎春,俗谓“打春”“演春”等,实应称为“迎春礼”,是清代民间主导、官方参与的一种节日庆典活动,主要为庆祝“立春”节令的到来。在文化属性上,它既属于民间风俗的范畴,又具有官方典礼的性质,具体体现于地方志的编写中。平阳府地方志中有关于“迎春礼”的内容,大多置于《风俗志》一卷,也有放
在《典礼志》一卷的①如(雍正)《临汾县志》卷四《风俗》与(道光)《太平县志》卷六《典礼》。。
迎春礼举办的时间是在立春前一月至立春当日,主要仪节有“报春”“演春”“迎春”和“打春”等。
首先“报春”。在立春前一月内,由“乐户”装扮为“春官”“春吏”“春婆”等向“官长”“绅荐之家”报告春之将到,并送祝福。(同治)《浮山县志·风俗·迎春》载:
立春,先期一月,用乐户假之冠带,曰“春官”“春吏”,又装春婆一人,叩谒于官长及合邑荐绅之门,诵吉语四句以报春。[5]196
“演春”“迎春”则在立春前一日。“演春”主要是由乐人扮演“毛女”作戏,戴春花妆演春事。各地守土官到城市东郊祭祀芒神,迎土牛、勾芒回公堂后宴饮。(康熙)《临汾县志·风俗》:
立春前一日,妆春事,戴春花,迎土牛,以送寒气。[22]104
又(光绪)《翼城县志·风俗》:
至期,先一日,令拘集里设稚,并优人小妓,谓之“毛女”,演之署中。明发,率僚属,盛冠带,侈仪从,迓之东郊,谓之“迎春”。归则鼓吹导前,土牛、勾芒居后,舁之公堂而宴之。[9]439
在迎春活动中,民众参与的活动主要是观看土牛、食春饼,目的是驱寒气、占卜年岁水旱与个人苦乐。(乾隆)《续修曲沃县志·地理志·风俗》:
立春,先一日,迎芒神于东郊。簇春盘,啖春饼,
远近竞看土牛,以芒神占岁水旱、人苦乐。[10]423
立春当日有“打春”活动,也称为“鞭春”。活动内容是,由官员击鼓三声,并甩鞭击打土牛,使其破碎,三击告退。百姓取碎牛土写“吉利”二字于自家房门,并食萝卜数片,意为“咬春”。(同治)《浮山县志·风俗·节序》载:
至五更礼毕,鞭牛使碎,名曰“打春”。是日,人家取春牛土书“吉利”字于门;并噉萝卜数片,曰“咬春”,取荐辛也。[5]194
以上是平阳府地方志中从民俗角度对迎春节庆活动的叙述。除此之外,也有材料认定迎春为官方庆典活动,并从礼典角度来对其仪节作相关描述。如《大清通礼》:
直省迎春之礼,先立春日,各府州造芒神、土牛。立春在十二月望后,芒神执策当牛肩;在正月朔后,当牛腹;在正月望后,当牛膝;示民农事早晚也。届立春日,吏设案于芒神、春牛前,陈香烛果酒之属,案前布拜席,通赞执事者于席左右立,府州县正官率在城文官丞史以下朝服,毕,诣东郊。立春时,至通赞赞行礼,正官一人在前,余以序列行就拜位。赞:“跪叩兴。”众行一跪三叩礼。执事者举壶爵跪于正官之左,正官受爵酌酒,酹酒三,授爵于执事,复行三叩礼,众随行礼。乃舁芒神、土牛,鼓乐前导,各官后从,迎入城,置于公所。各官执彩杖环立,乐工击鼓击土牛三,乃各退。[8]7064-7065
在整个迎春活动中,音乐表演非常丰富,主要为鼓吹乐和戏曲音乐两类。前者一般用于导引。(光绪)《山西通志》载:
乃舁芒神、土牛,鼓乐前导,各官后从,迎入城,置于公所。[8]7065
后者主要用于“演春”仪式,起娱乐、助兴作用。这类表演称谓颇多,有名为“百戏”“杂剧”或“角抵戏”者,实指同类事物。(光绪)《山西通志》载:
立春之时,守土官迎春东郊,祀芒神、鞭土牛如仪,俗谓之打春。陈百戏谓之演春。[8]7065
又(乾隆)《乡宁县志·礼俗·俗尚》:
立春先一日,东西两社扮演杂剧,导官迎春东郊。次日,吉时鞭春。[11]80
又(道光)《太平县志·坊里·风俗》:
正月立春,前一日,迎芒神于东郊,伶人为抵角戏,各执所事以导,城市皆行。[13]294
平阳府地方迎春活动的音乐表演者主要为民间吹鼓手、戏班以及妓女、优伶,大多属于社会特殊群体——乐户②“乐户”,指中国古代社会以“贱民”为主体的专业乐人群体。关于“乐户”“乐籍制度”参见项阳《山西乐户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上文引(光绪)《翼城县志》“令拘集里设稚,并优人、小妓,谓之‘毛女’,演之署中”便是极好例证。虽然清代雍正元年(1723年),国家颁布法令取消乐籍制度,免乐户贱役,敕娼妇从良,但迎春活动中妆演“毛女”“春官”“春婆”的活动并没有停止。(同治)《浮山县志》载:
雍正元年,令乐户、娼妇归良,春官、春吏、春婆仍旧焉。[5]194
但也有些州县因此而停止了装扮“春官”“春吏”“毛女”的表演。(光绪)《翼城县志·风俗》:
国朝雍正元年,奉旨令乐户、娼妇归良,“春
官”“春吏”“毛女”,俱无矣。[9]439
清代平阳府地方迎春活动是官民双方共同参与节庆活动的典型,它是社会各阶层相互沟通的平台之一。在整个迎春活动中,音乐表演起了烘托气氛、融合阶层的作用。平阳府境内各州县在迎春活动中的各个方面都基本相似,迎春仪式及其音乐表演具有普遍性。
(五)庙会
庙会,是民间在祠庙、寺观、坛壝等场所定期举行的节令性风俗活动。它以各类民间宗教祭祀活动为主要内容,附带其他诸如集市贸易、音乐表演、娱乐交流等社会活动。
清代平阳府民间庙会活动非常普遍,其首先体现在各地密集分布的神庙建置上。以隰州为例,据(康熙)《隰州志》载,当时仅隰州境内就有坛庙22处、寺观38座,而且各坛庙、寺观均有赛祭;①(康熙)《隰州志》卷十《祠祀》记载文庙诸祠连同城隍庙、关帝庙等坛、庙22处,各有赛祭;卷之十一《寺观》记载安国寺等寺、观38座。成文出版社编选《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四二七号)。(雍正)《平阳府志·祠祀》中所列临汾县境内祠庙多达120余座。[1]241-305
众多的神庙意味着供奉神系的庞大。在民间传统信仰体系中,神灵的种类非常之多。有风雨雷电等自然神,也有尧王、关公等人格神;有专司一职的财神、福神,也有无所不能的天神、地神;有土生土长的道教神,也有外来传入的佛教神……
从文献记载的内容来看,众多神灵可总分为三类:一是国家礼典承认并颁布法令致祭的“正统神”;二是国家礼典不予承认并严厉抵制的“野鬼邪神”;还有一类是国家礼典不予承认,但也不反对的“宗教神”。对于三类神灵的祠庙,国家采取三种态度:以财力支撑正统神庙的建设,大力拆毁“淫祠”“野庙”,任宗教神庙自生自灭。
在众多神庙及传统多神信仰的背景下,民间举办用以祀神的庙会活动相当之多。仅以永和县为例,该县方志载:
三月三日,真武庙设醮,名曰“杨柳会”。
(三月)十八日,祭赛圣母,即后土神。
(三月)二十日,祭赛送生圣母。
(三月)二十三日,祭赛痘疹圣母。
四月八日,贺佛寿。关帝庙献戏。
五月五日,端阳节,祭赛龙王。
(五月)十三日,祭赛关帝庙。
六月十八日,祭赛本县城隍庙。
(六月)二十日,祭赛眼光乐王神。
七月十五日,士祭魁星,农挂田幡。佛寺设“盂兰醮”。
(七月)二十三日,祭赛华佗神。
九月十三日,祭赛关圣帝君。[16]278-285
民间庙会的活动时间一般为约定俗成的时令,如春秋仲月之类;或以“圣诞日”为期,如五月十三关帝圣诞、四月初八佛诞等,地点为各个神庙。
民间庙会的主要内容是祭神,而对于各路神灵,祭祀人员、祭祀方式则多有不同。如佛教、道教诸神之祭一般由寺观宗教人士主导,仪式均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而村舍土神一般由当地有声望者主持,仪式可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在祭神的同时,音乐表演也是民间庙会的重要内容。民间称庙会音乐表演为“赛”,庙会也被称作“迎神赛会”。这种“赛”的表演一般由民间乐人来完成,在雍正前,大多属于“乐户”群体。(康熙)《隰州志·风俗》载:
神庙中,集乐户歌舞神前,曰“赛”。南门东岳庙三月二十八日,西门三义庙四月初八日,北门龙王庙四月十三日皆有赛。[23]196
音乐表演的形式大体有歌舞、鼓吹、戏曲及佛道法乐四类。前三类属于民间音乐的范畴,而后一类则属于宗教音乐的范畴。在佛寺、道观中举办的庙会活动,一般会以宗教性的法乐表演为主体,但可能也有少量歌舞、鼓吹及戏曲音乐表演的参与。如浮山县的圣母庙中既有法事活动“打醮”,又有民间俗乐“演剧”,二者分别体现了该庙会音乐活动的宗教性和丰富性。(光绪)《浮山县志·风俗·节序》:
(三月)二十日,圣母庙演剧设醮,祈保婴孩。[24]516
在非宗教的民间神庙中,音乐表演有歌舞、鼓吹及戏曲等表演形式,尤以戏曲、戏剧的形式较多。(同治)《浮山县志》载:
(三月)二十九日,“火星圣诞”,演剧四日,放架火以答神功。
(三月)二十日,圣母庙演剧设醮,祈保婴孩。
火星庙,在南关。雍正十三年乙卯闰四月,邑宦张世捐赀创建。岁正月二十九日圣诞,献牲、演剧、放火,前后四日亦有贩鬻牲畜货物者。[5]194
清代平阳府地方戏曲音乐的繁盛相对挤压了庙会中歌舞及鼓吹的表演空间,所以文献中对后二者在庙会中出现的记载相对较少,但并非没有其存在的例证。(光绪)《续修乡宁县志·艺文志》载“前人”所著《重
修关帝庙东西廊碑记》一文中提到乡宁县城关帝庙时有“岁时赛社,歌舞神庥,老扶幼携,喁喁□乐”[25]144之句。另外,(光绪)《翼城县志·风俗·节序》也载:
三月初八日,相传为栾共子忌辰。南梁诸乡人于是日备鼓吹,设稚、楮幡、神宴,迎栾将军于栾池旁,士女集者以千万计,相与嬉游水滨,溯洄竟日,至晚乃罢。[9]439
总体来说,以“乐”“舞”“歌”“剧”命名的各种音乐表演共同组成了民间庙会音乐活动的整体。
民间庙会音乐表演的主要场所是各个神庙中的剧场。平阳府境内现存古代神庙戏台、碑刻非常之多,这些实物资料与地方志文献共同反映了清代平阳府境内庙会音乐的表演盛况。
首先,平阳府境内神庙剧场的称谓有多种,如“歌台”“歌庭(亭)”“乐台”“乐楼”“乐庭(亭)”“戏台”“戏楼”“舞庭(亭)”“舞台”“舞楼”等。仅从“乐”“戏”“歌”“舞”等字,即能看出这些以“亭”“楼”“台”等命名的众多神庙剧场的基本性质与功能。平阳府地方志及碑记中记载的剧场材料颇多。如(康熙)《隰州志·艺文志》录清人邵凤翼《重修三义庙记》一文载:
峙州境之西关有三义庙,不知创兴何时……复构歌台,大观瞻也。[23]407
另,同卷清人李呈祥《重修城隍庙碑记》又载:
盖修庙事神,余心好之……余往观焉,见正殿、后宫、两庑、享亭以及大门、牌坊、栏杆、乐楼涣然一新。[23]397
另,同卷清人胡文涣《新建关庙记》:
因建正殿三间、东西廊各五间、台楼一座,歌颂兴焉。[23]404
清人李时贤《重修文昌祠记》载:
隰州文昌阁,肇自前明万历年间,迄今三百载……悉修补而增□之原建正殿三楹,东增建奎楼一座,西官厅三楹、乐亭一座,较旧为加备焉。[26]138
又,(民国)《洪洞县志·建置·坛庙》:
城隍庙,在估衣街路北……前戏楼三间,戏楼前大门三间,题曰“城隍庙”……清康熙十六年,知县罗映台添建戏楼。[27]423
又,清人冯继祖《重修苏土、乌华村三义庙碑记》载:
尝闻修庙宇而礼神明帝君……今苏土、乌华两村,旧有三义庙一座,旁有十师①疑为“石狮”二字。,上有报厦乐台三门,无不齐备……今历年久远,鸟栖鼠窜,正殿毁坏,神像剥落,乐台东倒,大有倾圮之势。[16]588
除了以“乐”“歌”“舞”“戏”等字为名的剧场,还有另一类不以这些字为名的“台”“亭”,也同样具有音乐表演场所的性质。如洪洞县关帝庙有“露台”,实际上也是音乐表演场所。(民国)《洪洞县志·艺文》录“前人”(按:可能为清人)于璞《重修关帝庙记》载:
殿之前为献亭,亭旧为间者一,今增二而三,亭两旁建回廊十二。东西翼然相向,以拱护正殿。亭前十步许为露台,台之上亦建亭,为三。岁时栖伶人以拱丝竹。[27]1338-1339
民间庙会活动中的音乐表演一般由民间戏班、鼓吹班、僧道及其他民间乐人来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关帝庙、文昌帝君庙、城隍庙等“正统神庙”,官方、民间均会致祭,但方式完全不同。以关帝庙为例,首先区别在于音乐表演的形态。前文提到,国家礼典对关帝庙致祭的规定是“六佾”乐舞表演、正印官致祭,而民间关帝庙会则是以戏酬神,民众致祭。此外,音乐表演场所也有所不同。官方礼典中乐舞表演应在“丹墀”,而民间与之相对的是“戏台”林立。(民国)《洪洞县志》载:
关帝庙,在便德坊街北。元大德十年,里人苏汉臣重建。正殿三间,前享亭一间。明嘉靖十年邑绅张天禄增修。正殿为五间,享亭三间。两翼建迥廊十二间,亭前为露台……清顺治二年,邑绅刘令誉增建戏楼。康熙四十九年邑绅韩居大等重修春秋楼并戏楼。[27]429
再有,祭祀时间也不相同。官方祭祀关帝时间为“春秋二仲月”及“五月十三日”,而民间除此三日以外,还在“四月八日”“九月十三日”②如(民国)《永和县志》卷五《礼俗略》:“(九月)十三日,祭赛关圣帝君”。成文出版社编选《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八十八号),第278-285页。等时祭祀。最为不同之处是,官方致祭关帝绝不会与各类宗教合流,而民间四月八日祭祀关帝却与“贺佛寿”“浴佛节”相关联。如(同治)《浮山县志·风俗·节序》载:
四月八日,祀关帝,又为“浴佛节”,洪祖院设醮,保安婴孩。[5]195
又,(民国)《永和县志·礼俗略》:
四月八日,贺佛寿。关帝庙献戏,今废。[16]283
面对同属“吉礼”的祭神活动,官方与民间的不同做法凸显了“礼”与“俗”的对峙。但二者仍然有融通的
一面,体现在民间“俗”对官方“礼”的尽力模仿上。平阳府蒲县东岳庙有一通刻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的“永垂永久”碑,碑文说:“乾隆丙辰岁,东神山纠首老先生等十位,因土戏亵神,谋献苏腔。”[28]435这里就明确划分了“苏腔”与“土戏”的高下等级。明清以来,昆剧“苏腔”被视为官戏,“土戏”(梆子腔)不能与其相媲美。官方祭神有乐舞,民间缺乏财力,只好用最好的音乐表演——戏曲来代替。有土戏还认为不够资格、不够标准,必须要请“苏腔”来祭神,这样做才能算是不亵渎神灵。此为民间俗礼向官方礼典靠近的一个典型。
(六)其他节令
除立春、社祭以外,民间节庆活动尚有许多。如元旦(今春节)、上元、中秋、重阳、除夕等。这些节庆活动的娱乐性都很强,故而极可能有大量的音乐表演参与其中。虽然方志文献对此类音乐活动的记载不甚全面,但也仍能从中得到许多相关节庆音乐的信息。以上元(元宵)为例,(康熙)《平阳府志·风俗》载:
元宵,张灯球,架鳌山,鼓吹杂戏,火树银花,城市为多。[14]727
又(乾隆)《续修曲沃县志》载:
元宵,架鳌山,盛张灯球,鼓吹衢巷,火树银花,三日不绝。[10]422
(同治)《浮山县志·风俗·节序》:
上元,街巷张灯结彩,锣鼓喧阗,观灯者络绎充道。[5]195
(道光)《直隶霍州志》:
元宵,张灯吹鼓①应为“鼓吹”二字之误,今改。,扮抬高,办杂剧,士女骈集。[19]122
除了元宵节等全国性的大型节庆活动以外,尚有一些地域性较强的小型节庆活动有音乐的表演。这些活动可能只限于某些地域流传,其音乐很有可能是即兴表演的形式。如翼城县“花朝”游春活动中的歌舞表演。(光绪)《翼城县志》载:
花朝,邑人士多携酒殽,至东南两郊外浍水之滨,选地围坐,憨歌起舞,尽欢而罢,谓之“游春”,亦曰“踏青”。[9]439
总体看来,在清代平阳府的民间节庆活动中,鼓吹、歌舞和戏曲一直是音乐表演的主流。大多数节庆活动中都不缺乏这几类音乐表演的参与。
三、结论
清代平阳府地方音乐活动的品类非常丰富。本文按其社会属性(具体体现在人员、观念、经济等方面),将其大体分为官方祀典音乐与民间礼俗音乐两类。一是以国家机关执行、国家礼法约束、国家财政支撑为基本特征的官方祀典音乐。主要包括用于“参神”的文庙释奠、关帝庙致祭、文昌帝君庙祭、救护,以及用于“礼人”的乡饮酒、宾兴等活动。这些活动都需严格按照国家礼典的规定执行,地点一般在学庙、官府。其中,音乐表演主要是乐舞、鼓吹(导引乐)、笙歌、钟鼓等形式,由经过培训的学弟子员充当乐舞生来表演。二是以民众主导、民俗约束、民力支撑作为基本特征的民间礼俗音乐。其音乐活动主要包含在婚嫁、丧葬、社祭、迎春、庙会及其他节令庆典活动中。这些活动的举办一般是按照民间俗约来执行,地点大多在乡间神庙或百姓家庭。各种活动中,音乐表演主要有鼓吹、歌舞、戏曲、佛道法乐等形式,由吹鼓手、戏班及僧人、道士等民间艺人表演,有些艺人还属于“乐户”阶层。具体情况如表1。

表1 清代平阳府音乐活动一览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清代平阳府地方音乐活动的各个事项,现有的划分——“官方”与“民间”并非绝对准确。按照分类标准——人员、观念、经济来界定
这些事项,总会出现一些介于两类之间、“非此非彼”“既此又彼”的事项。遇到这种情况,用以界定事物分类的概念显得十分乏力,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属于“官方祀典”的乡引酒、宾兴和救护活动,虽然由官方主导,受国家礼法约束,也有国家财力的支撑,但参与活动的人员不仅有官员、学弟子员,还有许多民间人士,甚至处于社会底层的“乐人”都成为活动参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
(2)属于“民间礼俗”的丧葬、社祭、迎春、庙会等活动,虽主要由民间集资主办、按民间俗约举行,但其人员组织中又多有官员的参与,甚至个别活动中还有官方财力的支撑。
故而,诸如迎春礼的许多活动既体现官方祀典的部分属性,又具备民间礼俗的局部特征。此类骑在分界线上的活动事项就自然成为“官方—民间”二元分类中的“中间样态”。
事实上,从最广义的角度来说,清代平阳府地方音乐活动中任何一项都不会只具备一种单纯属性,而只是在整体上趋近于某一属性。实际上,平阳府的文庙释奠活动是不可能完全按照国家礼典丝毫不差地完成的。清代平阳府音乐活动的实际情况总会与典籍文书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甚至还有许多违反国家礼制而行的音乐实践。只有对此类问题进行进一步思考,才可使历史真相更加清晰。
[1](雍正)平阳府志[M]//凤凰出版社,编选.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44).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2]钦定大清通礼[M]//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摛藻堂本,第200分卷.
[3]赵尓巽,等.清史稿[M].点校版.北京:中华书局,1977.
[4](光绪)续修曲沃县志[M]//凤凰出版社,编选.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48).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5](同治)浮山县志[M]//凤凰出版社,编选.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55).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6]孔尚任.圣门乐志[M]//孔子文化大全编辑部,编.孔子文化大全.影印本.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89.
[7](民国)乡宁县志[M]//成文出版社,编选.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八十一号).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8](光绪)山西通志[M].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
[9](光绪)翼城县志[M]//凤凰出版社,编选.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47).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10](乾隆)续修曲沃县志[M]//凤凰出版社,编选.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48).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11](乾隆)乡宁县志[M]//凤凰出版社,编选.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57).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12](乾隆)蒲县志[M]//成文出版社,编选.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四二九号).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13](道光)太平县志[M]//凤凰出版社,编选.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52-53).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14](康熙)平阳府志.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丛刊(第六册).影印版.北京:中国书店,1992.
[15](乾隆)临汾县志[M]//凤凰出版社,编选.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46).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16](民国)永和县志[M]//成文出版社,编选.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八十八号).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17](民国)襄陵县新志[M]//成文出版社,编选.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四〇二号).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18](道光)赵城县志[M]//凤凰出版社,编选.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52).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19](道光)直隶霍州志[M]//凤凰出版社,编选.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54).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20](雍正)临汾县志.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丛刊(第五册).影印版.北京:中国书店,1992.
[21](光绪)汾西县志[M]//凤凰出版社,编选.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44).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22](康熙)临汾县志.国家图书馆,编.清代孤本方志选(第一辑,第十册).影印本.北京:线装书局,2001.
[23](康熙)隰州志[M]//成文出版社,编选.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四二七号).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24](光绪)浮山县志[M]//凤凰出版社,编选.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55).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25](光绪)续修乡宁县志.[M]//凤凰出版社,编选.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55).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26](光绪)续修隰州志[M]//成文出版社,编选.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四二八号).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27](民国)洪洞县志[M]//成文出版社,编选.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七十九号).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28]冯俊杰.山西戏曲碑刻辑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2.
(责任编辑、校对:刘绽霞)
Field Research and Overview of Local Music Performance in Pingyang County in Qing Dynasty
Sun Hao
Located in the central region in the vast plains of Northern China,Pingyang county in Shanxi province boasts a long history of ritual music,which has been recorded in local chronicles,analysis of which provides a glimps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itual music in the county.With diversified forms and rich connotations,the local music performance falls into two categories,namely the music for sacrificial ceremonies sponsored by governments of various levels such as those practiced in temples and the folk music performance organized by locals in celebrating matrimonial happiness and festivals,offering condolences and welcoming the ardent of springs.These performances includes dance,drums and gongs,singing and drama,which are considered gist of local music culture of Ping yang county with articulate features.
Ping yang County,Local Chronicles,Music for Official Sacrificial Ceremonies,Folk Rituals
J609
A
1003-3653(2016)05-0117-12
10.13574/j.cnki.artsexp.2016.05.014
2016-06-08
孙豪(1984~),男,博士,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古代音乐史、音乐文化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