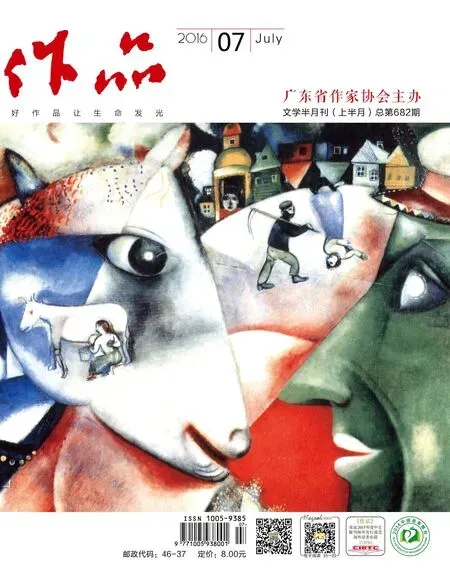恶、罪与审美
文/唐诗人
恶、罪与审美
文/唐诗人
唐诗人男,1989年生;文学博士,青年文学批评家;先后毕业于黑龙江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曾在《小说评论》、 《文艺评论》、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文学报》、 《山花》、 《南方都市报》等报刊杂志发表各类文章若干。现阶段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文学与伦理学关系研究。
关于“恶”的知识,我们其实是非常匮乏的,尽管我们每天都可从各种媒介中闻及恶的信息。比如恐怖主义、腐败案例、强暴杀人……这些触目惊心的日常新闻,已将我们对于罪恶的印象变得具体实在。不用谁来说服,我们都知道,这一类故意对无辜者施加不可忍受的痛苦折磨是罪恶的。但是,若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跟我们同样叫做“人”的人会选择恶的行径?是什么导致了他们如此凶残为恶?或者进一步寻思:什么是恶什么是善?我们是根据什么来判断他们的行为属于恶?这些罪恶事件所激起的疑问,正是我们思考“恶”的起点。
或许,追问为什么的时候,我们会习惯性地从作恶者的身份去思考,比如探究他们的背景、职业训练、教育、性格、成长环境因素等等。社会科学和心理学领域有很多知识点都在致力于这一理解。这些都是解释罪恶的思路,但是,这些加起来也永远无法完整地解释为什么人们做出了他们所做的选择。这种追问,表明我们需要探究关于“恶”的根本知识。从根本处思考恶,这是哲学问题。
一
在古希腊时期,人们认为,恶不是根本的人性,而是一种善的欠缺。苏格拉底说没有人甘愿作恶,恶是由无知造成的,有理智的人不会为恶。柏拉图追随苏格拉底,认为恶、丑一类属于最高的理念范畴。亚里士多德推崇一种“中庸”的德性,因此恶是“过与不及”的一种后果。普罗提诺则指出现实中的各种恶,都源于“物质”这一根本源头。他认为灵魂不具备心智、理性即恶。也就是说,当它缺乏中庸适度而又容忍其过度和不及时,它就成了恶与恶的根源。放荡、卑劣以及其他种种非分情感,缺德的心灵,都是由灵魂造成的,它诱导出虚伪的判断。而灵魂一旦善恶混淆,它就避善求恶。
基督教兴起后,有了一种至高无上的上帝和不可逾越的宗教规则后,恶开始与罪等同化,不信神是最大的恶。肉体的欲望,甚至现实世界中的一切,都有恶的性质。《圣经》中还有一个最核心的恶之代表——撒旦。它是幽暗世界的管辖者、掌控者,它引诱人作恶,把恶通过亚当夏娃导入了人类世界。古罗马时代,奥古斯丁坚信神是最高的善,神的创造中不可能有恶,恶只是每个人的过失而造成的,恶是缺乏善,是人的意志背叛了善,是对善的恶用。中世纪阿奎那,他不相信有所谓的至恶,恶只是意外、偶然,而且是由善良生出的结果,它是由于“附性的偶然,而非自性的本然”。
文艺复兴时代,随着文化思想上对人和世界的重新发现,对“恶”的认识也逐渐从宗教意义上的“罪”脱离,转向人间的、具体的恶。《神曲》中,但丁通过游览地狱、炼狱与天堂,帮助人们见识了许多类型的恶人和恶行,是宗教的结构,但在地狱图中,我们看到的都是恶人恶行,神的宽恕已经转化为人对它们的厌恶,惩罚看似来自神的正义,其实更是属于世俗世界里人的审判。艺术界的卡拉瓦乔对“恶”的呈现,不仅仅是自己生活浪荡放纵,还有作品中的血腥和审判。这些审判,有来自神的光,更有人间的不可谅解的追捕。在卡拉瓦乔身上,最典型地暗示了“恶”的观念变化,他个人的罪是人间的,也是宗教的,然而宗教上,神(主教)可以宽恕他,他把自己滴着血的头颅置入画中,祈求宽恕,有赎罪的含义,但这种赎罪抵消不了他在现世中所犯下的杀人之恶。但丁和卡拉瓦乔,分别在理性层面和异端、野性层面对“恶”有了新的理解。
启蒙思想兴起后,人性论开始丰富。培根对认为“恶”也属于人性中的天生趋向,它“表现为暴躁、好斗、嫉妒、幸灾乐祸、落井下石”。霍布斯有着典型的经验主义视角,他认为任何人的欲望对象,就其本人来说,都可称为善,而憎恶或嫌恶的对象则称为恶,轻视的对象则称为无价值和无足轻重。这里的“恶”不但是个人的事情,且还随着个人的心情变化而变化。霍布斯也指出,若是各人都任性地追求各自的目的,就会致恶,因此“恶”有“双重性”,这种双重性也表现在国家行为、战争行为中的“恶”。洛克认为善恶并不绝对,是比较而来的判断。杜威和詹姆斯,他们对善恶的理解与经验主义思想很类似,詹姆斯直接说有用的就是善的,而对于“恶”,只需要去避免和克服,不必去论述;杜威认为我们对善恶的判断不能绝对、僵死,要有过程性,要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经验-实用主义思想之外,大陆理性主义对“恶”也有着深刻的思考成果。莱布尼茨相信神的至高之善,但他也强调,恶的根源依然在于上帝,上帝身上含有着善和恶这两种现象的本源,恶只是部分的、个体的,是一种贫乏。康德把自由意志作为人的真正本体,认为从这个本体中才能真正探明恶的本质,寻到恶的根源。恶的根源就在于人违背自由意志、理性精神这一真正本体。康德对恶的思考,开启了恶论的新思维,他开始把恶从传统神学的知识体系中独立出来思考,认为恶是自由意志的一种选择,人有向恶的禀性,根本恶植根于人的本性中。黑格尔批判性地继承康德,在他的辩证法思维中,恶是人类有限性的一种表现,而上帝是无限的,因此是善的,有限的恶可以被扬弃,最终抵达绝对精神的善。他要求我们理性地面对恶,进而消除恶。而在谢林思想中,恶内在于人的自由。人的自由的根基同上帝的根基有一致性,在上帝那里,根据与实存、黑暗与光明可以得到和谐统一,因而是绝对善的;而在人身上,根基中的黑暗因素可能成为控制性力量,导致人的意志出现善恶颠倒,坠入恶的深渊。
与黑格尔同时代的叔本华,认为“意志”即是邪恶的起源地。叔本华指出很多恶是找不到缘由的,有着无缘无故作恶的情况。叔本华的悲观哲学影响了尼采的选择。尼采对于善恶的观念,具有颠覆性的论述,他不仅“敌基督”,言“上帝死了”。伯恩斯坦分析恶的道德心理学问题时,认为尼采的道德批判意在揭示一种自我欺骗的道德假象。尼采认为人们通常所谓的道德,实是建立在憎恨的情感基础上,即软弱无能者对高贵者的憎恨。“恶是憎恨的暴力显现”,这是现代道德最为普遍和危险的特征。伯恩斯坦通过将尼采视作辩证反讽家来论述,认为尼采的道德批判并不是针对过去的宗教教士,而是时代的憎恨心理。这种心理盛行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政治领域,非常危险。尼采主张超越过去的善恶观念、期待一个价值重估的时代到来,其实是要我们警惕现代道德和现代社会化进程中的阴暗面,以弘扬光明高贵来抵抗时代的危险心理。无疑,尼采的信仰还是一种“乌托邦”,而到弗洛伊德时,就指出了这种期待的幻觉特征。弗洛伊德认为文明的进步其实扼杀不了本能性质的“恶”。实际上,我们不可能根除恶,恶是潜意识内部的力量,我们只能用超我世界的意识去防范各种恶的莅临。
二
在西方的“恶”论之外,中国关于“恶”的观念其实也很丰富。《说文解字》里,对“恶”的解释是:“过也。从心亚声。”清段玉裁解释说:“人有过曰恶。有过而人憎之亦曰恶。本无去入之别。后人强分之。”在思想家里面,对“恶”有过论述的很多,孔子稍有提及,《里仁》篇:“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当然,这里面的“恶”更可能是表示一种情感上的厌恶,而非善恶之恶,比如钱穆先生就更赞同解释为“厌恶”。《尧曰》中,也提到“四恶”:“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这是“恶”的四种类型,也非常有代表性。但是,孔子对“恶”的源头、本质问题未具体谈及,更多的是谈及这一现象。有人指出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说法中分别开启了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蔡元培也指出孔子思想中已有偏于性善说的倾向。孔子之外,战国初期还有世硕,他最早指出人性有善有恶,王充记述:“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性各有阳阴,善恶在所养焉。故世子作《养书》一篇。”世硕持性有善有恶说,告子则认为性无所谓善恶。孟子从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等现象来说明人性本善。荀子从人的欲望出发,认为性本恶,需要礼仪道德,以“化性起伪”。当然,亦如蔡元培所言,孟子荀子的性善性恶,其实都未必是本源上的问题,而是一种倾向性,他们无法解释对立面的问题:“孟子持性善说,而于恶之所由起,不能自圆其说;荀子持性恶说,则于善之所由起,亦不免为困难之点。”
鱼瘦素表达水平与其营养状态相关[17]。经过一段时间饥饿后,鱼类瘦素表达水平增加[18]。瘦素与鱼类代谢相关[19-21]。鱼类瘦素通过调节糖(血糖)和脂类代谢而调节鱼类的摄食及能量代谢平衡[14,22-23]。
此外,先秦时期,道家、墨家、法家也有相应的善恶观。《老子》有言:“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庄子指出礼义法度,“应时而变者也”,认为道德这些东西也是不定实的,常因时因地而迁移。老、庄这种“相生”和“迁移”的思想,把美、恶、善、不善等的相互关系指出,令我们联系起西方现代思想中的善恶观,取消源头性的、本质性的思考,在对比中、情境中去判断,似乎才更具科学性。当然,这里面也有根本的差别,老、庄是由此相信,人们应顺应自然、顺乎本性。墨子思想中,“兼相爱”就是善,“别相恶”即是恶。韩非继承了荀子性恶的思想,认为人都在争夺名利,被欲望控制,因此主张“严刑峻法”。
后世思想家的恶论中,杨雄折中孟子荀子观,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韩愈把性、情分开论述,“性”是天生,“情”是后天,性有上中下三品,只恶无善是下品;情也有三品,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情,若过甚或不及,那就是下品。王安石主张从“理”的视角判断善恶,这里的“理”是现世的道理,是说性情落实为行为之后,才能平量其合理与否,才能判断善恶。朱熹遵从儒家性善论,只承认相对性的恶:“善为天命赋之所本然,恶为物欲生之所邪秽。”因此要“存天理,灭人欲”。而王阳明心学思想中,“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至善至恶是良知,为善为恶是格物。”据陈来的分析,船山思想中,恶的根源在于“情”,这“情”与“性”不同,“情”是韩愈指出的“七情”,包括喜怒哀乐,也包括爱、恶、欲。“人苟无情,则不能为恶, 亦且不能为善”,所以,“恶”是源于“情”,与“性”无关。除开以上思想家,后世还有廖燕、戴震、龚自珍、严复、章炳麟等等,但他们的善恶观念,并没有多少新的突破,还是在性无善恶或有善有恶阶段。其中,章炳麟结合进化思想,也指出人性的善恶都在进化。总体而言,确实如很多论者指出的,我们的传统思想中,关于“恶”的探讨,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对“恶”的认识,在严密和庞杂性上有所欠缺。
三
思考恶,也需要将它同“罪”区隔开来。对“恶”(evil)与“罪”(sin/guilty),我们经常混着用。“罪恶”总是挂在一起,好像它们亲密无间。“罪”与“恶”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这涉及到宗教、法律问题。一般而言,“罪”是道德、法律范畴上的概念,“恶”是伦理范畴内的概念。当然,正如道德和伦理的概念之差一样,它们有区别,更多的还是交叉。
在犹太教基督教思想中,人一出生就携带了“原罪”(original sin)。人类祖先亚当夏娃没听从上帝,犯了规矩,有了“罪”。由这一典型“罪”来看,所谓“罪”,它需要有一个“规矩”、“法则”,作为判断的依据。在宗教世界,“罪”是违反了宗教教义。圣保罗指出人除开犯了原罪外,还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本罪”,即违反上帝律令的罪行,比如违反“摩西十戒”。莱布尼茨在对恶的分类表述中,认为道德上的“恶”在于罪过之中,也就是违反了道德规则或者犯了罪的。基督教里有“七宗罪”之说,即阿奎纳列举的七种恶行表现:傲慢、妒忌、暴怒、懒惰、贪婪、贪食、色欲。这些都是冒犯教义精神的恶,是恶行,也是罪行。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他就直接将“恶”与“罪”等同。在奥古斯丁看来,恶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东西。被称作恶的,都属于罪或者罪的惩罚。而罪则是因为意志的问题,如果没有主动的意志,罪就不能成立。这里奥古斯丁把罪归入了主动意志问题,他的罪就是恶,是意志上对善、对上帝的背离。基督教中的“恶”还包括“自然的恶”,这就是非人为的,比如疾病、地震、干旱等自然灾祸。不管是道德上的恶还是自然的恶,都引起痛苦,于是都可以纳入“神正论”的探讨问题中,神创造的世界,为什么会有痛苦、死亡?许多宗教神学家都探讨过这一问题。
内心的罪感,这在东西方,都会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赎罪。在基督教思想中,谈论恶时,它与赎罪难分难舍。原罪的存在,因此人生在世须不断地赎罪。宗教上的“赎罪”需要一个信仰“原罪”的前提,这种前提在中世纪之后,不断受到怀疑,到康德时,对“原罪”的信任开始转为对道德责任的承担。责任概念是康德伦理学的中心。按照康德的说法,责任是道德价值的源泉,是良知感的外在表现。康德这种责任伦理,发展到二十世纪的罗尔斯时,“罪”的含义几乎完全变成了存在者的不承担责任。因此,现代世界,世俗化时代的忏悔与赎罪,更多的情况是表现为个体对良知的清醒认识和对责任的自觉承担。表现在文学上的忏悔和赎罪,不仅仅是服罪、受惩罚的问题,更是内心良知的发现,是自我苛责和道德愧疚。
刘再复、林岗对“原罪”问题进行解释时,把“原罪”引申解释为一种普遍性问题:“用我们今天的语言解释,‘原罪’其实就是人性深处某些不善的东西。这些不善的东西作为邪恶的念头存在于我们的心里,它就是一个不善的动机,或许转化为日常行为的恶行,这就叫做‘guilty’。”“原罪”不局限于宗教范畴,更是普遍存在于人类内心的恶之可能。承认这种恶的可能,核心就是呼唤人的“赎罪”意识。在犹太-基督教内,人要忏悔、要赎罪。而宗教之外,面对这种可能性,人也应该时刻警惕,警惕内心世界里恶的流露,而如何警惕?这需要清醒的道德律和良知感。
近代以来,全世界范围内的宗教都有衰微的表现,世俗化愈来愈明显。在赎罪问题上,中国与西方也有很大的不同,这来源于文化中罪恶观念的差异。在西方,罪恶基本上会联系到宗教,而于中国,谈及罪恶,基本上是与法律制裁或者道德谴责相关,更多的情况是良心的不安问题,这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差异。
四
对于善、恶、美、丑,今天我们已熟知康德美的无目的、无利害观念,能够把审美判断和善恶判断区别开来,加上唯美主义、浪漫主义以及西方现代美学、文学思想的发展,恶已经不是简单的伦理问题了,更是价值范畴与审美范畴上的重要问题。因此,在恶与丑、恶与美之间,不能简单应付。
对于恶与丑,李泽厚主编的《美学百科全书》对此作了概念上的区别:“丑与恶是相联系又相区别的范畴。其联系主要表现在:二者都是畸形、令人压抑的事物。但丑是恶的表现的一个侧面,丑是恶的外在形象显现,恶以形象表现出来便是丑;恶又是丑的内容:1.恶可由概念、判断理性抽象形式去把握;而审美范畴的丑必须以外在感性形式来表现,若无感性形象,也就不存在丑的美学概念。2.恶与功利直接相关,更属于伦理学范畴,其深含的是其内在的抽象的内容;而丑则属美学范畴,不与功利直接发生关系。”不管这种概括全面与否,应该承认,恶在现实中,或者在文本中,它所呈现出来的“面目”在广义上还是可以划入“丑”的领域,即恶的形象应该是丑的。即使唯美主义文学和思想中有着把恶“美化”的现象,但其“美”是血腥的、残酷的,其“美”也是美学层面的“美”,并不是外在的“美”,它们依然属于“丑”的形象呈现,在审美上依然是审丑的问题。
“恶”可以归入美学审丑话题,反过来却不能成立,即并不意味着“丑”就等于“恶”。“丑”更多是指向外在形象,包括现实中的表面现象,也包括文本中的具体内容情节和语言特征。但这种“丑”并不一定就是“恶”,正如前面所提及的,丑可以是有德性的、善的,丑的形象内部或许隐藏着崇高的人格和善良的灵魂本质。因此,我们关于恶的审美价值探讨,在广义上,依然是属于关于丑的审美,也是一项美学审丑的内容。
美学上有审丑一说,那么,继续追问丑的内部的话,可否形成一种美学审恶的知识?在美学思想史上,黑格尔曾明确地说关于恶的美学是自相矛盾的,认为恶不允许成为艺术的对象,但亦有学者做出“美学审恶”的研究。法国学者彼得-安德雷·阿尔特的《恶的美学历程》,就对西方文学史中的“恶”进行了极其全面深入地探讨,他提炼了六种非常有代表性的文学之“恶”,或者说六种恶的美学类型。阿尔特探究这些文学之恶的思想资源,是浪漫主义以来的文艺思想,这也说明,自浪漫主义开始,书写“恶”的文学与关于“恶”的思想逐渐兴盛。阿尔特说:“直到18世纪末,一种独立的恶的美学在进行了得到一致赞同、令人信服的研究后才发展起来。1800年前后建立了一个纲领,它试图将艺术理解为一个独立于宗教、伦理和法理规则的部门。”这种冲向独立、自由状态的文艺观,恶的表现正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内容。“恶”从传统的表现规则中解脱出来,怪诞的、非道德的、令人恶心的、血腥的、丑陋的、变态的内容逐渐繁多。这些性质的文艺作品,文艺复兴时代有了萌芽,并逐渐增多。盛行于16-18世纪的以“怪”为美学特征的巴洛克文艺风,但丁、拉伯雷、塔索、卡拉瓦乔等,甚至于莎士比亚,他们追求“变形”的美,作品中叛逆的、怪诞的、丑恶的内容或精神气质非常明显。而到浪漫主义文艺运动开始,蒂克、霍夫曼、拜伦、萨德、歌德等人的文学实践,文学摆脱了道德的束缚,文学中的“恶”也呈现得更为“自由”。蒂里希曾指出,19世纪20年代发生了一个浪漫主义思想的转型,从开始时期强调无限临在于有限之中,到后期的时候,无限的方面不仅一直抵达神,而且下降到魔性当中。这种魔性延伸到唯美主义以及存在主义、现代主义的各种艺术思想中,比如未来主义、颓废主义等等,成了“宣扬”丑恶的美学。这些艺术、文学作品中的“恶”极为普遍。王尔德直接要把道德从小说中驱逐,小说也把恶的内容描绘得美轮美奂。波德莱尔《恶之花》一般被认为是现代主义的开端之作,也是研究文学与恶关系的代表作品。他用诗去书写各种丑恶和卑污的物体与事件。文学作品之外,还有思想上的“恶”论,比如弗洛伊德心理分析中的魔鬼、力比多思想,施莱格尔的黑色诗学,黑格尔、马克思等人的恶之发展动力说,以及存在主义以及巴塔耶、福柯等人的“恶”论。总之,近代开始,西方文学和思想中对“恶”的描绘与论述愈来愈多,对恶的审美也逐渐成了习以为常。
艾柯在《丑的历史》中梳理了西方文艺史上的丑恶类型,著作最后,他指陈了当下社会中无数的丑恶事件,认为我们被恐怖景象所包围,我们恐惧度日,也明白何为恶,会流露同情与愤慨;在审美上,我们也清楚,文艺中的丑恶内容,本质上也并不是要引起我们的喜悦之感。今天的艺术早已是边缘化的存在,但艾科也强调:“但艺术提醒我们:尽管一些形而上学家满怀乐观,但有个无法改变的令人难过的事实——这个世界里有个恶意的东西存在。”艾柯的意思是,在这个野蛮时代,文学书写“恶”存在其难得的价值。当然,对“恶”的这种文学认同,仅仅是发现它的提醒作用还是不够,局限于一种社会功用上的发现远远不足以概括美学之“恶”的意义。而且,对“恶”的书写与欣赏,确实如黑格尔强调的,它是矛盾的。伊格尔顿曾指出:“认为邪恶是富有魅力的观点,是现代所犯的道德上的最大失误之一。”这个观点置入文学审美中可能不完全适用,但也提醒我们,对“恶”元素的审美,需要警惕一种恶趣味的趋向。“恶”的书写与鉴赏均有内部的矛盾性,有着复杂的思辨空间,审“恶”的美,需要细致、科学的辩证思维。
(责编:王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