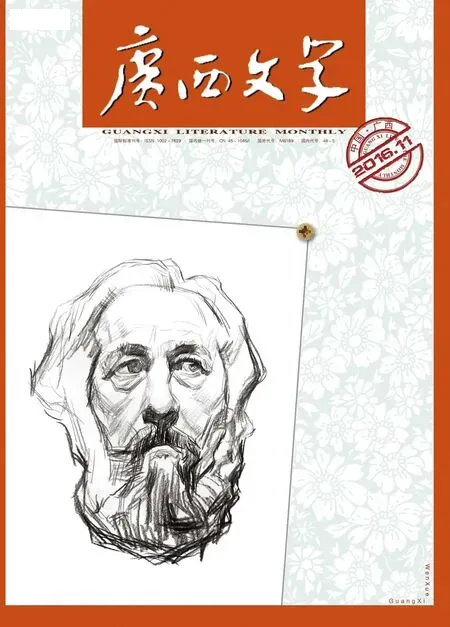十万大山十万诗
——广西诗歌的四个面向
桫 椤
在“广西诗歌双年展”上,我看到广西百余人的诗作,这个庞大的体量令我震惊。广西或许经济不发达,但十万大山十万诗,在诗歌意义上是富足的。我没到过广西,而透过诗歌理解广西是纯粹的。广西诗歌在多个面向上的表现,让我切入那片丰饶的土地以及繁盛的诗歌现场——是的,是表现而不是呈现,诗人们从未呈现过广西的现实容貌,他们以诗的方式和力量表现他们眼里的广西,而我也以这些诗作为眼,构建属于我的广西——也许我的感受对于我或者广西都可能不是独特的,但此刻,它们属于广西。
本 土
地域文化对人的心理结构和精神建构有着重要影响,以乡村为例,南帆说过,乡村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生态空间,至少在文学上,乡村同时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文学关注的是这个文化空间如何决定人们的命运、性格以及体验生命的体征①南帆:《后革命时代的转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170页。。对于“广西特质”这样无法赋形或具象的文化属性,诗人们将自我的理解以诗来表现,为理解精神意义上的广西提供了可能性。
朱山坡在西贡的两首诗从某个角度呈现了对此的探索,《在西贡与友人谈论母亲》由一个清澈的异国之梦开始,后以大幅度的情绪转折表达内心隐痛,“锥子扎在肉做的地方”,让人感受到诗本身的张力与内心痛感程度是相同的;接着用“别人的母亲”呈现痛因。对于身居边陲的人,家国与私情紧密,异国之旅并未享受到快乐,而体会到一条河、一片海模糊的归属所带来的精神痛苦,这样的诗歌立意是有“边地写作”脉络可寻的;在写作方式上,这首诗凸显了“表现”与“呈现”的区别,通篇有痛感却无“痛”字。《7月4日在西贡》则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表达身在异国的感受,对家国的深情、自豪和崇高感渐渐进入疏朗之中,“这一天,专门用来爱仇人、饶恕邪恶/为正在干坏事的人祈福/我还想劝慰正在忙活的越南人/今天是独立日/不要怨恨美国/不要奴颜婢膝/不要心怀恐惧/今天所有的爱都给自己”。诗人的感受是独特的,当这种独特性来自国家边陲一个思考者的体验时,那是深厚而又开放的世界涵育出来的。
朱山坡上述诗作生成于游走异地之后的回望,是“生活在别处的”的漂泊感。而陆辉艳两首有关码头的诗则呈现了当下的生存情状和生活伦理,作者的心依然是漂泊的,是身在广西的“心灵流放”。《在南宁港空寂的码头》中,诗人带着自己的孩子在水边挖沙,而即将弃之不用的旧港繁华不在,搬运工也不得不去寻觅新的生计,整理行李、最后一次走进屋子,然后“站着抽了一支烟,抓抓脑袋,想起了什么/朝晾衣绳上,取下那条红色裤衩——/刚才它还在风中,哗啦啦的,旗帜一样飘扬”,而今那面“旗帜”“降”下了,也降下了南宁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模式。虽然“我”的生活平静如昨,但南宁人日常生存背景的变化还是给诗人的内心投下风暴。
上一首诗,诗人的客观和理智尚在,且是站在一个审视者的角度观察现场,而《上尧码头》,则被生活现场的凌乱和颓败困顿到窒息,观察让位于汹涌的感觉,“悄无声息的码头。时间尚早/低矮的电线杂乱地横在空中/那上面晾着男人的T恤,裤衩,糟糕的生活”。面对荒凉,诗人期望人声,但只有几只麻雀。一些地方在生长,一些地方却在委顿,身处一个巨大变化的共同体,复杂的现实表征让人无所适从,在这个维度上广西是整个国家的缩影。这些诗来自生活现场,像十万大山的树,是自然生长的,因而是及物的。及物性让诗沉稳,逻辑也是顺畅的,自然而然的顺畅感令意蕴凸显。
日 常
辛波斯卡说:“我无法想象诗人不去争取安闲和平静。不幸的是,诗歌并非诞生于喧闹、人群之中,也并非诞生于公共汽车上。所以,必须有四面墙,并且保证电话不会响起。这是写作所需要的一切。”②原载《辛波斯卡诗选2:我曾这样寂寞生活》,胡桑译,湖南文艺出版社版2014年2月版,转自胡桑《碎语、奇迹市场,或希望》,收入《2014年中国诗论精选》,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选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4月版。这样的生活在当下已是难题,但并未影响诗歌的产生,而她所指的“安闲和平静”我则理解为灵魂的状态。于坚说:“诗意是天然的,先于世界存在的。”③于坚:《还乡的可能性》,商务印书馆2013年2月版,第62页。显然诗也先于诗人存在,灵魂的安逸为肉身打开通往诗的秘道。诗人眼里没有俗世,最日常的生活也是诗的神龛。日常的喧嚣被诗改造为人与灵魂之间的密室,而诗人以神示般的直觉感受到密室里纵横牵绊的力量。
拓夫的《一个手拿弹弓的人》从一个日常场景切入,渐入不可见的世界:“眼睛四十五度向上/那是一棵树的某个枝杈”,世界的神秘性在于无限可能性,诗人不打算以一个叙述者的视角代替被叙述者进行选择,由“他”而“我”再转向“他”,诗结束在一个被完成的动态场景中:“我在不远处/静静看着他/他手里那颗弹子/始终没有/射出” 。这个极为常见的生活片段,诗人写出了蕴藏其中的普遍逻辑和意象之间的平衡关系,那个手举弹弓试图射鸟的男人,鸟、女人的面孔、天空和拿弹弓者构成了一幅静态的图画,但支撑静态的却是蓄势待发的紧张。“我”的镇静与隐含的紧张之间构成了相反的对称关系,生活逻辑同构了诗歌逻辑。
拓夫的《灰烬》中,日常经验里的神走出密室,直陈诗意。“我把一沓旧信/拿到楼下空地/点燃/看纸一张张由白/变黑”,燃纸这个充满民俗意味的行动昭示了诗人将历史神化的过程,信或许是旧时光和旧情谊的物化载体,而灰烬成为人神合体的象征物。在此之后是人、时两忘的对视,俗世生活在诗人的视角转换下完成了“密室逃脱”的游戏,千般不忍的闷钝痛感弥漫于仪式的全过程,日常变得极为奥妙。拓夫的诗,是口语化的顺畅言说,“诗到语言为止”的技法不存在,词语在能指和所指之间保持着一致性。
非亚的诗在这个向度上也以语言的澄明将现实生活净化,俗世成为温暖、洁净的灵魂居所。他的《杏仁饼》写一次简单的就餐引起的回忆,还原语言的身体性,“我们”与“它们”之间形成一种意象上的关联,探知一次日常的片段内在的温暖。非亚语言有日常性,《月光下……》用口语化语言重建鲜活的场景:“那个老头就住在我的楼下/每天,晚上/他睡着后/一扇蓝色的门就开始缓缓打开”,到此诗意开始呈现,主角睡着后——我们宁愿相信那是真实的睡眠。诗人“看”到老人的日常生活被死神模仿,老人入眠了,而“死神”则在思索。生命与时间的紧张关系油然而生,显现在日常中时就变得令人恐惧。
变 化
在当下的中国,“日常”的词义已经极其狭窄,反而是“变”成为“常”的替代者。但在广西诗人的诗作中,据以理解和确定“变”的,依然是“常”的传统,诗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视域中有一个不变的坐标系,俗世生活的变化是相对于坐标点的变化。盘妙彬的《三江片断》,域内的旅程与朱山坡的异域之行相仿,也经历了从明亮到晦暗的过程。诗人欢天喜地地去三江后,最初的期待被现实打碎——诗人的想象还停留在过去的传统生活里,但侗乡男女间纯洁的“坐夜”习俗已经变了味道,“原汁原味的坐夜/改为表演的坐妹”,诗人自此发出“我”与他者的隔膜——事实上那是灵魂与俗世的隔膜:“今夜有两个三江/我一个人一个,其他人共一个!”山水也变得面目可憎:“一个同来的柳州人说/这里怎么没有闻到山区草木的味道呀/我答,是呀/夜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的不只是夜色,还有诗人颓败的心情和诗中颓唐的气势,最后变成结尾处对这冷漠人世的无限哀怜。
现实社会中传统文化、伦理道德、自然山水的衰败呈现三位一体性,这一衰败过程有着相同的根源,即工业文明刺激下的人类贪欲泛滥,社会世俗化的进程日渐加速。与《三江片断》相似的主题和叙事风格也出现在刘春笔下,他的《流失》深具乡愁意味,尽管一再强调对故乡的熟识,每一行诗却都在述说乡村生活衰败之后的陌生,这种陌生感在少年时暗恋的邻家女孩身上达到顶点:“终于,我看到年少时暗恋的邻家女孩/我流出欣慰的泪水/她朝我瞟了瞟,目光又落在/手中的麻将牌上”,泪水与麻将牌之间最朴素的对照揭示了社会伦理生活已跌落到深渊。
刘春的另一首诗《叙事》述说男女情感、家庭关系在道德沦丧中土崩瓦解的过程,叙事使诗意更直接。男人与女人相识、相知,失去道德约束各自寻欢,诗人以旁观者的视角观察他们的情感战争。结尾以总结性口吻将具体事件升华为俗世规律与轮回,通俗的言说呈现现实的真相。
青 年
广西90后诗人祁十木、赵山河、牙侯广和高寒等,他们是改变广西诗坛格局的力量,不仅仅因为青年预示着希望,而是他们以并不太深厚的人生经验能在诗中透射出的气象和潜质。
强烈的生命体验是他们着力在诗中表现的内容。他们对生命怀有敬畏,并能严厉审视压抑而荒唐的现实,极少“为赋新词强说愁”。祁十木的《捏食物的人》从生命的尽头折返,写一个贫病交加中的人如何走向死亡,“捏”成为描写生之艰难最准确的动词,现实的残酷震撼着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生命的轻薄与现实的沉重之间形成悖论,诗歌就像电极那样依靠矛盾的连线获得力量。
诗人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发现真相,并以诗歌的方式无限接近真相。牙侯广的《讨债》撕掉了这个世界最后一层遮羞布,揭穿了美丽诱人的谎言。面对拖欠的装修费,“父亲哑口无言/收拾完工具/抽了几口闷烟/走了”;时间一年一年过去,钱始终无法讨回,父亲的善良被利用,他只能把愤怒和无奈埋在心里,父亲的木讷是对现实世界的绝望和控告。诸如此类的遭遇发生在大多数人身上,牙侯广尝试着挖掘现实的本质。
青年诗人的创作还表现了对家园的眷恋。传统在90后一代人身上的影响远没有前代大,所以在朱山坡、黄土路、盘妙彬、刘春等的诗作中据以对现实进行比照的历史坐标在90后的写作中是缺失的,他们在诗中反复书写的是当下的乡村生活经验。而在对现实经验的表达中,故乡和母亲两个传统母题又常常是其中最重要的书写对象。高寒的诗在生活场景中捕捉诗意,诗意温暖中伴随着伤感。赵山河的诗来自生活的寓言,注重内在场景和意象的关联性,《娘的电话打不通》既写出了母亲的艰辛,又表达了自己远离家乡无力帮助母亲的内疚感,动人心弦。
牙侯广的《一只患病的母狗》和祁十木的《叙事:献牲》是广西90后诗歌中的重要篇章,这些在乡村生活语境里诞生出的诗篇,天然带有质疑现实的基调。前者人与狗具有相同的身份角色,当狗因为患癌而痛苦地死去时,母亲的话打碎了人之为人的所有可能性。而在《叙事:献牲》中,人打着敬神的幌子,将人类的罪恶用无罪的牲灵代替,人性与兽性发生反转,生命的洁净与肮脏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