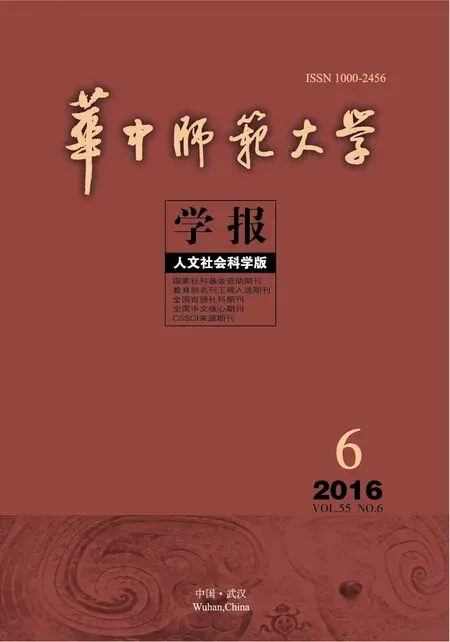南漕北运:中国古代漕运转向及其意义
吴 琦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南漕北运:中国古代漕运转向及其意义
吴 琦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漕运连接着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区域,其线路方向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汉唐期间,漕运为东西方向,由东至西;唐宋期间,漕运转变为东南、西北方向,由东南而西北;元明清三朝,漕运进一步转变为南北方向,由南至北。漕运方向的不断变化,意味着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在空间上的地域关系的变动,总体趋势是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分立北南,南粮大量北运。这一变局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漕运作为实物赋税的运输形式持续存在,始终成为政治中心紧扣、牵绊经济发达之区的绳索,另一方面,由于漕运长距离运输的空间特点,各王朝意识到漕运除了供食京师之外尚可发挥其调控与制衡社会的功能,于是漕运越来越多地运用于社会赈济、救助等领域。此外,漕运客观上引发了区域社会经济格局的变动,促生了运河经济带的产生,这个经济带在明清时期的经济功能及其辐射意义巨大。漕运线路变动的背后还存在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即中国古代统一王朝为什么始终选择内河,其价值取向与内在理念何在的问题。
中国古代; 漕运; 南漕北运; 漕运转向; 运河经济带
自秦至清,在漕运发展、漕制建设的同时,漕运线路也在发生着变动,漕运的区域指向随之出现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意味着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在空间上的地域关系的变动,同时引发区域社会经济的变动;与此同时,各王朝逐渐意识到漕运除了供食京师之外尚可发挥其调控与制衡社会的功能,于是漕运越来越多地运用于社会赈济、救助等领域。漕运线路的变动还隐含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中国古代统一王朝对于内河与海洋选择、利用的价值取向与内在理念。
一、漕运的演进及其线路变动
(一)早期漕运及其路线:由东向西
漕运始于秦汉。《汉书》卷64《主父偃传》记载:秦时,“使天下飞刍輓粟,起于黄(今为山东黄县)、月垂(今为山东文登市)、琅玡(今山东胶州一带)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最初的漕运与军事行动紧密相关,而且属于临时性需求,无定时,无定量。当时京师所在的关中地区尚属富裕之区,对于“凡事草创”、官僚机构尚不十分烦冗的秦汉政府来说,基地所产的粮食尚能满足朝廷的需求,汉初,运于“中都”之粮仅数十万石,“不啻足矣”①;而秦汉两代的军事活动较为频繁,需要大量的粮食作为后盾,因此,漕粮多用于军事活动。
随着经济的恢复、河渠的开凿及政府的重视,《史记》卷30《平准书》记载:元狩四年,河漕达400万石;元封元年,致粟山东一度高至600余万石。这一方面说明漕运在汉代的长足发展以及所达到的规模,“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而“天下用饶”;另一方面表明漕运的运行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秦汉两朝均定鼎西北长安,当时,全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关中和山东最发达,漕粮多半取给予这两个地区,漕运则经由横贯中原的黄河和渭水。因而,漕运方向大致为东西向,即由东向西。这一时期,虽也屡凿河渠,但多利用自然水道,负担馈粮者颇多,加之造船技术低下,漕运经验尚有不足,缺乏统一、严密的组织与制度,因此,漕运费用、损耗极大。《史记》卷30《平准书》称,秦时,三十钟才得一石;汉时,至少也需十余钟乃至一石。
由此,早期(秦汉时期)的漕运表现出如下特征:其一,漕粮多为军事费用;其二,漕运随需而作,属临时性的粮食运输,无常制,无常时,无常额;其三,漕运方向为东西向,依托黄河、渭河由东向西的漕粮运输。
这一时期,由于南方尚未开发,漕运活动并未指向这一区域。但是,汉代漕运的地域范围以及江南。《汉书》卷6《武帝本纪》记载:元鼎二年,汉政府将水潦移址江南,“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说明汉统治者已经注意并利用这一地区。《后汉书》卷35《张纯传》记载:东汉光武建武五年,朝廷委派大中大夫张纯领颍川突骑,安集于荆、徐、扬,“部督委输”。不过,总体而言,秦汉时期这一地区尚未受到重视。事实上,秦汉两代无力也无须从这一地区转输大量粮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重心已出现南移的端倪,江南已引起了更多的统治者与政权的关注,并进而认识到这一地区的经济作用。《晋书》卷100《陈敏传》记载,西晋时,陈敏奏曰:“南方米谷皆积数十年,时将欲腐败,而不漕运以济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因此,一些统治者开始注重沟通南北的水路交通,漕运南方粮食。魏正始二年,开广漕渠,《三国志》卷28《魏书·邓艾传》称,“又通漕运,每东南有事,大军泛舟而下,达于江淮”。广漕渠的开发,沟通了北方与江淮地区的水路联系,江淮地区日受重视。北方政权在两湖一带漕粮的运输途径有二,一是通过江淮达汴(河)、黄(河),一是经由“沔、汉达江陵”,溯汉水,运抵北方。晋时,杜预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水道,“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②。
南方各政权则就地取材,对本地的漕运工作极为重视。南齐时,萧衍令郑绍叔督江湘粮运,以“汉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粮运资储听此气息”③。这说明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正在逐渐提高。
(二)发展期的漕运及线路变动:由东南至西北
隋唐时期,由于统一王朝的建立,漕运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制度建设方面。隋朝立国时间不长,但其两项措施对以后各代的漕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作用。
一是运河的开发。隋文帝四年,为通漕运,开广通渠,从渭河达于黄河;大业元年,开通济渠,引黄河通淮河,以利转输;邗沟的整治则使淮河与长江相接。隋代前后三次进行的大规模的运河开发,使洛水、黄河、汴河、泗水与淮河、长江联为—体,使北方都城与经济日趋兴盛的南方富源直接联系起来,从隋朝的东都可直达江都和两湖。
二是粮仓的设置。隋朝在开发河渠的同时,还在各重要河津设置仓廪,以利转漕。开皇三年,因京师“仓廪尚虚”,隋政府在十三水次募丁运米,并在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以南方漕粮转相输于京师。这一方法对唐、明两代漕运影响很大。唐代漕运采用递运法,在各河段分置漕仓,转相递运;明代采用过支运法:以分置漕仓为漕粮的转运点。
唐代是漕运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时,漕运基本形成了—套制度,其体系已渐趋形成。唐代定都长安,关中虽仍称沃野之地,但其产粮土地狭小,《新唐书》卷53《食货志》记载,“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有唐一代,渐以转漕东南之粟为主。唐初,江淮漕米皆输于东都洛阳,岁不过20万石,高宗以后才逐渐增多。民送租者,皆有水陆之值。高宗始,洛阳以东的水运改为直运,但是,沿线道路多梗,花费颇巨,漕船行驶日少,受阻之日反多。玄宗时,裴耀卿建议仿隋代漕运濒河置仓。于洞口(黄河通汴河的入口)置虎牢仓。巩县置河口仓,使江南漕舟不入黄河,黄河漕舟不入洛河,节级转运,不受季节、水情的影响,河水通畅则运,水浅则“寓于仓以待”,这样,“则舟不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④。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收效甚大,三年转运漕粮700万石。
唐中后期,安、史兴乱,淮运受阻,唐政府被迫另择运道。江淮漕运改由襄汉以达京师,江南漕粮集于湖北,“自江、汉抵梁、洋”⑤。“安史之乱”后,漕运重归原道,江淮漕粮集于扬州北运。转运使刘晏定纲运制,每船载米千斛,十船为一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采用接运,“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⑥,岁漕东南110万石。
唐代,朝廷逐渐把漕运重点放在南方,漕运线路也由秦汉的东西向变为东南西北向。此时,江南地区的经济作用十分明显,漕运地位开始确立。岁供漕者,以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为主。
隋唐时期,漕运表现为如下特征:其一,开始注重制度的建设,以保证漕运的稳定、持续和有效;其二,不少举措和制度的探索,对于后世具有重大的影响和意义;其三,漕运的重心已出现南方的指向,说明南方对于政治中心的经济意义逐渐突显;其四,漕运的方向在东西向仍然保持的同时,东南、西北向的漕运线路越来越重要。
宋代多藉唐代旧法和漕运手段,但比唐代有较大的发展。宋代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组织,北宋漕粮基本上都用于军事和朝官俸禄,而军队占用的比重更大。《御定渊鉴类函》卷135《政术部十四·漕运》记录刘攽《漕舟》一诗,写道:“太仓无陈积,漕舟来无极;畿兵已十万,三陲戍更多;庙堂方济帅,将奈东南何?”有官吏把当时的漕粮支出分为了三份,“二分在军旅,一分在冗食”⑦。
北宋设都汴梁,以汴河、黄河、惠民、广济四河漕运,其中,以汴河所运漕粮最多,主要负责漕运江南、淮南、浙东、浙西、荆湖南、荆湖北六路的粮食,自淮入汴至京师。宋代景德四年始定年漕额为600万石(大中祥符初年一度达700万石),其中,淮南130万石,江东100万石,江西120万石,两浙150万石,湖南65万石,湖北35万石。年漕额的确定,说明漕运趋于稳定。各地漕粮先运至真、扬、楚、泗四仓,再分运京师。由于宋代国都南移,宋代漕运比唐代便利。
自仁宗朝起,宋代漕运改直运法,六路“上供斛斗”并东南杂运至京师,“虽湖南、北至远也直抵京师,号直达纲”⑧。大观年,又复转盘法,但漕运弊端已多,漕法渐坏,以至于“雇舟差夫不胜其弊。民间有自毁其舟,自废其田者”⑨。南宋时期,漕运制度发展甚微。由于京城南迁临安以及频繁的战争,江南地区的漕运地位十分突出。
宋代漕运体现如下特点:其一,漕运制度有很大发展,相对成熟;其二,漕运渐趋稳定,表现为有相应的成法以及额定的年漕量;其三,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漕运重点已移到南方,体现在漕运的方向已由原来的东西向、东南西北向兼具完全转变为东南西北向。
(三)成熟期的漕运及其线路:由南至北
元朝定都大都,京城用粮仍依赖江南(元以前皆指长江沿线及其以南地区)。由于大都在正北,原来的东南西北向运道已不能适应元政府漕运的要求,于是,开会通河,北接御河,下达清泗,至徐州会黄河,南通江淮;又开贾鲁河以通颍、蔡、许、汝之漕;开通会河,联结京(京城)、通(通州)。
但是,由于会通等河属新开河道,岸狭水浅,载重漕船难以运行,元代漕运只好另择蹊径。大都离海较近。元政府依附的江浙地区濒临大海,江湖地区可顺江而下直达海口,因此,元政府采用海运,且终元之世,皆以海运为主。元代运输的粮食数量不多,漕额最多的天历二年,也只有352万石。较之宋代约减一半。元代以万户府和漕运司统辖海运和河运,河运无常,海运则分为春夏二运。
元代属于漕运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时期,漕运体制不完备,发展不大,与前代相异之处就是实行较大规模的海运。元代在海运的同时,对河运也做过一些努力,曾多次设置河运职司,频繁地开凿、疏浚内河,只是效果不佳,旋浚旋淤,畅通时甚少。
明清两代,是漕运制度的成熟时期。明初,朱元璋建都南京,由于运河不通,北运漕粮多取海道,并多为军事所需。成祖即位以后,迁都北京,永乐十三年浚会通河,罢海运,转河运。明代的漕运制度主要是围绕三次漕法的变化而建立起来的。《明史·食货志》记载;明代漕运“法凡三变,初支运,次兑运、支运相参,至支运悉改为长运而制定”。支运,也称“转搬法”,由粮户自备船只,运至淮(安)、徐(州)、(临)德、通(州)四仓。由卫所官军分段接力,运到京师,年凡四次。此法始于永乐十二年。但是,由于百姓运粮“往返几一年,误农桑”,宣德六年,明朝廷改行兑运法,即军民联运,粮户只将粮运抵水次,交由官军运抵京师,粮户只按道里远近,交纳给运军一定数量的耗米和轻赍银。此法沿用数十年,于成化七年被长运法取代。长运又名“改兑”,是直达法。由运军直接赴各地兑运,然后径赴京师,百姓不再负担长途运输,只是在原有的耗米之外,加米一斗。不久,各有漕省“悉变为改兑,而官军长运遂为定制”⑩。
明初,漕粮无定额,每年多寡不一。成化八年,始定年漕粮额为四百万石,这一数额为清初所沿袭。一年一度的漕运往返时间较长,为了不耽误次年漕运,明政府对漕运程限限制严格。宪宗时,规定各有漕省的漕船必在九月初一以前抵达京师。世宗时,进一步具体规定南方各省漕船的出发和过淮时间。
明代,以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山东、河南等为有漕地区,其漕运组织机构十分严密。景泰二年设漕运总督,总理漕政,下辖各类漕运官吏和漕司,领十二把总,由十二把总率卫所屯丁分运各有漕地区的漕粮。
清代,漕运达到其巅峰时期。如果说明代漕运制度还有一个渐趋完善的过程,那么,清代漕运制度则已臻完善。从漕运的组织层次和总体法规来看,基本上是清承明制,但是,清代漕运制度更全面、更具体、更完备,涉及的范围更广。

具体从事漕粮运输工作的旗丁是由明代的卫所屯丁转变而来的,清世,归于州县,专事漕运。清代,裁明代把总,以千总领帮出运,并于地方选一武举“随帮效力”。各船帮在有漕州县兑漕水次上均有固定的分配。
清代,各有漕省根据生产水平的高低、道里的远近、运输的便利与否等因素,确定了具体的有漕府州县。漕额以江浙为最,山东、河南为末,漕粮起交除正、耗米外,还有诸多杂项钱粮。顺治九年,定漕运为官收官兑,州县负责催征。清代政府对漕运的时间要求十分严格,各船持“水程”,由各州县注明其出入境时间。
对于漕船的分配、修造和处理,清政府也有明文规定。清代漕船以载500石漕米为准。漕船使用时间以十年为限满,如若年限未到而致船坏者,视漕船出厂年份,按例追罚。限满漕船可在京师变卖,重新打造。
综观明清两代的漕运,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突出特点:其一,漕运制度完备,其组织和机构较之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严密和健全;其二,明清漕运涉及的范围很广,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漕运不断发挥诸多的社会功能;其三,从明清时期所规定的几个有漕省份看,漕运的重心已完全落在南方。这一时期,漕运线路已转变为南北向,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分立北南的格局下,南粮持续、大量北运。
二、空间上的意义:漕运羁绊南方经济发达之区
中国古代漕运经历了由东西向到东南、西北向再到南北向的转向过程,漕运线路在空间上的这种变动意味着什么?对漕运的指向区域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形式上,漕运是一项经济活动,实质上其政治意义远大于其经济意义,漕运具有十分强烈的政治属性,始终是朝廷最重要的事务之一,与王朝政治休戚相关,漕运线即为生命线。漕运线路的变动是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变动的结果,一方面漕运连接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另一方面,漕运又使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具备分离的条件,分处两地。所以,漕运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构成空间关系的重要因素,需要明确的是,这种空间关系乃政治中心对于经济重心的依赖、索取与牵制,因此漕运实则朝廷羁绊经济发达之区的重要手段。
漕运始终指向经济发达区域。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有一个逐渐南移的过程,对此学术界多有探究,学者们多从南北政局的变动、经济环境的变化、北方人口南下以及北方经济水平的下降与南方的开发、经济水平的不断上升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一般认为,经济重心的南移是一个长时段的过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始现端倪,隋唐五代快速发展,两宋时期经济重心最终转移至南方。应该说,这个观点总体是成立的,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这一经济变动过程的实际情况。然而,经济重心的南移既是一个历史过程,又是社会各领域深层变化的本质体现,经济重心南移在诸多领域均有反映,并引发社会现象和经济活动的变化。与此同时,朝廷与经济发达区域的关系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漕运线路的一再转向十分清晰地揭示了中国经济格局的变动趋势:秦汉时期,黄河中下游的关中、山东一带为农业经济发达之区,也即经济重心所在,这一区域也便成为朝廷的主要赋税征收地,所征赋税通过黄河、渭河由东向西运抵长安,此时的经济重心与政治中心基本上是联为一体。隋唐两代尤其是宋代以后,南方经济崛起并日益成为朝廷依赖的物资供应区,经济重心与政治中心逐渐分离。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唐代以后,政治中心逐渐东移,尤其元明清三代王朝政治中心向东北方向迁移,并从元朝开始确立在了更北方的区域;而经济重心则越来越明确地确立在南方,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于是,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分立北南。





无论是按照哪一种估算方法和数据,朝廷每年须完成四百万石漕粮的征运,耗费的钱粮数额十分惊人,成本巨大。其实,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也是应该计算进去的。漕粮的征派对象绝大部分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对于他们,时间和人力都至为重要。
作为一项重大事务,漕运所体现出来的强烈政治属性意味着漕粮征运的重要性,但高度的重视通常导致对于事务成本和具体问题的忽略,严密的制度意味着保障和规范,清代的漕运制度把诸多人事因素(诸如漕运官员的职权、地方士绅协助征漕等)都纳入到该制度体系的保护之中,这些因素既包括官府的,也包括民间的,既包括各级官员,也包括地方社会力量,而在漕运活动的运行中,制度恰恰为各方官员和地方力量提供了共同“侵漕”的机会;而强烈的指令性意味着地方社会的被动状态,不容置喙地执行和完纳;高成本则意味着地方社会的巨大代价,这不仅把广大的农民直接推向“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境地,而且影响地方社会的发展,并致使地方社会的矛盾不断积累。
由此可见,漕运紧密地关联着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并由此赋予漕运十分鲜明的政治属性。漕运线路既是连接二者的纽带,又是朝廷伸入富裕之区的触角,羁绊着经济发达之区,制约区域经济的发展,并导致地方社会形成复杂的政治秩序,不断强化有漕地区对于朝廷的政治附着性。
三、制衡与调控:线路变动中漕运社会功能的运用
由于漕运线路的变化,尤其是漕运线路趋长,漕粮的运输成为一项巨大的工程,在更大的空间运行中,朝廷越来越认识到漕粮运输所具有的调控意义和价值,越来越多地利用漕粮进行社会制衡。尤其是漕运线路转变为南北方向之后,漕粮征派、运输的空间相对稳定,朝廷的政治意识更为明确,利用漕运解决问题的政治意图与手段也更为成熟。漕运越来越成为王朝的政治手段,用于区域社会调控。
自宋代开始,朝廷开始注重将漕粮用于解决社会问题,调节社会经济发展的失衡,而明清两代,朝廷已经十分重视对于漕粮的利用,并呈现出利用越来越频繁、范围越来越广泛、解决问题越来越多的趋势。朝廷运用集权的优势,充分发挥漕粮的社会功能,对于漕运及其相关环节进行调控,将漕粮用于地方军饷和仓储、平抑粮价、赈灾备荒等方面。不过,漕粮对于区域社会调控效果较为明显的还在于其用于籴粜与赈济。

相对于宋代,明清时期利用漕运调节市场表现出了更大的灵活性。明清两代对于漕粮运输进行随时随地地截留、调拨,以应对因各种原因而随时出现的粮食市场的波动。明清时期的文献记载中,关于截留漕粮用于平粜的记述很多,从这些记载的情况来看,明清两代完全是因事而粜,没有制度的限定,由朝廷直接掌控。如果说,宋代是以籴为主,明清时期则以粜为主。

清代尤其突出,清代政府利用漕粮的实物特性和优势,频繁地截留和拨运远在南方的漕粮,越来越多地运用漕粮来解决社会问题。从时间上看,清代漕粮的截留与拨运从康熙年间开始逐渐递增,至乾隆时期进入高峰状态,表现出持续性强、规模大、频率高的特点;从空间上看,被截漕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各省,受益地区多为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山东、河南等有漕省份,以及福建、广东、广西、贵州、陕西、山西、直隶地区等无漕省份,而直隶地区为受益的重点地区。由此可见,清代漕粮截留、拨运的输出地与输入地的主要区域集中于运河一线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即有漕诸省和直隶地区,无疑这是清代最重要的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于清王朝的重要性而言,皆居首位。清代朝廷认识到漕粮资源的社会意义,利用漕运线路所具有的空间优势与便利条件,充分发挥漕运及其线路的流动意义,在不增加物资、运输等成本的情况下,广泛发挥漕运的社会功能,重点解决运河一线、长江中下游、直隶地区等重要区域的社会问题,兼顾周边或确需急救的其他区域。
截留和拨运总体体现出救助、应急的性质,除了充实军饷、备战应战的用途之外,其充实仓储、平抑粮价、赈灾备荒等均是运用于社会,起着平衡地区积贮、调控市场、安民固本的作用,在朝廷的调配之下,着力解决区域社会问题,调节、平衡、稳定社会秩序。




清代,在其发展的全盛时期,朝廷利用其对于漕粮的完全控制权力,频繁地对漕粮进行截留拨运,极大地拓展了漕运的社会功能。清代漕粮截拨对于政府调节民生、维护秩序以及稳定社会的积极意义由此可见一斑。朝廷通过对于漕运资源的调配,力图解决一系列常年出现的影响国计民生的问题,维系地方社会秩序稳定,客观而言,还是起到了一定的调控效果。
四、运河经济带的生成
随着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分离格局的确立,漕道成为沟通两大重要区域的最重要的通道,而这个通道主要是水道。在中国古代,水道的最大优势在于其往来便捷、承载量大以及便于长距离运输。这便决定了在经济重心与政治中心在远距离分立南北的格局下,借用水道运输漕粮成了朝廷不二的选择。
北宋建都开封,水运漕粮的主体河道是汴河,汴河水上物资运输因此繁盛的记载不绝于书。汴河与江南运河等水道联成一体,承载着大量的南方物资。南宋时期由于都城南迁临安,已经置身于经济重心的区域之内,运道的问题基本上是可以忽略的。
元代定鼎大都,漕运南方的粮食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元代政府在运河全线开凿修浚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自不待言,虽然因为技术方面的问题,元代运河的漕粮运输难以通过运河达成,不得不通过海运的方式北运漕粮,但运河贯通南北的格局正式形成,并在物资运输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明清两代,自明代永乐迁都北京以后,南粮北运皆通过大运河水道完成。巨量的漕粮通过运河运输,本身就意味着运河具备的运输条件、能力和优势。应该说,明清时期的运河已经具有了不可替代的性能。也正是这种性能,促成了运河经济带的形成。从隋唐运河的开通,到宋代的利用,再到元明清时期作为完全意义的漕运线路,运河的社会经济意义和功能逐渐进入全盛的状态。运河经济带不仅在于沟通南北,更重要的是这个经济带成为元明清时期最具活力、最有生机并最有辐射影响力的区域。
这里所谓的运河经济带,主要是指运河水道承载漕粮运输的同时,沟通巨量的南北物资交流,不断促发更多的经济活动与事象,连接更多的区域、市镇、物资、行业与人群,形成一个相对成体系的、流动状态的、具有发散与辐射作用的经济带。因为这个经济带的形成与发展是以漕运活动作为先决条件,且漕运本身也成为这个经济带的要素,所以,这个经济带的诸多问题必须要从漕运的角度去审视。例如,在范围的考察上,至少应该把长江中下游地区纳入这个经济带,该地区是明清漕粮的主要征运地区,因为漕运而与运河构成了一个整体。
元明清尤其是明清两代,运河经济带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经济现象,如南北物资的频繁交流,长距离商品贩运,运河沿线及长江中下游商品经济的活跃,大批市镇的兴起与繁荣,商人群体的汇聚以及大量贸易人员的参与,等等。其中,商品流通的兴盛是带动运河经济带迅速崛起的核心因素。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数量基本无法进行准确的量化计算,但通过漕运而开展的南北物资的交流数量却是可以大概计算出来的。


在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多与交通便利的水道发生密切的联系,无论哪个时期,漕运线路上总是会出现较多的商品经济发达的城镇,尤其是明清时期。这一现象说明,漕运具有促进商品经济活动及相关城镇生长与发展的意义。明清时期,漕船与城镇、水次形成了互为市场、互为买卖的关系。

由漕运线路形成而带来的运河经济带的主要内涵在于商品的丰富和频繁流通、沿线城镇的密集出现、商人云集和商事繁盛。毫无疑问,这个经济带具有十分广泛的辐射意义。
然而其中有两个问题必须思考。

其二,漕运对于商品经济具有的双向作用。漕运对于商品经济尤其是商业贸易和商业城镇或城镇商业具有刺激和促进作用,然而,漕运基本上始终是实物赋税的形式,自南而北地常年不断地运输,由于漕运而南北流通的物质数量十分庞大,尤其是粮食。从市场发生、发育与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家控制下的大规模的物资调配的存在,极大地影响自由市场的产生与发展。因此,由于漕粮的持续供应,围绕京城巨额的粮食消费并未促成巨大粮食市场的形成。从此而言,漕运对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展实为双刃剑,一方面直接推动运河沿线甚至更大范围的商业与城镇的繁荣,另一方面,又限制了更高层次的市场与商品经济的发展,限制了整个国内货币化的实质推进。
五、河运抑或海运:南漕北运背后的海洋意识
漕运何以选择河运,而非海运?这是漕运深入研究中必然会思考到的一个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政治中心都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撑与物质供应,因此历代王朝都会十分重视加强对于经济发达之区的连接与控制,在集权体制的政治背景之下,在市场功能极其微弱的经济条件下,漕运的运输形式成为统一王朝建立伊始的不二选择,通过这种形式,朝廷完成了向地方(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征运粮食的目的。漕运,水转谷也。但水运可以是内河运输,也可以是海上运输。内河运道的形成是自然河道加人工河道的组合,不仅修浚的成本巨大,而且长期的维护与修复更是一项浩繁的工程;海运以自然水道为主,但自然风险有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失。当南漕北运的格局形成之后,各王朝首先都没有考虑通过海运的形式来完成赋税的运输。
中国古代各王朝的经营重心在于内陆,尤其是宋代以后,内倾现象十分明显,着眼于内部空间的治理,海洋意识明显缺乏,这从国家的大政方针到朝野的各种认识皆有充分的反映。朝廷对于海域的关注,都是针对出现的问题,尤其是统治秩序与王朝安全的问题。其潜意识中海岸线几乎就成了边境线,因此,各王朝除了对外贸易的需要而有所涉及海域外,基本放弃对于海洋疆域的治理与利用,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国家对于东南海域知之甚少,水情的了解、水道的勘察与开发、海上运输技术等几近于一张白纸。因此,既无观念上的重视,又无技术上的支持,东南海域的各种资源被长期弃之一边。
中国古代的赋税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征自各地的赋税(包括诸多的项目),另一方面即是所谓的漕赋。前者在地方征收以后,各级官府按比例留存和起运上交。留存是地方官府将赋税的一部分留下,作为地方行政的运营所需,起运则是将另外部分上交朝廷,进入国库。地方和中央的比例分配以3∶7为主,但也有地方存在4∶6的比例分配。这种赋税交纳包括粮食、丝帛、钱钞等;而后者则是所谓的漕赋,属于实物的性质,虽然有些地区有折色交纳的情况,但都有比较特殊的原因。无论是赋税还是漕粮,都关系到王朝从中央到地方的生存、运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任何一个王朝都不会将漕运置于不了解、不安全的运输环境之中。因此,我们可见王朝不遗余力地开凿运河与年复一年地疏浚运道,虽然成本毫无穷尽,但朝廷坚定不移地选择河运。
汉唐宋时期,都城确定在长安、洛阳、开封,从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空间关系上看,漕粮确实没有海运的必要。然而元明清三朝定都大都、北京,漕运选择海运应该具备了较为充分的理由。然而,河运仍然是三朝漕运的首选。

明初,建都南京,漕粮北运只是为了北部边防,北运漕粮的负担不重,明初朝廷选择了海运的方式,这仍是因为运河无法重运通行而沿袭了元朝以来的海运方式。然而,明初的海运是短暂的,明成祖迁都北京,对元代运河河道设施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治理与改造,使河道趋于规划合理,水量相对充足,管理制度渐成体系,疏浚护理成为常态。此后全面实行河运漕粮。

由上述可见,元明清三朝皆有海运漕粮,尤其是元代,海运成为王朝漕粮运输的主要方式。但是,元、清两代的海运皆为河运的转变,转变的原因都是因为河运无法运行和维持,属于运输方式的被迫转变;而明代一旦条件具备,便不遗余力地全面实行河运。对于王朝的统治集团而言,河运始终是主导,实施海运实为无奈的选择。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海运仅为河运的补充。

内河漕运所促成的社会经济格局具有很大的脆弱性,持续的商品流通与物质交换很难引发区域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变化。试想,如果实行漕粮海运,中国古代的商人集团是否会是另一种政治与经济环境?商品市场是否会有更好的社会环境?中国的海域与海洋资源是否会得到更充分的开发和利用?中国的海洋社会是否会是别有一种情景?这是一种假想,或历史发展的另一种可能,并非真实的存在。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的海洋探索与追求从未停止,但国家的海洋意识与深度融入至为重要。
注释
①《史记》卷30《平准书》记载:“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18页。丘浚《大学衍义补》卷33《漕挽之宜(上)》按:“然是时也,凡事草创,所以给中都官者仅数十万石,不啻足矣。”《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17页。
②《晋书》卷34《杜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31页。
③《梁书》卷1《武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0页。
④⑥《新唐书》卷53《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66页,第1368页。
⑤王殿甲:《漕运汇选》第四章《漕运史料》,民国刊本,第20页。
⑦《宋史》卷179《食货下一》载,天章阁侍读贾昌朝言:“计江、淮岁运粮六百余万石,以一岁之入,仅能充期月之用,三分之二在军旅,一在冗食,先所蓄聚,不盈数载。”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351页。
⑧嘉庆《湖南通志》卷36《田赋·统部》,布政使司衙门藏本,嘉庆二十五年重修,(本卷)第2页。

⑩《明史》卷79《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18页。





































责任编辑 梅莉
Grain Transportation from South to North:Direction Changes of Water Transport’s Line and Its Significance
Wu Q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In ancient China,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enter of a region were connected by water transport, and the direction of water line was always in change. In the Hang and Tang period,water transport was in the direction of east-west. In the Tang and Song period,it changed into the southeast and northwest direction. And in the dynasties of Ming,Qing and Yuan,it further changed into the north-south direction. The frequent change of direction signifies the geographic movement of the reg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enter which means the separation of regional political center from the economic center, with the former locating in the north and the latter in the south. It also brought the transporta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grain from the south to the north. This significant change of direction shows that, as a way of in kind tax the water transport continued to exist and becme a tool of the political center to conta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 center. On the other hand,due to water transport’s characteristic of long distance,each government realized its function of reconciling and controlling the society, so water transport was used in social relief and assistance more and more widely. In addition,water transport led to the changes of the pattern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promoted the birth of canal economic belt which had the huge economic significanc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inally,there is underlying question behind the direction changes of water line, namely why ancient China always choose river transport and what is its value orientation and inherent reason.
ancient China; grain transportation; grain transportation from south to north; change of water transport’s line; canal economic belt
2016-07-10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漕运对于区域社会环境影响的实证研究”(14AZS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