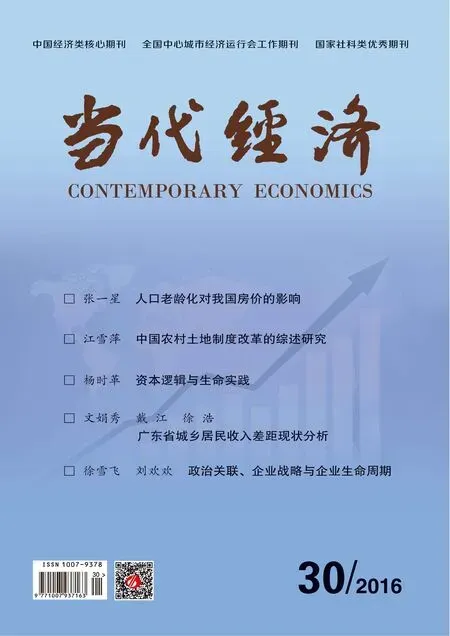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综述研究
江雪萍
(华南农业大学 数学与信息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综述研究
江雪萍
(华南农业大学 数学与信息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本文从制度变迁理论、产权理论的视角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研究进行文献梳理,主要从农地制度演变的过程对现行农地制度的制度缺陷,现有农地所有制关系的争议,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地权的稳定和土地承包立法等方面进行概述。
农地制度;农地产权;产权明晰
中国农村最基础的制度是土地制度,而“三农”问题中的最基本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村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源于我国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土地的所有制度和经营制度就成为农业最基本的经济制度,而且是国家经济社会制度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一、农地制度演变的四个过程
从建国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在不同的政治环境变化影响下,经历了大致四个相应的演变发展过程。一是,建国初期实行的土地改革,把封建土地制度改变为“耕者有其田”的农民所有私营制,呈现出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二是,以土地改革为基础,实行以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入股分红的互助合作形式的农民私有合营。三是,借助高级农业合作社、农村人民公社来实现的集体公有公营。从制度变迁理论和产权理论来分析,人民公社制度存在包括产权模糊和残缺、代理人的两难选择、监督和激励的困难、退出机制的丧失等缺陷(傅晨,2001;陈剑波,1994),从而在70 年代末,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实行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即“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因而农地制度演变到第四个阶段,通过建立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互分离的新土地制度,使农民获得了自主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权利,重新确立了农户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形成了现有的家庭承包背景下的农地制度。
二、现行农地制度的研究概述
但是家庭承包制背景下的农村土地制度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农地制度的极限,结合我国特殊的国情和经济发展态势,现行农地制度的研究主要关注其制度的缺陷、土地所有制关系的调整、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地权的稳定和土地承包立法等等。
1、现行农地制度的主要制度缺陷
(1)土地产权的主体和客体模糊,即其主体虚置、权属关系不清。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是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还是集体组织的成员所有,“集体”是指哪一级等等在政策法规上依然比较模糊。在法定体制中,“集体经济组织”并未明确指定,在现实村庄中最重要和最关键的角色由村委会承担,而村委会作为政府代理人、集体财产法定代理人和公共事务管理者,在政府行政、村务管理、农民财产保护方面,其三位一体的角色蕴藏着巨大的矛盾冲突(陈剑波,2006),政治权力结构使乡村干部成为土地所有权的人格化主体(党国英,2005),出现大量的土地违法行为,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从而一定程度上导致集体统一经营形同“虚设”。
(2)农民的土地产权不完整,依然残缺。农户的土地经营权虽然相对充分,但财产权严重不足,也没有退出集体经济的权力,不具备完整的自主经营权,土地使用权保障预期很低(党国英,2005)。比如,农民不具备土地抵押权,无法抵押土地使用权以获取银行贷款。还有,虽然农民具有土地的转让权,但现有农地产权主体不明晰,产权不完整,产权交易市场不完善,使得现实土地资源要素的配置扭曲,土地产权无法有效的交易和变现,产权效率很低,农民并未能实现有效的产权收益(阮建青,2011)。此外,农民由于各种原因,往往缺乏充分行使自己土地权利的能力,组织化程度也较低,使得其土地权益易受侵害,这使得产权缺乏有效的实现途径和保护机制。而如何行使和保护农民的土地产权,现有的政策和规范却是落后于实践发展的需要。
(3)农业经营规模不经济。农村按人口均分土地的方式形成了超小型的小块土地经营格局,而人动地调的方式进一步强化了土地经营规模不断细分的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土地均分细化的持续进一步促使了土地经营的兼业化和副业化,严重阻碍了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郭晓鸣,2011)。我国农业的关键问题是小规模家庭经营,主要是小规模与细碎化、兼业化、副业化、老龄化与妇女化,农户“不以农为主、为生、为业”(罗必良,2007)。
(4)土地承包关系不稳定。农民的承包地由于人口变动而频繁调整,土地经营规模更趋于细小和零散,由此,农民无法对土地经营产生稳定的经济预期,将加剧其对土地的短期化掠夺或经营行为。如此不稳定的土地分配和调整方式更使得土地经营权市场难以发育。
(5)土地产权不对等。我国土地被划分为国有和集体所有两种,严重的不对等普遍存在于两类土地的产权中,国有土地可以在一级市场交易(阮建青,2011),而农村集体土地只能通过征收转为国有,而这一过程中政府过度介入现象日趋严重,普遍的“代民做主”使农民权益被大肆侵害。政府为增加土地财政而竞相进行的土地掠夺造成大量农地的流失。
2、土地所有制关系的争论
学者们认为,现行土地集体所有制造成土地经营规模过小,从而导致农业经营规模过小而引发农村改革的突出矛盾,这就使得调整土地所有制关系成为讨论热点,主要观点有土地产权私有化、土地产权国有化、在坚持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完善。
(1)农地私有化。中国农村现在面临的最核心问题是土地制度问题,而农村土地不属于农民所有是“三农”问题的根本症结,应当实行土地私有化(杨小凯,2002)。反对土地私有原型,即私人拥有土地的目的是为了耕种,就是认为农民不会认真种地,应该在加大国家土地管理力度的基础上使土地私有原型明朗化、稳定化(魏正果,1989)。还有学者提出,在某些地方,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只具有一定的法律象征,农民倒成为土地的实际所有者(李庆曾,1986),应当将农村土地的所有权给予农民,真正实现马克思所说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李永民等,1989)。上述观点对中国国情缺乏深刻认识,中国农民未必欢迎土地私有。而且在经济转型期,农地私有产权的农业绩效低(陈志刚等,2007)。土地私有化将引发巨大的政治风险(刘国臻,2006),将使中国爆发 “马尔萨斯危机”的可能性处于不可控制的境地(杨成林等,2011)。
(2)农地国有化。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土地公有制,现行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主体缺位,产权不够明晰,只强化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农村土地名义上是集体所有,实质上却是国家所有(文迪波,1987)。有学者认为,现实可行的一种制度选择是实行土地产权国有化,这不会引发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剧烈动荡(安希伋, 1988)。国家所有,私人经营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最佳选择,便于国家对土地资源的高效管理(杨勋,1989)。一方面可以通过国家租赁制,全部土地国有,成立专门的经营管理部门,将土地租给农民,农民按租赁合同规定向国家缴租、纳税(蔡昉,1987;杨勋,1989);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国有永佃制,即所有权归国家,不允许土地的买卖或转让,通过法律形式将土地使用权永佃给农民,政府只征收统一地税(安希伋,1988)。但上述观点也受到了质疑,包括土地转归国家是通过收买还是剥夺,如何解决在农地利用过程中的纵向困境和横向困境(陈志刚等,2007),所有权被形式化是否就是私有化等等。
(3)坚持完善土地集体所有制。根据我国现阶段社会生产方式和基本国情,现行的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制度是基本适应的。因而,农村土地制度现阶段改革的重点不是改变土地所有制,而是完善两权分离机制,土地经营使用制度的改革是核心,促进土地有偿使用和合理流动机制的建立和健全(刘书楷,1989)。在农村土地制度建设上,关键是稳定和强化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力求强化农民承包权,明确土地所有权,积极开辟承包权流转市场(骆友生等,1988)。深化改革家庭承包制,核心是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实现土地使用权的长期化,把土地承包期限延长,把农民土地使用权内涵拓展,并给予制度确认和法律保障(迟福林,1999)。还有学者提出建立“土地微观使用决策权、收益权以及一般转让权归农户,宏观使用权与最终处置权归国家所有”的复合土地产权结构的观点(曲福田,1991),并对农地制度和征地制度提出改革方案(党国英,2005),还从农业绩效优化的角度探讨了农地集体所有制是相对较优的所有制安排模式(陈志刚等,2007)。上述观点坚持“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给农村土地制度未来发展进一步留下空间。
3、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
(1)土地制度创新的前期实践。新制度经济学和产权学派的理论,为农地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更为广泛和深刻的理论支持。现行农地制度的合约结构,农地经营的组织特征,农地产权安排和产权残缺等因素在制约着农户的投资、积累和长期预期(刘守英,1993)。由此开展的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局部实践,包括“规模经营”、“四荒”使用权拍卖、“两田制”、土地股份制等制度创新。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改革体现了新产权合约及其执行和保障系统之间的互相配合,不仅仅是产权创新(周其仁,1995)。中国农村改革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是赋予了家庭经营的劳动者剩余索取权,从而不必对劳动进行监督和计量(林毅夫,1992)。
(2)土地的市场化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够畅顺,农地征收矛盾突出等现象的原因在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不明晰、土地流转制度不够完善、农民的土地权利无法得到有效的制度保障等(郭晓鸣,2011)。应该通过农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流转,而不是土地的行政调整,来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杨学成,2001)。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如何加速和规范农地的流转成为关注的热点。大量的实证研究关注农地流转的各种影响因素(罗必良,2007;傅晨等,2007)。当前全国各地普遍面临的农地制度改革复杂难题,就是规范构建土地有限产权的交易制度、实现对有限产权的利益保护。
(3)近期土地制度改革的典型模式。在推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这些年以来,出现的比较典型的创新模式主要有“成都模式”、“嘉兴模式”和“苏州模式”。其中,“成都模式”是以“还权赋能、农民自主”为核心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包括确权颁证有权,出台相关法规,搭建交易平台,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投资平台,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在全国率先设立耕地保护基金。而“嘉兴模式”是指“两分两换”,把宅基地与承包地分开、搬迁与土地流转分开,以宅基地置换城镇房产、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等权益。“苏州模式”是指“三集中”、“三置换”与“三大合作”。此三种模式具有创新意义和典型意义,是因为它们加强了土地资源的规模利用,改进了农业生产效率,实现了农民土地的财产性收入,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它们的出现都是朝着制度演变中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方向发展的。
4、地权的稳定和土地承包立法
(1)探讨地权的稳定。学者应用计量经济模型探讨农地制度与农业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农民的绿肥使用面积受到地权稳定性的显著的正面影响,产量并未受到显著影响。稳定地权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促进土地长期投资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而不是产量的立竿见影的效果(姚洋,2000)。还有实证研究以广东省为例得出,土地产权制度安排或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不仅影响农民对农业用地的长期性投入,以提高土地肥力,还影响其农业用地的短期投入(何凌云等,2001)。从土地的职能角度来看,土地的长期稳定产权在于稳定农民的社会保障,学者认为,在当前土地对农民的生存保障功能重于生产功能的条件下,土地规模是影响农户家庭经营投资行为的决定因素(温铁军,2000),土地的长期使用权促使农民投入的增加,通过农业产量来提高农民的收入。
(2)土地制度的法律困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性质是法学界的民法学者和产权经济学者讨论的主要议题。大体上看,中国相关法律的改进已经整体滞后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实践。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中,促进土地流转相关的法规有很强的限制性,自愿性的谈判协调机制和利益激励机制极其缺乏;不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直接与集体经济组织协商,不可以直接通过土地产权交易在集体土地上从事非农业建设和经营活动;政府对农用地转化为非农用地拥有绝对控制权,农民作为土地产权主体所应有的权利被极度忽视,农民在土地利益分割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郭晓鸣,2011)。学者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的研究正试图不断分析和解决上述法律困境。
综上所述,现行农地制度中,家庭经营条件下农民得到的土地长期经营权,并不是诱致性的制度变迁演化而来的,并未经过市场途径,还是通过国家强制的制度安排而得的,这就使得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仍存在其产权被不断侵蚀模糊的可能,特别是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因此,进一步推进农村土地产权明晰化进程,不断加速农村土地适度集中和规模经营,依托产权的分割和产权的流动,构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发展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解决好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等将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发展思路。
[1] 文迪波.《还农村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本来面目》,《农业经济问题》1987 年第 8 期.
[2] 安希伋.《论土地国有永佃制》,《中国农村经济》1988年第 11 期.
[3] 杨勋.《国有私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现实选择》,《中国农村经济》1989 年第 5 期.
[4] 魏正果.《我国农业土地国管私用论》,《中国农村经济》1989 年第 5 期.
[5] 李永民,李世灵.《农村改革的深层障碍与土地产权构建》,《中国农村经济》1989 年第 4期.
[6] 刘书楷.《构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基本思路》,《经济研究》1989 年第 9 期.
[7] 骆友生,张红宇,高宽众.《土地家庭承包制的现状判断和变革构想》,《经济研究》1988年第 11 期.
[8] 孔泾源.《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过程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1993 年第 2 期.
(责任编辑:李 健)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比较优势、农业分工与生产性服务外包”,项目编号:k(15YJC790036)。
——基于农地福利保障调节效应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