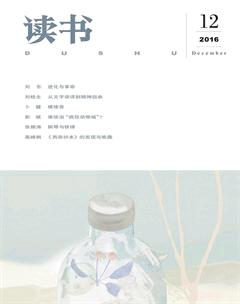本土化:学术与意识形态的双重诉求
所有关心中国时局的人都会发现,最近几年,整个中国的思想气候、文化气候、学术气候都正在发生巨变。整个舆论环境正在被重构。这一状况正在促使人文社会科学产生结构性改变。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这艘巨轮已远离起航时所依托的“反文革”海岸,进入到一片相对陌生的水域。静水深流,烟波万顷,在这片空旷的水域里,这艘巨轮将会驶往何方:是“文革”“西方”“传统”,还是某个未知的彼岸?这是所有关心中国未来的人最想知道的。《把中国“中国化”—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一书中所收文章,反映了笔者近年对这一问题所做的跟踪观察和初步思考。
在我看来,整个中国正在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发展,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任务是加速向本土化转型。促成这一趋势性变化的当然有意识形态因素。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综合国力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掌握相当话语权之后,当局希望在世界文化话语体系中也能掌握相应话语权,这大概就是近年来主流学术机构纷纷高扬“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大旗的出发点。但本土化显然还有更充分的学术自身的原因—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是上个世纪初以西方,特别是以欧美为蓝本建立起来的,这个结构体系的所有层面和板块主要是西方的,包括所有的研究范型、理论工具、方法路径、设计旨趣均是西方的,基本上是一种全盘性的横向移植。这套西方的解释体系与中国经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脱节,则是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学界有目共睹的事实。此一脱节现象近年表现尤剧。当“理论”和“模型”与“经验”不符时,我们应该放弃或调整什么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本土化”或“中国化”主张的由来。譬如,中国近三十多年来以快速工业化为内容的经济奇迹的发生,用西方的“经济模型”是无法解释的,但我们又没有同步发展出基于中国经验的自己的“模型”,所以呼唤本土模型的主张应运而起。
其实,中国的本土化趋势早已被海外观察家敏锐地捕捉到了。当今世界所发生的最重大事件,就是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重心正在东移。著名的《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用“东方化”这一概念来概括这种转移。他最近出版的专著《东方化》,已经引起西方主流学界的普遍关注。二○一六年八月十五日,拉赫曼在《金融时报》发表《全球重心东移,西方霸权式微》的专栏文章,再次对他所提出的“东方化”及“东方化时代”概念进行了强调。我认为,拉赫曼提出的这两个概念十分重要:西人眼中的“东方化”,不正是我们自己眼中的本土化吗?最近,著名汉学家包弼德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目前中国的发展,在借鉴世界先进技术与文化的同时,更应着眼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中国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关于社会制度、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如何改善人类福祉的看法,对于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仍然具有借鉴意义。”(见《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二○一六年第四期)无论这些西方人做出这样的判断有何初衷,都表明他们已经预测中国的现代化试图要走一条与西方迥然不同的道路。
如同前面所说,本土化,已成当下学术和意识形态的共同诉求。尽管来路与去向可能并不一致,但怀抱这一愿望的学者与政治家在这一点上已可能走到一起。这其中无疑包含着官方的政治考量,但更多的则是处在大过渡时代的中国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正是因为存在这种纠缠,所以对本土化取向进行否定的学者往往会将学术本土化归结为对政治的依附。其中多多少少存在着误解。关于本土化的争论往往成为意识形态上的站队,原因也在于此。这也反映出转型期中国学术的一种无奈。
自从本书的若干篇章刊布之后,不少朋友,特别是熟悉并关心我的老朋友,就产生了一个疑问:这个人是不是也“转向”了?有的朋友甚至开玩笑说:早岁“西学”,晚年“中学”,是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一个常见现象,现在又添了一个新例证。笔者的解释是:这些文章不过是指出了一些正在发生的变迁,某种已形成趋势的走向,如此而已。这就如同我说天要下雨或已经下雨了并不意味着我祈盼下雨和不希望下雨一样,我只是指出了一个事实而已。这样解释是想说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是不应混淆的两回事。
笔者认为,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前者似乎对学者更为重要,因为它是所有认知形成的基础。即使事实判断与价值立场存在冲突,我们也必须本着对对象负责的精神首先做出事实判断。这是一个学者,特别是一个学术史研究者应该独立于研究对象的最起码要求。坦率地讲,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向与我及相当一部分有启蒙背景的人的心理预期有着不小的差距,也屡屡有让人感到愕然之处,但我觉得,个人的情感倾向与揭示出真正的学术变迁相比并不更加重要,在学术研究中我们只有尽量克制自己的好恶,才能更加接近真相本身。
(《把中国“中国化”—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王学典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