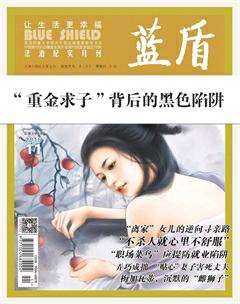陆川 我一直在拍生存的挣扎
郑廷鑫
拍第一部电影《寻枪》前,陆川去选景,行经广西,看到路边处处树着“陆川补胎”的牌子,颇觉奇怪,一问才知附近有个陆川县。该县有两样东西出名,一样是补胎,一样是陆川猪。十几年后,陆川参加电视节目,主持人王自健拿出一袋写有“陆川猪”字样的肉干请陆川品尝,自己却拒绝来一块,因为“不能得罪你”。
其实陆川已经用“猪猪”作为网名多年。他亲手组建过小团体“猪盟”,或叫“猪友会”。大家叫他猪老大、猪哥哥。他的粉丝说,我们叫“粉条”更合适,因为猪肉炖粉条。偶尔有新来的人在他博客上问:你怎么会叫猪猪?像个小女孩的名字。他回答:我属猪。
以上这些实在不像陆川导演的一贯形象——严肃的、深沉的、文艺的;面对争议,总正面对杠,大声为自己辩护;容易落泪,但不卖萌,不自黑。尽管卖萌和自黑已经是这个时代应对嘲讽的有效武器。
他的第一个网名“愤怒的猪猪”也许能联结这两个形象。那是1999年到2002年,他是新浪论坛“影行天下”版的版主。《愤怒的小鸟》还没有面世,那些圆滚滚的绿猪形象还没有深入人心。那时,“愤怒的猪猪”为了电影整夜灌水拍砖,“开始拼智慧,然后拼打字速度,最后拼体力。说理说不过,还有骂。用各种马甲加入战团,如同指挥着千军万马。”
之后,他在严肃的“愤怒”道路上跋涉前行,直到拍第6部电影,才拐到了可爱的“猪猪”道路,制作迪士尼的自然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5组顶尖摄影师拍了18个月,重点讲述大熊猫、雪豹、金丝猴三家的萌系故事。自然电影不同于传统的纪录片,虽然在拍摄中同样不允许干预拍摄对象,但在后期制作时,自然电影在强烈干预,用拍摄的素材重新讲故事。
小葫芦
陆川现在每天6、7点起床。这位在家“能躺着绝不坐着”的主儿,以前都是9、10点起床。去年10月,儿子小葫芦出生,他发现如果还按以前的作息时间,就见不到醒着的儿子。于是,他调整作息,早上带胖儿子出门遛遛,再去上班。
他给小葫芦换尿布、喂奶、洗澡……他猛然发现世界新的一面打开了,他本来觉得活到四十多岁,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知识是他完全不知道的了。小葫芦一来,他发现,以前电视里播的傻乎乎的母婴产品,原来缺一样都不行。电影里的父子母女桥段,以前觉得俗,嗤之以鼻,现在一看就揪心。他突然开始给朋友们的孩子买礼物,尽管有的孩子都十几岁了,从来没收过他的礼物。“算弥补我这么多年对他们的忽略。”陆川说。
生孩子那天,他特意约来朋友,给太太拍一套美美的纪实照片。他觉得这是电影人的记录本性,是一定要做的。后来拿着反复看,每次都觉得特别值。他甚至发了三十多张照片在微博上,感觉像自己的第6个作品首映。“那事其实是做给自己的,就是有特别强烈的冲动要去跟人分享。”他说。
小葫芦出生后的大半年,正是陆川剪辑《我们诞生在中国》的大半年。孩子出生后两小时,他不得不离开医院去机场,飞到洛杉矶开剪辑会。然后就待在英国和美国剪,不时看看小葫芦的照片。一个月后,他受不了,要求无论如何得回家一段时间。这可不像他的工作风格,做《九层妖塔》时,他在公司沙发上睡了半年。考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时,他在办公室的折叠床上睡了一年。他之前拍每部电影都把自己折磨得筋疲力尽,用他自己的话说:“像个巨大黑洞,在肉体和灵魂上都要吞噬你,最后完全把你吸进去干掉。”
尽管英国可以退税,在那剪辑更省成本,迪斯尼还是同意陆川回北京剪一个月。到了春节,美国人不懂这日子对中国人的重要性,继续安排了工作。陆川又请了3天假,来回飞机占去一大半,只剩三十多个小时跟小葫芦待着。还是想见一下。
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诞生在中国》。“很多媒体朋友看完之后说,不太像我的东西。可能这些帮我发现了人性中的另一面。”陆川说。
1999年,陆川在博客的第一篇文章里写:“对于婚姻我有恐惧,这来源于我对于父母婚姻长年的偷窥与思考。……当我看见父亲年复一年地坐在同样一个主席位置上冷漠地吃饭和宣布着命令,我感到婚姻的本质是一个陷井。……于是我幼小的心灵中便坚信这样一个信念:婚姻会使人失去理性和崇高的品德。”
现在再问他,他笑笑说:“我这观点其实没有太大变化。婚姻确实会让人钝化。婚姻和养育意味着要付出和妥协,但创作是自私的、独裁的。家庭生活需要你改变自己,创作需要你别改变自己,你最好像一把刀子一样越来越尖利。”
他已经开始想到,男孩跟父亲在很长一段时间会是敌人。“所以我很珍惜现在这段时间,在他还没能力成为我敌人的时候。”他当然希望小葫芦生活得健康积极,但又觉得,童年有了挫折和艰难,才能够给人灵魂中注入一种有力量的东西。可挫折和艰难的程度难以把握,要是过量了,容易像自己一样,成为看很多问题悲观的人。
羊头白蘑菇
陆川的每一部电影都和前几部看来很不相同。不过他觉得里面有一以贯之的东西——总在拍生存/生命的挣扎。
“这种生存挣扎的感觉会吸引你吗?”我问。
“不是吸引我,我觉得它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他停顿下来,垂眼想了一会儿,猛然抬眼,“对,它确实会吸引我,你说得很对。因为我感受到的是,人生中自由、快乐、满足都是暂时的,而那种挣扎、纠结、困顿、迷茫的感觉却是永恒的。那个主题贯穿一生。包括我看我孩子,他一天天地从混沌、懵懂走向一个理性的世界,但他是不是在走向幸福?真的,未必。我觉得他后来会发现,现在做的所有事情只是一个准备,一旦冲进去,并不知道会面对什么。”
《我们诞生在中国》里,陆川最喜欢雪豹达瓦的故事。一开始,3个故事都是太平安定的,“全是好人好事”。雪豹妈妈养大了小雪豹,肥壮的小家伙们开始出门打猎了。陆川觉得这不是中国,“在中国没那么顺的事儿,我觉得这个不是我的电影。”有一天,他偶然跟英国剪辑师说,有没有你扔到垃圾箱的素材,你觉得肯定用不了的,给我看一看。对方拿出一个硬盘,里面存着他觉得永远都不可能出现在迪士尼电影里的素材。陆川找出了雪豹和牦牛搏斗的镜头,还看到了好几只雪豹的死亡,有的病死,有的冻死,有的死在血泊里。他突然觉得,这故事有了。
达瓦和牦牛搏斗,重伤,挣扎很长时间,浑身是血,被大雪覆盖。美国人看到惊呆了,这是要给全球的孩子看的,不能这样残忍。陆川剪掉挣扎的过程,一帧帧擦掉血,把毛发还原成干净的颜色。“你意识到没有?你从小看大的动物世界都没有血。其实真正的捕猎都是血肉横飞的,叭一口,咬到动脉上,血刺啦就出来了。”他比划着血喷出的高度,“我这次才知道,这些镜头都被处理了。”电影的末尾,仙鹤带着动物的灵魂去投胎,熊猫又产了一胎。这是一个轮回的故事。
陆川对神秘主义的东西着迷。他朦胧记着小时候在新疆,最多两三岁,他在草坡上看到许多大大的白蘑菇,走近了才知道是农场杀羊时丢下的羊头。他多次说起过这个场景,里面有他敏感的暴力、死亡和神秘。他还写道:“那时我浑身上下都绑着皮带,把能捡到的棍子都插在身上。妈妈说这昭示着我未来的命运,从军。”
体制中的作者
陆川本来没想从军。5岁时,他随着上海籍的父母从新疆来到北京,进了广电部大院,父亲被公开宣布要审查,一审就是4年。周围的孩子没人理这个新来的家伙。他记得一帮孩子去一户人家看电视,只有自己会被择出来不让进。
后来,瘦弱的他经常会被院子里的孩子暴捶。而在家,他因“不喜欢学习,热爱撒谎,经常挨家长的打”。他写道:“我经常幻想自己能身强力壮,具有超凡的功力,打败那些欺凌我的人。我经常陷入这样的幻想:单枪匹马,如虎入狼群一般独自一人暴揍全楼的孩子。在上学的路上脑袋中还编织着这样的故事,有时候嘴里还嘀嘀咕咕地念叨出来,手舞足蹈,两眼发直。”
14岁时,他看到了电影《红高粱》,想成为一个导演。父母觉得荒唐,母亲想让他成为医生,父亲想让他做学问。高考那一年,遇上特殊的日子,父母觉得还是军校安全。而陆川想离开北京,去外面看看。他去了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英语专业。
在那里,牙刷、牙膏在牙缸里的方向要一致。男生也得每天伸出手,检查是否剪短了指甲。惟一能够表现出一点个性的是比拼谁的皮鞋更亮。
1993年毕业文艺汇演,他们队偷偷打探来其他队的表演节目,全恶搞串在一起,提前演出来。比如人家跳秧歌南泥湾,他们就扮猩猩跳南泥湾,人家唱《我们工人有力量》,他们就扮猴子唱《我们工人有力量》……等人家再出来,完全演不下去了。
大学入学教育时,学院领导说我们要做无名战线上的英雄,陆川觉得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类似的激动还出现在陆川作为奥运火炬手在沙滩上奔跑200米时,他本能地热泪盈眶。事后他思索激动从何而来,“因为我参与、见证了一个历史时刻?还是这个机会蕴含着巨大的荣誉和责任?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意义?说实话,我也一直没有想清楚。”
2009年,他回母校做讲座,说起了部队生活对自己创作的影响:“我觉得我内心能够有更大的力量,或者说,在拍东西、选择题材的时候有更大的情怀,都跟在军队这8年密不可分。因为我们心里面,不管怎么样,都会有国家、民族这个概念,肯定不是一个小我。而这个东西确实是在军校的这4年,非常强制性地给到你内心中间去的。”
陆川的电影总在追求某种崇高,几乎都在讲述各式略有缺点的英雄:拍南京大屠杀,他一开始想到的落脚点不是展现惨烈,也不是探讨人如何变得如此之恶,而是中国人如何抗争。拍《王的盛宴》,主角刘邦不是英雄了,但另两个主角项羽和韩信成为理想主义者的化身,虽然他们在历史上的形象并没有那么清白单纯。
陆川的硕士论文题目是《体制中的作者——新好莱坞背景下的科波拉研究》。本来他想研究黄建新,但后来放弃了,他觉得研究外国人应该会更自由一些。论文里写的体制是以观众为核心的好莱坞体制。他写道:“科波拉逐渐在体制中成长,并找到了在体制中生存/创作/成功的思路:这就是尊重个人艺术信念,在创作中坚持对于人类命运的探索;与此同时,尊重体制的核心要求,自觉地从自身电影体制所赋予的土壤中出发进行创作;并以高度的自觉区分个人创作和大众艺术创作的创作姿态,尊重体制的期待。”
几年后,他拍出了《寻枪》,在和倪震教授的访谈中说:“我比较想做主流电影,想做能在电影院里放的那些电影,而不是一个酒吧电影,同时这个电影里又有个性化的东西。”
在抢车位的游戏中,他都能寻找到体制的秘密。他发现新注册小号可以为主号提供隐秘的地下车场。而网站也获得了更多的注册人数。“我突然觉悟到这是规则保护下的作弊,这是一个双赢的博弈。一个新的财富时代开启的时候,必须要深入了解规则,了解体制。”他写道,“这个简单的现实告诉我们,要在体制中生存且生存好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和体制保持同谋关系的同时,也要保持距离,要让自己具有体外循环的机能。”
完美主义式修改
陆川执拗起来,10头牛都拉不住。他想拍南京大屠杀,没过审,没资金,他个人打借条借了100万建剧组。此时他已工作十多年,房还没买。办公室的墙上,红纸黑字贴着“决战南京舍我其谁”,另一边是黄纸黑字的“还历史本貌”、“死磕”。他四处找关系, 向人陈述他要拍摄的理由。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案头那时有4个南京大屠杀电影策划案,只能拍一个,本来从任何角度说也轮不到陆川。但陆川最后成功了。
《九层妖塔》拍摄前开过几次座谈会,陆川看到了盗墓现场的录相:棺材碎了一地,骨头和陪葬的东西到处乱丢。盗墓的人说,如果坑里有一万件瓷器,他们会挑10件好的拿出来,其他全部砸碎,保证这10件卖高价。陆川觉得“一下子给顶着了,反胃。这是入室抢劫,没有任何可以去美化,不管你用任何传统去包装它”。陆川决定不拍盗墓。
“编一理由去盗墓我觉得还是能找到,墓穴里的东西献给国家什么的。但我就不想写,就这么简单。”陆川说,“我没必要给盗墓贼找理由。”哪怕这明显会惹恼原作的众多粉丝。在这部商业大片里,他还塞进一句“让孩子先走”,发生在石油小镇被怪兽袭击时,明显嘲讽当年那句“让领导先走”。
完美主义让他到了拍摄现场仍然大改剧本,或者说,这就是他的创作方式。他会对演员说:“这本子就是一个垃圾,你可以把它扔掉。”演员吓一跳,自己嘀咕,导演这是你写的啊。“照剧本拍有点对不起自己。”陆川觉得。他喜欢站在搭建好的现场,去感受闭门写剧本时体会不到的东西。
《南京!南京!》原剧本里,刘烨饰演的中国军人惟一活到了最后。但站在断壁残垣的南京城里,陆川突然发现这么个强壮男人不可能在那时活着出城。陆川试着拍摄各种角色救刘烨,都说服不了自己。后来,实在超期太久,刘烨不得不离组,陆川才拍摄了这位军人死去。
拍《王的盛宴》时,他布置好鸿门宴的场景,100个人排练好,开拍时他突然发现,史书里的一个关键情节无法发生:樊哙冲不进来。那个1米9的哈萨克族壮汉演员,戴着甲胃要冲进去救刘邦,门口的几个武士一站,演员咣一声弹回去了。陆川陷入思索,头几个人都撞不开,后面还有那么多人就更不行了。他觉得历史在他面前呈现出不同的模样:“这一切发生的可能不是因为樊哙特别牛,是因为项羽让你进去了。换句话说,项羽不想杀刘邦。”电影的核心变化了。
2012年,陆川表示要在年内出版自传《野孩子的电影梦》。书展参加了,发布会开了,书在各大售书网站上线了,豆瓣条目、百度百科条目都有了,甚至ISBN号和出版时间2013年1月也公布出来了。但实际上,这本书根本没出,被他叫停了。“因为我不知道该结在哪部分,而且我觉得太早了。但我确实已经写很多。”
散文诗一样的话
陆川的前5部电影里,他自己最喜欢《王的盛宴》,而不是给他带来更佳口碑和更多奖项的《可可西里》或《南京!南京!》。这部风格强烈的电影,着力展现刘邦作为统治者的恐惧,颇有思考和新意。但偏于晦涩的表达让电影收到不少差评,票房也只有8000万,远远收不回过亿成本。《王的盛宴》上映后的那段日子,是他从业多年里最痛苦的一段时光。
这个时代,卖萌和自黑已经成了应对嘲讽的有效武器。但这些不是他的方式,他老迎面撞上去。有记者来采访:“你上一部片子拍得很糟糕,那这一部……”陆川会截住话头反问:“你看过吗?哪部片子很糟糕,我跟你讲没有糟糕的片子。我们做电影是有底线的。”参加电视节目,有校友站出来说,北电的老师说您特别会装。陆川这次很克制,可一个人要如何才能证明自己真不是装的呢?他讲了许多母校的好话,最后说:“我拍所有的电影,我信。”
陆川在剧组里是人脉广阔的老大,酒量好,有本事拉来一个又一个投资方,还要解决制片管理的一堆琐事。但他同时有着书生范儿。美术指导郝艺多次讲起,他问陆川那个墙纸怎么弄?陆川回答:要像一个迟暮的妓女,可能年轻时很美貌,但现在已经老了,可还是抹很多粉,劣质的粉,冬天在门口等客人。“我去,什么意思?是不是要做旧?”这位手臂上有大片文身的美术指导也算文艺人,但他受不了陆川“老说像散文诗一样的话”。陆川回答:是,而且要起卷,最好拿那时的旧报纸糊, 糊完了还得拉丝,再拿烟熏一下。郝艺说:“你给我说这个就好,别说前面那个。”
每次电影开机前,陆川会剃光头,还要求导演组的人也全剃光头。这是拍《寻枪》时跟姜文学的。拍《南京!南京!》时,他比照当年拉贝难民营工作人员使用的样式,让服装组做了几百套白色袖标,要求所有工作人员都戴上,没有实际作用,“就需要这种形式感。”
文艺天真有时会一头撞上现实腐败。说今天来1000个群众演员,陆川感觉数目不大对,突然关门数人,实际不到800人。200人的空头被吃了。配套的200份盒饭钱也被黑了。镜头只会在白天扫到路灯,道具组却买来了18套价格不菲的真正路灯。“咱不是搞基建工程,怎么能这么干事?”陆川觉得很崩溃,“怎么会有人用拍电影来黑钱呢?我会觉得这个事儿想不通啊,天塌下来了。”发现这事时他已经在拍第三部电影。《寻枪》时由制片方派人管钱,《可可西里》时剧组里大都是相对单纯的同学。他从来没想象过,“这样一个白莲花种在这么臭的一块地里。”后来慢慢了解,他“发现这是中国电影的普遍现象,是产业化的”。他开始明白这事不可能靠一个人完全铲干净,只能树规矩,想尽办法减少这一类损失。
现在,腻在家庭温暖里的陆川,开始有点儿怀念前几部电影“很愤青”的状态。而那时的他,常好奇婚姻是什么,家庭生活会如何。十几年的动荡、愤怒和尖利之后,他把现在算作自己的转型期。未来不知如何,但现在有一部《我们诞生在中国》映射自己当下的状态,“还挺有意思的。”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