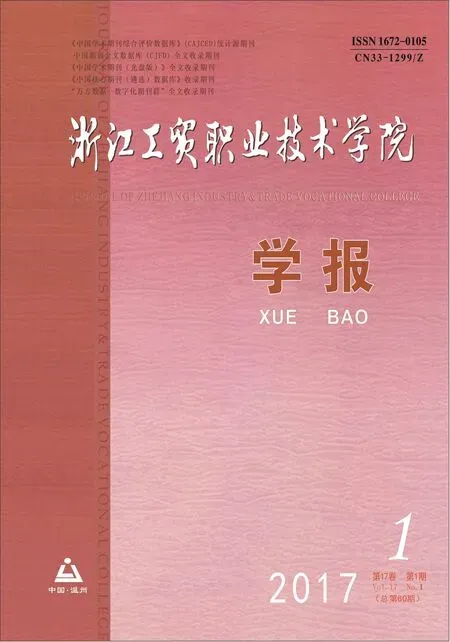民间金融供求及其运行机制研究*
——基于温州历次金融风潮与金融改革的思考
易元芝,王慧文
(中共温州市委党校,浙江温州325038)
民间金融供求及其运行机制研究*
——基于温州历次金融风潮与金融改革的思考
易元芝,王慧文
(中共温州市委党校,浙江温州325038)
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温州民间金融,其产生和发展过程是中国民间金融发展模式的一个缩影。以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民间金融三次金融风潮为例,比较发生金融风潮的背景及原因,分析温州金融改革的亮点所在,探讨引导和规范民间金融理性发展的路径,对于当前深化金融改革,促进民间金融又快又好地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民间金融;金融风潮;金融改革
民间金融,在我国没有确切的定义,它是在中央银行监管当局监管和控制之外的金融活动,不属于正规金融,其资金活动是游离于现行法律制度边缘,划分于体制外的非正规金融范畴,存在于正规金融制度的边际,在正规金融发展的夹缝中生存,也被称之为民间信用、民间融资、民间借贷等。当正规金融对民营经济融资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不能提供资金支持,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时,民间金融应运而生。它的运行机制、供求关系、交易行为、契约治理与民营经济是协同发展的,它可作企业的流动资金,也可作固定资产投资,投资到运输、金融服务、飞机制造等行业,进入外贸、对外投资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温州民间金融,其产生和发展过程是中国民间金融发展模式的一个缩影。比较历次温州的金融风潮与金融改革,探寻民间金融生存发展的普遍规律,剖析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对于当前深化金融改革,促进民间金融又快又好地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温州历次金融风潮及比较
(一)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的历次金融风潮
1.20 世纪80年代“会案”大灾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在此大背景下,温州的民营经济迅速发展,涌现出大量的个体户、家庭工商业,资金的需求量越来越大。20世纪80年代,由于金融体制原因,98%的小微企业和个体私企根本无法从正规渠道获得融资,民间金融应势而生,筹集资金的民间各种互助会迅速盛行,成为大量的个体户、小微企业重要的融资手段。随着市场的开放,温州的经济由个体和家庭作坊走向股份合作,走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原有的互助会一对一借贷方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出现了新的借贷方式。早期的金融会是以互助为目的的,慢慢发展演化蜕变为地下钱庄、轮会、呈会、摇会、台会等等。在高利率诱惑下,风险不断积聚,加上当时的政府监管缺位,部分金融会变为不断抬高利息的一种投机性非法集资的“抬会”①,有的甚至异变为投机诈骗机构,有的是以会养会,月息甚至高达7%~40%。如乐清的“抬会”在几个月内被疯狂复制蔓延扩散,出现了大同小异的变种金融会,波及温州全市及经济发展较快的邻县、地区,吸引的大量资金没有投入生产流通领域,经过一些别人用心的人精心安排,部分资金被携带出逃,还有部分会主无法偿还高利率,资金断裂,民间会案爆发。这次巨大的民间金融风潮会款金额达到12亿元,涉及温州全市30万人,造成严重影响。[1]
2.20 世纪90年代企业“逃废债”风波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和民间金融机构的整顿,加上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温州发生一场“逃废债”风波。整个90年代,温州曾经有276家的“两社一会”——城市信用社、农村金融服务社、农村合作基金会,包括基金会的民融资金服务部、资金调剂服务社等组织,属于半正规的、介于体制内外的地方性小微民营金融机构,分布在温州各个乡镇。平均每个乡镇至少有一家,其中有188家农村合作基金会,34家农村金融服务社,51家城市信用社,另有3家融资性投资公司。[1]从事存贷款业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私营经济的金融需求。1995年12月发生了温州“两社一会”发展分水岭事件,泰顺县金鑫城市信用社储户纷纷提取存款,导致金鑫城市信用社支付危机,最终破产。截止1998年底,有72家国有大集体企业“悬债”,欠银行债务金额达2.85亿元,961位企业主要负责人外逃,涉及金额6.30亿元,几乎影响温州的所有金融机构[2]。
3.2011 年民营企业老板“跑路”引爆的金融危机
2009年,在国家4万亿元刺激经济背景下,银行多头授信、过度授信,助长了企业的非理性融资,温州民间金融活跃非凡。为民营经济“输血供氧”,成了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部分资金进入高风险行业,演变成疯狂的高利贷活动。据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统计数据,2011年1月23.01%的民间借贷利率到11月猛增到25.44%[3],2008—2011年又集中爆发了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民间借贷风波事件。截止2012年,温州出走的企业234家,涉及银行授信的出走企业152家,到2013年9月,温州市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307.6亿元,不良贷款率达4.27%,达到近十年来的历史高位。[3]
(二)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历次金融风潮比较
第一次的民间“会案”发生的背景只是民间借贷活动,是民间互助性信用形式,导致会案发展的关键是“会套会”,会主以超高利率为诱饵进行金融融资,从中获取盈利。同时还刺激民间借贷利率不断升高,加上人们对各会套会信息不对称、退出成本较高、预期失误,对其风险缺乏认识,最终发生倒“会案”。其破坏性极大,涉及面广,发生多起非法拘禁、扣压人质,甚至人命案,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在这次会案大灾难中,温州因倒会非正常死亡50多人,大会首李启峰等被判处死刑,1987年首批依法判决14人[1]。
20世纪90年代企业“逃废债”风波不同于1980年代发生的会案,它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改制与正规金融领域,互相交结。当时的温州“两社一会”民营机构绝大多数是私人所有,产权与政府无牵连关系,经营管理权集中在少数人或者一个人上,缺少相互制衡的内控约束,有的股东按股息分红不问经营,有的大股东分权,各管各拉存贷款,收益、风险自负,个别股东还存在个人网点承包经营等极端形式。欠债企业采取兼并、关闭、改制、另搞股份制等方式转移资产进行“悬债”或甩掉银行贷款。
2011年民营企业老板“跑路”引爆的金融风潮与前两次的金融风潮有着较大的区别,有国际、国家宏观环境大气候因素,也有温州小气候因素,有金融服务方面的问题,更有民营企业自身方面的问题,它是产生在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同时并存的二元融资结构中的。这次金融风潮伤害的不止是经济,也破坏了温州的信用体系,银行、融资机构、企业之间的信用度越来越低。
二、温州屡发金融风潮的原因分析
(一)民间利率过高,资金流通量过盛,
温州历次发生金融风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民间借贷高利率是导致金融风潮的主要原因之一。温州屡发金融风潮,民间借贷都有利率过高的现象,只不过温州第一次、第二次金融风潮主要是资金流动性过盛造成,第三次金融风潮是资金量充沛而获取渠道有限引起的。由于2011年后,国际经济不景气,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国内货币政策趋紧,温州民间借贷活跃,约1 100亿元民间资金流通,利率不断攀高。在全国经济降温、实业生态恶化、利率不断升高的多重影响下,温州的民营企业在资本逐利性的驱使下过度投资,把汇聚的大量民间借款投资到高风险暴利领域,还有大量的中小企业进行了以钱炒钱的财富游戏,实业空心化现象严重,风险成倍放大,最终收益无法弥补借贷成本,温州民间借贷危机走向顶峰,在国内引起轰动。
(二)过度投资、治理缺陷、抗风险能力低
第一次的民间金融风潮,主要是民间借贷的“会中套会”所致,许多人以盈利为目的,组织连环会,既是会员又是会主,集资的雪球越来越大。当这种行为盈利空间被广泛认识和过度操作时,使互助性金融会偏离了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轨迹,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所能支撑的成本,导致资金链极度绷紧和资金来源紧缺,一旦资金链条环节出问题,无法支付庞大的利息,引发民间金融风潮;第二次的民间风潮主要是通过个人或合伙形式创办的大量小型金融服务社、农村合作基金会、典当行或以其他形式名义变相从事传统的存贷金融业务,由于治理缺陷,不注重内控制度建设,管理水平低下,违规拆借资金、风险意识淡薄等因素导致经营不善引发的金融风潮,特别是“两社一会”股东或实际经营者执行信贷政策不严,导致风险集聚,最终发生支付风险。“金鑫信用社破产事件”引起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加强了管控,“两社一会”的许可证被取缔。没有了特许经营权,有些股东或经营者有了最后捞一把的念头,采取趁机转移利润、增发股东贷款或加大分红等机会主义行为,也有的借款人借此机会采取拖延、逃废债或否认债务。而第三次的民间资金链断主要是受国家宏观调控的货币紧缩和、通货膨胀、房价受控和温州实体经济的空心化的影响引发的。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实业利润薄如刀片,大部分企业陷入生产经营困境。国家为了促经济发展,鼓励消费投资,激发了温州民营企业多元化的投资热情,在监管缺位和延续数年的宽松货币政策的情况下,不少企业获得超额贷款进行高风险的投资,投入光电、生物科技和房地产开发等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当政策转向,银根缩紧,银行不再续贷或者抽资,企业无法正常运转,不得不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形式,实行短期“过桥”融资,借高利贷填补流动资金漏洞。然而投入到新产业的资金尚未回笼,加上民间借贷利率不断推高,实业利润难抵民间高息,民企无法偿还民间高利率借贷,最后资金链断裂,导致信用链破裂,企业倒闭,引发金融风潮。
(三)过度担保,资金链安全性较低
在温州中小微民营企业苦于缺少资金或抵押不足或贷款笔数多、数目大无法获得银行抵押贷款,大多采取互保、联保,在经济形势良好时为企业融资打开了便捷大门,提高了企业获贷的可能性。但在银根紧缩、经济运行下行时,过度使用担保,乱用、滥用联保互保,随意对外担保,使“担保链”导致“债务链”。部分正常经营的企业受到牵连,出现一家企业资金链出现问题,波及参与联保、互保的诸多企业,遭遇“铁索连舟”“火烧连营”之祸,出现破产一家、倒下一批企业的现象。据调查,在银行融资的企业,90%以上参与联保、互保。许多企业因担保链、资金链断裂,老板无力偿还贷款或借款,纷纷跑路,有的甚至自杀,出现了企业倒闭现象。
三、温州历次金融改革
(一)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第一次金融改革(1986—1991年)
温州第一次金融改革是以利率市场化浮动为切入点,是基层自发、需求诱致揭开了金融体制改革的序幕,是一项被动应对市场压力、基层自发试点、局部试点到取得显著成效、被国家承认、全面推广的金融改革。1980年10月,改革的首发地苍南县金乡镇金乡农村信用社根据当时业务萎缩、连年亏损,而当地民间借贷利率高,自身生存发展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采取大额存款(500元以上)月利率上浮为10‰(原月利率4.5‰),贷款利率月利率上浮为15‰(原6‰),通过利率浮动一举,金乡农村信用社摘除了连续26年的亏损,1981年以后开始盈利。1983年4月,苍南县农行对农村经济较发达地区进行利率改革试点推广,效果显著,1986年5月时任国务委员兼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率中行、农行、工行行长来温考察,肯定农行关于实行利率浮动改革的成效,并对金融体制改革作了指示。利率浮动改革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地方金融市场上有诸多创新,对后来的温州金融发展改革产生了影响。如方培林组建的第一家方兴钱庄、市人民银行劳务公司创办的第一家集体金融组织府前信用服务部和新中国第二家典当行——金城典当行,此后还组建了多家城镇集体金融组织;首创鹿城城市信用社、东风城市信用社(属民营股份制金融机构),增资扩股的方式是发行股票,为直接融资迈出了重要一步;瑞安农行在全国率先建立温州市第一个多层次的银行同业短期资金拆借市场,开展信贷资金横向调剂业务,突破资金的地区封锁等等。
温州的第一次存款利率浮动金融改革虽然与当时民间会案灾难的时间差不多,但并不是因它而促成改革,关键是利率改革得到高层的政策认可,取得了合法性。1986年8月,温州被确定为全国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城市之一。1987年9月21日执行《温州市利率改革试行方案》,增加了信用形式和信用工具,加强了银行企业化管理,开拓了资金市场,更好地发挥商业银行的杠杆作用。
(二)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第二次金融改革(2002—2004年)
温州第二次金融改革主要是在80年代改革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不是民间自发的,而是人民银行自上而下地以利率市场化为主题的改革,是温州利率改革向国家统一的市场化进程靠拢的过程。为了进一步理顺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路径,作为全国农村信用社试行存贷利率浮动改革试点的8个县(市)之一的温州实行存贷款利率浮动改革。2002年3月21日,规定新的定期存、贷款利率上浮标准。由于存款利率浮动效果不明显,2002年10月再次调整,存款利率上浮幅度上调至30%,贷款利率浮动幅度为70%。并且规定单位的活期结算帐户存款实行上限管理,上限利率为法定活期存款利率,执行由人民银行温州市支行制定的银行机构利率改革方案;贷款利率在法定的贷款利率基础上可以最高上浮50%,最低下浮10%等。[4]
2004年1月1日,全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有了实质性进展,全国统一执行存款利率上限管理,温州的贷款利率改革试点失去独特性,2004年11月,温州农信社存款利率浮动方面被叫停,统一执行全国政策。
(三)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第三次金融改革(2012—至今)
2011年出现的金融风潮,使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再次被提上日程,同前两次的金融改革相比,此次更加注重民间金融的规范化、阳光化、合法化。
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改革试验区,确定了金融改革的主要任务十二项。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近五年来,积极探索多元化的金融体系,多层次的金融服务项目,有效化解了资金链和担保链,实现了不良贷款的双降,保证了区域金融总体的稳定。
2014年3月开始实施《温州市民间民间融资管理条例》,设立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开展民间融资备案登记。因信息公开和风险救济措施,民间借贷公共服务平台得到借贷双方的认同,目前全市已有43家融资中介,5家独立的备案中心,7家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为了反映民间融资市场走势和利率水平,温州市金融办编制反映温州民间借贷利率的“温州指数”,于2013年1月1日起实行按日发布。
多渠道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壮大地方金融组织,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6年末,温州民资已经进入金融领域的资金规模合计超过500亿元,其中进入银行业的民资超过278.52亿元。2015年3月末,民间注资20亿元的温州民商银行开业,有4家温商持股5家民商银行(全国首批),金额超过40亿元,温州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服份制改革和温州银行增资扩股,都有民间金融介入[5]。
初步建立企业帮扶和金融风险化解有效机制,抽调人员实行集中办公,实体化运作,分级分类处置不良贷款,强化风险处置组织保障。出台全国首部金融地方性法规和专门规范民间金融的法规,成立金融审判庭,建立府院联席会议制度,开创企业破产审判新机制。成立温州地方金融管理局,开创地方金融非现场监管系统,监管系统于2013年底开始常态化业务数据报送。
四、若干启示
综上所述,比较历次温州的金融风潮与金融改革,从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增强金融风险防范意识,金融管控要适度
金融管制要适度,不可过宽,也不可过严,要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相适应,[6]这决定了民间金融改革成败的关键。只有健全地方金融监管体系,有效化解民间金融风险方为上策。如果政府不对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进行管控,任其发展,极易产生“寻租”道德风险,埋下多重风险隐患,如果政府过度管控,民营资本无法进入金融领域[6],民间资金多、投资难;中小企业多、融资难的问题更加突出,只有充分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积极性和创新能力,发挥市场作用。地方政府应从制度创新层面建立完善的“条块结合”的监管机制,从而将潜在金融风险限制在局部和可控的范围内。同时要加强投融资者风险教育,培育理性、成熟的投融资文化,提高风险意识,鼓励组建各类融资行业协会,不断创新完善、规范调整,才能平抑各种金融风险,维护好金融秩序。
(二)创立新型融资市场,优化金融结构和功能
金融改革的活力在于地方金融创新,要想金融改革落到实处,就要调低金融的进入门槛,开放民营投资领域,向社会资本开放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入的服务领域,引导民间资本促进产业升级。培育利润高的领域吸引民营资金的投入,让部分传统低端制造领域的企业退出市场,加快经济结构转型。民间资本是否介入直接影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疏则百利,堵则众伤。创立运营监管相协调的新型融资市场,让金融资源反哺实体经济。设计监管内容时要注意民间资本的运营方式,要考虑投资各方的利益平衡,要搭建好地方民间融资网络平台,根据民间资本的需求和存量结构,分层次、分类别、分步骤拓宽投资渠道,让其进入金融领域,促进民间融资运营与监管协同发展,优化地方金融结构和功能,重视挖掘和盘活现有的金融资源,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以股权、债权等形式参与;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地方金融组织,做大做强地方金融组织,促进民间融资与民营经济协同发展,让更多活水金融浇灌实体经济之田。
(三)加强利率自律和管理,实现金融参与主体市场化
存款利率浮动上限放开后,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进入新阶段。推进利率市场化与实现金融参与主体市场化的改革,才能使金改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和突破。灵活的利率定价是民间金融健康、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金融机构要认真执行浙江省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和自律公约,杜绝过分抬高存款利率水平和付息成本,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实现金融参与主体市场化。要继续发挥民间金融的优势,发挥小微型金融机构、地方法人机构的本土化优势,让参与金融主体服务于地方中小企业。这样既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成本过高的问题,又能把大量的闲置的民间资金引导走入正轨道上,避免投机动机,消除套利空间,提高民间借贷与小微型机构的对接。使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的民间资本逐渐规范化、合法化和阳光化[7]。
(四)加强社会信用制度建设,完善民间金融的法律法规
只有在完善的法律体系保障下,民间金融才能阳光化、合法化、规范化。虽然温州有了第一部金融地方性法规和专门规范民间金融的法规,有了《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及三个操作指引,但是民间金融运作形式多样。对高利贷、非法集资和非法交易等违法行为要进行严厉打击,加大失信惩罚机制,将各种信用活动都纳入约束力、制衡力强的信用规则下运行,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只有在风险预警、防范、处理、补救机制健全的情况下,在建立了合理的监管体系针对不同形式的民间金融实施有效的监管情况下,才能将其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这还需我们在实际操作中不断完善。要想民间借贷有明确的法律保障,如何处置他们和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还需我们做深入的研究。
总之,温州金融改革要借鉴和吸收国内外其他地区的有益做法和经验,加强国内外各地区的密切合作,更好地应对新常态下经济金融的区域化、一体化、国际化发展趋势,认真谋划下一阶段的金融改革措施,促进民间融资与民营经济共生演进、协同发展。
注释:
①抬会是指1985年八九月间,在海屿乡、乐成、柳市镇首先出现,是民间“单万会”(百人每人每月百元成单万会)的变种,一般会首收到会脚一次性交付的金额较大的会费,会首再分期还本付息,存贷交替、本息混合,月息高达7%~40%。它不同于有固定会员人数、会期的呈会,抬会的会员是不断扩大的,一旦会员无法增加下去,抬会就面临崩溃。
②银背是指原始的借贷中介,以小会主的身份四处呈会,将拿到的会款当作会钱呈更大的会,获利差,还有一种是从借款人那里借到钱,以稍高一点的利率贷给贷款人,吃利差。
[1]陈明衡.温州金融改革三十年[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12):30-58.
[2]张震宇,周松山,孙福国,等.非公有制经济下区域性金融风险及其管理:温州个案研究[J].金融研究,2002(2):110-118.
[3]王敏,杨屹东,聂兆祝.民间金融历史变迁规律的温州样本探析[J].金融与经济,2013(6):61-63.
[4]孙福兵,丁骋骋.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的三次金融风潮与金融改革[J].社会科学战线,2013(10):54-62.
[5]潘忠强,王春光,金浩.2016年温州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4):123-134.
[6]易元芝.地方金融组织体系与区域金融市场发展问题的研究——基于温州金融改革背景下的思考[J].上海经济研究,2015(10): 70-75.
[7]丁骋骋.温州试点最有可能的突破口[N].上海证券报,2012-6-18.
(责任编辑:台新民)
AStudy on Supply and Demand and the Mechanism Operation of Folk Finance --AStudy Based on Wenzhou Economic crises and Economic Reform
YI Yuan-zhi,WANG Hui-wen
(Municipal Party School,Wenzhou,325038,China)
Wenzhou folk finance is Featured in typicality and representativeness,and its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become an epitome of China folk finance developing mode.Taking the three financial crises of Wenzhou folk finance since China introduced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as an example,this essay has explored how to lead and standardize the developing path of folk finance, which has a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folk finance quickly and smoothly and deepen the current financial reform.
folk finance;financial crisis;financial reform
F832.7
A
1672-0105(2017)01-0047-05
10.3969/j.issn.1672-0105.2017.01.012
2017-01-22
2016年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民间金融供求及其运行机制研究-基于温州历次金融风潮与金融改革的思考”(16wsk276)
易元芝,女,中共温州市委党校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经济;王慧文,女,上海市浦发银行信用卡中心风险政策部,研究方向:区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