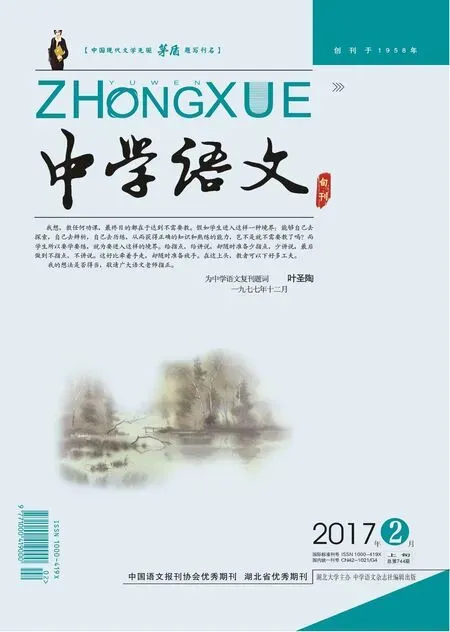一个诗意空间的精神言说
李利琴
一个诗意空间的精神言说
李利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诗歌是遣兴的艺术。就拿当下诗坛来说,几乎一夜之间,大大小小的博客、微信群以及微信公众号在以瞠目的速度催生大量分行文字,但这些分行文字又在以惊人的速度枯朽、失效,一不小心就陷入了精神指向、艺术手法庸常的樊笼。
诗歌的穿透力往往随着时空的推移,呈摇摆的势态,“生存还是灭亡,这是一个问题”。总有一些诗歌在历史节点的冲突、断裂与崩解中生存下来了,它们像大浪淘沙淘出的金子,在诗歌史册上发出独特的光芒。戴望舒的《雨巷》就是这样一首诗歌,他也赢得了“雨巷诗人”的雅号。叶圣陶对这首诗给予高度评价,说它为中国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对这首诗的评估,我们已不能停留在“好诗”的言说层面,它应是一首很“重要的诗”,以一个诗意空间的精神言说而成诗歌谱系的经典文本。
在一个诗意空间“雨巷”里,诗人述说了一个凄美迷茫的梦。他在说什么,我们似乎不怎么懂,因为他说的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诗家语。“诗家语是诗人‘借用’一般语言组成的诗的言说方式。一般语言一经进入这个方式就发生质变,意义后退,意味走出;交际功能下降,抒情功能上升;成了具有音乐性、弹性、随意性的灵感语言”(周振甫《诗词例话》)。这种语言不仅是诗人的“我说”,同时“语言进一步言说”。有能力让“语言言说”的诗家语,才是新诗生存下来的本体依据。
一、元诗意图的语言言说
对于许多诗人来说,写诗是对客观生活材料提炼、加工。戴望舒则挖掘出一个奇妙的核心意象“雨巷”,雨巷不是直接通向客观,而是通向语言和灵魂的“奇境”,这就是所谓的“元诗”,即关于诗本身的诗。诗中的诗人言说,是为了进一步激发出“语言言说”,“我说”和“语言言说”之间有一种美妙的张力。“独自彷徨在这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在诗人的主观视距中,世界缩小了,物质空间转化为“语言言说”的无限的精神空间。悠长既指向时空,更指向一种慢节奏的、舒缓的情感基调,在审美意念——彷徨上集中,曲线性的无望的延展里,产生了一种突围的意想。传统的写作一般是诗思萌生于落笔前,而元诗意图的写作,诗思是在写作中与语言一点一点同步发生的,它的“奇境”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美妙的“偶然性”,即“逢着”丁香一样的姑娘。诗人循着一种神奇的诗思动力前行,由彷徨到“逢着”丁香姑娘,再由丁香姑娘“彷徨”于诗人的雨巷,这里彷徨→逢着→彷徨,构成了一个回旋变化,逢着→飘过→逢着有似于重章复沓,伴着悠长悠长→走近走近→远了远了→悠长悠长错落有致的韵律,诗人并不完全有语言深处具体会发生什么的自觉,循着“语言言说”的踪迹,诗歌好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叙事,又好像处于未完成的叙述过程中。
“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君掌盛无边,刹那含永劫”,英国诗人勃莱克的诗道出了元诗的审美意味达到的高度。所言客体的形状、颜色、空间或运动,只是作为媒介,意在达成与人类情感的异质同构。理解了元诗“语言言说”的这些特点,我们就会明白,诗人在“雨巷”这个诗意空间言说了一个精神事件,让我们触摸到他无以排解的哀怨,在无望中的执着幻想,幻想有一种奇遇,彻底让他解脱。他因何哀怨,因何惆怅,他要追求什么,我们都不能确切得知,但每个人又可根据不同的阅历、修养、情感有不同的猜想。正如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中说:“艺术符号是一种终极意象—一种非理性的和不可用言语表达的意象,一种诉诸于直接的知觉的意象,一种充满了情感、生命和富有个性的意象,一种诉诸于感觉的活的东西。终极意象之“终极”,指其不可再分析、推理,难以转述,但可以感动你心灵最幽暗的角隅,透入你的直觉、潜意识,被你知觉、体验。无“理”而更有丰盈的意味。”
在“我说”与“语言言说”之间接合,诗人靠对言语纹理的敏悟力,化若无痕。纯粹自足的诗语脱颖而出,“我”由存在而无痕地消失,所谓“我丧我,确是扩大的我”。
“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之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这正是《雨巷》历经近90年而魅力依旧的原因吧。
二、言说意蕴的精神内核
诗的思想,绝不止是肤浅的、普泛化的道理,而应是深入生命体验的个性化的发掘和体悟。一首有真义的诗,会超越本身,“吸附”未知深层生命体验,它一般会有两个以上主旨,除去诗歌情境固有的,另外的则是自我持存、“无中生有”的语言奇境。也可以说,“言说意蕴”的可能边界是诗歌“主旨”的可能边界,可能深度是诗歌“主旨”的可能深度。诗的语境产生后,脱离诗人的另一个生命形式出现了,言说意蕴成为不确定的、具有更多的秘甬暗道的审美空间,生命元素构成了言说意蕴的“精神内核”。“永远不可能奢望‘语言自身’”(保罗·策兰语),诗歌成为语言与精神之间的一种特殊周旋、磋商,不只是语言的凸现,更是精神的凸现。
自古写“愁”的高手很多,《雨巷》写“愁”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令人窒息的“雨巷”让人难以“活命”的时候,在诗人的突围意念里萌生出一个“丁香”姑娘,他似乎从窒息中“活”了过来,可这点亮色,这点希望还没能完全看明白,“丁香情结”便给诗人带来亮点幻灭后的更深重的愁。在雨巷的背景中,实中有虚,虚实相生,丁香——姑娘——“我”物我合一,人我合一。我有无告的愁苦,何以解愁?却唯有结着愁怨的“丁香姑娘”,丁香有愁心,姑娘结愁怨,愁上加愁,岂不是愁更愁?以愁觅愁,以愁诉愁,正如以毒攻毒,以毒疗毒,诗人愁绪之深,愁毒攻心,无由排遣,只能借助“自虐式”的幻想。一个“愁”字构成了“言说意韵”的精神内核,这是对愁绪杂质的“清洗”,堪称幽微绝妙之笔!“不是绿色语言,就不会继续生长”,诗人潜意识深层水域自然涌上的“语言言说”,是源于有机的、绿色的生命体验,它们才通往我们生命最隐晦、最疼痛、最脆弱、最遥远却最迫近的角隅,我们的灵魂受到一次梦游般的复杂的阅读快感。诗的语言由诗人创造,但当言说意蕴进入“精神的瞬间”,你会发现,言说更像是一种“倾听”,倾听精神内核的引导和召唤。
诗家语的言说结构,一定要以坚实的“精神内核”做支撑。单纯的“我”的言说,只是滤色镜后面的言说。许多诗人靠仿写创作,丧失了对生存个体质询的“精神内核”,不乏“美感”而缺少活力,这必定是诗歌速朽、失效的本体因素。
三、言说本真的有效性
诗家语是有生命的,生命要向下扎根,扎进心灵的根有多长,诗歌的生命就有多长。当“优美、生动”不再是新诗的圭臬后,对诗家语言说本真的挖掘,成为诗人追寻的基本意向。
意象是言说本真的基本单位,《雨巷》以意象的组合达成言说本真的承载。①雨与巷的组合:南方小巷悠长、寂寥,雨中小巷更易伤情。雨与巷的组合,较之单独的“雨”或“巷”,更有情致,更见寂寥;②油纸伞与诗人的组合:油纸伞在传统诗词是常见意象,将其放置于雨巷的诗人头顶,油纸伞就浸染了诗人的哀怨,诗人也因头顶的油纸伞遮了一方天地,更加孤独,情绪化的雨巷更加悠长、寂寥;③丁香与姑娘的组合:自古以丁香入诗的诗人很多,丁香成为美丽、高洁、愁怨的象征。诗人承续了丁香的传统文化内涵,又以“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将丁香人化,将姑娘物化,“丁香姑娘”成了一个有别于传统意义的意象,这个新意象,是一个实在的人,但又是一个抽象的意象。人与物天然相和,物我合一,是诗人心中理想的化身,也是诗人突围“雨巷”的一根稻草。
雨巷、油纸伞、丁香姑娘,这些意象是诗人偏爱的,恰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影象,是主观情志的物化。这种组合已将形式与内容消泯了界限。
诗人身处乱世,时世的走向“剪不断,理还乱”,雨巷、油纸伞下更显孤独的诗人、丁香姑娘这三个意象,构成了一幅流动的、朦胧的写意画面,将“苦闷、彷徨”这种人在遭遇与环境的冲突时所特有的精神处境提纯再提纯,简化再简化,最大限度地接近了言说本真。“诗不是某一个官感的享乐,而是全官感或超官感的东西。”它直接通向读者那“微细到纤毫的感觉的”神经。
诗人的求真意志,容留诗人生命体验中的矛盾因素、逆反因素,扩大了语境的承载力,使诗歌成为时代血肉之躯上的活性细胞。它从个体主体性出发,以独立的精神姿态和言语方式,处理个体生命、生存与时代的关系。当言说本真成为超越个体性的“泛本真”,它就具有了“生命力”维度的有效性。
求真是要达成有效,如果说《雨巷》意象的组合是基于求真,那么组合意象的再组合则是基于有效。在审美求真的建构中,诗人在一个完美期待的视野里,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圆点式的“泛本真”,艺术穿透力也正是在于意象之点与意境之圆达成了圆融的合奏。如梦一般飘过的丁香姑娘,在诗人留有一线希望的视野里消逝在雨巷的尽头,此时诗人的理想好像已经破灭,又好像还没有真正到来,依旧留在心底。它留给我们的是下一次相逢的酝酿,于是“撑着油纸伞”又“独自徘徊在悠长而又寂寥的雨巷”,走的是同一条雨巷,又像是全新的一条雨巷,全诗就这样周期性无限性地运动着、循环往复着,画着耐人寻味的意境之圆。这种凄美在无限重复中渐渐磨砺了绝望,构成一种安静的流动感。每个意境之圆的完美处处以意象之点为要素。意象之点油纸伞、“我”、丁香姑娘,没有像一般诗歌的意象单独地存在下去,它在完美的意境之圆中消弭了界限,彼此勾连。意境之圆与意象之点天衣无缝的组合,使得这首诗达到了本真的极致。如果只局限于诗中意象之点的解读,而忽略了意象之圆的无形存在,那我们就有可能读到了无边的绝望。
正如孙飞龙在《印象》与《秋蝇》的精神解读中指出:“戴望舒诗歌创作时常把个人放在两难人生境界的交接点上,即让自己始终处于精神困惑的边缘状态,呈现一种边缘状态的美学特征,他让我们看到美的东西总是让人忧伤的,雨巷拥有不衰的审美生命力,也正在于它在更深的意义上彻底揭示了美好事物的存在方式。”
这种圆点式的“泛本真”在我们今天读来也是有效的:当遇到生活中的不如意,捧起《雨巷》,雨巷中那个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的人仿佛就是我们自己,“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便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觉。文学作品固然会打上时代的烙印,而“言说本真”有效的诗一定是跨时代的,穿透历史烟云,“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抛开戴望舒的“雨巷”,我们仿佛走进了自己的“雨巷”。
把一首诗写得象“好诗”并不难,把一首诗写得有生存的“有效性”,才具有真正的难度。如果诗歌只是一种惟美的遣兴,一种不痛不痒的言语迷醉,那么已有足够多的作品可以载入诗歌史。而唯独像《雨巷》这样的诗歌成为了经典,就是因为“惟美”和“迷醉”是无法衡量诗歌成色的。
①周振甫,《诗家语·诗词例话》,1982年第8-11页。
②王雯:《论戴望舒〈雨巷〉的艺术特征》,《长城》,2013年第2X期第92-93页。
[作者通联:河北张家口市怀安县职教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