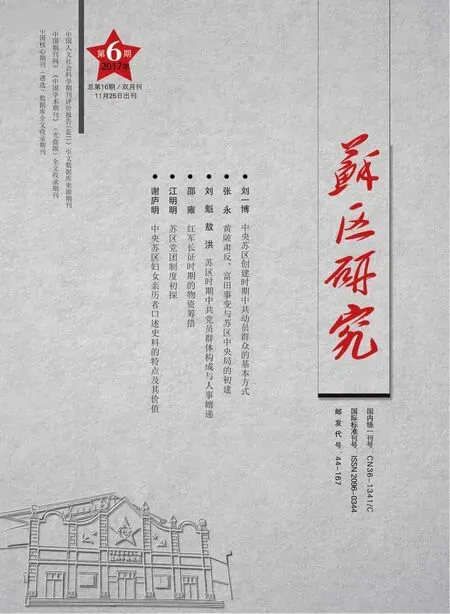黄陂肃反、富田事变与苏区中央局的初建
黄陂肃反、富田事变与苏区中央局的初建
张永
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调集重兵准备进攻苏区,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的方针,但遭到李文林等江西行委干部的反对。红军攻占吉安后缴获了一些敌人间谍的材料,毛泽东认为有反革命分子打入红军和苏区内部,于是在黄陂发动了大规模肃反。肃反在野蛮落后的农村环境里出现严重扩大化,刑讯逼供盛行一时,红一方面军三万多人中有4400人被捕,被杀人数粗略估计达到2000人左右,进而引发了二十军武装反抗的富田事变。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认为,集中的权力结构是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力量来源,虽然毛泽东领导的肃反有些过火,但富田事变武装反抗上级更加不可容忍,因此在这一事件的处理中大体支持毛泽东。项英初建苏区中央局时肃反有所缓和,但任弼时等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后,新苏区中央局再次推动大规模肃反,并波及整个中央苏区,闽西肃反短短几个月竟然杀了3000多人。在付出了高昂代价之后,中央苏区和红军逐渐建立起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结构。
黄陂肃反;富田事变;苏区中央局;毛泽东;远东局
在文革结束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大背景下,江西、福建党史工作者在1980年前后开始对中央苏区肃反展开调查研究,收集档案文献,采访当事人。戴向青发表了《略论“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其历史教训》(1979)*戴向青:《略论“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其历史教训》,《江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富田事变考》(1979)*戴向青:《富田事变考》,《江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论AB团和富田事变》(1989年)*戴向青:《论AB团和富田事变》,《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并和罗惠兰一起出版了专著《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1994)*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这些成果依据档案文件和回忆录,理清了富田事变的基本史实。文宏搜集整理的文史资料《关于富田事变及江西苏区的肃反问题》(1982)*文宏(搜集整理):《关于富田事变及江西苏区的肃反问题》,政协江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江西文史资料选辑》1982年第2辑(总第9辑)。主要依据萧克等的回忆,虽然不是学术论文,但内容丰富、条理清晰,在以后的研究中常见引用。蒋伯英的论文《闽西苏区的“肃清社会民主党”事件评述》(1982)*蒋伯英:《闽西苏区的“肃清社会民主党”事件评述》,《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2期。、《闽西苏区的“肃清社会民主党”冤案》(1989)*蒋伯英:《闽西苏区的“肃清社会民主党”冤案》,《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理清了闽西肃反的基本史实,问昕的博士论文《闽西苏区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2013)*问昕:《闽西苏区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福建师范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又补充了很多细节。台湾学者陈永发的长篇论文《中共早期肃反的检讨:AB团案》(1988)*陈永发:《中共早期肃反的检讨:AB团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上册(1988年)。主要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展开分析。余伯流、凌步机的重要专著《中央苏区史》(2001)*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十九章“中央苏区的肃反运动”全面探讨了中央苏区肃反,在材料收集和分析上都更加深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10册(2002)披露了有关富田事变的不少史料,姚金果《富田事变是如何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2008)*姚金果:《富田事变是如何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百年潮》2008年第3期。、陈胜华《富田事变的起因及共产国际的定性》(2014)*陈胜华:《富田事变的起因及共产国际的定性》,《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使用了其中的资料,不过这两篇文章都很简短。
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做进一步的探索。在材料上,本文使用了《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的罕见资料,更充分地利用共产国际档案,还使用了近期出版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中的资料。在分析思路上,以往研究主要着眼于平反冤案,或者着眼于权力斗争,本文尝试从组织结构成长的角度进行探索。虽然在中共中央、红军领袖和地方干部三个层次之间产生意见分歧是难免的,但从列宁主义革命党的组织原则来看,武装反抗上级威胁到了组织体系的根本,必须严厉制止,这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关于富田事变决议的基本出发点。
困难形势是对组织的考验,迅猛发展的形势也同样如此。1930年国民党大规模派系战争给中共带来巨大机遇,但尚不成熟的中共组织在急速发展中出现了混乱。在城市,以李立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罗章龙派及留苏学生群体发生激烈对抗,结果中央丧失威信,被共产国际改组,留苏学生进入领导层,而罗章龙等走向决裂。在农村,红军在集中整编方面取得巨大进展,先是中央苏区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成立了共同前委,后各地红军又在中央指示下建立了军团和方面军,但红军各自为战的情况仍很严重,不同来源的红军会合时,常常爆发激烈争论,造成决策困难。同时,红军与地方组织关系紧张,毛泽东与江西行委之间出现严重分歧,这是黄陂肃反和富田事变的诱因。苏区中央局的建立是革命重心向农村转移的关键一步,中共中央力图借此解决矛盾冲突,整合各种力量,在苏区建立党、政、军一体化的军事政治体系。
一、红一方面军黄陂肃反
肃反发生的原因很复杂,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是政策前提。1930年10月红军攻占吉安之后,毛泽东在缴获的材料中发现苏区有奸细与敌军通信,据此认为在敌军大规模进攻之际,必须先清除内奸。同时,毛泽东在集中指挥权的过程中,始终面对激烈纷杂的不同意见,感觉十分棘手,这也让他怀疑这些不同意见中包含有敌人奸细的作用。
字面意义上的AB团是1926年底由段锡鹏、周利生、程天放等人在江西成立的反共组织,到1927年4月以后已经不复存在。*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第40页。但是,在江西党内文件中,还是习惯于把各种反对革命的势力泛称为AB团、改组派,一般是把支持蒋介石南京政府的称为AB团,把接近汪精卫国民党左派的称为改组派。
赣西南苏区肃AB团是1930年5月从地方开始的,9月份达到高潮,抓了几千人,上千人被杀。10月13日赣西南特委会议记录提到:“党过去杀一千多AB团,内中一定含有很多可以教育过来的”,*《赣西南会议记录》(1930年10月13日),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31页。不过这个阶段肃反对红军影响不大。值得注意的是,后来被打成AB团的丛允中等人,此时却是肃反的领导者,他们在8月二全会议后很积极地整肃AB团,杀了不少人。“在‘二全会议’后,丛允中杀害丘会培、凌开招等一批同志时,说他们就是AB团反革命。”*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第95页。二全会议是江西党内斗争非常激烈的一次会议,丛允中在会后肃反杀人,不能排除他借肃反打击反对派的意图。红军刚开始肃反时,赣南地方组织还派人来帮忙,“赣南特委派左基中、周高潮、马木彬来红三军团专门组成一个办公室,动员打‘AB团’”,后来纠正肃反错误时,红三军团又召开公审大会,把这三个人杀了。*《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6页。
10月4日一军团攻占吉安,缴获不少间谍在苏区活动的材料,怀疑已经有大批奸细混入苏区。这也并非多虑,蒋介石的亲信、剿匪司令部秘书长邓文仪认为,情报工作是国民党围剿苏区战争获胜的重要因素。当时蒋介石的谍报机关主要是中统、军统和司令部秘书处第三科,邓文仪说:“我们也派了些人打入渗透共匪的组织和工作”,“共匪的群众组织都有我们的细胞,我们在前方与军队党政工作人员密切联系,在后方情报都很迅速确实,反间谍反情报工作成效卓著,这是当时反共斗争胜利的主要因素。”*邓文仪:《武汉反共斗争怎样转败为胜》,《反共斗争经验谈》,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2年版,第155-156页。虽然邓文仪是在谈到围剿鄂豫皖苏区时说的这些话,而且不免有夸大的成分,但也说明国民党派间谍进入苏区、渗透群众组织的情况确实存在。
郭化若也认为:“AB团在当时肯定是有的。我们从两个迹象可以看出:1、红十二军成立之初军长伍中豪在福建遭到地主武装袭击,就是AB团告密的;2、小布埋伏打不成,被谭敌发觉,也是由于AB团告密。这说明有反革命。”*郭化若:《回忆第一次反“围剿”期间的有关史实》,《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2-143页。李廷序认为:“应该肯定,当时反革命分子是混到我们队伍里来了。这也说明肃反是必要的。”*李廷序:《对于都北部地方革命武装的回忆》,《回忆中央苏区》,第45页。
在大军压境的险恶形势下,红军处于弱势地位,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肃清间谍被当作极为紧迫的任务,一切违反纪律、牢骚不满、意见分歧等都成为疑点,成为追查奸细的线索。“四军在赣东与敌接战时,某部队上火线发谣风逃跑,由此找到红军中的线索,破获了整个方面军AB团组织”,*《赣西南的(综合)工作报告》(1931年9月2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421页。红一方面军三万多人1930年11月底在黄陂开始了全军肃反,这是红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肃反。
李志民回忆:“我是军党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也是肃反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参加过审讯,领导叫怎么搞就怎么搞,当开始审出‘AB团’成员时,我曾大吃一惊,认为自己过去思想麻痹,敌人已经钻进我们军部来了还没有察觉。可是,过了几天,‘AB团’越抓越多,我便逐渐产生了怀疑,不相信会有那么多‘AB团’;特别是对刑讯逼供的做法看不惯,心想:古代小说中写过许多‘屈打成招’的冤案,我们怎么能搞这一套呢?但在当时的形势和政治气氛下,谁也不敢提意见,谁提了意见,轻者说你‘右倾’,重者会引火烧身,也被当成‘AB团’抓起来,招来杀身之祸。”*《李志民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141页。
有的亲历者认为肃反扩大化的重要原因是没有执政经验。李廷序说:“当时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呢?主要是没有经验。反革命头上又没写字,我们初掌政权,过去又没有做过这项事情。但这段时间不长,只几个月,在这几个月中,杀错不少人。”*李廷序:《对于都北部地方革命武装的回忆》,《回忆中央苏区》,第45页。在野蛮粗糙的环境中,捕风捉影、刑讯逼供成了抓AB团的主要方法。“用烧红了的烙铁烙背部,那个滋味可不好受哇!”熬不过酷刑招认的大都被枪毙,坚决不招的还有机会活下来,二十七团书记官周贯五一连两天大刑都挺了下来,最终熬过了肃反。*袁林:《征途漫漫——我的红军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
知识分子大多富裕家庭出身,在肃反中更容易受到怀疑。三军九师肃反最积极的是矮个子炊事班长,他是师士兵委员会主席,也是肃反委员会委员。他的理论是:“文化高的人肯定家里有钱,有钱的人就是资产阶级”,“像宣传队长呀、卫生队长呀、书记官呀、参谋呀,都是文化高的人,十有八九是AB团分子。像我这样苦出身大字不识的人,就根本不可能是AB团!”*袁林:《征途漫漫——我的红军生涯》,第97页。“师一级都成立了肃反委员会”,“杀人权就放在师级,往往是凭口供就杀人,也没有什么申诉和辩护。三军团打下长沙时,从监狱里出来跟队伍走的知识分子被杀了不少。讲怪话也有掉脑袋的危险。”*江华:《追忆与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邱会作认为:“这场政治大灾难,有政治路线错误的原因,这是主要的,但是以落后地区农民组成的红军部队的愚昧也加重了这场风潮的灾难性。”*《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2页。
随着肃反的展开,被捕被杀的人越来越多,红军损失惨重。“经过刑讯逼供的人大多屈打成招,一承认是‘AB团’,不几天就枪毙了。当时红五军不到一万人,肃反就误杀了二三百人,搞得人人自危,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李志民回忆录》,第139-140页。“李井泉、杨立三同志当时负责审问总司令部直属机关的AB团”,“到达黄陂时,总司令部有五个副官,肃AB团时杀了两个”。*刘恋:《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在宁都黄陂、小布、青塘等地活动情况》,《回忆中央苏区》,第169页。“一个在无意中戴歪了军帽的战士也被抓,他在酷刑之下胡乱地供认该连队有不少AB团,但又推脱说记不起名字。矮个子班长威迫全连列队,逼迫他逐个指认,他在昏昏迷迷中,把五十多人指认为AB团。”*袁林:《征途漫漫——我的红军生涯》,第99-100页。
关于黄陂肃反被捕、被杀总人数的史料很少。毛泽东在《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提到:“此次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以上。”*《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1985年内部印行,第634页。1931年2月《盖利斯、米夫和马雷舍夫同任弼时谈话记录》提到:“中央提款员在返回途中(在长沙地区)宣读了毛的呼吁书,呼吁书中说,军队清洗了约4000名AB团分子,因此它在政治上和在作战能力方面大大加强了。”*《盖利斯、米夫和马雷舍夫同任弼时谈话记录》(1931年2月19日于上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同日《雷利斯基同向忠发和周恩来谈话记录》也提到:“最近撤出吉安后,我们军队的同志——毛、朱、彭——对军队进行了清洗,他们清除了大约4000人,有的被枪毙,多数被逮捕。”*《雷利斯基同向忠发和周恩来谈话记录》(1931年2月19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第84页。
有的学者认为被捕的4400人全部被杀,但这种说法难以成立。在各苏区肃反中,从没有把被捕人员全部处决的政策,一般都允许工农出身的士兵自首,很多人被红军开除,他们在部队中消失了,但并未被杀。还有干部虽然被逮捕,但坚决不承认,后来不但被释放,还官复原职,比如红三军27团团长李聚奎和副团长陈华堂,他们获释后马上带队参加了第一次反围剿。*《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91-95页。雷利斯基谈话中也提到,多数只是被捕,被杀的是一部分。按前面李志民的说法,五军不到一万人杀了200-300人;萧克提到,工农出身的可以自首,十二师抓了100-200人,分两次杀了80多人,当时四军共七千多人,抓了一千三四百AB团,杀了约一半,就是600多人。*文宏(搜集整理):《关于富田事变及江西苏区的肃反问题》,《江西文史资料选辑》1982年第2辑(总第9辑),第110页。红一方面军当时包括红一军团约16500人和红三军团约17000人,*《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书面报告》(1930年11月3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90-492页。总共约33500人。少量新部队未集中,黄陂附近大约有30000人,被捕4400人约占15%,其中大约一半被杀,约占总人数7%,当然这只是很简单的估算。
不同部队肯定是有差别的,大致五军杀的少些,三军杀的多些,四军在两者之间。欧阳钦1931年9月报告称:“红军中的AB团在一次战争前只第三军及廿军比较严重,其他各军比较少,但三军经过大的破坏已经渐次肃清,其他各军亦有破坏”,*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385-386页。《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也提到“三军的AB团,特别布置的多”,*《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第634页。这说明出自赣西南的三军在肃反中被杀人员比例肯定更高,根据上面材料仅能粗略估计1930年11-12月黄陂肃反被杀人数可能在2000人左右,对于只有三万多人的红一方面军,这是相当惨重的损失。
黄陂肃反被杀总人数比较多,但其中高级干部相对较少。鄂豫皖白雀园肃反和湘鄂西红三军肃反被杀人数大约是几百人,但湘鄂西肃反被杀的师级以上干部就有段德昌、唐赤英、宋盘铭、盛联钧、王一鸣、胡慎己、傅光夏等,夏曦四次肃反中仅第一次就整肃了团级以上干部28人,有威望有能力的干部大多被杀;*张永:《湘鄂西苏区肃反研究》,《史学集刊》2015年第4期,第90-95页。夏曦:《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关于肃反等问题给中央的报告》(1932年7月8日),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1985年内部印行,第226-233页。鄂豫皖白雀园肃反被杀的有许继慎、周维炯两个师长,潘皈佛、高建斗、王则先、萧方、王明、魏孟贤六个团长,封俊、江子英、袁高甫、吴精赤、刘性成五个团政委,十个团政治处主任,陈昌浩肃反报告中提到的团级以上干部有23人;*张永:《鄂豫皖苏区肃反问题新探》,《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130页。陈昌浩:《红四军反对反革命的伟大胜利》(1931年10月),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编:《鄂豫皖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985年内部印行,第532页。相对于鄂豫皖和湘鄂西,黄陂肃反中高级干部被杀的不多,李志民说:“这一次肃反在红五军中没有误杀到团以上干部还算万幸。”*《李志民回忆录》,第140页。
二、赣西南爆发富田事变
(一)富田事变的诱因——赣西南领导人与毛泽东的分歧
毛泽东1929年初带红四军下井冈山,2月中旬在赣南初遇李文林领导的二、四团时,对赣西南党和红军评价很高,认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不公开建立政权的赣西南模式是最好的。但到1930年,苏区敌我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毛泽东的想法改变了。他在1930年1月信中批评林彪不注意建立政权的游击思想,强调“有计划建立政权”,“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甚至要“一年争取江西”,*《给林彪的信》(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集》第2版(2),苍苍社1983年版,第127-129页。这标志着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战略初步成型,这时他对不公开建立政权的赣西南模式态度就不同了,认为这在新形势下是消极右倾。
此时在赣西南,刘士奇是激进派,江汉波(即张怀万)是保守派,他们围绕进攻吉安、整编红军、土地政策等争论激烈。刘士奇批评省巡视员江汉波“取消为攻吉安而组织的总行委及红军总司令部,主张二、四团分开游击”,“反对群众热望的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认为“否认政权的急需也是江同志最大的错误”。*刘士奇:《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给曾觉非同志的信》(1930年2月28日),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一)》甲,1988年内部印行,第51-52页。二七会议后赣西南特委报告提到:“江汉波的思想确实代表了赣西南党内一部分右倾分子,影响斗争不小”,“故西特正确主张的执行发生了许多阻碍,致形成党内的分裂,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各项中心工作都因此停顿在半生半死的状态中。在这样党内政治纷争不能解决的严重关头,四军前委率四军由闽来赣”,帮助赣西南打开了局面。*《中共赣西南特委给江西省委的报告》(1930年3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一)》甲,第60-61页。
毛泽东率四军到赣西南后,1930年2月7日主持召开陂头会议,明确支持激进派刘士奇,认为赣西南部分领导人过于保守,“土地迟迟分配是极端严重的机会主义”,“平分能夺取群众,否则不能夺取全部群众,据他处各处的经验,皆如是”,会上发生了“严重的争论”,“结果按毛同志的意见通过”。*《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张怀万巡视赣西南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4月5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一)》甲,第92页。会议决定建立公开的苏维埃政权,彻底分配土地,扩大红军,进攻吉安,赣西、赣南、湘赣边三特委合并成赣西南特委,由刘士奇担任书记,王怀、李文林、肖道德、丛允中为常委,并且“由前委负责开除江汉波的党籍”。*《中共赣西南特委给江西省委的报告》(1930年3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一)》甲,第61、67页。
但受到批评的赣西南领导人并不服气,而且新特委书记刘士奇性格急躁,“有不满意的地方即乱骂,在乱骂的言词中常有‘枪毙’的话语”,*《中共赣西南特委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7月22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一)》甲,第254页。这也加剧了赣西南的党内斗争。在立三路线时期,李文林5月到上海参加了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他回来后再次与刘士奇发生激烈冲突。刘士奇拒绝李立三对赣西南“农民意识浓厚,保守观念,武装不集中”的批评,“说中央指示不对”,不肯召集会议让李文林传达中央指示。在8月5日召开的赣西南二全会议上,刘士奇遭到多数干部反对,从第二天起就拒绝出席,结果会议决定开除刘士奇党籍,选举曾山为书记,王怀、李文林、郭承禄、肖道德为常委,郭贞、陈婉如为候补常委。*《中共赣西南特委朱昌谐给中央的工作报告》(1930年10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二)》甲,1988年内部印行,第133-137页。赣西南领导人自以为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对毛泽东的总前委也不很尊重了,此时立三路线代表中央,毛泽东自己也受到批评,拿赣西南领导人没有办法。
红军10月攻占吉安后,赣西南党、团、工会等按立三路线指示合并,成立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李文林为书记,曾山、段良弼、丛允中等为常委,李白芳为秘书长,实际上就是新的江西省委。江西行委反对诱敌深入方针,甚至影响到群众也不肯帮助红军。这更让毛泽东怀疑争论不是简单的意见分歧,而是有人故意破坏。很多赣西南领导人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毛泽东进而怀疑他们受家庭影响,站到了土地革命的对立面。按当时的革命道德,这就可以划为敌人了。据当时毛泽东的秘书徐复祖回忆,毛泽东早就“批评丛允中做了三年特委书记,脚不越雷池一步,工作没有发展,就是不抓武装,就是不分田”。*徐复祖:《毛泽东同志关怀边区武装》,《回忆中央苏区》,第80页。随着国民党大军压境,形势越来越紧张,毛泽东和江西行委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
从组织结构的角度来看,江西省行委与红一方面军前委之间权力划分模糊也是爆发冲突的重要原因。立三路线时期,中央在1930年3月的指示中规定:“前委与省委的关系也是横的关系,而直接隶属于中央军委。故边特与省委只能以横的关系供给前委的政治领导而不能指挥前委,前委更不能直接受边委与省委的支配,意见有不同时,直接决之于中央。”*《中共中央关于成立红一军及军事工作的指示》(1930年3月18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422页。中央7月22日全国组织会议决议又赋予行委很大权力:“党的组织在武装暴动时,完全要军事化,全党形成一个军营,一切指挥绝对集中”,“行动委员会在行动中,是最有权威的集中的组织”。*《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1930年7月2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05-206页。“行委”的设立带来了组织系统的混乱,江西省行委试图干预红军作战。而红军是苏区的决定性力量,前委希望地方组织配合红军,双方的上下级关系不清楚,都想指挥对方,这引发了尖锐矛盾,成为富田事变的重要诱因。
(二)黄陂肃反波及地方,富田事变爆发
红军10月在吉安缴获的材料中涉及了李文林等,于是毛泽东把敌人奸细和土改滞后、战略分歧等争论联系到一起,把赣西南当成了肃反的重点地区。离开吉安之前,毛泽东10月14日给中央写信说:赣西南党“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为要“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毛泽东:《给中央的信》(1930年10月14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05页。
中央代表周以粟与毛泽东意见一致,也坚决主张肃反。他对陈正人说,八月赣南特委二全会议“是AB团操纵”,*中共吉水县党史办:《关于李文林被错杀的情况调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江西党史资料》第1辑,1987年内部印行,第332页。在10月19日给湘东特委的信中说:“在赣西南自党团的最高机关、西南两特委、西南苏府直至支部与赤卫队、红军、红色邮局,充满了AB团,很有计划的与邓英等联络一举消灭赣西南苏区的大暴动。幸此吉安夺取,这一阴谋被破坏镇压,这是多么严重的教训!”*周以粟:《给尺冰同志转湘东特委诸同志信》(1930年10月19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第507页。
吉安缴获的名单在肃反中起了关键作用。“占领吉安时发现了在党、苏维埃政权和军队中活动的AB团分子的名单。根据这份名单,许多省委委员都是AB团分子”,“这份名单在通过毛关于逮捕省委的决定时起了很大作用”。*《盖利斯、米夫和马雷舍夫同任弼时谈话记录》(1931年2月19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第82页。据朱德说,文件“涉及AB团,这是国民党的秘密特务组织,在整个苏区进行破坏和组织暗杀网”,“AB团员的名字都是密码,共产党在好几个月内都译不出来。但文件也有不少疏忽的地方,提供了重要线索”。*[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22页。
肃反很快波及江西省行委和新建立的二十军,总前委根据吉安缴获的材料,11月首先逮捕了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又根据肃反中得到的供词,于12月3日派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带毛泽东的信和一连士兵到江西省行委驻地富田。李韶九此时执掌肃反大权,深受毛泽东的信任,但实际上他却是不值得信任的人。刘作抚7月给中央的报告就提到,李韶九担任三军一纵队政委不称职,他一方面揽权包办,另一方面却“只于未出发前的训话非常的勇敢,作战则畏惧怕死”,“一纵大部分人不满意他”,“最不满于李的是北路地方党部与群众”,“北路已向特委建议撤销他的工作给与处分”。*《中共赣西南特委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7月22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一)》甲,第234页。毛泽东重用品质不好的李韶九,也是肃反严重扩大化并激起富田事变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让李韶九带给省行委的信中说:“党内地主富农成分现在举行大规模叛变”,“据此间所获AB团刘天岳、周赤、曾昭汉供出现在省委省苏工作之李白芳、江克宽、小袁、老曾,红军学校之曾国辉,遂川之刘万清,都是AB团要犯,周赤并供段良弼是AB团,龙超清是AB团,除龙超清已由此间直接讯办外,特派李韶九同志率兵一连代表总前委及工农革命委员会帮助省委省苏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省委接到此信务必会同李同志立即执行扑灭反革命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犹豫。”“赣西行委及红军学校方面须防AB团闻信暴动,故处置亦须迅速,二十军须找得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总前委致省行委信》(1930年12月3日),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第98页。
两天后,根据龙超清的最新口供,毛泽东12月5日致信李韶九:“异常严重的党内地主富农反叛已经形成了极普遍的局面,你们需下决心给他一个扑灭。为了要找得线索不可和前次破获特委机关一样将首要杀得太快了。本日据龙超清供称段良弼是省委机关总团长,袁肇鸿是宣传科长,组织科长是江克宽,除江克宽现在东韶即由我们去捉外,段良弼、袁肇鸿是重要犯须立即捉起详审外,再则李白芳更比段袁重要,谅你们已捉了,并且你们要从这些线索找得更重要的人。”*《总前委给韶九同志并转省行委信》(1930年12月5日),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第99页。
12月7日李韶九到达富田后,会同曾山、陈正人,抓捕了省行委和二十军几个重要领导人,包括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军事部长金万邦,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周冕,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几天之内抓捕了一百多人,紧急处决了四十多人。
从毛泽东的两封信可以看出,他对形势做了极为严重的判断,认为在敌军大举进攻的严峻情况下,党内潜藏的敌对分子正在策划大规模叛乱。毛泽东似乎完全相信了刑讯逼供中得到的口供,认为党内存在一个系统性的反革命组织,这些高级干部不可能随便乱供。他说:“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的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他同志呢?别人还可以乱供,段、李、金、谢这样负省行委及军政治部主任责任的为什么可以呢?”*《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第634页。
段良弼的陈述可以回答毛泽东的问题:“我觉得人生在世死是不可免的,不过迟早的关系与死法的不同耳。于是两个大手指几被其打断,身体已被烧烂,几成体无完肤了。忽然停止打,李韶九道:良弼你要死我不给你死,无论如何你要承认是AB团与说出你们的组织,否则给你一个不生不死。”段良弼听此话,心理上再也无法承受,说“承认好了”。李韶九“马上拿我从打地雷公的刑场解下来,拿起笔来要我承认,我握笔写了我是AB团。但李韶九不许,还要写出AB团的组织,否则再受第二套刑罚”。“于是执笔隔了大约一小时,心中总是在思索如何是好,偶然心生一计,我料到此次被捉的人恐无生存,于是我写了李白芳是的,写完之后心悔不该,这是非布尔什维克的行动,但李韶九令士兵将我解到囚房里面去,后提李白芳审问也受了同样的惨刑,结果也承认了,俟后一一提审与受刑罚,结果被捉者皆体无完肤。”*《江西省行委紧急通告第九号》(1930年12月15日),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第104页。
12月9日,李韶九押解谢汉昌到东固二十军军部肃反,会同军长刘铁超,准备大批抓捕二十军干部。二十军是刚从农民游击队升级而来的,并没有经过多少组织纪律训练,也缺少合格的干部,编成正规红军的条件并不成熟,刘作抚7月报告认为“编二十军不对,应当扩充四、六军才正确”。*《中共赣西南特委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7月22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一)》甲,第237页。刘士奇10月报告说得更详细:“二十军是地方赤卫队(特务队)编成的,有枪两千五百枝”,“军事政治干部非常不够,地方主义的色彩比较要浓厚点”,“政治水平比三军还差得远”。*《中共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二)》甲,第88页。二十军干部战士思想简单,政治上不成熟,突然遇到肃反被冤的复杂局面,出现了过激反应。174团政委刘敌12月12日带领独立营武力反抗,抓捕了李韶九和军长刘铁超,又和谢汉昌一起带二十军直属队占领富田,释放了被捕的二十多人,然后把二十军拉到赣江以西,并把红军学校缴械。更为严重的是,他们不仅自己走向分裂,还向地方组织和群众公开发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试图制造红一方面军的更大分裂。
段良弼、丛允中、李白芳等在吉安附近的永阳仍自称江西省行委,并在12月28日按立三路线精神发出进攻吉安通告:“以武汉为中心争取一省与数省政权的首先胜利,是有十二万分的可能”,“现在敌人已进至赤色区域,即是我们围缴敌人的枪的时机到了,就是夺取吉安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时刻到了”。“决定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起至七号止为拥护全国苏维埃纪念周,各县区须开群众大会拥护,七号为夺回吉安总攻击。”*《江西省总行委紧急通告》(1930年12月28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二)》甲,第160-161页。他们在1931年1月1日的决议中提到合法性问题:“省行委是合法的,因为省行委的委员除陈正人、曾山以外其中的委员皆存在,因此省行委是合法的,即是过去的省行委”,“省行委毫无疑问的要存在,并且要领导广大劳苦群众坚决夺回吉安,争取江西首先胜利”。*《江西省行委第二次常委会扩大会决议案》(1931年1月1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年》甲,第4-5页。
在富田事变中,赣西南红军和地方组织都受到影响。“赣西特委书记王怀同志也受到谢汉昌、刘敌等人的影响,后来与他们结成了一伙,还召开了所谓赣西特委扩大会议,指出红二十军在富田举行事变打省苏维埃政府不是反革命行为”,谢汉昌、刘敌、段良弼等人“在河西苏区宣传他们的所谓党内正在进行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谬论,使河西苏区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极端混乱,甚至还影响到河东苏区部分人民和部分党员的认识也渐渐模糊起来”。*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回忆中央苏区》,第19页。红一方面军在苏区遭到了如同在白区的形势。谭震林说:“为什么不去东固?因为东固、富田有AB团。他们造谣,说我们逃跑,不打白军,使那里的群众产生怀疑,不信任我们。”*谭震林:《谈中央红军反第一、二、三次大“围剿”》,《回忆中央苏区》,第146页。三十五军回到信丰城,看到“城里出现很多标语,‘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赣南行委宣”。*陈必达:《回忆三十五军和独立三师》,《回忆中央苏区》,第104页。
丛允中还伪造了毛泽东的信件,信上说要逮捕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企图孤立毛泽东,制造红军分裂。彭德怀识破了伪信,他“当即写了一个不到二百字的简单宣言,大意是: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性质的”,“阴谋分裂红军,破坏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一、三军团在总前委领导下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同志”,对维护红军团结发挥了关键作用。但黄公略听了彭德怀的讲话,只和邓萍说了句“老彭还是站在毛这边的”就走了,没有和彭德怀交流,*《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166页。这说明他的看法有所不同。黄公略领导的红三军出自赣南,也许受军队情绪的影响,他曾经对毛泽东有所怀疑,但后来还是决定支持毛泽东,朱德也表示支持毛。
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公开宣言支持毛泽东,避免了主力红军的分裂,中央六届三中全会指示的及时到达也发挥了作用。12月17日朱彭黄宣言称:“我们敢说毛泽东同志是没有错误的,尤其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总前委的工作路线,完全与中央最近三全大会的路线相符合。”“我们敢大叫一句‘朱毛彭黄’团结到底,打倒反革命的AB团取消派。”*《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为富田事变宣言》(1930年12月1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第601-602页。18日,朱彭黄又给赣江以西的曾炳春、王怀、段起凤并转二十军一封公开信,强调诱敌深入“是整个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策略,已不是泽东同志个人意见,所谓反对泽东同志右倾,等于无的放矢,尤其所谓毛泽东好用政治手段造成一系势力的谣言,更是不从实际说话,挟意攻私,小人伎俩,不值一辩”。“革命潮流低落的荒谬理论,就使一般小资产出身的革命分子,对革命动摇悲观加入AB团,骑墙起来。革命胜利他们是共产党领袖,革命失败他们是AB团,所谓进了保险团,红白都去得。一种最无聊最可耻的卑鄙行动。”*《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给曾炳春等一封公开的信》(1930年12月18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第604页。
在敌军大军压境的危急形势下,富田事变领导者公开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并且召开扩大会议,公开说“毛泽东想作党皇帝”,“毛泽东布置要将江西的忠实干部一网打尽,造成清一色的江西毛党”。*《中央局给西路同志信》(1931年2月4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2)》,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2页。丛允中等还伪造信件,试图分裂红军,这可能给红军带来全面崩溃的危险,是富田事变被定为反革命事件的重要原因。当然,富田事变导致红军发生局部分裂混乱,给国民党十八师师长张辉瓒造成了错觉,以为有机可乘,轻率孤军深入,反而给毛泽东送上了险中取胜的机会,这样复杂的因果关系是任何人都预料不到的。
三、苏区中央局的初建与中央肃反政策的实施
(一)项英初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相对宽容
毛泽东得到富田事变的消息非常愤怒,认为是反革命暴动,派十二军去追击,幸而二十军到赣江以西,两军没有实际交战。他认为富田事变恰恰证明了AB团确实存在,肃反非常及时。《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强调:“AB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五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设不严厉扑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第634页。
虽然毛泽东12月底领导红军取得龙冈大捷的辉煌战绩,但黄陂肃反和富田事变还是对他的威望产生了不利影响。黄克诚、李志民等干部已经对肃反产生了怀疑,不相信这么多熟悉的同志竟是暗藏的AB团,痛惜枉杀战友,朱德、黄公略等高级将领也有很大保留意见。据龚楚回忆,朱德曾对他说:“杀AB团引起的富田事变,也完全是老毛一个人所弄出来的。许多同志全给自家人杀害了”,“现在好了,中央迁到苏区来了,一切由党来解决,不能由一个人来决定了”。*龚楚:《我与红军》,香港南风出版社1954年版,第266页。
项英于1931年1月上旬到达苏区,1月15日在小布宣布建立苏区中央局,并在周恩来未到的情况下,代理中央局书记,此时中央局只有项英、毛泽东、朱德三人能在一起开会。中央局成立的第二天即通过决议,认为:“即使在组织上还没有证明他们全部是AB团取消派,但是他们反党破坏革命的行动在客观上是与AB团取消派等的联合一致的反动行动”,并且把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刘敌、金万邦五人开除党籍,决议同时也批评总前委在肃反中刑讯逼供和扩大化错误。*《中央局通告第二号》(1931年1月16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第639-640页。
决议认为没有在组织上证明富田事变领导者是AB团,只是认为客观效果上是反革命行动,与毛泽东的说法不同。这个决议能够在中央局通过,表明至少项英和朱德不同意原来毛泽东的看法,甚至毛泽东自己的立场可能也有所转变,或许他也意识到肃反错杀了同志。毛泽东非常自信,极少承认错误,但是在红军肃反问题上,他后来曾不止一次公开认错,承认杀错了人,进而主张党内斗争不开杀戒。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公开说:“内战时期,我就打过AB团”,“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杀错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7页。他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谈及江西苏区肃AB团时又说:“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9月10日),《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7页。
1931年2月,邓小平、李明瑞率红七军从广西抵达赣南,刚好赶上富田事变发生不久,当时赣南行委曾一度支持富田事变,三十五军改组赣南行委后,感觉进退两难,宣布与毛泽东的总前委和富田事变后的省行委都断绝关系。赣南党组织后来在报告中说:“赣南党受富田事变的影响,东西河交通关系断绝和敌人的进攻,所以当时虽然建立了苏区党的最高指导机关——中央局,和建立了赣西南党的领导机关——赣南特区委,也无从和他们发生关系,接受他们的指导,这一时期,赣南党活似一个没有爹娘没有依靠的小孩子一样。”*《中共赣西南特区委西河分委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1年6月16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年》甲,第80页。
邓小平接触了赣南干部,为解决冲突做了一些工作。他一方面坚决反对分裂红军,同时也对肃反扩大化提出批评,持相对客观的立场。他说:“过去总前委与省行委向来有冲突”,“故有富田事件之爆发”。“我到后与他们讨论到此问题,批评他们这种脱离组织的解决办法不对,仍须与两方发生固有组织关系,但声明富田事件候中央解决”,“他们同意了这个意见”。“我对总前委之反AB团的方式亦觉有超越组织的错误,这种方法事实上引起了党的恐怖现象,同志不敢说话。”*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4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1册,第690-691页。
七军在解决富田事变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而二十军发动富田事变,犯了近乎叛乱的严重错误,不可能再保留番号。中央5月决定把二十军编入七军,同时提醒七军前委:“在改编二十军时,应当很谨慎的、很周到的不使二十军的群众发生了误会,要把AB团的阴谋在群众中揭发出来,要把二十军中拥护总前委的可靠的干部和士兵群众夺取过来,合编为七军。”*《中央给七军前委信》(1931年5月14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3)》,第1612页。红七军从广西转战千里到达江西,损失很大,由此得到相当的补充,而二十军被取消了番号,大部分干部后来被处决。
(二)段良弼上海告状,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做出严厉决议
谢汉昌、段良弼、李白芳等带二十军过到赣江以西后,认为只有中央才能解决问题。1931年1月段良弼等出发去上海找中央告状,力图推倒毛泽东,他们于2月初到达上海。2月中旬,湘东南党委书记刘士奇和中央提款员易尔士到达上海,他们带来了对毛泽东有利的报告,他们并不是毛泽东派出的,这更增加了报告的可信性,而段良弼却在上海失踪了,从此下落不明。
中共中央和远东局综合分析后,接受了刘士奇代表团的说法,虽然他们认为毛泽东的肃反也有些过火。段良弼的告状甚至起了反作用,他们并不清楚立三路线已被清算,批评毛泽东不攻打大城市,反而证明毛泽东早已自觉反对立三路线,与共产国际不谋而合。向忠发、周恩来向远东局汇报时提到:“‘AB团’根据自己的需要很好地利用了李立三的政策。他们对我们的同志说,你们为什么不执行中央的方针,不去攻打大城市,而呆在农村。”“毛反对这个路线。他就此写信给全会,证明这个路线是错误的。他建议首先清除苏区的一切反革命组织”,“他说,现在去大城市,会使现有的根据地变得不巩固”。*《雷利斯基同向忠发和周恩来谈话记录》(1931年2月19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第83-84页。很明显,毛泽东的主张更符合共产国际的政策。
中央决定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代表团,加强苏区中央局,解决富田事变。2月23日给第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指示信称:“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在中央代表团没有到达以先,从总前委起,江西省委,各特委各红军党部一直到各地党的支部都要立即停止这一争论,无条件的服从总前委的统一指导,一致的向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中央代表团到达以后,中央局立即组织起来,各地党的组织与红军必须统一于这一指导之下,应绝对服从中央局关于这一事变的解决。”*《中央给第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信》(1931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页。
3月18日,远东局做出正式决定,把富田事变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肯定了毛泽东的立场:“1.红20军的暴动”“毫无疑问是阶级敌人及其主要战斗组织——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策划和进行的反革命活动”。“2.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前委同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的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1931年3月18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第175-176页。远东局要求立即解散永阳的省委,20军回到军部指挥之下,否则武力解决:“现在的20军领导应该使全军返回红军并绝对执行总部的一切命令。不履行这一(要求)将会引起同该军的残酷武装斗争。”“革命军事委员会应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20军重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不允许我们的其他军事部队将来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1931年3月18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第177页。
从红军权力结构的角度,远东局强调红军必须集中权力,公开批评上级是不允许的:“20军暴动的惨痛经验使我们不得不认为,并不是军队中的所有党组织都领会了中央和全党赋予它们的使命。”“军队党组织的基本任务是维护红军部队的革命纪律和战斗力”,“每个党员和共青团员的首要的和基本的任务是执行由上级机关任命的指挥员和政委的命令”。“不执行命令、批评作战命令和计划、批评最高指挥员的策略是绝对不允许的”,“公开批评(在会议上、用公开信等)红军指挥部的作战计划和命令是不允许的,即使在红军以外的党组织(即在非军事党组织)内也不允许”。*《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1931年3月18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第178页。
从党的组织体系角度,远东局强调决不允许通过分裂红军来解决党内分歧,武装反抗上级必须受到最严厉惩罚:“十二月事变表明,受反布尔什维克联盟引诱和欺骗的20军部分党员认为,他们所发现的党内分歧可以通过分裂军队来加以解决。”“必须毫不含糊地宣布,任何党内分歧,无论是关于红军问题的还是关于我们的一般经济、土地和组织政策问题的分歧,都决不应引起不仅是军队的分裂,更不要说脱离,而且还不应造成拒绝执行最高军事指挥部指令的行为和军队纪律的下降。对于我们的党员拒绝履行这种起码的义务的行为,作出的反应应该是实行最严厉的惩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1931年3月18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第178-179页。
远东局的决定深入阐发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对中共军队建设影响非常深远。中共中央政治局也在3月28日做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其内容与3月18日远东局决定基本一样,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的绝对服从态度。*《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1931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203-209页。
(三)中央代表团到达,新中央局推动肃反再度升温
4月,任弼时等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苏区中央局所在地宁都县青塘,传达了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决定,推翻了项英主持通过的富田事变决议,组成了新的中央局。新中央局认为原中央局“关于富田事变的解决,也是错误的”,“模糊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没有认清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的参加的反革命暴动,而用‘党内派别斗争’来解释这个事变”。*《中共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决议第一号——关于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1931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1册,第695-696页。
富田事变的主要参与者最后基本都被杀了。郭化若说:“我当时是肃反委员会秘书长。我记得第二次反‘围剿’后,抓到李文林。我参加了审问。李文林说:‘你们不要动刑。我不是AB团分子。我在上海汇报时见过陈独秀,我是陈独秀单派的。’审问后,我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根据他的口供,看来不是AB团,于是把他放了。以后王明路线搞肃反扩大化时还是把他杀了。”“不久,我们又将周冕、陈中日抓来审问。动刑后,周、陈要求作书面交待。但他们写了一下,写不下去。我在旁边观察,觉得他们不象AB团。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不能向他们赔礼道歉。随后,我又把丛允中抓来,这回没动刑,只是向他交待政策,并用了‘诱供’(比‘逼供’更厉害)。这样,他自编了一些谎话,我们信以为真,就把他杀了。”“刘敌回来后,总部开庭审问他。那时主持审问的是朱德同志和董必武同志。审问时,要刘敌说出‘为什么要把部队带到河西去’。他招认是AB团。于是把他杀了。”*郭化若:《回忆第一次反“围剿”期间的有关史实》,《回忆中央苏区》,第141-142页。
在新中央局的推动下,1931年春夏苏区肃反再次掀起高潮,重新出现严重扩大化。吴德峰的肃反工作报告提到:“在三次战争前后,把AB团扩大到无以复加,如各机关打了一次AB团大部被捕后,从他处调一部分人来,不久又被供为AB团而全部被扣留(如邮政局)。”“当时把AB团的力量估计得太大,看得太神秘,以致弄得脚忙手乱。”“在三次战争中,省保卫处有一个奇怪的意见,就是认为富农全体有被认为AB团的可能,提出把富农完全扣留起来,候战争结束后,再审查释放,甚至于公开的说,宁肯杀错一百,不肯放过一个。”*吴德峰:《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续二)~肃反工作》(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479-480页。
这一时期,肃反机构成了超党超政府的独裁机构,肃反成了一切工作的中心。“因为对AB团估量过分,所以当时一切机关都认为打AB团是中心、最中心的任务,把一切工作停顿起来,用全力去打AB团。”“省保卫处自认为是代表党、代表政府的,一切问题独断独行,形成一个超党超政权的组织”,“更有凭借肃反权利而实行其假公济私的,如雩北区有一个村肃反委员与一苦力争野老婆,将苦力捉来说他是AB团用严刑拷打”。*吴德峰:《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续二)~肃反工作》(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480-481页。
这一轮肃反深入波及地方,当时地方干部普遍文化水平不高,作风粗糙强硬,刑讯逼供再次成为主要手段,且花样翻新,酷刑竟有一百多种,指名问供、滥杀无辜普遍存在。“过去肃反工作,缩小在拘捕、审讯、处置这三种范围以内,侦探工作完全没有进行。所有AB团的破获完全是根据犯人的口供去破获的,并没有耐心去考查犯人的口供和搜查旁证,审犯人的技术,全靠刑审。”“在三次战争剧烈之时,天天在行动中,而拘捕之人犯,又多无时间来审讯,于是把拘捕的人犯或被AB团供有组织的机关内工作人员站队点名,询问,如承认加入AB团的,即允许自首自新,不承认的即认为是AB团坚决分子处以死刑(省保卫处处置一次整个保卫队,就是这个办法)。”*吴德峰:《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续二)~肃反工作》(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477-479页。
1931年夏天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后期,中央觉察到肃反简单化和扩大化的危害,8月30日发出给苏区指示信:“中央肯定反AB团的斗争是绝对正确而必要的”,“但不是每一个地主残余或富农分子便一定是AB团”。“农民中的落后意识,群众中党员中的不满情绪和腐化现象,常常被AB团拿来利用,但不是每一个党的错误路线执行者和拥护者,每一个落后的农民,每一个犯有错误倾向或行动的党员或群众便一定是AB团。”“你们对AB团的斗争一方面是将他简单化了。”“另一方面你们又将AB团扩大化了”,“过分夸大敌人的破坏力量与减弱我们自己阶级的坚信心,这是有危害的”。*《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1931年8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372-374页。
(四)闽西肃反杀人较多
在赣西南开始肃反以后,闽西也很快肃出了所谓“社会民主党”。1930年12月,邓发、左权、萧劲光等先后到达闽西,在坑口召开党代表会议,成立闽粤赣省委,邓发担任闽粤赣特委书记,左权任十二军军长、萧劲光为参谋长。这些中央派来的干部执掌军政大权后,积极贯彻中央路线,12月闽粤赣代表大会把傅柏翠开除党籍,是闽西肃反的先声。
事实上,傅柏翠参加革命确实有些勉强。他在政治上是改良主义者,对中共激烈的阶级斗争政策并不认同,最初因为与陈祖康、罗明是好朋友被拉入党。陈祖康叛变、罗明调走以后,他越来越表现出脱离中共的趋向。上杭北四区完全是傅柏翠的势力范围,他被开除党籍后,一个月的时间内,“上杭北四区二百多党员在傅柏翠的领导底下,全体退出党籍,区委支部宣布取消”,“区乡苏维埃宣布取消,另行成立农民联合会”,还提出了“土地、和平、自由三大要求”。*《中共闽粤赣特委给罗明的信》(1931年1月30日),中央档案馆编:《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至1931年),1984年内部印行,第27页。
闽西肃反大致从1931年2月开始,在闽粤赣特委书记邓发和闽西苏区裁判部长林一株的推动下,很快扩大化。3月中央已经得到报告,其中提到傅柏翠以社会民主党的名义活动。“以傅伯翠为首的主力已经脱离12军。傅伯翠是福建的农民领袖,地主的儿子。他现在正在我区招募部队同我们作斗争”,“他们拼凑了所谓的‘新共产党’。工作常常是以社会民主党的名义进行的。主要口号是:‘打倒苏维埃政权!’、‘打倒共产党首领!’、‘反对红军!’、‘农民协会万岁!’、‘自由贸易万岁!’、‘第二国际万岁!’”。“反对我们的第一次暴动是在广州起义周年日之际在傅伯翠的领导下进行的。此后又发生过另外几次骚乱。”王稼祥和任弼时到达当地的那天,刚好发生了一次暴动。“傅伯翠的人夺走了10条枪,解除了警卫的武装,还拿走了钱和食品。他们寻找党的书记和司令部长官,打算把他们杀死。”“在乡村贫农中作口头宣传时,傅伯翠的人使用了这样的口号:‘你们为苏维埃政权奋斗了三年。现在你们没吃没穿。这是给你们的钱,拿去吧,给自己买点吃的穿的。’他们把钱散发给穷人。”*《雷利斯基同周恩来、张国焘和向忠发谈话记录》(1931年3月27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第184页。
中央代表团对闽西肃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月15日到达永定虎岗与闽粤赣特委会合,正碰上闽西党与傅柏翠的冲突。三人在3月23日给中央的信中说:“十二军内的许多政治工作人员,以及红军党的中级干部,各级苏维埃政府机关负责的”都是社会民主党,“我们认为这次特委破获社党一般是对的,所捕人都是根据三个至五个人的口供而实行逮捕的,许多与抄出的明档是相符合。被捕的大多数,并未经拷打”。“我们是主张采取严厉的制裁。一切加入社党而负有责任的”,“一切加入社党而在党团、政府及工会、红军中负责的,均实行枪决”。“现在的情形很严重,然在邓发来后,总算某部分工作中是有进步的”,“尤其是最后社会民主党的破获等,这都算是进步的工作”。*《家、弼、霖自闽粤赣苏区来信》(1931年3月23日),《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至1931年),第72-76页。
邓发得到中央代表团的支持后,肃反更加坚决,在党、政、军系统中一批又一批地破获了所谓“社会民主党分子”。5月27日杭武县东五区发生武力反抗的坑口事变,很快遭到严厉镇压。闽粤赣省委7月15日工作报告称:“永定的党一贯来受社会民主党的把持”,“龙岩的社党,十一次破获他们的县委”,“龙岩党大部分是社党,负责人大部分是社党负责人”,“龙岩二千的党员现在只剩二百,一千的团员现在只剩二十余人了”。“杭武县委也只剩下一个书记(还是我们派去的),其余的人员也没有。”“汀连的县委及各机关,在最近的半月来也破获了大批的社党,县委书记外,全体是社党,县苏主席、肃委主席、军委主席也是社党,各群众团体也是社党把持。”“我们在六月总共枪决了八百二十四个社党,入模范监狱的有二百六十六人,释放的有一百人,半年来所扣留的社党不下四千人(整个闽西),枪决的也不下二千人了。”*《中共闽粤赣省委报告第十三号》(1931年7月15日),《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至1931年),第226-232页。中央巡视员8月3日的报告更为惊人:“据新从那边来的同志的谈话,现在被我们捕杀的已有三千人,拘禁的仍不算。”*《中央巡视员巡视福建情况报告》(1931年8月3日),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7),1984年内部印行,第326页。
中央逐渐对肃反扩大化有所警觉,8月29日写信提醒闽西党组织:“中央认为你们坚决反对社会党是对的,但你们对社会党的认识和处置是不够而且有许多的错误:第一,你们把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和肃反工作的对象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从你们的文件和工作中可以看得出),这显然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你们把社会党组织看着无微不入神妙不可测了”。“第二,因为你们把苏区一切不好的现象都只看作社会党的作用,所以苏区的党,团,苏维埃以及种种群众组织,在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都就不能得到正确的仔细的检阅和纠正,自然亦就不能发展真正的自我批评。”*《中央致闽粤赣苏区省委的信》(1931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350页。
虽然7月邓发去江西就任中央局委员,但闽西肃反至少持续到9月。中央巡视员余泽鸿在8月31日给中央的信中提到:“此间昨日开群众大会纪念彭杨,白沙到近二千人,我参加。下午枪决社党二十余人,我也打了两个,痛快!”“政治保卫处林一株(是副处长),最近发现是社党特委书记,最近扣留,我也去拷问的,他已承认,说出许多材料。”*《中央巡视员余泽鸿自闽粤赣苏区给中央的信》(1931年8月31日),《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至1931年),第290页。在中央的干预下,罗明、郭滴人等开始控制肃反,林一株9月被以社会民主党罪名处决,标志着肃反基本结束。闽西肃反杀了三千人左右,可能是各苏区集中肃反杀人最多的,党政军干部大部分都被杀了,结果是“干部的缺乏真是万分困难,过去县委县苏的负责人,现在留下不上十分之一,区委区苏的负责人,至多也留不上十之三”,*《中共闽粤赣省委报告第十四号》(1931年8月20日),《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至1931年),第250页。损失极为惨重。
1931年底周恩来经过闽西苏区,实地了解到肃反扩大化严重后果,12月18日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现在许多群众不敢与共党接近,恐怕结果又是社党。究竟社党与共党之别在哪里,何种情形方可算罪,群众简直答不出。扩大红军,说群众不积极,十二军团长团政治委员亲口对我说闽西群众不好,而他们一下子便拘捕五六十人(在一百人之中全都是农民而且多是贫农),给以严刑(只据别人一点口供,还说不打不招,等审问清白,连释放都难,因为身体已伤),对群众将成如何影响!这样无怪现在扩大红军之遇到最大的困难了。”“据我在途中所见到闽西党的最近决议及中区党的文件,都还只言反AB团反社党的成功,而未及他的错误。可见此事转变之难与问题之严重性。”*《纠正肃反中的严重错误——周恩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1年12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1册,第835页。
中央1932年1月21日致信闽西省委,严厉批评闽西党在肃反中捕杀大量工农分子,犯了严重政治错误:“中央认为闽西党目前最大的任务是在同肃反中的严重错误做最坚决的斗争。党要绝对禁止对于没有确切的反革命证据的工农分子实行逮捕,严刑拷打与杀戮。”“难道在一个支部内因为书记或其他少数分子是社党,所以能以此证明其他的同志都是社党,以致要逮捕整个支部的同志,而加以严刑拷打吗?”“这种任意逮捕拷打与杀戮我们的同志与工农分子,这种恐怖现象的造成,实际正是在帮助反革命,破坏革命。”“这一错误并不像中央区有些同志讲的,只是一些技术上的错误,而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上的错误。”*《中央为肃反问题致闽西省委信》(1932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3-64页。
四、小结
1930年苏区和红军都获得重大发展,但毛泽东与赣西南领导人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在立三路线支持下,以李文林为书记的江西总行委与毛泽东的总前委在政治、军事方针上有重大分歧。国民党中原大战结束,开始调集重兵准备进攻苏区,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面临空前严重的威胁。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的方针,艰难说服了红军中的不同意见,但遭到李文林等江西行委干部的质疑和反对。红军攻占吉安后缴获了一些敌人间谍的材料,引起毛泽东的警觉,认为有反革命分子打入红军和苏区内部,于是发动了大规模肃反。肃反在野蛮落后的农村环境里出现极为粗暴的扩大化,进而引发了富田事变的反抗。
肃反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肃反扩大化和当时革命队伍生长于野蛮环境,多数干部战士文化不高、思维简单粗暴有很大关系。1930年12月初的黄陂肃反演变成红军历史上一场大灾难,刑讯逼供盛行一时,红一方面军三万多人的队伍,竟有4400人被捕,被杀的人数难有精确的统计,粗略估计达2000人左右。在大敌当前的严峻形势下,红军和苏区陷入一片恐怖气氛中。
远东局和中共中央认为,集中的权力结构是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力量来源,虽然毛泽东领导的肃反有些过火,但富田事变武装反抗上级更加不可容忍,他们在这场党内纷争中支持了毛泽东。项英初建中央局时苏区肃反有所缓和,但任弼时等到达后,新苏区中央局再次推动大规模肃反,并深入波及整个中央苏区,闽西肃反短短几个月竟然杀了3000多人,这是指上级领导的集中肃反,在各地基层群众性肃反中被杀的人数就很难统计了。
从苏联经验出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认定肃反是苏区建立政权的必要手段,强调“站在巩固苏维埃政权的观点上,各苏区应厉行肃清反革命的工作”,“应该注意政权内部政府机关中,红军赤卫队中,工农劳动团体中,文化教育经济机关中,甚至共产党青年团中有无阶级的敌人反革命的侦探暗藏在内,有无进行破坏政权破坏党尤其是破坏红军的阴谋和组织”。“各苏区在革命胜利的第一秒钟便应有肃清反革命委员会的组织,施行对反革命的镇压,同时就要逐渐的开始筹备并建立自上而下有系统的、经常的、政治保卫局的组织和工作。”“肃反委员会要随着它自己工作的深入与有系统,逐渐开始政治机关中红军中各级‘政治保卫局’的建立。”*《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1930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440-442页。
在残酷战争中,既要通过肃反来巩固苏区和红军,又要避免肃反扩大化造成的严重后果,中共不得不在两难之中寻找平衡。在付出了高昂代价之后,中央苏区和红军逐渐建立起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结构。
EliminationofCounterrevolutionariesinHuangpi,FutianIncidentandtheFoundingofCentralBureauinSovietArea
ZhangYong
Facing the attack of Kuomintang in October 1930, Mao raised the "let them in"strategy, but was opposed intensely by the cadres in Jiangxi province. Mao believed there were spies in Red Army, so he began to eliminate the counterrevolutionaries in Huangpi. About 4400 people were arrested and 2000 killed among 30000 soldiers in the 1st Front Army. It triggered the 20th Army's armed rebellion in Futian, which was named Futian Incident.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Far East Bureau and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lieved that centralized power structure was the power source of Bolshevik organization. They believed that the Futian Incident was
more intolerable than Mao Zedong's purges. So they generally supported Mao Zedong in the process of dealing with this incident. When Xiang Ying began to build the Soviet Central Bureau, the elimination eased up. However, after the arrival of the central delegation led by Ren Bishi, the new Soviet Central Bureau once again promoted large-scale elimination movement. The movement has spread to the whole Central Soviet Area and more than 3000 were killed in West Fujian province in a few months. After paying a high price,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and the Red Army gradually established a highly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Elimination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 in Huangpi; Futian Incident; Central Bureau in Soviet Area; Mao Zedong; Comintern Far-east Bureau
10.16623/j.cnki.36-1341/c.2017.06.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