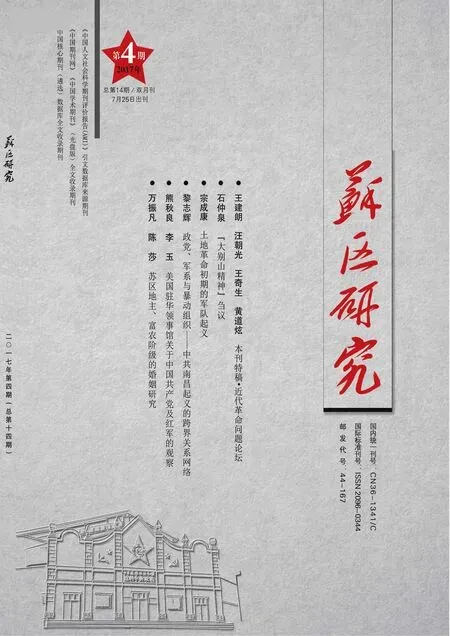苏区地主、富农阶级的婚姻研究
万振凡 陈 莎
苏区地主、富农阶级的婚姻研究
万振凡 陈 莎
苏区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全国执政的探索时期,在如何处理敌对阶级的婚姻问题上,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中共从“阶级斗争”理论和现实出发,对革命阶级的婚姻给予强力支持和保护,同时剥夺敌对阶级从婚姻中获得幸福的权力,尽可能从地主、富农阶级手中夺取“女性”资源,把它送到农民手中。由此形成独特的“阶级成份婚姻”现象,使苏区时期地主、富农阶级的婚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婚姻观念对解放后很长一段时期中国人的婚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苏区;地主;富农;婚姻
苏区时期的婚姻问题,已引起了有关学者的关注。李奎原等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就中国共产党对中央苏区封建婚姻的治理策略和绩效进行了探讨。*李奎原、齐霁:《中国共产党对中央苏区封建落后婚姻的治理》,《苏区研究》2017年第1期,第90-105页。汤水清对苏区有关婚姻法律法规的颁布和实施进行了考察。*汤水清:《苏区新式婚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党的文献》2010年第4期,第62-67页。吴小卫等从妇女解放的视角,对苏区婚姻制度变革进行了研究。*吴小卫、杨双双:《中央苏区婚姻制度改革与妇女解放》,《南昌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第102-105页。黄东从社会改造的角度,对苏区婚姻自由、保护女性等进行了分析。*黄东:《红色苏区婚姻改造述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26-30页。郭静《苏区的阶级与婚姻研究》,对苏区《婚姻法》赋予不同阶级的婚姻权利以及各阶级的婚姻状况作了初步的梳理。*郭静:《苏区的阶级与婚姻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4-41页。然而,现有成果并没有对苏区地主、富农阶级的婚姻问题进行过多的讨论。本文拟从探讨苏区时期地主、富农阶级所处政治、经济地位入手,分析苏区《婚姻法》对地主、富农婚姻权益的限止及剥夺,考察苏区时期在阶级斗争冲击之下地主、富农阶级的婚姻境况,剖析苏区时期这一制度安排对后来中国婚姻问题所产生的长远影响,旨在进一步推进苏区婚姻史研究,并为人们观察、理解现当代中国婚姻现象提供一个窗口。
一、被专政、制裁的反动阶级
按照党的理论,农村中的地主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代表中国最落后的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是革命的对象。富农对农民既有地租剥削,也有雇佣剥削和高利贷剥削,他们“对革命表现出极大的惶惑”,态度“始终是消极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20页。,是农村革命“限制”的对象。土地革命目的,不仅要在经济上摧毁封建经济制度,而且要在政治上推翻地主、富农几千年来在农村的统治。
苏区对地主的政策是毫不含糊、毫不宽容的,这个政策的基本精神,就是打倒地主阶级,从各方面对地主阶级“施行严厉的制裁与镇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24日),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1页。,在经济上用土地革命的办法,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房屋等分给农民,彻底摧毁农村封建制度存在的经济基础;政治上通过对地主实行清算、戴高帽子游乡、关监狱、驱逐、枪毙等措施,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4-26页。据毛泽东《兴国调查》,革命初期兴国第十区四个乡地主的命运是:第一乡,地主不在本乡,都住外地,但田地均在本乡,被没收和分掉了。第二乡,有三家地主,一家在革命中被杀了两个儿子,另两家自动拿出田契来烧,把自己的田分给了农民。第三乡,有两家地主,两家房屋都被人烧了,人则逃亡在外。第四乡,三家地主,一家逃亡在外,一家被杀,一家被政府看押,家财被抄。*《兴国调查》(1930年10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1-212页。苏维埃政府对留在苏区的地主则加紧对其进行剥夺和镇压。1933年6月查田运动开展后,苏区对地主政策的“左倾”化逐步升级,有些地方的做法是将豪绅地主阶级,不论大小,全部抓起来,“编为永久的劳役队”*张闻天:《是坚决的镇压反革命还是在反革前面的狂乱》,《红色中华》1934年6月28日,第1版。;有的地方把所有的地主,“不论大小都捉起来,一律杀尽”*张闻天:《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斗争》第67期(1934年7月10日),第1版。,采取了从肉体上消灭地主的做法。
对富农,苏区在革命初期实行“限制政策”,即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但在实践中限制政策逐步升级,演变为反对甚至消灭富农的政策。1931年9月5日,中共赣东北省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关于苏维埃工作决议案》对富农提出了以下政策:“坚决的反对富农。政治上剥夺他们参加政权的机会,肃清富农的反动,经济上加重他们的经济负担,限制其发展,组织上拒绝他们参加一切群众武装组织的权利。同时,要发动雇农反富农剥削的阶级斗争。”*江西财经学院经济研究所、江西省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99页。1932年中共中央决定在苏区党政机构中发起“清洗富农”运动,把原来参加革命的富农,从党政军组织中彻底“清洗”出去,征发富农组织劳役队,在赤卫军监督下,承担苏区的各项劳役。*《中央人民委员会第35号命令——征发富农组织劳役队》,《红色中华》1932年11月28日,第6版。毛泽东《兴国调查》为我们展现了革命初期兴国第十区实施富农政策的具体情况:第一乡共有十二家富农,其中被杀了家长的有两家,壮丁逃亡在外的有五家,被认为是AB团遭到逮捕的有两家,“捐了款子,平了田”的有三家。第二乡一共有九家富农,其中被杀的有六家,被政府“捉起了”的有一家,自动焚烧田契,把田地分给农民的有两家。第三乡一共有九家富农,其中抄家被杀的有一家,逃亡在外的有三家,被认为是AB团成员被捉起来了的有两家,捐了田和钱的有三家。第四乡一共有两家富农,两家均被杀。*《兴国调查》(1930年10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3-215页。从兴国第十区的情况看,32家富农中,被杀的11家,逃亡在外的8家,被政府“捉起了”的5家,捐出田和钱的8家,被杀和逃亡的富农占总数的60%。
可见,在土地革命的冲击下,苏区的地主、富农,相当一部分逃不过被杀或外逃的命运。国民党方面的材料也证实了这一点。如1930年11月,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向南京政府呈送的报告中就提到:苏区“稍有资产者,或已远循,或已被杀”,“居留之人大半为农工阶级”*《匪共祸赣概况》(电讯),《大公报》1930年11月20日,第3版。。战后国民党方面的有关人员在江西农村调查、考察时也发现:江西苏区“稍有……财产者,未遭残害,亦相率逃亡”*汪浩:《收复匪区之土地问题》,正中书局1935年7月印行,第28页。;“稍有知识或财产者,未遭残害,亦相率逃亡,不敢返乡”*江西省政府经济委员会:《江西经济问题》,台湾学生书局1971年6月影印版,第50页。;崇仁“居民中上产者,多逃至南昌,余亦惶惶惚惚,大有朝不保夕之慨”*陈赓雅:《赣皖湘鄂视察记》,上海申报月刊社1936年12月编印,第14页。;南丰“略有资产土地的地主、富农、商人,甚至中农均被杀害”*爱伯夏:《赣省收复县区视察记》,江西铭记印刷所1935年10月编印,第34页。;南城农村稍有积蓄者“跑的跑、躲的躲,没跑没躲的就遭了杀戮”*刘哲署:《东北大学豫鄂皖赣收复匪区经济考察团报告书》,东北大学编辑部1934年12月编印,第55页。;临川“麋集此间之难民,……数共五千……惟细询之,则无一而非抛财产、弃田园之中产以上者”*陈赓雅:《赣皖湘鄂视察记》,第5页。。这类史料比比皆是,它说明当时农村地主、富农阶级的被杀和外逃的确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即使没有外逃或被杀,在苏区留下来的地主、富农,也受到了严厉的专政。正如1934年1月24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所指出:苏维埃对地主和剥削阶级实施“严厉的制裁与镇压”,“第一件是拒绝他们于政权之外。完全取消他们的选举权,取消他们在红军中在地方部队中服兵役的权利。……第二件,是剥夺一切地主资产阶级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第三件利用革命武力与革命法庭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311页。。在经济上苏区对地主、富农也实行严厉的剥夺政策。1931年夏,苏区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政策,同时苏区政府把捐税重点放在富农身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颁布暂行税则的决议》(1931年11月28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566页。,对富农进行没收、罚款、派捐、征发谷物等剥夺。*刘哲署:《东北大学豫鄂皖赣收复匪区经济考察团报告书》,第137-139页。1932年秋,中共中央决定对苏区地主残余与其家属,实行“绝不能分得土地”,其“所有田地、山林、房屋、池塘通通没收外,其家中一切粮食、衣物、牲畜、农具、家私、银钱等一概没收”的政策。*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训令——为深入土地斗争,彻底没收地主阶级财产》(1932年12月28日),见厦门大学法律系、福建省档案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5页。1933年夏“查田运动”开始后,各地实行“消灭富农的路线”,以至发生“从肉体上消灭富农的现象”。*张闻天:《是坚决的镇压反革命还是在反革前面的狂乱》,《红色中华》1934年6月28日,第1版。可见,苏区地主、富农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其生存条件彻底恶化。
总之,在苏区地主、富农阶级是革命的对象,受到革命阶级的严厉专政和制裁,不仅土地、房屋、财产被没收,而且政治上成为被专政、被镇压的阶级,在社会上成为最受孤立、鄙视的阶级。地主富农阶级这种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为苏区推行剥夺、限止地主、富农婚姻权益的法律和政策奠定了基础。
二、《婚姻法》对地主、富农阶级婚姻权益的剥夺
与上述政治、经济领域的革命斗争相配合,在婚姻家庭领域,苏区也实施了反“地主富农阶级”的婚姻法。从法理上看,法律作为国家统治的工具,具有很强的阶级性,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当统治阶级需要超越道德来维护自身统治和利益时,就会通过法律保护统治阶级的权力和地位,对敌对阶级的权力和利益则进行最大限度的限止和剥夺。苏维埃政权是工农兵政权,工农兵是国家的主人,地主富农是敌对阶级,因此苏维埃政府毫无疑问要实行保护工农兵婚姻权力,剥夺地主富农婚姻权益的婚姻法律和政策。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以前,苏区各地方性法律建设中,就已经出现了限止和剥夺地主、富农阶级婚姻权力的婚姻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1930年4月颁布的《闽西婚姻法》,现将其主要内容摘录如下:*《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82-83页。
一、男女结婚以双方同意为原则,不受任何人干涉。
二、取消聘金及礼物。
三、寡妇任其自由结婚,有借端阻止者严办。
四、夫妇离婚后妇女田地不得归夫家没收。
五、夫妇离婚后子女归夫家养育,但妇女愿意负责者除外。
六、男女结婚须向区乡政府登记。
七、有下列条件之一者准其离婚:①反动豪绅的妻妾媳妇要求离婚者,准予自由。②如有妻妾者,无论妻或妾,要求离婚者,准予离婚。③婢女准其离婚自由。④如有乘白色恐怖来时,将女子嫁有钱者严办。⑤丈夫出外二年以上不通音讯者,准予离婚。⑥妇女离婚后,尚未与人结婚时,男子应帮助其生活。
除闽西外,同时期苏区各地关于婚姻问题大都有类似的条文和规定。如1932年2月公布的《湘赣苏区婚姻条例》,其中涉及地主、富农婚姻的条例主要有:第五条规定“男女因政治意见不和或阶级地位不同,无论男女可以提出离婚”;第六条规定“有妻妾者无论妻或妾都可以提出离婚,政府得随时批准之”。*江西省妇女联合会、江西省档案馆选编:《江西苏区妇女运动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5页。再如赣南苏区其他县份也出台了诸如“离婚结婚有绝对自由”“禁止虐待童养媳”“富农及富农以上的老婆实行离婚之后,在未结婚之前,其间的生活应由男子负责”“在离婚时,其中的财产杂物和牲畜有享受平均分配之权”等等政策。*《江西苏区妇女运动史料选编》,236页。这些政策的基本精神同《闽西婚姻法》差不多,明显具有鼓励地富妻妾同地富离婚的意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以国家的名义先后颁布了两部婚姻法,一是1931年11月28日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二是1934年4月8日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为了分析问题起见,现将两部婚姻法的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共7章23条,涉及地主、富农婚姻的条款,主要有以下几条,其大意如下:*《红色中华》1931年12月18日,第4版。
第一条:男女婚姻必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任何形式的包办、强迫、买卖婚姻,严禁养育童养媳。
第二条: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禁行一夫多妻制或一妻多夫制。
第八条:男女结婚双方必须到乡苏维埃或城市苏维埃进行登记,领取结婚证,没有登记的婚姻将不受苏维埃婚姻法保护。
第九条:离婚自由,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或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即可办理离婚手续。
第十一条:离婚前子女抚养权的归属,如果男女双方都要求抚养,则抚养权归女方,如果女方不愿抚养,则男方必须抚养离婚前子女。
第十四条:离婚后女方抚养的小孩,男方必须承担小孩三分之二的生活费用,直到16岁为止。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共7章21条,涉及地主、富农婚姻问题的条款包括总则在内共有九条,这些条文的基本精神如下:*韩延龙、常兆儒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4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90-795页。
总则: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
第一条: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禁行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
第十条:离婚自由,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或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即可办理离婚手续。
第十一条:红军战士的老婆提出离婚,必须得到红军战士本人的同意,才能办理离婚。
第十二条:男女结婚双方必须到乡苏维埃或城市苏维埃进行登记。
第十三条:在结婚满一年,男女共同经营所增加的财产,男女平分。
第十五条:离婚后女子如未再行结婚,并缺乏劳动力,或没有固定职业,因而不能维持生活者,男子须帮助女子耕种土地,或维持其生活。
第十六条:离婚前所生的小孩及怀孕的小孩均归女子抚养。如女子不愿抚养,则归男子抚养。
第十七条:所有归女子抚养的小孩,由男子担负小孩必需的生活费的三分之二,直至十六岁为止。
从上述史料来看,从1930年地区性的《闽西婚姻法》到1934年全国性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条件、离婚条件和离婚后的子女财产分割的表述基本相同,其剥夺地主、富农婚姻权益的基本精神一脉相承。下面以《闽西婚姻法》为例对此作些分析。《闽西婚姻法》虽然是闽西苏区所有的居民在婚姻问题上都必须遵循的规范,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似乎是一个专门针对地主、富农阶级婚姻问题的婚姻法。七条内容,每条都与限止、剥夺地主、富农的婚姻权益有关,具有明显的革命性、阶级性。
从结婚方面看:由于革命前地主、富农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对于普通农民有绝对优势,经常出现有钱有势的人利用权势强抢民女、民妻,或买卖婚姻现象,《条例》通过肯定结婚“自愿”、“自由”及“取消聘金及礼物”等原则,取消了地主、富农在这方面的优势;《条例》规定“男女结婚须向区乡政府登记”,这条规定便于苏区政府对地主、富农阶级婚姻进行监管,如果发现地主、富农违反苏区《婚姻法》,则不但不批准其结婚,还会进行严厉的制裁。条例规定“如有乘白色恐怖来时,将女子嫁有钱者严办”,是为了防止局势不稳定时期,人们把女子嫁给有钱的地主、富农。
从离婚方面看:《条例》规定离婚条件包括:“反动豪绅的妻妾媳妇要求离婚者,准予自由”,“如有妻妾者,无论妻或妾要求离婚者,准予离婚”,“婢女准其离婚自由”,“丈夫出外二年以上不通音讯者,准予离婚”。这里的“有妻妾者”、有“婢女”者,都是指有权有势的地主、富农;因在革命的冲击之下,原苏区的地主、富农大量的逃亡在外,所以《条例》提到的“出外二年以上不通音讯者”也包括这些逃亡在外的地主、富农。可见,所有的条文给予了地主、富农的妻妾离婚的便利条件,都在支持、鼓励地主、富农的妻妾与地主、富农离婚,以便嫁与革命阶级为妻。
从婚后子女和财产分割方面看:《条例》规定“夫妇离婚后妇女田地不得归夫家没收”,“夫妇离婚后子女归夫家养育,但妇女愿负责者除外”,“妇女离婚后,尚未与人结婚时,男子应帮助其生活”等等,这些条款不仅为地主、富农的妻、妾离婚解决了后顾之忧,而且还使她们在离婚时能带走一部分地主、富农的财产,地主、富农不仅要失去妻、妾,还要失去财产。
总之,苏区通过颁布和实施上述婚姻条例和婚姻法,对地主、富农的婚姻权益进行了全新的规范和强制性的剥夺,并以苏维埃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如有违犯则会受到苏维埃国家执法组织如法院、监狱、军队等的严厉惩罚。
三、阶级斗争冲击下的地主、富农阶级婚姻
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不仅打破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传统乡村地主、富农阶级的婚姻境况。
土地革命前由于地主、富农阶级具有政治和经济上的优越条件,因此他们的婚姻较之一般农民具有很大的优势。在革命之前,苏区的地主富农阶级中一夫多妻制普遍存在。经过苏区革命的涤荡,地富阶级的土地、财产、房屋大都被没收,经济上还不如一般农民。加上政治上地主、富农被打入另册,成为反动阶级,被打击的对象,他们在婚姻方面的优势荡然无存,其婚姻生态变得非常恶劣,婚姻变得十分艰难。
1.地主、富农本人的婚姻。如前所述,苏区地主、富农分三种情况,一是被杀,一是逃亡在外,一是留在苏区。被杀的地主、富农,其本人不存在婚姻问题,只是留下了他们妻妾的婚姻问题,对此后文进行分析。
携家逃亡在外的地主、富农,除了那些特别有钱、在外特别有势的大地主的婚姻状况比较稳定外,其他的地主、富农的婚姻都面临极大的困境。许多中小地主在外花光了所有财产后,逼迫自己的妻、妾、媳、女去卖淫来养活他们,这种婚姻关系名存实亡。如1930年4月5日,《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就提到“大豪绅已离开吉安而跑往沪宁,下焉者生活无计……则迫令媳女妻室卖淫”。*《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182页。1930年10月7日,《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也提到“土劣的妻女,以前威风凛凛的,现在大半在吉安、赣州当娼妓,土劣则挑水做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361页。可见,同以前相比,逃亡在外的地主、富农本人的婚姻生活非常悲惨。
留在苏区的地主、富农,由于政治、经济地位的下降,其婚姻也岌岌可危。如上所述,苏维埃颁布的婚姻条例和婚姻法,旗帜鲜明地鼓励地主、富农的妻妾与其夫离婚再嫁他人。在苏维埃政府的鼓励下,为了摆脱困境,许多地、富的妻妾纷纷同地主、富农离婚。史料记载苏维埃政府“对地富的妇女要求离婚是很容易批准的,因为离了婚可以和农民结婚了,而且在运动中不少地方发现把妇女当果实分配给农民做老婆”的情况。*梁红:《认真检讨妇女工作严格批判错误观点》,《新华日报》1948年12月31日,第2版。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革命时期“女人的身体就会和土地一样被重新加以分配,总的流向是从富人家到穷人家”。*金惠敏:《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4-55页。显然,地主、富农本人的婚姻陷入了危机,女性“资源”日益流失。
2.地主、富农妻妾的婚姻。被杀、外逃的地主、富农多为家长和壮年男子,除了随同地富老公被杀、外逃之外,其他地主、富农的妻妾则留在了苏区。她们如果不同地主富农离婚,同样要受到严厉的镇压和打击。《红色中华》第59期发文号召:要无情的严厉打击“对于地主富农家属的怜悯现象”。*刘祥文:《对于地主富农的“怜悯”》,《红色中华》1933年3月9日,第3版。有些地方因为“地主婆每日笑骂群众”便由群众大会决定将其枪毙了。*邵式平:《闽赣省查田突击运动的总结》,《红色中华》1934年4月28日,第3版。有的坚持反动阶级立场的地主、富农妻妾,被编入“劳役队”,开垦荒山荒地和做苦工。有些地主婆表面不对抗革命,但心存不服,同样也遭到打击。《红色中华》第185期一篇题为《好厉害的地主婆》文章,揭露地主婆在苏维埃政府筹款时,“总是坚决的拒绝,最后他便冒充乞丐,以图掩饰群众的耳目……始终不肯拿出分文”,后来把她几个女儿抓起来审问,才在“地主婆家里挖出金子一两四钱,现洋三百四十九元,银子三十余两,羊皮三件,还有鸦片烟一碗,衣服多件”,文章提出地主婆“是非常顽硬的、机诈的”,必须对她们进行无情的斗争。*张仁贤:《好厉害的地主婆》,《红色中华》1934年5月7日,第3版。
经过革命的再三剥夺,留在苏区的地主、富农妻妾,不仅政治上抬不起头,而且基本上没有了经济来源,迫于生活的重担和社会的压力,许多地富妻妾只好另寻出路。有的跟了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比如有史料提到“区政府打土豪捉来一个土豪婆(靖卫团总的媳妇)罚了大洋四十元,结果未交款,便由一个委员拿去做了老婆”。*朱权:《西冈区的严重现象》,《红色中华》1932年2月24日,第7版。有的则主动寻求出路,如1932年3月23日《红色中华》第15期记载,在闽西南的选举运动中,就出现了“地主富农家之女子因没有选举权,纷纷到政府要求离婚,不愿做地主富农老婆”的现象。*口城:《闽西南选举运动中的成绩》,《红色中华》1932年3月23日,第7版。以致1933年12月15日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出台“未结婚的党团员应教育他不能同地主富农结婚”的规定。*《江西省女工农妇代表大会第四天——闭幕》(1933年12月15日),《江西苏区妇女运动史料选编》,第133页。这说明苏区存在比较多的地主、富农妻妾同地、富离婚,而与革命阶级结婚的事实。
3.地主、富农女儿的婚姻。地富的女儿由于生活条件优越,保养得好,较之一般农民的女儿更加漂亮。那些从未碰过女人、“苦大仇深”的农民认为,以前我们受尽地主富农的剥削、欺凌,娶不到老婆,现在天天革命,搞个把地主富农女儿算得了什么。因此,革命中地富的女儿(包括部分地主富农年轻漂亮的妻妾)被强奸以至轮奸的应当不在少数,只是事发后不敢报案,因为即使报案,苏维埃政府的政策也是残酷无情地打击地主富农,不可能站在地主富农一边。有不少地富的女儿被苏维埃政府的地方干部强迫嫁娶。有的地方“强迫地富的女儿与未婚农民成婚,而不问其本人是否愿意”。*《中央局滕代远巡视湘鄂赣苏区的报告》(1931年7月12日),张叔复等编:《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6页。宜黄县东陂区在1932年9月捉拿了一个地主的女儿,年轻漂亮,苏维埃政府答应只要女子家里凑足105元大洋来保这位年轻妇女,就可以把她放回家。但是区苏维埃裁判部部长李衣禄“公开把这个女子放出来弄去同他一床睡觉”,一个月后这个土豪女子家里送来了105元,然而“裁判部长李衣禄还是把她留在身边快活”。*熊珍:《贪污与腐化》,《红色中华》1932年11月14日,第8版。当然,与地主富农女儿结婚或有染的人,后来其政治前途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影响,许多人还受到清查。
也有不少地方,地主富农主动将女儿嫁给乡村苏维埃政府干部或革命农民为妻,希望社会地位与生活条件有所改善。*陈赓雅:《赣皖湘鄂视察记》,第120页。对此,苏维埃政府进行了干涉和限止。1931年12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出台了《对于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规定“豪绅地主及加入反革命组织和自动领导群众反水的富农的老婆、媳妇、女儿同工人、雇农、贫农、中农结婚的,本条例颁布以后,不得分配土地”,“以招郎形式试图保住财产的豪绅地主富农家庭的财产、房屋仍一律没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4卷,第124页。1933年9月30日颁布的苏区“查田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查田运动中的阶级分析》也指出:“地主富农的妻女媳妇与贫苦工农结婚后,他的阶级成分是不能改变的,她们过着地主富农剥削的生活,革命后或者是革命前不久,同贫苦工农结婚,他的成分不因嫁了一个贫苦工农的老公而变改。当然不能和贫苦工农一样分田。”*欣:《查田运动中的阶级分析》,《红色中华》1933年9月30日,第6版。党和政府认为地富阶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地主女儿剥削阶级思想是不易改变的,娶她们做老婆会影响老公的革命工作。所以,尽管许多地富女儿愿意嫁给革命农民,却不被接纳,以至出现“地富女孩子因找不到老公而自杀”的现象。*李六如:《谈湘赣苏区土地革命》,《回忆湘赣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0页。
4.地主富农儿子的婚姻。革命前由于家庭条件优越,地主富农的儿子一般都能娶到一位如花似玉的妙龄姑娘为妻,有的还会三妻四妾。经过革命的冲击,地主富农儿子娶不到老婆则成为常态。首先,一般女孩不会主动跟地主富农的儿子结婚。因为苏区时期地主、富农是“反革命阶级”,不仅在政治上没有政治权力、经济上没有分配土地和财产的权力,没有任何政治经济前途,而且还要经常受批斗、受镇压。一个女子如果与地主富农儿子结婚了,这个女子就成了地富婆,就成了阶级敌人,成为革命打倒的对象。而且苏区政府规定“不论何时与何种成份结婚,所生子女的成份与父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933年10月10日),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61-62页。就是说其子子孙孙都逃不脱“反动阶级”的命运。因此,家庭成分是贫下中农、工人的女孩,往往不会选择地主、富农的儿子作为恋爱和结婚的对象。
其次,苏区党和政府,对地主富农儿子的婚姻权力进行了种种限止和剥夺,基本精神就是“将对革命有危险的人踢出局,剥夺这些人从婚姻中得到幸福的权利”。*金惠敏:《身体的文化政治学》,第62页。前述苏区婚姻法,不仅在结婚条件上对地主富农儿子的婚姻权力有种种限止,而且即使地主富农儿子娶了老婆,苏区政府也积极支持、鼓励她们离婚。许多嫁到地主富农家做媳妇的女人,为了和地主、富农家庭划清界限纷纷离婚。一顶地富帽子会让地主富农儿子终身抬不起头来,“地富”作为一个被打倒的阶级,过着比“贫下中农”还苦的日子,在社会上遭受敌对和孤立,地主富农儿子是不敢奢望从婚姻中得到幸福的。他们同以前的贫苦农民一样,很难娶到老婆,最好情况是娶到一些“低档次”的女人为妻,比如同样是阶级成份不好的女人、智力有问题的女人、身体有问题的女人或离过婚的女人等。部分地主富农儿子开始品尝“光棍”生活滋味,有的甚至一辈子都没有“碰”过女人。
四、结论
苏区时期,为了推翻封建统治、打倒地主富农阶级,中共把阶级斗争引入到苏区社会的各个层面,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对地主富农阶级进行严厉制裁与镇压。在婚姻家庭方面,苏区同样实施了剥夺地主富农婚姻权益的政策和法律,在结婚条件、离婚条件和离婚后的子女、财产分割等方面对地主富农的婚姻进行严苛的限止和剥夺,基本上否定了地主富农阶级的婚姻权力,使地主富农阶级的婚姻生态极端恶化。在阶级斗争的冲击下,地富本人处于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境地;地富的妻妾虽然大量同地富离婚,而嫁入革命阶级家庭,但同样受到了歧视和打击;地富的女儿有的被强迫与农民成婚,有的主动嫁给革命阶级为妻,希望改善社会地位与生活条件,但这种希望因苏维埃政府关于嫁与革命阶级为妻的女人其“阶级成分不能改变”的规定而破灭;在苏区,地主富农儿子娶不到老婆成为常态,他们最好情况是娶到一些“低档次”的女人为妻,有的甚至一辈子打“光棍”。
苏区在地主富农婚姻问题上的这些做法,在当时对于打击地主富农阶级嚣张气焰、削弱敌对阶级力量、巩固苏维埃政权、推动革命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由此形成的“阶级成份”婚姻观念,为后来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所继承,并对建国后中国人的婚姻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依然可见它的历史痕迹。但是这种建立在阶级斗争化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婚姻观念和制度,使婚姻离它的“两情相悦而结合”的本质相距甚远,两性关系中的感情已不再是婚姻的基础,男女婚姻具有功利化的特征。尽管这种做法在革命战争年代无可厚非,但在和平年代,人们要做的应该是让婚姻回归它的本真。
责任编辑:魏烈刚
A study of the Marriage between the Landlord and the Rich Peasant Class in the Soviet Area
Wan Zhenfan Chen Sha
The Soviet area was the period wh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arried out the national power. Therefore, there was no ready-made experience to draw upon about how to deal with the marriage of the hostile class. Based on the theory and reality of "class struggl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trongly supported and protected the marriage of revolutionary class, whereas deprived the hostile class of the power to derive happiness from marriage. The party seized the "female" resources from the landlords and the rich peasants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delivered them to the peasants. Because of this policy, an unusual phenomenon of "blended-class marriage" was then shaped, not only bringing upside-down change to the marriage between the landlord and the rich peasant class in the Soviet area, but also exerting a significant and long-lasting influence on Chinese people's marriage and marital life.
Soviet area; landlord; the rich peasant; marriage
10.16623/j.cnki.36-1341/c.2017.04.011
万振凡,男,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陈莎,女,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江西南昌 33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