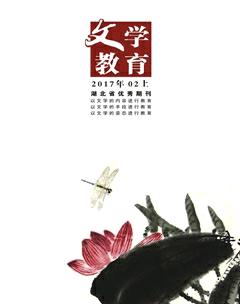词的隐匿与隐匿的词
记得那是一个傍晚,我在江夏医药园下车,前往朋友所在的饭馆。朋友在电话里告诉我饭庄就在精神病院对面,我随意问了一个路人:阿姨,精神病院怎么走?那个中年妇女一脸的惊愕和厌恶,至今令我印象深刻。这次经历在我读完杨邪的《那儿》再一次被唤醒,平心而论,这篇散文触及了一个在观念世界里不大吉利的词——死,它与殡仪馆、癌症等词相伴相生,充满禁忌,始终处于日常口语中被遮蔽的地带。事实上,这一类的词语还存在不少,诸如性、疯癫、艾滋病等等,人们对它们的讳莫如深,实则是一种有意地放逐与规避。
《那儿》起笔颇巧妙,一大清早,“我”拦下了四辆出租车,都没能成功地去往“那儿”,这种小说的笔法使得文章疑虑重重。在费尽力气坐上了红色出租车后,“我”深知如果说出地点是殡仪馆后,自然无法逃脱被拒载的命运。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女司机的询问,“我”王顾左右而言他,明明知道目的地,却始终以“那儿”搪塞她。“我”与她的对话颇具荒诞色彩,几个来回的交锋中充满了话语缝隙。终于,司机得知“我”是去往殡仪馆,满脸的冰冷扑面而来。
到达了“那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的白色”,这种冰冷的色调给人更多的是悲凉感。毋庸讳言,那个胖妇女乘坐公交车去殡仪馆的笑话又一次呼应了“我”早晨的经历,其中的尴尬与无奈只有自己知晓。“我”是去参加一位画家的追悼会,殡仪馆的局促、冥币与鞭炮的残骸、逝者亲属号啕大哭声……这些颇具死亡气息的意象引起了“我”的思索,在追忆与画家的交往后,“我”的内心生发出一种敬意与慨叹,他经过与死神的“这场战争”,赢得了十八年的时光,这段抗争的岁月凸显了生命存在的价值与信仰的意义。
在接下来的行文中,死亡的气息逐渐向作者靠拢。准备过六十大寿的三叔被查出肺部长有恶性肿瘤,生命所剩时间不长。对于家族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噩耗。而“我”明知事实,却想尽办法编故事来隐瞒真相,甘愿配合“完成出色的演出”。不难看出,“我”的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痛苦,这就是一种命运的怪圈,当我们试图戳破词语坚硬的外衣时,却又不知不觉中给他裹上了一层隐形的壁垒。说出真相是残忍的,因为真相中藏有那些我们在生活中谨小慎微规避的“不良”词汇。饶有意味的是,作者将对死亡的思索与书写进一步延伸到了自身,轮椅上的三叔在“我”的幻觉中变成了“我”,而推着轮椅的“我”则像是“我那年幼无知的儿子”,这种角色的转换无疑拓宽了个体生命对死亡思考的深度与广度,使得死亡具有一种普遍而肃穆的意義。文末,“我”胸口剧烈的咣当之声,看似身体发出的信号,实际携带着丰富的人物心理讯息。从叙事层面上看,结尾的“咣当之声”是对散文开头四次拒载的回应,它是一种小说叙事笔法,流露出作者较强的叙事能力。
在我看来,“那儿”是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词语。它既指代文中出现的“殡仪馆”,又暗指被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社会因素自觉或不自觉规避的一系列词汇,这些词语沉潜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之下,在我们的口语中难觅其踪迹,渐渐地成为被放逐的对象。发掘那些被规避的词语,寻找到其隐匿于生活的路径与原因,从而窥见词语背后携带的巨大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信息,不失为一条颇有艺术野心的写作之路。我以为,《那儿》的意义就在于此,杨邪的散文也因此而拥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周聪,青年评论家,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现居湖北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