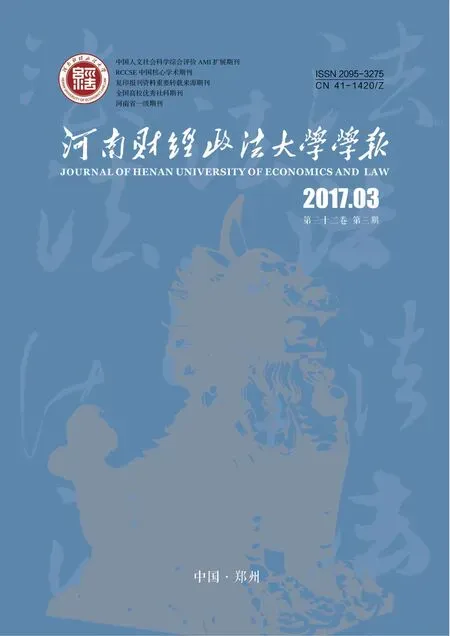论律师职业伦理的冲突与消解
索站超
(河南大学 法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论律师职业伦理的冲突与消解
索站超
(河南大学 法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律师常常面临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之冲突、多重责任之冲突以及职业主义和商业主义之间的冲突,根源在于其自身公共性与商业性的内在冲突以及职业伦理与大众伦理的分野。由于制度安排,中国律师还面临着自治困境、忠诚困境和认同困境等特殊的职业伦理困境。除了借鉴他国对律师公共责任的强调以及制定行为示范规则外,我国还应当在律师的重新定位、职业养成与训练、职业准入制度等方面进行调整,同时增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实效性,从而最大限度地消解职业伦理困境,促进律师职业的健康发展。
律师;职业伦理;律师责任
律师作为权利卫士与民主的斗士,理应是一个受人尊重和爱戴的职业,但事实上,律师却很少享有此殊荣和地位,坊间时常流传一些讽刺和挖苦律师的段子。这种状况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都有发生,美国的“快乐湖案”、中国某明星之子强奸案等都让人们对其中的律师职业伦理产生了强烈的质疑和批评。随着法律服务市场的兴起,不少律师逐利倾向明显,远离了刑事辩护等传统业务。人们不禁要问律师为何要坚守与普通人不一样的行为准则,律师是商人吗?如果律师只是在兜售法律,正义如何才能获得?作为法律职业的一员,律师职业承载着人们对社会正义的期待与希望,律师的伦理危机必然会带来较多的负面影响。世界各国历来都重视对律师职业的规制,通过各种努力缓解律师的伦理冲突。我国律师职业恢复三十年来发展迅速,但也出现了较多影响行业发展的问题,职业伦理困境就是其一,亟待解决。本文从普遍的律师职业伦理冲突入手,围绕我国律师职业伦理的特殊困境展开研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消解的路径,希望对我国的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律师职业伦理冲突的现实与根源
律师是一个毁誉参半的职业,常常要面对诸多的伦理困境,无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柏拉图的“杀光所有的律师”,克罗曼所描述的“迷失的律师”以及我国近年来对律师的一些负面评价都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对于哪些是因为违反职业守则而招致的批评,哪些是律师正常执业却被误解的,公众并非能够弄清楚。因此,很有必要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对律师职业伦理冲突的现状和根源进行分析。
(一)律师职业伦理冲突的现实
关于律师伦理之冲突,一般认为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律师对程序正义的追求与公众的朴素正义观之间的冲突,二是律师的职业精神与商业追求之间的冲突[1]。本文认为除此二者之外,律师所承担的多重责任之间也会经常发生冲突,并且难以协调。
1.程序正义观与朴素正义观之冲突
正义是普罗修斯的脸,具有不同的面孔。随着法治意识的增强,人们发现程序正义同样重要,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立价值。然而,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在很多情况下却并非一致,例如,侦查机关为收集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证据而进行刑讯逼供,暴力取证,律师接受当事人的委托为其辩护,可能提出非法证据的排除请求,为当事人进行无罪或罪轻辩护。这时就出现了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之间的冲突。选择何种正义,对律师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实体正义符合人们的朴素正义观,是人们不懈的追求。如果刑事诉讼被告人因为控方证据的瑕疵而被判决无罪,逃脱了法律制裁,虽然程序正义的价值得到了充分体现,但却与人们对实体正义的追求相距甚远,律师也会因之受到批评。
2.职业主义与商业主义之冲突
律师被认为是传统意义上的三大职业之一,具备庞德所说职业(profession)的三大特征:第一,建基于深奥理论基础上的专业技术,以区别于仅满足实用技巧的工匠型专才。第二,为公众服务的宗旨,其活动有别于追逐私利的商业或营业(Business)。第三,形成某种具有资格认定、纪律惩戒和身份保障等一整套规章制度的自治性团体,以区别于一般的“工种”(Occupation)[2]。因此,职业的主要特征也就在于专业性、公共性和自治性。律师职业发达的西欧国家,很长时间以来,律师都被认为是典型的职业类型,拥有良好的职业修养和职业尊荣。
随着法律职业的发展,法律服务市场逐渐形成,律师的商业属性也逐渐被人们认可。律师通过为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获得相应的报酬,从本质上讲也是一种交易行为、市场交换和有偿服务。然而,律师商业性的一面却很容易遮蔽其公共服务的职业宗旨,而引起社会的误解和批评。有公众认为律师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有许多公众甚至认为,律师拿着有罪的委托人所给的“黑心钱”为其进行辩护、开脱罪责,因而是司法正义的终结者。这恰恰也是律师职业伦理合理性论证难题的症结所在,是律师的伦理困境之一。
3.律师多重责任之冲突
在多重利益面前如何选择也是律师职业经常面临的又一个伦理困境。律师不只是委托人的代理人,要对其忠诚和守密,维护其正当权益;与此同时,律师承担着司法制度上的责任,需要对法庭负责,并维护公共利益。律师执业还不能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正是因为律师同时兼顾这多方面的利益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这就给律师的选择带来了较大的难题,使其纠结甚至陷入伦理困境。
利益冲突中最典型的是在当事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虽然律师在诉讼中应保持相对独立,但是对委托人的党派性忠诚却是首要的义务。律师对职业伦理的坚守,有时候会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因此也会遭受批评与指责。20世纪70年代美国有名的“快乐湖案”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该案的律师由于没有向社会和受害者亲属披露其从当事人处获得的秘密,而在案件真相大白之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引起了公众和当事人亲属的谴责和不满,其中一名律师甚至被提起诉讼。尽管最后法庭认定律师保守秘密的行为符合职业准则,该律师没有受到法律惩罚,不过在社会舆论那一关,两位律师却伤痕累累,败下阵来。
(二)律师职业伦理冲突的根源
律师职业有较强的社会性,其伦理困境很大程度上与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念有重要的关联,所以研究律师职业伦理冲突,除了关注律师职业自身属性以外,还应注意公众对律师评价的影响因素,大众伦理与律师伦理的关系。
1.公共性和商业性的内在冲突
关于律师属性的基本定位,学界有诸多讨论和提法,有学者认为律师职业具有法定性、社会性、专业性和专门性、独立性、自律性和自治性等专门属性[3]。然而,律师职业又不同于其他的社会中介组织,律师的事业关系公民的权利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律师还应具有属性。其实,法律服务作为一个公共职业并不是新鲜的观点。从罗斯科·庞德到美国律师协会,法律职业一直都被描绘为一个公共性的职业。庞德把公共精神的理念看作是法律职业的精髓,他认为,法律职业中的公共服务精神是并且应当是一个成熟司法体制的先决条件[4]。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也认为,律师制度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向一切需要他们的人提供法律服务以及政府和其他机构合作进一步推进正义和公共利益的目标”,“应特别注意对穷人和其他处境不利的人给予帮助,使他们得以维护自己的权利并在必要时请求律师协助”*该原则于1990年9月7日通过,参见程味秋等:《联合国人权公约和刑事司法文献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267-272页。。
随着法律服务市场的形成以及大型律师事务所的出现,律师业的商业化倾向不可避免,律师的商业属性也日益彰显。由于律师是一个赚钱的行业,所以就难免会滑入过度商业化的境地。美国律师业发展的历史应该成为律师职业发展的前车之鉴。早在19世纪末,美国的律师就已经出现了商业化的倾向,伯纳德在其《美国法律史》一书中对这种倾向进行了形象的描述,认为“律师事务所已经逐渐成为现代企业”[5]。由此可见,在世界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律师职业的商业化似乎是各国律师职业所遇到的共性问题。律师职业本身的商业性和公共性二者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公共性强调律师的利他服务,商业性则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律师对待自身存在的这两种属性,难免会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形,所以就极有可能受到负面评价,而陷入伦理困境之中。
2.职业伦理与大众伦理的分野
职业伦理不同于朴素的大众伦理,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分野,所以律师正常的职业行为也有可能遭受公众的不满和误解。这是导致律师陷入伦理困境的另一重要原因。
律师所遵循的伦理与大众伦理并不总是一致的。美国的法理学家朗·L·富勒曾就律师的职业道德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刑事案件中,律师替一个他明知有罪的人辩护是完全妥当的。非但如此,而且律师还可以收取费用,他可以出庭替一个他明知有罪的人辩护并接受酬劳而不感到良心的谴责。富勒说,假如被告所请的每一位律师都因为他看上去有罪而拒绝接受办理该案件,那么被告就犹如在法庭之外被判有罪,因而得不到法律所赋给他的受到正式审判的权利。……假如他因为认为一个诉讼委托人有罪而拒绝替他辩护,那么他便错误地侵占了法官和陪审员的职权[6]。律师可以为他明知有罪的人辩护,这一职业伦理与普通伦理的明显抵触也是一个例证。因为大众道德是服务于实体正义的道德,而在律师看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只要程序允许的就是对的,只要为了委托人的利益就是对的和善的[7]。
律师的职业伦理困境具有普遍性,无论是在欧美国家还是大陆国家,抑或是在我国,它与职业自身的特点紧密关联。然而由于律师职业在各个国家司法制度中的安排不尽相同,因而各国律师也会面临不同的境况,会有其特殊的伦理困境。
二、中国律师职业之特殊伦理困境
在世界律师商业化趋势的影响下,我国律师职业也面临着与西方国家同样的伦理困境,即公共责任与商业化之间的冲突困境。另外,由于在律师养成、管理制度和亚文化等方面的特殊性,我国律师的伦理困境也有着自己较为明显的特殊性。为了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律师的实际情况,除了对现有的一些律师手记、律师传记、律师访谈以及关于律师的写实小说等进行深入研究外*目前看到的有:王俊凯:《草根律师成长日记》,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赵国君:《与正义有关:中国律师纵横谈》,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郭登科:《律师手记》,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范一丁:《回归使命——律师的“实践”之责》,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韩启照:《律师的黑白人生——永不妥协》,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慕容雪村:《原谅我红尘颠倒》,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笔者在2013年还曾对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河南、山东、陕西等七个省市的32家律师事务所的部分律师进行问卷调研,对年龄分别在25岁到66岁的多位执业律师进行个别访谈*其中既有从业一年的律师,也有30多来一直坚持在律师行业的老律师,如河南开封时代律师事务所的王律师,他对30多年来中国律师的发展变化就深有感触。。由此,本文对中国律师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认为当前中国律师至少有以下三种伦理困境:自治困境、忠诚困境与认同困境。
(一)独立与依附之间的自治困境
律师自治是律师职业伦理的关键内容,也是重要基础。律师职业伦理的核心是律师与当事人、法官、检察官和同行之间的关系规范,出于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和社会公平正义的考虑,律师需要对法官和检察官的司法公权力进行潜在的制约,而制约作用的发挥必然需要独立的律师来完成。
所谓自治,就是以自己的意志来自律性地处理自己的事情。律师自治就是把对律师资格的审查和惩戒处分权交由律师自律,律师的执业活动和规则不受法院、检察院和行政部门的行政干预[8]。由于排除国家监督和维护国民基本人权、实现社会正义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基于如此重要的宪法功能和意义,世界各国都通过各种形式来保障律师自治。在访谈中,有多位律师朋友都对笔者设计的问卷表提出意见,即为何没有列出律师对司法行政管理的看法呢?言谈中,笔者发现他们中的不少人对当前的律师行政管理状况表示担忧,认为司法行政管理的方式有待进一步改善,有些措施违背了律师工作规律,是一种不恰当的外部干预。这种状况也是笔者的前见,所以设计这样的选项可能意义不大,会出现一边倒的绝对情况。但是,在与另外一些律师朋友的谈话中,有人提出不同看法,那就是鉴于中国律师当前体制之外的地位,还是需要有一个“婆婆”能在体制之内为律师说话。第二种意见反映了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虽然这样的情况明显不符合律师独立性和律师自治的要求,影响律师功能的正常发挥,但是如果拒绝外部的管理和“代言”,那么中国律师的执业环境和执业行为恐怕又会遇到更加困难的情形。所以说,当前中国律师遇到了职业独立还是依附这样的自治困境。
在中国当前现实语境下,如果选择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职业,那么,由于身在体制之外,律师很难在我国的政法体制中有话语权,也很难与其他法律职业进行平等沟通和交流,1996年以后的二十年实践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法官缺乏对律师的尊重,检察官和警官与律师关系紧张等等。二十年来,律师职业许多权利的争取都是经由司法行政机关的努力而获得的。比如在历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司法部都能对其中关于律师的条款提出意见,为律师顺利执业做出了一定的努力。有研究指出,“律师在内心的潜意识里还是较为认可这样的‘上级主管部门’,希望能在国家强势机关中寻找一个归属,这个归属地位能够帮助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在与其他国家强势机关交往时找到代言人,在律师自身要维权时能够寻找到便捷的救济管道,在与当事人交往时能够用对方习惯的方式接受”[9]。很多律师事务所喜欢在所里醒目位置放置获得司法行政机关授予的先进单位与个人的牌匾,也从侧面反映了律师对司法行政管理的接受程度(当然不排除把奖牌公开还有其宣传目的)。
既然选择司法行政机关作为上级主管部门,就要接受其管理。现实中,司法行政机关不仅仅是律师的代言人,还承担着律师的教育与惩戒职责。作为司法行政机关,必然要代表国家行使对律师管理和教育的任务,对律师界的教育整顿等也是由司法行政机关来推动。
如此,随着律师业的进一步发展,律师所面临的自治困境就逐渐突出起来,选择自主,律师业面临现实的生存危机;选择依附,却不符合职业自身的性质和要求,而且易于受到过多的干涉。
(二)委托人责任与“国家责任”之间的忠诚困境
在律师的多重责任中,原本没有国家责任这一项,除了委托人责任以外,律师还需承担公共责任、司法制度上的责任以及对其他当事人的责任。然而,在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下,律师还有特殊的使命和定位,即与现行的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中国律师这个特殊的使命和定位不同于通常意义上所谈到的公共责任、社会责任或司法制度的责任,由于这一责任往往被要求与国家、政府等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因此,本文暂且称之为律师的“国家责任”。
我国律师在1997年《律师法》实施以后,就已经去“公”为“私”,不再是国家工作人员,而是一个相对自由的法律职业者,按照法律规定,律师需要勤勉、尽职地为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为其保守秘密,实现党派性的忠诚。律师也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执业者,才能得到委托人的信任,律师职业方有生存的根基。现实中,我国还要求律师承担一定的“国家责任”,要求律师具有大局意识。然而,委托人利益和“大局意识”之间很多时候并非一致,这就使得律师在两种责任面前陷入了两难境地,陷入一种特殊的伦理困境,本文称之为忠诚困境。对当事人利益的积极维护,在有些时候会被批评为“立场”有问题;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却有可能违背职业使命与职业精神。
在现实中,我国律师还要接受来自各个管理部门的制约,传统管理思维依旧在起作用。虽然律师已经不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但是主流的意识形态却仍然以公职人员政治正确的标准来要求律师,律师在替当事人维权,制约公权力的时候,很容易遭到否定性的评价。当前这种思维在我国仍有一定的市场,成为我国律师职业所面临的第二大伦理困境。
(三)公共责任与商业化之间的认同困境
公共服务是律师职业伦理中的重要方面,在现代社会,律师职业越来越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和功能,公众对律师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在增加。然而,基于律师的商业属性,随着法律服务市场的发展,商业化也在不断侵蚀着律师职业,使其有偏离公共服务的趋向。商业化给律师职业精神所带来的冲击和负面影响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难题,对于我国律师来说,概莫能外。中国律师在恢复不久就卷入了全球律师商业化的浪潮。本文在做调查时,针对律师职业的认同等问题设计了相应的问卷。在问到是否认同“律师和商人差不多,律师业就是一种商业”这样的观点时,填写问卷的171名律师中,有36人选择了“认同,其实就是这样”,另有80人选择“不完全认同,商业性只是律师的一种属性”,也就是说超过67%的人对其持不同程度的认可。
作为一个专门“职业”,具备公共性和公共服务的精神,是其一个必要特征。律师提供的是法律服务,一方面关系当事人的财产权利、人身权利甚至是生死问题,另一方面关系国家法律的有效实施和社会正义的实现,所以公共性是应有之意。美国律师基金会研究顾问雷蒙德在其所著的《律师、公众和职业责任》一书中也认为:“法律实务是一项公众事业。”[10]作为律师,也应当把公共服务作为一个重要的执业理念和信条,而不单单是当事人雇佣的“枪”。也只有如此,律师才会赢得更多的尊重,并同时维护普通大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与对社会正义的期待。律师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责任,可以称之为律师的公共责任,它是律师所承担的众多责任中的重要方面。
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律师商业性的一面却迅速放大。有一些律师在执业中以“金钱至上”为原则,专挑案件标的额高的“金钱案”,甚至与司法人员建立不正当的关系,为个人私利大量办理“关系案”,丧失了必备的道德良知,没有履行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使命。但是,如果深究律师商业化过度发展的原因,不难发现主要源于律师职业自身的教育和职业发展的环境,律师职业缺乏一个更加开放、多样的发展空间,除了商业化,似乎没有更好的方向。刑事辩护难、律师维权难等现象长期困扰中国律师,作为一个体制外的法律职业人员,也几乎没有进入体制内的可能性。所以说,商业化对当前中国的律师来说是一个现实的必然选择。由于中国律师体制外的定位以及有偿服务,中国律师更多地被认为或自认为就是与商人类似的职业,公共服务的意识和宗旨不明确。加上现实中律师向体制内转入的困难,更淡化了律师公共性的一面,促使律师走向商业化。过度商业化导致律师的公信力下降,有人曾针对律师的公信力做过一系列调查:谈到群众对律师业的认识时,15.3%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律师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认为律师是专门帮助别人打官司的占35.3%,说律师是专门为“坏人”和有钱人服务的竟然占到46.5%;在谈到判断律师好坏的标准时,有61.5%的人选择了职业道德和执业素养,看来公众最看重的还是律师的职业伦理和专业素质;在谈到对当前律师的评价时,有46.8%的人选择了“一般”,但是有高达39.6%的人选择了“较差”,从这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公众对律师的信任度和认可度相当低[11]。
但是,由于律师在中国社会的特殊地位,缺乏进入体制内的管道,不选择商业化,律师又能何为呢?这可以说是当前中国律师面临的一个突出的伦理困境,本文称之为认同困境。
三、律师职业伦理冲突之消解
律师职业由于存在着前文所提到的诸多内在冲突,所以其职业伦理的冲突似乎不可能得到消解。即便如此,各国律师协会仍然通过各种努力规范律师行为,加强律师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引导,以期改善律师的社会形象和社会评价。这些努力也是解决我国当前较为突出的律师伦理问题之重要借鉴。
(一)律师职业伦理消解的域外经验
1.强调律师的公共性与公共责任
美国律师协会在《律师职业行为示范规则》的前言中多达10次提到了律师的公共性,并把律师定位为具有为公共服务理想的公民。大陆法系国家也同样强调了律师的公共性。欧洲大陆的传统律师模式本来就不是为商业而是为行使公共职能的政府服务的。大量的、优秀的法律毕业生进入政府文官和司法系统服务,剩下的人则从事私人执业的工作。律师被看作是一种长袍贵族,他们具有独立的尊严地位,他们给予无知识的人以法律劝告,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作为一种公共捐赠[12]。在这方面,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意见书即认为,律师作为“可依赖的伸张正义者”,无论在法庭内外,都是国民“可靠的权利保护者”,因此,他们应该具有超出一般的业务活动,在“公共性空间”实现正义这样一种社会责任感。其具体内容和实践方式有多种多样,如义务法律咨询、为国民提供法律服务、从事公务、参与培养接班人的工作等,以此为社会作出贡献。日本律师联合会明确提出:律师制度是国家司法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个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基本人权、实现社会正义的社会公益性的崇高职业[13]。
比如美国律师协会《律师职业行为示范规则》第6·1条就规定*美国律师协会是美国律师的全国性自愿专业协会,对法学院进行认证,为执业律师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开办课程协助律师和法官工作,并倡议为公众完善法律体系。为使最贫困的人们获得法律服务,美国律协于1983年制订了第6·1条行为规范,该项行为规范于1993年进一步细化,专门针对需要法律服务的低收入贫困人士。:
每位律师都应对无力支付的人们提供法律服务。律师每年应至少提供50个小时的无偿公益服务。为履行这一责任,律师应当:
(a)无偿提供50个小时的法律服务,或不指望得到报酬,将绝大部分时间应用于帮助:(1)收入有限的人或(2)慈善、宗教、公民、小区、政府和教育组织办案,其主要目的在于满足收入有限的人的需求;以及
(b)通过以下方式提供任何其他服务:(1)以免费或大幅削减服务费的方式提供服务,服务对象是谋求获得或保护民权、公民自由或公共权利的个人、团体或组织,或者为弘扬其组织宗旨的慈善、宗教、公民、小区、政府和教育组织,支付标准的律师费将严重消耗该组织的经济资源或显得不恰当;(2)以大幅削减服务费的方式向收入有限的人提供法律服务;或(3)参与完善法律、法治体系或法律职业的活动。此外,对于向收入有限的人提供法律服务的组织,律师应该自愿提供财务支持。
强调律师服务为公共服务,目的是将律师服务视为一种产品或服务,将当事人视为消费主体;将律师服务视为公共服务,实际上蕴含了“律师服务不能侵害最基本的公共利益来为当事人谋求利益”这样一种深层理念。希望通过对律师公共性和公共责任的强调,有助于纠正律师单纯的商业化倾向,纠正人们对律师的片面认识,并最终有助于律师认同困境的消解。
2.通过职业伦理规范来约束律师执业行为
由于律师职业经常要面临前文所述的众多伦理困境,也极易为个人私利而损害当事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所以有必要制定职业伦理规范,维护整个行业利益,消解伦理困境。美国在制定律师职业伦理规范方面具有代表性,下文就以美国为例来介绍律师协会职业伦理规范在约束执业行为方面的努力。
1887年,美国阿拉巴马州律师协会制定了第一个州律师行为守则——《阿拉巴马州伦理守则(alabama code of ethics)》,该规则后来成为许多州律师伦理规范的模范,并且为1908年美国律师协会制定《职业伦理准则》奠定了基础。美国律师协会(以下简称ABA)于1908年在纽约州萨拉托加(saratoga)成立。在其后的一百多年间,作为美国律师界的代言人和最重要的自治组织,ABA也在不断根据历史的发展而逐步制定与完善更为详细的法律职业伦理规范。包括1908年的《职业伦理准则》在内,它总共制定了三部律师伦理规范,即1908年的《职业伦理准则》、1969年的《职业责任示范守则》和1983年的《职业行为示范规则》。
2002年ABA依据“伦理2000委员会(Ethics2000)”对该示范规则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全面修改,试图为美国各州的律师职业伦理提供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标准[14]。截至2002年8月,共有45个州(包括哥伦比亚特区)采用了《职业行为示范规则》。《职业行为示范规则》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规制律师行为的:
一是规范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为了规范委托人与律师的关系,职业行为准则一般从律师的能力、代理的范围、律师的收费、保密义务、利益冲突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规定。
二是制定律师在诉辩中的行为规则。例如提出有价值的主张、加快诉讼的规则。规定为了实现委托人的最大利益,作为辩护者的律师有责任诉诸法律程序,但是也有责任不滥用法律程序。对法庭的坦诚,保证法庭审判的公开、公正等行为规则。
三是制定律师同委托人以外的人交往的行为规则。主要从律师的真实义务、律师对第三人的尊重等几个方面对律师职业行为进行规制。
四是规定了对律师的公共责任与公共义务。要求律师提供公益性的法律服务,同时也对律师在法律服务信息方面做了详细的要求。例如要求律师每年应当提供不少于50个小时的公益性法律服务,不管其职业声望或者工作负担如何。律师不得就其本人或其服务进行虚假或误导性的信息交流[15]。
以上主要介绍了其他国家规制律师的部分经验,公共责任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消除人们对律师商业化的担忧,也从另一个方面提醒律师还应有更高的追求。具体的职业伦理规范则是对律师执业的直接约束,它不仅划定了律师职业伦理的边界,同时也越来越法律化,成为规范律师、惩戒律师的重要依据。
(二)中国律师伦理困境消解之探索
中国律师虽然是舶来品,但是短短几十年的发展,不仅出现了与西方国家律师职业同样的伦理困境,还有前文谈到的一些特殊困境。因此,中国律师伦理困境的消解既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也必须有自己的探索。
中国律师的定位虽然经历了由“公”到“私”的转变,但是在我国当前的体制下,律师的社会责任或者国家责任一直是有较高要求的,因此,在律师公共责任方面,我国似乎没有西方国家存在的诸多问题。在律师职业行为规范的制定方面,我国也一直有较多的强调,从形式上看也无需做过多的要求。那么如何消解我国律师行业当前的自治困境、忠诚困境和认同困境呢?本文认为,首先应当分析这些困境的原因,然后再做相应的对策。
中国律师的伦理困境有以下诸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律师定位的偏差,法律服务者的定位不仅让律师游离于体制之外,无法与法官和检察官等法律职业实现平等的交涉,而且使律师不得不放弃政治家理想,而专注于经济利益的追求;二是律师制度本身的缺损,当前律师养成制度存在的不足难以保证中国律师具有高度的职业精神;三是职业伦理教育的缺失,让很多涉嫌违规的律师有些“冤枉”,因为有时候律师并非有意违规,而的确对之知之甚少。所以,在研究如何消解律师伦理困境时,也就应当从这几个方面来入手。
1.重新定位中国律师职业
一个法治国家如果没有律师的积极参与和发挥作用,是不可想象的;有了律师,如没有明确的角色定位和相应的权限,律师也就不能履行其职责,发挥其应有作用。中国律师退出公职身份以后,服务性和商业性被过多的强调,导致体制之外的中国律师出现了明显的商业化倾向,基本的政治参与和公共服务意识缺乏,负面评价增加,陷入伦理困境之中。所以,在研究中国律师如何走出伦理困境之时,首先应该反思当前我国律师的定位,有必要通过重新定位的方式,来解决律师职业发展的种种问题。
重新定位中国律师,并非要全盘否定原来的律师定位,笔者主张的重新定位,只是对其进行补充和完善。原来的律师定位在把律师从公职人员变为法律服务者的同时,缺少了对律师职业应有的公共性的考虑,这样给律师执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所以有必要重新定位。
(1)强调律师的公共性与公共责任
虽然律师在我国当前的环境下,已经被赋予较多的“国家责任”,似乎再无需强调对社会责任与公共责任了,但是,通过研究人们会发现,当前我们国家对律师所要求的虽有社会责任的一面,但是并没有明确其具体的范围,因而显得空洞和泛化,不具有可操作性。根据前文所谈日本学者对公共责任的界定,我国对律师公共性的强调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要求:
一是要求律师在接受委托之时,不应仅仅考虑案件的标的额和自己的收入,也应考虑到维护公民权利和社会正义的职业使命,确保每一个需要律师帮助的人都能够得到高质量的法律服务。现实中,有很多律师往往出于经济收入的考虑,给自己划定一个受案的标准,对于可期待收入较小的案件则不予接受。其实,有些案件虽然标的额较小,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却非同小可,牵涉当事人正当权利的实现。如果所有的律师都如此设限,那么势必导致这部分法律需求得不到满足,律师的公共性也无法得到彰显。
二是要求律师尽可能地参加社会公益服务。基于法律服务的公共物品属性,在很多国家中,除了法律援助这种直接由政府负担的、免费的法律服务项目以外,律师无偿公益服务也是一种模式。律师无偿公益服务(Pro Bono Publico,拉丁语字面意思是“为了公益”),是指律师提供的法律顾问、代理和调研服务,其服务对象是无法支付律师服务费且公共财政资金不足以满足需求的个人和非盈利性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和小区的公益倡导)。在当前律师商业趋向较为突出的情况下,对律师公益服务的强调十分必要。通过公益法律服务彰显的公共性,有利于改善其过度商业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维系人们对法律、对律师的信赖和尊重。
三是促进律师在政策形成中的积极贡献。律师不仅精通法律,而且了解百姓疾苦与社会需求,并对法律的适用及其中的问题最为了解。因此,律师应当在国家立法和政策制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也是日本学者森际康友着重强调的律师公共责任的一个方面。虽然,我国律师只是体制之外的法律服务者,但仍应当在以后的法律和社会政策的制定上积极献言献策,做出自己的贡献。2011年《民事诉讼法》修订之时,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就曾提交过一个律师建议稿,虽然并未被实际采纳,但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表明中国律师已经开始在履行这方面的公共责任。
(2)明确律师执业的独立性
作为一种职业,独立性是其应有之义,独立性也是法律职业的基本价值之一。世界许多国家在《律师法》或者相关的律师行为守则中都特别强调了律师的独立性。德国、英格兰、美国、加拿大与日本等国在其《律师法》或《职业行为准则》里都明确规定了律师的“职业独立”[16]。我国《律师法》没有明确规定律师的独立地位,仅仅把律师规定为“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这给我国律师执业带来了较大的困难,一方面律师的执业受到司法行政机关的管理和制约,另一方面,律师又不得不照顾到法庭的感受或者说需要“取悦于”法庭,难以摆脱其他方面的影响。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就是我国律师还必须保持政治正确,律师执业需要具备大局意识,对政府和组织负责。这样的要求,势必损害律师的独立性,使律师陷入明显的忠诚困境。虽然,我国对律师的政治要求也并非绝对一无是处,但其实并无必要。因为律师依照法律规定行使职业权利,维护民权、制衡公权,有利于社会正义的实现,并最终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与执政党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我国党和政府应当改变传统思维方式,在未来的立法中明确规定律师的独立地位,确保律师依法独立执业。
2.完善律师养成制度
顾名思义,律师养成制度指的就是关于律师教育、培养、塑造等方面的制度。一套完善的养成制度目标不应仅仅是训练律师的职业技能,也应该包括培养律师的职业精神。我国也应当在律师准入标准、资格考试制度以及实习制度等方面进行重新设计,培养和选拔具有较高专业技能和职业认同的律师队伍,这对于解决我国律师当前存在的职业认同困境也会有重要意义。
(1)提高职业准入条件
我国当前对报考人员的条件限制是: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并具有法律专业知识。我国之所以实行较低的限制,是因为在律师制度恢复之初,律师数量不能满足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对律师的需求,所以允许非专业的人来报考,目的是迅速扩大律师队伍。但是在法学高等教育已经比较普及的今天,我国从业律师人数已经较为庞大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律师服务的质量,应该重新设计律师的准入门坎,选拔精英律师人才。较高的准入门坎有利于克服以前准入标准低所带来的执业律师水平层次不齐、鱼龙混杂,进而导致律师职业整体形象受损情况的发生,因此,严格限制非法学专业人士直接报考司法考试非常必要。另外,需要对对申请律师资格的人进行品行考查。将品行良好作为一项考察标准是为确保律师恪守职业道德而设定的一道门坎。设立一套完整的品行考察制度是《律师法》配套的法规规章亟须考虑的环节,笔者认为,立法修改应进一步明确规定申请律师执业者必须达到的职业道德水平,以防止那些有品行不良、严重违法行为记录的人员进入律师队伍。
总之,我国在法律职业的准入限制上,应该采取严格的标准,把好入口关。诚然,准入方面的严标准并非完全能够保障未来执业律师良好的业务和道德水平,但是过宽的标准则必然会给未来的职业群体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2)调整考试与选拔方案
当前我国律师执业中已经呈现竞争加剧甚至恶意竞争的局面,这也是带来律师伦理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律师职业具有商业性因素,竞争不可避免,但是过度竞争极易带来行为失范问题。面对律师职业的竞争,一方面要规范律师执业行为,另一方面也应对从业律师数量进行限制,防止由于法律服务市场上不合理的供求关系而导致过度的竞争。而要做到对供求关系的调整则必须从考试与选拔制度入手。
首先,应当加强律师执业之前的操作能力与伦理判断之训练。一方面培养其职业技能,另一方面使其伦理判断成为习惯。要达到这样的目标,非经过较长时期的职业训练不能完成。德国、法国和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都对律师资格的获得设计了多次考试和为期几年的训练,也许正是基于以上培养合格律师的考虑。美国虽然没有规定司法考试后一定阶段的训练,但是由于其大学法学教育即是诊所式教育的培养方式,法学院学生在日常的专业学习中就锻炼了实践的技能和伦理推断的能力。而我国只规定一次司法考试合格即可从业,没有再附加较长时间的研修训练,无疑不利于律师实践能力与伦理精神的培养。因此,我国亦应当借鉴其他国家在律师养成方面的重要经验,重新设计律师资格考试制度。我国的司法考试改革可以这样来设计:即实行两次司法考试,第一次考试以笔试为主,主要考察法律专业知识,第二次考试则主要测试申请者的实际操作技能和职业伦理水平,以面试和申论为主要考察方式。而在第二次考试之前应当有两年的研修期,对其进行专门的技能和伦理培训。
与这种构想相适应,我国的法律人培养也需要做一定调整,即应当有专门培训机构来负责技能和伦理的训练。在日本,是由司法研修所来承担此项重任。因此,我国也可以考虑设计类似的机构,通过提高标准来选拔精英,并控制律师人数。以此来保证律师的执业利益,防止恶意竞争。
3.加强法学教育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
在前述关于我国律师职业伦理困境原因的分析中,我们发现职业伦理教育的缺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有些通过技术性考试获取资格的律师其实对于律师的属性与使命并不熟悉,认为其仅仅是一个赚钱的行业,由此可见职业伦理教育亟待加强。我国现行的律师行业教育整顿是针对执业律师的,属于继续教育的范畴。由于律师业务繁忙,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参加教育和培训,并且一经形成的惯性思维和执业习惯也不会因为一个短期的教育整顿而轻易改变,因此,以提高律师职业伦理为目的的继续教育的实际效果可能并不乐观。应当重视在律师养成阶段的职业伦理教育,具体来说,就是重视和加强对法科学生的职业伦理教育。如何做好法科学生的职业伦理教育呢?在我国当前情况下,需要思考两个问题:第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目的是什么。第二,如何提高职业伦理教学的实效性。
(1)明确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目的。作为一门关于法律人如何执业的学问,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目标和方式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国内外都有学人对此有专门研究。美国学者伊恩·约翰斯顿(Ian Johnstone)和玛丽帕特里夏·特洛伊特哈特(M.P.Treuthardt)曾经指出职业伦理教育的目的至少有三个:其一,它是一种教学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为学生介绍未来做一个法律人所要面对的伦理困境,让学生意识到这种职业角色困境有助于他们对在特定情形下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其二,通过职业伦理的训练,让学生对法律职业及其在社会中的角色有进一步的认识;其三,刺激学生积极从事审慎判断的能力[17]。罗德(DeborahL.Rhode)教授认为,职业伦理教育的目标首先是要建立起对影响和决定律师行为法定标准和调整方法的理解,与之相关的目标就是帮助学生根据这些标准和主要的道德框架去认识和分析众多的伦理问题。未来的执业人员需要知道伦理的底线在哪里,与此同时,他们也要考虑这条线应该设在何处,该如何面对这些职业规则并非很明确,为人们判断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帮助学生建立起审慎的判断能力(capacity for reflective judgment)应该是职业伦理教育的主要目标。总之,职业伦理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鼓励未来的律师更多地思考他们想要的生活方式,想要从事的职业以及二者如何能够对一个公正的社会理想有所贡献”[18]。我国则有学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目的主要在于培养学生的伦理问题意识与伦理推理、伦理选择的能力[19]。
从上述国内外学者对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目的的研究可知,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不仅与现代法治社会中的法律职业必备的质量密切相关,还是培养法律职业必备的基本能力的重要途径。因此,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应当是法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合格的现代法律人。
(2)科学设计职业伦理课程教学。基于职业伦理课程的特殊性,如何设计该课程就需要认真对待。职业伦理课程的设计需要考虑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仅靠一门课程是否能完成;二是专门的职业伦理课程的教学方式。
对于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我国及国外都有学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仅靠一门课是不够的,因为职业伦理要解决的并非是简单的思想政治问题,而是和律师执业实践有密切关系的,所以一个有效的职业责任的教育不仅要关注这个学科本身,还要关注其在制度上的关联。国外有学者认为,“理想的情况下,伦理教育这个主题应该是贯穿整个核心课程,并且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予集中关注的一个集合体。因此,伦理教育应该渗透在诸如税法、商法、家庭法、刑法等一些实体法领域”[20]。我国三十多年来的法学教育实践过于注重对专业理论知识与技能的教学,而忽视对法科学生伦理思辨能力与伦理选择能力的培养,没有开设专门的职业伦理课程,更谈不上在部门法中贯穿法律伦理的教学。
第二个层面的问题也迫切需要解决。因为职业伦理教育方式方法直接关系该课程教学的效果与成败。美国法律伦理教育专家罗德教授曾对职业伦理教育的问题、挑战和对策展开了专门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改进的策略,或许对我国未来的法律伦理教育有所帮助。他认为,有三点需要注意:一是把职业责任同诊所式课程或者校外实习阶段联系起来;二是书本以外的其他的材料也是伦理教学的有用的辅助,比如电影、电视片段等等能为课堂讨论提供有效的材料;三是一些业界精英的个人历史和传记也同样能够作为补充,有助于丰富对职业角色的理解。比如约翰亚当斯、林肯,霍姆斯、米歇尔等法律人的故事与传记能为道德判断提供积极的典范。另外,来自商业、医学、新闻、工程等其他职业伦理的专家和材料也能为法科学生提供审视自己职业的窗口,进而去思考诸如信任关系、利益冲突以及对第三方的责任等等,这也是一个学习职业伦理的好方法[21]。
我国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虽然刚起步不久,但是也有学校和教师开始在这一方面进行探索。鉴于我国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不高,律师也有较多的不当执业行为和负面评价,我国学界和实务界也应该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国外法律伦理的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职业伦理教育模式和方法。加强对法科学生和执业律师的伦理教育,让受教育者能够深入洞察法律背后的伦理结构,建立起稳定、宽厚的职业伦理信仰,避免法律知识成为危害社会的技能[19],这样才有利于中国律师走出当前的伦理困境。
四、结语
律师职业的伦理冲突是一个天然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消解。然而,为了律师行业的健康发展,各国仍然不遗余力,通过制度的变革、法律意识的普及以及对律师职业的教育引导等方面的工作,希望有助于缓解律师的伦理困境。当前,我国律师除了具有普遍性的伦理冲突之外,还有三大特殊困境,即自治困境、忠诚困境与认同困境。这些伦理困境的出现,除了制度上的原因之外,还有我国律师行业自身的因素。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促进律师业的稳步发展,我国应当认真对待当前的律师伦理困境,借鉴其他国家在律师管理上的经验,在律师的重新定位、职业养成与训练、职业准入制度等方面进行调整,同时加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
[1]宋远升.刑辩律师职业伦理冲突及解决机制[J].山东社会科学,2015,(4).
[2]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98.
[3]司莉.律师职业属性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129.
[4]Gordon,Robert W.Corporate Law Practice as a Public Calling[J].Maryland Law Review ,1990,(2).
[5][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M].王军,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10-220.
[6][美]哈罗德·伯尔曼.美国法律讲话[M].陈若桓,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26.
[7]孙笑侠,等.法律人之治——法律职业的中国思考[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277-278.
[8][日]森际康友.司法伦理[M].于晓琪,沈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50.
[9]卫磊.法律行动的实践逻辑[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79.
[10][美]雷蒙德,等.律师、公众和职业责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53.
[11]牛烨.论我国律师的社会公信力[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10.
[12]朱景文.法律职业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一种比较法的观点[A].张文显,等.司法改革报告:法律职业共同体研究[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52.
[13]裘索.WTO体制下日本律师业的变化[J].政治与法律,2000,(3).
[14]王进喜.美国律师协会职业行为示范规则(2004)[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2.
[15][16]北京律师协会.境外律师行业规范汇编[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163-260,538,60,236,371.
[17]Ian Johnstone ,Mary Patricia Treuthart.Doing the Right Thing: An Overview of Teaching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J].JournalofLegalEduc,1991,(1)
[18][20][21]Deborah L.Rhode.Teaching Legal Ethics[J].SaintLouisUniversityLawJournal,2007,(4)
[19]齐延平.论现代法学教育中的法律伦理教育[J].法律科学,2002,(5).
责任编辑:何学斌
On the Conflict and Resolution of the Lawyer Profession Ethics
Suo Zhanchao
(LawSchool,HenanUniversity,KaifengHenan475001 )
Lawyers often confront conflicts of procedural justice and substantive justice,conflicts of multiple responsibilities and conflict between the professionalism and commercialism,those are rooted in its own internal conflicts of public and commercial and the division of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public ethics.Because of the arrangement of our system,Chinese lawyers also faced the following three special ethics dilemmas:the autonomy,loyalty and identification.In addition to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s that succeeded in other countries,emphasis on lawyers public liability and formulate model rules of behavior,our country should adjust these systems:relocation of the lawyer profession,cultivation and training of profession and etc.at the same time,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 about legal ethics,so as to resolve the professional ethics dilemma,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wyer profession healthily.
lawyer; professional ethics; lawyer’s liability
2016-11-29 基金项目:本文为河南省教育厅2014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律师职业伦理:困境及其消解”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2014-QN-007)。
索站超,男,河南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诉讼法学、司法制度。
D926.5
A
2095-3275(2017)03-006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