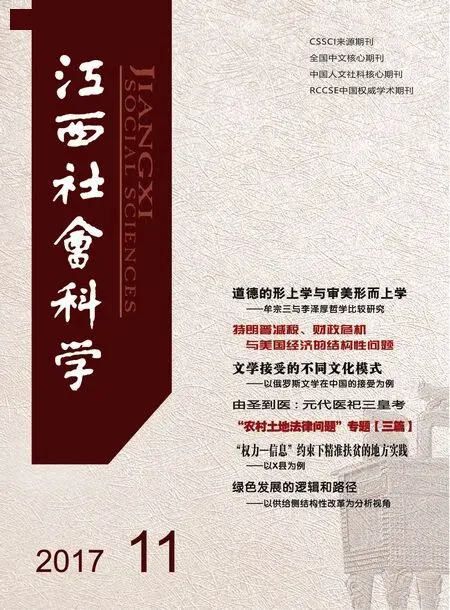政治生态与传记书写:明中后期史书对王越形象塑造的演变
■蔡果利
政治生态与传记书写:明中后期史书对王越形象塑造的演变
■蔡果利
王越;明中后期;传记书写;政治生态
传记是一种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文体。与记载一朝或几朝兴衰的国家史不同,中国古代传记可视为个人史的承载形式。古代人物传记虽有单独成篇者,却大多依附于各类史书中,如纪传体史书、实录体史书、方志、笔记小说等。传统传记的分类形式不一而足,如吴讷把传记分为七种:“一曰史传,二曰私传,三曰家传,四曰自传,五曰托传,六曰寓传,七曰假传。”[1](卷四百八十三,P63)传记的书写和传主形象的塑造不仅受制于不同的文本类型,更是当时政治局势与社会环境的一种反映。同一传主在不同文本中形象的变化,亦与政治生态①之变化密切相关。本文拟以成化、弘治时期名将王越为例,考察明中后期②政治问题的凸显与演变,分析在明王朝日渐式微的窘境下,史学家是如何通过对王越传记③的书写来展现其政治诉求的,进而探寻政治生态变化对传记书写的影响。
王越(1426—1498),字世昌,直隶浚县(今河南浚县)人,景泰二年(1451)进士,初为御史,成化中累官至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封威宁伯,成化十九年(1483)因罪除名削爵,弘治七年(1494)复左都御史,弘治十年加太子太保,总制三边,后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弘治十一年卒。王越为明中叶著名将领,其一生征战西北,“三任参赞,两膺总督”[2](P520),屡立军功,事迹详载《明实录》与明代其他官私史书。诸书所载王越传记,选取事件不一,褒贬各有侧重,众史家对王越的态度,亦有矛盾之处。明中后期,北疆形势错综复杂,宦官专权屡次上演,这些都干扰着治史者的神经,进而影响着王越传记书写的走向。
一、从罪臣到名将——成化、弘治两朝国史对王越态度的转变
王越首次入传于《明实录》。明代无官修本朝正史④,故历朝《明实录》地位甚高,明人目之为国史。按《明实录》凡例,文武官三品以上,殁皆书卒,并概见其行实。但《明实录》在为官员作传时,多突破此例。谢贵安概括了实录体史书“编年附传”式体裁的三种处理方式,分别为将传记相机切入传主去世时、朝廷为传主赠官时、传主被贬从此结束政治生命时。[3](P160)成化十九年,王越被安置于安陆州,弘治初放回原籍,《明宪宗实录》修于弘治元年正月,成于弘治四年八月,当时编修官认为王越的政治生命已结束,故在朝廷对其论罪处插入传记。后王越于弘治七年被起用,卒时官至正二品,按正德时所定《明孝宗实录》凡例[4](P8),得以立传,由此便出现了《明实录》中罕见的一人二传现象。然细读两篇传记,发现其对王越之记载多有龉龃之处。简而言之,《明宪宗实录》王越传对王越极尽贬低之辞,而《明孝宗实录》则有褒有贬,并有为之前的立论翻案之嫌。国史对王越形象塑造的前后不一,反映了实录编修官对王越态度的不同,进而体现了弘治、正德时政治生态的微妙变化。
(一)两篇《明实录》王越传之相悖记载
据顾炎武所说:“每一帝崩,修《实录》,则请前一朝之书出之,以相对勘。”[5](卷五《书吴潘二子事》,P114)与《明宪宗实录》相比,《明孝宗实录》对王越的记载,并不是简单的补充生平事迹,而是对其进行大规模改动,造成了王越形象的互歧之处。《明孝宗实录》对《明宪宗实录》所塑王越形象之变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由贪功起衅的有罪之臣到识人善战的常胜统帅。景泰、天顺年间,明朝北部边防日益空虚。阿罗出、孛来、毛里孩诸部相继进入河套地区,使得大同、宣府、甘肃、宁夏、延绥、陕西诸地边防压力大增,“套虏”成为明朝北疆防御的一大忧患。成化三年二月,时任巡抚大同右副都御史的王越受命赞理军务,经略西北。此后,王越多次大举搜套,先后破虏营于红盐池、威宁海子,战功卓越。战事虽均载宪、孝实录王越传记,文字表述与所记重点却截然不同。《明宪宗实录》王越传对红盐池之捷一笔带过,对王越邀功之事大书特书:“(越)心甚怏怏,乃移疾乞还京,寻莅院事。又命提督十二营操练,与汪直选军。每以河套劫营功大,将士赏不酬劳,讼愬不已,奏请所司覆奏升赏之,诏以越首谋成功,特升兵部尚书,仍加俸一级,余职如故。”[6](卷二百四十三,成化十九年八月壬申,P4108-4109)更把威宁海子之捷称为侥幸,认为此役遗祸不浅:“见朱永邀功辽东,升国公,亦欲觊其封爵,乃因延绥小警嗾直,请出师,而已提督军务,侥幸威宁之捷”[6](卷二百四十三,成化十九年八月壬申,P4109),“威宁之役,虏忿恨,报复不已,得中国人肆其惨毒大为边害者数年,皆钺(当作越,笔者按,下同)所致也”[6](卷二百四十三,成化十九年八月壬申,P4110)。《明孝宗实录》王越传对此一一进行修改:“越以河套功大赏轻,言于朝,乞移所加官禄赏将士,上遂升越兵部尚书,进太子太保,支正一品俸。”[4](卷一百四十五,弘治十一年十二月壬辰,P2523)将王越“讼愬不已”之记载删去,认为其升职乃当之无愧。又言宪庙实录对其苛责太过,“河套贺兰之捷,实有功于边,论者概指为开衅生事,亦过矣”[4](卷一百四十五,弘治十一年十二月壬辰,P2525)。并赞他善出奇兵,知人善任,“用兵善出奇方,虏入寇,阳若不闻,伺其得利稍怠,乃伏兵归路邀杀之,故多胜无败。尤善用人,所部将士率以一时谋勇,皆不次拔擢之”[4](卷一百四十五,弘治十一年十二月壬辰,P2524)。
二是由挟势弄权的权阉同党到因势利导的蒙冤之臣。《明宪宗实录》将王越传记附入朝廷对汪直一党立罪处,固然符合实录立传之例,却也是修史者对其认知的反映,王越“罪臣”与“阉党”的形象就此确立。据《明宪宗实录》,王越“封威宁伯,仍兼左都御史。又与永、直等帅师往大同,以黑石厓之捷,进太子太傅,岁加禄米四百石,掌前军都督府事,为五军营总兵,时成化十七年春也。是年,直渐见疏,至秋,命越出宣府击虏,乞班师,不许。明年遂命留镇大同。以清水营之捷,加禄米五十石。又命移镇延绥。至是竟为言论与直俱败”[6](卷二百四十三,成化十九年八月壬申,P4109),其得势与失势均与汪直相关,是成也汪直,败也汪直。不仅如此,编修官于此对王越开列罪名:“于大臣有不悦者,阴嗾台官击去之。”[6](卷二百四十三,成化十九年八月壬申,P4109)暗合了此前诏书所言汪直一党“排摈正直”[6](卷二百四十三,成化十九年八月壬申,P4107)一罪。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明孝宗实录》虽言王越与汪直“相得欢甚”[4](卷一百四十五,弘治十一年十二月壬辰,P2524),却又将之解释为“直有宠于上,所建白必从,越欲借其权以成事,故善事直”[4](卷一百四十五,弘治十一年十二月壬辰,P2524),意为“事直”仅为权宜之计,借权守御边疆才是真正目的。并言王越之败是受人中伤所致,“当路者素忌越才,遂从中下其事”[4](卷一百四十五,弘治十一年十二月壬辰,P2524)。
三是由“一败涂地”[6](卷二百四十三,成化十九年八月壬申,P4110)的讽刺性评语到“求如越比,盖亦难其人焉”[4](卷一百四十五,弘治十一年十二月壬辰,P2525)的盖棺定论。除刻意贬低王越所立功勋、对其安插罪名外,《明宪宗实录》犹记载了两个故事,进一步贬低其形象。据《明宪宗实录》王越传,王越获罪后,“上遣锦衣卫指挥陈玺赍敕往谕之,越闻丧魄,几欲自尽,及闻敕有从轻之言,始变色”[6](卷二百四十三,成化十九年八月壬申,P4109),俨然一个贪生怕死之徒,大将风范全无。此事不见其时他书,《明孝宗实录》王越传亦不载,似为杜撰或刻意诋毁之辞。《明宪宗实录》复载其廷试时试卷为风扬去一事:“钺廷试时疾风卷其试卷,扬空而去,所司以闻,命更卷与之,至是一败涂地,人皆谓先兆云。”[6](卷二百四十三,成化十九年八月壬申,P4110)此事有迹可循,最早见于叶盛《水东日记》[7](卷二十,P124),朝鲜《李朝实录》亦见相关记载,“到记儒生殿讲时,书九为执册承旨,望单为风所卷,直入云际,如皇朝威宁伯王越廷对故事”[8](卷三十七,正祖十七年二月甲戌),当为事实无疑。但《明宪宗实录》编修官却将之视为王越获罪的先兆,实属无稽之谈,其对王越“一败涂地”的定论,亦有失公允。相较之下,《明孝宗实录》将以上捕风捉影之语删去,作出了“求如越比,盖亦难其人焉”[4](卷一百四十五,弘治十一年十二月壬辰,P2525)的评论。这既是对王越的盖棺定论,也是修史者对忧患之际国无良将的感叹。
(二)国史立论产生变化的原因分析
两部国史对同一人之描写出现如此大的反差,缘于实录编修官对王越认知的不同及变化。而认知的不同及变化又受弘治到正德初政治生态变化的影响。弘治元年正月,明孝宗下令编修宪庙实录,任命刘吉、徐溥、刘健三人为总裁官[4](卷十,弘治元年正月戊辰,P206),且以刘吉为首。刘吉为人深沉阴险,忌妒贤能,成化时既与王越等人不和,而史官多秉承其意,数次对王越进行笔伐。《明宪宗实录》曾记一事:“都御史王越遇珝与吉于早朝。越曰:‘汪直行事尽公道,如黄赐专权纳赂,非直谁能去之?且商、万二公在任久,是非多,故有所忌惮。二先生入阁几日,况直又扶持,何为亦论列乎?’珝默然,吉曰:‘不然,某等言事为朝廷,非为身谋也。设使汪直行事皆公道,朝廷置公卿大夫欲何为?天下后世谓此为何等时邪?’越无以应,遂与吉疏。”[6](卷一百六十六,成化十三年五月丙子,P3010)王世贞对此进行考证后认为,此处是刘吉的刻意曲笔,力折王越的应为刘珝[9](卷二十五《史乘考误六》,P447)。根据文献记载,该事当时仅有王越、刘珝、刘吉三人知情,《明宪宗实录》修纂时,王越、刘珝均已被排挤出朝,故录此事者当为刘吉。为了打击政敌、粉饰自身形象,刘吉不惜篡改历史。由此可见,成化末至弘治初的权力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明宪宗实录·王越传》书写的真实性。
《明孝宗实录》始修于正德元年(1506)正月,初以刘健为第一总裁,后易为李东阳,而实际秉笔于焦芳。彼时王越已物故,与几人并无嫌隙,李东阳亦曾为王越撰写过墓志铭[10](卷八十三,P877-879)。而
王越又在弘治时得到了孝宗皇帝重用,据史料记载,王越起复后,多次遭科道弹劾,但孝宗不为所动,并赋予其总制甘肃、宁夏、延绥三边之权。孝宗之所以重用王越,当与北部边疆形势的持续恶化紧密相关。成化年间,蒙古各部相继进入河套地区,“套虏”成为明中期的主要边患。弘治时,小王子崛起,不断进入内地劫掠。在这种情况下,孝宗果断起用王越,“敕加致仕左都御史王越太子太保,总制甘凉各路边务,兼巡抚地方......先是虏寇肃州之沙窝堡,珉等不能御。兵部乃议设总制官,初拟上三人,再拟四人,皆不用,后乃拟越,遂用之”[4](卷一百三十,弘治十年十月乙酉,P2305)。事实上,王越也是当时唯一能担此重任的将领,成、弘年间几次成功的捣巢作战,均为王越统率。其卒后,朝廷再无能抵御蒙古的将领,如弘治十四年,“虏入陕西平凉境,杀虏纳粮民七人,掠其布,并牛二百余以去。又攻烟墩山等处,杀掠人畜,官军御之,得所遗骆驼二,马四十四,牛四十,羊八百余”[4](卷一百七十六,弘治十四年七月己巳,P3235),朱晖、史琳帅兵御敌,先后斩虏只十二级,“闻议者耻之”[4](卷一百七十八,弘治十四年八月辛亥,P3272)。到正德初年,北部边患持续加重,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国无良将的局面困扰着统治者,对王越的评价也在发生变化,其“挟权启衅”的形象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知人善任、懂得随机应变的将领。《明孝宗实录》编修官在写作王越小传时,在参考李东阳撰墓志铭的基础上,对王越作出了与《明宪宗实录》截然不同的描写与评价。
二、弘治以后诸史书对王越个人史之演绎
弘治以后,史学日益兴盛,地方史籍和笔记体文献的编撰日渐增多,诸史书中所载王越的形象也在不断地演绎。正德、嘉靖年间众史书对王越形象的塑造基本继承了《明孝宗实录》王越传的论调,对其既不过分贬低,也不过于褒扬。地方志方面,分别刊行于嘉靖元年(1522)与十二年的《湖广图经志书》[11](卷十《名宦》,P940)《山东通志》[12](卷二十五《名宦上》,P246)均对王越着墨不多,仅对其流寓安陆及任职山东按察使之事一笔带过。较详细记载王越生平的私家史有嘉靖年间成书的郑晓的《吾学编》[13](卷二十四,P467),郑晓参考了李东阳对王越的评价,详细记载了其战绩及迁转经历,对王越持基本肯定态度。又嘉靖十二年,崔铣应王越次子王时之请,为王越作神道碑铭。与李东阳所撰墓志铭不同,崔铣首次明确了成化时王越获罪的原因:“内阁万学士忌公功名太盛,台臣承其意思,论公生事夷狄,作诗怨望。罢公为民,谪居安陆。”[14](卷七,P550)并言:“铣少闻先君子称公有文武大略,后入翰林,多以任术毁公者。正德初,修皇考实录,得见国史,考公守边身伟。夫忌功娼才,心惨于戈戟。”[14](卷七,P549)指出王越对国家边疆功劳甚伟,弘治时翰林对他的贬低实为出于忌妒之举。崔铣的这番论述,被后来的史书多次引用,影响深远。王世贞在《史乘考误》中详谈了“国史”“野史”“家史”三者的阙漏与优长之处:“虽然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讃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9](卷二十《史乘考误一》,P361)受《明实录》凡例所影响,《明实录》所载王越传记集中于叙述王越之任官经历,故篇幅不长,叙事也较为简洁。与之相比,私家史所载王越传记对王越的刻画更为生动,诸多故事增入,并不断演绎,这固然与修史者所处立场的不同有关,亦受史书撰写环境变化的影响。总之,正德特别是嘉靖以后,众传记对王越的书写更为形象具体,并附入了几个传说及逸事。史家们对王越的描写与评价亦出现分化,一方面,对其军事功绩和军事才能大加赞扬,另一方面,对其依附汪直之事进行批判。
(一)明中后期边疆形势的恶化与“军事奇才”形象的深入
与实录相比,王世贞笔下之王越更具有传奇色彩。《弇州续稿》所收王越传,篇幅多达2434字,尤详于对其军事才能的描写。如将王越与明前期文将进行对比,“前是文臣视师者,多从大军后,出号令、行赏罚而已,至越而始多选骁勇跳荡武骑为腹心,将而与敌搏,始有战矣”[15](卷八十八《史传》,P271),认为从王越开始,文臣视师者才发挥了将领的作用;记载战争场面也更为详细,并增入了王越在行军时的逸事,赞扬其气度豪迈、仗义恤下,如记赠妓于千户一事:“行过陕西,秦王宴之,奏伎,越语王:‘下官之为王吠犬久,宁有以相酬否?’因尽乞其伎女归。一日大雪,方坐地罏,使四伎抱琵琶捧觞侍,而一千户诇敌还。即召入,与谈敌事,甚晳,大喜曰:‘寒矣。’手金巵饮之。复谈,则益喜,命弦琵琶而侑酒,即并金巵予之。已又谈,则又喜,指其中最姝丽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户所至为效死力,积功至指挥。”[15](卷八十八《史传》,P273-274)又记王越拜老卒一事,赞其知人善任、虚心纳谏:“而其夜袭敌帐也,将至而风暴起,尘翳目,众惑欲归。一老卒前曰:‘天赞我也!去而风使敌不觉,归而卒遇敌入掠者,还而我据上游,皆是风也。’越不觉下马拜,功成,推卒功以为千户。”[15](卷八十八《史传》,P274)将王越刻画得有血有肉,可谓入木三分。《续藏书》[16](卷十三《勋封名臣》,P329-332)《名山藏》《皇明辅世编》《明史窃》[17](卷九十三,P513-515)《西园闻见录》[18](卷七十四,P655-656)等均记录了以上两事。唐鹤征感慨曰:“世之才略气魄,有能万一襄敏者乎?使遇汉武卫、霍,何足道也。史称卫、霍出塞,海内为之虚耗,襄敏不闻繁费。卫、霍部下或迷失道,襄敏所用未必皆名将,所至成功。”[19](卷二,P389)认为王越之将才过于卫青、霍去病,评价不可不谓之高。
明中后期诸私家史对王越军事功绩的大书特书,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修史者对国家边疆问题的关注及担忧。弘治以后,政治腐败,国库空虚,边备废弛,朝无良将。明世宗刚愎自用,数次绝贡,导致边疆形势持续恶化。嘉靖二十九年,鞑靼部首领俺答联合蒙古诸部威逼京师,震惊朝野,此为“庚戌之变”。之后虽在隆庆五年(1571)实现了俺答封贡,但明朝积贫积弱的现实并未改变,严峻的边疆形势仍在激发着史学家们的忧患意识。万历二十年(1592),宁夏副总兵哱拜勾结蒙古诸部,起兵反叛,明神宗派兵平定。平定哱拜叛乱与平定播州杨应龙之叛、抗倭援朝战争,在明史上被称为“万历三大征”,它们耗费了巨量的军饷,加剧了明朝的财政危机。而蒙古诸部持续劫掠的警报尚未解除,努尔哈赤却在建州迅速崛起。万历二十四年,努尔哈赤初征瓦尔喀,大约经过二十年的时间,统一了东海女真的主要部落,并于万历四十四年建立“大金”政权。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袭取抚顺。之后明朝在萨尔浒之战中惨败,被迫对女真从进攻转为防御,明政府陷入了空前的危机当中。面对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史家们忧心忡忡,他们一方面批判当局者的懦弱无能与推诿,一方面寄希望于出现一位杀伐果断、有勇有谋的将领。这时,王越在成、弘时期的战绩被想起,“帅卒慵懦,其冒功费财滋甚,天下乃以追才越”[20](卷六十六《臣林记》,P382),王越的个人史被进一步塑造与丰富,对王越功过的评价也发生了转向。过庭训认为其将才超过了古名将:“其智勇足备,如此虽古名将何以加焉。”[21](卷十《北直隶大名府》,P225)唐鹤征更是对之百般推崇:
虽然世谓其功不掩罪,则过矣。世之小人但有其罪,而无其功,则又何如?彼一时不有陈乎?余惟以王文恪、崔文敏之论为公故并附之。王文恪公曰:“世昌红盐池劫虏取胜,本兵家奇术,议者往往黜其功。”崔文敏公曰:“少闻世昌文武大略,比入翰林,人多谓其任术不足数。及修泰陵实录,得见国史,知其塞上功甚伟。”世昌姿表奇迈,慷慨自许,论议英发,见事风生,久膺师寄,历西北诸镇,身经十余战,其于边徼险易、虏情真伪、将才士势定诸胸臆,核如示掌,出奇取捷,虑成发中,颠倒才智,柔驯辨强,皆乐为之用,效之者皆自以为不及其识。其力壮老一致,虽罹挫衂,而志不少衰。善奖拔士,尝特荐杨守随、侣钟、屠滽、王睿四御史,健将武较多出其门。又长于吏事,判断章奏,口占授吏,曲当事情。博学多闻,凡兵法、射艺、象纬、堪舆之说,罔不该究。为诗歌,雄迈跌宕,若不屑意。睦族敦旧,赒穷恤贫,援接卑幼,如恐不及。[19](卷二,P390-391)
可见,明朝中后期所面临的军事危机与严峻局势,影响了修史者对王越的认识与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王越传记书写的走向。
(二)明中后期宦官干政的加剧与“屈膝附阉”故事的演绎
隆庆以后,诸传记对王越附汪直之事的描写亦愈加生动,这主要表现在对笔记小说所载事迹的采用上。如王世贞曾记一小宦官唱戏之事:“上尝曲宴,而内伶为戏者以贵人装,两手各操金钺,恣睢前。问为何人,曰:‘汪太监。’所持何物,曰:‘两钺耳,不仗此不能一歩。’上笑而弗罪也。”[15](卷八十八《史传》,P272-273)笔者检阅现存史书,查得此事最早见于王鏊所著《震泽纪闻》,“时优人颇用事,当道者或结之以毁誉人......又一日进曰:‘天有两月,一人击之。’曰:‘月一而已。安得有两?’应曰:‘内有陈钺,外有王钺,岂非两月乎?’盖皆有阴嗾之者”[22](卷下,P488)。值得注意的是,王鏊记载此事的目的是批判当道者与优人相勾结,并非批判王越。此事流传较广,亦见载于《续藏书》《皇明辅世编》《国朝献征录》[23](卷十《伯二》,P355-358)等书中。另,邓球于《皇明泳化类编》中记载了王越跪汪直一事:“越每直必跪,时吏部尚书尹旻等欲诣直,属越为介,私于越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越先入,旻阴伺之,越跪叩头出。及旻等入,旻先跪,诸人皆跪,直喜。比出,越尤旻,旻曰:‘吾自见人跪来,特效之。’越大惭。”[24](卷五十一,P88)将王越的谄媚之态刻画得淋漓尽致。据查,此事亦来源于成弘时期的笔记小说:“予闻都御史王越特为汪直所厚,旻偕卿贰欲诣直,属越为介,私问越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者乎?’越先入,旻阴伺之,越跪,白讫,叩头出。比见直,旻先跪,诸人皆跪,直大悦。越尤旻,旻曰:‘吾自见人跪来,特效之耳。’”[25](卷九,P695)笔记小说虽是重要的史料,但其中不乏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之事,王世贞、邓球等人以之为史源,也可看出史家对宦官干政的痛恨。
宦官干政问题缠绕了大半个明代,严重扰乱了明朝的政治秩序。先有正统年间王振擅权误国之祸,又有成化时汪直恃宠乱政之恶,宦官干政始终困扰着明朝的史学家,不符合修史者信奉的士大夫治国的理想,故他们多对之持批判态度。而随着明朝统治危机的加深,宦官干政并未消除,反而愈演愈烈。正德初年,刘瑾用事,以其为首的“八党”权倾天下,威福任情,文官集团亦进一步分化,张焦芳等均成为刘瑾爪牙。后刘瑾集团虽于正德五年覆灭,宦官当权的局面未改,“张永用事,政仍在内,魏彬、马永成等擅窃威柄,阁部仍敛手而已”[26](卷四十三,P1175)。万历年间,宦官的触角更是伸到了经济领域。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明神宗多次向地方派遣矿监税使,他们大肆搜刮,作威作福,严重影响了明朝的统治秩序,遭到了大多数官吏的反对,“大臣言官疏请者日相继,皆不复听。矿税之害遂终神宗世”[27](卷二百一十八,P5758)。吴瑞登曾评价曰:“自天顺后,王振、汪直、刘瑾三大阉用事,以故内则管军、管匠、置立田宅,外则织造、镇守,无不受其荼毒。岂知苏杭之地,自有抚按有司责而成之,自可如式,不然,或设一同知提督,事可办而费可省矣。若专任内臣,岂独机户丝行,以一倍百,即道涂往来骚不赀,民皆不堪命矣。”[28](卷一,P514)宦官的势力遍及政治、军事、经济领域,人民不堪其扰,多次爆发民变和兵变。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邪恶当道,明朝的政治黑暗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空前的统治危机使得史学家忧心忡忡,他们对阉党问题极为敏感,曾与汪直交往过深的王越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批判的对象,“跪事汪直”记忆的翻出和强化,“内伶借戏讽喻”故事的演绎,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们的心态。
三、结 语
如前所述,本文之政治生态侧重于政治环境对史家们思想及观念意识的影响。在明代,作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学者与朝廷官员的统一体,史家们对史书的创作也是为统治集团而服务的。明中后期,权力斗争愈演愈烈,边疆形势日趋严峻,这些问题无时不刻地刺激着史家的神经,影响着他们对历史文本的书写。
明中后期的史学家对王越个人史的书写亦充满了矛盾,既肯定其保卫边疆的历史功绩,褒扬其将才,又为其依附宦官感到痛恨与惋惜。这种复杂的心态与明中后期的政治生态息息相关,是明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加深的反映,而矛盾的加深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1644年,清军入关,明朝结束了其近277年的统治,但史家对一代名将王越个人史的书写仍未完结,对其评价亦达到了最高点,如清初孙奇逢曾曰:“惜后之人无有能用贤者,元气俱丧,宗社沦亡,因忆杨忠敏、王威宁乃国家最有用之人,未可轻訾议也。”[29](卷二,P202-203)孙承泽亦评价王越乃“真命世才,数百年不一见者也。使当日能自特立,慎所依附,虽古之韩、岳,何以加焉”[30](卷二十,P577)。然明朝已往,史家对王越的回忆亦不过成为一种追思而已。
终明一世,外多边疆之患,内多宦官干政,此二者均反映在对王越个人史的书写上。王越既因其搜套之功得到颂扬,又因其结交权珰为人诟病。査继佐叹曰:“吾悲其不得已而委身权侍也。”[31](卷十一中,P502)宦官专权对明朝政治影响巨大,王越与汪直结交,造就不世之功,为史家所歌颂。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随着明朝统治危机的加深,王越依附宦官之行为也不可避免地遭到批判。史家对王越形象的塑造及其改变,体现了他们的政治诉求,更是明朝政治生态变化所影响的结果。
注释:
①近年来政治生态一词越来越多地进入史学研究范畴。相关论著有:周膺、吴晶的《南宋四洪的思想和学术进退——宋代士人的别一种思想和政治生态》(《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11年12月),展龙的《元明之际士大夫政治生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李佳的《“以谏为忠”与“以谏求名”——论晚明士大夫的谏诤观与政治生态》(《史学集刊》2015年第6期),王家范的《从知县形象看明清基层政治生态》(《历史教学问题》2016年第2期),等等。相较于政治局势、政治权力等概念,政治生态更侧重于政治环境对某个群体思想及观念意识的影响。本文所论政治生态,不仅包括明中后期朝廷所面临的政治问题,还包括在这种矛盾下,当时的史学家所表达的史学心态或政治诉求。
②学界对明中后期的起讫时间并无定论。本文取成化朝至崇祯朝这一历史阶段。
③本文所述王越传记,指能较系统地介绍王越生平事迹,并对其加以评价之文字,包括《明实录》王越传、志书载王越传记、王越碑传文及年谱、其他明人所撰王越传记等。
④万历时,应陈于陛之请,朝廷曾下令撰修本朝国史,惜并未修成,仅有残稿传世。
[1](明)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0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2](明)王越.黎阳王襄敏公疏议诗文辑略[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第3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3]谢贵安.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4]明孝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
[5](清)顾炎武.顾亭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明宪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
[7](明)叶盛.水东日记[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4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8]李朝实录[M].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影印本,2011.
[9](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明)李东阳.怀麓堂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5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11](嘉靖)湖广图经志书[M].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12](嘉靖)山东通志[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第18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
[13](明)郑晓.吾学编·名臣记[M].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史部第45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14](明)崔铣.洹词[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6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15](明)王世贞.弇州续稿[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8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16](明)李贽.续藏书[M].续修四库全书本:第30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7](明)尹守衡.明史窃[M].续修四库全书本:第3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8](明)张萱.西园闻见录[M].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16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9](明)唐鹤征.皇明辅世编[M].明代传记丛刊本:第29册.台北:明文书局,1991.
[20](明)何乔远.名山藏[M].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史部第4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21](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M].续修四库全书本:第53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2](明)王鏊.震泽纪闻[M].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16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3](明)焦竑.国朝献征录[M].续修四库全书本:第5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4](明)邓球.皇明泳化类编[M].明代传记丛刊本:第81册.台北:明文书局,1991.
[25](明)黄瑜.双槐岁钞[M].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16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6](清)夏燮.明通鉴[M].长沙:岳麓书社,1999.
[27](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8](明)吴瑞登.两朝宪章录[M].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35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9](清)孙奇逢.畿辅人物考[M].明代传记丛刊本:第143册.台北:明文书局,1991
[30](清)孙承泽.畿辅人物志[M].明代传记丛刊本:第142册.台北:明文书局,1991.
[31](清)査继佐.罪惟录[M].续修四库全书本:第3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王立霞】
王越为明朝成化、弘治时期著名军事将领,其传记详载明朝各官修、私修史书。诸书所载王越传记,选取事件不一,褒贬各有侧重,众史家对王越的态度亦有矛盾之处,这是明中叶政治生态发生变化的反映。明中后期,北疆形势错综复杂,宦官专权屡次上演,这些问题始终影响着明中后期的史学家,进而影响着王越个人史的书写走向,呈现出一种矛盾与复杂的态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
K248.2
A
1004-518X(2017)11-0136-0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明实录》整理与研究”(13&MD090)
蔡果利,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天津 300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