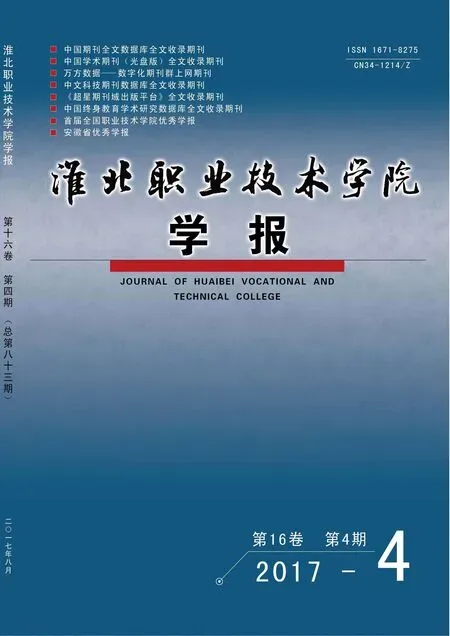“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对当代中国法治的启示
王天煜
(淮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对当代中国法治的启示
王天煜
(淮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恶法亦法”强调法的形式,“恶法非法”重视法的内在价值,这两种观点共同催生了现代法治。当下中国仍处社会主义法治的初级阶段,强调 “恶法亦法”和“恶法非法”两种观点的结合,有助于法治的完善。立法层面上,法律的制定要具备前瞻性,要结合本国的国情,要体现自然法的价值追求;司法层面上,要注重探求情、理、法在司法裁判中的兼容;守法层面上,要强调对法律的绝对服从。
恶法亦法;恶法非法;立法;司法;守法
“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是西方新自然法学派和分析法学派争端的一个焦点,两种观点的产生有着各自的历史背景、时代意义和一定的局限性,而当下法学界对此争端早有定论,更不用提经济分析法学、社会法学等学派的出现,使得这一矛盾的基础——应然法和实然法之争显得无足轻重了。然而,通过对这一争端产生和发展的重新审视,对当下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仍大有助益。
一、“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
明确这一争端,首先需要认知两点内容:其一,“恶法”存在的前提是承认有“良法”和“恶法”的区分,用以区分二者的标尺可以笼统地归结为抽象的道德。通常情况下,“恶法”大多在法律原则上为“良”,即法律在创制时体现出的法律制定者的意志和价值追求、对社会秩序保护的预期往往是“良”的,然而通过法律规则形成法律条文时,可能出现表述不周或在法律实际运行过程中出现“为恶”的现象。其二,关于法之“善恶”的讨论范畴为何。根据严存生教授的观点,法可分为必然法、应然法、实然法。其中,必然法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是客观法;应然法是人理想中的法,是以人类美好价值为内在的法;实然法是被制定出的实在的法律,后两者都属主观法的范畴。所谓“良法”“恶法”,是针对实然法也就是人定法来说的,而客观法则无善恶之分。[1]
(一)恶法亦法
“恶法亦法”的观点可上溯到苏格拉底。19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革命完成,无产阶级业已产生并作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此时,资产阶级为巩固其统治地位,迫切需要一套新的法律理论体系以维护自己的统治,此时,分析法学派应势而生。分析法学派认为:实然法才是法学应该研究的范畴,而应然法和道德则是伦理学等学科进行学术研究的领域;法是国家主权者的命令,是一个“封闭的逻辑体系”。由此可见,分析法学派将法律孤立于道德和伦理之外,认为“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它的功过则是另外一回事”[2],强调划分“实际上是这样的法律”与“应该是这样的法律”,法律是否有效取决于它是否是由适格的主体以法定的形式颁布,而非在于它是否符合道德的评价,“恶法亦法”由此而生。
(二)恶法非法
与“恶法亦法”相对应,二战后非神学的新自然法学派兴起,新自然法学派的法学家们举起了“恶法非法”的旗帜。新自然法学派承袭自然法一贯的脉络,重视法律存在的客观基础和价值目标,认为法的本质是一种客观规律,这些规律和价值可统称为用以评价法律的外部价值。自然法学家们认为法与道德有着天然的不可割裂的联系,于是划分出法律的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进而提出二者是统一又相互影响的观点。基于此种观点,“良法”“恶法”顺势而生,即自然法学派认为“良法”是符合法的外部价值的应然性法律,而“恶法”则是与外部价值相悖,自然称不上是“法”,即“恶法非法”。
(三)两种观点的价值和局限
“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这两种观点产生的背景有所差异,但结合它们各自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社会背景来看都有其合理性。“恶法亦法”主张法律至上,将重心放在如何利用技术更好地对法律进行操作这一问题上;而“恶法非法”更注重法律的内在精神和价值,更关心法是否能符合道德的评价标准,是否能体现人本思想和保护公民的权利,而非变成政府为恶的工具。分析法学是人类法律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产生的较为成熟的法学派,其意义在于使法学摆脱一直以来依附其他学科的尴尬境地,而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自然法对于法的价值的探索,对人本思想和权利的追寻则指引了人类对于正义价值的诉求。我们今天对于法学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二者的结合,而“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正是打开现代法学研究之门的一把重要的钥匙。
以今天的法学视角看来,两个学派在对法的认识上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分析法学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分析法学派否定了法与道德的必然联系,单纯研究“法律的实在”,而不重视法律的内在精神和价值。其二是分析法学派认为法只要满足其形式,就可以判断它是法,而不论法律本身的善恶,这样的观点往往容易导致专制与暴政。自然法学的局限性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然法学派将其许多命题都建立在臆断的基础上,忽视了法律本身内容的合理性、普遍性和真实性。二是自然法学用以评价法的外部标准通常是抽象而不能具体书于文字的,正如对法核心价值之一——正义的认识,从西方法哲学千年历史来看,不同学者对正义的内涵持有自己的理解,可见这种外部标准是很难被唯一定义的;同时,社会在不断发展,环境也在不断变化,这就导致用以评价法的外部价值也是不断变化着的,法就会缺乏内在的稳定性。纯粹以外部价值对法进行评价,会导致法的内部评价体系缺失,法学得不到独立的学科地位。当然,通过外部价值评价法律对法治的完善大有助益,然而忽视法律存在的现实基础,忽略繁复的社会因素而抽象地谈论法律,并不可取。
二、“恶法非法”和“恶法亦法”对中国法治的启示
“恶法亦法”“恶法非法”的争端,是西方法治不断发展进步的表现。现代中国的法治建设起步较晚,虽然法律体系已初步建设完成,但中国仍处于一个法治的初级阶段。“恶法亦法”“恶法非法”的争端在立法、司法、守法三个层面上仍能给我们许多启示。
(一)立法层面
1.立法要与时俱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律数量增长迅速,法律体系逐步完善,但是法律量的增长并没有带来质的突破,有些法律不能取得民众认同,有些法律出台不久就已不合时宜。究其原因,这类法律或脱离了实际,或不能紧扣时代的脉搏,失去了“良”的基础。
实践证明,并非有了法律就有了法治。法治的推进首先需要追求立“良法”的状态,在法律制定过程中,不仅要注重法律的形式,而且要体现自然法的理念,探求法的外部价值。而自然法所追求的外部价值,即“良”的标准也是随着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特别是当下日新月异的社会,社会不断发展变化也使人们的价值观不断受到冲击,那么用以评价法的外在价值就不可能丝毫不变。正如“以德报怨”和“以直报怨”:“以德报怨”曾一度为传统观念所推崇,而从正义的角度进行评价,“以德报怨”只会助长不道德者的气焰,让正义跌入尴尬的境地;“以直报怨”显然更符合正义的理念和当下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因此我们在立法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外部价值上的变化带来的影响,即法律的制定要具备前瞻性,因为只有具备前瞻性的法律才不会被快速淘汰,才能成为“良法”,而只有“良法”才能具备内在的说服力,才能被民众承认并得以有效推行下去。反之,我们制定的法律滞后而不合时宜,就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自然称不上“良法”。
2.立法切忌照搬
基于对“恶法”“良法”的认定,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是否在他国已被实践证明为“良法”的法律,在我国也能照搬适用?西方的法制体系完善,法治程度很高,我们应借鉴其长处。然而从实践来看,并非所有在本土之外的环境下已经被证明为“良法”的法律,都适合本土的法治环境,对外来法律体系进行纯粹的照搬只会使其在本土环境中失去活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虽成果卓著,但客观看来还是与发达国家存在不小差距,纯粹照搬国外“良法”却不考虑国情,只不过是又温习了“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的教训。法律的制定应该基于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拿来”的法律需要被改造,使其适应我国国情,才能焕发出应有的活力。除此之外,法律对于公民权利的开放和限制也应该与社会发展程度相匹配,在社会发展程度低的情况下,无节制的赋予公民权利,会导致“良法”为恶。
3.立法应体现外部价值
法与道德不可割裂的关系为自然法思想所认可,道德也成为法的重要渊源之一。这种渊源还可以体现在奖励性法律中。例如,见义勇为不能成为法律上的义务,但是可以制定相关法律对见义勇为之类的行为加以确认,用奖励性的法律条文对这类正面价值加以鼓励,从而使法律更直观地体现自然法的思想,抽象的道德化为了具体的规范,法的外部价值得以实体化和规则化。
(二)司法层面
“良”法在其制定时就具有“善”的初衷,但在实际施行过程中,却并非都能达到“良”的效果,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实在法在适用时僵化所致。大陆法系成文法的特点决定了法官极少在法律条文之外裁判案件,但非正式的法律渊源仍作为大陆法系法官在司法裁判中的重要考量因素。自然法对法的外在价值的探索为司法解释工作给予了大量支持,同时对运用非正式的法律渊源,特别是运用判例进行裁判提供了有力武器,这对于法治的完善至关重要。一方面,许多原本不能纳入法条体系的案件可以通过自然法的法律理念得到救济;另一方面,它既给了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同时又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划定了界限。
中国传统司法讲求“国法”“天理”“人情”三者的结合。如宋代的司法,当时的“兼职法官”更多地在判案过程中奉儒家经典为裁判依据,而非当时已略具体系的《宋刑统》。因此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并没有司法,在笔者看来,中国古代的司法更符合自然法的理念:儒家经典中的优秀传统价值正是作为自然法所追寻的外部价值被实在地运用到了司法裁判中。在现代的司法实践中,我们仍应继续追求情、理、法在司法审判中的兼容,特别是在运用法律原则及非正式法律渊源辅助裁判的过程中。
(三)守法层面
从西方法律思想发展演变的线索来看,“恶法亦法”到“恶法非法”的争端和高下之分与社会的发展和法治的完善程度息息相关。无论是“恶法亦法”或是“恶法非法”的提出,都是基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法治的初级阶段,必然追求法的权威性与法律实施的效率,“恶法亦法”在其时代背景下对法的推行、法治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而提出“恶法非法”的观点是对法的价值讨论的回归,是限制恶法的必要,挣脱实然法的桎梏,在法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突破到对应然法的求索。
我国的法治仍处于初级阶段,公民的法律意识尚且淡薄,更遑论法律常识和法律知识。在这样的法治环境下,强调“恶法亦法”,对于在人们心中建立法律的形象、树立法律的权威,意义重大。法治的关键在于实施,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不论什么样的法律,即使“道德上邪恶的规则可以仍是法律。”[3]只要是法律,无论其正义或是邪恶,都要求公民须绝对服从,才能真正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当然,我们强调“恶法亦法”,并非不追求“良法”,“良法”始终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法律,但是要想切实推动中国法治的建设,适当强调“恶法亦法”也是必要的。
时下中国的民众对待法更多的是一种不信任,不尊重的态度。我国法治建设起步较晚是一方面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公权力没有给予法律应有的权威地位,公权力干预司法的例子屡见不鲜,甚至少数官员“以身试法”,而法律视而不见,这是法治推进的重大阻碍。苏亦工教授在早年的文章中提到:官府做民众的道德标杆不易,只因官府自身在道德上存在瑕疵,如何能要求民众都成为道德标兵?[4]法治若想推进,除要求公权力的他律之外,也要求公权力自律,先律己方能律人。
[1] 严存生.“法”的“存在”方式之三义:必然法、应然法、实然法[J].求是学刊,2015(2).
[2] 张文显.二十一世纪西方法哲学研究思潮[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85.
[3] 哈特.法律的概念[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207.
[4] 苏亦工.朕即法律:从《贞观政要》对唐太宗的评价谈起[J].民主与科学,2008(1):58-61.
责任编辑:寸 心
2017-05-08
王天煜(1988—),男,安徽淮北人,法学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学理论。
D920.0
A
1671-8275(2017)04-008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