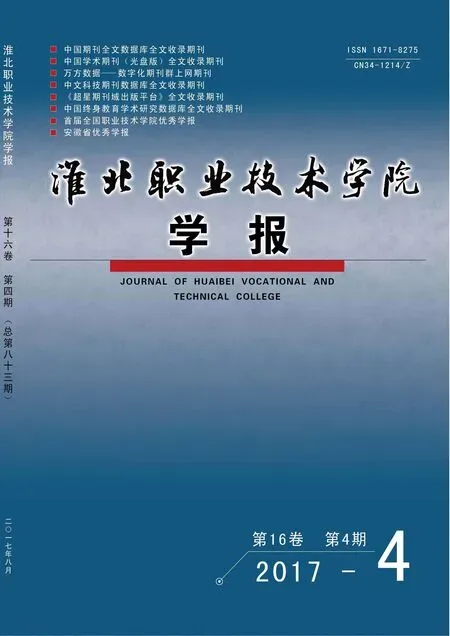从《商市街》的语言策略看萧红对贫穷的抒写
吴慧理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从《商市街》的语言策略看萧红对贫穷的抒写
吴慧理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商市街》是民国女作家萧红的一部具有自传性质的散文集,主要记录了二萧在哈尔滨早期生活的情境。萧红在其中运用隐喻、反复以及反讽等语言策略,抒写了她对底层穷苦人们的悲悯情怀,表现了这位天才女作家在抵达人的生理和精神极限处的独特生命体验。
萧红;语言策略;隐喻;反复;反讽;对贫穷的抒写
萧红的《商市街》[1]写于1935~1936年初,共收散文41篇,是继《跋涉》和《生死场》之后首部具有自传性质的散文集,主要记录了她于1932~1934年和萧军在哈尔滨早期生活的情境。在已资本主义化的商业都市哈尔滨,萧红倍受贫穷和饥饿的侵袭,加之被前夫汪恩甲抛弃的命运和弃子之痛使她精神上也饱受摧残。萧红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变成一个穷人,由于相同的命运,她更加同情底层广大的穷苦大众,以其切身感受,运用独特的散文语言,抒写了她对贫穷的感受和对底层穷苦人的悲悯情怀。
一、隐喻
在《商市街》中随处可见隐喻手法的运用。如在《弃儿》中,当写到被围困在水中即将丧命的小猪时,隐喻的运用使文本意蕴深远。文中这样写道:
水在它的身边,一个连环跟着一个连环的转,猪被围困在水的连环里,就如一头苍蝇或是一头蚊虫被缠入蜘蛛的网罗似的,越挣扎,越感觉网丝是无边际的大。小猪横卧在板排上,它只当遇了救,安静的,眼睛在放希望的光。
——《弃儿》
在这段描写中,萧红将被围困在大水里的小猪与被缠入蜘蛛网的一头苍蝇或一头蚊虫联系起来,苍蝇或蚊虫缠入蛛网越是挣扎就越是深陷其中,而此刻水中的小猪也是如此,越是挣扎就越有可能被卷入漩涡而丧命,而此情此景又何尝不是对人的命运的一种隐喻,在贫穷的生活中与饥寒做着斗争的底层穷苦大众的命运不也正是如此吗?“隐喻意义并非词语意义:它是语境创造的意义。”[2]这种隐喻手法的运用,使看似浅白易懂的文字蕴含了丰富的意味,这也正是萧红散文耐人咀嚼的关键所在。在这种特殊语境下,浅白的词句也具有了非凡的意义,传递出萧红对贫穷、对人的无法把握的命运的思索与悲悯,为读者创造出以无限启迪与思考的空间。
巴赫金曾经说过:“在语言的自身中研究语言,忽视它身外的指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正如研究心理感受却离开这感受所指的现实,离开了决定这一感受的现实。”[3]我们之所以研究语言,是因为语言中含有和我们生存处境息息相关的东西,透过它能传达出一种人生意义,萧红的散文语言即是如此。在《同命运的小鱼》中,小鱼最终逃不过一死的命运,将萧红的思绪引到对人的命运的悲叹。文中这样写道:
这时我不知该怎么样做,我怕看那悲惨的东西。躲到门口,我想:不吃这鱼吧。然而它已经没有肚子了,可怎样再活?我的眼泪都跑上眼睛来,再不能看了。我转过身去,面向着窗子。窗外的小狗正在追逐那红毛鸡,房东的使女小菊挨过打以后到墙根处去哭……
——《同命运的小鱼》
作者在这里运用隐喻的手法,看似是在可怜一条小鱼,而标题里的“同命运的”却扩展了文本的含义,小鱼的命运正与这世间一切受着不平等待遇而身处困境中的人们一样,正如同使女小菊,她在挨过打以后只能到墙根处去哭。然而,这悲苦的命运却又如同“窗外的小狗正在追逐那红毛鸡”一样再平常不过了。传统的封建等级制度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位高者欺压位低者被看作理所当然,人们对此漠然接受,这只是日常生活图景中再平常不过的一幕,萧红用隐喻的手法将人的命运同鱼的命运等同起来,从表面上看,她的方式是加以淡化、弱化,而实质上所取得的效果恰是一种强化、深化。其中暗含的是对人如动物般生死,毫无尊严的生存处境的愤怒,于不动声色中,透视出封建等级制度下的人性残酷。
二、反复
《商市街》独特的语言魅力,还在于萧红非常规化的反复手法的运用。在《祖父死了的时候》一文中,萧红用一种繁复的叙述和看似平淡无奇的语句来强化其内心感受:“父亲对我是没有好面孔的,对于仆人也是没有好面孔的,他对于祖父也是没有好面孔的。因为仆人是穷人,祖父是老人,我是个小孩子,所以,我们这些完全没有保障的人就落到他的手里。”[4]64在这里,一个孩子幼小心灵所受到的伤害,正是由这繁复的叙述而得到了如烙印般的呈现。父亲整日里板起面孔的冷漠形象给一个孩子眼中造成了对现实世界的奇怪印象。同时,文本的潜在叙述者又传达了一个成年女性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和评价。讲述故事的孩子是弱势的、天真的,面对父亲的强势是只有被动接受的,然而站在孩子背后的隐身叙述者萧红却是一个已经历过人世冷暖的成年女性,她所看到的是一个令人感到荒谬而又悲凉的现实世界,从中揭示出封建父权制社会给人带来不幸的本质。
在《饿》一文中,萧红把自己饥饿到极点时对食物的渴望描绘得动人心魄。饥饿的萧红几次三番地想要去偷别人门扇上挂着的列巴圈,文中对萧红想要偷的矛盾内心有着繁复的叙述,在萧红眼中,面包和牛奶不仅香甜,而且“列巴圈”也比平日里大了些。饥饿放大了人对周围事物的感受,却也使饥饿者的灵魂坍塌、缩小,“过道越静越引诱我,我的那种想头越想越充涨我:去拿吧!正是时候,即使是偷,那就偷吧!”[4]126但我最终战胜了自己,却也更使自己的灵魂趋于软弱、虚脱,“过了好久,我就贴在已关好的门扇上,大概我像一个没有灵魂的、纸剪成的人贴在门扇。”[4]116萧红细致地、反复地叙述着自己的饥饿感受,把她在抵达生理极限处时,精神也近于崩溃的极度慌乱状态毫不掩饰地表露出来,体现了一个初出茅庐的女作家大胆剖露自我内心的勇气。此后,饥饿的萧红独自在房间内,又从窗口所看到的一幕穷苦女人的四处乞讨引发了她对饥饿与贫穷的更深刻的感受。文中这样写道:
一个女人站在一家药店门口讨钱,手下牵着孩子,衣襟裹着更小的孩子。药店没有人出来理她,过路人也不理她,都像说她有孩子不对,穷就不该有孩子,有也应该饿死。
……
那女人一定正像我,一定早饭还没有吃,也许昨晚的也没有吃。她在楼下急迫的来回的呼声传染了我,肚子立刻响起来,肠子不住的呼叫……
——《饿》
在这段描写中,萧红观察乞讨女人,用孩子般絮絮叨叨的语言反复叙说路人的态度,穷人的命运,通过这种繁复的絮絮低语,饥饿者萧红写下了她对乞讨女人的深切同情,而同样在忍受饥饿的萧红通过这种如呓语般的文本语言也是在怜悯着与乞讨女人有着相同境遇的自己,透过这种看似啰嗦的如孩童般不讲逻辑的重复,把处于饥饿中有些精神紊乱的萧红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展现出一个抵达了生理极限的女作家在内心中却仍不忘关怀着底层穷苦人民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性光辉。
三、反讽
萧红往往通过反讽的语言策略使叙述语与语境之间相互映照,从而曲折地传达出更深层的内涵、意味,文本的表面叙述与潜在叙述往往构成一种悖反关系。如《春意挂上了树梢》一文:“世界上这一些不幸的人存在着也等于不存在,倒不如赶早把他们消灭掉,免得在春天他们会唱这样难听的歌。”[4]171所谓“倒不如赶早把他们消灭掉”以完全抛弃人道的口吻来给穷人定位,以完全厌恶的口吻来形容穷苦大众,实际上是一种反讽,内中包含着叙述人对穷人深深的同情,这种恶语背后是对穷人真正的悲悯,使我们在为萧红的叙述语言震撼的同时也体会到了比直截了当的表述更复杂的含义:整个哈尔滨都市社会对弱者的漠视,以及在这漠视中包含着的人性邪恶,而句子表层意思与实质内涵的悖反关系则使表达富于张力而又耐人寻味。
在《三个无聊人》中,标题即为一种讽喻,文中这样描写那个狭肩头的人:
狭肩头的人,愤愤懑懑地,整整一个早晨,他没说无聊,这是他看了一个无手无足的乞丐的结果。也许他看到这无手无足的东西就有聊了!
——《三个无聊人》
文中那个狭肩头的人,衣食无忧,整日无所事事,感到无聊,而能消除他这种无聊感的唯一方法便是去公园里看“没有手脚的乞丐,”待到观看到这一惨状后便回到家来“愤愤懑懑地”待个早晨,暂时忘掉享乐,午饭也只吃面包,而这种因同情别人而克制自己的状态却并不能维持多久,竟致到最后连看到报纸上“电车轧死小孩,受经济压迫投黄浦自杀一类的”[4]68事情也“治不了他这个病了。”萧红用“三个无聊人”为标题,把无聊人对下层穷苦人的虚伪同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也讽刺批判了当时一些毫无同情心而只是打着爱国、爱人民的幌子以此装腔作势的伪君子。
同样是在《三个无聊人》中,开头运用简笔画式的勾勒:“一个大胖胖,戴着圆眼镜。另一个很高,肩头很狭。第三个弹着小四弦琴,同时读着李后主的词。”这里开头描述无聊人的形象就用了“大胖胖”一词,不难看出萧红的鄙夷之色与轻蔑态度,把无聊人写得丑态毕露。而对另一个无聊人的描写,一个“狭”字,写出了无聊人的卑锁与粗浅,只从外形上,作者即运用反讽,对其投入了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表达了作者对这种人的嘲笑憎恶之情。这种简笔画式的勾勒,运用反讽,寥寥数笔即写出了三个无聊人猥琐、无聊的形象,透露出叙述者对这种无聊人的鄙视、厌恶。
正如胡风对萧红所做的评价,她是凭借着天才在创作。诚然,萧红的散文创作好比一块未经加工的璞玉,却也因其不加雕饰的天然质朴而更显珍贵。《商市街》是其初期作品,艺术上尚未达到成熟水平,但是其创作才华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展现。在《商市街》中,萧红运用隐喻、反复、反讽等修辞手法,充分展现了其文体创作的自由性,使整部散文抒情意蕴浓厚而又饱含着对广大贫苦人民的悲悯情怀。《商市街》让我们看到了萧红与众不同的文本语言,也让我们体味到这位天才女作家在抵达人的生理和精神极限处的独特生命体验。
[1] 萧红.商市街[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
[2] 保罗·利科.活的隐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258.
[3]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83.
[4] 萧红.萧红全集·散文卷[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张彩云
On Xiao Hong’s Description of Poverty from the Language Strategy inCommercialStreet
WU Huili
TheCommercialStreetwritten by a woman writer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Xiao Hong is a prose in the nature of autobiography,which mainly records their early life situation in Harbin. Xiao Hong uses the language strategies of metaphor,repetition and irony,to express her compassion feelings for lower-class poor people. It shows the talented woman writer’s unique life experience when reaching her physiological and mental limits.
Xiao Hong; language strategies;metaphor; repetition; irony; the description of poverty
2017-04-26
吴慧理(1989—),女,安徽淮北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I206.7
A
1671-8275(2017)04-0120-03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