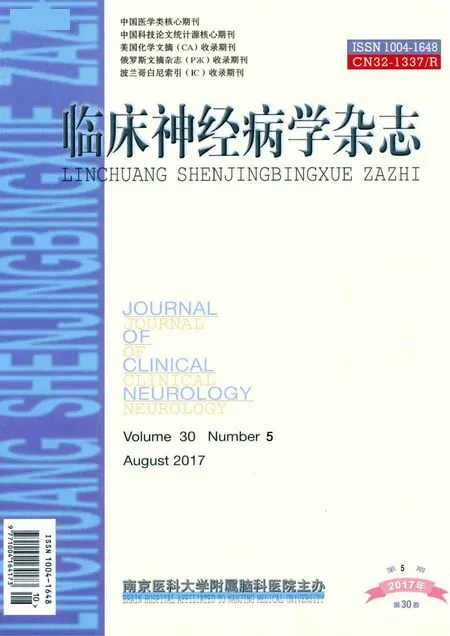光学相干断层扫描在帕金森病患者视网膜检测方面的研究进展
李娅娅,钱进
·综述·
光学相干断层扫描在帕金森病患者视网膜检测方面的研究进展
李娅娅,钱进
帕金森病(PD)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临床上主要表现为运动迟缓,静止性震颤,肌强直,姿势步态异常等运动症状,也可出现非运动症状如认知障碍、精神症状、自主神经症状、视功能异常等,这些非运动症状不但有较高的发病率,而且在疾病初期就可能出现[1-2]。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是近来发展起来的一项眼科检查技术,它可以快速、重复的评估视网膜的形态学,以一种独特的视角来观察视网膜的结构变化。目前国外已开始用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检测。有研究[3-4]提示,PD的高危人群可出现某些视觉相关损害,视觉受损指标可能具有一定早期诊断价值;并且某些视觉受损指标还可能随着疾病的进展而发展。因此,OCT对PD的病情评估也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1 视网膜与OCT概述
1.1 视网膜与多巴胺神经元 视网膜包含多层神经组织,由内到外可分为神经纤维层(NFL)、内部视网膜层(IRL)以及外部视网膜层(ORL)。IRL包括神经节细胞层(GCL)、内网状层(IPL)及内核层(INL)三层,ORL包括外网状层(OPL)、外颗粒层(ONL)、光感受器细胞层以及色素上皮层。IPL主要为网间细胞和无长突细胞,而无长突细胞是多巴胺神经元,富含酪氨酸羟化酶(TH)。酪氨酸通过血-脑屏障后被载入多巴胺神经元, 在TH的作用下先转变为左旋多巴(L-DOPA), 再经多巴脱羧酶的作用形成多巴胺[2,5]。多巴胺是视网膜中的主要神经递质,在视网膜层中有不同水平,主要集中在IRL的无长突细胞及内网状层的网间细胞[6]。但最接近CNS的是无长突细胞上的多巴胺神经元。无长突细胞为神经节细胞输入递质信号,神经节细胞通过多巴胺的D1、D2受体接受递质信号的调节,而神经节细胞的轴突形成视网膜神经纤维层厚度(RNFL)。RNFL缺乏髓鞘,在神经变性病中其结构的改变主要表现为具有独特性的轴突损害[2,5,7]。
正常人的RNFL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较一致认为RNFL与年龄、屈光度成负相关[8]。且组织学研究[8-9]证实,视神经纤维随年龄增加以每年500 根的速度减少,一生大约丢失35%。RNFL与视乳头的部位、视乳头的面积、性别、人种、玻璃体后分离、眼压以及视野等的关系研究[8-12]结果不一致,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1.2 OCT检查与视网膜评价 OCT是利用近红外光对眼部组织进行横断面扫描,以视网膜各层表面的不同折射方式来编码视网膜内不可见的改变,根据数据重建组织学,使眼睛内无形的视网膜层变为可见和可量化的图像。其分辨率及穿透率极高,可以观察到视网膜所有的分层。因此,OCT可以直接评估视网膜细胞的损伤。测量时大多以视乳头中点为中心,将扫描直径定为3.46 mm的环形扫描。扫描分为上方、下方、颞侧、鼻侧、颞上、颞下、鼻上、鼻下8个象限进行。由计算机按照指定程序扫描视盘边界,同时根据扫描结果计算不同视盘参数。每只眼进行3次扫描,选择其中最清晰的图像连同四个象限的平均视网膜厚度、伪彩编码图进行打印[13]。
OCT于1991年被引入眼科检查,且OCT已证实RNFL在眼科疾病,如青光眼、糖尿病性眼病、高度近视眼等中可变薄[4,14]。同样的,OCT发现RNFL厚度在一些神经疾病中,如2004年首次用于PD中发现视乳头旁的NFL变薄[1],在多发性硬化、视神经脊髓炎、Alzheimer’s病、遗传性共济失调、脊髓小脑共济失调以及多系统萎缩等中,也可变薄[3,15-18]。
2 OCT在PD视网膜评价中的应用
PD除典型运动症状外,临床上视觉相关的非运动症状也较常见,如视功能受损症状,包括眼干涩、阅读困难、光敏度下降、视幻觉等。国内已有研究[19]对PD患者进行VEP检查,发现PD 患者P100 波幅降低、潜伏期延长,这表明PD 患者的视觉传导通路存在异常,推断可能与PD的多巴胺能神经元在传递光信号及向视网膜神经细胞提供营养障碍有关。近年来,国外研究[1]发现PD患者会出现视网膜形态学及视功能的异常,表现为RNFL厚度变薄及视敏度下降。这提示PD患者的视网膜存在多巴胺的缺乏以及多巴胺神经元的减少[20]。且在尸检及动物MPTP实验模型中也已证实,多巴胺神经元的缺乏主要集中在视网膜的无长突细胞[2]。视网膜的IPL、RNFL可作为PD神经元及轴突病理改变研究的标志物。而多巴胺对神经节细胞输入减少而导致的神经纤维退行性改变可通过OCT检测证实[21]。
虽然OCT无法识别无长突细胞和其他的视网膜细胞的多样性,但已有研究[2,7]表明OCT可以直接评估PD的视网膜细胞损伤,说明OCT在PD诊断中的特异性以及应用价值。为了评估视网膜是否可以作为PD的一个生物标志物,研究者应该把重点放在一个特定的视网膜层,评估视网膜的变薄是否与PD进展有关[22-23]。但目前,大家对多巴胺能治疗是否影响视网膜变薄以及多巴胺能治疗是否影响特定的视网膜层等知之甚少,这些问题对本研究造成了困扰。目前大多研究集中在NFL的厚度研究,少数研究重点放在IRL的厚度研究[23]。尽管研究结果中有不一致,但多数结果倾向PD的NFL厚度及IRL厚度较对照组变薄。且在研究中需考虑PD的治疗、PD的病情、PD的病程以及PD的亚型等因素对视网膜改变的影响[5,23-28]。
目前对于PD的早期诊断及病情评估的研究很多,但仍缺乏足够的手段。OCT能很好的检测视网膜病变,尤其是视乳头周围神经纤维层以及黄斑的病变,它在测量PD视乳头周围、黄斑以及中央凹视网膜层厚度上具有应用价值,在PD早期诊断、病情随访中具备优势。
2.1 OCT对PD视乳头旁NFL的研究 NFL代表了神经节细胞的轴突,它是视网膜神经元的输出。多数研究发现PD的RNFL变薄,但Archibald等[29]研究结果却为阴性,归咎于受检者的高龄以及PD病情较重,但将年龄变量控制后仍得到阳性结果。分析影响该结果的可能原因还有:对照组不详细的眼科评价、不同的OCT设备、受检眼睛的选择等[30]。比如,Shrier等[31]就报道PD患者双眼视网膜之间存在不对称。La Morgia等[32]报道RNFL变薄更易出现在肢体症状较严重的对侧眼睛。Cubo等[33]研究发现黄斑小凹变薄的眼睛出现在震颤明显的肢体的对侧眼。所以,如果随机选择,可能使诊断阳性率下降,建议最好同时检测双眼。在现有的研究中,颞上方、上方、颞下方、鼻下方这些象限均被报道在PD中易受损[34],且颞侧最明显,推测这可能与颞侧纤维在神经变性病中较敏感、易受影响有关[32]。
2.2 OCT对中央凹、IRL、黄斑的研究 中央凹主要包含光感受器,主要为视锥细胞,且中央凹的中心的光感受器和神经元结构分布最密集,这就使中央凹的中心对空间对比和颜色差异最敏感。中央凹光感受器相互连接是通过视网膜各层中不同类型的神经元到神经节细胞的调制,然后再通过NFL连接到大脑。
PD的视力丧失通常表现在对比敏感度和色觉上,这些依赖于视网膜中央凹神经元的处理。如果这些缺失起源于视网膜,那么黄斑体积的减少应该在PD组和对照组检测出差异。现测量黄斑体积包括IRL和ORL。然而,在视网膜中央凹,极少有IRL组织,并且ORL在PD中不受影响。因此,在PD中检测黄斑中央凹厚度以及黄斑体积减少很困难。然而,一些OCT研究通过限制分析PD的中心凹周围的一个环形区域确实发现黄斑体积的减少[22-23]、黄斑中心凹变得更薄、更宽[26,35]。
IRL是在离中心凹中心约0.75 mm的斜坡上才开始出现,所以IRL厚度的增加主要源于与黄斑小凹中心的距离。大量研究[29,36]已证实在PD的视网膜中心凹段没有观察到任何厚度减少。但多数研究报告IRL变薄[23]。Spund等[26]已证实了黄斑小凹旁斜坡变薄的现象。因此,通过量化黄斑周围区域变薄可辨别IPL。多巴胺能无长突神经元位于INL和IPL之间的分界处,而OCT的分辨率是仅为5 μm,这显然对于确定细胞的不同类型是不够的。但Spund等[26]的研究结果为多巴胺能无长突细胞潜在的病理变化,如多巴胺神经元缺失、多巴胺水平下降,做出了解释。
目前OCT在PD中的研究[2,23,26,29]发现黄斑、中央凹较视乳头旁NFL检测有更高的诊断价值,关注黄斑IRL对PD的早期诊断有很大帮助。但现在研究大多采用细分和量化在鼻、颞、上、下部分的视网膜厚度并计算其平均值;然而,这种计算却漏掉从中心凹径向距离的影响[14,34,37]。另外一种较为可取的方法是以小的体像素量化厚度,特定离中央凹径向距离以0.25 mm幅度变化。这种以离中央凹不同距离量化厚度的方式可以提高阳性诊断率。研究[23,38]发现离中央凹距离1~2 mm区域是最容易受PD影响的部位。且已证实视网膜的厚度在PD中黄斑小凹周围上方、下方以及黄斑颞侧是最薄的[23,26,31,36]。
3 PD视网膜厚度的影响因素
很多研究分析了PD的临床相关参数(包括发病年龄、病程、Hoehn-Yahr分期、统一PD评定量表评分、PD亚型、治疗情况等因素)对视网膜改变的影响。目前较为确定的是PD发病年龄对视网膜影响不大。但对于病程、病情分期、统一PD评定量表评分等对视网膜的影响多数研究倾向于与视网膜变薄相关[39],但仍有与此结果不一致的研究。考虑这与样本量小、OCT设备及测量方法不同以及PD患者的差异性等因素有关。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目前大多研究没有将视网膜进行分层测量并独立比较视网膜各层的厚度变化。
3.1 PD的病情 通过对PD病情分析,多数研究[40]报道NFL及黄斑体积与H-Y分期成负相关,而与日常生活活动量表(SE-ADL)成正相关;且提出视网膜中央凹厚度可能预测PD严重性及生活质量。如Cubo 等[41]观察到在PD的Hoehn-Yahr分期≥2与H-Y分期=1相比,前者RNFL明显变薄。但也有少数研究如La Morgi等[32]研究发现上述临床相关参数和RNFL测量之间并没有相关性。
对于左旋多巴治疗对视网膜影响,尽管OCT研究发现PD组较正常对照组视网膜变薄显著,且PD组中的治疗组较未治疗组病情严重、统一PD评定量表评分高,但治疗组与未治疗组二者视网膜厚度改变并无显著差异。还有研究[24,42]发现多巴胺激动剂治疗组较左旋多巴治疗组视网膜变薄更明显。推测这可能与左旋多巴对PD的视网膜有营养保护作用有关。这仍需更多对于治疗药物、治疗剂量、治疗时间等同质因素控制后进一步研究证实。
3.2 PD的相关症状 OCT在PD运动症状以及非运动症状中的相关研究不多。Moreno-Ramos等[17]报道RNFL厚度和MMSE分数和Mattis痴呆量表有相关性。而Cubo 等[41]提到OCT检查与PD运动症状及非运动症状的严重性缺乏相关性。以及Garcia-Martin等[43]报道在PD患者中RNFL厚度和MMSE分数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需要更多这方面的大样本研究。
在PD的亚型上,研究已证实震颤组较肌强直组发展慢、对药物反应时间长、出现认知障碍晚。同样,Rohani等[27]使用OCT发现上方及鼻侧的RNFL厚度在肌强直组较震颤组变化更明显。但此研究样本量偏小,仍需进一步研究。
视幻觉是PD常见精神症状,在PD中达30%~60%[4,44]。但目前对于RNFL在PD伴有视幻觉患者中的研究较少,对于视幻觉的形成机制也不明确。目前幻觉多被归因于多巴胺能治疗、路易体疾病出现、代谢原因等。也有认为是额叶、颞叶的外侧皮质进展性损害导致。一些研究则强调视觉输入受损可能是视幻觉的必要条件。 Diederich等[45]提出视幻觉应该被视为一种调节障碍:即对外部感知和内部图像产生的控制和过滤调节障碍。Lee等[38]应用OCT发现视网膜变薄与视幻觉有显著的相关性。但这与Ales等[46]应用OCT研究结果不相符。Ales等[46]发现RNFL厚度在PD伴有视幻觉与PD不伴视幻觉两组中没有差异性(P=2.5),提示视网膜结构和功能的改变在PD视幻觉形成中不发挥主要作用,考虑更多与大脑的形态、功能改变有关,或更复杂的视网膜功能改变导致,且这种改变可能不仅仅体现在视网膜的厚度变化上。
视敏度下降也是PD常见的视功能受损症状,有OCT相关研究提到PD的对比视敏度下降与黄斑IRL厚度减少相关,因为IRL富含多巴胺神经元,其功能的缺失及萎缩改变可能是视敏度下降及IRL变薄的发病机理的基础[14,23,25],但仍需大量研究的支持。
4 总结及展望
OCT是一种利用近红外光对眼部组织进行高分辨率及高穿透力扫描的影像检测技术,其能较直观的观察、定量的测定视网膜的厚度,是一种非接触性、非侵入性、高敏感性的诊断技术。对于诊断神经变性疾病,尤其在PD的诊断中具有重要意义。OCT应用到PD的研究中,对研究视网膜在神经变性疾病中的变化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相信随着OCT在PD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其对PD的病理生理、早期诊断及病情评估和随访等方面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1] Inzelberg R, Ramirez JA, Nisipeanu P, et al. Vision Res, 2004, 44: 2793.
[2] Bodis-Wollner I, Miri S, Glazman S. Mov Disord, 2014, 29: 15.
[3] Galetta KM, Calabresi PA, Frohman EM, et al. Neurotherapeutics, 2011, 8: 117.
[4] Nucci C, Martucci A, Cesareo M, et al. Prog Brain Res, 2015, 221: 49.
[5] Cubo E, López-Pena MJ, Diez-Feijo VE, et al. J Neural Transm, 2014, 121: 139.
[6] Satue M,Seral M,Otin S,et al.Br J Ophthalmol,2014, 98: 350.
[7] Bodis-Wollner I. Parkinsonism Relat Disord, 2013, 19: 1.
[8] 李庄钰,其其格,金宝泉.内蒙古医学杂志,2014,46:527.
[9] Balazsi AG, Rootman J, Drance SM, et al. Am J Ophthalmol, 1984, 97: 760.
[10] 张艳明.中国老年学杂志,2014,19:5439.
[11] 孙冉,张健,刘大川,等.中国现代医学杂志,2015,25:66.
[12] Sani RY, Abdu L, Pam V. Ann Afr Med, 2016, 15: 52.
[13] Slotnick S, Ding Y, Glazman S, et al. Mov Disord, 2015, 30: 1692.
[14] Kaur M, Saxena R, Singh D, et al. J Neuroophthalmol, 2015, 35: 254.
[15] Shen Y, Shi Z, Jia R, et al. Front Cell Neurosci, 2013, 7: 142.
[16] Rebolleda G, Diez-Alvarez L, Casado A, et al. Saudi J Ophthalmol, 2015, 29: 9.
[17] Moreno-Ramos T, Benito-León J, Villarejo A, et al. J Alzheimers Dis, 2013, 34: 659.
[18] Pula JH, Towle VL, Staszak VM, et al. Neuroophthalmology, 2011, 35: 108.
[19] 李玲,季晓燕,毛成洁,等.中华内科杂志,2015,54:521.
[20] Chorostecki J, Seraji-Bozorgzad N, Shah A, et al. J Neurol Sci, 2015, 355: 44.
[21] Sari ES, Koc R, Yazici A, et al. J Neuroophthalmol, 2015, 35: 117.
[22] Garcia-Martin E, Larrosa JM, Polo V, et al. Am J Ophthalmol, 2014, 157: 470.
[23] Adam CR, Shrier E, Ding Y, et al. J Neuroophthalmol, 2013, 33: 137.
[24] Sen A,Tugcu B,Coskun C,et al.Eur J Ophthalmol,2013, 24: 114.
[25] Bodis-Wollner I, Glazman S, Yerram S. Behav Neurosci, 2013, 127: 139.
[26] Spund B, Ding Y, Liu T, et al. J Neural Transm ,2013,120: 745.
[27] Rohani M, Langroodi AS, Ghourchian S, et al. Neurol Sci, 2013, 34: 689.
[28] Schiess MC, Suescun J. JAMA Neurology, 2015, 72: 859.
[29] Archibald NK, Clarke MP, Mosimann UP, et al. Parkinsonism Relat Disord, 2011, 17: 431.
[30] Laudate TM, Neargarder S, Cronin-Golomb A. Behav Neurosci, 2013, 127: 151.
[31] Shrier EM, Adam CR, Spund B, et al. J Ophthalmol, 2012, 2012: 728457.
[32] La Morgia C, Barboni P, Rizzo G, et al. Eur J Neurol, 2013, 20: 198.
[33] Cubo E, Tedejo RP, Rodriguez MV, et al. Mov Disord, 2010, 25: 2461.
[34] Lee JY, Ahn J, Kim TW, et al. J Parkinson’s Dis, 2014, 4: 197.
[35] Bagci AM, Shahidi M, Ansari R, et al. Am J Ophthalmol, 2008, 146: 679.
[36] Albrecht P, Muller AK, Sudmeyer M, et al. PLoS One, 2012,7: e34891.
[37] Stemplewitz B, Keserü M, Bittersohl D, et al. Acta Ophthalmol, 2015, 93: e672.
[38] Lee JY, Kim JM, Ahn J, et al. Mov Disord, 2014, 29: 61.
[39] Yu JG, Feng YF, Xiang Y, et al. PLoS One, 2014, 9: e85718.
[40] Mailankody P, Battu R, Khanna A, et al. Parkinsonism Relat Disord, 2015, 21: 1164.
[41] Cubo E, Lopez-Pena MJ, Perez-Gil O, et al. Mov Disord, 2013, 28: 206.
[42] Yavas GF, Yilmaz O, Küsbeci T, et al. Eur J Ophthalmol, 2007, 17: 812.
[43] Garcia-Martin E, Satue M, Otin S, et al. Retina, 2014, 34: 971.
[44] Goetz GT, Ouyang B. Mov Disord, 2011, 26: 2196.
[45] Diederich NJ,Goetz CG,Stebbins GT.Mov Disord,2005, 20: 130.
[46] Ales K, Eva M, Brebera D, et al. Parkinsons Dis, 2015, 2015: 1.
R742.5
A
1004-1648(2017)05-0392-04
116011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一科
钱进
2016-12-28
2017-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