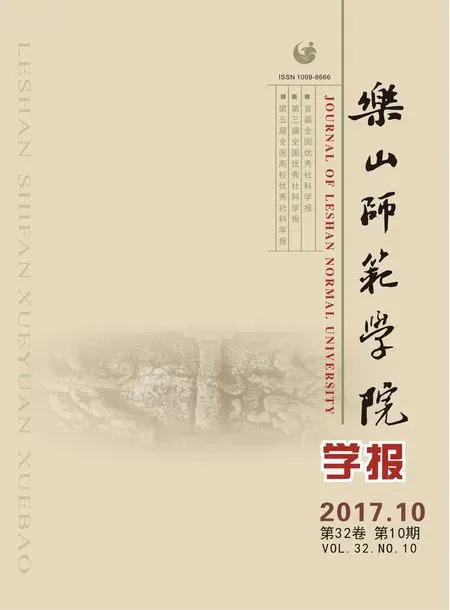论宋代咏史诗繁荣的史官文化背景
张 焕 玲
(1.遵义师范学院 人文与传媒学院,贵州 遵义 563002;2.四川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四川 成都 610064)
论宋代咏史诗繁荣的史官文化背景
张 焕 玲1,2
(1.遵义师范学院 人文与传媒学院,贵州 遵义 563002;2.四川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四川 成都 610064)
宋代史学发达,宋人编撰的史籍为文人提供了优秀的历史教科书,推动着历史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咏史创作的繁荣。而且,它所代表的史官文化心态也渗入到了咏史创作中,使咏史诗在接受和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实现了与史论、史评等史学体裁的融合,并成功地完成了由叙史言志到论史鉴世,从资政劝诫到童蒙教育,从文人雅赏到市井娱乐的功能转换。
宋代咏史诗;史官文化;史评;史论
两宋时期,咏史诗的创作群体空前壮观,王禹偁、梅尧臣、欧阳修、张方平、李觏、邵雍、刘敞、曾巩、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李纲、李清照、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刘克庄等都有叙议皆精、脍炙人口的佳作流传。咏史诗众体兼备,既有传统的五七言古体、律体、绝句,还有楚辞体、乐府体、集句体及四、六言古体等。据《全宋诗》《全宋诗订补》统计,宋代的咏史诗有7402首,数量可观,远超前代,立论新颖,以理致取胜,在古代咏史诗的发展历程上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种成就的取得与宋代发达的史官文化背景关系密切。
一、穷究治乱,上助圣鉴
“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宋贤史学,今古罕匹”。[1]238-240古代重史的优良传统到宋代得到了极大的弘扬,形成了崇史的文化氛围,并最终促使古代史学走向了鼎盛期。宋代史学在史官制度、史学著作、史著体裁、史学大家及史学领域诸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宋帝对修史的空前重视、宋人对撰史的极度热衷,各种官修史书卷帙庞大,一些史学新体裁先后创立,为前代所不及。官修史书更趋全面化、系统化和制度化,有了记载保存一手资料的起居注和时政记。
宋人在“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2]9607的思想指导下,修史、治史的目的性很明确。如欧阳修有感于五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3]173,效法《春秋》,以个人之力编撰《新五代史》,“以翼大道,扶持人心”[4]10383。《〈伶官传〉序》从五代后唐庄宗遽盛遽灭的历史事实中引发出深刻的经验教训:“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种哲理性的名言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罕见的历史深度,体现了宋代的史学精神,从客观上适应了宋朝革除五代乱世之弊、重振纲常的政治需求。又如司马光“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编为《资治通鉴》,希望皇帝能“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2]9607。全书体例谨严,结构完备,叙事清晰,质朴简洁,考证严密,文笔流畅。不仅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而且富于一定的文学色彩。唐史专家范祖禹认为“今所宜鉴,莫近于唐”[5]3,故著《唐鉴》以警示统治者。嗣后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均为编年史名著。
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则以重大历史事件立目,独立成篇,各篇又按事件的时间顺序撰写,创纪事本末体史书。郑樵的《通志》综合历代史料,带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大大扩充了史书的记述范围。朱熹与学生赵师渊据司马光《资治通鉴》《通鉴目录》《通鉴举要历》及胡安国《通鉴举要补遗》,增损改编成《资治通鉴纲目》,自序云:“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统正于下而人道定。大纲概举而鉴戒昭,众目毕张而几微著。”[6]30朱熹认为司马光不分正闰的做法不符合正统观念,全部要改回来。《资治通鉴纲目》寓意褒贬,强调正统,简明易记,较符合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总之,宋代史著长篇巨制之多,史家成就之大,都足以凌驾汉唐,睥睨明清。宋人除了以修史撰文来规范君臣大义外,还自觉地取鉴资治,常用《春秋》笔法在诗歌的世界里品评历史,故咏史之风遽尔勃兴。如宋庠《读贾谊新书》云:“谁谓贾生学,兼之文帝朝。死忧王坠马,生赋如鸮。被召宣温密,矜功绛灌骄。勤勤论五饵,史笔未相饶。”[7]2206诗人写读贾谊新书后之感想,并结合其一生行藏评其功过。又宋庠《进读唐书终帙》云:“隋室重氛极,唐家景命新。地归裂残壤,天洗战余尘。遂纳诸戎贡,争陪二月巡。瀛洲登俊老,烟阁尽名臣。轻重非关鼎,兴亡要在人。旧都纷秀麦,前事徧书筠。哲后疑图暇,西厢访古频。终篇见成败,摘句屡咨询。青史嘉遗直,元龟遗圣辰。愿将稽古意,万一助尧仁。”[7]2213则明确表达了以唐为鉴,再造清明盛世的殷殷期望。
二、酌古理今,资治惩劝
宋帝力图将修史与取鉴、资治更紧密地结合到一起,成为巩固统治的有效手段。宋朝建立伊始,宋太祖就下令修《五代史》,以便从中汲取历史教训。曾说:“昨观新史,见梁太祖暴乱丑秽之迹乃至如此,宜其旋被贼虐也。”[8]125宋帝及士人都认为“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4]13149,故要“大厉名节,振作士气”[9]3086,故在意识形态领域内集中理学、史学、文学各种力量大力整顿纲常,收拾世道人心。这场思想领域的整顿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对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分裂割据,巩固大一统局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宋代的科举考试也为大批有才能、有识见的孤寒布衣之士进入上层统治阶级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而这股以科举入仕、充满生机的新兴势力,依仗的正是博古通今以治国平天下的才力和学识。他们只有不断地从历史的宝库中汲取养分,提高资治能力,保持自身优势,才能在政治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新兴士大夫阶层不仅喜好研经读史,而且也有意识地将这种优良传统在各个领域内发扬光大,小到家庭教育,大到治国平天下,经史成了无所不能的制胜法宝。风气所及,不仅文臣熟读经史,就连武人也积极学习历代用兵成败之道及前世忠臣之节。名将狄青作战英勇,但无史识。范仲俺授以《左氏春秋》,他“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由是益知名”[4]9718。
宋代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也促进了史学研究的繁荣。外族的进犯,朝廷的退让,频繁的战与和,促使士人阅读史书,以史为鉴,从成败盛衰中汲取治国理乱的经验教训,从历代典制的因革损益中,为今天的措施规划寻找出路。形形色色的史著、史论好比士人从各自的角度开出的药方。同时,为了使良药不必苦口而利于病,宋人又对史籍的体裁进行创新与改进。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是“病”十七史的浩繁难读,袁枢著《通鉴纪事本末》又是“病”《资治通鉴》年代悠长,难辑一事首尾。纲目体的创造也是为了使《资治通鉴》更好地发挥历史惩劝的功能,体现朱熹“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9]196的思想。同时,还出现了以浅显易懂的语言改写的普及读物《三字经》《十七史详节》《十七史蒙求》《史学提要》等。司马光在编撰大部头《资治通鉴》以外,还写了简明通俗的历史读物《稽古录》,受到好评。总之,不管是深奥雅正的史学专著,还是浅显易懂的诸史蒙求,都为史学的推陈出新、经世致用作出了不同的贡献。
宋代还具备推广普及史学所必需的物质技术和经济条件:兴旺发达的造纸术与印刷术。印刷、造纸技术的不断改进,印刷成本的降低,使书籍大量印行,部头较大的史籍也变得容易流传,便于集中和保存。宋仁宗时就由政府汇刻十七史流播于世,史籍不再难求。庆历后,民间刻书业普遍兴起,各种史著刻本得以大量流行。官营印刷业更是发达,国子监在东京专门设有掌管印书的官署,史籍刻版甚广,像《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九朝通略》等也类多镂板,流布四方。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学者们的眼界,提高了他们的史学素养和著述兴趣。当时从中央的三馆、秘阁到州学、县学、民间书院等都藏书万卷,私人藏书家如宋敏求、叶梦得、晁公武、陈振孙等都坐拥书城。社会上读经诵史的风气随之而日益浓厚。这股读史以资治劝惩的思潮,上自皇帝本人、官僚世家,下到各级官吏和地主士绅,形成一个比唐代更为庞大且有一定文化教养的文人阶层,为史学著作及咏史诗创作的繁荣提供了极其优越的物质条件。
三、援史入诗,史论互鉴
宋代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加之印刷术、造纸术的进步,为史学发达提供了较好的条件,而科举考试的需要,历史知识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宋人也更加重视史学著作的撰修及史学教育。据《宋史·艺文志》及历代书目著录,宋代的史地著述数量甚夥,且质量上乘。史学从史官、史家的书本里解放出来,汇融到广大士人的学问和思想里,使他们的言论和作品具有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性。宋代始终尖锐的民族矛盾,使文人作品中爱国主义、抵抗侵略的内容占据主导地位。而这种爱国主义激情的抒发往往是和深沉的历史见解紧密关联的。这种鲜明的时代特点在咏史诗创作中表现得特别突出。
(一)评古论今,资治与蓄德兼有
宋代自皇帝大臣至方外高士皆喜论古今得失,资治蓄德的氛围空前浓厚。如:张方平晚与苏洵游,“论古今治乱及一时人物,皆不谋而同”[13]950;苏轼“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11]85;李廌“喜论古今治乱,条畅曲折,辩而中理”[4]13117;宋释觉范云“余世缘深重,夙习羁縻,好论古今治乱、是非成败,交游多讥诃之”[12]408。又乾道三年(1167),孝宗诏大臣洪迈夕对选徳殿,极论古今治乱之事。而大臣也建议孝宗为太子遴择师友僚属,“相与讲论古今治乱之理,他日民情吏事不患不知”[13]644。孙应时《胜果僧舍与叶养源论武侯出处作数韵记之》,论史而以诗记之。谢枋得“一与人论古今治乱国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跃自奋,以忠义自任”[4]12687。同时由于科举考试偏重策论,更直接影响到当时的文风。宋代文人将丰富历史知识、精辟凝炼的典故写入篇章,综览古今,气吞山河,不仅有力地表现了博大深邃的思想内容,而且收到了意境深远的艺术效果,形成了独特的时代风格。宋代重史的文化氛围、丰富的史籍、以史为鉴的思想不仅为咏史诗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创作素材和可资仿效的艺术表现手法,而且它所代表的史官文化心态也渗入到了诗歌中。
咏史诗借古抒发诗人情志,非宋代独有。然而宋人却能够一扫过去那种单纯吊古之幽情,变为蕴藉着现实内容的历史反思,并以清新的笔触,饱蘸爱国主义激情,谱写出一曲曲汹涌磅礴、动人心魄的壮歌。宋代文人援史入诗,入词,入文,入平话戏曲,无论在广度、深度上,还是在思想、艺术性上,宋前就是后来的明清也难以望其项背。历史总是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永远都在映射着当下处境中人们的情思。那些心胸阔大、关注现实的人,往往对历史也倍加关怀。大文豪苏轼的作品多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他不仅撰写了不少评古论今的史论文,而且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咏史诗。王安石也常通过咏史怀古之作,寄托政治抱负,如《商鞅》《范增》《张良》等。司马光极深厚的史学根基和文学素养使得《资治通鉴》成为史学和文学完美结合的范例,他还创作了不少咏史诗,纵论古今人物,其史学观点与《资治通鉴》基本吻合。陆游“集中十九从军乐”,多是以历史英雄作楷模。他在《书愤》一诗中备极推崇“出师一表真名世”的诸葛亮,寄托了出师北伐的理想。再如忠君爱国、义薄云天的文天祥,多青睐历史上的爱国志士,写《题苏武忠节图》《怀孔明》《颜杲卿》《二王》等诗,借史抒怀,既是在赞美古人,也是在自我激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就透露出他强烈而深沉的历史感。在北上燕京途中,他又作《刘琨》《祖逖》《许远》等诗,表达了对爱国英雄的赞美,抒发了不屈的爱国志节。如《祖逖》一诗云:“平生祖豫州,白首起大事。东门长啸儿,为逊一头地。何哉戴若思,中道奋螳臂。豪杰事垂成,今古为短气。”[7]43048赞美了祖逖闻鸡起舞,恢复中原的宏大志向,为其功败垂成而叹息不已。《集杜诗》是以诗补史的佳作,感情深沉,激昂顿挫。《正气歌》更是中华民族忠臣义士的光荣榜,激荡着一腔民族正气。这些也有力地证明了宋人历史知识的丰富与博通,以史为鉴的自觉性与普遍性。因为只有对史实了如指掌,并加以消化吸收、融汇贯通,才有可能运用自如。咏史诗是宋代史学经世致用、鉴古知今的一个侧面,说明史学的思想内涵与文学的表现形式经过高度有机的融合,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咏史论史,史咏与史评相彰
咏史诗是一种跨“文”“史”的“边缘”创作。从文学题材角度看,应归入集部,然而也有一些目录学家将其视为史著,归入史部,或单列为“史咏”一类,或并入“史评”,或附于史论著述之后,成为四部之中的两栖著作。如明高儒《百川书志》卷六史志三中列有“史咏”一类,著录元明人的咏史集6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在史部史评类收入顾正谊《顾氏诗史》、黄鹏扬《读史吟评》2种。《四库未收书辑刊》将史梦兰《全史宫词》、吴阆《十国宫词》、谢启昆《树经堂咏史诗》归入史部史评类。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史部“咏史之属”就著录清及近人的咏史集多达36种。阳海清编撰《中国丛书广录》在史部史评类列史咏之属,著录古代咏史集多达66种。可见,在学者眼里,咏史诗集具有与史评、史论相同的属性、功能和价值,并且在创作中互相借鉴,互相影响。
史论,即评论者对历史的总看法。宋代史论在继承褒善贬恶的优良传统下,特别强调治史为现实服务,在历史观上则否认汉唐史学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说。范祖禹《唐鉴》、孙甫《唐史论断》都明确地提出了借古讽今、以史为鉴的思想。同时,受史家实录精神的影响,诗论家甚至以“史才”作为评价咏史诗成败优劣的标准。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文学在塑造人物时,往往是抓住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事件大写特写,对不重要的东西则一笔带过,而且还善于运用多种手法比如语言描写、行动描写、心理描写、对比衬托、气氛烘托等来刻画人物。宋代咏史诗在刻画人物时当然也全面接受了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的影响,多剪裁最能突出人物个性特点或契合自己观点的历史细节,或浓墨重彩,或以偏概全,娴熟地驾驭史料为己所用,史传体、翻案体、史论体等体式大备。
宋人在文学创作中常以诗论史,藉以表达个人的史识。如苏轼的友人史经臣彦辅曾说:“阮籍登广武而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其名!’岂谓沛公竖子乎?”他对曰:“非也,伤时无刘、项也,竖子指魏、晋间人耳!”[14]7苏轼读李白“沈湎呼竖子,狂言非至公”之句,知白亦误会嗣宗语。他认为嗣宗虽放荡,本有意于世,以魏晋间多故,故一放于酒,不至以沛公为竖子。故赋《甘露寺》诗,感慨“聊兴广武叹,不得雍门弹”,将论史、读史之歧见纷争赋为咏史,自抒机杼,以释众疑。苏轼又云:“仆尝梦见一人,云是杜子美,谓仆:‘世多误会予诗。《八阵图》云:‘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世人皆以谓先主、武侯欲与关羽复仇,故恨不能灭吴,非也。我意本谓吴、蜀唇齿之国,不当相图,晋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吴之意,此为恨耳。’”[15]2119诗人以杜甫在梦境再现嘱托的形式,委婉巧妙地传达了他对老杜咏史诗所表现之史识的独到见解。苏轼又云:“咏二疏诗,渊明未尝出。二疏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谓既出而返,如从病得愈,其味胜于初不病,此惑者颠倒见耳。”[15]2114则是诗人对前人咏史的评价中独抒己见,与史论无异。
宋人颇喜评价历代咏史诗创作,多从其立意构思与史书记载相比较而言。如二程云:“王介甫咏张良诗最好,曰:‘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当此毎从容。’人言高祖用张良,非也。张良用高祖尔。……或问:‘张良欲以铁槌击杀秦王,其计不已疏乎?’曰:‘欲报君仇之急,使当时若得以铁槌击杀之,亦足矣,何暇自为谋耶?”[16]233二程赞美肯定了王安石咏张良诗的不凡的史识,心有戚戚焉。可见好的咏史诗,犹如简洁有力之史论,让读者回味无穷。
咏史诗所表现的史见、史识,有时也为史学家所用,发为史论。甚至有人认为史论言简意赅,较史事尤胜一筹。王义山曾云:“咏史有诗,人多言胡曾,不知左太冲、张景阳尤为东莱所取。”[17]33则认为左思、张协咏史诗中的观点为吕祖谦的史论所借用采纳。又刘攽《咏史诗》云:“自古边功缘底事,多因嬖幸欲封侯。不如直与黄金印,惜取沙场万髑髅。”[7]7310其说则完全脱胎于司马光的史论《论李广利》,认为武帝欲侯宠姬李氏之弟广利而使将兵伐宛,盖不欲负高帝之无功非侯之约。而军旅大事关系国安民生,欲徼幸咫尺之功,藉以为名而私其所爱,不若无功而侯之。则二论异曲同工。又王安石《张良》一诗云:“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于此每从容。固陵始议韩彭地,复道方图雍齿封。”[7]6725而胡寅认为汉业存亡在俯仰间,而留侯于此每从容焉。诸侯失固陵之期,始分信越之地,复道见沙中之聚,始言雍齿之侯。此论与王诗如出一辙,则是史论借用咏史之意。又刘克庄《赠防江卒六首》其四云:“身属嫖姚性命轻,君看一蚁尚贪生。无因唤取谈兵者,来此桥边听哭声。”[7]36182则是概括苏轼《代张方平谏用兵书》之意,认为皇帝只是看到战胜后的凯旋捷奏,拜表称贺,没有听到远方之民因战事而家破人亡,哭声遍野。又黄公度《汉高祖论》认为伤弓之鸟惊曲木,奔渴之牛急浊泥。项惊天下以弓,而帝饮天下以水。而冯必大《咏史》云:“亭长何曾识帝王,入关便解约三章。只消一勺清凉水,冷却秦锅百沸汤。”[7]34810则是夺黄氏之意而化用之。又叶绍翁《汉武帝》云:“殿号长秋花寂寂,台名思子草茫茫。尚无人世团圞乐,枉认蓬莱作帝乡。”[7]35141此论出于林之奇《武帝论》,认为武帝好长生不死之术,聚方士于京师,启巫蛊之祸,使皇后、太子、公主皆牵连而诛,可悲可笑!又陈傅良《论项羽》认为项羽戮子婴、弑义帝、斩彭生、坑秦二十万众而范增不劝阻,与秦、商鞅之行为何异?而钱舜选《项羽》云:“项羽天资自不仁,那堪亚父作谋臣。鸿门若遂樽前计,又一商君又一秦。”[7]42027与陈氏之论无异。总之,对于历史来说,文人发为韵语,则为咏史;形成文字,则为史论:二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与此同时,二者之间还相互借鉴,相得益彰。
一言以蔽之,在宋代发达的史官文化的影响下,不仅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读史、鉴史、修史、论史、咏史、记史之风,而且增强了宋人重史思想、史官意识和创新精神。具体在咏史诗创作中的表现是以史为鉴,翻案求新,咏史、史论、史评互相借鉴。并成功地完成了由叙史言志到论史鉴世,从资政劝诫到童蒙教育,从文人雅赏到市井娱乐的功能转换。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司马光.资治通鉴[M].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76.
[3]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范祖禹.唐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6]朱熹撰,清圣祖批.御批资治通鉴纲目[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
[7]傅璇琮.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9]黎靖德.朱子语类[M].王星贤,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苏轼.东坡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91.
[11]苏轼撰,施元之原注,[清]邵长衡删补:施注苏诗[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
[12]释觉范.石门文字禅[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
[13]王十朋.王十朋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4]苏轼.东坡志林[M].青岛:青岛出版社,2010.
[15]苏轼.苏轼全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
[16]程颢,[宋]程颐撰,王孝鱼点校.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7]王义山.稼村类稿[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
[责任编辑、校对:王兴全]
On the Historiographer Cultural Background Behind the Prosperity of Historical Poems in the Song Dynasty
ZHANG Huɑnlinɡ1,2
(1.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Media,Zunyi Normal University,Zunyi Guizhou 563002;2.Center for Post-doctoral Studie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Sichuan 610064,China)
As the historiography in the Song Dynasty history was developed,the historical records compiled at that time provided excellent history textbooks for the literati,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education and the prosperity of the historical poems creation.Moreover,the cultural ideology of the historiographer penetrates into the historical writing,making the historical poems gradually integrate with historical criticism,historical comments and other history-recorded styles in the process of the acceptance and spread.Thus,it successfully achieved the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from expressing one’s aspiration to enlightening the world,from exhorting capitalists and politicians to educating the children,from serving as literati taste to the ordinary entertainment.
Historical Poems;Historiographer Culture;Historical Comment;Criticism
I206.2
A
1009-8666(2017)10-0020-06
10.16069/j.cnki.51-1610/g4.2017.10.004
2017-04-1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古代咏史诗集整理与研究”(13XZW010)
张焕玲(1976—),女,河南南阳人。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2014年9月入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科研流动站研修,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及古典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