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杯换盏
晓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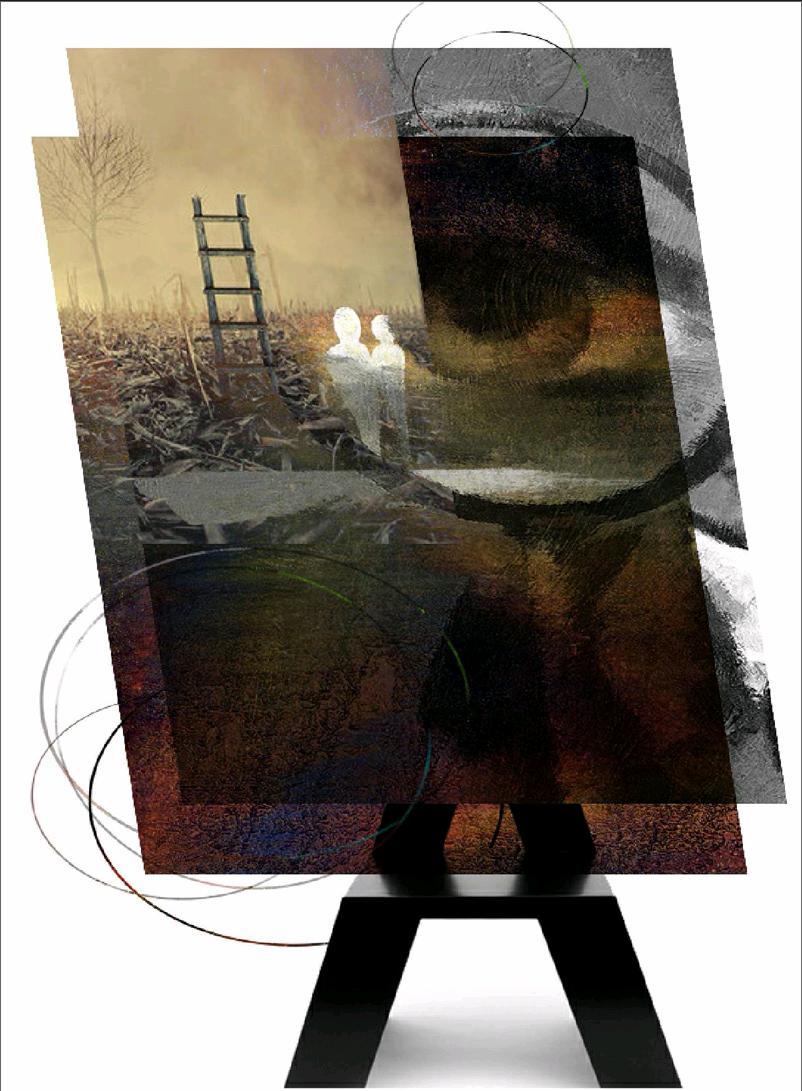
1
下雪的那天早晨,我睡到八点多才从床上爬起来。打从毛英跟王羊跑了以后,我每天都叉着胯子睡懒觉,再也没起过早床。老婆都跟别人跑了,我还起那么早搞啥?再说,搞啥都没得意思。
那场雪,真他妈下得大。我起床后推窗一看,满眼都是白花花的。地上的雪已堆了尺把厚,像铺了一床棉絮。我心里想,肯定是哪个狗日的给老天爷戴了一顶绿帽子,把老天爷气疯了。老天爷一气之下就把他床上的棉絮给扔下来了,一家伙扔到了我们油菜坡。
气温降得厉害,少说也到了零下三度。我本来想出门屙泡尿的,可我刚把脑壳伸到门外,马上又缩进来了。外面冷得要命,还刮着风。风如饿狗一般吼着,好像要扑上来啃老子的脸。我赶紧关了门,然后把尿屙在了一个木盆里。这个木盆是用来洗脚的,但我好久都没用它了。回想起来,我差不多有半个月没洗过脚了。毛英在家时,我天天都洗脚。她跟王羊跑了以后,我就懶得每天洗了。我想,晚上睡觉时脚头连个女人都没有,脚还有个屌的洗头!
屋里也冷得要命,手脚都冻麻了。我赶忙从厨房抱来一些劈柴块子,把火房里的火炉烧燃了。火炉烧燃后,火房里的温度一下子就升了起来。我搬来一把椅子,紧挨着火炉坐下,将双手伸到火炉上烤,像烤两只茄子。烤了一会儿,我浑身上下都不冷了。我觉得火炉真是个好东西,比老婆要好得多。它不光让我感到暖和,还不用担心它跟别的男人跑了。
毛英是阴历八月十六那天跟王羊跑的。这个日子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头一天是中秋节,王羊的老屋正好在那天夜里失了火,连床和被窝都烧光了。失火的第二天,毛英就不见了影子。我想她肯定是跟王羊跑了。开始,我还以为他们去了宜昌的九女沟。九女沟有个磷矿,王羊过去常年带一班人在那里挖磷。我前两年也去九女沟挖过磷,毛英还在那里煮了一年饭。毛英跑了以后,我立即赶往九女沟去找她,但没找到。后来,我才听说她跟王羊去了河南的平顶山。平顶山有很多煤矿,王羊从前曾去那里挖过煤。我本来还想追到平顶山去找毛英的,但路途太远,加上手头缺钱,所以就没能成行。
那天,我一直都待在火房里偎着火炉烤火,连厨房都没去。火房的墙脚下堆着一些红薯,我的早饭和中饭都是烤红薯吃的。红薯放到火炉上一烤,香得不得了,我每一顿都吃好几个。不过,红薯烤了虽说好吃,但吃多了胃受不了。下午四点钟,我的胃就开始折腾起来。它先是胀气,接着就往上反酸水,害得我不住地打嗝,还吐了好几次。我的胃本来就不好,到了五点钟,它居然疼起来了。直到这个时候,我才不得已去了厨房。
进到厨房后,我打算用白菜煮一碗面条吃。我喜欢用白菜煮面条,又简便又清淡,吃了又养胃。扫兴的是,厨房里没有白菜,我翻箱倒柜找了好半天,连一片白菜叶子也没找到。其实,我家的白菜多得很,只是都长在地里。按说我可以现到地里去砍一棵回来,但外面实在太冷了,我想去砍又不想去砍。正犹豫不决,我的胃又猛烈地疼了一下,像针戳的。它这么一疼,我就不再犹豫了。我想,即使冷死,我也要去地里砍一棵白菜回来煮面条吃。
开门出去,我的两眼一下子就傻了。到处都是雪,远处的山梁,近处的水沟,还有周围的田,都埋在了雪下面。门前的那条公路,也不见踪影了。
菜地在房子旁边,也被雪严严实实地盖住了,连菜的一点影子都看不见。我恍惚了一会儿,还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过去。我把镰刀咬在嘴上,双手扒了好半天,才从雪窝里扒出了一棵白菜。
我砍了白菜往回走,快到门口时,身后忽然传来一声喇叭响,吓我一跳。我连忙扭头去看,只见公路那边开过来一辆红壳子客车。它开得很慢,像一只蜗牛在雪地上爬。车轮在雪路上滚动时发出刺耳的摩擦声,我一听就知道是上了防滑链。这趟车我认得,是从襄阳开过来的,一直要开到老垭镇。在我的印象中,这趟车从我门口经过时一般都不停,总是他妈的一晃就过去了。奇怪的是,它这天却有点儿反常,竟然在我门口停下了。
车刚停稳,就下来一个人。那家伙是从车上滚下来的,像滚一个麻袋,一直滚到公路的边沟上才停住。停住以后,那家伙好久都没有动弹。我压根儿没想到那是个人,还以为是从车上掀下来的一袋垃圾。大约过了十分钟,那家伙才强撑着从地上坐起来。直到这时,我才发现他妈的是个人。
天色已有些昏暗了,我看不清那家伙的脸。不过,看块头和动作,我能断定那家伙是个男的。他一坐起来就开始吃雪,好像刚从饿牢里放出来的,抓起雪就往嘴里塞。他吃得咯嘣咯嘣响,听起来像是在吃糖。猛吃了一阵子,他陡然住了手,嘴也住了,仿佛喉咙管子被啥东西卡住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过劲儿来。然后,他把双手撑在地上,弓着腰,耸着肩,想站起来。可是,他四肢无力,挣扎了好半天也没站起来。
按理说,我应该去公路边拉他一把的,但我没去多管这个闲事。雪还在一个劲儿地下,寒风刮得呼呼作响,我的手和脚都冻僵了。再说我也饿了,肚子里的螬虫叫个不停,胃也越疼越凶了。我急着赶快进屋,要进屋烤火,还要抓紧用白菜煮面条吃。可是,我刚一转身,那家伙却猛然喊了我一声。
陶贵!他是这么喊的。
谁在喊老子?我一边回头一边嘟哝。
那家伙说,我是王羊,快来拉我一把。
我先是大吃一惊,然后骂道,妈的,原来是你狗日的!
王羊伸出两只手,不停地向我招着,显然是指望我去把他拉起来。但老子没理他。我才不会去拉他呢。这个狗日的,不光给我戴了绿帽子,还把我老婆勾引去了河南的平顶山,害得我在家里打了两个月的光棍。这两个月来,我差不多每天都会想到王羊。一想到这狗日的,我就恨不得吃他的肉。
见我站着不动,王羊把手招得更快了,嘴里还一声接一声地喊我的名字,好像老子是他的一根救命稻草。但我还是没动,稳如泰山。他狗日的也不想一想,我咋可能去救他呢?即使他快要冻死在雪窝里,我也不会去救他的。说句不该说的话,我还巴不得他被冻死呢!
早在前年春天,毛英去九女沟磷矿煮饭的时候,王羊就把绿帽子给老子戴上了。那阵子,我正在筹钱盖楼房。如果不是想跟着王羊挣一笔钱,我当时就不会轻饶他。接下来的一年多,我忍气吞声,装聋作哑,差点儿把肠子都憋断了。直到去年秋天楼房盖好时,我才跟王羊撕破脸。我警告他说,你要是再跟我老婆打皮绊,小心老子要你的命!打那以后,王羊一直待在九女沟,大半年没跟毛英来往过。可是,狗永远改不了吃屎的本性。今年中秋节,王羊突然回到了油菜坡,一回来就把毛英约到了他的老屋,两个人又打起了皮绊。我在床上捉住他俩时,肺都气炸了。当时我手上拿着刀,要不是怕杀人抵命,我当场就会一刀捅死他。谁想到,我放了他一马,他狗日的不但不领情,反而还把我老婆勾跑了。
王羊还在对我招手,一直招个不停。我仍然没理他,站在门口一动不动。不过,我没再急着进屋。 说来有些奇怪,一见到王羊,我身上猛然就不觉得冷了,胃也好受了一些。
认出王羊后,我心里还一下子生出了许多疑问。王羊把毛英勾跑之后,村里有人对我说,他打算去平顶山挖一个季度的煤,想挣笔钱回来把烧毁的老屋修补一下,最早要到过年才能回油菜坡。眼下刚刚进入冬月,离过年还远得很,我不晓得他为啥这么早就跑回来了。更让我想不通的是,毛英呢?她不是跟王羊一起跑的吗?为啥她没回来?本来,我想去问一下王羊的,他肯定能回答我的这些问题。但我想了想,还是没去。主要是,老子不想理睬这个狗日的。
这时,我的胃又疼了一下。我想,我必须赶快进屋煮面条吃,再也不能拖了。我也没工夫去管毛英。她既然跟王羊跑了,回不回来都不是我的事。假如她到时候万一回不来,我会找王羊要人。这么想着,我就推门进屋了。进屋以后,我又回头朝公路上看了一眼。我看见王羊还在向我招手。招个屌!我自言自语地说。说完,我就把门扑通一家伙关上了。
2
陶贵这王八蛋,心够狠的。我跟他招了半天手,手都快招断了,他也不来拉我一把,还一转身进了屋。看来,他是巴不得我被冻死。
我晓得陶贵恨我。前年春天,在九女沟磷矿上,我和毛英打上了皮绊。因为我给陶贵戴了一顶绿帽子,所以他就对我怀恨在心。但我没想到的是,他会把我恨到这个地步。我虽然睡了他老婆,可我并没有白睡。且不说我给毛英买了多少衣裳和首饰,也不说我送了多少烟和酒给陶贵,单说他现在住的这栋楼房,至少有我王羊一半的功劳。不看别的,只看在这栋楼房上,陶贵也不该这么对我,居然见死不救。
天眼看着就要黑了,雪还在筛糠似的下。我想,我必须尽快从雪窝里爬起来,不然真要冻死在这里了。我咬紧牙关,全身使劲,拼命地往上撑。可是,我的手和脚全是麻木的,像安上去的假肢,一点儿都不听我的使唤。折腾了好一阵子,我还是没爬起来。
我不光是冷,还饿得要死,前胸都贴到后背了。清早,我离开平顶山的时候,啥也没吃。那会儿天刚麻麻亮,车站附近的餐馆都还没开门。不过,即使餐馆的门开了,我也没钱吃。到平顶山挖了将近两个月的煤,我还一分钱的工资都没弄到手。身上剩下的几个钱,勉强只够我买车票。中午在襄阳转车时,我饿得两眼直冒金星。车站旁边有个巷子,小吃店一个挨一个,卖啥的都有,可我只能站在远处看,一边看一边吞口水。快上车时,有个人买了几根油条,不小心掉了一根在地上。他嫌脏没捡,我便赶紧跑上去捡了起来,连灰也没吹就塞进嘴里吃了。要不是那根油条,我说不定早就饿昏过去了。
陶贵真是绝情,看见我在地上抓雪吃,也不同情我一下。不说把我叫到屋里去吃顿热饭,他起码也该扔个冷红薯啥的给我填填肚子。不管咋说,我都是对得起他的。要不是我出钱帮他建这栋楼房,他至今都还住在从前的土屋里。
当然,错误首先出在我身上,我不该给陶贵戴绿帽子。不过话说回来,我和毛英打皮绊这件事,最先还是陶贵牵的线。前年春节过后,我从油菜坡带一班人去九女沟挖磷,陶贵也跟我去了。起初本来没有陶贵,临走时他却突然找到我,要我一定把他带上。他说,他家的土屋快塌了,想出门挣点钱回来盖栋楼房。我这人心软,听他说得可怜巴巴的,就带上了他。刚到九女沟那阵子,我们都在矿上的食堂吃饭。食堂的饭死难吃,还贵得要命。不久,我便决定找个煮饭的,打算我带的这班人自己开伙。我一说要找人煮饭,好几个人都推荐自己的老婆。陶贵最积极,猛夸毛英的手艺好,还说她能把素菜弄出荤菜的味道。他一边夸一边给我上烟,并且亲自给我点火。就这样,我同意了毛英去煮饭。
毛英的手艺的确不错,特别会烧茄子,吃起来像五花肉。她的相貌其实长得一般,只是屁股又大又圆,撅起来洗菜的时候,看上去就像一匹母马。她也很勤快,经常帮我洗衣裳。不过,毛英到九女沟的头两个月,我并没有打她的主意。两个月过后,陶贵请假回油菜坡掰苞谷。就在那个空里,我和毛英打上了。事情说起来很简单。有一天,我吃过晚饭后没马上离开厨房。当时别人都走了,毛英正撅着屁股在灶前洗碗。我从后面蹿上去,试探着在她屁股上摸了一把。她没有躲闪,也没骂我。这样一来,我的胆子就大了。摸了—会儿屁股,我就得寸进尺脱她的裤子。长裤脱得很顺利,脱到短裤时,她突然丢下碗,用她的手把我的手挡住了。
别慌,我有个条件,你得先答应我。毛英说。
我问,啥条件?你说吧。
你每个月给我加三百块钱的工资。毛英回过头说。
我爽快地说,没问题,从这个月就给你加。
厨房里支着一张简易床,毛英每天晚上都住在那里。我答应她的条件后,她立刻把手松了。我一边喘气,一边脱了她的短裤,然后就把她抱到了床上。
我又在地上抓雪吃了,一连吃了四五把。雪其实不是个好东西,越吃越冷,我感觉我的肠子上都结了冰。说实话,我真想忍着不吃,可我忍不住。肚子饿得实在太难受了,好像不吃马上就要饿死。
本来,我可以不在陶贵门口下车的。班车再往前开一段,就是一栋半新的楼房,也是我从前的家。我和老婆离婚后,新楼虽然归了她,但我要是去了,她也不会坚决把我拦在门外。如果我死皮赖脸地求她,她最终还是会让我进屋,并给我弄点吃的。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们毕竟一起生活了十几年。在没发现我和毛英打皮绊之前,老婆对我一直很好。事情暴露后,她虽说一怒之下跟我离了婚,但我们的感情并没有完全破裂。再说,那新楼也是我一手盖起来的。离婚的时候,我本想留一两间给自己住,但又想婚都离了,还住在一栋楼里多别扭。这么一想,我就把新楼全都给了老婆,自己住进了以前的老屋。不过,老屋暂时是回不去了。它在两个月前被火烧了。要不是老屋遭了火灾,我也不会去平顶山挖煤。
我之所以在陶贵门口下车,是我有重要的事情跟这个王八蛋说。当初,毛英跟我一道去平顶山,陶贵肯定以为是我把她勾跑了。现在我一个人回来,毛英卻留在了那里。这中间的情况,我必须跟陶贵说清楚。不然的话,他到时候绝对会找我要人,弄得不好还会让我吃不了兜着走。
陶贵长两片厚嘴唇,还长着一口宽牙。他看上去一副憨样,实际上精得很,比他娘的王八还精。我和毛英打皮绊的事,他其实很早就晓得了。但他一直都忍着不作声,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故意装傻。
在九女沟时,我带的那班人都住在一个木板屋里,只有陶贵和毛英住在隔壁的厨房。每隔几晚,陶贵都要到木板屋斗一次地主。他一来,我就趁机溜到厨房去找毛英。头几回我还有些紧张,老是担心被陶贵捉住。后来毛英说,你别慌手慌脚,他中途不会回来的。听她这么说,我才放了心。去年秋后,陶贵和毛英离开九女沟,回到油菜坡盖楼房。在他们盖房期间,我回来过七八次,每次回来都要瞅空跟毛英睡上一觉。有一天晚上,我和王英躲在盖房工地上的窝棚里睡,正睡到兴头上,我老婆突然来了。当时,陶贵正在窝棚前吸烟,我老婆一来就问,你看见王羊没有?陶贵想也没想就说,没看见。事实上,我进窝棚时,陶贵分明看见了。
那晚要不是陶贵出面挡驾,我肯定被老婆抓个现行。从窝棚里出来后,我连忙跑到附近杂货铺,给陶贵买了一条烟和一瓶酒。陶贵从我手上接过烟酒时,一点儿客气也没讲,好像我是应该给他买的。烟酒到手后,陶贵忽然跟毛英说,水泥用完了,明天再不买,后天就要停工。他一边说一边拿眼睛扫我,仿佛我欠他的水泥。第二天,我只好买了一车水泥,乖乖地送给了他们。其实在那之前,我已经给了毛英五万块钱,还送了他们一车钢筋。
我没料到,陶贵这王八蛋后来会突然跟我翻脸,说翻就翻了。事情发生在去年冬天,说具体一点,就是在陶贵楼房完工的那天晚上。楼房盖好了,村里人都去祝贺,送礼的送礼,放鞭的放鞭。陶贵和毛英高兴得嘴都合不拢,还请了喇叭班子,酒席从清早一直摆到天黑。我那天也到了场,还跑前跑后地帮他们招待客人,又是上烟又是倒茶,腿都差点跑断了。
那天吃过晚饭,客人们都陆陆续续走了,只有我没马上离开。我喝醉了,想等酒醒一醒再走。陶贵也喝醉了,醉得比我还厉害。我醒过来的时候,他还歪在桌子边,像一堆烂泥。毛英当时已收拾好碗筷,刚解下腰里的围裙,露出了她那个又大又圆的屁股。一看到她的屁股,我的身子一下子就硬了起来。我饿狼般地扑上去,像扛麦捆一样将毛英扛到肩上,直接扛进了二楼的客房。那晚我和毛英都有点儿性急,一进门就上了床,连门都没顾上反锁。谁也没想到,陶贵那么快就醒了,更没想到我老婆那会儿会来。进到客房不到半个钟头,外面突然响起了脚步声。当时我和毛英刚完事,衣裳都没来得及穿。我急忙抓过裤子,刚穿上一半,客房的门就被陶贵一脚踹开了。接着,我老婆就冲了进来。
陶贵这个王八蛋,真是翻脸不认人。他那晚一进门就甩了我一耳光,还朝我裆里踢了一脚,险些把我的卵子都踢破了。我从来没发现陶贵这么凶,当即吓得屁滚尿流,提着裤子就跑。我跑的时候,陶贵还在后面追,一边追一边骂我。他一直追到门口才停下来,然后恶狠狠地对我说,你今后不许再来我家,要是再来,老子打断你的腿!
打那以后,我就接二连三地倒起霉来,先是老婆跟我离了婚,后来老屋又失了火。那场火烧得特别凶猛,不仅烧了我的衣裳,烧了我的粮食,烧了我的铺盖,还差点连人也烧死了。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如果没有雪光,我肯定伸手不见五指了。雪还在下,风还在刮。我越来越冷,也越来越饿。后来,我决定四肢着地,爬到陶贵的门口去,不然就真要死在雪窝里了。
3
我吃完白菜煮面条,刚放下碗,忽然听见有人敲我火房的门。敲门声很急促,吓我一大跳。我没有马上去开门,疑惑地问道,谁呀?门外回答说,是我。他的声音细若藕丝,听起来像一个快要断气的人。
我急忙从火炉边走到门后,抬起手正要开门,心里猛然想到了王羊。我想,该不会是王羊这狗日的在敲门吧?这么一想,我抬起来的手很快又放下了。愣了一会儿,我绕到窗户边上,借着屋里的灯光朝窗外看了一眼,果然看见了王羊。他趴在我家门口的台阶上,看上去像一只癞蛤蟆。
王羊的手上和脚上都是雪,两个膝盖上也是,显然是从公路上爬到我家门口来的。我觉得王羊真是不要脸,明知我不爱见他,居然还好意思往我家门口爬。不过,我也有些好奇,不晓得他爬到我家门口来搞啥。但我没开门,不想让他进我的屋。我扭头回到了火炉旁,顺手往炉子里加了一块劈柴。
可是,王羊脸厚,一点儿也不知趣,还在一个劲儿地敲我的门。我在心里暗暗地说,敲吧,你就是把手敲出血,老子也不会给你开门的!但他仍然不停地敲着,还一边敲一边哀求说,陶贵,让我进屋吧,我又冷又饿,好像快要死了。我干笑了一声,然后幸灾乐祸地说,死了算毬!像你这种打皮绊的家伙,早就该死了,死了世上少一个祸害!我这么一说,敲门声陡然停了下来。我想,王羊这一下总该死了心。然而我想错了,没停多久,他又开始敲起门来。
我有些心烦地说,别再敲了,你快点给老子滚开,要死滚到别处去死!
王羊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知道你希望我死,但我想在死之前跟你说几句话。
你要说啥?我问。
毛英出事了!王羊说。
王羊话音未落,我的心不由猛地往下一沉,仿佛一只鸟被枪打中,眨眼间从悬崖上跌进了万丈深渊,摔了个稀巴烂。我感到我的脑壳也摔破了,像西瓜一样裂开了花。我一下子晕 了,两眼发黑,浑身瘫软,有一种天塌地陷的感觉。
我对毛英的感情,说起来有些复杂。她勤劳,灵活,顾家,人也长得富态,能找到她做老婆,算是我陶贵的福气。那年去九女沟煮饭时,她和王羊打上了皮绊。我发现后虽说心里很难受,但一想她是为了盖楼房筹钱,就原谅了她。我当时只骂了她几句,连巴掌也没打她一下。那会儿,我以为她只是和王羊逢场做戏,压根儿没料到她会动情。楼房盖好以后,我让毛英立刻与王羊断绝关系,她满口答应了,还给我点了头。可是,只断了半年,她又跟王羊死灰复燃了,并且还主动把自己送到了王羊的老屋。那天晚上,我实在忍无可忍,就打了毛英一顿。谁知,打她的第二天,她居然不声不响地跟王羊跑■。毛英一跑,我就開始恨她了,还盼着她出点啥事才好。没想到的是,一听说她真的出了事,我却一下子紧张得要命。
约莫过了十分钟,我才镇定下来。我再一次走到门后,颤着嗓子问,我老婆咋啦?王羊却说,你先让我进屋,我再告诉你。这个狗日的,还跟我讲条件呢!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只好答应王羊,开门让他进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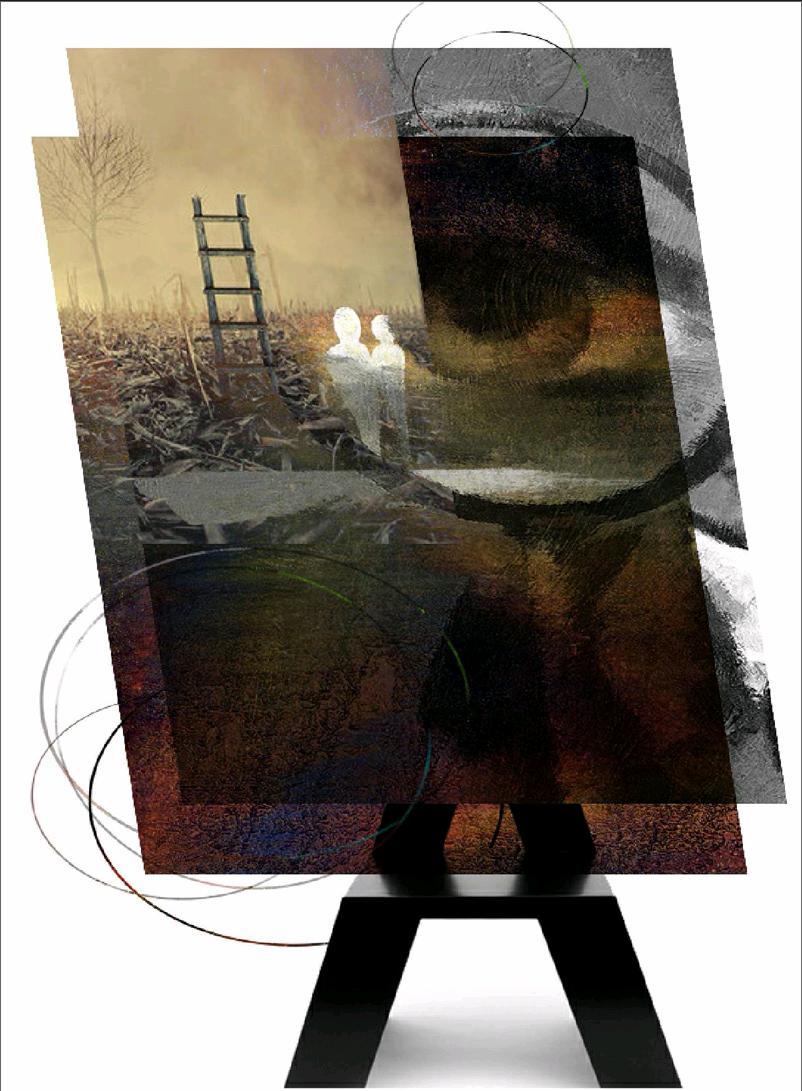
王羊是爬着进屋的。他一进门,我就迫不及待地问,毛英出了啥事?王羊没回答我,直接爬到了火炉跟前。他脸色苍白,嘴唇乌黑,眼皮子垮着,似乎只剩下了最后一口气。他在火炉边停下来,好半天没动,只是嘴巴张开了一条小口,默默地吸着从火炉里冒出来的热气。烤了许久,王羊的眼睛才睁开了两道细缝。但他没看我,目光一下子落在了我刚才吃面条的那个碗里。碗放在火炉边的茶几上,一根面条也没有了,只剩下半碗汤。我这时又问,毛英到底出了啥事?王羊仍然没回答,好像没听见我的话。他猛然伸出一只手,端起了那个碗。他小心地把碗移到嘴前,一口气将那半碗汤喝光了。
喝下半碗汤,王羊身上陡然来了一股劲。他双手扶着茶几,腿脚使劲撑了几下,竟然站起来了。但他体力不支,有点儿站不稳,不停地晃来晃去,像一株风中的芦苇。幸亏我及时搬来一把椅子,不然他又会一屁股瘫在地上。
王羊在椅子上坐稳后,带着一丝感动对我说,难为你了!他说得很诚恳,还用柔软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但我没领他的情,突然感到有点儿后悔。我冷冷地对他说,其实我不该给你搬这把椅子的。王羊一愣问,为啥?我直截了当地说,像你这种人,就应该一直趴在地上!他问,凭啥?我说,因为你睡了我老婆!听我这样一说,他就不吱声了,像是被我的话噎住了嗓子眼儿。
沉默了一阵儿,我又想起了毛英。你快告诉我,我老婆究竟出了啥事?我盯着王羊的脸问。王羊忽然吐了—口清水,然后用商量的口气跟我说,陶贵,你能给我弄点吃的吗?等我不吐清水了,再细细地跟你说毛英的事。我冷笑了一声说,嗬,你屁事还不少呢,刚才不是喝过面汤吗?王羊露出一脸苦笑说,我一整天没吃东西,半碗面汤不顶事呀,刚一喝下去就被螬虫抢跑了。他说着,又吐了一口清水。
看着王羊饥饿难耐的样子,我有点哭笑不得,还有些左右为难。我低头想了想,然后抬起头说,这样吧,你先跟我说毛英的事,说完我烤个红薯给你吃。我一说到红薯,王羊的两只眼睛顿时胀大了一圈,还闪出了两道绿光。他一边吞涎水一边问我,红薯呢?你先给我吃红薯,我一吃完就跟你说毛英。这狗日的,还在跟我讲条件。我一听火就来了,马上板着脸说,你想得倒美,不说毛英的事,就别想吃老子的红薯!王羊的脸一下子红了,有气无力地说,我实在是饿了,连说话的劲儿都没有了。再说,毛英的事也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王羊这么一说,我的态度又软了下来。犹豫了一会儿,我便走到墙脚下,拿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红薯。
我本想把红薯烤熟了再给王羊吃的,但我刚把它放到火炉上,王羊就一把抢过去了。接着,他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连皮都吃毬了。
吃了红薯,王羊立刻就有了劲儿,说话的声音也大了。他还算爽快,没等我催就主动说起了毛英。不过,他是从他们离开油菜坡的时候开始说起的,听起来有些啰嗦。我说,你直接说毛英现在的情况吧,扯那么远做啥?王羊说,你别慌嘛,事情必须从头说起,不然说不明白。没办法,我只好耐着性子听他说。
王羊说,在中秋节之前,他并没想过要去平顶山,打算过完节还回九女沟。平顶山煤矿上虽说工资结算快一些,但离家太远,而且下井特别危险,不是透水就是瓦斯爆炸,随时都会送命。相比之下,他还是更愿意在九女沟挖磷。我问,那你为啥没回九女沟?王羊迟疑了一下说,毛英让我去平顶山。我一愣问,她为啥给你出这个主意?王羊说,毛英嫌九女沟磷矿结账太慢,希望我尽快去平顶山挣笔钱回来,好早点把失火的老屋修一下。更主要的是,毛英想跟我一道出去,但九女沟太近了,担心你跑去找她扯皮拉筋。她说平顶山远在河南,你绝对不会找到那里去。听了王羊这番话,我好像突然掉进了一个醋缸里,身上的每一块肉都酸了。
我好半天说不出话来,有点儿恼羞成怒。过了许久,我才平静下来。我质问王羊,毛英为啥突然要跟你跑?王羊想了一下说,这你应该比我清楚。我厉声说,她是跟你跑的,我清楚个屁!你从九女沟回来之前,她跟我过得好好的,一点儿跑的兆头也没有。你一回来,她就跟你跑了,肯定是你勾引她!王羊否认说,我没勾引,是她主动的。我打个哈哈说,笑话,你不勾引,她会跟你跑?王羊说,我真没有勾引她。她提出跟我去平顶山,是有原因的。我连忙问,啥原因?王羊说,你晓得!我先怔了一下,然后说,我不晓得。王羊直直地盯着我问,你是真不晓得还是假不晓得?我嘴一硬说,真不晓得。王羊说,既然你真不晓得,那我就直说了。
王羊开口就问,你还记得我老屋的那场火吗?我说,咋会不记得?它把天都烧红毬了。王羊说,那场火烧得很蹊跷,它早不烧晚不烧,偏偏在你抓住我和毛英的那天晚上烧了起来。我扩大嗓门问,你狗日的啥意思?王羊古怪地笑了一下说,我怀疑是有人故意放火。我赶紧问,谁放的?王羊瞪着我说,这我不能乱说,但只要派出所去查,一查就能查出来。我问,那你为啥不去报警?王羊说,我本来要去报警的,但毛英不让我报。开始我没听她的,坚持要去派出所。后来她居然给我下跪了,求我千万别去报警,还说她已决定陪我去平顶山挖煤,帮我挣钱回来修老屋。她一直跪在地上求我,我不答应她就不起来。没办法,我只好不报警了。
我压根儿没想到毛英曾给王羊下过跪。要是王羊不说,我还真不晓得有这么一回事。听王羊说了以后,我不禁恍惚了一阵儿,像喝酒喝醉了,感到头重脚轻,眼前黑黢黢的。
过了好久,我才回过神来。我有些不耐烦地对王羊说,别再跟我扯那些陈谷子烂芝麻了!你直接告诉我,毛英到底出了啥事?王羊说,你不要慌嘛,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
4
我一說到老屋失火的事,陶贵这王八蛋就显得很紧张,两眼像老鼠似的东张西望,额头上的汗都冒出来了。
陶贵急于知道毛英现在的情况,但我没办法马上告诉他。我刚才一口气说了老半天,肚子里的那个红薯早已消耗完了。我问陶贵,你还有红薯吗?再给我吃一个,我又饿得没劲儿说话了。这一回,陶贵还算不错,二话没说就起身给我拿来了一个红薯,比上一个还大。他把红薯递给我之后,又给我倒了一杯开水,还客气地对我说,一边喝水一边吃吧,别把喉咙卡住了。
进屋之前,我浑身冻得僵硬,连鼻孔也堵毬了。喝了一杯开水,鼻孔猛地通了。这时,我闻到了一股尿味,臭得呛鼻。我用手扇着鼻孔问,啥味这么臭?陶贵红着腮帮子说,尿。我一怔问,屋里咋会有尿?陶贵指着一个墙角说,外面太冷,我把尿屙在脚盆里了。我顺着他的手看过去,果然看见了半盆尿。我冷笑了一声,觉得这王八蛋太不像话了。我本想把他臭骂几句,但想了想,还是忍着没骂。吃了两个红薯,我身上又有了一些力气。我很快站起身来,将那盆尿端到门外倒了。
陶贵没想到我会给他倒尿,一下子愣住了。我倒完尿进来,他马上给我上了一根烟,看我时的眼神也变得柔和了。接着,他又给我倒了一杯开水。
我重新坐到火炉边,先喝了一大口开水,然后一边吸烟一边讲毛英去平顶山之后的事情。陶贵听得很认真,两个耳朵都竖起来了,像一只野兔。
五年前,我去平顶山挖过一年煤,还在那里结识了一个姓储的洞长。储洞长是河南人,每顿都吃面食,每顿都要喝酒。要是哪顿没有面食和酒,他连桌子都懒上。为了讨好他,我经常买点面条和酒给他送去,还口口声声叫他大哥。他很讲义气,把我当他的小兄弟看,每月都要多发我几百块钱的工资。后来离开了平顶山,我和他一直都有电话联系。
陶贵问我,你们这次去平顶山,碰到储洞长没有?我说,肯定碰到,我们这次就是冲着他才去的。从油菜坡出发之前,我就给储洞长打过手机。他说,你来吧,我的洞子里正缺人呢。打手机的时候,我没告诉他我带了毛英。到了平顶山,他看见我身后跟一个女的,不由一愣问,她是你什么人?我灵机一动说,她是我老婆,也想来你这儿打工。
说到这里,我特意停下来,悄悄地看了陶贵一眼。这个王八蛋,他的脸居然一下子黑,黑得就像电视里的包公。我连忙解释说,如果不说毛英是我老婆,我怕储洞长不安排她做事。过了好一会儿,陶贵的脸才恢复正常。
储洞长听说毛英是我老婆,马上皱起眉头说,女人是不能下井的。我连忙说,大哥,你能不能让她去食堂煮饭?她的面食做得特别好吃。说完,我快步走到他跟前,赶紧把事先准备好的一瓶白酒给了他。储洞长接过酒,看着毛英说,食堂本来不差人手的,既然你这么远来了,就先到食堂帮忙吧。我和毛英都非常感激,觉得这个大哥够意思。到平顶山的当天晚上,储洞长还把我和毛英请到他住的地方坐了一下,又是上烟又是泡茶,还给毛英吃了两个橘子。
陶貴这时插嘴问,储洞长不和矿工们住一起吗?我说,他五年前是和矿工们一起住的,都住大工棚。从去年起,他在洞子附近租了一间民房,搬出去一个人住了。陶贵又问,你和毛英晚上住哪里?我先支吾了一下,然后如实回答说,头一个月,我在大工棚里住,毛英和另外两个煮饭的女工住在食堂里。从第二个月起,我们也在外面租了一间民房。我的话刚说出口,陶贵这王八蛋就生了气,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这个狗日的,真是不要脸!我没有还嘴,只顾默默地吸烟。
到平顶山的第二天,我和毛英就上班了。我下井挖煤,她到食堂帮厨。储洞长很大方,答应每个月给我五千块钱的工资,给毛英三千。他还承诺说,每个季度结一次账,绝不拖欠。我当时喜得要死,心想,等干到过年回家,修老屋的钱就差不多够了。
陶贵性急地问,那你为啥没到过年就回来了?我压低嗓门说,因为毛英出了事!陶贵陡然提高声音说,她到底出了啥事?你快点说出来,别老是让我的心悬在半空里。他显得很不安,仿佛一只热锅上的蚂蚁。我看得出来,陶贵对毛英的感情其实还是很深的。我能理解陶贵。将心比心,连我这个打皮绊的都对毛英有感情,何况他和毛英还是多年的夫妻呢。
老实说,我对毛英的感情也是很深的。当初在九女沟,我还没太感觉到。到了平顶山,我就有了明显的感觉。尤其是租了民房住到一起后,我对毛英的感情一下子就上来了,简直可以说是爱上了她。然而,谁也没想到,我们在一起还没住到一个月,毛英就出事了。
她到底咋啦?陶贵冲我吼了起来。
我勾下头说,她跟储洞长打上皮绊了。
你说啥?陶贵突然从椅子上弹起来,眼珠鼓得圆圆的,像两颗黑药丸。
我伤心地说,储洞长也给我戴了绿帽子。
毛英到了平顶山,先在食堂打了几天下手,一周之后便负责做面食了。她蒸包子,做馒头,擀面条,样样都会,不久又学会了做河南烩面。储洞长租住的地方有厨房,大部分时间自己开伙,偶尔也会到食堂来吃一顿。自从吃了毛英做的烩面,储洞长就不自己开伙了,每天都跑毬食堂来吃。他夸毛英的烩面做得比河南人还地道,简直把她夸到天上去了。到平顶山的第二个月,储洞长突然跟毛英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让毛英去给他开小灶,也就是当他的专职厨师。
陶贵问,毛英去了没有?我点点头说,去了。陶贵又问,她为啥要去?我说,储洞长许诺每个月给她加五百块钱。其实,我是反对毛英去的,一开始我就觉得事情不妙。但毛英主意已定,我怎么劝都劝毬不住。头半个月,我还没发现啥异常。每天晚上七点左右,毛英都会按时回到我们租住的地方。可是,半个月以后,她就不再按时回来了,有时是八点,有时是九点,有时还拖到十点以后。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起了疑心。
难道你就没审问过毛英?陶贵问我。我说,审问过,但她不承认,不是说在帮储洞长洗衣裳,就是说在陪他斗地主。陶贵又问,你就没去查过吗?我说,我想过去查,但顾虑太多,一直没好意思去。不过,我最后还是去查,没想到,一查就查出了问题。
我是在离开平顶山的头天晚上去查的。那天晚上,毛英直到半夜还没回来。我想,洗衣裳也不会洗到这么晚,斗地主也该散场了。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头,便不顾一切地去了储洞长住的地方。我到那里时,储洞长的门也关了,灯也熄了,连毛英的影子都没看到。后来,我轻手轻脚地走到了储洞长寝室的窗外,侧耳一听,居然听到了一串熟悉而又陌生的叫声。
陶贵胀大眼圈问,谁在叫?我沉默了一会儿说,除了毛英,还能有谁?陶贵问,难道毛英还叫床了不成?我说,她咋没叫?叫得吓死人的。陶贵破口大骂道,这个骚货,真是不要脸!
我没有再接陶贵的话,陡然感到寒气袭人,每个毛孔都凉飕飕的,浑身上下颤个不停,连牙齿也打起架来,仿佛打摆子了。陶贵一惊问,你咋发抖?我说,我好冷。陶贵立刻又往火炉里加了一块劈柴,火房里的温度更高了。可我还是感到很冷。陶贵问,房里这么暖和,你为啥还在发抖?我说,心里冷。陶贵想了一下说,你八成儿是受寒了,我去给你找壶酒来,让你喝酒祛寒。
陶贵很快提来了一壶苞谷酒,还拿来了两个杯子。他说他已有好长时间没喝酒了,也想趁机喝一杯。我们马上喝了起来。酒还真能祛寒,两杯下肚,我身上就不觉得冷了,也不发抖了。开始,我和陶贵各喝各的,连杯子都不碰一下。喝了五杯的样子,我感觉有点儿醉了。人一醉,心里就会生出一些跟平时不一样的想法。猛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很对不起陶贵,于是就想敬他一杯酒。
我又斟了一杯,端起来说,陶贵,我敬你一杯酒!陶贵惊奇地问,你为啥敬我?我打个酒嗝说,我对不起你,不该跟毛英打皮绊,让你戴了绿帽子!陶贵听了很感动,欣喜地说,狗日的,难得听你给我道个歉!这杯酒,老子喝了。喝下我敬的酒,陶贵也醉了。他这时也满斟了一杯,反过来要敬我。我眨巴着眼睛问,你敬我搞啥?他喷着酒气说,我也对不起你,也想给你道个歉。我问,你有啥对不起我的?他说,我不该放火烧你的老屋!话音未落,他就一口干了。我顿时也非常感动,连忙端起杯子说,王八蛋,你终于自己承认了!这杯酒,我干!说完,我便一饮而尽。
后来,我和陶贵又连续喝了好多杯。我们相互认错,相互安慰,你来我往,推杯换盏,号啕大哭,泪流满面,直到把那壶酒喝得一干二净才停下来。末了,我们醉成了两堆烂泥,一同倒在了火炉边。倒下后,我们开始说酒话了。陶贵说,我要赶在过年之前去平顶山把毛英找回来。我说,我陪你去。
选自《作家》2017年第1期
原刊责编 王小王
本刊责编 胡 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