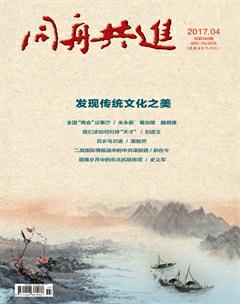蒙曼:今天恰是弘扬诗词文化的大时代
蒋保信
2017年春节,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春节。特别之处在于,在很多家庭,一家老少都坐在电视机前看《中国诗词大会》,掀起了全民读诗的热潮。在蒙曼看来,这个节目之所以能如此火爆乃是情理中事,因为中国人的诗心未死,诗性未泯,只是未被激活而已,更因为古诗词承载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审美、智慧、情感、信念等财富。
【父母并未刻意引导我读诗】
《同舟共进》:很多人看了诗词大会后,一家人都成了您的“粉丝”,估计不少家长都希望把孩子培养成像您这样饱读诗书的“文化偶像”。所以,我想请您讲讲您跟诗词之间的故事。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8岁时因读到《唐诗故事》而喜欢上诗歌。我比较好奇,您父母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当时是刻意引导您阅读诗歌呢,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蒙曼:我父母比我厉害多了,他们是上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受“文革”影响,还没毕业就被分配到了家乡的中学教书。他们都非常爱读书,爱到什么程度呢?从1979年开始,新华书店每次进新书后,店员都会拿着手抄的书单到我家来,让我父母勾选他们想要的新书,然后店员再骑车把书送来。我父母都是普通的中学教师,当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是他们却愿意拿出很多钱来买书。我想,这不论是在我们县城,还是在中国其它一般的县城里,都是非常少见的。所以,在我小时候,家里到处都是书。
现在的父母在培养孩子时,可能总喜欢指导孩子读书,可我父母从来没有指导我,他们只是各读各的书,也不管我。但有两件事情,我至今都印象深刻。
第一件事,我七八岁的时候开始读《唐诗故事》,知道了李白叫青莲居士,然后我就跟爸爸讲,李白叫青莲居士”。他当即回答:“不错,你还知道青莲居士呢。”我第一次因为有了点诗词方面的知识,而得到了父亲的赞赏,很开心。
第二件事,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跟父亲到书店去买书,看中了一本清代的诗集,想要买,父亲也没说什么就给我付了钱。在回家的路上,我边走边翻这本新买的书。父亲就提到,其实清朝的诗没多大意思,因为“诗不下盛唐,文不下秦汉”。这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因为父亲虽然不喜欢清代的诗歌,但也并没有不许我买。这说明父亲很尊重我,這种教育方式非常好。假如他当时跟我说,这本书你不能买,要买就买《唐诗三百首》,这样反而会让我反感。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印象深刻,不过这跟诗词没什么关系。我上初一时才11岁,有一天逃学在家看《福尔摩斯侦探集》,正好那天父亲的同事临时跟他借钱,他就带着同事回家拿钱,把逃学在家的我逮了个正着。但他很给我面子,没说我也没骂我,只是跟我说,“你也在家呀”。我回答:“我也在家呢。”他见我看的是《福尔摩斯侦探集》,就跟我说,这本书你现在也看不懂啊,然后随手拿一本《红岩》给我,说,你还不如看这个。父亲就是这样开明,他虽然没提我逃学的事情,但他是知道的,所以我第二天肯定不敢再接着逃学了。
我家里一直有很多书,因为我妈妈是教英语的,所以还有很多英汉对照的简写版世界名著。我没事就在那儿翻,翻完后再去看全译本,这个过程很好玩。比如说,我是先看了简写版的《牛虻》,知道了大概的故事情节,后来才去看全译本。
现在很多人问,怎么样才能让小孩喜欢上看书?我经常反问:第一,你们家有书吗?第二,你本人喜欢看书吗?如果这两个前提条件都具备了,孩子不喜欢读书是不可思议的。
【我跟诗词相处的方式是:没事闲翻】
《同舟共进》:《唐诗故事》这本书对您有什么影响?
蒙曼:《唐诗故事》刚出版时是四卷本,每册都很薄,只有手机这么厚。我是一篇一篇翻过去的,第一次系统地了解了那么多诗人。这本书有个非常大的优点,因为作者是个地质学专家,一个外行人写唐诗,他肯定是从兴趣出发而不是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的。对当时的我来说,这点太重要了。假如作者是从“初唐四杰”开始写起,一路把中唐和晚唐的诗人介绍一遍,那我可能就不喜欢唐诗了,因为这不符合我当时的心智。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会把写建筑的一类诗歌放在一起,比如关于大明宫有什么诗,关于大雁塔有什么诗。此外,他还会把描写唐朝人是怎样生活的诗歌放在一起,比如《新嫁娘》之类的诗,让人感到很有意思。所以,我对诗词的兴趣被这本书歪打正着地激活了。
《同舟共进》:在您接触唐诗后,在往后的成长历程中,诗歌对您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您平时是如何和诗歌相处相守的?
蒙曼:我跟诗词的相处方式就是没事闲翻。我是做历史研究的,诗歌从来都不是我的主业。但是,我喜欢诗、词、曲,我几乎把中国文学史里的主要著作都翻了一遍。当然,我在学生阶段,翻得最多的肯定还是唐诗、宋词、元曲。为什么呢?因为学生时代时间是零碎的,不可能有大段的时间去通读整个文学史里的作品。而且,当时我的兴趣点其实主要在小说上,《红楼梦》和《金瓶梅》我都看了很多遍,对它们的熟悉程度绝对超过了对《资治通鉴》和两唐书的熟悉程度。《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我也读得很多,只有《西游记》读得少点。我不喜欢《西游记》是因为觉得里面的妖精都太像了,而且书中提到的饮食也很乏味。我读到孙悟空大闹天宫为止,此后的取经故事我不喜欢,因为觉得孙猴子被戴上紧箍就玩完了。
《同舟共进》:问得具体一点,“没事闲翻”是一两个月翻一次还是几乎每天都会翻翻?
蒙曼:“没事闲翻”是指我读诗并没有一个具体计划,不会规定自己每个月必须读多少,或必须读什么。我的床头有个书架,《红楼梦》《唐诗三百首》以及钱锺书点校的《宋词》是我长期的枕边书。没事就翻翻,兴之所至也拿起来看看,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晚上睡觉前,如果让我读一下艾略特的《荒原》,我肯定读不下去,但是让我读一首李白的《春思》,“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六句话而已,我会很容易读下去,而且感觉很美。我就是这样,把这些诗词翻了一遍又一遍,对很多诗词自然就熟了。
《同舟共进》:从小到大,您有没有刻意背过诗歌?
蒙曼:背过一些,但是从来没检验过有多少,主要是因为没参加像《中国诗词大会》这类的比赛。但我对很多诗歌都很熟,而且心领神会。很多诗都能整首背诵下来,但不一定记得每一首的标题。比如说,“舍南舍北皆春水”这样的诗句我能张口就来,但未必能说出这首诗的名字叫《客至》。这也说明我读诗完全是出于纯粹的兴趣,没有带着任何功利的目的。
【诗词展现了不一样的世界】
《同舟共进》:您喜欢没事闲翻诗歌,那诗歌对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如果说诗歌能滋润人的生活的话,表现在哪些方面?
蒙曼:我觉得诗歌很美,它们展现了一个跟现在不一样的世界。古人常讲天人合一,他们的感觉特别敏锐,一花一草在他们眼里都是有生命的。我们现在看外面的花花草草,假如一个人非常多愁善感的话,也仍能产生很多生命感触。但问题是我们现在整天被高楼大厦包围着,要是对一栋大楼生出一些生命感触来,那就太不自然了。所以,现在的生活本身就没有古代那么有诗意了。
另外,古诗中有个非常重要的题材是“相思”,这也是现代人不太可能有的感触了。现在交通这么发达,通讯这么便利,无论思念谁,哪怕远在天边,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跟对方视频聊天。所以,现代人的思念都很短、很窄,特别苍白,失去了古代那种绵长的感觉。这其实是不利于锤炼人的内心的,使得我们既不敏锐,又不深沉。可是,我们却能在古诗里发现这么美好的东西。
总的来说,古诗词能让我跟现实世界有一种疏离感,这种感觉对我非常重要。因为人在红尘中打滚,如果完全跟红尘融为一体,那是很可怕的。诗歌能让我在精神上进入另一个世界,让我觉得生活有意思得多,轻松得多,也丰富得多。
《同舟共进》:所以阅读诗歌相当于让心灵有个美好的栖息地。
蒙曼:是的。而且因为我的专业不是研究诗词的,这点也特别好。如果把诗词研究作为专业,那就可能会让我感到很累,因为有时候必须要面对一些研究目标。可是,当诗词只是业余爱好时,想读的时候就随时读,这更自然而然。就像我看小说一样,想看的时候就找来看,不想看的时候就把书放下,一点心理负担也不会有。
《同舟共进》:所以“没事闲翻”,这个“闲”字可能也是阅读诗词最好的心态。
蒙曼:其实,古人的生活比现代人要闲很多。现在生活节奏太快了,一天的时间总是被乱七八糟的事情填满,可是到了晚上回想一下,却又说不清一天到底干了些什么。并且,我们所忙碌的事情都是必要的吗?也不一定。但就是没什么闲散的时间。人要是闲不下来,精神就会特别紧张,精神紧张,怎么会有幸福感?
《同舟共进》:从您个人经验而言,读诗从来都没有觉得苦吗?
蒙曼:是,我还真的是从来没觉得苦。可能很多人第一次读到的诗歌,刚好是他不喜欢和不感兴趣的。如果大家碰到这种情况,不妨多给自己两三次考察机会,再多读几首试试。但假如一个人读了几十首诗,仍然不能感受到诗词的美好,那就先放下吧。世界上总会有些东西是不适合自己的,也会有些东西是适合自己的。假如一个人一辈子都对诗词不感兴趣,他其实仍然可以是一个好人,并且仍然可以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但假如你发现自己对诗歌有兴趣,这是好事,不要扼杀这个兴趣,多给自己一些时间来接触诗歌,看看我們对世界的认知和感受能丰富到什么程度。
【诗歌里的中国是个丰富的中国】
《同舟共进》:您最喜欢的诗歌是哪几句?
蒙曼:我好像没有最喜欢的几句诗,对我来说这可能是个不存在的话题。既然我们刚才聊到“闲”,那我就分享几句与此有关的诗——“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这是李白的《山中与幽人对酌》,我很喜欢。我来逐句解读一下。
“两人对酌山花开”,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在一个山坡上喝酒,眼前是漫山遍野的闲花野草,没有其它东西。喝酒的场所很重要,如果在酒楼,则过于奢华腐败;如果在家里,则又可能放不开,因为可能有各种人伦关系的拘束。可是,两人在开满鲜花的山坡上喝酒,这种感觉会是多么的自由自在?
“一杯一杯复一杯”,这不是为了工作上的应酬而喝酒,也不是在很有氛围的家宴上喝酒,只是两个好朋友坐在那里喝酒,一杯一杯又一杯,也没有别的什么事。
“我醉欲眠卿且去”,你想想看,谁跟谁才能这么说话呢?假如咱俩坐一块喝酒,你肯定不敢喝醉,当然我也不敢。第一,咱俩还没那么熟;第二,各自背负着一种身份,我是一个大学老师,要是喝醉了那成什么样了?你是一个记者,喝醉也害怕出事。所以,能够“一杯一杯复一杯”地喝酒,说明俩人肯定是知心朋友。喝醉了,想要睡觉了,就各回各家。
“明朝有意抱琴来”,这里用了一个有关陶渊明的典故,陶渊明收藏了一把无弦琴,没有弦,但曲调却在内心之中,好朋友之间会有这种会心感。
谈到李白的诗,我们一般会想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说明他很狂;也可能会想到“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这是小清新的风格。但我觉得李白其实是一个很自在的人,《山中与幽人对酌》就能说明这一点。
《同舟共进》:您比较喜欢的诗人是谁?
蒙曼:就是李白,他是我心中一个永远的梦。对我来说,无论是李白的诗,还是李白本人,都是精灵一般的存在。李白不像杜甫那样厚道、温暖,正因如此,我才那么喜欢他,他像是站在云端上照镜子,让我感到跟神仙一样。读李白的诗歌就好像进入了春天。
如果要给盛唐找一个“代言人”,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李白,因为他天真、任性、浪漫、多才。而且李白身上寄托了很多寒士的理想。所谓寒士的理想,就是能凭借自己的本事,在这个世界上自由自在地活着。
《同舟共进》:在您看来,古诗词里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蒙曼:诗歌里的中国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中国。就拿唐宋时期的诗词来说,唐诗里的中国,主体上是一个情感的中国,反映的是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情感;而宋代的诗歌,更多的是说理,比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其实,诗歌里的中国,跟其它文学作品里的中国都是一样的。从它反映的范畴来讲,中国有多广阔,中国的诗歌就有多广阔。
诗歌能让人更敏锐,因为它不仅是语言上的提纯,还是生活的提纯。诗歌能把生活中最典型、最精致、最美以及最残酷的面相提炼出来,通过诗歌来触摸中国,更能直指核心,更容易把握一个时代。
《同舟共进》:诗歌里的中国人和现代中国人有什么不同?
蒙曼:古代人没现代人这么大的能力,所以更知道自己局限,当他们面对这种局限时,比我们要更深情一些。现代人太自信了,觉得自己无所不能,觉得天边的风月都是可以够得着的。古代人往往会感到自己渺小,比如一个在荆楚之地的人,可能并不知道塞北是什么样子,因而很容易就有渺小感。可是现在呢,人们很方便就能看到全世界的全景图。我觉得现代人自信心爆棚,但不敏感,也少了些谦卑和深情。假如一个人喜欢诗歌,我敢说他的精神世界会更丰富。
【诗词就像猫嘴上的胡须】
《同舟共进》:有媒体人撰文指出,在清末以前,古典诗词的社会功能都还在,所谓“兴、观、群、怨”。但到了如今,诗词教育已经不再是无可替代的手段,也不是现代人生活之必需,而成了一种文化偏好或说是进阶学习,诗词可以说是“老虎嘴上的胡须,没有也不碍事”。您同意这个说法吗?现在对于孩子的诗词教育,我们到底是做得太多还是远远不够?诗词教育与其它的素质教育(诸如钢琴、奥数等)是不是一样可有可无?
蒙曼:我不知道老虎嘴上的胡须是否真的没用,但我知道猫嘴上的胡须看起来没用,但实际上特别重要。猫需要用胡须来探路,测量洞口或道路的宽窄,如果没有胡须,它很容易被卡住,甚至变得不会走路。
无论古诗词也好,还是传统文化也罢,我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它们就像猫嘴上的胡须,是一种特别重要的存在。虽然诗词跟水、米、空气不一样,它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但假如生活中真的没有了诗词和传统文化,这也是件可怕的事。因为我们不但不知道自己是从何处来的,也不会养成良好的审美观。比如当我们说“流水落花”时,大部分中国人会想到“流水落花春去也”,这是有点伤春的意思了。但假如你完全没有接触过中国文化,那就不能体会到这一点。所以,如果不懂点诗词,有时候甚至都没法和别人交流,也没法和古代的祖先交流。古人留下了很多好东西,但我们都完全不知道,你说这是不是挺可怕的?
假如生活中没有诗词,那你的肉身所在之处,就是你的全部世界了。你想想,这个世界有多狭窄,看山就是山,看水就是水,乏味极了。但假如我们生活中还有诗歌,那肉身所在和精神所在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肉身可能只是蜗居在几平米的陋室里,但精神世界却可以很广阔。
诗歌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帮助我们去感触过去那个已经消失了的世界。当我们在面对新世界时,敏锐度就更高了。你说人更敏锐好,还是更迟钝好呢?所以,我觉得对孩子的诗词教育很重要,我们不要轻视精神的力量。孔子说的“不学诗无以言”用在今天也合适。我们不读点诗歌,可能都不会审美地说话了。一张口只能是粗话、俗话,让人听了感到厌恶。所以说,在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的今天,恰恰是弘扬诗词文化最好的大时代。
【诗词教育要解决三个问题】
《同舟共进》:《中国诗词大会》冠军武亦姝母校的一位教师说,在应试教育的夹缝里传承诗词文化特别难,如今中小学老师都是“考什么教什么”“怎么考怎么教”。而学生们也只是把古诗词当作语言材料,机械地练习和记忆,背离了诗歌作为文学和文化的本质。对于今天的诗词教育,您有什么建议?
蒙曼:如今学校的诗词教育,有三个特别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個问题,学校现在的诗词教育是不成体系的。相较而言,古代的诗词教育更讲究循序渐进,这是人们更喜欢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在小孩开蒙的时候,会有专门的开蒙读物。开蒙之后,小孩才沿着小经、中经、大经这样一个序列学习,由浅入深,由具象到抽象。古代教育跟现在还有个很大的不同,它一开始可以说是一种综合性的教育,不仅教文字,还教人生观。比如,《三字经》是蒙学读物,“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这里面不仅有诗词韵律,而且还包含了做人的道理。《三字经》学完后,开始读《论语》,然后是《大学》《中庸》,非常有层次感。
中国现在的诗词教育,在小学、中学和大学里是这么衔接的吗?小孩子在小学时学的诗歌真的适合他们吗?我没有翻过小学教材,但前两天一个年轻的记者妈妈跟我讲,她女儿刚上小学一年级,老师给指定的诗词读本就是《唐诗三百首》,我想这是有问题的。《唐诗三百首》第一首是张九龄的《感遇》,“草木本有心,何求美人折”,这是一个中年人才能懂得的情怀,人要历经挫折后,才会有这样的想法。你让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去读这首诗,他怎么能理解?所以,在诗词教育中,学生在不同阶段,应该学习什么样的诗词,这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谁来教,现在的一些语文老师能不能教好诗词,我有所保留。诗歌最大的特点是,“诗无达诂”,诗只是一个触媒,你怎么理解,就要看它触动了你内心深处的哪一块。但老师在教诗词时却通常喜欢给个标准答案。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现在的孩子都觉得这是在说野草生命力很顽强。可是,你知道蘅塘退士怎么解读的吗?他说,这首诗讲的是君子和小人之争。“离离原上草”指的是小人;“一岁一枯荣”的意思是,不管你怎么打压小人,他都会卷土重来;“春风吹又生”,天气暖和了,小人又开始当道了;“远芳侵古道”,“古道”指的是君子,这句诗的意思是小人把君子都给遮蔽住了;“晴翠接荒城”,“荒城”指的是荒唐的皇帝,意思是小人老是能亲近皇帝;“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小人最后得势,君子只能黯然收场。蘅塘退士说,这才是白居易这首《草》的正解。蘅塘退士是个老官僚,当的官也不大,只不过是个县令,但他可能自认为是个正人君子,一辈子没少被小人遮蔽。所以,他读《草》这首诗就会有这种理解。当然,一个年轻人读《草》,看到的是野草顽强的生命力,这也是没问题的。正由于“诗无达诂”,所以教诗词的老师需要有很高的素质。如果让小孩去背指定的标准答案,那就是件可怕的事情了。
第三个问题,学校的诗词教育应该克服功利心,而不能培养功利心。教育的本来目的,应该是帮助人在精神上有更高层次的追求,而不是相反,就好比一些小孩热衷于学奥数,其实是出于功利的目的而不是兴趣。同样道理,如果抱着一颗功利心来学诗词,要考高分,或者要赢得一个比赛,那么所有的诗词,无论好坏,当然都只能是素材而已。现在社会的评价标准是单一的,其实不应该这样,教育应该让每个人按照自身资质,以不同方式和不同速度去成长,而不能只有一个功利的目标。这可能不单是诗词教育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