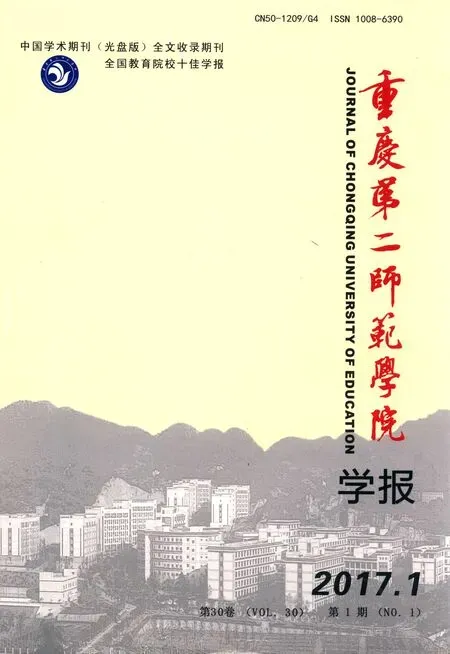《白鹿原》与《百年孤独》鬼神观念的比较研究
邓子敬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南宁 530006)
《白鹿原》与《百年孤独》鬼神观念的比较研究
邓子敬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南宁 530006)
鬼神观念作为人类自古以来解释自然的思维存在,具有较高的普遍性和鲜明的地域性。《白鹿原》所体现的中国关中地区传统的鬼神观与《百年孤独》所体现的拉美地区的鬼神观,在人鬼二元关系、鬼神存在方式、幽冥相通形式和特殊意象等方面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显著差异。把这种异同置于各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以比较,颇具现实意义。鬼神观念的变幻是区域民间文化的反映,而区域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民族的思想意识。在相似的历史条件下,两地都孕育了相对保守的文化,而这种保守的文化心理也许阻碍了所在地域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但对文学来说,它却以奇异的色彩成就了伟大的作品。
《白鹿原》;《百年孤独》;关中地区;拉美地区;鬼神观
《说文解字》释“鬼神”,曰:“鬼,人所归为鬼。从人,像鬼头,鬼,阴气、贼害。”“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又,《说文解字注》释“魂魄”,曰:“魂,阳气也;魄,阴神也。阳言气,阴言神者,阴中有阳也。”魂主动,魄主静;魂统领精神,控制人的情感思维,魄统领肉体,控制人的身体感知、新陈代谢。由此可见,在古人的思想观念中,鬼就是人死后的阴魂、阴气,带有一定的负面感情色彩;神是超自然万物的创造者,包括人类祖先的魂灵,因其超自然的正能量而被人类所崇拜。人的躯体跟灵魂是分开的。钟敬文先生认为,人类最初的信仰是从自身开始的,如对梦境和死亡的不解,导致人们相信人是由肉体和灵魂组成的,灵魂附在肉体上,做梦、生病则是灵魂暂时离开肉体的反映,一旦灵魂离开肉体不归,人就死了,但是肉体虽然腐烂了,灵魂却能变成鬼或鬼魂。[1]189鬼神观念反映了人类最初的民间信仰,灵魂、山川、图腾无不如此。而鬼所生存的冥界的主宰者也就成为能够主宰人的生死的神。佛教传入中国后,注入了地狱和因果报应观念,对人施加的影响更强烈,也更令人恐惧。显而易见,鬼神是在人们的文化传统中形成的,是根据人们的价值观念来判断的,它们的象征意义离不开人们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而在同一个文化区域,文化群体的生存方式以及文化特性都是相似的,带有这个文化区域所特有的性质。鬼神观念也不例外。不同地域的文化群体创造了不同的适于其自身的鬼神观念,即使生活在同样的大文化区域内,各自的特性也千差万别。如在中华文化区内,中原文化、关东文化、巴蜀文化等又在不同的地理空间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态文化系统。就鬼神观念而言,中国与西方就有所不同。在西方,鬼是魔鬼,恶鬼的意思,神就是指上帝 ;而在中国,鬼神一家。[2]83因此,鬼神观念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由于各地域文化之间存在差异,中外之间的鬼神观念也具有多样化的色彩,具备鲜明而丰富的可比性。《白鹿原》体现的是中国关中地区传统的鬼神观念,而《百年孤独》体现的则是拉美地区传统的鬼神观念。本文试图将这两部名著所体现的鬼神观念的异同进行比较,以期对中外文学名著研究和中外文化交流有所裨益。
一、《白鹿原》所体现的鬼神观念
《白鹿原》所体现的鬼神观念是属于中国关中地区这个特殊地域的。自古以来,关中地区的巫神文化就很发达。位于关中地区的白鹿原所孕育的鬼神观念自然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敬神畏鬼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鬼神是依据人的道德价值标准来评判的。人们普遍认为,神能给人带来福祉,鬼却给人带来祸患。鬼神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名词,而是被人们赋予了强烈的感情色彩,中华民族由此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敬神畏鬼观念。
在《白鹿原》中,几乎一切人为的或自然的灾祸都被看作是恶鬼作祟的结果,诸如战争、瘟疫、干旱等。人们基于对未知力量的恐惧以及自身的孱弱,本能地将一切恐惧的因子都赋予鬼这个意象。鬼作为一种符号成了邪恶、堕落和恐惧的代名词,当地人对鬼怀有深度的恐惧和憎恨。白嘉轩最引以为豪的是他一生娶了七房老婆,而他的第六房老婆却梦见了之前从未见过的五个女人,相貌特征跟真人吻合,成天担惊受怕,从此精神萎靡而死。而白嘉轩的前几房女人都变成了恶鬼,她们不停地在阳世作乱,给白嘉轩新娶的女人带来恐惧,以至于不得不请道士收服这些恶鬼。在人鬼不可调和的传统观念里,鬼带给人间的是骚乱和恐惧。在《白鹿原》中,鬼因被赋予了邪恶、低劣、堕落的文化因子而遭到无情的憎恨,而神则是能带给人们光明和福泽的。这部作品中的神灵因为集中了当地人单纯而美好的信仰受到人们的崇敬。神是正义的化身,是被主流观念所认可并受到人们尊崇的;神鬼的矛盾对立也同样尖锐。所以田小娥死后要撒布瘟疫,引起人们恐惧,并要求人们为其造神庙。她费尽心机想由鬼变成神,就是想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尊重。
白鹿原因一只白鹿精灵而得名。白鹿是当地民间传说中的神,是白鹿原的人们心中信仰的神鹿。在白鹿原上,只要白鹿经过的地方必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白鹿能杀死一切毒虫猛兽,扶危救难,拯救黎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具有无与伦比的正能量。白鹿是人性的化身,也是民间文化的精魂。白鹿原上的人尊崇白鹿为他们的神灵,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单纯而美好的信念。白鹿原上的朱先生也被尊为半神。他是白鹿原上关中学派的最后一位传人,是当地人的精神导师,拥有传统文化认可的成神的所有潜在要素。他修白鹿书院教书育人、搞禁烟运动、只身退兵、清廉赈灾、投笔从戎等一系列行为无不体现出他拯救黎民百姓于水深火热的动机。他所体现的精神是儒家文化所提倡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2]84朱先生大义大勇,凭借只手之力,挽狂澜于既倒,把朱先生尊为半神是符合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的。
(二)人死为鬼,灵魂不灭
在远古时代,人们认为人死了灵魂是存在的,人的躯体和灵魂是可以分开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人们对生与死的理解也是具体的。生是肉体与魂魄的合二为一,死后肉体腐烂,魂魄脱离肉体而游荡。“能够超越人的肉体存在的灵魂自然是不死的,人的死亡不过是灵魂脱离肉体到处游荡而已。这种灵魂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就产生了鬼魂、冥世、地狱、轮回转世等一整套体系。”[3]53人死后,灵魂脱离出来,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存在。佛家讲生死轮回,灵魂在轮回中得到永生;道家讲奈何桥,一碗孟婆汤让人忘记前世而重新投胎。所以,中国自古就有人死为鬼、灵魂不灭之说。
在《白鹿原》中,白嘉轩的六房太太死后鬼魂一直纠缠不清,田小娥冤死后变成鬼魂报复当地人,就是人死为鬼、灵魂不灭的鲜明体现。白鹿原上的人们在祭祀祖先时,往往会摆上许多美味佳肴当祭品,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们也能在另一个空间享用这些美食。这既是白鹿原上的人骨子里根深蒂固的灵魂不灭观念的行为反映,又是对自己祖先的一种人文精神的祭奠和缅怀。在当地人眼中,鬼魂不是虚无缥缈的神秘事物,而是他们生活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对于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人们都会把自己的思想观念或意愿付诸鬼神。这既使鬼神具有超越常人的力量,又使其具有常人的思想和行为特征。
(三)动物特殊意象之兴寄
《白鹿原》塑造了一系列神秘的动物意象,如神秘的白鹿、恐怖的白狼、飘飞的蛾子等,无不带有神秘离奇的色彩。这些动物意象存在于人们的口耳相承的传说中,它们神通广大,或正或邪,总是在天有异象的时刻出现,具有毁天灭地的力量。这种描写体现了中国民间自古以来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心理现象。有学者认为,生活在农耕社会的人们,平时经常谈论的就是重复出现的怪声,飘浮不定的幻影,白马、白牛、白虎、白龙等或圣洁或污秽的形象,以及其他一些稀奇古怪的物象,它是构成中国民间神秘文化体系的一种独特的畸变的心理折射。[4]149
在《白鹿原》中,神秘的白鹿精魂带给白鹿原人光明和力量,它所到之处一切灾难都将烟消云散,它是白鹿原人渴求安定和平的一个象征意象。而恐怖的白狼,一口咬断人的脖子,哪里有它的踪迹,哪里就血流成河。白狼身上散发的恐怖、神秘的气息,让人不寒而栗。可以说,白狼象征着邪恶,象征着流血,象征着恐惧。白狼这个意象所折射的恰恰是白鹿原人对死亡、流血的恐惧和对时局不稳、草菅人命的不安。而飘飞的蛾子,实际上就是田小娥死后的怨气所化。人已逝而怨难消,读之不禁令人黯然神伤。凡物皆具有灵性;以我为中心,万物皆着我色彩。这也许是中国人共同的思想感情倾向。
(四)幽明相通
幽明相通的常见形式是鬼魂附体。如前所述,中国古人认为,灵魂和肉体是可以分开的,脱离了肉身的灵魂是不死的。不死的灵魂只要再找到一个载体(人或物),同样能代表原来的肉身行事。[3]65在《白鹿原》中,田小娥将自己的鬼魂附在鹿三的身上,当白嘉轩准备去请法师制服她时,她又跑又躲。她通过鹿三的嘴诉说自己的不幸。这样一个女人,到白鹿村不曾偷过别人的任何东西,不曾骂过任何一个长辈,没有搡戳过一个娃,但白鹿村就是容不下她。她哭诉自己的委屈,她知道自己不干净,可黑娃不嫌弃,跟黑娃过日子,村子里住不成,就搬到村外烂窑里住。族长不准进祠堂,她也就不敢去了。田小娥是一介弱女子,她手无缚鸡之力,却要承受生活的压力和整个社会对她的唾沫。“大呀!俺进你屋你不认,俺出你屋没拿一把米也没分一根蒿棒棒儿,你怎么着还要拿梭镖刃子捅俺一刀?大呀,你好狠心……”这无疑是田小娥这个弱女子借助鬼魂对整个封建社会的血泪控诉。这样的鬼魂附体是幽明相通的一种传统形式。鬼魂借助他人的身体,来倾吐自己的爱憎情感,表达自己的想法,实现自己的目的。
幽明相通的重要形式还有托梦。当人醒着时,肉体与灵魂合一;睡着后,灵魂可以暂时自由外出活动,这便是梦。梦中能与死去的人谈话、共事,这就是灵魂之间的交流。[5]65梦能满足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愿望。由于梦的神秘感它常常被当作传统社会里幽明相通的一种重要形式。所谓的“托梦”就是如此。在《白鹿原》中,鬼魂、梦境等体现得较突出的是白嘉轩前五房女人托梦给第六房女人胡氏,田小娥托梦给她婆婆,白灵死时同时托梦给她的爸、妈和大姑妈等。人死了鬼魂的存在和梦可以相通,这是一种传统的幽明相通形式。借助梦境,活着的人可以和死去的人相会,而且还可以模拟现实情景,体验梦中的真实感,却不会对人造成任何形式的伤害和负担。显然,梦境沟通了世俗世界与人的情感世界。在梦里,人的情感可以尽情宣泄,而鬼魂也可以通过进入梦境来诉说其愿望。
二、《百年孤独》所体现的鬼神观念
《百年孤独》所体现的鬼神观念代表了拉美地区对鬼神的传统看法。这部作品中很多具有魔幻色彩的情节,均源于马尔克斯自身的生活环境和真实经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鬼二元和谐
在《百年孤独》中,鬼魂并没有被人们刻意赋予或光明或邪恶的含义。人死后为鬼魂,而鬼魂作为另一种生命存在,似乎存在于另一种能量世界,自由穿梭,人鬼无害,由此呈现出一种高度和谐的状态。帕斯认为,在古代墨西哥人眼里,死亡和生命的对立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么绝对。生命在死亡中延续,反之,死亡也并非生命的自然终结,而是无限循环的生命运动中的一个环节。[6]213所以人可以坦然地面对死亡,死亡只是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生命在死亡中继往开来,灵魂只不过是脱离了本体的另一种生命存在。
在《百年孤独》中,阿玛兰妲可以在一年前就早早得知自己将要死亡的消息,甚至能够准确测算出自己的死亡日期。她活着时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给自己编织一件精美的裹尸布。那么平静,那么坦然而超脱地面对死亡。这是一种超脱了生死的状态,生与死、人与鬼在这里达到高度和谐。梅尔基亚德斯在天地之间纵横驰骋,返老还童,自由穿梭,几度变为鬼魂,又几度复活。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死后,鬼魂常常流连于他生前一直被捆绑的大树下,他亦能感知到人世间的一切。在这部作品中,人的生命形式体现出一种和谐统一的状态。人们对生并非显得十分留恋,对死亡也并没有显得特别恐惧,而是平静地面对生命的终结。或许在拉美地区人们的眼中,生命或灵魂常在,只是生命体在不同阶段所呈现的形式不同而已。
(二)鬼魂超脱永恒
《百年孤独》中的鬼魂是不受时空限制的,它是超脱永恒的。它没有转世投胎或天堂地狱的说法,鬼魂是永恒的另一种生命体的存在。一切都能打破,包括其存在界限(生与死的存在界限如梅尔基亚德斯的几度复活,鬼魂与活着的人的存在界限)和能量因子(构成人与鬼两个世界的最小元素)。正如帕斯所指出的:“在古墨西哥人看来,死亡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人进入生命创造的过程,同时,作为人,偿还欠上帝的债;另一方面,供养社会生命和宇宙生命,而社会生命是由宇宙生命供给营养的。死亡是一面镜子,它能反射出生命在它面前做的各种徒劳的姿态。”[6]213似乎活着只是生命的短暂停驻,而死亡却是生命的永恒。帕斯的说法不仅仅是墨西哥人的看法,也是整个拉丁美洲人的看法。
且看《百年孤独》中的梅尔基亚德斯。他在回到马孔多后,不过几个月便经历了一个急剧衰老的过程,很快就变为那类无用的老翁。他和老布恩迪亚游荡在幽灵般的卧室里,高声追怀美好的岁月却无人理睬,直到某天清晨死在床上才被人想起。而之后的一个星期四,在叫他去河边之前,奥蕾莉亚诺听见他说自己已经发热病死在新加坡的沙洲上。之后他又几次复活,几次通过鬼魂指点布恩迪亚的后代。在梅尔基亚德斯死后准备下葬时,老布恩迪亚都还在固执地相信他是不会死的。显然,作品中的这个梅尔基亚德斯是个不受生死界限约束,能够在天、地、冥三界纵横穿梭的人物。我们有时会突然发现他早就死在新加坡的一片海滩上,可是,他又一次复活于马孔多。当他在马孔多再一次死去后,那个不甘寂寞的幽灵还是会在这里出现,为布恩迪亚的子孙指点迷津。他身上有着无限神秘而奇幻的色彩,上晓天文,下通地理,了解过去,预知未来,马孔多的历史被他记载在那一卷羊皮书中,也展示了布恩迪亚这个百年家族的命运。由此可见,《百年孤独》里的灵魂是超脱而永恒的,灵魂已经成为生命体的一种高级存在形式。孤独的灵魂在这里可以自由穿梭,毫无顾忌地往来于天地之间,传说中的“永生”在这部作品里得到了完整的演绎。
(三)人鬼多元沟通方式
在生与死,人与鬼的界限完全被打破的区域,人与鬼魂沟通便有了多种多样的方式。在《百年孤独》中,只有气质接近的人或一腔执念的灵魂才可以相互感应,直接交流。这种直接交流方式并不为气质不同的人所感知。可以说正是无限孤独的灵魂无限逼近的联系,才产生了这种独特的直接交流的方式。
一种是心灵感应式的直接沟通方式。例如,梅尔基亚德斯在死后变成鬼魂指点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后代的时候,就是用一种心灵感应的方式相互沟通,其他人却视之不见。有时候,鬼魂也会主动上门交流。作品中有这样的情节:忍受了多年的孤独之后,那个被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刺死的仇人邻居的鬼魂主动找到了布恩迪亚,颤颤巍巍来到他的卧室,迫切希望与他交流。仇人的鬼魂屈死了好多年迫切地需要一个灵魂伴侣。而对阴间那种死亡逼近的强烈的孤独恐惧感与对生者的无限眷恋,最终使他放弃了仇恨,并对这位最大的敌人产生了怜悯与好感。
另一种是身体感知式的直接沟通方式。死去的老布恩迪亚的鬼魂一直都在生前被捆绑的那棵棕榈树下,他会因受到外界的刺激而自言自语,仿佛常人一样生活着。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鬼魂在因浸泡了好多雨水而腐烂不堪的棕榈棚下打盹时,因上校的热尿溅在靴子上而被惊醒,更有惊醒时所说的一些难解的言语。
在《百年孤独》中,人鬼之间还有一种间接的沟通方式。不过,这种间接的沟通方式在作品中不多见,如寄信的方式。这种交流方式就像是人世间远方的亲人,由于路途遥远,不便直接去看望他们,于是就托路人给捎个信、问个好。在人鬼沟通中,生死、人鬼的界限被打破,鬼魂不再神秘,人鬼之间也不再彼此陌生,其沟通方式显得多种多样。
(四)赋予事物象征意义
在《百年孤独》中,一些奇特的意象十分神秘,却又耐人寻味。这些意象总是伴随人的生老病死,伴随自然的沧海桑田。这些特别意象在特殊的时刻出现,不仅显示出可能发生的事件的征兆,而且是预言和象征。
作品中的黄色总是给人带来厄运。例如,梅尔基亚德斯泡在碗中的假牙长出开黄色小花的植株不久就撒手人寰;族长何塞·阿卡迪奥 ·布恩迪亚去世,下了整整一夜的黄色小花雨;黄色车头的火车带来了美国香蕉公司的布朗先生,同时还带来了奴役、剥削和大屠杀。在马孔多的当地人看来,黄色意味着灾难和死亡,是孤独、消极、落魄、死亡的颜色。黄色作为一种灾难的符号,被当地人所憎恶。黄色在特定时刻出现,无不预示着人物的悲惨命运。
作品中一些动物的意象也别具意味。例如,蝴蝶象征爱情,黄蝴蝶却象征爱情的悲剧。梅梅发觉在马乌里肖·巴比伦出现之前总会看到那些黄蝴蝶。梅梅在洗澡间里洗澡时,费尔南达踏进她的卧室,偶然看见卧室里的蝴蝶密密麻麻,数量多得几乎令人窒息。也就是在那天晚上,马乌里肖·巴比伦被守夜人一枪放倒。而此时的梅梅则在蝴蝶与蝎子的环绕中,痴痴地等他。这里的蝎子象征恐惧和不安。在蝎子与蝴蝶的环绕中,梅梅内心深处充满了不安和恐惧。这两种意象的搭配恰恰预示了一种悲剧的爱情结局。在以“自然崇拜”为核心的“万物有灵”[5]65观念的引导下,一切生物在荒诞中都被赋予了人的特殊象征意义。
三、《白鹿原》与《百年孤独》鬼神观念的比较
中国和拉美国家一样经历过漫长的苦难时期。近代以来,中国从多重浩劫和苦难中挺立过来的这段特别痛楚的历史经历,与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所描绘的哥伦比亚历时百年惨遭外来殖民文化野蛮统治和强烈冲击的民族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4]147而在相似的历史条件下,除了文化发展的共性之外,不同区域的文化还具有各自不同的个性,鬼神观念也不例外。白鹿原属于中国关中地区,而关中地区靠近古代帝都,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兴盛之地。无论《白鹿原》中的民俗民风,还是陈忠实创作中所体现的心理气质,均可看到区域文化的影子。而《百年孤独》中那种神秘魔幻的鬼神色彩同样具有拉美地区鲜明的区域特征。可以说,地域文化是孕育作品的土壤。
《白鹿原》与《百年孤独》中所表现的鬼神观念的共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关中地区和拉美地区都具有根深蒂固的“人死为鬼、灵魂不灭”的观念。人的死亡并非就是生命的完结,人死之后,肉体不复存在,而灵魂却继续存在于另一时空,并作为另一种生命体的存在对活着的人施加影响。这种灵魂不灭的观念深刻地影响着当地人的生活。《白鹿原》中的人们通过一系列祭祀活动来慰藉自己祖先的亡灵就是这种观念的典型例证。《百年孤独》更直接,人的鬼魂可以永恒存在,并纵横来往于任何时空,这里的鬼魂已经和活着的人没有太大区别,他们完全是另一种形式的生命存在。灵魂不灭的意识,使他们在生与死之间得到了超脱。
其二,鬼魂具有人的情感思维,与生活密不可分。无论是在《白鹿原》还是《百年孤独》中,鬼神都是具体可感而非抽象的。鬼神同人一样,具有思想感情和爱憎观念。在当地人眼中,鬼魂不是虚无缥缈的神秘事物,而是他们生活中的一种常见现象。无论是鬼魂托梦,还是一些人间灾难,《白鹿原》中的一切灵异事件都能从鬼神的活动中发现端倪。而《百年孤独》不仅将鬼魂的活动作为一种生活常态来看待,而且让鬼魂和人直接进行交流,打破了一切存在的界限,更为具体可感。
其三,无论是关中地区还是拉美地区都信奉“万物有灵”的观念,不同的东西都被各自地区的人们赋予其各自不同的象征意义。《白鹿原》中将白鹿奉为当地人的保护神,将白狼看作杀人狂魔,体现了人们在战乱和瘟疫肆虐下朝不保夕的生存状况,以及他们畏惧暴力,害怕死亡的心理状态。这也正是在原始的本能下人们因无法摆脱自身的生存困境而产生的变形反应。《百年孤独》里也往往有一些奇特的意象,它们神秘而又耐人寻味。这些特别的意象在特殊的时刻出现,伴随人的成长和死亡,伴随整个世界的沧桑巨变。作品中有象征爱情的蝴蝶,象征邪恶与恐惧的毒蝎,象征死亡的黄颜色,象征毁灭的猪尾巴,更有村庄被黄沙吞噬,万物被蚂蚁蚕食这样的毁灭结果。所有这一切都使拉美地区变得无限古老而又神秘,万物有灵更被演绎到魔幻的极致。
而《白鹿原》与《百年孤独》所表现的鬼神观念的个性,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人鬼二元关系上,《白鹿原》所体现的关中地区的传统鬼神观念在整体上呈现一种对立的姿态。人死为鬼,死而不可以复生,这是生与死的对立;鬼为恶佞,作祟人间,人鬼对立,几乎不可调和。人死为鬼后不能直接复生,才有转世轮回之说。所以关中地区的古老习俗造就了这样的现实,鬼被贴上了一个邪恶的标签,当人鬼矛盾激化到一种不可调和的境地时,驱鬼师的普遍存在就成了这种人鬼对立的典型代表,消灭恶鬼也就成为驱鬼师们的职责。而《百年孤独》所呈现的拉美地区的人鬼关系,则是自然而协和的。人鬼相安无害,和谐共处,鬼魂并没有被贴上恶的标签。生命在死亡中继续,灵魂是生命的最高形式,是生命的延续。鬼魂自由穿梭,与人和谐相处。这种人鬼关系呈现出高度的协和状态,与关中地区的人鬼对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是在鬼神的存在方式上,无论是《白鹿原》还是《百年孤独》所展现的鬼神,即使它们拥有同人一样的思维和情感,也无不存在于另一个宇宙空间。但《白鹿原》中的鬼神,人无法直接感知它们的存在,需要借助于一种外在的形式(梦、附体等),而《百年孤独》中的鬼神,人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感知它们的存在,无须借助外在的形式,通过意念就可以相互沟通。无论合理与否,这种鬼神存在方式都是自然而协和的,没有因人鬼混杂而显得突兀。
三是在幽明相通的形式上,《白鹿原》中唯一的形式是间接沟通,包括鬼魂附体和托梦。例如,田小娥死后附于鹿三之体,借鹿三之口控诉现实世界的罪恶,而鹿三被附体后的举止就跟一个忸怩的姑娘一般。再就是托梦。田小娥死后托梦给鹿三媳妇,告诉世人是鹿三杀了自己。而在《百年孤独》中,幽明相通的形式就显得比较简单。鬼魂和人一样,就是另一种生命存在。人鬼可以直接交流,用意念进行交流。例如,梅尔基亚德斯与上校的意念沟通,其他人根本看不出来。另外,人鬼还可以通过捎信的方式进行间接交流,如阿玛兰妲临死前带走其他人送给去世亲人的信,就是一种间接交流的方式。
四、结语
中国和拉美地区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不仅仅因为都有着几千年厚重的文化历史,而且在进入19世纪后,大洋两侧均经历了相似的被侵略、奴役、剥削的苦难,也有着相似的反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国近代痛楚的历史经历,与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描绘的哥伦比亚历时百年惨遭外来殖民文化野蛮统治和强烈冲击的民族历史很像,但我们却能从中强烈地感受到中华民族传统历史文化所具有的厚重坚忍的独特性。《白鹿原》表现出来的鬼神观念是独特的、新颖的,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绵密的气韵和厚重的民族精神特质一脉相承的。[4]147而《百年孤独》中的拉美地区经历了相似的命运,封闭的城市,固守的观念,这把沉重的文化枷锁深深烙在每一个拉美人骨子里。拉美地区荒诞的鬼神观的存在,同样有着几千年历史文化的影响。白鹿原和马孔多的人们没有经历过欧洲那样的思想启蒙,落后保守的思想意识在突如其来的改变面前显得弱不禁风,其骨子里的这种集体无意识,对于推动民族的发展确实是无益的,但这种集体无意识却造就了瑰丽的魔幻色彩。鬼神的变幻不仅形成了各自民族独特的文化韵味,而且成就了《白鹿原》和《百年孤独》这样伟大的文学作品。
[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2]李化来.符号人生:鬼神人——符号解读《白鹿原》[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8(4):81-85.
[3]代江平.从文学人类学的视角看《白鹿原》中的神秘文化[J].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2):52-54.
[4]梁福兴.神秘魔幻白鹿原——《白鹿原》与《百年孤独》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比较[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S1):147-151.
[5]李惠芳.中国民间文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6]郑克鲁.外国文学史(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于 湘]
2016-06-16
邓子敬(1991— ),男,河南林州人,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民俗学、民间文学。
I206.7
A
1008-6390(2017)01-006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