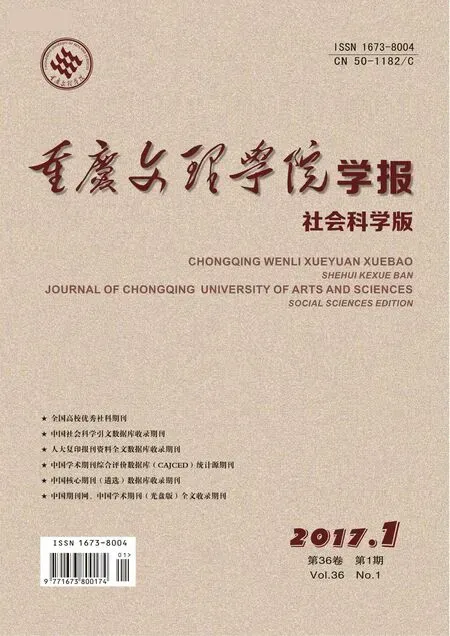《舍巴日》的民间叙事性言述
陈丽娜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北碚400715)
《舍巴日》的民间叙事性言述
陈丽娜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北碚400715)
《舍巴日》是孙健忠后期小说创作之代表,也是他热衷于表现湘西土家族神魔艺术的佳作。文本内多处使用湘西方言俚语、濒临消失的土家族语言,集中展示土家族远古神话与传说,为民间叙事提供丰富素材。在创作手法上,他巧妙地运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俯瞰全景,并采用说书式的自由叙事方式及边缘性的叙事姿态,书写土家族的民族性与民众心性,让《舍巴日》成为具有审视民族心理、阐述时代变迁、批判民族劣根性的民间叙事佳作。
《舍巴日》;土家族;民间;叙事
沈从文与孙健忠被当代学者谭桂林评为 “本世纪文学史最痴迷也是最有成就地描绘湘西文化”[1]的两位作家。作为当代土家族优秀作家,孙健忠更热衷于书写湘西土家族地区民众生活与文化,为土家族文人文学增色添彩,被学者吴正锋称为“土家族文人文学的奠基者”[2]。孙健忠的文学创作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以现实主义创作为主,如《醉乡》再现湘西土家族农村的经济改革,《甜甜的刺莓》则将目光聚焦于“四人帮”横行的“文革”时期农村真实的生活场景,赞颂从人民利益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共产党农村基层干部。而后期的小说创作则集中展现湘西土家族特有的神话、传说及民间故事,以荒诞、怪异的神魔体系审视湘西土家族民族心理,阐释湘西土家族民族历史变迁,批判土家族的民族劣根性。《舍巴日》即孙健忠后期创作的代表,文本大量运用湘西方言俚语及濒临消失的土家族语言、集中展示土家族远古神话与传说,为民间叙事提供丰富素材。同时,孙健忠巧妙地运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事,采用说书式的自由叙事方式及边缘性的叙事姿态,书写土家族的民族性与民众心性,揭示在民间叙事背后土家族的民族劣根性。文本分别从民间元素的运用、叙述策略以及民间叙事的意义三方面入手,重点阐述《舍巴日》的民间叙事性。
一、民间元素的运用
民间叙事即“民间叙事是老百姓的艺术创作,以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的方式而存在,口头性是它的基本特征”[3],如想认定文人文学是否运用民间叙事手法,应确定该作品是否运用民间元素,即对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歌谣谜语等为主体的运用,这也是作者是否站在民间立场的有力证据。孙健忠一直致力于描写湘西的民俗文化与历史变迁,将湘西土家族的神话、传说、风俗习惯融入作品中来。正如孙健忠所言:“文学艺术活动也许是人类童年时代的游戏。天真烂漫,幼稚单纯,外部世界不可思议,新奇和神秘乃至恐惧,因而产生幻觉和幻想,产生梦。这是人类童年时代的特征,也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基础。”[4]613童年的回忆几乎成为他创作的唯一主题。孙健忠不仅在作品中回忆童年时所听到的传说、故事,对湘西土家族历史变迁、民俗风情也展现得淋漓尽致。本文从孙健忠对民间神话、传说的叙述,对民间俗语、土家族语言的运用,以及对湘西土家族习俗的呈现三方面阐述《舍巴日》对民间元素的巧妙运用。
(一)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的叙述
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作为民间叙事的一大主题,它既代表人们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信仰的文化积淀。人们通过叙说民间故事或传说,表达自己对人生、生活形成的理解,以及追寻内心渴望的美好愿望。《舍巴日》是孙健忠对记忆中湘西土家族世界的再现,文中字里行间均散发出浓烈的民间气息。《舍巴日》中老惹勤勤恳恳种田务农,种出“铜壳子”、种出银元,希望再努力种出金子,这流传于湘西民间祈求富裕的民间传说改编的小说情节,是人们对天降奇迹,让人富裕,摆脱贫穷愿望的表达。文本中还描述老惹被蜘蛛精布下的网缚住,痛苦不堪,多年后网子突然散掉,老惹重获自由的情节。蜘蛛精布网即民间故事的一种,民众在劳作期间受风寒,全身酸痛,不知原因,只能以妖精施法作解释。此外,文中多次提到土家族老祖宗廪君死后化为白虎,从此土家儿女信仰白虎神,遇到劫难、灾害,或大获丰收时都会敬白虎神。湘西土家族聚集在偏远山区,人生的众多不幸难以被解释,他们只能依据情感推动艺术想象,将不能解释的客观现象加以重构,找到慰藉心灵的精神支柱、感情寄托,铜壳子、金子、蜘蛛精、白虎神即是土家儿女萌生的带有感情寄托的艺术想象。
《舍巴日》开篇讲述:
滔天的洪水退了,
世间上没有人了,只剩下葫芦船上的两兄妹,
阿哥叫不所,
阿妹叫雍尼。 ……[4]529
这些湘西土家族的创世神话,与西南地区的众多创世纪神话相似。土家族生存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繁,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繁衍面临危机,该民族创世神话也是本民族远古历史进程的反映。创世神话作为一种口头文学,其应用性强,内容丰富。正如恩格斯所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5]土家族作为一个拥有民族语言而没有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在日益进步的生产力与现代文化的冲击下,创世神话很容易被现代知识消解而失去原有的吸引力,进而导致最终的消失。孙健忠将本民族的创世神话融入文学作品当中,一方面丰富文本的历史性质,另一方面亦传承了本民族的历史与记忆,让文学作品具有较强的史料价值。
(二)方言俗语、土家语的运用
方言俗语是展现一个地区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亦是承载一个作家民间建构的必要手段。方言俗语、少数民族语言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它能够让读者感受到本地区的文化特色。孙健忠的文学创作与沈从文一样,致力于呈现湘西民族文化,因此在文学创作中常使用湘西方言俗语及土家语言,用心营造他心中的湘西大地。
《舍巴日》中语言运用最具特色的是谚语与俗语,如 “姑家女,伸手取,舅家要,隔河叫。”[4]545展现湘西土家族在婚姻法颁布以前,流行近亲结婚,尤其是姑表婚,舅舅家具有优先拥有姑姑家女儿的婚配权。“天下百艺,做田为本”[4]549,说明湘西土家族民众重农心理,种田耕土才是最本分的职业。湘西土家族原生态谚语俗语作为土家族民众思维形成作品的主要工具,它所反映的是民众的人生经历与坚守。孙健忠受到湘西语言的浓烈影响,在文学创作上努力追求最原始、最民间的形态,将原始生命张力与自然主义美学彰显到极致。
方言词汇的运用亦有精彩之处,湘西方言词汇展现的是一个较为粗俗但极具真实性的民间世界。如“啊哞一口”中“啊哞”作为象声词,表示将嘴巴张得很大后发出的声音,这在湘西的使用频率极高,尤其是描绘鬼怪野兽吃人的场面;再如“背时、砍脑壳”,隶属湘西民众骂人的粗俗用语,孙健忠在文学创作中的使用让作品更显“湘西味儿”。其他词汇如“功夫”(农活)、“几时”(很早)、“咬起牙巴骨”(咬紧牙关)、“血翻”(烦躁到极点)、“起火”(非常生气)等,都具有湘西所独有的山味儿。此外,湘西方言中儿化音众多,如伢儿、锅儿、碗儿、罐儿、慢慢儿、蜂子儿、萝卜秧儿、钵儿等,都是湘西方言的显著特色,作者对此的巧妙运用让读者在阅读文本时直达热情奔放的湘西世界,以此展现《舍巴日》的民间状态。《舍巴日》中土家语言的加入让民族性凸显得更彻底,如“梯玛”(土老司)、“掐壳”(大森林)、“掐普”(花儿)、“里也”(可耕种的土地)、“啊撮”(岩洞住屋)、“麦岔”(好晴天)等都是《舍巴日》中民间元素的构成,是反映土家族民族特色的重要标志。
正如孙健忠自己所说:“从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追求上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我力求在作品中写出那么一点‘湘西味’,那么一点‘山味’和‘野味’。”[6]孙健忠对湘西方言俗语、土家族语言的使用,让这种具有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的“湘西味儿”表现得淋漓尽致,文本大量引用湘西土家族原生态方言俗语,让人物形象更具民族性的自然本真,提升了小说民族性的主题。
(三)湘西土家族习俗的呈现
别林斯基曾说:“风俗习惯构成着一个民族的面貌,没有了他们,这民族就好比一个没有面孔的人物,一种不可思议、不可实现的幻想。”[7]习俗是人类社会群体在民族进程中形成的共同文化意识,在同一区域或同一民族,许多的民风习俗是人民心底特定的法约力量,它会限制人们的生活方式,引导人们跟随约定的步伐前进。
《舍巴日》将环境背景置于湘西地区,也建构出众多湘西特有的民间习俗。如作品中详细记录掐普出嫁时的“抢亲”古仪,新娘被藏在某处,迎亲人必须找到,寻找过程中还会受到阻挠,最后当收到礼品后,新娘的家人停止阻挠,任由新娘被抢去。此外,《舍巴日》中有一段关于丰收禳祈的描述:“屋后果林里,有人在为来年的丰收禳祈。一个人拿把斧头在果树上敲打,并且边打边问:‘结不结?’一个提灯笼的角色回答:‘结,结得像饭团!’问:‘甜不甜’答:‘甜,甜得像蜂糖!’‘掉不掉?’‘不掉,结得牢又牢!’独眼老惹知道,当提灯人回答:‘结得像饭团’这话时,应将预先准备下的饭团随手朝果树上撒去。”[4]596这种习俗与弗雷泽在《金枝》中提到的模拟巫术与接触巫术一致,人们为了祈求果树大丰收而通过语言表达出自己的希冀,并通过扔饭团的行为模拟祈求果实的丰收。这些流行于湘西民间的习俗表现出作者在文学作品中极力建构土家族族群意识,既有助于对人物形象的深度刻画,又有益于表现土家人民特有的民族心理与性格,也最有力地表达了《舍巴日》的民间叙事性。
二、叙述策略下的民间叙事性
孙健忠通过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全面书写了十必掐壳与里也的生活状态与时代变迁,并采用说书式的自由叙事这种随意的、明显带有传统民间文学叙事特点的叙事策略,将《舍巴日》的民间叙事性凸显出来。《舍巴日》同时将视野聚焦于原始部落的流变以及现代化影响下的湘西土家族山寨,采用边缘性的叙事姿态,凸显《舍巴日》的民间叙事性。
(一)第三人称叙事视角
视角指“叙述者或人物与叙事文中的事件相对应的位置或状态”[8],而叙述视角指叙述者在讲述故事的过程时所采用的角度和方式。民间叙事一般多采用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分为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与限知视角两类,《舍巴日》即采用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全知叙述视角的特点是“没有固定的观察位置,‘上帝’般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可从任何角度、任何时空来叙事:既可高高在上地鸟瞰概貌,也可看到其他地方同时发生的一切。对人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均了如指掌,也可任意透视人物的内心”[9]。《舍巴日》的叙述者作为全知全能的“作家”,作品中的场景、时代背景、人物形象及故事情节等无不处于其调度之中、主宰之下。
文本中的叙述者站在全知的角度向读者展示了三条人物主干线:一是掐普作为原始社会、野人部落的女儿,嫁到农业文明社会之后所遭遇的不幸与痛苦。借此反映湘西土家族儿女在面对现代意识的冲击下所受的伤害与不快,导致最后做出逃避的反应,以此穿透湘西土家族的整个历史经历与社会人生。二是独眼老惹在经济时代环境冲击下的保守与传统所造成的悲剧,为了阻挠小儿子背离土地,像大儿子、二儿子一样奔向文明社会,他以死相逼让宝亮娶了原始部落的掐普,导致悲剧的发生。三是宝亮想要出走的欲望与受阻,宝亮一心想要加入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却无奈被市场经济下的丑恶人性送上一刀,阻挠了也割断了他出走的道路。整篇小说作者都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俯瞰掐普、独眼老惹与宝亮的经历,站在客观的立场与旁观者的视野下审视湘西土家族民众面对现代市场经济文明时的民族心性,在批判市场经济下人心险恶的同时也批判了土家族保守狭隘的民族劣根性。
(二)说书式的自由叙事
《舍巴日》作为承载土家族民族文化、表现民族心性的代表作,孙健忠必会抓住彰显民族历史与民族文化的机会,于是将作品与民间文学说书式的自由叙事结合起来,以此展现《舍巴日》自由、随性的民间叙事性。总体概观,《舍巴日》以空间叙事机制为横向坐标,从而推算湘西土家族的时间叙事机制,由此掌控整篇小说的发展方向。正如文本所说:“从十必掐壳(小野兽和大森林)出发,走到啊撮(岩洞住屋),又走到麦岔(好晴天啊),最后到达了目的地——里也(可耕种的土地)。她当然不明白,这原是一个民族所走过的路。同样一条路,这个民族走了几百年,而她只走了几十天。”[4]554土家族的历史从空间到时间交错前进,总体看似叙事逻辑清楚紧凑,但仔细阅读文本,便会发现《舍巴日》杂乱分散的自由叙事性。如第二章介绍里也的基本情况后,直接跳到马蹄街的景象上,这种空间跳跃是完全自由式的,没有太大的逻辑联系。而后讲述宝亮因饭铺老板与西尼嘎的串谋迫害被警察带走后,一边叙述掐普为救出宝亮求白虎神后胡言乱语,一边又写独眼老惹将心思置于收谷之上,这时的老惹仿佛完全忘记还在监狱的儿子,一天忧心忡忡地盘算着要怎样更好地获得丰收,期间还插入大儿子与二儿子突然回家昏睡七天七夜醒来又马上离开里也的情节,最后讲述赶年、过年的到来,大老王寻思租赁老惹的田土被斩钉截铁地拒绝,掐普在得知宝亮要被放回后的回归。这种完全跳跃式的叙述方式逻辑性较弱,让读者有些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但总体而言,作者通过时间、空间跳跃背后的自由叙事方式表达了对土家族民族历史进程中所遭遇挫折的同情以及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
(三)边缘性的叙事姿态
孙健忠是一直致力于书写湘西世界的土家族作家,他后期的创作热衷于对湘西土家族神魔体系的建构。在《舍巴日》中,孙健忠将假定性的原始部落与野人融入现实的农耕文明社会,将土家族的神魔体系摄入现实体系,这种假定性因素成为诠释主题的决定性因素,现实与假定交叉开展的两条线索使文本的叙事出现边缘性姿态。《舍巴日》中掐普作为原始部落野人,因对外界的向往,而跟着查乞从十必掐壳一直往外走,经过啊撮、麦岔后到达里也,走到文明世界。文本中掐普经过的几个地方现如今在湘西仍旧存在,但十必掐壳的野人世界早已消失,他们是从假定环境走向现实环境,标识着一个民族由原始社会走向市场经济社会的经历。当掐普嫁给正在追求市场经济文明社会的宝亮时,她不懂得文明与礼貌,一身的野人气息无疑会成为宝亮追求经济文明的绊脚石,而聪明热情、作为当代文明代表的岩耳却是宝亮心仪的对象。但独眼老惹作为农耕文明的代表人物,他不能接受宝亮从田土中逃离,走上从商的“伤风败俗”之路,于是以死相逼要求他娶了掐普。宝亮与岩耳的自由恋爱思想很明显背离了传统文化,在他们努力争取的同时也触发了与掐普、老惹的矛盾,这也是年轻人在追求现代文明必然遭遇的矛盾。而掐普这一假定的原始部落野人注定是不属于文明社会的。于是在作品最后,掐普逃离了农耕文明社会与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孙健忠将假定的野人因素与现实中的追求现代文明的青年结合在一起,这种光怪陆离的结合表现出《舍巴日》边缘性的叙事姿态,同时,野人部落是土家族最原始的部落,孙健忠将此注入文学作品,旨在表现其对民间文学的重视,由此揭示文本背后所隐藏的民间叙事性。
三、民间叙事的意义所在
民间叙事是通过对某一地区的民俗文化、历史变迁的描写来反映民众思想、心理及趣味,是关注社会底层老百姓的叙事。《舍巴日》采用反映现实与自由想象相结合的民间叙事手法,将湘西地区土家族民俗文化、生活习俗展现于读者面前,土家族历史变迁的民族史诗彰显于世,并由此审视土家族的民族心性,形成对土家族的民族劣根性的深刻反思与严厉批判,这也是孙健忠在作品内容上的创新。正如吴正锋在《土家族民族历史叙事与湘西神魔艺术建构——孙健忠后期小说创作研究》一文中所说:“发表于1986年《芙蓉》杂志第1期的《舍巴日》标志着孙健忠创作的转向,孙健忠开始有意摆脱对土家族社会生活的纯粹政治叙事视角,转而从湘西土家族民族历史变迁的文化层面进行描绘。”[10]可见,孙健忠采用民间叙事的方式,将目光聚焦于湘西土家族民众生活与历史变迁,摆脱前期作品如《甜甜的刺莓》《醉乡》限于政治批判的狭隘视野,更具文学魅力。
(一)土家族民族性的书写
“民间叙事深刻地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思想感情、生活智慧和沉淀于意识深层的历史记忆,从显、隐两方面体现着一个民族的心灵世界。”[11]孙健忠作为土生土长的湘西土家族作家,“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家”,他的记忆大多是对童年时期湘西世界的记忆。孙健忠甚至在谈论到自己的创作时说:“童年时的回忆对我竟如此重要,使我着迷,几乎成为我创作的唯一母题。”[4]613他脑海中的湘西土家族风俗文化、历史变迁成为其创作的主要源泉,并运用民间叙事的方式构建起他心中的土家族世界。本文第一章作为民间叙事的基础——民间元素的运用,将湘西土家族的创世纪神话、神魔传说以及方言俗语加入文本之中,彰显土家族的民族记忆,是作者民族性书写的最好表现。其次《舍巴日》描写来自原始部落的土家族姑娘掐普嫁到受现代文明感染的里也,她不洗脸、不洗澡,吃肉连毛,吃酒连糟,吃饭是猪拱潲,还用粗茅扦打死放养的家猪,与宝亮做爱时“像母狼一样,残忍地撕咬宝亮,露着尖利的牙齿,伸出长满小刺的舌头,还伸出一对锋利的前爪……”[4]568十足一个野人,但土家族最古老的祖宗廪君化作白虎神的原始神话是她骄傲的因素;会跳舍巴日(摆手舞)是她自豪的源泉。她要求与现代文明的标志品岩耳比试投剑、划土船、打野猪、采野果子,最后还因岩耳的不应战而鄙视她。很明显,掐普是孙健忠塑造的一个带有神魔色彩的土家族原始文化的承载者,她了解土家族的由来与原始文化,是民族的标志性人物形象,孙健忠正是通过边缘性的民间叙事方式来刻画的。其次孙健忠对跳摆手舞、抢亲、祭果树神等土家族习俗的叙述,既是民间叙事性的特征所在,亦是通过民间叙事的书写方式来诠释土家人民特有的民族心理与性格,有利于建构土家族的族群意识与特有的民族性。
(二)为土家族民众而作
民间叙事一直是为百姓而作,是植根于平民生活的创作。孙健忠作为土家族代表作家,一直将目光聚焦于土家族民众,书写土家族的传统与历史,这也是《舍巴日》民间叙事性的体现。作品中的主人公掐普、宝亮、独眼老惹都是湘西土家族儿女的代表形象,掐普作为原始社会土家族女儿,她热情奔放、勤劳刻苦,且努力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从第一次查乞对里也如天堂般的描述,煽动起他心中的那点向往,于是为了自己向往的生活,踏上了走出十必掐壳的道路;当与宝亮结婚后,发现丈夫爱着的是另外的女人,她并没有选择退缩,而是勇敢地与之理论,这是对土家儿女坚持自我、勇敢向前的民族心性的彰显。但同时,这中间不乏土家人冲动与鲁莽的心性,孙健忠对掐普的这些性格的凸显也是对土家人某些民族劣根性的讽刺。当宝亮被警察带走后,掐普求白虎神帮助的那种执着与坚持,是土家族民族心理的标志性特点。最后当掐普发现自己不属于文明世界,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表明她的果敢与洒脱,作者又对这种性格给予高度赞扬。
而宝亮作为追求市场经济下的现代文明的热血青年,在父亲以死相逼下,不得不娶掐普为妻,这种结果也是必然的。土家族位于武陵山区,交通闭塞,思想落后,市场经济刚出现不久,这与当地的传统农耕文明是相悖的,他对现代文明的追求备受质疑,所以也注定了他爱情与事业的悲剧。独眼老惹作为思想保守狭隘的顽固派,千方百计地阻止儿子们舍弃田土,并以死相逼,包办宝亮的婚姻,也拒绝一切工业化、机械化,相信双手能种出金子,这一切表明了他对土地的痴迷与固执。同时,作者通过对老惹的塑造,以文化人的视野去揭示湘西土家人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展现出来的狭隘、固执、落后和保守的民族劣根性。《舍巴日》以民间叙事为手段,为湘西土家儿女书写民族历史变迁的史诗长卷,在这史诗背后,土家人美与丑的民族心性得以审视,这才是民间叙事的意义所在。
四、结语
《舍巴日》是孙健忠由现实主义转向土家族神魔艺术创作的标志性作品,作品以土家族习俗为名,内容以土家族历史变迁为主,书写土家族的神话、传说等异域奇观,运用民间叙事的边缘性手法,关照和穿透湘西土家族的社会人生,将湘西土家人的精神面貌与民族性格全面呈现于读者面前。综上所述,孙健忠作为土家族文人文学的奠基者,他不断地努力探索,锐意进取,在寻求到湘西神魔体系的新领域后,一直致力于通过现实性与假定性的结合,展示土家族的远古神话、传说与风俗文化,书写土家族的民族历史与民众心性,这些具有土家族永恒性的东西将会得以流传,而对这种东西的深究与探讨也极具意义与价值。
[1]谭桂林.守着土地,也守着那份浪漫与真情——读孙健忠《倾斜的湘西》[N].湖南日报,1991-06-19(3).
[2]吴正锋.孙健忠:土家族文人文学的奠基者[J].文学评论,2008(4):170-174.
[3]董乃斌,程蔷.民间叙事论纲:上[J].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3(2):12-21.
[4]孙健忠.魔幻湘西[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3.
[6]孙健忠.文学与乡土[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7]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M].成都:时代出版社,1953:41.
[8]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9.
[9]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04.
[10]吴正锋.土家族民族历史叙事与湘西神魔艺术建构——孙健忠后期小说创作研究[J].求索,2010(7):204-206.
[11]董乃斌,程蔷.民间叙事论纲:下[J].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3(5):38-51.
责任编辑:罗清恋
Research on the Folk Narrative of Sheba Days
CHEN Lina
(School of Literature,Southwest University,Beibei Chongqing 400715,China)
Sheba Days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late novels of Sun Jianzhong and is also the masterpiece of showing the Tujia mythical artistic item.There are a lot of Xiangxi slang dialect,the endangered Tujia languages and Tujia ancient myths and legends in the novel to provide rich material for the folk narrative.Sun Jianzhong used the third-person omniscient point of view in the creation cleverly and wrote Tujia Nationality and people’s heart and mind by the free way of storytelling and the edge of the narrative attitude,so Sheba Days is looked into a folk narrative works to gaze at the national psychology,explain the changing of the times and criticize the national evil.
“Sheba Days”;Tujia nationality;folk;narrative
I207.7
A
1673-8004(2017)01-0034-06
10.19493/j.cnki.issn1673-8004.2017.01.006
2016-10-31
陈丽娜(1991— ),女,湖南湘西人,土家族,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少数民族文学与民俗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