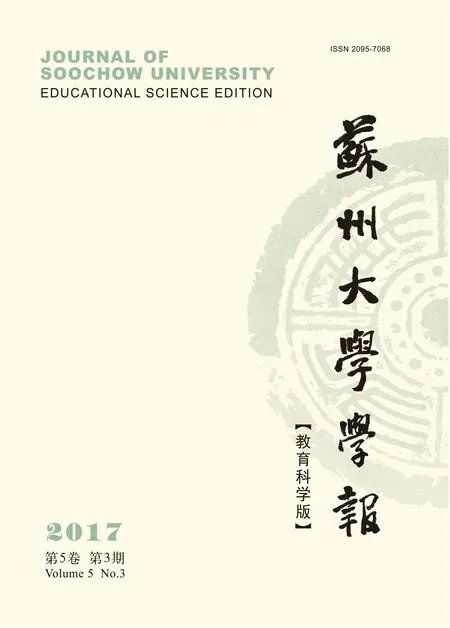意识研究的量子力学方法兴起
陈 向 群
意识研究的量子力学方法兴起
陈 向 群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从量子力学角度来解释意识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意识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它源于意识和量子力学在解决量子测量问题过程中的关联。量子物理学家不仅基于量子理论角度积极寻找人脑内的量子效应,而且还提出了相当多解释意识问题的意识理论,为意识问题的量子力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相较于以往,量子力学解释意识问题不再拘泥于复杂的神经计算,不仅极大地突破了原有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而且对人工智能研究也具有新的启示,意识研究的量子力学方法具有积极的意义。
意识问题;量子力学;量子理论
在意识科学不断发展的今天,意识研究的方法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以神经生物学方法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同时,量子力学方法逐渐兴起并发展成为与神经生物学相竞争的另一研究进路。研究首先是从寻找大脑中的量子效应开始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希罗姆·乌姆扎瓦(Hiroomi Umezawa)为代表的一大批物理学家就积极地从量子理论角度来描述人脑内的神经生物活动,并提出了各种量子大脑理论假设,量子大脑动力学(quantum brain dynamics,QBD)逐渐兴起。不仅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戴维·玻姆(David Bohm)、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亨利·斯塔普(Henry Stapp)等量子物理学家还纷纷提出了各自理解基础上的意识理论,我们称之为意识的量子理论(quantum theory of consciousness),为量子力学解释意识问题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最终,在世纪之交,量子力学方法成为包括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在内的大多数意识研究者所认同和接受的新方法,一种在量子力学视域下的意识研究路径在意识研究领域内逐渐兴起。
一、意识和量子力学的最初联姻
在意识研究领域内,量子力学方法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原因的。在量子力学建立之初,着眼于解决量子测量问题,量子物理学家们就引进了观察者这一主观因素,希望借助观察者有意识的观察来坍缩波函数,以达到调和宏观世界和量子世界在描述物质状态存在相矛盾的目的。而最先提出测量过程中的主观主义解释的当属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马克斯·波恩(Max Born),他基于对波函数物理意义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波函数的概率诠释,认为波函数并不是三维空间中的电磁波那样的真实波,而是多维空间中的概率波,其模的平方(绝对值平方)的大小决定粒子在该处出现的分布密度。玻恩认为,波函数的演化并不是遵循薛定谔方程(Schrödinger equation)的U过程,而是遵循着R(Reduction)过程,即波函数在收到外界观察和测量时会发生坍缩,而引起波函数坍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观察者的测量。于是,在玻恩对波函数的概率的诠释中,他首次提出了测量过程中“观察者的测量”这一主观因素,被认为是意识和量子力学关联的开始。
如果说玻恩只是提出了测量过程中的主观因素,而在玻恩之后,围绕着“薛定谔的猫”(Schrödinger’s cat)所引发的争论则正式将测量问题的解决指向了意识(consciousness)这一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薛定谔的猫”是由奥地利著名物理学家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在1935年所提出的著名思想实验。薛定谔认为,波函数的物理意义并不是将其作概率波解释,因为它是永远处于叠加态的物质波。鉴于此,薛定谔假设了这样一个思想实验。在这个实验中,有一只猫、一瓶毒药、一个锤子和一个开关共同存在一个密封的箱子里。其中,锤子位于毒药瓶的上方,它由开关所控制,如果开关打开,锤子下落,毒药瓶被打碎,猫就必死无疑。相反,开关不打开,猫则安然无恙。而更为关键的是,开关的打开与否是由具有概率性放射的原子衰变来控制的,其衰变与不衰变的概率均为50%。[1]42这样,根据玻恩对波函数的概率诠释,箱子里的猫则时刻处于“既死既活”的叠加态中。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佯谬,即箱子里的猫所可能存在的“既死既活”的状态,它在现实中我们却永远无法观察到。难道量子力学是不完备的理论吗?它只适用于微观世界?
然而,也正是基于解答这个问题,物理学家魏格纳正式将波函数坍缩的最终原因归结为了观察者的意识。在其论文《关于心身关系问题的评论》中,他提出了另一个思想实验“魏格纳的朋友”(Wigner’s friend),试图通过其朋友的观察来告诉我们,观察者的意识是猫波函数的坍缩的根本原因。魏格纳假设,他有一个朋友戴着防毒面具,在箱子里观察薛定谔那只顽皮的猫,而魏格纳本人则在箱子外面观察整个箱子里的情况。在一段时间以后,如果你问他朋友箱子里猫的状态,他朋友一定会告诉你只看见了一只“要么死,要么活”的猫,而非“既死既活”的猫,原因就在于他朋友的意识坍缩了猫的波函数,即在其朋友观察猫之前,他头脑里已经早已预设了猫的状态。[2]然而,源于休·埃弗雷特(Hugh Everett)的相关态解释(relative state interpretation)的多世界解释(many worlds interpretation)理论则否认意识坍塌了波函数,而是认为,在测量过程中,包括观察者、被测系统和测量仪器在内的复合系统的波函数分裂成了多个分支态,形成多个平行的世界,而造成波函数分裂的原因同样是观察者的意识。就如狄维特所说:“不可避免的是,在测量后通常不再是个单一的状态。而是由叠加状态所组成的复合系统,其中的每一个分子都包含了一个确定的观察者状态和一个确定的物体系统状态。”[3]10这样,在多世界解释理论看来,之所以我们在现实当中观察不到薛定谔那只顽皮的猫,原因就在于观察者的意识使得猫的波函数发生了分裂,以至于我们只能观察到自己世界中的猫状态。
因此,通过玻恩关于波函数的概率诠释以及围绕着如何拯救薛定谔那只顽皮的猫所引起争论,我们可以看出意识才是解决测量问题的主要因素。这样,着眼于解决量子测量问题,意识和量子力学发生了关联,成为日后量子物理学家从量子力学角度来寻求解答意识问题的依据。对此,现纽约大学著名哲学家教授大卫·查尔莫斯就说:“我之所以频繁地提到意识和量子力学之间的联系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有意识的观察者的测量要求引起波函数的崩溃。按照这一解释,意识在物理学理论中起着核心作用。”[4]149
二、寻找大脑中的量子态
如果说在量子力学建立之初,意识参与了量子理论的构建,成为了人们从量子力学角度来解释意识问题的初衷。那么,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不断有量子物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试图从人脑中寻找相关的量子效应,则可以看作量子意识研究从最初的构想到实践研究的开始。其中比较典型的有,日本量子物理学家乌姆扎瓦(Hiroomi Umezawa)从量子场论的角度来理解人脑,将记忆等意识现象理解为能大脑皮层场中能量子的能量交换过程;神经生物学家弗洛里希(H. Fröhlich)提出了神经网络中的量子相干波概念;神经生物学家吉布(Mari Jibu)和雅苏(Kunio Yasue)则认为,脑量子场中皮层子和玻色子运动所形成的量子相干态伴随着细胞内的量子信息转换过程。这样,在乌姆扎瓦、弗洛里希、吉布和雅苏等人的努力下,量子大脑动力学理论逐渐兴起,为之后量子物理学家建立意识的量子理论提供了生物基础。
量子大脑动力学的兴起最先源于日本物理学家乌姆扎瓦从量子场论角度来解释人脑内神经元细胞的量子相干过程。在乌姆扎瓦看来,记忆就如量子场中的全息图片,它是个非定域性的整体性活动。在1967年到1979年的长达10多年的时间内,乌姆扎瓦先后与他人合作发表了三篇关于脑的量子场论的论文,最终将记忆等意识现象理解为大脑皮层场(cortical field)中皮层子(corticons)的发放和吸收的动态过程。乌姆扎瓦认为,人脑是个非常复杂的生物系统,既有位于微管蛋白质以及细胞膜内的电子所组成的亚微观系统,也有神经元生物分子及其电化学传递所组成的微观系统,以及神经网络所组成的宏观系统。而位于亚微观系统内部电子的振荡运动所形成电偶极矩(electric dipole moment)则组成了具有量子相干性的皮层场(cortical field),其内部的电子则称为皮层子(corticons)。但皮层场不是孤立的场,它通常会与其他的能量场(微观分子系统以及神经网络宏观系统)发生能量交换,最终导致皮层子的发放和吸收,而意识就产生于这个能量交换过程中。“我们认为,皮层子和光子的创造和消失动态过程就是意识的物理过程,它可以通过量子真空态来实现,即能量从神经和树突网络的宏观系统传递到丝状的蛋白质分子的微观系统所形成的物理状态。”[5]182
几乎与乌姆扎瓦提出脑量子场概念的同时,弗洛里希在相关研究基础上也提出了神经网络中的量子相干波概念。他认为,生物分子的细胞膜中由于存在着电势差,使得多余的能量聚集而形成类似于波色—爱因斯坦凝聚态(Bose Einstein Condensation)的同一态。在其中,存在着电子的偶极矩(dipole moment)或相干矩(coherent moment),而处于偶极态的电子两极会以大约每秒1011~1012赫兹(Hz)频率发生振动进而产生量子相干波。弗洛里希认为,这种量子相干态不仅存在于细胞膜中,而且还存在于生物分子的化学键尤其是氢键(hydrogen bonds)以及一些非定域性的电子区域内。不仅如此,弗洛里希还通过对酶(Enzymes)分子的实验,进一步证实了细胞膜内所存在的量子相干效应及其振荡行为。
在弗洛里希之后,神经生物学家吉布和雅苏基于乌姆扎瓦的脑量子场论基础上提出了神经信号的量子转换假设。在他们看来,大脑内量子场中的玻色子和皮层子的长距量子相干波伴随着细胞内量子信息的转换机制,它们能对因玻色子的运动所形成的热能量具有抵消作用,从而使得大脑中长时间保持量子相干态,对意识的产生极为重要。“从理论角度来说,由玻色子运动所引起的细胞内量子信息转换的全局性系统是实现大脑动态的非定域性对称性的关键。没有量子场论的长距信息转换,大脑也就无法长时间保持导致意识出现的对称性的动态机制。”[6]不仅如此,吉布和雅苏还认为,具有非定域性的长距量子信息转换并不局限在人脑中,它还遍布于我们身体的各个生物器官内,实现着人的全身信息的流通。因而,一旦细胞内的量子信息转换受阻,信息无法在身体内顺利互动,我们就失去了意识,这或许也就很好地解释了麻醉的作用。
这样,在乌姆扎瓦等量子物理学家的努力下,量子大脑动力学理论逐渐兴起,极大地推动了意识研究的向前发展。从此以后,人们不再仅仅是从神经科学的角度将人脑内的神经元活动理解为单纯的神经生物过程,量子效应也被认为是其中可能存在的现象,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人们对大脑活动的固有认知。近年来,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卡维里理论物理研究所(Kavli Institute for Theoretical Physics)教授马修·费舍尔(Matthew Fisher)从波斯纳分子群(posner molecules)中寻找量子效应就可以看作是量子大脑动力学理论的延伸。费舍尔认为,波斯纳分子群中的磷原子核的自旋状态就是一种量子纠缠现象,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和思维。[7]
三、量子力学解释意识的主要理论
与神经科学家解释意识建立了各种精彩纷呈的意识理论一样,量子物理学家在研究意识过程中也同样建立了各种意识理论,我称之为意识的量子理论(quantum theory of consciousness)。意识的量子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并最终在世纪之交成为多数意识研究者所接受和认同的意识理论。与意识的神经科学理论对意识的神经过程解释不同,意识的量子理论着眼于量子理论,从人脑内寻找相关的量子机制来解释意识,并最终将意识理解为量子活动的结果。在所有的意识的量子理论中,比较典型的有意识的序解释、Orch OR模型、心理物理理论、心脑相互作用二元论、“量子自我”理论等等,这些理论的提出得益于之前量子物理学家们对大脑中量子效应的研究,同时也促进了相关研究的向前发展。这里我们不妨选取其中几个主要的意识的量子理论作简要阐述,来看看它们究竟是如何来解释意识问题的。
1.意识的序解释:意识是脑内神经元对脑外物质的全息投影
1980年,戴维·玻姆(David Bohm)在其《整体性与隐缠序:卷展中的宇宙与意识》一书中,提出了从隐缠序(implicate order)理论角度来解释意识问题的新方法。玻姆认为,我们大脑中的神经元就如量子,它们在大脑内的运动具有隐缠序规律,而意识就是脑内神经细胞对脑外物质的全息投影。具体来说,当我们看物体时,物质通过视网膜以量子信息的方式“卷入”到我们大脑的神经细胞内以全息形式储存起来,一旦全息记录被激活就在大脑中形成了神经全息图,它隐含了脑外物质的所有信息特征,而这个神经全息图就是意识。在这里,物质的信息特征隐含在神经细胞内并在一定时刻展现出来的过程就是一个隐缠序过程。[8]105可以看出,玻姆关于意识的序解释是建立在全息脑理论基础上的,它将意识理解为脑内神经细胞对脑外物质的全息投影也为我们从整体性角度去看待意识及其特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从某种程度上也反驳了传统身心关系的二元论。
2. Orch OR模型:意识是微管内量子引力所引起的波函数坍缩的结果
Orch OR模型是由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和斯图亚特·哈梅洛夫(Stuart Hameroff)在20世纪90年代所共同构建的一种量子意识模型。它主要由两个部分所构成,分别是OR和Orch,前者是指客观还原论,后者是“Orchestrated”的缩写,指的是对微管中的客观还原进行精心编制或谐调。在彭罗斯看来,量子系统中并不是意识坍缩了波函数,而是波函数坍缩导致了意识的产生。而且,彭罗斯还认为,波函数的坍缩是由量子引力所引起的客观坍缩,所以称之为客观还原,以区别于哥本哈根解释的主观还原。在此基础上,彭罗斯结合哈梅洛夫的微管结构理论,认为客观还原所发生生物场所就在微管结构中。这是因为,微管表面的微管蛋白内的电子会在伦敦力(London forces)的作用下形成具有量子特征的耦合态,它们会在量子引力达到一定阈值时发生坍缩,而意识就源于电子耦合态的坍缩过程中。[9]不仅如此,哈梅洛夫认为,客观还原在微管中的量子活动就如乐队进行编曲一样,是精心编制(Orchestrated)的过程。由此,在彭罗斯和哈梅洛夫共同努力下一起建立了基于OR理论和微管结构基础上的意识的量子理论,即Orch OR模型。
3.心理物理理论:意识是对顶层神经编码的选择
著名量子物理学家亨利·斯塔普(Henry Stapp)认为,意识不仅是心理层面的,而且还是个物理过程。基于多年的量子物理学研究并结合神经科学对意识研究基础上,他在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了一种心理物理理论(the psychophysical theory),认为意识就是对人脑顶层神经编码的选择。斯塔普提出心理物理理论是基于他对人脑神经结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在他看来,物体的不同特征对人脑的刺激会导致人脑内出现多重神经发放模式,而当这些发放模式最终协调集合为某种统一发放模式(通常是40赫兹)时整体性的意识就会出现,那么,意识事实上就是对导致意识出现的最高兴奋水平的神经发放模式的选择。如果每重神经发放模式就是一种神经编码,那么,意识就是对顶层神经编码的选择。[10]107-108不仅如此,斯塔普还从心理物理理论角度对意识的感受性做了解释。在他看来,之所以不同意识主体对相同物体特征的感受性千差万别,是因为表征这些特征神经信息在人脑内所注册的神经编码不一样。
以上简单介绍了几个意识的量子理论,并阐述了它们是如何从量子理论角度来解释意识在人脑中产生的。总的来说,它们对意识的解释都是在借鉴量子力学的相关机制如叠加性、纠缠性基础上来说明的,可以说为我们从物理学的新视角来看待意识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说明。有了意识的量子理论,量子力学解释意识问题就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此以后,从量子视域下来解释意识问题不再只是泛泛而谈,而是有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四、相关的积极意义分析
当前,意识研究虽然面临着不少困境,但这并不表明意识研究就应该停滞不前。而量子力学方法的兴起不仅为我们突破当前困境提供了新的希望,而且具有积极的意义。具体来说,它不仅使得意识研究方法有了新的突破,而且避免了传统神经科学所坚持的神经计算方法的复杂性,更是为当前人工智能研究提供了新的启示。
首先,弥补了意识和物理学在研究疆域上的界限,弥补了意识研究方法的不足。在以往,人们都认为,意识作为一种描述人类心智活动的精神现象,它与描述自然界中物质运动规律的物理学是不相关联的。然而,随着量子力学的诞生,意识研究的疆域不再局限在哲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它还拓宽至物理学领域。这是因为,量子力学作为20世纪所兴起的一门新物理学,它与传统物理学有着很大的不同。它不再只是从决定论和机械论的观点来看待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而是基于非定域性、不确定性、概率性、纠缠性等“反常性”观念来理解微观世界中的粒子运动规律。而量子力学的这些“反常性”特征都与人脑内的神经元细胞活动具有某些相似性,自然,从量子力学角度来解释意识就变得有了可能性。而随着量子力学方法加入到意识研究中来,意识研究的方法也必将更加丰富多彩。
其次,避免了传统神经科学方法在解释意识上的复杂性,使得意识解释更加简单明了。神经科学在意识解释上坚持神经计算解释,即将意识理解为脑内神经元细胞之间神经信息的加工计算的结果。这样的意识解释是复杂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人脑是个非常复杂的生物系统,其内部存在超过几百亿个神经元,即便可以通过实验仪器去观察神经元的发放活动,但我们也不能精确计算出各神经通路之间的信息值;另一方面,意识本身也是复杂多样的,不仅同一个物体的不同颜色、大小、形状,大脑神经元的反应各异,而且不同物体对大脑的相同脑区的神经刺激也存在不同,我们又如何去计算这些复杂意识的神经信息值呢?而不同于神经科学对意识的解释,量子力学将意识本质上理解为脑内量子活动的结果,这样的意识解释根本不用考虑神经信息之间的神经传递值,而只须根据量子的活动机制来描述意识的产生过程,必将大大避免神经计算的复杂性。
再次,对当前人工智能研究具有启示意义。当前人工智能研究是建立在神经科学的计算主义基础上的,它以认知主义和联结主义为理论基础来模仿人脑的运动规律,希望以此达到真正具有人的智能能力。然而,从目前情况来看,当前人工智能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突破,但是其所具有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并不能具有人脑所具有的逻辑性、对语义的分析性以及对文化的认知性,更不能具有人的感受性和意向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脑是个生物脑,是长时间进化而来的,而人工智能脑是个由金属材料和塑料等组合而成的机器脑,因而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具有人的意识。而根据Orch OR模型,人脑是具有高强度相干态的量子脑,意识产生于神经元微管结构的量子过程。人工智能研究或许可以借鉴Orch OR模型对意识的研究,将意识理解为脑内量子活动,构建一个具有量子特征的量子脑来模拟人的意识或许是一种候选的方法。
结语
以上,自20世纪初,意识和量子力学发生关联以来,量子物理学家基于量子理论角度来描述人脑内的神经生物活动,量子大脑动力学兴起。在此基础上,量子物理学家建立各种意识的量子理论,为意识的量子力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样,在世纪之交,一种在量子力学视域下的意识研究新路径在意识科学领域内逐渐兴起。不仅如此,量子力学方法作为研究意识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它不仅突破了意识和物理学之间固有的研究界限,避免了原有方法的复杂性,而且为当前人工智能研究提供了新启示。然而,作为研究意识的新方法,量子力学方法也同样具有不少缺陷,如它将意识理解为脑内量子活动的结果,但并没有就量子意识所具有的特点作具体说明,因而使得其在解释意识产生的因果性上过于模糊。不仅如此,量子力学方法在解释意识上还极大地依赖于脑的神经活动,其在理论构建上显然并不是完全物理意义上的。再者,最主要的是,相关理论并没有得到实验强有力的证实,这恐怕是量子力学方法遭受各方面质疑的最主要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量子力学方法作为研究意识的一种新方法它极大地推动了意识研究的向前发展,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
[1]李宏芳. 量子实在与“薛定谔的猫佯谬”[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2]Winger E P. Remarks on the mind-body question[J].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1995,6(6).
[3]DeWitt B S,Graham N. The many- worlds interpretation of quantum mechanic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1973.
[4]大卫·查尔莫斯.有意识的心灵:一种基础理论研究[M].朱建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5]Jibu M,Yasue K. Quantum brain dynamics and consciousness:an introduction[M]. John Benjiamins Pubulishing Company,1995.
[6]Jibu M,Yasue K. Intracellular quantum signal transfer in umezawa’s quantum brain dynamics[J]. Cybernetics &Systems,2007,24(1).
[7]Matthew. Quantum cognition:the possibility of processing with nuclear spins in the brain[J]. Annals of Physics,2015,(362).
[8]Bohm D. The Essential David Bohm[M]. London:Routledge,2003.
[9]Hameroff S,Penrose R. Orchestrated reduction of quantum coherence in brain microtubules:a model for consciousness[J].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s in Simulation,1996,(40).
[10]Stapp H. Mind,Matter and Quantum Mechanics[M]. Springer,2009.
[责任编辑:杨雅婕]
The Use of Quantum Mechanics in Consciousness Research
CHEN Xiang-qun
( School of Humaniti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189, China )
To explain conscious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antum mechanics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 methods of current consciousness research, which derives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ciousness and quantum mechanics in solving the quantum measurement problems. Quantum physicists are not only actively finding the quantum effects in our brains based on the quantum theory, but also putting forward many relevant theories to explain consciousness, laying a solid theoretical basis for quantum mechanics research. Compared with the past, the complicated neural calculation is not the only way to explain consciousness problems under the quantum mechanics now, which greatly breaks the limitation of the original research method. Moreover, the breakthrough is useful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so the use of quantum mechanics in consciousness resear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consciousness problem; quantum mechanics; quantum theory
B842.7
A
2095-7068(2017)03-0024-06
2016-12-10
10.19563/j.cnki.sdjk.2017.03.004
陈向群(1983— ),男,江西九江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意识哲学、认知科学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