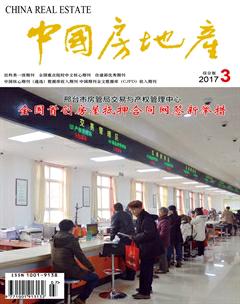从“类住宅”蔓延看大城市如何完善供地制度
李宇嘉
一、“类住宅”的兴起和现状
近日,上海住建委表示,自1月6日起,上海市住建委会同相关部门对商办项目进行集中清理核查,在此期间暂停此类项目的网上签约。所谓商办项目,是在商业办公用地上建设、可分割出售、原本为商旅人士提供的装修式公寓,俗称“酒店式公寓”或“商住房”。目前,由于这类物业将商办用途的单元(上海规定单元面积不低于150平方米、层高大于4.5米)横竖分隔成小单间,接通天然气,设置阳台、卫生间、空调外挂架等生活设施,事实上改变土地和房屋用途而成为“类住宅”。
近年来,随着大城市相继启动旧城改造,“类住宅”的种类也在增加,比如顺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趋势下,个体创业者基于办公居住空间融合的要求,在工业用地上建设可分割出售的创新型产业用房、创意园区用房。这类“类住宅”在上海深圳正在大量涌现,手握工业用地,不愿支付转住宅的高额补缴地价、不愿补足配套的国企和园区最积极。再如,为盘活存量低效商业用地,培育租赁市场,2016年“国务院39号文”提出鼓励商业用地改造为租赁住房,开发商打着租赁的旗号,政策红利和漏洞尽享,开展“以租代售”业务,表面是机构化租赁,实则是“类住宅”的另类开发和销售。
目前,大城市各区都要发展第三产业、都有产业升级转型的量化考核,需要建设商办综合体等地标,于是出让了很多商办用地。但是,城市外围商办项目“去化”和招商困难,为提高开发商投资热情,京沪穗深等城市允许商办项目开发部分“类住宅”。更多“类住宅”的出现,则是2010年热点城市实施住宅“限购”以来。特别是,2016年房价快速上涨,“类住宅”价格(包括租金)仅为同类商品住房的60%,加上其不限购的优势,成为“刚需”、外来购房人群和房产投资等需求的“出口”。特别是,“类住宅”“宜商宜住”的特点,适合办公和租赁,投资需求非常青睐。
以深圳为例,2004年“类住宅”在商品房成交中仅占比4.5%,2015年上升到11.5%,2016年上升到17.8%,近10年销售价格年均涨幅达到16.1%;北京“类住宅”市场更火爆,2016年全年成交商住房6.8万套,比2015年增长了196%,接近全年普通住宅成交的1倍,占商品房成交总数的60.1%,成交均价达到2.9万元,比2015年上涨了14%;2012-2016年,上海共出让691块经营性用地,“类住宅”地块达359块,占比52%。2016年,上海商住房成交27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了145%,商住房销售均价达到2.57万元,同比增长23%,目前在售楼盘消化周期仅5.3个月。
二、“类住宅”与大城市用地政策存在冲突
此次上海严格控制商住房,不排除像北京一样启动商住房限购的可能。另外,京沪深等大城市“类住宅”泛滥,与大城市空间需求转向存量用地盘活有关。从2017年开始,我国大城市供地政策出现新的变化,一是供地要与人口流动在空间上匹配,即人口流入多的城市要增加供地,这与过去大城市“一刀切”地缩减供地并以此作为人口控制工具完全相反;二是增加住宅用地比例,以契合人口净流入、就业率高的第三产业大发展的趋势,这意味着要减少工业、商办等非住宅用地;三是盘活存量用地,即新增用地减少,空间需求转向存量二次开发。
比如,近期国家批复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20)》显示,上海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从原来的3226平方公里调减到3185平方公里。近年来,国家划定大城市边界,限制大城市新增供地、城市外圍扩张,并非是抑制大城市空间需求,而是倒逼主政者转向存量盘活,释放低效产业和商办用地。但是,基于短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和税收贡献的考虑,大城市每年产业和商办用地供应均占60%以上的新增份额。此外,政绩考核“上下其手”,城市各区政府也有招商引资、发展工商业、建设区域商业办公地标建筑的内在激励,从而造成工商业项目遍地开花。
问题是,产业讲究上下游的积聚效应,更依赖人口聚集,商业则讲求商圈气氛培育,背后则是购买力在支撑。即便建起了高楼、园区,但招商、商家入驻往往都非常不理想。笔者所在的深圳,每一个旧改片区都要配套商办,即便中心区的商办综合体,二楼以上不乏大量空置,外围区域商业办公空置已成常态。因此,以有效回笼资金来提振开发商积极性,捆绑建设部分可销售的“类住宅”(酒店式公寓、商住房、创新型产业用房等)已成普遍现象、不得已的选择。
上海此次叫停的146个类住宅项目,多位于嘉定、松江、浦江、浦东等城市外围。2016年5月已启动“商住房”限购,全面叫停新批商住项目的北京通州,更是占据全市商住房销售30%的份额。2011年以后,大城市启动住房限购政策,房价地价快速上涨,“类住宅”成为突破限购,分流需求的出口。规划设计上,原本规定不低于150平方米、不高于4.5米高的商办单元,由于不得已的妥协,被横竖分割成50-60平方米的小单元,天然气禁止接入、公共卫生间而非独立卫生间、不能设置阳台、空调外挂架等设计规范也被突破,以迎合需求并大规模向市场推出和销售。
国家允许京沪深等大城市增加供地,但并非是新增供地,而是存量盘活。也就是,向存量要空间是未来大城市空间扩展的唯一路径。近年来,京沪深等城市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已超过70%,但45%左右的存量建设用地仍旧为工业用地。从地均产值和人口密度看,工业用地有必要向第三产业、住宅倾斜。但是,掌握工业用地的国企、园区,希望尽享土地开发红利,不愿缴纳功能转换的巨额出让金(土地是划拨的),无力做住宅片区的公共配套,结果是存量盘活局限在原用途,政府也有以土地换取对低效国企长期补贴的想法,这也是“类住宅”异军突起的原因。
笔者调研发现,上海很多老牌国企动辄占据数平方公里土地,都成立旗下开发公司或联合开发商成立置业公司;深圳工业用地和园区改造,也在向房地产转移。起初,大家一窝蜂地开发创意园区、写字楼。商业办公过剩后,便转向打擦边球的“类住宅”。“类住宅”反映市场对住房需求旺盛的态势。如前所述,买这类住宅的多为刚需、被限购者或投资客。问题是,这些区域本身规划为商业办公,居住氛围差,缺乏教育、医疗等公共配套,需求过旺必然是无效供应和资产泡沫衍生。
三、“类住宅”本质和突出的问题
首先,“类住宅”违反了土地用途管制、城市分区规划,造成城市生活和生产功能区混杂穿插,用地效率较低、“城市病”突出;其次,“类住宅”大行其道,擅自改变房屋内部结构的空间分割愈演愈烈,消防和安全形势严峻;再次,缺乏配套的“类住宅”盛行,导致住房投资氛围恶化,人口管理失控;最后,“类住宅”游离于住房统计,或导致未来住房供应过剩和风险爆发。2015年5月,北京启动通州商住限购,意图在于,通州是疏导首都功能的行政副中心,而非泡沫集中地或又一个“睡城”。
本质上,“类住宅”迎合了住宅需求旺盛,特别是刚需购房和租房、投资性购房,也反映大城市住宅供地不足,更是土地用途管制下,市场绕过监管获取“管制外收益”的结果。监管在规划、设计、审批上固然要有所诟病,但区域发展“房地产化”、短期政绩考核、产业人口不积聚才是根本。大城市遍地开花、多布局于外围的“类住宅”,尽管作为租赁市场成为中低收入者“落脚”城市的选择,但造成城市功能和空间结构混乱,倒逼公共配套高成本四处铺开、城市病积重难返。
四、以土地制度革新解决“类住宅”难题
因此,京沪相继控制“类住宅”市场蔓延很必要。但同时,从人口流动、新增供地潜力看,大城市增加宅地和盘活存量已处于倒逼境地。一方面,“类住宅”繁荣是政府监管与市场突破监管的结果。销售类住宅需求旺盛,一味地从需求端“堵”很难奏效;另一方面,也是规则限制与市场突破限制的结果。大城市宅地需求、存量用地盘活诉求强烈,但土地用途管制,片区规划限制,各区都要发展政绩,加上国企负担重,土地调整功能成本高,造成一边是住宅需求嗷嗷待哺,另一边是商业办公、工業却严重过剩,中间夹着供应效率低、野蛮生长的“类住宅”。
2017年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增加大城市宅地、盘活存量用地、抑制资产泡沫,不仅是房地产市场的主题,也是楼市供给端的重大变化,更是长效机制建设的重点内容。目前,“类住宅”的蔓延有违于上述目标的实现。笔者认为,监管从“堵”变为“疏”是控制“类住宅”市场蔓延的关键,这就要从土地用途管制和规划等方面,开展体制上的改革和机制上的创新。首先,存量工业用地很多集中在城市中心区,盘活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很高。要以地均产值、就业人口为刚性指标,建立划拨类工业用地和园区腾退红线,触及红线的工业用地和园区一律由政府收回。其次,以土地出让净收益全部用于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投入为切入口,加快推进低效工业和商业片区转作住宅片区的规划调整,降低存量用地盘活成本,增加住宅用地有效供应。再次,控制地方政府基于短期固定资产投资和税收考量的低地价招商政策,避免低效工业屡屡登堂入室、商业综合体遍地都是,避免随后变相发展房地产业,“子产业”大过“母产业”的乱象,给“类住宅”蔓延创造空间。最后,新兴产业要从“落地”变为“落房”。地方政府给予新兴产业扶持是必要的,但要从过去的土地支持变为给办公空间支持,避免新兴产业利用多余的用地发展房地产。
李求军/责任编辑
——以杭州为例的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