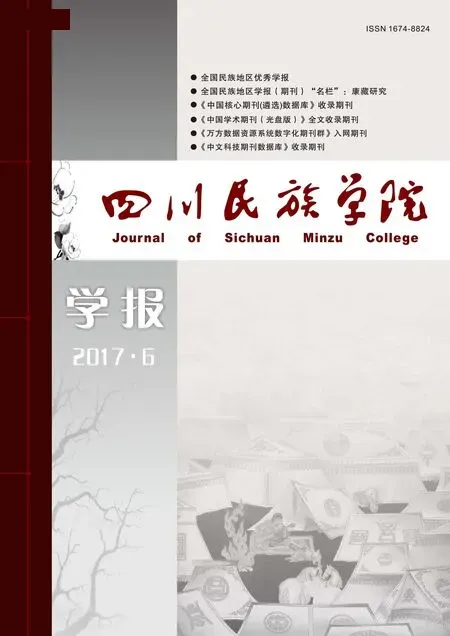民国时期中央政府治藏思想述略及反思
胡延龙
在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历代王朝均面临着一定的民族问题。民族政策的成败得失,对历代王朝的兴衰存亡,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有着重大影响。西藏自元代起,就正式纳入了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中,成为了中国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明、清两代继承了对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传统,而尤在清代,还形成了一整套管理西藏的体系,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行政管理进一步加强,民族融合进一步加深。与之前的封建王朝相比,建立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基础上的中华民国有着绝对意义上的不同,所面临的也是前所未有的世情与国情。一般认为,中华民国时期由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1912年至1927年)和国民政府统治时期(1928年至1949年)这两个重要时期组成。就整个时期来看,包括西藏在内的所被侵略势力渗透的这样的边疆地区处境艰险,甚至局势日益严重。面对这样的形势背景,中央政府先后做出了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政策实践以及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的一些努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边疆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对边疆的治理能力,也具体体现着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的民族思想。纵观历届中央政府在处理西藏问题上,除了采取传统思想策略、特别是以清代治藏经验教训为借鉴外,还有着受西方民族主义影响下的、别于其他时期的新的特点和新的思想体现。本文旨通过对民国时期中央政府治藏思想脉络的梳理,以评价及反思。
一、治藏思想述略
(一)“从俗从宜”思想
“从俗从宜”是中国历代中原王朝治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常用思想策略。这一思想可以追源至《礼记正义》中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因着历史时期和统治对象的差异,“从俗从宜”思想所呈现的特点和侧重点也不尽相同。但整体来看,其核心却有着一致性,即根据不同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制度和历史状态以及地域特点以形成多样性的中央——地方关系,以实施相应的较为有效的统治措施。基于这一思想对藏的实践,元、明、清三代成效显著。在历代“从俗从宜”治藏方略的传承演变之中,包含了羁縻互用、刚柔相济,尊崇佛法、因俗而治等具体策略。虽然说中华民国的建立,终结了中国传统的封建王朝治式,掀起了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统管及治理地方的新篇章,但在整个民国时期对这种思想方略却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继续奉行。
中华民国在建国之始,认定清代治藏的经国大典《钦定理藩院则例》为特别法之一,在未颁布新法令以前,予以参照援用,对于西藏历代政府制定发布的法典、封文、通告、定制、法旨、训令等也都给予承认;《中华民国宪法》和《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对西藏地方自治制度予以确认,允许西藏维持其政教制度。[1]中央政府尊重西藏宗教信仰,优待西藏上层人士,特别是对宗教领袖人物,特加优待,遵照历史传统,给予了黄教两大领袖同样的礼遇。如中央政府先后带嘉奖令及礼物册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封号,并颁金印、金册等;如此,还见之于达赖、班禅的转世问题,中央政府基本遵循了历史定制仪轨,如选派代表到拉萨致祭十三世达赖和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以及选派卫队护送班禅返藏等。另外,中央专设管理机构、掌管藏务,遵循清朝派官驻藏之先例、设驻藏办事长官等,如先后设立的蒙藏事务处、蒙藏事务局、蒙藏院、蒙藏委员会;颁布法规条例,如《达赖、班禅代表来京展勤办法》《管理喇嘛寺庙条例》《喇嘛登记办法》《喇嘛转世办法》等,以管理寺庙喇嘛,规范宗教活动;中央政府发布任命,西藏高级官吏应照旧例呈请中央等等。这些都体现了对“从俗从宜”思想的沿用。这种做法对于稳定西藏和解决西藏问题起到了基础保障和支撑的作用。
(二)“五族共和”思想
“五族共和”可溯源于清末立宪运动的“五族大同”。对于持“五族大同”之说者自初始主张“宪政之基在弭隐患,满汉之界宜归大同”,“放弃满洲根本,化除满汉畛域,诸族相忘,混成一体”,到提倡 “汉满人民平等,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再至清帝国的倒亡、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五族一体”“五族大同”这样的论述在立宪派的理论阐述中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斗争实践中,渐认同和接受了立宪派的民族观,遂转向了“五族共和”的“大民族主义”。而依此长期累积之势,事实上,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时,“五族共和”说已被国内知识界、政界等社会群体广为认同、普遍接受,而《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之郑重宣告以及将“五族共和”写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标志着“五族共和”思想及其政策主张的法律化。[2]南北议和之后,从思想的高度上,“五族共和”成为了当时民国中央政府处理民族事务之依据和指导。“五族共和”思想的重要内涵在于, “国家之统一”“民族之统一”和民族(种族)平等等,具有鲜明的指向性。这对于凝聚藏族在内的中国境内诸族起到了巨大的感召作用。
从对藏影响及实际效果来看,由“五族共和”思想所释放出的民族平等、团结及友好相处的善意,在范围和程度上,首先在留京的西藏人士上表现出来。西藏旅京同乡会于1913年国会议员选举之后,呈文北京政府蒙藏事务局表示:“已将大总统廑念西藏之德并五族共和之要旨,呈报达赖活佛及西藏同胞……会员等亦应黾勉从公,竭力传播五族共和之大旨,解释从前西藏同胞之误会,同享五族共和之幸福”。[3]在积极而广泛的宣传之下,西藏上层人物对“五族共和”思想的理解与认同也有了大的变化。九世班禅在1912-1913年这样的时候就拥护“五族共和”,拒绝参加达赖的驱汉运动,及至内地后是经常宣传“五族共和”,并且提出“五族共助”,希望国内政局稳定,国家和平统一,“共同抵制强邻之侵略”。[4]达赖十三世在与甘肃代表朱绣等人会面时,明确表示了“余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共和”的态度,并提出了“同谋五族幸福”的愿望,更在晚年时向中央政府做出了“不亲英人,不背中央,愿迎班禅回藏”这样的保证。十三世达赖喇嘛晚年的转变,表明其认识到拥护“五族共和”,回归中华民族大家庭才是必然正途。[2]另外,西藏地方政府在给中央政府信件及中央政府在对藏人宣讲治藏政策时也常常提及五族共和说,如1930年,西藏地方政府在给南京国民政府信中指出:“西藏为我五族之一,唇齿相依,荣辱相与,断无离异之理。”[4]这些都说明了五族共和说在当时所发挥的作用和蕴涵的价值。
(三)“国族”思想
“国族”理念在经历了孙中山的“五族共和”与“民族统一”,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并以美国熔炉模式“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之所论,到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的“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于一致”“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云”之说,[5]乃至《中国国民党宣言》“以一民族成一国家,其继乃与他民族糅合搏聚以成一大民族”之说的演进。终在1924年“民族主义六讲”中正式创出。[6]当然,这里的“国族”理念演变,也包括了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愈演愈盛,广泛见诸政府公开言论中的所谓“宗族-宗支”论。此时,“宗族”概念代替了“民族”概念,成为了“国族”概念的实际支撑点。其意表含了各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宗族、宗支,并有着强调从“宗族”(仅承认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到合一为“国族”(“中华民族”)的思想建构。如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9年3月)所主张的:“求汉、满、蒙、回、藏人民密切的团结,成一强固有力之国族,对外争国际平等之地位。”[7]蒋介石1942年8月27日在西宁发表的题为《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责任》的演讲所谈及的:我们中华民族乃是联合我们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组成一个整体的总名词。我说我们是五个宗族而不说五个民族,就是说我们都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分子,像兄弟合成家庭一样……我们集许多家族而成宗族,更由宗族合成为整个中华民族……”[8]这种“国族”理念的演变路径,所体现的其实即是一个与中华民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相适应的民族观的探寻过程。其主要目的无不外是为了突出“中华民族”这一政治实体,同时强调各少数民族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从而更在基础上剥离“民族”的政治含义,以期对此时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说所带来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地位威胁达到最大消解。
具体的就对于西藏方面的作用而言,1931年之前,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中央政府的对藏理念主要表现出西藏与内地应该保持统一,使藏族的特殊性逐渐弱化这样的要求,同时,还有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西藏的这样的要求表现。[9]这是前面思想所述方面的具体展现,实际也即为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对待西藏等边疆民族问题的主导思想。但是国民政府对待西藏问题的实践活动与此理念却并不相统一,甚而表现的是相行渐远、相差愈大。在南京国民政府初建立不久,在对藏问题上强调与内地的一致性,推行地方自治,随着宣慰等措施的失败,又把一致性过渡为特殊性。“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逐渐以国防问题和边疆问题取代民族问题,在对藏实践上,奉行和平主义原则,企图通过军事护送班禅回藏,从根本上解决西藏问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出于自身实力和英国的压力,又被迫放弃了这一实践。而此后,也没有很好的抓住热振摄政时期内倾的这一机会,及至达札摄政之后,代表此思想的对藏实践更是表现地无可作为,影响微弱。
二、评价及反思
总结整个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的对藏思想脉络,不难看出,虽中央政权更替频繁、政令多变。但是,坚持国家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对藏思想的基本点,历届中央政府却是一脉相承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思想理论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所提出的民族政策主张更多的也只是一个框架,且很多地方也有失偏颇和有所偏离,由于内战、抗日战争等原因也多数未能具体实施,可以说,实践效果与目标追求之间远未达到一致性。具体如下:
第一,纵观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的对藏政策,我们可以看出在西藏问题上,贯穿于始终的便是一种中国传统边疆治理策略。但这一思想策略中央王朝能成功运用的并不多,因为它时常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通常情况是,当边疆地区和中央政府处于不正常的关系状态时,中央政府要使得治权恢复,往往需要先诉诸武力,施之以兵威,然后再施之以恩抚,礼遇民族首领,安抚百姓,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抑制分裂势力或结束不正常的关系状态。[10]而事实上自辛亥革命以来,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西藏基本上处于一种 “相对独立”、相对分离的自治状态,对于整个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的任何的想要改变这种状态的举措都必然遭到西藏地方当局的强烈反对。这种情况下,正如前面所述客观上要求中央政府必须先“威”后“恩”,即先从政治上解决原则问题,再施以恩抚。但连年战争消耗了民国政府的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国力衰弱。民国政府根本拿不出更多的精力解决边疆问题,因此对藏用兵基本上处于理想阶段,更多只是体现了恩抚,即所谓的“柔性的政策之羁縻”。因此传统边疆治理策略的运用得其形而失其神,效果被动,诚如蒋介石所言,只起到了避免西藏局势更加恶化的作用。
第二,可以肯定的是,“五族共和”从法理上否定了传统上的“内诸夏而外夷狄”“尊夏贱夷”之类的观念,且其所倡导的“国家之统一”“民族之统一”和民族(种族)平等,对消解“华尊夷卑”的等级观念,促进民族平等及加强民族团结,以及对缓解民国初年边疆民族地区的分裂倾向、强化国家统一具有积极的作用和一定的现实意义。无疑这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观念的一次重要转型,也是我国历史上处理西藏问题的一次重大变革,为有力地团结广大心向祖国的藏族同胞,缓和西藏地方的紧张局势,增强对中华民国合法性的认同,继而为强化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提供了有力支撑和起到了切实的推动作用。如果以今日的眼光来看,在一个多民族的中国,当时的“五族共和”提法是有些粗糙简单的,虽然在当时,各政治派别、民族地方对“五族共和”思想的重要内涵理解大体一致,[11]孙中山和袁世凯也都曾公开反复宣讲过“五族共和”思想。但是以下两点无法否认,一是,“五族共和”仅只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政治主张,对于如何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之统一”却没能制定出明确的政策,也缺乏足够理论与实际操作性制度实践的支撑,因而其效果并不能持之以久;再者,“五族共和”用在民族上,并不能全面地反映我国众多的民族成份和体现民族的平等权益,甚而被分裂分子所利用,使得在近代中华民族的建构与整合历程中,不利于“五族”之外其他民族对“国家”和近代“中华民族”的认同,也即不利于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正如,孙中山在后期(1920年)所进一步指出并强调的:“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9]又如更早所见的云南之实际,辛亥革命后的云南军都督府提出的是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族结为一体,维持共和……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统一之国家……汉、回、蒙、满、藏、夷、苗各族视同一体”这样的主张。[12]但不管怎样,依当时边疆的内外形势,除了“五族共和”,尚没有其他更好的主张来团结藏族同胞。而也正是通过“五族共和”,使得这一时期西藏局势得以大体稳定,没有出现严重的国家分裂局面。
第三,与前两者比较起来,“国族”思想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统合用意则更为浓厚,饱含了应对当时边疆危机和维护国家完整性以及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刻指向性。它的提出,也正是为了规避《大西洋宪章》所认可的民族自决,回应国际社会较为盛行的民族主义浪潮。当时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手段更加多样,并且利用着“民族自决”不断鼓动外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脱离中国而“独立”,在这样的形势背景下,民国政府所进行的“国族”思想建构及其实践,着意强调了五个“宗族”的同源性以及中华民国的不可分割性。这有利于引导和推动包括藏族在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向“中华民族”的凝聚,强化包括西藏地区在内的其他边疆地区对中国主权的承认和对“中华民族”国家的认同,对维护中华民族的一体性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国族”思想其思想内核是不承认国内有其他民族的,其极力主张民族同化,充满了大汉族主义。以汉族同化其他“宗族”来构建“国族”——“中华民族”,这是典型的强制同化政策。这样只承认一个“中华民族”的存在,实际上是否定了国内各个民族的存在,否认国内各民族是各个民族群体,从根本上抹杀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的差别。这就必然导致国民政府制定民族政策的偏颇,同时也为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提供了理论依据。另外,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后期,广泛见诸中央政府正式场合中的所不断宣扬的“宗族-宗支” 理论,显然也是对“三民主义”以及民国时期前期会议中一些所被肯定的民族观的一种公开否定。使得民族同化从隐性实施变成了公开推行,从而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多元性和各民族的长远发展。因此,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是无法达到预期目的和真正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对藏政策实践以及对藏问题的解决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结语
民国时期在我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在近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其民族思想在具备了现代主义的因素的同时,也保留了传统的浓重印痕。总的说来,民国时期的民族思想以及所体现其的民族政策在维护国家统一、实现边疆地区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在探寻与中华民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相适应的民族治理的过程中,从孙中山到蒋介石的历届中央政府并未能找到适合于中国的合理路径。民国政府通过一些措施进行“国家之统一”“民族之统一”建构的努力,更多的只是对当时条件下民族分裂危机的一种回应。不断面对外侮内乱的民国政府通过构建“中华民族”这一政治共同体,以期弥合边疆与内地的裂缝,实现对全体中国国民的统合。然而,这种国家政治建构的方式因其未能摆脱汉族中心思想和忽视了整合民族的文化纽带而举步维艰。与传统的文明帝国(如以儒家文化认同为核心的中华帝国)和法律帝国(如以统一的罗马法整合各民族的罗马帝国)不同的是,“现代的民族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与政治的结合”[13]。在拥有悠久历史和众多民族的传统中国建设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不顾中国的实际,照搬西方“民族-国家”模式是不行的。传统中国民族观的开放、包容与非排他性为政治与文化的结合提供了有利的思想基础。因此,国内民族问题和中国边疆问题的解决,除了在于国家的实力、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诸多地区建设的具体步骤,还在于正确的民族思想理论、切合实际的民族政策实践,当然还有赖于所不可忽略的各族之间长期的文化交流。
[1]王丹屏、王玉青.重审“从俗从宜”治藏思想对构建“和而不同”和谐社会的意义[J].法制与社会,2011 年第25期
[2]高国良.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思想及其对西藏的影响[J].西藏发展论坛,2011年第6期
[3]藏文白话报1913年诸号
[4]张双志.孙中山与西藏[J].中国藏学,2005 年第4期
[5]郝时远.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内涵之演变[J].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
[6]冯建勇.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之历程——民国中央政府统合边疆民族地区的理论探讨[J].社会科学,2014 年第2期
[7]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
[8]王洪刚.民国时期西藏的地位及其治理[J].贵州民族研究,2015 年第2期
[9]林恩显.国父民族主义与民国以来的民族政策[M].台北:国立编译馆,1994年
[10]徐中林、刘立敏.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十年的西藏政策[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11]潘先林.“五族共和”思想的内涵与实质探析[J].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6期
[12]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续云南通志长编(上册)[Z].云南: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5年
[13]许纪霖.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年第6期
——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的模式与效应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