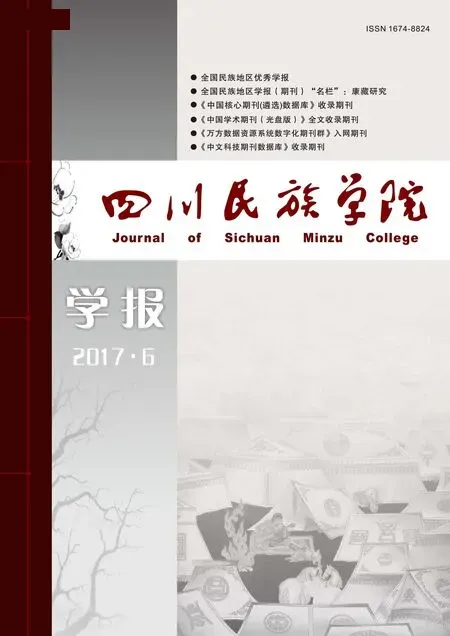康巴藏族民间故事中“宝物型”故事的文化内涵
朱茂青
“康”是我国三大藏区(卫藏、安多、康)之一,属于地域概念,指青藏高原东部的藏区,而“康巴”是族群的概念,指生活在“康”区的操康方言的藏族。人们也习惯用“康巴”指代“康”。民族学、藏学专家评价康巴文化“在一个民族地区内包含着如此之多的文化形态,在世界都可算作罕见。更难得的是各种文化在这里互不干涉……”[1]“就多样性而言,世界上恐怕很少有一种地方文化能够与康巴文化相媲美。”[2]而民间故事包罗广泛,可以从其间探查民间的历史、现实与发展,亦可以窥见民间存在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及道德、情感、文化、心理等等。“宝物型”故事是民间故事的重要类型,康巴藏族民间故事中也有不少此类故事,但是纵观对康巴藏族民间故事相关研究,有对动物、植物、创世、宗教、机智人物等的专门研究,尚无论文对“宝物型”故事进行系统的把握和深究。在此,将以康巴藏族民间故事里的“宝物”作为窗口,探查康巴民间独特的文化特征和精神品格。
中外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明确地列举了中外民间故事中与生活用品类相关的故事类型,但其中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是:并非所有的生活用品都被列举出来,而是仅列举了其中带有魔力的宝物。比如:《阿尔奈-汤普森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确立的民间故事分类编码体系:Ⅱ普通民间故事一类就专门列出560-649神奇的物件;[德]艾伯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中“五,创世,混沌初开,最初的人”里有“63、神奇宝物;64、隐身帽”“十二、巫师,神秘的宝藏和奇迹”中涉及到“宝扇、银器、食具、钟等等”;丁乃通先生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一般的民间故事(300-1199)之560-649为神奇的宝物”;金钟华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里(560-649)神奇的宝物中,则有560宝石戒指;563桌子驴子棍子、576隐身帽;592魔箭;597聚宝盆;598不忠的兄弟和百呼百应的宝贝;599开启宝山的钥匙”。康巴藏族民间故事中,宝物型故事为数也不少。
康巴藏族民间故事,本就是基于康巴民间的生产、生活而产生的民间成果,所以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各类生活用品。查询了大量的藏族民间故事后,就会发现其中很多生活用品都带有魔力。生活用品是物质文化范畴,但它又是精神生产的一种结果,所以它作为物质文化为适应环境而创造的与衣食住行有关的一整套生活方式及生活物质,又有着与其相对应的一整套精神文化、政治、道德、伦理、信仰、风俗、艺术、情感、心理等等的表现和载体。本文仅考察此类带有神性魔力的生活用品,考察民间透露出的经济、政治、观念、文化、心理等,明确其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和复杂的信息。
一、经济方面
抛开其魔力,单从生活用品本身看,它可以反映康巴藏区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康巴西北部有着平坦的高原平面,河流的上流又分布宽平的谷地和平地,成为良好的牧场区,而南部分布着冲积而成的盆地,利于农业的发展。在康巴民间故事中,既有牧区游牧的帐篷,也有定居的房屋。既有农区的生产生活方式,《狼心的媳妇》中,媳妇将小布袋里的石头扔进白菜地里,白菜瞬间长得又大又嫩;又有牧区的生产生活方式,《贡扎绕登与洞洛真》里大姐色洛真和二姐额洛真都让国王贡扎绕登扮成的老头子到阴山放牧,自己却在阳山放牧。当然,在康巴藏族民间故事中,能够明显地反映康巴藏区生产生活方式的生活用品不胜枚举。同时,无论是牧区还是农区,都会通过战斗和狩猎来维持生活,所以在故事中,经常出现佩刀、弓箭、木棒等用具,在战斗、围猎中是战胜对方的工具,在生活中又成了装饰房屋及自身的点缀。比如《卓嘎和恩巴》,故事开头就明确地介绍了发生地——康巴亚柯,恩巴为见自己的心上人,作了一番打扮:穿上白氆氇藏装,右手一支五彩吉祥箭,左手拿着金刚棍,腰间系着一个大木碗。就这身装扮,可以看见康巴吃穿用度的独特风格。质朴、自然的半牧半农生产生活环境中,孕育了独特的历史文化,而文学、艺术中可反窥这一特殊的康巴藏族传统生产生活场景。
另外,故事中宝物的占有者通常是一无所有的或弱势的一方,但这也明确地反映出康巴地区的经济关系。藏族从原始社会进入封建农奴制社会,政教合一的政治经济制度造成社会上分配极度不公,贫富悬殊极大。在《小嘎嘎》中小嘎嘎母子俩住在山脚下歪歪斜斜、破破烂烂的小土屋里。阿妈给土司帮工,天不亮就忙到太阳落坡,而每天的工钱是一小木碗青稞。故事中为了得到宝物来到小嘎嘎家当媳妇儿的土司女儿,则衣着华服,妆饰着松耳石头饰。两方形成鲜明对比。《聪明的小格桑》中小格桑的父亲给头人干一辈子苦活,临死前的愿望是“多想喝一口酥油汤汤”,死后还欠头人三千包青稞。小格桑和阿妈每天给头人家背水、放牛、炒青稞,黄昏时又杵起打狗棒,端着破木碗挨户乞讨。小格桑意外地得到了妖婆的木碗和铜锅,木碗可变糌粑,铜锅可变出酥油。结果头人贪心地想从妖婆处得到更多的宝贝,去了妖婆的住所,却再也没有回来。幻想中的宝物使赤贫的一方争得了工作、财产权、粮食和金钱,颠覆了现实中的经济地位。但是,这种颠覆完全是精神层面、虚构的,大量宝物类型的故事出现反而说明了现实中,经济、政治上剥削和压迫的严重,导致此类幻想层出不穷,此类愿望强烈持久。
随着宝物的出现,故事中还经常出现“夺宝”“盗宝”这样的情节,在康巴民间故事中,大多宝物被弱势的一方持有并获得无尽的财物,愿望得到满足后,都会引起强势一方的觊觎。这类“夺宝”“盗宝”型的故事,都侧面反映出私有制下人们的财产观念和人际关系。而故事呈现的道德评判也一目了然,对弱势的肯定和同情,对强势的否定和批判,而这种道德判断也是私有制的直接结果。不过,尽管有强烈的愿望和明确的道德评判,弱者的胜利仍然处于幻想中。另外,故事中出现了“商人”,也出现了相关的做买卖的必需品“秤”。这些又都明显反映出了商品经济在藏区的出现。
二、政治方面
可透过“宝物”这一民间主观缔造的“物质”关照其民间意识形态本质。“民间”与“官方”总体呈显二元对立格局,“民间”不仅蕴含下层看待政治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方式,而且“民间”呈现出对官方的态度取向。“于是人们使用‘民间社会’时的着眼点多不在‘民间社会’自身内部的种种结构差异,而是特别突出了‘民间社会’在面对官府、官方时的整体性、一致性、同质性,从而也就是‘战斗性’。[3]” 历史上存在的各种思潮和观念往往将民间作为对统治者和官府的颠覆性力量。当然在康巴藏族民间故事里,也明显地表示了这样的一种反抗和颠覆的企图,有的故事如《聪明的小格桑》中的奴隶和头人,《金摊锅和金鼓槌》中的放牧娃和国王,《“不好意思”的故事》中的砍柴郎和土司,《小嘎嘎》里的乞丐和国王等等,即使是涉及到兄弟姐妹或朋友、亲戚之间,也是明显地呈现贫富差异、强弱悬殊。在这样二元对峙的人物安排下,情节完全一致:均是弱者凭借“宝物”获得财物或愿望的满足,而对立面都受到相应的惩罚。“宝物”的出现,使得“弱势”一方的所有“胜利”都显得合情合理,符合逻辑。情节的雷同,真实地反映了面对统治者和强权,下层弱势普遍的社会愤懑和抵抗情绪。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虽然在故事里,所有的弱者和底层都是“战无不胜”的,却始终停留在“文学创作”中,停留在幻想或理想中。那么美国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应该较合理地解释了这一创作现象“贯穿于大部分历史过程的大多数从属阶级极少能从事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活动,那对他们来说过于奢侈。……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活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是典型地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农民阶级在政治上是无效的,除非他们被外来者组织和领导。”“更重要的是去理解可以称为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斗争——农民与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地斗争。”[4]Eric Hobsbawm.也将这种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称为“使制度的不利降至最低”。周晓霞的《颠覆与顺从》中,将这种对现实的颠覆企图作了更深入的探讨,因为说到底“颠覆”没有变成现实,它一直只是存在于叙事作品中,是虚构的“抗争”和“胜利”。其一,其叙事虽有人物,也有冲突,但这些冲突与传统叙事相比都显得单薄而空乏,也有对立面的失败或死亡,但又无关于社稷安危和重大的伦理道理。其二,“抗争”因其具有象征性和颠覆性企图。所以,在短期内可以对弱势或底层起平衡、调节心理的作用。因此,“宝物”类民间故事反而是高压政治统治中官民、强弱关系的润滑剂。当然,某种程度上来看,这确实是一种社会情绪的反映,是一定社会时代、民情、民心、民意的表示,它即使达不到现实的目的,但肯定是强烈的社会舆论,可以催化社会、时代的变迁。
三、伦理道德方面
“宝物”类故事反映了康巴藏区的伦理观念、道德习俗以及现实中的伦理道德状况和伦理道德评判。在古代藏族的世俗道德中就存在善良、仁义、诚爱利济、孝敬等等,这些在松赞干布制定的做人“十六条”、古代的佛教典籍及文学作品如《礼仪问答写卷》《萨迦格言》《格桑尔王》等,都或系统或零星地有所体现。同时,由于藏族文化本身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所以对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文化有所吸收和兼容,在漫长的文化碰撞中磨合、加工,形成了藏民族普遍尊崇的伦理道德规范和道德评判。康巴藏族民间故事不仅展示了相关的伦理道德观、是非观,而且成为伦理道德观念传承的一种重要方式。故事中的“宝物”实现了对“做人之道”的回报和肯定,对“非做人之道”的批判和惩戒。首先,“宝物”类故事在伦理道德方面展示了明确的评判标准。藏文文献《礼仪问答写卷》云:“做人之道为公正、孝敬、和蔼、温顺、怜悯、报恩、知恩、知耻、精神、勤奋……;非做人之道是偏袒、暴戾、轻浮、无耻、忘恩、无同情心、易怒、骄傲、懒惰”。在康巴藏族民间故事中,人物不仅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呈二元对立的模式,在道德伦理方面也呈相应的对立状态。强权者、富有之人往往是暴戾、贪婪、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无诚无德。而弱势底层尽是忠孝仁义、恭敬有德、诚信正直。*注:迄今,藏族伦理思想尚无系统整理和研究,但又明显受到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因此,在此的评判带有中国传统儒家的思想和观念。《小嘎嘎》用家里仅剩的一小土罐青稞救了三个“张布”(乞丐),三个阿爷回赠“宝物”:口袋、木碗和木棍,而狡猾、贪心的土司和女儿夺宝不成,还变成了猴子。《狠心的媳妇》,放牛娃救了瞎眼的老人,结果老人给的小布袋把石头变成了金子。而将老人赶出家门的媳妇却被宝物变出的白菜胀死。《一家土司的故事》孝顺、勇敢、聪明的儿子为给继母治病,得到三样宝物:夜明珠、皮口袋、牛角。而狠心、冷酷的继母却被封死在牛角钻成的岩洞里。《兄弟俩》中捕鱼为生的弟弟得到了神奇的金瓜子,嫂嫂谋财害命杀了小儿子,而当大臣的哥哥也不说出真相,最后铲刀显神砍掉哥哥的头。“宝物”的拥有者都是德行好的一方。“宝物”的实质是道德伦理的评判。明确的人物观念、人物言行之后是“宝物”的明确归属。因此,在故事中的“夺宝、盗宝”情节也是对这种归属评判的强化。“好人”从别处,哪怕是从坏人,妖魔或意外得到的宝物,都可运用自如,意愿尽达。而“坏人”夺宝、盗宝后不仅达不成意愿,往往还被严厉地惩罚。《加措学艺》中小弟用仅有的一块银子救了一位“热巴”,“热巴”送了他一支胡琴。小弟伴着胡琴在海边唱歌,龙王听到美妙的音乐,邀请小弟到龙宫,并送了他一张可以变任何东西的桌子。回家后小弟变了一座宫殿,两个哥哥霸占了宫殿,宫殿又变成了乱石堆。《奔波利卡许》奔波利卡许贫穷、善良,救了阿爷,得到呼兵唤将的木棒;救了壮年人,得到可以变铁房的木桩;救了阿婆得到了一只仙桃。被他收留的三个朋友,为了财宝,谋害了奔波利卡许,结果神仙救了奔波利卡许,还把夺宝害命的三个恶人变成了狗和牛。在故事里,不道德、心存恶念的害人者即使宝物在手也不能顺心如意,还会落个悲惨的结局。
另外,“宝物”故事还是道德伦理观念的承传方式,从有限的藏族文献记载来看,少有系统完整的政策、文献来对对道德伦理方面作引导和教育。除了以言传身教来作道德伦理观念的承传以外,文学特别是民间文学就担负了主要的训诫和承传的作用。在《奔波利卡许》的结尾写道:“乡亲们都教训自己的子孙,种下青稞就会有好的收成,做一个好人总会有好结果。”不同于藏族古文献《十六净法》《礼仪问答写卷》等的直白抽象,文学以形象,生动的内容来浸润人心,陶冶情操。虽然是虚构,但不是胡思乱想,而是建立在生活基础上的一种艺术化的合理想象。经过民间千百次的加工、制造,更有效、更集中、更可信地表现了相关的内容,所以,民间文学以他的开放性、流动性成为树立道德,塑造思想的有效方式。
四、“宝物”故事还反映出康巴藏族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在所有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幻想故事类型都达200个。但民间故事不论写实还是幻想,都离不开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境遇和愿望。从“宝物”入手,可以破译其隐藏的人类甚或具体到康巴藏族对宇宙、对人生的看法,探寻形成这类特殊艺术形象相关的原始思维、观念和信仰。“宝物”类的幻想性故事题材种类非常广泛、丰富,单就康巴藏族民间故事中,涉及到的也不少。生活中所有的用品都可被赋予神力,这与藏区自然崇拜,原始宗教和巫术,以及功利目的相关。
马长寿先生的《苯教源流》中说到:“因对自然的不可抗拒,人类将身边的一草一木,万事万物都作为供品,表达对自然的未知的敬仰、以求及庇护。”[5]“万物有灵”的观念在藏族的原始思维中普遍存在。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论述“原始人把一切现象的东西都与神灵的意识组成一个相互渗透的联系。”[6]平凡的生活用品也在夸张和想象中赋予魔力,达成人类的意愿。
由神话的出现导致原始宗教的产生,而神与人的桥梁则是巫师。一方面巫师试行巫术总要通过物器进行,巫术利用产生神秘的与量对现实社会造成影响。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到:“……一切宗教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7]在康巴藏区,巫术、宗教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影响都非同一般,巫术、宗教、宝物类民间文学都是妄图通过一种神秘的超人力量达成人的美好生活。
实践中的“人”能力有限,不能满足所有愿望,于是就幻想出各种奇幻现象,而生活用品是人最熟悉的一类,人们可以根据器物的特性进行夸张幻想。在此,器物的能力不管多大,首先,它必须有所归属,为特定的人掌握,另外,它的超自然能力目的是为“人”服务,所以虽然“人”描述着各种宝物,但这宝物的最终指向还是“人”。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生活用品的增多,宝物的种类也越来越多,魔力的呈现也越来越丰富。但纵观康巴民间故事,宝物还是一件“物器”,没有生命,没有思想,只会服从,永远都隶属于“人”。所以,宝物的出现实质是人对于自身的认识和观照。
五、“宝物”故事是对诙谐文化的传承
民间故事大多有浓厚的戏剧性,从讲述风格和听众反应看,有很多和笑话没有多大区别,“社会文化的进程中官方意识逐渐稳固、确信,而在现存的秩序和制度中,总有方式来解决寻找、排解、轻松的途径。千百年来形成的诙谐的民间文化,其中隐藏着独特的而非幼稚的深刻思想。”[8]从巴赫金的这句话我们既可说明世界诙谐文化的源远流长,也可说明诙谐文化的文化意义。民间诙谐文化的价值并不只是否定旧秩序,诙谐既有嘲笑-否定作用,又有欢快-肯定作用。藏族本来就具有开朗、热诚、直爽的性格。其在展示智慧、娱乐生活、应对压力的过程中也产生了特有的诙谐文化。“宝物”类故事中大多是善恶分明,惩恶扬善,宝物出现后,总能扭转局面,于是穷的、弱的,善良的、美好的一方获胜,富的、强势的、可恶的、丑陋的一方失败。由于依靠了“宝物”,所以,听众在此并不觉得不合逻辑,而是认为合乎情理,终会会心一笑,得到心理的满足。
宝物故事虽然遍及世界各地,但是,“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地理环境中产生的文化现象不可能有完全的一致,表现形式的相似不等于内容的相似,有时即使内容相似,但在各自的文化中的意义和作用也不一样。”[9]康巴藏族民间故事中的“宝物”取材于康巴藏族的现实生活实践中,带有浓厚的地域和民族特色,另外,此类故事体现了康巴丰富的民间想象和智慧,同时,也体现了康巴藏区深层次的政治、经济、伦理道德、宗教、文化内涵。
[1]李昭明、任新建.康巴学简论[J].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
[2]石硕.关于“康巴学”概念的提出及相关问题——兼论康巴文化的特点、内涵与研究价值[J].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2005年第2期
[3]张静.国家与社会[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p36
[4]美国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M].江苏:译林出版社,2011年,p2
[5]马长寿.锛教源流[C].民族学研究集,1943年9月第3期
[6]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7]弗·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23卷)[M].p96-97
[8]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中文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p248
[9]张汝伦.文化的反思[J].读书,1986年第12 期
——林俊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