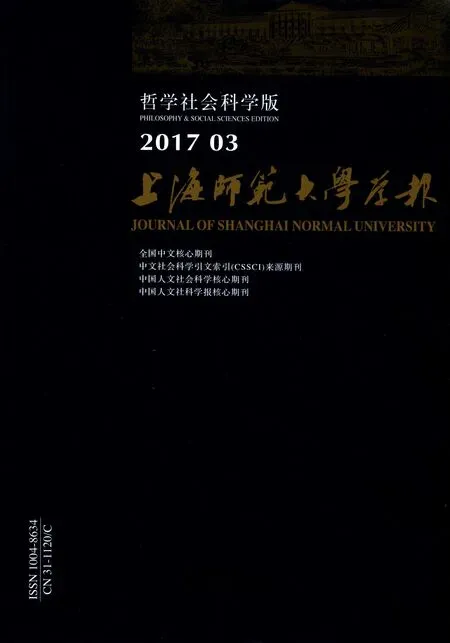论知识技术创新的价值向度
李 凯,祝智庭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信息技术系,上海 200062)
论知识技术创新的价值向度
李 凯,祝智庭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信息技术系,上海 200062)
“创新”已成为当今社会的流行语和高频词。在一个言必称创新的时代,有必要对创新的内涵做出重新梳理和拓展。知识经济时代的创新应该超越既有的认知框架。创新不仅指向技术创新、组织创新、业态创新,而且应该上升为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创新是一种奠基于个性发展的现代价值观,以开放多元的生活态度为内在支撑。万众创新是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迫切呼吁创新型社会和创造性人格的生成,这就需要在实践中积极培育个体价值。
创新;技术创新;万众创新;价值向度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①这里的创新,主要是指技术上的自主发展能力,强调创新是社会进步的阶梯。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首次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方略,万众创新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力引擎。呼唤全民参与创新的意识,倡导人人都可创新的理念,是知识经济时代新一轮的思想解放与社会动员。创新是对既有认识的突破,因而需要一系列新的价值观念为其奠基。正如埃德蒙·费尔普斯在《大繁荣》中所说,焕发高度活力的国家都有相应的生活态度作为支撑,确立起了人文主义价值观和启蒙理性。[1](P338)如何使人们养成创造的智慧?如何使人具有创造的思想力?这是创新时代的哲学任务。创新应该上升为普遍的社会价值导向,把人文价值取向引入创新驱动,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正义,实现创新服务美好生活的目标。
基于互联网的商业社会转型,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社会组织模式的转变,人们的价值取向、伦理标准和行为模式也随之发生激进的变革。传统的价值观念显然无法适用于新生的社会现实,借用昆廷·斯金纳的说法,需要一批“创新型意识形态专家”来解释道德原则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互动和内在紧张。作为当今社会关键词的“创新”观念的崛起,背后既有社会变迁的动因和塑造性力量,又有特定的社会语境和思想语境。如何认识蕴含在创新概念中的伦理图景和社会想象?如何判定创新型人格的属性?其核心特质如何具象化地表达?众创人格应如何培养?为了更好地回应时代精神的召唤,有必要对创新的内涵做出新的诠解。社会崇尚的人格特征也将转向面向市场的人,社会需要一种强大的动力,去创造一种适用于创新时代的人格范型。
一、何为创新?
这是一个言必称创新的时代。“创新”已成为社会的流行语和高频词,但是对于什么是“创新”,似乎仍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要讨论这一问题,我们同样无法绕过熊彼特关于“创新”的经典定义。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 A. Sehumpeter)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从工业生产的角度,把创新界定为“执行新的组合”,即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将某种原先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他认为,创新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1)引入一种新的产品;(2)引进一种新工艺或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一个新市场;(4)取得或控制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种新的供给来源;(5)实现一种企业的新组织。[2](P3~4)在笔者看来,熊彼特所说的这五种形式的创新,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科技创新和业态创新。其中,(1)(2)(4)可归为科技创新;(3)(5)则是业态创新中的商业模式创新和组织创新。按照熊彼特的说法,创新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表现为新事物的出现,即发明创造;二是表现在应用的转化方面,创新就是出现的新事物在应用中的表达。在熊彼特这里,创新主要是作为一种实践方式被强化,作为一种价值观向度的创新,尚未引起必要的关注。熊彼特对创新的多种分类,展现出创新本质的复杂性。
著名进步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指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在于用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经济发展过程,熊彼特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具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3](P94~95)与熊彼特的创新思想的本质区别在于,马克思的创新是资本的内在冲动。“资本家要想售出他的商品,就必须使他的商品更能够符合市场的需求——正是在这里造成了资本家在主观上追逐占有更多剩余价值的动机与他通过创新所生产的商品在客观上总能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的效果之间的统一。因此,第一,在企业层面上,创新必须具有强烈的驱动动机;第二,在社会层面上,创新并不是作为人们一种‘求善’的主观愿望,而是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表现出来的。”②“巨大的物的权力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这种物的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4](P360)创新的成果实质上形成了对自然的集权统治,将人类的无机身体肢解、分化,制造了人与自然物质变化的断裂。
国内外学者关于创新的研究重点大多放在创新与经济增长这一经济学分析范式中。创新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且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但是,若从更为广泛的层面看,对创新的内涵仍可做出进一步分解。其一是经济能力增长意义上的创新。新的技术、制度、方法的发明和应用,其产生虽是价值中立的,但这些新的发明存在着实践领域的善。其二是伦理评价意义上的创新。包括创新的伦理条件、伦理后果、风险评估,带来的社会、政治、环境等一系列的影响,创新的规范问题,技术发明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等等。三是社会价值观意义上的创新。作为价值观念的创新,需要确立对“创新”价值内涵的基本认同,也离不开对创新本身的时代解读和价值定位。
创新要成为人人生命的自觉,成为社会的日用常行,才能更好地转化为现实中的创造力。问题是如何使创新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成为我们生命的能力?当前社会提倡的万众创新,包括经济上的投入、组织制度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更好地激发出每个人身上的创造活力。如果我们将创新视为改革要达成的一个重要目标,则恰恰可以借鉴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框架,现在制度变革、组织变革都是为了在正式制度上促成创新成为风气;还要在非正式制度上做出变革,这就涉及心智构念问题。心智构念很大程度上是指文化构成的思维和反应模式。在心智构念上解决创新的问题,一方面是接续中国文化传统中重德的一面,让创新活动包含更多的自觉目的上的善;另一方面则是要接续西方的文化精髓,让现代的创造文化、有助于提升创造能力的机制认同深入我们的生命自觉中。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和突破,背后就伴随着一系列创新观念上的变革,或许可以从历史的对比中找到合适的突破点,而且这一讨论背后深层的方面是对人文与科学关系的协调与探讨。
当前国家提出“万众创新”,实质上是强调了创新主体的转变,或者说是强化了在创新问题上全民参与的意识。万众创新,至少包含以下三层内涵:第一,万众创新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意在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让民众意识到创新是全民皆可参与的事情,而不只是科技工作者的事情。虽然各个阶层在创新上都有所贡献:工人在生产中的技术革新,农民在养殖、种植方面的革新,普通创业者在商业模式上的大胆尝试,这些实际上都是创新,但在一般民众的意识中还经常认为只有科研工作者才可能有创新,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普通人创造力的发挥。强调“万众创新”,并不意味着否认精英阶层是创新的主要力量,实际上尖端的科技创新往往还是要依靠科技精英,但是这一口号的提出却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力。第二,突出了创新的“应用”内涵。创新不只是简单的发明,而是能施之于社会发展需要的实践活动。创新实质上离不开“大众”,任何创造或发明要想称为创新的实践就必定离不开技术上的转化;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和需求,这都离不开大众的需求或者参与。第三,“万众”还表明了“创新”的伦理蕴涵,即一项活动如果能称为“创新”,就必然要符合民众的需求和利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创新的根本坐标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创新必须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一项实践活动之所以能称得上“创新”,除了它自身所具有的新事物的特点外,重要的还在于这种新的发明或实践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反之,如果一项新的发明或实践活动背离人民的利益和需要,只可能诱发罪恶,这样的发明或实践就应该被否定。
二、 技术创新的伦理条件
创新不仅是技术上的发明创造和组织形式的变革,而且内嵌着深刻的社会价值观变迁。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技术创新,不仅需要注重创意和研发,而且更重要的是搜寻、利用和转化创新成果。为了确保创新的应用性和高效率,必须完善自我约束与制度制约。现在整个社会关注的重心是如何鼓励和保护创新,但是还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如何与更广泛的发展目标结合起来,如何防范和制约过度创新带来的社会风险和伦理后果?
创新是否需要伦理条件的支撑?或者说需要做哪些伦理准备才能更好地促进创新实践的发展?诚然,创新不仅需要物质条件和智力支持,还需要制度、伦理、法律等多方面的支撑。所谓“创新的伦理支撑”就不是表现为一个纯粹的伦理问题,而是涉及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的问题。但是如果严格从道德规范的角度审视创新,是不是只有符合了某些伦理要求或具备了某些伦理特质的创新活动才能更好地得到实现?从经验层面看,一个人的创造力和他本身的道德水准似乎并没有必然关系,有时候拘泥于道德规范反倒可能限制某些创造力的发挥。如果我们能证明一种发明的存在本身就是罪恶,它的出现也只可能带来罪恶,这种发明已经不再是道德中立的,不仅没有任何工具上的善,而且还是内在目的性的恶,那在伦理上可以规定禁止做这样的创造和发明,这也是对创新的一种伦理支撑的表现。就技术发明本身来说,一项发明本身往往是道德上中立的,只是因为人类的应用才会有或好或坏的后果,因而只有在发明的运用上才需要伦理的规范。伦理规范对创新来说好像永远都是事后才起作用的,因而不是抽象地支撑创新,而是具体地规范某一新生事物的发展,在这种规范中更好地刺激后续的创新。
如果承认创新需要某种伦理支撑的话,那真正需要的可能是伦理审查意义上的支撑,也即任何发明创造的程序是不是符合伦理规范。明晰严格的伦理审查有利于规范研究和发明,从而推动创新的发展。但伦理审查明确的也只是禁止性权利,所以它也不是积极意义上的支撑创新的伦理条件,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限制发明创造。伦理审查只是基于伦理上的审慎原则,它在根本上也无法证明某些科学研究的绝对危害性,因而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正确性;而且某些伦理上的审慎反倒可能会阻碍科技的进步。就像前些年欧洲的大型强子对撞机实验,有团体就担心粒子碰撞的实验可能会产生黑洞进而吞噬整个地球,从而反对这一实验。如果这种担心成为伦理审查的依据,那就可能会阻止这一实验的进行,也就不会有后来一系列的实验成果。对创新问题的伦理关注,必须结合具体的创新实践——观察一项发明运用中潜在的伦理风险,或者是发现一种新的类型的实践活动中存在的伦理争议问题。这样的研究,就不同于以往抽象的研究,而且是真正的应用性研究。强调和具体实践相结合,不只是从概念到概念,而且是针对具体实践事务的研究,或者是对某一类型的事务要有其共性的研究。这种应用上的突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解决和阐释新事物中的伦理问题,一是为新的伦理价值与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做论证。
解决和阐释新事物中的伦理问题,就是针对新事物中出现的新的伦理问题做出解释,给出解决方案。针对新问题的回答和思考而言,在某种意义上也能算作是伦理的创新。而为新的伦理价值与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做论证,就实践原来的状态而言,其本身并不包含某一伦理价值,现在发现了这一伦理价值与这种实践活动之间的联系,就需要对这种联系做出论证。就像经济活动原来只是单纯的生产、消费关系问题,现在要把劳动福利、环境保护等因素考虑进来,就需要论证这些新的价值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如果能发现新的伦理价值与这一活动之间的联系,并通过论证将这些新的价值考虑到这一实践活动中,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创新。
创新需要伦理支撑,但是这种需要主要不是前提上的需要,而是规范上的需要。对创新进行伦理评价不是伦理审查意义上的,而是对创新过程和结果的伦理评估。这种评价的意义在于规范对新事物的运用。发明创造在运用方面的转化是创新的最后环节,也正是在这里才真正有了伦理运作的空间。如何使发明创造的运用符合伦理的要求,或者这些新的发明或创造的运用要符合哪些伦理要求,这是在伦理上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创新的完成意义上也算是一种伦理支撑。因此,讨论创新的伦理条件,还需要对技术创新的伦理后果、风险规避做出深刻反思,深入考察创新的伦理之维,使技术创新实现伦理上的“软着陆”,建构新技术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之间的缓冲机制,实现技术创新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三、技术创新的本质追问
这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技术成了我们时代的命运。现代技术已从哈贝马斯所说的“作为意识形态”的存在发展为一种权力性存在,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具有支配性作用。人不断“被技术化”,在技术创新中生存发展,又在技术创新中获得解放和自由。“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5](P74~75)技术创新促进了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增长,把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为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解放奠定了物质基础,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技术创新是对人自身的超越,技术在充满活力的文化现实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现代文化以现代技术为基础,并越来越被技术控制和决定。弗洛姆曾对技术发展的两大指导原则提出质疑:第一,凡是技术上能够做的事情都应该做;第二,追求最大的效率与产出。只关心技术创新的成果和效率,忽视了技术创新的价值理性维度。利奥塔曾直白地指出:“技术不属于与真善相关的一种游戏,而属于与效率相关的一种游戏;当一个技术活动比另一个做得更好或者消耗更少的能量时,它就是‘好’的。”[6](P99)技术创新的唯利性,使技术异化为单向度的存在,手段成了目的,技术创新的多维价值被消解了。
这是一个由工具理性操作和规划的时代,如何走出工具理性的普遍强制性,开启一种新的可能性?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开宗明义说:“技术不同于技术之本质。”通常认为,技术无非是一种手段和人类行为,是价值中立的存在物。海德格尔认为,这远远没有触及技术之本质。“现代技术既不仅仅是一种人类行为,根本上也不只是这种人类行为范围内的一个单纯的工具。”[7](P939)为了通达技术之本质,我们必须追问工具的意义。海德格尔通过提出“座架”概念,特别阐明了技术对于人类自由的意义。
技术创新的价值证成可以区分为两个基本维度:一是工具性价值,二是内在性价值。除了技术创新所固有的物化价值,还应该考量创新对生活世界的意义,对人性、人的本质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就技术本身而言具有价值中立性,但它同时又是价值的负载。它和何种价值立场结合,就会服务于何种价值。技术就是合目的的手段和工具。
作为价值观意义上的创新,不仅要关注“能不能”,还应追问“该不该”? 新的不一定是好的,对创新的伦理评价离不开一个善的维度,包括工具善与目的善。创新之善作为一种价值观念的根据,可以由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性得到论证。现今,创新“技术是人的存在方式”,[8](P2)通过“工具、机械以及相伴随着的技术,我们已经把这个世界变得更适合于我们的需要,变成了一个更为安全的所在”。[9](P31)C·米切姆也指出:“社会化的技术不仅要从这个星球表面消除匮乏,而且作为一种人的‘类生活’也将完成哲学和宗教所不能完成的事业,通过使自然成为人类本质力量的反映,技术将允许人类最终证实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而不仅仅是存在于思想和天堂中。”[10](P83)创新技术已经成为一种使人类安适的重要方式,尤其是在现代高新技术的影响下,创新使社会日益进化为一个人技关联、流动和相互作用程度很高的整体。
创新的本质表现为基于人类需要而产生的制作的真实性与生成的合宜性。创新之善的特殊性就是制作真实性与生成合宜性的结合与实现,因其影响到个人利益及公共利益的实现、甚至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变,因而更为重要,也更值得关注。如果我们认同医疗创新的善在于健康,建筑创新的善在于建造更舒适的房屋,那么,医疗或建筑创新的善能否获得实现的关键在于实施者是否具备“为何而为”的价值理念与“应该如何而为”的责任意识。
如果我们从具体实践层面理解创新,正像康德所主张的,创制或“技术是人们出于某种目的和意图而实施的生产或制作等活动方式,技术的善的实现离不开行为者的道德责任”。[11](P33~35)我们提出将创新作为一种价值观,重在强调从业人员的行为动机与目的的伦理自主性,注重创新行为的价值判断,强调在行使公共权力或从事创新活动中,通过内化的信念和善恶标准,从内在良知上体现出对公共利益的关怀,做到在创新活动领域中充分履行其应有的责任。
一个人如果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与选择从事某项创新活动,他都会尽力把自己所从事的活动完成好。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对一个吹笛手、一个木匠或任何一个匠师,总而言之,对任何一个有某种活动或实践的人来说,他们的善或出色就在于那种活动的完善。”[12](P19)对于那些出于自己意愿与选择的行为,行为者既然明白“为何而为”与“应该如何而为”的道理,那么,做的好或坏通常都在行为者的能力范围内,这样,他也理应从价值的定位与材料的把握上尽力推进创新之善的实现。
技术和人性的交互作用总是处于动态的构建之中,技术悲观主义与技术乐观主义都有值得借鉴和反思之处。科学精神就是希腊的人文精神,根本上就是自由精神。现代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仍然基于实用的层面,对于科学精神中根本的东西不予关注。③创新是走向自由的人类活动。自由劳动作为人的本质的体现,它是人的一切活动的目的,具有理想性。自由劳动重要的是劳动主体与自身劳动本质对立的消除,让创新成为一种人本质化的需要,创新活动是达成自由劳动的重要手段,也是最具有现实可能性的途径。
四、 创新价值观的品格培育
互联网技术和平台的联姻,不仅仅是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简单相加,而是体现了新的发展生态,创造了新的价值空间,使传统行业获得了新的生机。创新已不再是少数精英的专利,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共同事业。原创性新技术的崛起,特别需要尊重多样化、个性化、独特性的自由想象力。创新型社会和创造性人格,是创新价值观生成的土壤和载体,需要在实践中积极培育个体价值,促进个性自由和差异化发展。
创新是生命的存在样态和本质要求。在万众创新的时代,重温工匠的创造精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能工巧匠”“巧夺天工”,都是对工匠创造精神的写照。《说文解字》曰:“‘工’,巧饰也。”《考工记》曰:“天有时,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工匠精神首先是术业专攻、业精于勤的不懈探索精神。发明了墨斗、刨子等器物的鲁班,就是工匠精神的典型化身。“木匠做木匠的事,鞋匠做鞋匠的事,其他的人也都这样,各起各的天然作用,不起别种人的作用,这种正确的分工乃是正义的影子。”[13](P172)中世纪欧洲兴起的技术革新运动,是工匠们跨越几个世纪经验技术积累的产物,凝结着工匠阶层巨大的创造热情和灵巧智慧。近两百年来的德国现代化道路,从外部看,是一条技术兴国、制造强国的道路;从内部看,支撑这一道路的是“工匠精神”——对技术工艺宗教般的狂热追求远远超越了对利润的角逐。[14](P68)
在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中,匠人精神脱颖而出。书中断言匠人的劳动是光明时代的象征,应该让手工劳动者重获其在古希腊时代的声誉。狄德罗推崇下等阶层的活力,希望人们仰慕而不是可怜平凡的工人。狄德罗认为,无聊是最具腐蚀性的,它会侵蚀人们的意志。伏尔泰在小说《憨第德》中,通过憨第德这个忠厚老实、头脑迟钝的学生之口,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还是种咱自己的园地要紧。”对那些在生活里遭遇不幸的人来说,简单的劳动是一剂良药。遭遇不幸的人应该去打理花园,而不是顾影自怜。
模范是参考和刺激,而不是强加命令,刺激我们通过模仿,不断去实现创新。面对新技术和大机器,人应该许可自身的局限性,并用自己的个体性来对抗机器和技术的优越性。个体性可以赋予我们以特色。韦伯强调“志业”(Beruf)能够“增加”生命的价值。韦伯的志业观念扎根于宗教,是上帝的召唤,是外在于自我的天职(Calling)。通过创新,可以不断强化知识技能和信念。现代价值观,如创造性、好奇心和生命力的培育和强化,是社会经济创新发展的原动力。草根创新、大众创新呼唤永不停歇的构想、实验和开拓精神,这种草根精神是由现代主义的生活态度和信仰驱动的,勇敢运用理性批判和自我反省,勇敢追求丰富多元的生活。现代主义的核心是,个人应该有追求幸福的自由。个体通过创新活动寻找生活的意义,通过工作精神获得了客观化的表达。创新过程是生命活动的自我展开,使用并发展着自己的能力和技能,变成了一种忘我的投入,因为获得了真正的满足感而感到自由和幸福。
全球化的后果之一是同质化和平庸化,把人性磨成一律,个体成为平面化、单向度的存在。“人类要成为思考中高贵而美丽的对象,不能靠着把自身中一切个人性的东西都磨成一律,而要靠在他人权力和利益所许可的限度之内把它培养起来和发扬出来。”[15](P74)密尔认为,大众民主社会出现的同质化,会导致集体的平庸,这才需要在思想观念上高扬“个性”,并在实践中培植人的个性。
一个具有高度创造性的现代社会,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一个多样性的社会,是一个能够让每个人有充分发挥自己个性和才能的自由空间。如何高扬或培植起人的个性、克服或抵抗这种大众化的趋向,从而获得个人的自我发展?借用密尔的说法,创新型社会大致具有以下特质:第一个特性就是首创性(originality),注重个人的活力和多元分歧。第二个特性就是特异性,即个人的差异性和行动的独特性。这实际上也意指在大众平凡的社会中保持人行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一个大众化的社会里,应该格外地鼓励个人发挥自己的“怪异”,不仅因为这样的怪异体现着个人的个性,更重要的还在于这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矫正大众民主社会的平凡性与专制暴虐的最好方式。第三个特性是独立性。所谓独立性,就是要用自己的理性去思考、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盲从、甚至依从于社会的一般观念、经验乃至风俗。创新型社会就是能够涌现“首创性”的社会,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做出自己的“首创性”。就像在英国工业革命中那样,那些做出“天才式”首创性的人很多都是普通的人,如发明水力纺纱机的阿克莱特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乡村理发师;而发明蒸汽机的瓦特也只是格拉斯哥大学的实验员。
苹果创始人乔布斯毕生践行了毕加索的名言:领袖和跟风者的区别就在于创新。乔布斯执着于用创新理念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美国社会价值观具有一种追求创新力的英雄主义情结,个人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感有人文基础的支撑。美国成功建立科技园区,整个社会环境给创新力以沃土,教育过程中尤其注重对创新能力的培养。创新价值观的塑造,不仅是关于经济成长的探讨,而且是关于人类共同幸福的思考。正是福特汽车创始人“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一辆汽车的平等主义的理想”创造了福特汽车的辉煌,指明了创新的价值方向,成为人类创新史上的不朽佳话。汽车不应该只属于少数富人,而应该让每个人都买得起,才能使这个世界更加美好。从价值观的层面看,创新的本质正是为了促进美好生活、社会正义和人类福祉。
创新要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习惯,需要提供试错和风险成长的试验场。创新是探求未知领域的事业,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创新文化应该提倡敢于冒险的精神和宽容失败的氛围。领衔世界级科技创新的贝尔实验室,就是这一创新精神的最好例证。贝尔实验室的创新文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允许失败,特别是对那些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的失败容忍程度更大。
把创新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来考察,还要依托传统伦理资源和思想史的经验。从理念到原则,再到制度,为新兴的“众创社会”铸造适用的品性。比如休谟等人对勤勉、审慎等观念如何上升为社会广泛认同的基本价值观的考察,《易传》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贵在求新传统,以及“五四”以来“创造”日益成长为备受推崇的价值,都是可资借鉴的思想史资源。在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当创新真正成长为我们的价值观,人类才能自觉安顿自己的精神家园,合理规避韦伯所批评的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蚀。以个性充分发展为旨归的创新,才是个体快乐的源泉,也是整个人类的福祉。
注释:
①江泽民同志1995年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②关士续:《马克思关于技术创新的一些论述》,《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年第1期。印度著名经济学家乔杜里(Roychowdhury)将马克思的创新思想分成两种类型:一是既定生产过程的技术合理化,包括与总体技术变化不一致的成本降低的各种情况,如技术进步等;二是一种技术向另外一种技术的转移,如生产方式的革命、发明、机器改良等。K.K.Roychowdhury: The classical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The Macmillam Company of India Limited, 1979.
③吴国盛认为,现代科学的两大基因是希腊的基因和基督教的基因。基督教的自由更强调意志自由,因为基督教无法回避上帝这个环节,而这种意志自由绝对不是希腊意义上的理性自由。到了近代,意志自由就转化为一种对外部的支配。人类就像上帝那样,变成了秉承自由意志的一种存在体。今天重提希腊精神,也是西方的思潮,它是现代西方人反省现代性以及从现代性危机中自我拯救的一个大趋势。参见吴国盛:《技术哲学演讲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 埃德蒙·费尔普斯.大繁荣[M].余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2]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 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英文版)[M].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2.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冯俊,等.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7] 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A].海德格尔选集·下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8] 吴国盛.技术哲学演讲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9] 杜威.经验与自然[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10] Mitcham C. 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 The path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Philosoph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11]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2002.
[12]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03.
[13] 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4] 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15] 约翰·密尔.论自由[M].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责任编辑:法 芒)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LI Kai,ZHU Zhiting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Innovation has become the buzzword and high frequency words in today’s society. It is necessary to re-clean up and expand the connotation of innovation. Innovation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should go beyond the existing cognitive framework. Innovation not only points t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format innovation, but also should rise to universal social values. Innovation is a modern value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ity and motivated by open and diverse attitudes towards life. Innovation is a new round of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an urgent call for innovative society and the creation of creative personality, which requires the active cultivation of individual values in practice.
innov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ass innovation, value dimension
2016-12-20
李 凯,山东菏泽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信息技术系,主要从事教育技术学研究。
B821
A
1004-8634(2017)03-0034-(07)
10.13852/J.CNKI.JSHNU.2017.03.005
祝智庭,浙江衢州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信息技术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技术理论、技术哲学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