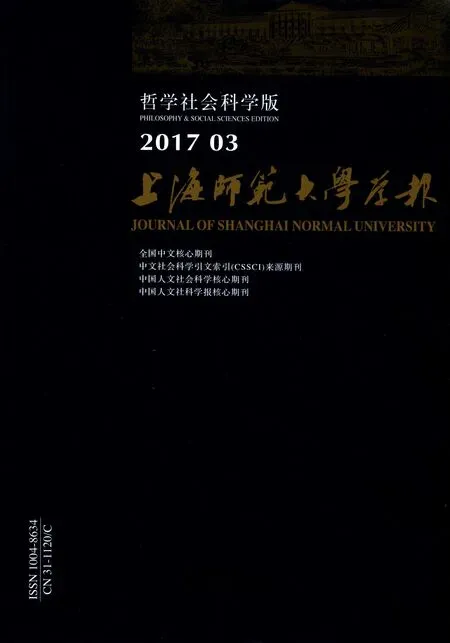中国临时仲裁制度的构建
张贤达
(大连海事大学 法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0)
中国临时仲裁制度的构建
张贤达
(大连海事大学 法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0)
从立法上将临时仲裁予以排除,不仅与国际通行不相吻合,也会产生许多不公平、不对等的问题。文章从历史、政治、社会、经济背景等多方面入手,认为阻碍中国引入临时仲裁的因素已经消除,并试图为中国引入临时仲裁的理论桎梏解套。在构建临时仲裁制度方面,不仅包括对仲裁协议有效要件的修改,还应从三个方面着手构建中国的临时仲裁制度:为临时仲裁提供相关配套机制;建立全国仲裁协会;提高仲裁员适用临时仲裁的水平。
仲裁制度;临时仲裁;制度构建
一、临时仲裁在中国的现状及问题
在当今社会,仲裁已经发展成为国际商事最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①目前的国际商事仲裁体系基于《纽约公约》运行。《纽约公约》建立起一个高效的法律框架,它能有效地促进跨境纠纷的解决,亦有利于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②
根据仲裁程序是否由仲裁机构引导和管理,商事仲裁分为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临时仲裁比机构仲裁早产生了几千年。由于仲裁本质上的分散性,同时也出于纠纷当事人所关心的保密性,很难搜集到准确的数据来比较临时仲裁和机构仲裁案件数量孰多孰少。但总体上,这两种纠纷解决方式在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是齐头并进的。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瑞典等多数国家的仲裁制度中既包含机构仲裁,也包含临时仲裁。甚至在少数国家如葡萄牙,临时仲裁成为主要的仲裁形式。希腊还曾一度取消机构仲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临时仲裁。③
临时仲裁在效率和规则灵活性等方面具有机构仲裁无法比拟的优势,在国际商事诸多纠纷领域,当事人也更倾向于选择临时仲裁而非机构仲裁来解决争议。但中国在加入《纽约公约》后,并未建立起临时仲裁制度,中国《仲裁法》将仲裁委员会的明确规定作为仲裁协议有效的要件之一,从立法上将临时仲裁予以排除。《仲裁法》的这一规定,不仅与国际通行不相吻合,也会产生许多不公平、不对等的问题。例如,中国南通市港闸造船厂诉荷兰埃伯造船服务公司、荷兰船用设备与维修公司、中国化工建设总公司船舶建造合同纠纷主管异议案,与达利特商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沧州东鸿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两案仅因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地(前者约定仲裁地为荷兰,荷兰仲裁法承认临时仲裁;后者约定仲裁地为北京,中国不承认临时仲裁,约定无效)不同而得到了截然不同的仲裁结果。仲裁协议是提起仲裁的前提,仲裁协议的有效与否不仅关乎当事人能否将争议提交仲裁,排除法院的管辖,更关乎当事人能否顺利地获得和执行仲裁裁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仲裁裁决是基于一份无效的仲裁协议而做出的,那么这份裁决可能被仲裁地法院撤销,也可能在《纽约公约》的成员国内被其他国家的法院拒绝承认和执行。对于同样的临时仲裁协议,仅因仲裁地的不同,却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这显然忽视了仲裁协议在仲裁中的重要性,且这样不公平、不对等的情况既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权益,也有悖于《纽约公约》的规定。除此之外,这一自相矛盾的局面不但不利于涉外经济贸易纠纷的及时有效解决,也不利于进一步吸引外商、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将不利于中国仲裁事业的长远发展。④
二、中国不设立临时仲裁的成因分析
1.对立法部门解释的评析
在《仲裁法》的起草过程中,对于是否引入临时仲裁制度,立法部门确实也进行过研究,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临时仲裁制度可以用来解决国际经济和贸易纠纷,但不能适用于解决国内的经济和贸易纠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法工委”)也做出了如下解释:“在仲裁制度的发展史上先有临时仲裁,后有机构仲裁,从今后发展趋势看,临时仲裁趋于衰落;中国设仲裁的历史较短,只有机构仲裁,没有临时仲裁。”⑤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法工委的这两个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第一,从世界范围内的仲裁发展来看,机构仲裁与临时仲裁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而且,如前述,临时仲裁制度不仅仍存在于许多仲裁发达的国家,而且甚至成为一些国家的主要仲裁形式。在某些仲裁领域,如海事仲裁,临时仲裁是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据统计,在瑞士国内的仲裁案件中,临时仲裁占40%,而在瑞典的全部仲裁案件中,临时仲裁则约占50%。⑥据调查报告显示,在国际贸易领域,贸易出口商中有45%的人要求选择临时仲裁处理纠纷。⑦可见,临时仲裁至今仍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仲裁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临时仲裁正走向衰败。第二,不能仅以中国的仲裁历史短以及无临时仲裁历史为由而将临时仲裁排除。事实上,就是因为中国仲裁历史较短,相比机构,临时仲裁以其自身的灵活性、自主性和高效性更容易建立起来。此外,从逻辑上看,没有临时仲裁的历史并不意味着将来就不会设立临时仲裁制度,中国的许多法律制度,如物权法律制度等,均是从国外引进,并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由此可见,法工委的上述两个理由无法成立。
为什么立法部门给出这么没有说服力的解释?为了探究隐含在政策背后的原因,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中西方仲裁史进行比较研究。笔者试图通过这一研究揭示中国仲裁发展历史中可能影响仲裁规则制定的因素,找到中国不设立临时仲裁制度的真正原因。
2.仲裁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历史
仲裁在西方社会中已经历了很长时间。早在公元前1500年,仲裁就被运用于古埃及。⑧早期的商事仲裁多发生于同行业的商人之间。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发生纠纷之后,为了节省时间和金钱,也为了避免繁杂的司法程序,即在同行业中推选他们共同信任且有威信的人居中调和或裁断。由于这些被推选的人往往与被推选的当事人存在商业伙伴关系,因此,在许多情况下,纠纷当事人之间难以共同推选出合适的仲裁员,故较为公正的做法就是双方各自提名其所信任的人担任仲裁员,由获提名的两名仲裁员共同处理该纠纷。而一旦这两名仲裁员之间产生分歧,意见难以统一时,则须由他们共同推选出一名“公断人”,由其独立做出裁决。在中世纪许多欧洲国家,仲裁在商事和海事领域均得到了很好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仲裁能够避免不同国家错综复杂的法院体系,并以其中立、高效及拥有商事专业人才解决商事纠纷的优势,使得仲裁备受商人的青睐。仲裁发展到现代社会,其在解决私人纠纷,特别是国际商事纠纷上的优势已经变得十分明显。在仲裁的发展过程中,直到19世纪中叶机构仲裁出现以前,临时仲裁独霸国际、国内商事仲裁,所有仲裁案件均通过临时仲裁的方式解决。
可以说,仲裁在西方经历了自下而上的发展道路。仲裁起源于纠纷当事人希冀通过第三方以友好的方式解决纠纷的愿望。仲裁的介入满足了当事人希望避开国家法院系统,以一种最大化的中立、灵活、高效、保密的方式来解决争端的意愿。随着仲裁的发展,国家法律和法院逐渐承认和尊重当事人的愿望,并设计了仲裁制度以支持或便利这种私人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践操作。
3.仲裁在中国的发展历史
仲裁在中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在20世纪之前,仲裁在中国没有得到发展。通观中国的历史,特别是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840年,中国处于封建社会时期,实施重农抑商的国家政策。在这样的政策下,经济活动并不活跃。因此,经济纠纷也相对较少,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仲裁得不到发展的空间。任何与财产或经济利益相关的纠纷均由官府主持解决。在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允许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进行商事交易。同时,清政府也意识到其自身的缺陷及所面临的内部矛盾。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清政府希望进行一系列改革。20世纪初,清政府主动促进商事活动的发展。当商事活动出现繁荣景象之时,商事纠纷也随之增多。但由于缺乏处理商事纠纷的经验,也由于当时并没有制定解决纠纷的程序规则和实体法律,清政府无力解决这些商事纠纷。⑨为了满足当时广大商民的需求,也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统治,清政府于1904年颁行了《商会简明章程》,规定“凡华商遇有纠葛,可赴商会告知总理,定期邀集各董事公理论,一众公断”。⑩由此,清政府正式授予了商会对商事纠纷的裁判权。此后,各地商会在创办过程中也纷纷将裁判权列入自己的章程之中。在实践中,部分商会还成立了如理案处、评议处等机构专门负责纠纷的调处,并聘请享有社会名望且行事公正的会员担任评议员。如在1909年,成都商务总会首创“商事仲裁所”,旨在“和平处理商业上之纠葛,以保商规,息商累”。这些都被认为是中国早期的仲裁制度。
在民国时期,出现了一个类似的仲裁制度。当时,商会在许多地方创建了商事仲裁分会处理商事纠纷。不幸的是,由于社会不稳定,战事不断,尽管许多纠纷都以仲裁的方式解决,但当时的仲裁制度仍然发展缓慢。
新中国成立以后,旧的法律制度,包括仲裁制度,都被废除了。1957年,中国开始推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即便是个体企业都无法独立做出决断。相反,它们只需要根据政府的决定生产、供应、购买或销售。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之间极少发生纠纷。即使有纠纷,也可以通过政府管理部门调和的方式解决。中国的仲裁在这一历史期间仅限于涉外商事纠纷。为了解决外国投资者投资纠纷,以及外商与中国企业的合同纠纷,中央政府建立了两个涉外仲裁机构专门处理涉外纠纷: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和海事仲裁委员会。
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被打破,市场经济体制开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这一经济体制的运行下,商业活动又恢复了活力。相比于晚清时期,这一阶段的经济环境需要一个新的纠纷解决机制。20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在现有的司法体制下建立了解决国内商事纠纷的仲裁体制,但仍延续计划经济时代的旧习惯及思想,行政机关仍被授权对仲裁体制进行管理,法律与规章也赋权政府机关“仲裁”纠纷。此外,根据法律的规定,一些如同政府隶属机构的仲裁机构开始处理仲裁纠纷。
但这些仲裁机构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仲裁机构。事实上,政府也明确说明了这些仲裁机构“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仲裁机构是不同的”,因为中国的仲裁机构是“代表国家执行仲裁权”,且“仲裁裁决代表国家的意愿”。这一仲裁体系与中国目前实践中的仲裁相比,也缺乏仲裁的自身特性。例如,仲裁并非一裁终局,争议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对裁决不满,均可在收到裁决之后将案件起诉至法院。由于中国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融合,为了使中国的仲裁制度更贴近现代仲裁原则和实践,中国于1994年颁布了《仲裁法》。
可见,与西方仲裁不同的是,中国的仲裁制度经历了自上而下的发展历程。在20世纪初叶以及80年代,为了发展经济,政府试图推进商业的发展,因此,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商业实践的需求,政府建立了仲裁机构使得商事纠纷得以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但我们应注意的是,在这两个历史时期中,中国仅建立了机构仲裁,而未建立临时仲裁制度。
4.中西仲裁的不同发展历程告诉了我们什么
通过对中西方仲裁史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相较于西方,中国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在西方,仲裁经历了自下而上的发展历程。仲裁起源于临时仲裁,与要法院做出公正判决这一诉求不同的是,临时仲裁是最适合商人对于中立第三方的需求的。机构仲裁晚于临时仲裁产生,其设立的目的在于为纠纷当事人和仲裁员提供专业服务。机构仲裁在产生之后在世界范围内也逐渐普及开来。而在中国则相反,仲裁的发展经历了自上而下的发展历程,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经历了长期不发达的商业发展道路。在中国,直到20世纪初及80年代发生剧烈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中国从未存在过对于仲裁的实际需要。当仲裁真正在中国建立起来时,临时仲裁也就不会被这一制度所吸纳了。
从比较研究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与西方仲裁制度自然发展不同的是,中国仲裁制度的发展在建立初期主要取决于政府政策。当中国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并设立仲裁制度时,政府可能认为没有必要遵循西方仲裁的发展模式,而这一模式毋庸置疑地包含了临时仲裁。相反,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政府只是简单地希望设立一个适应彼时社会需要的制度——一套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下,适应解决商事纠纷迫切需求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这一目的的驱使下,政府更倾向于建立压缩版的仲裁制度,摒弃了西方社会通行的双轨制,采用的是单一模式的仲裁制度,即仅有机构仲裁而没有临时仲裁。政府可以对这种仲裁制度进行有效的管理,且为仲裁实践提供规则和准则,为那些当时可能从未听说或参与过仲裁的纠纷当事人和仲裁从业者带来便利。这也使得当时的仲裁制度行政化色彩浓厚。从这一角度来看,相比机构仲裁而言,对于临时仲裁的控制、管理难度颇大,因此,临时仲裁也就得不到当时政府的青睐了。
5.《仲裁法》颁布时特定的社会背景
为了更好地理解《仲裁法》立法背后的理论依据,我们需要从颁布时的政治、社会、经济因素着手进行研究。如前所述,中国直到1978年才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样的经济体制转变一直持续到今天,且经历了艰辛的过程,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经济体制的变革在研究中国法律制度包括仲裁制度过程中是不容忽视的。
如前所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活动是被政府严格控制的,这也包括纠纷解决机制的运行。相反,这是民间性仲裁特别是临时仲裁所极力希望避免的。人们选择临时仲裁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它可以尽可能地摆脱政府的控制,并以私人的方式来解决彼此之间的纠纷。而且,临时仲裁的特点在于其灵活且高效,以致其很难被管理或控制。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计划经济体制与临时仲裁本质上是相互排斥的。
在市场经济实施初期,政府对处理改革非常小心。因为政府官员更倾向于以不断稳定的进步来面对如此频繁且剧烈的社会变革。事实上,当《仲裁法》颁布实施时,“仲裁”这一概念本身在中国是如此之新,以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胡康生眼中,《仲裁法》本身就富有“改革的精神”。例如,在《仲裁法》颁布之前,共有14部法律、82个行政法规、190个地方法规对仲裁进行规范。《仲裁法》的颁布实施,突破了多年来全国范围内分散且数目繁多的仲裁立法局面,更破除了当时有多个行政部门进行行政性仲裁的体制,在中国正式建立了统一的仲裁制度;这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欲从行政性仲裁过渡到民间性仲裁的决心。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中国立法机构希望循序渐进地实施改革的目的就变得可以理解了。一个缓慢的过渡期可以为政府提供充足的时间去放宽对于私有企业的控制,私有企业也可以从新制度内部积攒经验。与临时仲裁相比,机构仲裁无疑更适应这样的目的。政府可以更容易地控制仲裁机构,同样,也更容易控制具体的仲裁案件。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在决定是否引进临时仲裁制度之前,作为尝试,政府在刚开始时更愿意接受机构仲裁。因此,当《仲裁法》于1994年实施时,中国的立法机关并没有当然地选择世界上通行的双轨制,而是仅仅选择一种过渡且不完美但更适合当时社会、经济环境的仲裁制度。
中国拒绝引入临时仲裁制度的真正原因与中国的历史、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息息相关。但时至今日,这些阻碍中国设立临时仲裁制度的因素已经不复存在了。首先,计划经济已经被废除,政府已不再全盘操纵全国的经济事务,企业也无须依照政府的指令运营。相反,中国经济正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高速发展。其次,政府逐渐削弱其中央集中控制,不再像以往那样把控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民商事领域,中国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作为一项法律原则规定在中国法律中,《民法通则》《合同法》等均有体现。在纠纷解决机制中,意思自治表现在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通过协商、调解、仲裁或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如此,政府并不直接参与纠纷的解决。最后,《仲裁法》颁布至今,中国已经积累了充足的仲裁经验,且已经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拥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仲裁员及律师。
三、中国引入临时仲裁制度的理论障碍及其突破
在中国的仲裁理论界,就中国是否应当引入临时仲裁这一议题,纷争已久,大致可以划分为应当引入以及暂缓引入两种观点。
其中,多数学者积极主张在中国建立临时仲裁制度,相比持暂缓观点的学者而言,有绝对数量优势的论文体现。
持暂缓观点的学者所主张的理论依据主要包括:临时仲裁制度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到较高程度并产生了一些信望素孚的专业人士的法治环境下才可能确立,目前中国市场经济秩序仍不够有序,国家资产缺乏明晰的产权界定,地方政府指定贷款和指令破产逃债大量存在,在这样的状态下人们难以选择临时仲裁;在缺乏诚实信用的情况下,当事人对临时仲裁的公正性没有信心,而中国目前仲裁员自身素质还急待提高;临时仲裁的进行几乎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合意,如果当事人双方不能充分合作,如果不能合意选择仲裁员,仲裁就无法进行;等等。持暂缓观点的学者认为,临时仲裁制度不适合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因此应当暂缓引入。
笔者认为,随着中国仲裁制度的不断发展,反对者所持观点已无法成为中国引入临时仲裁的桎梏。中国现阶段存在设立临时仲裁制度的条件和可能,分析如下:
首先,对于因中国市场经济秩序仍不够有序,在国家资产缺乏明晰产权界定的情况下难以指定足具社会公信力的临时仲裁员而主张不引入临时仲裁的观点,笔者认为,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可能恰恰与临时仲裁缺失有关。这些现象实际上也正是在中国没有临时仲裁制度情况下存在的。至于临时仲裁员的公信力问题,《仲裁法》规定了仲裁员的聘任标准,如果中国成功引入临时仲裁制度,在具体仲裁程序中,当事人在临时仲裁中所选任的仲裁员与机构仲裁中的仲裁员都必须是符合《仲裁法》标准且由仲裁委员会聘任的仲裁员;仅因仲裁员身处临时仲裁而非机构仲裁中就否定仲裁员的公信力,笔者不敢苟同。问题的关键在于应当健全中国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并使临时仲裁员的法律责任与机构仲裁员的法律责任等同,如此,由临时仲裁所产生的国有资产流失的概率至少不会比司法判决及机构仲裁裁决高。
其次,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设立了处理涉外经济贸易的专门仲裁机构“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后几经更名,成为现在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委”)。虽然国内仲裁起步较晚,但《仲裁法》颁布至今,中国仲裁事业经历了二十几年的快速发展,在全国许多地方建立起了专业的仲裁委员会,培养了为数众多的专业仲裁员,这些仲裁员主要是各领域内的专家学者、资深律师。以下借助几组数据进一步阐明。2015年中国244家仲裁委员会共受理案件136924件,其中涉外案件共计2085件。这两项数据均位居世界前列。2014年中国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撤销的有203件,仅占全国仲裁案件总数的0.18%;被裁定不予执行的有106件,仅占全国仲裁案件总数的0.09%。2015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受案总量为1968件,是1995年受案总量的2.18倍(1995年受案量为902件),其中涉外案件受案437件。从1995年起,贸仲委的受案量曾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并被誉为最繁忙的国际仲裁机构之一。从这几项数据可以很直观地看到,面对如今诉讼爆炸的年代,中国已培养了为数众多且具有较高水准的专业仲裁员来处理数量繁多的仲裁案件。如果仲裁员的素质得不到当事人的认可,仲裁裁决得不到当事人的信赖的话,恐将出现大量被法院裁定撤销或不予执行的仲裁裁决。
再次,不用担心当事人会对临时仲裁的公正性缺乏信心。对于提起仲裁的当事人来说,他们是最关心裁决结果的,因为裁决结果将直接影响他们自身的利益。因此,当事人会尽可能地选择其信任的仲裁员,并尽可能地制定较为公正的仲裁程序进行仲裁。相比机构仲裁所提供的已经固化了的规则而言,在临时仲裁中,当事人对程序规则的制定则更有针对性、灵活性和自主性,也更符合当事人的意愿。对于仲裁审理过程及仲裁裁决的公正性问题,当事人双方势必会采取必要的监督措施,一旦有不公正的情形发生,则当事人必然会寻求法律救济途径。因此,当事人选择了临时仲裁,意味着他们对临时仲裁是信任的,自然谈不上对临时仲裁缺乏信心的问题。
最后,对于反对者担心的当事人如不能在临时仲裁中充分合作,则可能阻碍或拖延仲裁的问题,笔者认为可借鉴其他国家在此方面的有益经验。如针对当事人双方不能合意选择仲裁员这一问题,根据通行做法,可将仲裁员的选任权交由法院,由法院选任适格仲裁员进行仲裁。
四、中国引入临时仲裁的制度构建
在中国设立临时仲裁制度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将临时仲裁制度纳入中国目前的法律框架中,那么,对《仲裁法》中相关条款的修改势在必行。此外,建立全国仲裁协议,提高仲裁员适用临时仲裁的能力和水平也是至关重要的。
1.修改《仲裁法》相关条款
首先,在法律上为临时仲裁制度提供容身之处。根据中国《仲裁法》第16条第2款的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和选定的仲裁委员会。一旦中国决定建立临时仲裁制度,就应当将“仲裁委员会”的规定删除。
其次,需要在法律上为临时仲裁提供支持机制,这包括以下几方面:(1)《仲裁法》第20条关于仲裁协议效力的确定规则的规定,笔者认为应当完全删除。由于临时仲裁可能与仲裁委员会无任何关联,笔者建议,对于仲裁协议效力的确定规则可以采用世界上许多国家所实行的“自裁管辖权原则”,即将仲裁协议效力的确定权力交给仲裁庭。(2)笔者认为有必要增加规定仲裁庭组成时限的条款。这样的规定有利于防止一方当事人不配合,致使仲裁庭的组成久拖不决,双方争议无法进入仲裁,甚至形成僵局。因此,对仲裁庭组成时限的规定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这一时限也不宜过长。一旦仲裁庭成功组成之后,临时仲裁就可以与机构仲裁一样按程序进行,而不受当事人拒绝参与仲裁的影响。(3)建议制定司法任命仲裁员规则,这也有利于避免临时仲裁的过分延迟而影响其效率。这里可以借鉴《美国统一仲裁法》的规定,即仲裁协议有约定时从其约定,没有约定或有约定但无法执行时,法院根据一方的申请选任仲裁员。(4)需要在法律上为临时仲裁提供与机构仲裁一样的保护机制。例如,临时仲裁庭决定采取临时措施,那么这一措施应当与机构仲裁中的临时措施一样得到来自法院的有效支持。而且,法院应与对待机构仲裁一样的态度对待临时仲裁,而不应对机构仲裁有所偏袒。
再次,在仲裁员法律责任方面,中国《仲裁法》第38条虽规定仲裁员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形,但笔者认为该规定并未包含仲裁员的民事责任。基于世界上多数国家对仲裁员有限民事责任的设定,也为了给中国目前实践中已经出现的纠纷提供司法判决的依据,建议增加“仲裁员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应当对此承担民事责任”的条款。至于承担民事责任的形式,应当包括但不限于排除妨碍、返还财产、重新履行职务、赔偿损失。而承担民事责任的范围方面,有学者以仲裁员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为契约关系出发,认为仲裁员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的范畴应以仲裁员所收取的酬金为限。笔者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观点。仲裁员与当事人之间确为契约关系,而仲裁员所承担的前述民事责任是仲裁员违反其与当事人之间的契约所产生的违约责任,根据中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违约责任的承担范围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而非仅以违约方因合同所获利益为限。此外,如果仲裁员的民事责任范畴仅以其所收取的酬金为限,则因违法成本过低,反而使此民事责任的规定无法起到预防和警示的作用。因此,笔者建议,仲裁员承担民事责任的范围应相当于当事人所受损失为宜。
2006年6月29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规定了仲裁员枉法裁判的刑事责任。尽管在世界范围内,确实有极个别国家的成文法规定了仲裁员枉法裁决的罪名,如根据《德国刑法典》第339条规定:“法官、公务员或仲裁员在领导或裁判案件时,为有利于一方当事人或不利于一方当事人而枉法的,处1年以上5年以下自由刑。”但是“枉法裁决”或“枉法仲裁”的罪名有可能导致司法部门对仲裁的非法干预,使对仲裁裁决仅限于形式审查的规定流于表面,笔者建议应予以废除。但对于仲裁员在仲裁过程中收受贿赂、欺诈、毁灭证据等行为确有必要规定刑事责任,这既有国际的先例,也是符合中国的实践需要的。
最后,不能忽略的是,《仲裁法》中的相关规定均是在中国仅有机构仲裁这一认定基础上制定的。例如,对于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法院管辖权取决于仲裁委员会所在地而非仲裁庭所在地;可仲裁性问题由仲裁委员会判定而非仲裁庭判定;仲裁裁决上必须附盖仲裁委员会的印章;等等。因此,将临时仲裁制度引入中国仲裁法体系需要对《仲裁法》进行全面、系统的修改。除此之外,还需要考虑其他相关法律,如《民事诉讼法》(这些法律均以中国仅有机构仲裁这一前提而制定)的修改。
2.建立全国仲裁协会,提高仲裁员适用临时仲裁的水平
临时仲裁制度的好与坏,临时仲裁裁决是否得到当事人的拥戴并由当事人自愿履行,与仲裁员的职业素质和专业的法律、行业素养等密切相关。诚然,临时仲裁制度如果引入中国,将对仲裁员的专业水平、灵活运用程序规则的能力及外语能力等提出更高的要求,但笔者认为,这样的挑战不能成为暂缓或阻止临时仲裁制度引入中国的理由,反而能够成为提高仲裁员素质、使其更好地适用临时仲裁的契机。对此,笔者建议,应尽快建立全国仲裁协会,通过仲裁协会的统筹协调,全面提高仲裁员水平,并推动中国仲裁业发展。
《仲裁法》第15条虽规定了仲裁协会的相关事项,且早在1994年国务院办公厅就下发了《关于做好重新组建仲裁机构和筹建中国仲裁协会筹备工作的通知》,要求筹建中国仲裁协会,但时至今日,中国仲裁协会仍未建立。笔者认为,仲裁协会尚未建立,与中国的仲裁机构具有浓厚的行政化色彩不无关系。欲使中国仲裁行业还原其民间性,寻求独立于行政管理的有效途径,仲裁协会及时建立势在必行,这样也有利于临时仲裁制度的设立,更是确保其可信赖的有效保障。仲裁协会的功能除了法定的组织制定仲裁协会章程,监督仲裁委员会及其组成人员、仲裁员,以及依照相关规定制定仲裁规则以外,还应包含服务职责。对此,笔者建议借鉴美国仲裁协会的做法。美国仲裁协会内部设有一个专门负责教育和培训的部门,定期对仲裁员进行相关仲裁知识和仲裁技巧的培训并召开研讨会,使这些既有法律专业知识同时又具备仲裁专业技能的仲裁员能够充分发挥在解决争议案件方面的作用。笔者建议,通过仲裁协会定期展开对临时仲裁涉及程序规则、实体法、准据法的专门培训,并邀请国内外具有丰富的临时仲裁经验的仲裁员进行经验交流,这将使中国仲裁员不断积累临时仲裁经验,逐渐深化对临时仲裁的认识,有利于将来临时仲裁制度在中国设立之后更好地运用该制度。此外,仲裁协会可对临时仲裁员实施有效的监督,由此亦可有效地提升仲裁质量,促使中国的临时仲裁制度逐步走向规范化,避免临时仲裁制度设立初期可能产生的个别无序行为,进而提高临时仲裁的可信任度。这也可以排除学界对临时仲裁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是否能妥善适用法律和当事人的合意并做出公正裁决的担忧。
五、结语
《仲裁法》要求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必须指定仲裁委员会,这一规定使得临时仲裁协议在中国是无效的。在实践中,为了促使临时仲裁裁决获得中国法院的支持,当事人不得不将临时仲裁案件提交境外仲裁。中国不引入临时仲裁制度与中国仲裁的历史发展紧密相关,且与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不无关系,特别是当时中国正经历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但时至今日,阻碍临时仲裁在中国设立的原因已经消除。当中国越来越紧密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时,中国的经济也与世界经济形成日益紧密的联系。一国的仲裁体制优劣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笔者认为,《仲裁法》这一不合理的规定势必将阻碍未来中国仲裁业及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对该规定的修改及引入临时仲裁制度势在必行。当然,在中国设立临时仲裁制度,不仅需要对这一要件要求进行修改,可能还涉及对《仲裁法》其他条款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甚至重塑。笔者衷心地希望临时仲裁制度能够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和接受,期许临时仲裁制度最终在中国获得其合法地位。
注释:
①Christian Buhring-Uhle, Lars Kirchhoff & Gabriele Scherer: Arbitraiton and Mediation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27(2nd ed. 2006); Gerald Aksen: Arbitration and Other Means of Dispute Settlement, in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②Kofi Annan: Sec’y Gen. of the U.N., Opening Address Commemorating the Successful Conclusion of the 1958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n Enforcing Arbitration Awards under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③谭兵主编:《中国仲裁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④张贤达:《国际商事仲裁协议制度为“一带一路”护航》,《人民论坛》2016年第31期。
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律释义》,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⑥张秉银:《苏黎世商会仲裁院》,陈志春:《瑞典仲裁制度简介》,国务院法制局研究室编:《重新组建仲裁机构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180页。
⑦李双元、谢石松:《国际民事诉讼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00页。
⑧Thomas Oehmke, Comercial Arbitration 127, 127 (Martin Domke ed., 1958).
⑨郑成林:《近代中国商事仲裁制度演变的历史轨迹》,《中州学刊》2002年第6期。
⑩《商会简明章程》,《东方杂志》第1年第1期。
(责任编辑:知 鱼)
Research on Establishment of Ad Hoc Arbitration in China
ZHANG Xianda
(School of Law, Da 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Da Lian 116000, China)
The practice that ad hoc arbitration is excluded from Chinese Arbitration Law is not only inconsistent with the world practice, but will also create some unfair and unequal issues. After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social, economical and other background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factors hindering the introduction of ad hoc arbitration system into China have been eliminated. The paper also tries to release the theoretical shackles of ad hoc arbitration in China. When it come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d hoc arbitration in China, the paper suggests not only modifying the provision of valid requirements of arbitration agreement in Arbitration Law, but also providing relevant supporting mechanisms, establishing the national arbitration association, and improving arbitrators’ ability to use ad hoc arbitration.
arbitration system, ad hoc arbitration, establishment of system
2017-03-16
张贤达,福建泉州人,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主要从事国际经济法学研究。
DF974
A
1004-8634(2017)03-0057-(08)
10.13852/J.CNKI.JSHNU.2017.03.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