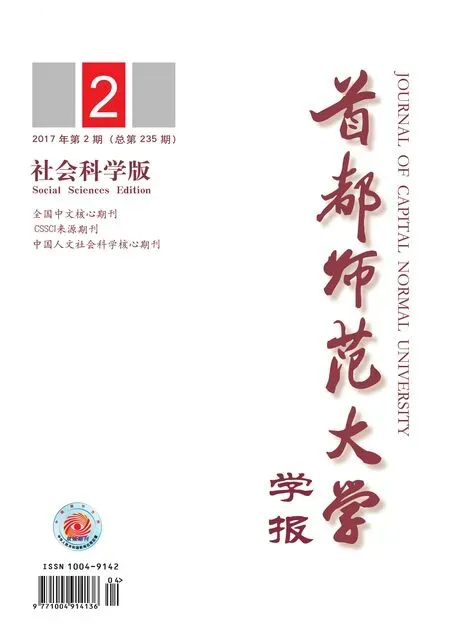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纯文学”问题
张 均
一
在“后革命”语境下,重新回顾新世纪以来的“纯文学”论争并清理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是目前学界切实而必要的工作。“纯文学”论争起于李陀2001年刊出的访谈录《漫谈“纯文学”》。在该文中,李陀对改革开放以来居于“主流”位置的“纯文学”概念深表不满,认为“由于对‘纯文学’的坚持,作家和批评家们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写作”,“使得文学很难适应今天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不能建立文学和社会的新的关系”,不能“以文学独有的方式对正在进行的巨大社会变革进行干预”。[注]李陀、李静:《漫谈“纯文学”》,《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参与者,李陀这种“从旧垒中来”的对“纯文学”的“反戈一击”,引发了持续的学术论争。虽然论争各方最终并未取得明显“共识”,但李陀等的批评在学理上还是更见合理性。
原因之一,是“纯文学”概念不符合文学生产的事实。1.仅在“写”这一层面,倘若作家尊重生活事实的话,那么他(她)势必难以提取“纯”的生活经验,因为所谓“纯文学”之“纯”,是就独立于国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公共领域之外的纯粹、自足的私人美学空间而言的。但如此之“纯”在现实经验中又怎能觅得?因为但凡人的生老病死、穷愁伸屈,又有哪样经验不是个体与其置身的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恰如伊格尔顿所言:“每一个文学文本都在某种意义上内化了它的社会生产关系。”[注]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当然,文学史上的确出现过不少被目为“纯”的文艺,如《受戒》、《竹林的故事》、《边城》等,但它们的“平淡朴讷”,很大程度上是作者有意“榨掉”对象生活中的权力关系、不顾“生活真实”而刻意“提纯”的结果。且这种“榨掉”,仍是作者自己所置身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如《受戒》的产生直接与汪曾祺文革结束以后被审查、反复写检查(如《我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关于我的“解放”和上天安门》等)的精神苦痛有关。2.更重要的是,即便是《受戒》这类以“艺术真实”为特征的“纯文学”,也会在“被出版,被审查,被买卖,被阅读,被评论,被评奖,被选入小学、中学、大学的课本,被进入文学史,被经典化或被排除经典化”[注]李陀:《李陀致吴亮之一》,李陀:《雪崩何处》,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的过程中再度“内化”它所在的“社会生产关系”。
原因之二,是“纯文学”概念在过去和现在研究中的“不纯”与无效。“纯文学”概念最集中的体现是“重写文学史”实践,“(它)原则上是以审美标准来重新评价过去的名家名作以及各种文学现象”[注]陈思和:《关于“重写文学史”》,《文学评论家》,1989年第2期。,但事实上诸多研究者已指认它在“审美”之外与政治共谋的双重意识形态特征。一方面,“重写文学史”被认为承载了某种知识分子政治,“代表了知识分子的权利要求,这种要求包括:文学(实指精神)的独立地位、自由的思想和言说、个人存在及选择的多样性、对极左政治或者同一性的拒绝和反抗、要求公共领域的扩大和开放,等等”[注]蔡翔:《何谓文学本身》,《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另一方面,它针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去政治化/去革命化”的反抗策略,还被认为“恰恰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着呼应关系”[注]张慧瑜:《“纯文学”反思与“政治的回归”》,《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2期。。可以说,在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在争取知识阶层利益等方面,“纯文学”都难以以“纯”自立。故洪子诚以为:“‘文学自觉’、‘回到文学自身’的文学‘非政治’潮流,也可以看到它的政治涵义”,“所谓‘纯’文学理论,所谓纯粹以‘文学性’、‘艺术性’作为标准的文学史”,“只是一种学术神话”。[注]洪子诚:《问题与方法》,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1页。而就当前研究而言,“纯文学”研究仍然受困于“新批评”的方法缺陷:割裂“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使文本成为封闭、孤立之物,既不能在宽阔的文化生产关系中理解文本构成,又不能在急剧的历史变动中阐释其意义生产。因此缘故,近年研究中出现了补救性的“历史化”倡导,“如果说,1980年代,是文学‘向内转’和‘把文学史还给文学’的话,那么1990年代,则是把文学重新历史化,把文本重新打开,将文学和社会、政治、历史实践以及其他话语重新联系起来”[注]旷新年:《文学史视阀的转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鉴于以上两层因素,学界似可与“纯文学”概念释然作别了。倘这样想,就不免是对“纯文学”背后的现实“土壤”和文化纵深缺乏“同情之了解”。实际上,尽管批评者占据学理优势,但“纯文学”守护者却绝无接受批评之意。相反,他们(如郜元宝)还反批评李陀等将“纯文学”理想“完全归为政治的权力运作”,是“故意”要把“本来浅近的道理”“变得异常暖昧”,结果就只能是“将渴望飞翔的精神的翅膀折断,大家一起滚入物质的污泥里去”。[注]郜元宝:《<中国的“文学第三世界”>一文之歧见》,《文艺争鸣》,2005年第5期。至于众多为《竹林的故事》、《受戒》所折服的读者,就更将“纯文学”视同于“好的文学”。
二
这意味着,当代文学研究若希望真正做到对“纯文学”概念有所扬弃,仅仅指出它与现实政治的吊诡式合谋是不够的(那样不定会落得“没有想好就说了一大通”、“许多人没有听清楚,跟着闹了一大通”[注]郜元宝:《<中国的“文学第三世界”>一文之歧见》,《文艺争鸣》,2005年第5期。的嘲讽),而有必要对“纯文学”的生产接受机制作进一步的剖析。对此,可从四个层面略而言之。
1.写作动力。吴亮以为“纯文学”是“不合作者”的“孤愤”之为:“你(李陀)指出文学应当有批判性,但文学有没有不批判的权利?当文学批判和文学干预的解释权掌握在一部分人手里,而这种解释并不为另一部分人认同的时候,另一部分人有没有权利从事另外类型的写作?”[注]吴亮:《吴亮致李陀:我对文学不抱幻想》,李陀:《雪崩何处》,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这是一针见血的判断,也点明了当代“纯文学”与古代文人传统的关系。实则“纯”是古文人作品的明显特征(小品、水墨乃至抒情诗),其动因往往在于政治“不合作”或“常恐罹谤遇祸”的内心忧伤(还可能上升为“人生无几何,如寄天地间”的“古的忧愁”),即便俗庸之辈也习于摹仿这种忧伤、“忧愁”。吴亮的“我把私人化写作看成反抗的无意识”[注]吴亮:《吴亮致李陀》,李陀:《雪崩何处》,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46页。的声明,是今人在叙述动力层面对古传统的征用,又因此有了“来自历史深处”的道德自信。2.讲述策略。古代“不合作者”和陷没于时间流逝的“古的忧愁”的文人,执笔之时多取自我放弃者姿态,他们对追求公义不抱信心,对“疗救”社会更无兴致。故其文字总是有意绕开“社会压迫和不正义”,视现实权力结构和不平等关系若无睹,以一句“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即将笔端跳向个人生命中那些逝去的往事断片,甚或饮食、器物、衣饰、民俗风物等物质主义细节之上(宇文所安据此将中国古典诗歌定位为“追忆的诗学”)。如此选择“可以叙述之事”的策略,在周作人、汪曾祺等“纯文学”作者那里极为分明。3.组织机制。往事断片既被遴选出来,那么又会通过怎样的机制将之组织为艺术的整体呢?古文人最擅用者是时间空间化机制,即将个体所承载的时间之痛转换为不同生命“断片”的空间化并置,并将意境视为“断片的美学”的艺术追求。对此,单世联指出:“生命如急管繁弦,越是美好的越是短促无凭,文字不能把握时间,但它可以呈现出与时光联系在一起的形象、画面、场景、意境,唤起与过去同样的感受与情绪。”[注]单世联:《记忆的力量——<红楼梦>意义述论》,《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4辑。无论是《受戒》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还是《桥》“很像一个梦境”,其实都呼应了古人的时间空间化机制。4.叙事效果。如果说真善美的完美统一是叙事最佳效果的话,那么“纯文学”的优缺点就甚为明显。其优点在于空间化意境所呈现的深永之美以及超越个体生命的无限意味,“本是一片段,艺术予以完整的形相,它便成为一种独立自足的小天地,超出空间性而同时在无数心领神会者的心中显现形相”,“诗的境界在刹那中见终古,在微尘中显大千,在有限中寓无限”。[注]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6页。但其缺点也至为明显,即他们对现实权力关系的回避无法经受“真实”的拷问。在中国这种被权力和财富高度主导、各类社会控制和压迫司空见惯的社会里,要做到“能够不理会的,我们一概不理会”(张爱玲:《烬余录》),无疑需要强大的“遗忘”能力。而叙事一旦不“真实”,那么其文字中善的吁求就可能被读者目为虚伪。
以上四层,约略是“纯文学”在生产方面的特点。这导致了“纯文学”的接受分歧现象。一方面,由于对现实权力关系“一概不理会”,“纯文学”的正义成分毋宁颇为稀薄。这使它在革命年代一直遭到边缘化处置,在“后革命”年代也受到不能忘怀于正义的知识分子的怀疑。曹征路在《那儿》中亦讽刺“纯文学”称:“现在说的苦难都是没有历史内容的苦难,是抽象的人类苦难,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那还搞什么纯文学。”另一方面,主观上对现实不义的“不理会”和客观上“使现存的事物秩序合法化”[注]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尤其“诗的境界”的营构,仍使“纯文学”拥有数量广大的读者。有休闲需要的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化了的知识群体,是其忠实读众。甚至汲汲于权势争斗的利益阶层,也乐于以“尘嚣缰锁”之外的文字来“平衡”自己的现实。后一种“原来势倾朝野的权臣同时就是逍遥幽栖的典范”[注]王毅:《中国士大夫隐逸文化的兴衰》,《文艺研究》,1989年第3期。的接受悖反现象的复活,恐怕也是当前“纯文学”守护者未曾料及的。
三
“纯文学”生产接受机制略如上述,当代文学研究若欲赢得方法论意义上的调整,首先须重识“纯文学”与“介入文学”(借用萨特概念对李陀等所推重的文学的命名)的关系。“介入文学”确实“在中国有自己的知识分子传统,特别是自‘五四’以来,多少代人都是在反抗压迫中站起,又在反抗压迫中倒下”[注]李陀:《也说压迫、反抗和批判:再答吴亮》,李陀:《雪崩何处》,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44页。,但“纯文学”更是中国“自己的知识分子传统”。虽然它弱于“生活真实”,但有关“诗的境界”的营构经验和接受基础必使之永与“介入文学”并存而互争短长。甚至,由于“纯文学”不挑战现实权力秩序的隐蔽特征利好于中产及其以上阶级、“介入文学”却往往需要作者成为“绅士阶级的贰臣”,未来“纯文学”势必数量占优而“介入文学”将日益成为不能忘怀于正义的“少数者”的事业。然而,真正具有伟大品质的文学注定只能从孤独的“少数”中产生。当代文学研究对此宜有清醒的认识。在此意义上,以“介入”为前提、参酌“纯文学”论争中各方合理意见、调整相关文学观及研究方法,就成为当前学界的必要之举。
第一,重新界定当下中国的“介入文学”。1.“介入”的准确含义。不少学者在论争中将“介入”主要理解为写重大题材,如打工、下岗、拆迁等。对此郜元宝颇为不满,并直接将文学定位在“上访材料、投诉电话、‘人大’提案、‘纪录片’、‘三农研究’、‘国企改革对策’、‘环保倡议’之外”[注]郜元宝:《〈中国的“文学第三世界”〉一文之歧见》,《文艺争鸣》,2005年第5期。。这是负气之辞。其实上访、国企改革等事件若真的构成了个体灵魂的重塑力量,又何尝不可以写呢?但“介入”本义不应是指参与重要社会事件,而更应是强调直接“面对”普通人的未经高度“提纯”(如《竹林的故事》)、未经抽象化(如“私人写作”)的原生态人生。所谓“原生态”必然涉及诸多“与老百姓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事情”[注]李陀、李静:《漫谈“纯文学”》,《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如老百姓所置身的现实社会权力关系、利益关系),但这并不意味文学可以“掠过”普通人的命运而直接将现实社会关系作为叙述对象。2.“介入”的“文学性”。不少学者都将“介入”效果集中在“参与社会改革”之上,这种理解对“介入文学”的发展其实极为不利。客观而言,其叙述效果不应定位在现实的行动效应,而应在于人性共鸣和“人心”重塑,此即“将这一切上升为人类普遍的情感,表达出来,期望超越个体生存的局限,被不同处境中的读者普遍地感到、懂得”[注]郜元宝:《〈中国的“文学第三世界”〉一文之歧见》,《文艺争鸣》,2005年第5期。。而这,意味着“文学性”、“审美性”必成为“介入”的基本前提,恰如马尔库塞所言:“艺术的政治潜能在于艺术本身”,“艺术通过其审美的形式,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中,主要是自律的。在艺术自律的王国中,艺术既抗拒着这些现存的关系,同时又超越它们”[注]马尔库塞:《审美之维———马尔库塞美学论著集》,李小兵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03页。。李陀反复提到的“以文学的方式”,大约亦是此意。
第二,调整当代文学研究的“介入”品质。这指的不是要通过研究“参与社会变革”,而是要引入文学社会学眼光,调整“纯文学”概念经“重写文学史”体制化以后对当代文学研究形成的限制。这种限制主要体现在:1.多用主流/异端、官方/民间等二元对立的观察模式处理文学史问题;2.将“纯文学”作为绝对普遍性的标准并以之“裁决”左翼文学、社会主义文学,从而在将后者“非文学化”、客体化的过程中失掉对其自我逻辑的真正把握;3.由于“纯文学”概念往往用抽象性的观念冲突想象历史,所以研究者就无力面对文学史内外多重“力的关系”,更无从设想“思想和‘再现体系’都是被相互竞争的群体用来争取其利益的话语‘弹药库’的组成部分”。[注]詹姆斯·卡伦:《媒体与权力》,史安斌、董关鹏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1页。那么,当代文学研究怎样突破限制呢?从目前研究看,“再解读”所开启的文化研究方法是有效的调整,它强调深入文本生产的现场,“不再把这些文本视为单纯信奉的‘经典’,而是回到历史深处去揭示他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架构,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掩、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注]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重返八十年代”倡导的“历史化”是另一种成功开拓。它提倡多元主义视角,力图通过相互竞争的多重“力的关系”呈现历史的全部复杂性。本文前述有关“纯文学”的动力、策略、机制和效果的分析,在对接形式与内容、文本与语境时其实也含有突破“纯文学”方法局限的尝试。
研究方法及文学观的调整,可以使当代文学研究赢得必要切实的“平常心”。就写作而言,“纯文学”、“介入文学”各有不同的叙事诉求与受众基础,其并存竞争自是长久之事,实在不必彼此目为“异端”甚至以“整顿”对方为快事。但就研究而言,告别“纯文学”方法、将视野从文本和个体灵魂延伸至“历史深处”的“力的关系”或历史的动态变迁之中,则实在是学术走向开阔之境的必经之途。
——以纯文学在近代和八十年代的两次现身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