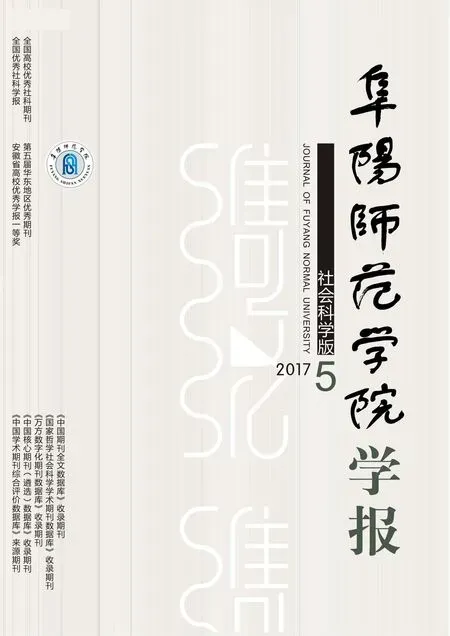皖北非遗文化空间的变迁与保护
谢政伟
皖北非遗文化空间的变迁与保护
谢政伟
(蚌埠学院 文学与教育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皖北非遗文化空间在城镇化进程中面临许多变迁,加强非遗文化空间保护显得极为重要迫切。要提升皖北非遗文化空间保护意识,维护其原生态;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推进整体性保护;重构非遗文化空间,使非遗在坚守中有效调适;“文化+”与经济社会融合创新,彰显非遗文化空间活力,从而有效实现非遗的活态传承与整体性保护,切实推进皖北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
皖北;非遗保护;文化空间;变迁;保护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国务院下发的《国家级非遗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国办发〔2005〕18号)第三条也明确:非遗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等;二是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可见文化空间作为“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同样是非遗保护的主要内容。2014年我国第九个文化遗产日主题为“非遗保护与城镇化同行”,展望我国城镇化进程中非遗保护面临的新问题及发展出路。
一、皖北非遗文化空间之变迁
作为皖北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伴随着皖北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非遗也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生存考验,尤其是其依存的文化空间日渐变迁甚至消亡,正在深刻地影响甚至改变着皖北非遗的保护、传承及发展。皖北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也使非遗文化空间保护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生产生活方式变迁
随着城镇化的大力推进,皖北乡村的生产生活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现代化程度逐渐提高,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发生相应的转变。大量农民从农村到城市、从乡村到社区定居或就业,老人与儿童成为一些乡村的主要留守人群。在农耕社会中,一些民众拥有一手民间绝活赖以养家糊口,如今已不再是重要的依靠。人口的流动使原来热闹一方的庙会、祭祀、节庆等民俗活动逐渐冷清,不再是精神生活之必要依赖。乡村基础设施严重缺失或毁坏,一些传统建筑、古村、古镇相继损毁甚至消失,相关历史遗址遗迹不同程度地毁坏,文化活动场所日渐孤寂,不少非遗项目失去安身立命之所。有的选择移植到城市社区延续其生命,有的则仍然坚守在乡村甚至原地存续、传承。在乡村孕育、发展起来的非遗与所依附的文化空间随时面临消失的境地,或被强行割裂而失去其原生态特质。
(二)思想观念发生变革
皖北城镇化的推进也深刻地影响着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过去赖以维系的深厚的乡土文化面对现代社会思潮的渗透、冲击也逐渐被稀释甚至模糊,信仰崇拜、祭祀先神等民间活动相继减少,原本坚守的非遗及其依存的文化空间变得不再重要。例如作为祭祀先祖、传承家风、团结族群的重要载体,祠堂在传统社会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蕴含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内涵,而如今皖北祠堂绝大多数已被损毁,祠堂文化已荡然无存。物质空间消失,文化空间也无所可依。一些旧时盛极一时、热闹一方的庙会活动无论是内容、规模还是影响力都已大不如前。不少民俗活动由过去的整体意识转变为局部意识甚至个体行为,有的甚至成为极少数人的孤独坚守。皖北民众的文化需求与消费结构也在悄然改变,近年来掀起的非遗文化热更多的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保护传承工作不够深入、全面,对非遗所依存的文化空间保护观念不到位甚至缺失。
(三)非遗文化在坚守与变革中抉择
皖北非遗与物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等资源本身存在着文化差异与发展的不平衡。多元文化交汇下非遗文化在坚守与变革中面临抉择,其文化空间存续有喜有忧。有的积极融合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的文化经济形态,不少非遗项目试图在城市寻求新的发展空间,非遗文化与现代多元文化的汇聚、非遗与经济社会诸多领域之间的融合创新为非遗注入新鲜血液。而有的则在经济大潮下面临文化基因被消解甚至消失的境地。民间大规模的祭祀活动趋于简单甚至消失。一些抛弃非遗文化特质的所谓“创新”,文化归属感不强,商业气息过浓,最终难逃赢利的目的,失去自我。一些庙会的原始功能逐渐丧失,经济功能过度放大,一些民俗更多地是表演的、商业的痕迹,缺少应有的原生态的味道,一些场所的娱乐功能过度放大、文化功能无限弱化,自然空间的再造、民俗活动的表面繁荣摆脱不了文化“贫血”的尴尬。
二、皖北非遗文化空间保护
农耕社会条件下产生并不断形成的皖北非遗保护、传承与发展在社会变迁之下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对非遗所依存的文化空间加强保护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结合皖北非遗所依存的时间、空间条件及相关特点,保护与重构其“自然场”“文化场”[1]82,培育适合非遗的文化土壤,延续其特有的文化基因,通过非遗文化空间保护能有效实现非遗的活态传承与整体性保护。
(一)提升非遗文化空间保护意识,维护文化空间原生态
广大乡村是非遗衍生、流传扩布的主阵地。皖北非遗在传统村落中自然衍生、流变,历经岁月沧桑、久经风雨洗礼,具有深厚的历史沉淀与文化底蕴,是当地民众的乡土情怀与精神寄托。“集体性体现了民俗文化的整体意识,也决定了民俗的价值取向,这是民俗文化的生命力所在。”[2]13非遗文化空间保护要上升为一种集体意识与行为,要增强对本地区非遗的文化认同、激发文化记忆,增强难以割舍的文化情怀。非遗因人而生、依人而传,非遗保护传承关键在于人,传承人是非遗保护传承的主体,是守护文化空间的主力军。要发挥保护传承人的主人翁意识与集体智慧,享受非遗带来的诸多实惠,增强文化认同感、凝聚力与文化自信,激发他们文化空间保护意识,赋予文化空间以生机与活力。要完善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相关空间的结构、布局,改善乡村文化生态,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的合理需求,使他们自得其乐、乐得其所。要充分尊重非遗保护传承主体的意愿,维护保护传承人基于非遗保护传承需要利用非遗文化空间的权利,从而充分挖掘文化空间的潜能,实现文化空间文化功能的强化。
“文化是日常的。”[3]355文化空间也应该是日常的、自然的、活的空间。“如果没有时间的沉积和人的‘在场’,文化空间只能成为刻板僵化的博物馆、展览馆。”[4]11要贯彻非遗“动态保护,活态传承”原则,就应该使非遗文化空间自然地、真实地、生活化地呈现,还文化空间原生态面貌。一砖一瓦皆风景,一草一木总关情,要为非遗留住“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要树立保护文化空间就是保护文化家园意识,让非遗文化空间更多更好地融入生产生活领域,民众在文化空间中自由地休养生息,使保护非遗及其文化空间成为民众日常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例如祭祀离不开一定的文化空间,阜阳临泉张家祠堂祭祀作为一种典型的家族式祭祀活动,保留其文化环境的连续性与适应性,避免遭受外界人为的制约甚至干预,避免此类民俗活动出现断层与割裂。
(二)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推进整体性保护
“民族文化的真正传习,应该是不离本土文化生境的、由当地民族自我完成的。”[5]102文化空间具有一定的时间、场域等条件限制,要结合皖北城乡一体化进程,充分尊重当地民众生产生活方式,以乡村为主阵地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打造文化特色较为鲜明、不同类型的非遗项目集聚的区域,注重非遗及其依附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相关的资源共生共存、和谐发展。要注重维护非遗依附的原生态环境,保护文化多样性,考虑文化空间特定性、差异性、适应性等特点。同时要保存好与民俗活动相关的舞台、道具、服饰等,加大对古村、古镇、传统建筑的保护与维护,重视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为非遗留住“一砖一瓦”,将原本稍显松散的非遗项目移植到一个相对稳固的物质载体范围内加以展示,为非遗请进来、走出去奠定基础,从而推进文化空间的整体性保护,避免碎片化、表象化。“庙会不是一朝一夕即可形成的,它需要稳定的社会生活,氏族通过庙会上的各种活动增强其凝聚力,而且是一定地区、族群社会认同与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6]21例如农历3月28日举行的涂山禹王庙会集众多的祭祀、歌舞、民俗活动于一体,在周边地区辐射力与影响力都较大,涂山历来保留了许多相关的历史遗迹,也衍生了不少民间传说,以涂山为中心、联动“中国花鼓灯第一村”冯嘴村等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能有效促进非遗及其依托的物质文化遗产及赖以依存的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确保非遗文化在一定区域内自然地、稳定地演进,避免单一化的保护方式,保护花鼓灯等非遗所依存的整体空间形态,形成聚合效应,维护其文化生态系统,避免文化断“根”失“魂”,实现全面性、整体性、生活化地呈现非遗面貌。
“‘人的城镇化’的基础是‘人的社区化’,包括岁时节日、人生礼仪、游艺、信仰、家族等在内的民俗传统,理性成为当代城镇化建设‘社区落地’的重要构建因素。”[7]124非遗要主动融入现代城市生活,现代城市也要为非遗存续适度保留“空间”。基于城市与乡村文化生态之差异,皖北一些城市可以借鉴黄山屯溪老街、南京夫子庙等做法,尝试在城区某一具有历史底蕴、文化特色较为鲜明的区域,整合相关的非遗资源优势,打造民俗文化一条街,营造极具特色的非遗人文氛围,避免过度的商业开发,避免文化功能弱化,从而仿造与复制,随意异地移植与重建,在异地重建过程中不能忽视非遗依存的文化土壤,避免与周围新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出现水土不服。
(三)重构非遗文化空间,使非遗在坚守中有效调适
皖北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非遗文化空间也不可能一成不变,非遗衍生时最初的原生态环境已经逐渐破坏甚至消失,要完全恢复既勉为其难也没有必要。对非遗文化空间进行重构以存续其文化生命力是当前非遗保护面临的重大课题。文化重构是“一种动态化地立足于原来文化特质上的再生产过程”、而非遗文化空间保护也同样是“一个不断调适、重构的过程”[8]54。文化空间重构不是简单的组合归并,也不是简单的移植与复制,而是一种在坚守文化特质的基础上进行自我调适、自我完善,在融合经济社会发展诸多领域的过程中重新选择与组合,以便更好地传承与创新。文化空间重构中要注重凝练特色、凸显主题,避免单一性与同质化。
面对新的文化发展环境,非遗保护传承人也不能无动于衷,要学会调适、有效融入文化发展浪潮。例如积极利用淮河及其支流,结合赛龙舟等传统民俗活动,用好“水”资源,由乡村向城市拓展其文化空间。在保护和提升中加强与城市经济的互动,推动乡村社区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例如余家皮影戏等在城市社区老年群体中、淮河琴书等在公园、市民广场等场所拓展扎根。通过积极推动适合的非遗项目进城,拓展城市社区文化领域,提升其再生与造血功能,以点带面,积少成多,扩大其文化空间范围,辐射其文化影响力,将非遗“火种”保护好、留得住、传下去,为非遗提供更多展示的机会与舞台。避免对非遗文化空间的认知缺失、不到位、不全面等问题,避免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不分场合地表演所谓的“民俗风情”,以致严重伤害特定风俗的庄严感、神圣感和特有群体的情感[9]436。避免文化空间中相关民俗活动出现的过度的产业化、舞台化、表演化甚至低俗化等不利倾向。
(四)“文化+”与经济社会融合创新,彰显非遗文化空间活力
文化环境向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发展也从来不是停止不前的。要确保非遗活态传承,文化空间持久存续,非遗的“守护者、承载者和实践者,在获得自身文化认同的同时,面对现代化的撞击时,适当地进行文化的调适和重新建构,使其自身能够迸发出活力”[8]57。要充分展现文化活力,就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有效融合与创新,体现其“活用价值”[8]15。“文化变迁主要指文化环境诸要素,如文化特质、文化模式、文化风格等的演变。”[10]12非遗在历来的保护传承过程中都是不断地吸纳一些新的文化特质、文化模式、文化风格等。面对开放多元多变的现代社会,皖北非遗文化空间要少一些封闭,多一些融合,少一些固守,多一些创新,将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合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化需求与消费习性相契合,从现代社会生活中汲取丰富营养,增强其再生及造血功能,为文化空间重构营造有利环境。要做好“文化+”大文章,促进非遗文化更加主动地、有效地渗透、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增强非遗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互动,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使非遗在新的经济社会变革中拓展出新的天地,打造新的极具活力的文化空间。“庙会不是一朝一夕即可形成的,它需要稳定的社会生活,氏族通过庙会上的各种活动增强其凝聚力,而且是一定地区、族群社会认同与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6]21例如皖北地区涂山禹王庙会、界首苗湖书会及大黄庙会、五河清明庙会等一些庙会活动传统的祭祀、信仰等功能相继减弱,但群众基础仍然较为深厚,其文化功能、社会功能等在现代和谐社会建设中仍然大有用武之地。作为一种传统的养生之法,五禽戏有机地融合现代养生理念,成为一门健身气功逐渐向全国推广,为现代市民所接受。一些传统民俗活动应该从现代社会生活中汲取营养,展示新的文化活力,发挥其应有的综合效用,彰显非遗文化空间的文化特质与社会价值,借助旅游挖掘文化空间的辐射潜能。非遗不能束之高阁,而要自觉地融入到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在不影响文化空间的前提下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衍生旅游产品等方式使非遗文化空间得以存续。诸如花鼓灯、泗州戏、阜阳剪纸等非遗项目完全可以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重放异彩、获得生机。一些传统工艺融入现代产品制作加工流程,促使传统工艺进一步升华,延续其非遗文化基因。文化空间不能沿袭过去较为封闭、固守自我的做法,展示其文化特质时除了“请进来”,也需要大胆“走出去”,改变过去一味口耳相传的传承方式,积极借鉴“互联网+”等新手段,开拓文化空间播布新途径,强化文化认同感,提升地域文化的自觉与自信。这样通过不同途径拓展非遗的生存空间,文化空间自然能够存续、扩布开来。
总之,皖北非遗及其文化空间是历代社会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在保护众多非遗项目的同时,对其依存的文化空间有效保护也显得尤为重要。通过保护皖北非遗文化空间,促进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更深入全面、扎实有效地推进,从而为皖北非遗持续有效地保护与传承奠定坚实基础。
[1]向驹.论“文化空间”[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3):82.
[2]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3.
[3]周宪.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355.
[4]伍乐平,张晓萍.国内外“文化空间”研究的多维视角[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3):12.
[5]周文中,邓启耀.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J].思想战线,1999(1):102.
[6]高有鹏.庙会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1.
[7]刘爱华.城镇化语境下的“乡愁”安放与民俗文化保护[J].民俗研究,2016(6):124.
[8]中国艺术人类学学学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上册[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54.
[9]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436.
[10]王国胜.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文化变迁探微[J].理论探索,2006(5):12.
The Change and Protection of the Non-heritage Culture Space in Northern Anhui
XIE Zheng-we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Education, Bengbu University, Bengbu 233030, Anhui )
The space of non-heritage culture in Northern Anhui faces many change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and urgent to strengthen the space protection of non-heritage culture. It is important to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protec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space in Northern Anhui, maintain its original ecology, build a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zone, promote holistic protection, and reconstruct the non heritage cultural space, so that the non-heritage can be effectively adjusted in its persistence; “Culture+”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can highlight the vitality of non-heritage culture space, thereby effectively realize the living heritage and integrity of non-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non-heritage in Northern Anhui province.
Northern Anhui; non-heritage protection; cultural space; change; protection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7.05.04
K890
A
1004-4310(2017)05-0019-04
2017-08-12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城镇化冲击下的皖北非遗文化空间保护研究”(SK2016A0586);校级淮河文化研究项目“共生理论视域下的安徽沿淮地区文化旅游区域合作模式研究”(BBXYHHWH2012B03);蚌埠市社科规划项目“‘文化+’与蚌埠文明城市建设对策研究”(BB17C038)。
谢政伟(1975- ),湖南衡阳人,蚌埠学院文学与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民俗文化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