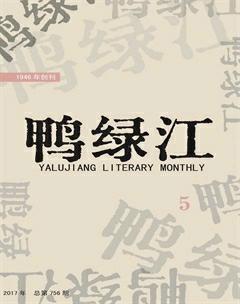遥远的事物
项丽敏
对吻娃娃
书橱里有对小瓷人,名字很别致,叫“对吻娃娃”。
80年代末,对吻娃娃在年轻人中间很受欢迎,尤其受女孩子青睐。
最早看到对吻娃娃是在好朋友萍家。萍是我的旅校同学,和我长得很像,圆脸,大眼睛,学生头。也许是这原因,从第一次见面就对彼此感到亲近,之后像姐妹那样处了好多年。
萍的对吻娃娃是她男友送的。在我们这班同学里,萍是最早就有男友的,初中毕业读暑期美术班时认识,比她大五岁,正在读师范。
萍的男友不仅给她买对吻娃娃,还给她写情书。几乎每周,学校的收发室里都有萍的情书,信封是美工笔写的,很漂亮的字体,邮票也很漂亮,看得出是精心挑选的。
萍总是拉着我一道去收发室取邮件。收发员的目光有些凌厉,在萍的脸上扫来扫去。萍接过信,双颊通红,又分明有着掩饰不住的春风。
我表姐也有一个这样的对吻娃娃。
对吻娃娃就放在她的梳妆台上。梳妆台的镜子上贴着大红的双喜剪纸。那年代,新娘的梳妆台上几乎都有一个对吻娃娃,象征着两人小世界的浓情和甜蜜。
每次到萍家或是表姐家,我都要盯着对吻娃娃看,目光简直移不开。我太喜欢这两个小人儿了,喜欢他们笨拙又可爱的样子,喜欢那略带异域风情又天真无邪的亲吻姿态。
对吻娃娃不只是无生命的瓷器、小摆设,而是我在那个年龄里对美好爱情所有的想象和期望。
我很想有一个这样的对吻娃娃。
没多久我也有了一个对吻娃娃,小小的,放在手心,刚好一握。
对吻娃娃是我自己买的。我已经等不及别人送,先给自己买上了。
我将买来的对吻娃娃放在小纱橱里。小纱橱是父亲给我的,放在我的房间里,专用来摆书。小纱橱是我最早拥有的私人物品,之后不久,我又有了一台收录机,记得是熊猫牌,放在小纱橱顶上。
小纱橱里的书大多是课本,也夹着几本别的书:《星星诗刊》、流行音乐、电影画报、港台文学等等。
对吻娃娃就放在小纱橱的角落,不留意是看不到的。
临近毕业的时候,同学和好朋友之间互送礼物,对吻娃娃成了礼物最热门首选。我收到一个对吻娃娃,比自己买的那个大多了,是萍送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对吻娃娃退出了属于他们的小时代。礼品店里再也看不到他们。蓝白两色的对吻娃娃,朴素又烂漫的对吻娃娃,永远那么小那么稚气的对吻娃娃,直到碎裂才能把他们分开的对吻娃娃,街面上所有的礼品店里再也看不到了。
我不算是一个惜物的人。事实上,对于物,我更多的是舍弃。当我离开一个住处的时候,总会留下一些物品,只带走极少的东西。
我甚至还有一种习惯,每隔半年清理一次房间,丢掉一些,送出去一些:买了之后又不想穿的衣服、多余的用具——将它们送给需要的人。
一些有纪念性的东西,为了避免引起伤感,我也会有意舍弃掉。人在这个世上,不能什么都留着,也不能什么都记着。舍弃和忘记,会让一个人活得轻松些,没有那么多纠缠和牵绊。
我慢慢地成了一个拥有少量东西和少量记忆的人。是的,我连记忆也变少了,不知道这是不是和年龄有关,很多事情,我都不记得,见过一面两面的人,对我来说和陌生人没有区别。
但我买的对吻娃娃还在那里,还在我的房间,没有丢失,也没有被我舍弃。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弄丢他们。我曾擁有过的许多当时很喜欢的东西,后来都一一消失了,从我的视线,从我的记忆。单单他们,那么不起眼又容易碎裂的小瓷人,还完好地在着。
如果按人的年龄来算,我的对吻娃娃也已是将近而立之年的人了。
萍送给我的大一些的对吻娃娃还是被我弄丢了。我完全不记得是怎么丢失的。可以肯定的是,不是有意舍弃。我只舍弃那些会引起痛苦或不适感的物件。
不知道萍的对吻娃娃还在不在。她最终没有能够和读师范的男友走到一起。也是情理之中吧。人在年轻时拥有的美好,很难会终身都拥有。
表姐的对吻娃娃应该还在。表姐是惜物的人,几乎不会乱丢东西。但我后来在她家并没见过对吻娃娃,也可能被她收起来了,收在专门存放旧物件、不轻易打开的柜子里吧。
彼岸花
很小的时候就见过彼岸花,在我出生的村庄里。村庄的河边、路边、山边,到处开着这种花。
那时不知道它的名字叫彼岸花,大人指着它告诉孩子,这叫秃子花,有毒,不能碰,更不能采来戴头上,会变成癞痢头,不长头发。
没有人想变成癞痢头,多难看啊。村里就有个癞痢头,脑门光光,一根头发也没有,还特别凶,动不动就摔凳子骂人。
他是不是误采这花才不长头发的?我很想问这话,又不敢问。
变成瘌痢头的恐惧使我对这花充满警惕,并且厌恶它,觉得它长得丑,细长的秆子,一片叶子也没有,突兀地顶着一朵花,花又那么大,又那么古怪,颜色也红得诡异——带着邪恶之气,一点也不像花儿该有的样子。
但是,奇怪的是,我似乎又总是被它吸引,走过它身边时,总被一个声音诱惑着:采一朵,采一朵,看看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
冒险的念头使我一次次把手伸向它,在快要碰到它时又缩了回来。万一真变成癞瘌头怎么办?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我解除了对这花的恐惧。有一天,竟然看见一个与我差不多大的姑娘,手里握了一大把秃子花,笑嘻嘻地从河对岸走过来,更吓人的是,她浓密又蓬乱的头发里也插了一朵,随着她一颠一颠的脚步不停晃动。
这是一个被村里人称作“孬子”的姑娘,不会说话,嘴角总挂着涎水,脸上也总挂着傻呵呵的笑。
虽是个孬子,智力的障碍却丝毫不影响她身体的发育,甚至使她生得更为壮实,早早脱离了孩子的生涩而趋向成人的圆润。
我等待着秃子花向孬子姑娘实施它的报复——把她变成癞痢头。但是半年过去了,孬子姑娘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头发还是原先的样子,浓密又蓬乱。
原来大人说的那么可怕的事并不是真的,不过是吓唬小孩子罢了。
恐惧解除了,这花对我奇怪的吸引力也消失了。我不再总是想要冒险去采它——它不过和别的花一样,甚至还不如别的花,因为它没有香气。
我仍然还是觉得它不好看。哪怕多年以后,得知它其实有一个诗意的名字叫“彼岸花”之后,得知我少女时最为迷恋的影星山口百惠曾歌唱过它之后,仍旧不能改变童年就对它产生的成见:它是丑的,是禁忌之花。
大约是我在县城读高中的时候,有次回家,听村里人说孬子姑娘怀孕了,生了个死婴。谁也不知道使她怀孕的人是谁,她父亲问她,她就把她父亲领到邻村一户人家屋子里,指着这家的男主人——那是一个还算体面的男人,有妻有子——他妻子还是方圆一带公认的美人。
那男人死活不承认这事和他有关,孬子的父亲也没办法,就把女儿带回去了,这事便不了了之。只是那个孬子姑娘,隔三岔五往屋后山头跑,她生下来还没见着就死去的孩子埋在那里,小小的坟上堆着几块石头。
村里人说,其实那不明来历的婴儿生下来时是活的,哭声很大,很多人都听到了。
孬子姑娘仍旧喜欢采那被村里人忌讳的花儿,去后山的坟地也拿着那花。
一年后,孬子姑娘突然从村里消失了,据说是她父亲给她找了一个婆家,把她嫁走了。她嫁去的地方村里人从没听说过,那地方究竟在哪里,也只有她父亲知道。
菠 萝
他有一个名叫菠萝的女孩。
他照顾她,陪伴她,和她做游戏,带她出门,去公园跑步,去有落日的江边游泳。
他还给菠萝写诗,写信。写温柔又美好的长句子,短句子。写“亲爱的菠萝,又想你了,不知道你现在怎样,有没有忧愁……”
这不免使人疑惑——那个被称为菠萝的,或者是他爱人吧?有美丽的容颜,脆弱,爱使性子,如同小王子照看的那朵玫瑰,独一无二,并且有细小的、让人疼痛,然而又是迷人的刺。
她看他在博客里写菠萝,断断续续,写了三年。后来的一天,他在博客里写道:菠萝死了。并且放上照片。
这时她才知道,原来菠萝不是孩子,也不是他的爱人,而是一只牧羊犬。
她感到难过,因为他很难过。可同时,她又感到一阵窃喜,秘密得到什么的窃喜——仿佛门前树上,那颗悬了很长时间的果子突然熟了,落下了,落在她怀里。
其实她并没得到什么,因为他不知道她的存在,不知道她在读他,读了三年,不知道她心里那么孤独的悲和喜。
真是孤独啊,活着很孤独,爱很孤独,悲伤和欢喜都很孤独。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隔着屏幕,隔着遥不可及的空间,一个孤独地写,一个孤独地读,以此抵挡更深的孤独,有什么不好呢。
故事到这里是否应该结束了?在这里结束算不算故事?男人和女人还没有见面,没有真正认识,算不算故事?
事实上,他们后来还是见面了,认识了。只不过又过去了几年。在这几年里,她也开始写那些长句子,短句子,温暖的,美好的,破碎的,痛疼的。也写信,给喜欢的一切写信,并称之为“写给万物的情书”。
她把写下的那些也放在博客,也有了默默的读者——博客的点击率告诉她,这看似只有她一个人的空间,其实有许多人,有许多人每天来看她,悄无声息地阅读她。
她不知道来读她的人是谁,也不想知道。她只需知道他们是存在的,在听她说话,就可以了。这样,她的书写——或者说她的活着,就不是绝对孤独的事了。
当他们终于见面的时候,他们已是一样的人。她还是喜欢他的,但已不是从前那种喜欢——当她变成了他,一种执着的、入迷般的东西就消失了。
他们像多年老友那样平静地说话,笑。他说了很多,她也说了很多,说他们共同读过的书、认识的人,吃过的食物。当他们的话题转移到动物上时,她忽然说:“我知道你曾有一只牧羊犬,叫菠萝。”
“哦,菠萝,菠萝,那是一只有忧郁症的可怜老狗。”说这话时,她看到他眼睛里泪光一闪。
桃枝与迎春
桃枝是一个月前采的,迎春也是。
桃枝采来时刚冒出芽尖,灰白色的小不点,怕冷似的缩在厚绒衣里。
迎春采来时已开了几朵,刚出壳的小鸭仔才有的嫩黄。
我只采了一枝迎春,在小区入口处的溪边。
采花时,心里有点愧疚,不安,觉得在做坏事。转念一想,我采它们不是拿来糟蹋,赏玩片刻就扔掉,而是拿回屋里插瓶,用净水供养,与之相伴如亲友,也就安然了些。
读书的时候就喜欢插花,学的专业里也有插花艺术的课程,也买过这方面的书来看。毕业后在一家宾馆工作,经常接待会议。特别喜欢布置会场的环节,乐此不疲。一个自认为有手艺的人,遇到可施展的机会,是多么得意的事。
我从宾馆的园圃里采来花草,按自己的审美和灵感搭配它们,剪去多余的枝叶,插在合适的花器里,置放到会场。
那些花草其实都很平常,成片生长,没人觉得有什么特别。可一旦被采回,搭配几片叶子,或者别的花,立马就有了不同寻常的美质,仿佛获得再生。
插花的过程真是享受啊,加班到半夜,还是兴味十足。我从不觉得这是工作,我把它当作一种私人喜好,是与花草们玩的游戏。
有几年特别想开一家花店,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再适合不过的事了,是自己喜欢的,擅长的,又可以养活自己。
可我终究还是没有付诸行动。无论开什么店,都得经营,要会算账,还要与人打交道——一想到这些,心便虚了,像充满气的气球给扎了一针,很快就瘪下去。
如今回想起来,年轻的时候还是有些想法的,想做的事有很多,想当厨师,想当美容师,想当服装设计师。就算当不成设计师,做个裁缝也不错呀。这些行业都是我有兴趣的,无论当时选哪一行,去学习,去践行,说不定后来就真的是个“有手艺”的人了。
当然还有比这些更高的梦想,比如当画家,当歌星……年轻时代就是梦想时代,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不足为怪。
一个人早年喜欢做的事还是会影响后来人生的。比如插花,它就培养了我对于植物的关注,也养成了我后来写作的方式:去自然选取材料,剪除多余部分,给予相宜的搭配,置放合适的容器,让它成为有靈魂的作品。
插花,写作,都不能刻意,也不能一味学习或模仿,而是凭着直觉,凭着个人对生命的认知、审美去做。
无意而为,往往会有意外之美,这也是自然之道吧。
比如迎春,将它采回后,因找不到空瓶可养,顺手放进养桃枝的容器里,竟刚好合了“艳与寂”的腔调(养桃枝和迎春的容器是只玻璃水杯,怕水杯会翻,又把它放进一只桶状的草编篮子)。
桃枝有三枝,每枝上又有几径分枝,点缀着细小的若有若无的苞芽。
采桃枝也是一时的念头。因新居刚装修好,又逢春节,便想采几枝放在屋里,就算不为避邪,也可装点下空荡荡的客厅。
迎春采回两天后,花苞就一朵朵地开了,开成一束明亮的春光。桃枝呢,仍在深度睡眠中,枯寂着,仿佛永不会醒来。
这桃枝能不能养活,会不会开花,我是没把握的,但我每回去新居(还未入住),最先做的事就是给它们换水。
我做我该做的,结果如何,听凭天意。
不知不觉正月过去,转眼惊蛰。
“惊蛰至,桃始华。”再去新居看桃枝,有几朵花苞鼓起,像一个爱娇的女孩嘟噜着嘴唇——果真就要开了。它们是什么时候挣开厚绒衣的包裹,什么时候长成这般模样,我竟全不知晓。
拿起手机,打开摄像功能,对准花苞。就在我点击拍摄的时候,一边的迎春悄然落下几朵。
再过一两天,这桃枝就将是另一番模样了,而彼时,开了一整月的迎春也将落尽。
一种花上场,由寂静转向盛开;另一种花退场,归于盛开之后的寂静,彼此相安,互不争艳,这是神秘的花约,还是自然之道,我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