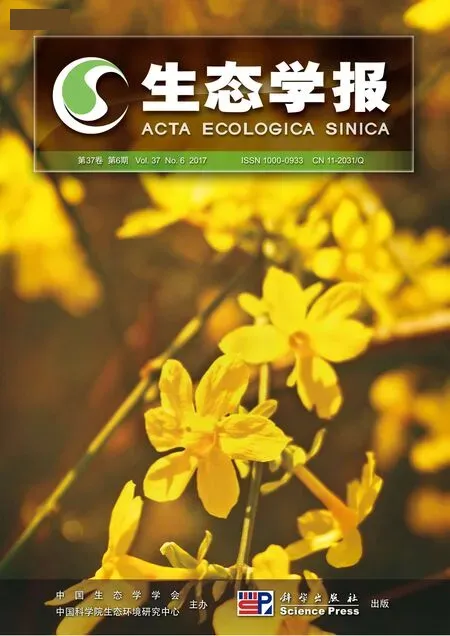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景感生态学思想刍议
张学玲, 闫 荣, 赵 鸣
北京林业大学 园林学院, 北京 100083
学术信息与动态
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景感生态学思想刍议
张学玲, 闫 荣, 赵 鸣*
北京林业大学 园林学院, 北京 100083
“景感生态学”的提出恰符人们和时代所需,其思想主张将人的感知,即视觉、嗅觉、听觉、触觉等物理感知以及心理感受纳入到城市生态环境研究中。中国古典园林是集水、土、气、声、风等元素为一体的综合生态系统,本文援引园林诗词、楹联匾额等古籍资料和实际案例,分别从园景营建、景感运营、生态审美三方面,阐述和探讨自然要素、物理感知、心理反应在园林中的运用,揭示景感生态学思想在我国古典园林中的体现,扩展人们对当下人居环境的建设视野。
中国古典园林;景感生态学;园景营建;景感运营;生态审美;人居环境
面对愈演愈烈的城市环境问题,人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一直是人们广泛关注和探讨的话题。与此同时,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环境品质的提升逐渐增高,这种需求更多的表现在环境质量的改善以及其带给人们精神上的慰藉和享受。由此,“景感生态学”概念的提出恰符人们和时代所需,其本意指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基于生态学的基本原理,从自然要素、物理感知、心理反应、社会经济等方面,研究土地利用规划、建设与管理的科学[1]。其思想主张将人的感知,即视觉、嗅觉、听觉、味觉、触觉以及心理感受等纳入到城市生态环境研究中[1-2]。中国古典园林是集水、土、气、声、风等元素为一体的综合生态系统,“景感生态学”的提出为中国古典园林的研究和赏析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国古典园林是指世界园林发展中以农耕经济为主开始的社会发展阶段的中国园林体系而言,按照园林基址的选择和开发方式的不同,分为人工山水园和天然山水园;按照园林的隶属关系,又可归纳为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三种主流类型以及衙署园林、祠堂园林、书院园林、公共园林等非主流园林[3]。然而,无论何种类型园林都与山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山水”按照中国传统来讲即自然、生态[4]。中国古人对“山水”的感知早已有了较深刻的意识,如魏晋咏左思的“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强调从心中感知山水美妙的自然之声;谢灵运的“乘月听哀狖,浥露馥芳荪”借听觉和嗅觉传达了视觉上月夜笼罩下江面上水气空濛、波光粼粼的景色;南朝谢朓“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借用绮与练颜色的不同传达出余霞的动与澄江的静,等等。园林作为以“夜雨芭蕉”、“晓风杨柳”、“溶溶月色”、“瑟瑟风声”等集色、香、味、触等为一体的生态系统,古代造园家们更是注重透过五官借用自然要素感知景物,营造从“物”到“境”的园林环境,以实现“物情所逗,目寄心期”的造园意图。
1 园景营建
《易·系辞上》有云:“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中国古典园林营建的第一要务是“察于地理”,即相地选址。古人在相地选址中十分强调综合地形、水、植被、日照等多种自然因素的影响。《阳宅十书》认为:“凡住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污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谓最贵地。”背山面水,空气流通,挡住呼啸的北风,青山绿水,鸟语花香,正符合人们理想生活的生态需要。《诗经·大雅·公刘》中记载道,周族酋长公刘率领全族迁居豳地,寻找土地富庶草木繁茂之地,他亲自登临山水,察看地形,“相其阴阳”,“度其隰原”,以确定建筑朝向和基址范围[5]。中国古代造园专著《园冶》[6]相地篇中强调:“园地惟山林最胜。” 山林之地“有高有凹,有曲有深,有峻有悬,有平有坦”,山水资源良好,地质地貌类型丰富,“自成天然之趣”,体现了古代先人早熟的生态环境意识。明代造园家计成指出:“凡结林园,无分村郭,地偏为胜。”说明古人在选址时已注意将噪音对园林环境的影响纳入到选址中,强调好的选址要避开城市繁华喧嚣之地,“竹里通幽”,“松寮隐僻”。基于这种生态意识的出现,就算建在喧闹的城中,没有得天独厚的清幽环境,古人也力图营造闹中取静的生态小环境。如苏州网师园位于极窄的羊肠小巷深处,藉以避大官之舆从也;素有“吴中第一名园”之称的留园,位于苏州阊门外,四周通达之路均为狭窄的石子小路;江南名园艺圃虽临近《红楼梦》中所写“红尘中一二等风流繁华之地”的阊门,但却“隔断城西市话哗,幽栖绝似野人家”;拙政园僻处苏州娄门内东北街,当年也是“门临委巷,不容旋马”,罕有车迹。
山水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极佳的生态环境,山水也是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主体和骨架,几乎无园不山,无园不水。水乃生命之源,赋予园林以灵动和生机。园林中水体不仅是不可或缺的景观形态,更是水生动植物生存的重要载体。白居易在午桥庄园林的改造中强调园林水体的营造要“引水多随势”,因势利导不强行,体现了对自然地形地势的尊重和利用。正如苏州拙政园营建缘由,因苏州地下水位高,拙政园更是处于城中低地,因而园内掘池得水,外连城市水系;池中垒土石筑岛山,山上遍植落叶树间种常绿树,山脚土坡苇丛,植物种类丰富;山间有溪谷,架小桥,形成以水池为中心的小型水陆复合的生态系统(图1)。拙政园中水面和岛屿的建造是根据因地制宜、遵循自然的原则将洼地生态改造成物种更丰富、生物链更为稳定的立体岛式生态环境。从生态角度而言,园内水体营造除了不仅有利于排蓄雨水,为园中灌溉、防火提供水源,同时也起到净化空气和调节小气候的功能。

图1 拙政园西部与中部水陆关系图Fig.1 The land and water relationship of the Humble Administrator′s Garden′s west and middle areas来源:改绘自网络
“水,活物也。”为保持水的“活”性,保持水质的清净,园中水多通过暗沟连接园外天然水渠,如寄畅园的主体水池“锦汇漪”,源自惠山的“天下第二泉”的泉水流入;白居易《池上篇》记载白氏旧园引伊水入宅为池;杭州郭庄引西湖水入园为池;苏州环秀山庄因其在山脚下掘地得“飞雪泉”,与山庄中水景池泉贯通,水有源,山有脉,既符合生态之理又表现出自然的和谐趣味。园林中水池多具备一定的体量,在控制游人规模的情况下,大比例的水面可以通过自净能力而保持水质清洁(表1),同时,池中水生动植物群落,也具备一定的净化水体能力,使园林水域达到生态平衡。具备了一定生态功能的园林环境为各种水陆生物提供了生存条件,形成了“鸟鸣蝉唱”、“鱼戏新荷动”、“稻花香里听蛙声”的和谐景象。

表1 主要园林水域比例一览表
“园林”重点在“林”上,如果没有“林”,那么“园”也就不称其为园了[7]。因此园林植物多有“榆柳两三行,梨桃百余树”、“江梅百株”、“绿树成林,绮蔬盈圃”的群体面状种植。对园林植物的配置和选择通常需要综合考虑地形地势条件、光照、土壤成分等因素,如“插柳沿堤”、“柳浪闻莺”等景名道出了古人经验性的于近水湖滨处植柳成林,不仅尊重了植物喜阴喜湿的生态特性,又考虑到水边土壤稀松潮湿的情况,变不宜因素为有利于黄鹂栖息的生境,得和风拂柳、黄鹂飞鸣之集视、听、触三感一体之景。“多年树木,碍筑檐垣,让一步可以立根,斫数桠不妨封顶[6]。”又传达了古人造园时对古树名木的尊重态度,从现代生态学观点来分析也是尊重生态的需要。经过多年生长繁茂的树木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生态位,对古树的保留实际上也是保存一个运转良好的小生态环境。正是由于古代造园家对配置植物的生态合理性,背阴种竹植桂、向阳栽牡丹种芍药、地高瘠薄之地育松柏配榆枣,才有了“松竹苍翠,花艳兰香”、“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之景。
2 景感运营
明代造园家计成在《园冶·借景》中首先明确提出了借景乃“林园之最要者也。”清代精通造园的学者李渔在其著作《一家言》中也强调了造园中“取景在借”的道理。《园冶·兴造论》中又曰:“‘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计成按照“得景”方式的不同,从观赏距离、角度、时间等方面将借景分为“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应时而借”等方式。可见,“得景”方式的不同,取得的园林景色各有千秋。而得景方式的不同取决于人运用听觉、视觉、嗅觉、触觉等感官感受外部事物的方式不同,促成了“得景”过程中体验方式的差异[8]。
2.1 “视”景
2.1.1 “春夏秋冬”
《论语·阳货》有“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之语。《庄子·知北游》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之论。自古以来,受四时意识影响,中国古典园林尤为重视四季更替对景物的影响,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园林景观是受季节变幻、气候变化影响的。正如《园冶·借景》中强调:“构园无格,借景有因,要切四时。” 中国古典园林或隐或显地借春夏秋冬的变化,显示四时景色之异。如杭州西湖十景的“苏堤春晓”、“断桥残雪”,燕京八景中的“琼岛春阴”、“西山晴雪”,钱塘十景的“浙江秋涛”、“孤山霁雪”,拙政园的“海棠春坞”、“雪香云蔚”,桂林十六景中的“东渡春澜”、“尧山冬雪”、“五岭夏云”、“阳江秋月”等,显现了景色的“四时不同”。园林植物观花观叶各有妙处,如唐杜牧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利用了植物的季相变化,用红枫似花的叶色破除冬日的枯寂。
2.1.2 “昼夜晨夕”
白昼与黑夜,是对立的两极,而晨、夕则是其间的过渡。昼与夜的代表性景象,就是日景和月景[7]。日景常常借用光、云、雾等自然气象造景。如借光之景,峨眉山清音阁下两条溪水汇合,急湍飞瀑在日光下出现虹影,形成“双飞两虹影”的景观。光是影响园林景观的重要元素,明高濂在《苏堤看桃花》中描写了六种不同时间气候变化下的桃花景观:“其一,晓烟初破,霞彩影红,微露轻匀,风姿潇洒;其二,明月浮花,影笼香雾,色态嫣然,夜容芳润;其三,夕阳在山,红影花艳,酣春力倦,妩媚不胜;其四,细雨湿花,粉容细腻,鲜洁华滋,色更烟润;其五,高烧庭燎,把酒看花,瓣影红绡,争妍弄色;其六,花事将阑,残红零落,辞条未脱,半落半留……”从中可看出在霞彩、明月、夕阳、庭火等不同光感和自然环境下,花之容、色、态、影、香的变化。又如苏舜钦《沧浪亭怀贯之》中云:“秋色入林红黯澹,日光穿行翠玲珑。”翠玲珑馆周围广种竹子,种类繁多,因日光照射,诸多竹子清翠欲滴,宛如碧玉,建筑馆也由此得名。于此同法的还有描写六月西湖之景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园林将水生花木大面积集中栽植,不仅增强水体净化能力,同时借阳光与植物的红绿组景,能造成强烈的色彩对比,突出视觉观赏效果。借云之景,如昆明黑龙潭中有“两树梅花一潭水,四时烟雨半山云”之景,山云衬掩,梅潭映照,动静对比,隐然在目。清何绍基描写成都茗椀楼:“花笺茗椀香千载,云影波光活一楼。” 荡漾的云影波光使吟诗楼也有了“活”意。又如杜甫的“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尤侗的“水流云在,月到风来”。不仅如此,西湖十景中又有“双峰插云”,豫章十景中有“南浦飞云”,峨眉十景中的“罗峰晴云”等以云组景,借云造景的园林景观。借岚造景,如潇湘八景的“山市晴岚”,桂林十六景的“北岫紫岚”等。
日月光感不同,景象亦有不同。袁宏道《西湖二》有云:“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水态,别有一种趣味。”“湖以平为美,月以秋最佳。”以月景取胜最为著名的当属西湖十景中的“平湖秋月”,通过秋月之圆满与湖水之平展形成圆与线的对比,构成独特的自然景象,并借西湖西端自然地势条件,于孤山上面水建“望湖亭”,可观“平湖秋月”之景。
2.1.3 “烟霞雨雪”
清汤贻汾《画筌析览·论时景》有云:“春夏秋冬,早暮昼夜,时之不同者也;风雨雪月,烟雾云霞,景之不同者也。景则由时而现,时则因景可知。”气候与天象构成气象景观,如“烟霞雨雪”。“风”、“景”二字,原意即指刮风与日照[7]。可见作为景观的风景和气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园林的至高境界即“纳千顷汪洋,收四时烂漫”之风景,正如清代邓石如所云“沧海日,赤城霞,峨眉雪,巫峡云,洞庭月,彭蠡烟,湘潇雨,武夷峰,庐山瀑布,合宇宙奇观,绘吾斋壁。”因此园林在造景中,离不开日、霞、雪、烟、雨等自然气象景观,通过其中光影、温度、色彩、声音等不断变化,赋予静态的地貌、植物、建筑等无穷的动态景象。
2.2 “听”景
丹麦学者拉斯穆森在《体验建筑》中强调:不同的建筑反射声能向人传达有关形式和材料的不同印象,促使形成不同的体验,事实上,不仅能“听建筑”,还能听“环境”[9]。舒缓美好的声音有“涤烦襟,破孤闷,释躁心,迎静气”的功效。中国古典园林中常常萃取自然之声,因时、因地、因境创造不同的声境景观,构成了园林独特的审美意境。
2.2.1 “水之音”
古代造园家善于理水,不仅善“理”水之形,更善于发现涧、泉、溪、池、瀑、雨等自然水流声音的变化,“理”其音,营建水声韵美的声景观。以涧声造景取境的佳作当数扬州无锡寄畅园的“八音涧”。古代张式引园外泉水至园内假山中,水随涧道曲径迂转,与山体怪石摩擦撞击,产生断断续续、聚散隐显的“金、石、丝、竹、袍、土、革、木”八种声音,正有“声淙淙而琴瑟”之妙,此声境之营建展现了古人善观自然、以声取境的高妙手法。著名的寺观园林峨眉山清音阁第一胜景“双桥清音”,于山区错落交界和黑、白二水汇流处营建清音阁,面向五显岗,背倚牛心岭,郁林簇拥;两侧涧瀑奔泻,喧腾而下,声传幽林深谷,成就了绝景胜迹。同为赏自然流水清音的景观还有避暑山庄的“远近泉声”、“风泉清听”,圆明园的“夹镜鸣琴”,谐趣园的“玉琴峡”等,或溪流潺潺,或泉水叮咚,或涛声澎湃,形成节奏自然生态的声景。雨与植物、建筑的搭配同时也增加了园林水声景观的丰富性,因此有了“留得残荷听雨声”、“蕉叶半黄荷叶碧,两家秋雨一家声”、“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的意境之美。
2.2.2 “风之声”
“风”在中国古典园林造园体系中如空气般如影随形,虽然自身处于无形无相的状态,但是常常与山水、建筑、植物等园林要素搭配,营造出独特的景感景观。如借“风”与墙体孔洞之间气流变化而发出萧萧之声,形成扬州个园“北风呼啸雪光寒”;借“风”入松林而发出瑟瑟之声,形成避暑山庄“万壑松风”之景和“松月生月凉,风泉满清听”之境;借“风”与假山摩擦之声,形成扬州个园“冬山惨淡而如睡”;借“风”拂翠竹似丝竹管弦之声,形成苏州沧浪亭“风过有声留竹韵”的意境。
2.2.3 “禽之鸣”
《诗经·周南·葛覃》描写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东晋谢灵运有“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之句。北宋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中有云:“清风忽来,留而不去;幽禽静鸣,各夸得意,此山林之乐。”可以看出,园林中动物之声让环境充满了生态野趣,传达出一种自然和合之美,人们喜闻乐见这种景象。由此,借“莺歌燕语、蝉唱虫鸣”,古典园林中出现了避暑山庄之“莺啭乔木”,随园的“老鹤立桥上,昂颈长鸣”,恭王府花园的“听莺坪”等景致。“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园林中也常以动写静,以禽语的喧闹反衬环境的清幽寂静,正如王安石描写半山园“惟有北山鸟,经过遗好音”,“风定花犹落,静中见动意;鸟鸣山更幽,动中见静意”。园林里中也常用梵呗钟罄声的乐感来打破山林的寂静,使静中又有动,如潇湘八景中的“烟寺晚钟”、西湖十景“南屏晚钟”等景观。
2.2.4 “琴之乐”
春秋时期俞伯牙和钟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故事千古流传,其美妙乐曲至今仍留在人们心底。其中不仅可以体会到知音难觅之情,更传达了古人很早就发现山水林木等自然之声与人听觉之间的默契关系,因而乐于以琴曲模仿和表现林泉之声,正如唐白居易《池上篇》所云:“虽有宾朋,无琴酒不能娱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于是,园林中通常都会设有琴室、琴亭、琴楼等建筑,如广东可园的绿绮楼、保定莲花池的响琴榭等,作为人们听琴品茗之处,营造“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之境。除此之外,还有如长安曲江园的“柳色箫声拂御楼”,利用箫声营造声境等方法。
2.3 “嗅”景
“嗅”景主要是通过嗅觉感知植物的花、果所散发的芳香为表现手法,从而达到“暗香浮动”、“花香袭人”等艺术境界。唐杜甫有“雨洗涓涓净,风吹细细香”之句,刘眘虚有 “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之诗,南宋陆游有“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之词,可见古人善于借助嗅觉感知事物和环境。自古以来也有利用艾叶、檀香、菖蒲、玫瑰花等芳香植物医治疾病的芳香疗法,以此来改善身心健康。造园家随利用人的嗅觉感知条件,借用园林植物的芳香来造景。如清代袁牧的随园就有“梅花绕屋香成海,修竹排云绿过墙”的景观,梅花绕屋,修竹排云,花香袭来,调动了人们的视、嗅感知,从而加深对环境的观赏与体验。较有代表性的当属狮子林的双香仙馆,夏借荷花之香远益清,冬借梅花之暗香浮动,四时变幻,花香四溢。以“嗅”景取胜的当属拙政园,营造了多处可“嗅”之景,如远香堂、玉兰堂、兰雪堂、香洲、荷风四面亭、雪香云蔚亭等,利用荷花、梅花、玉兰等多种植物散发的自然香气,增加园林艺术效果,加深游人对环境的感知印象。较典型的可为苏州虎丘冷香阁的“梅花香里钟声,潭水光中塔影”,全方位地调动了的视觉、听觉、嗅觉等感官,创造了集钟声、花香、水光、塔影一应俱全的园林景观。
2.4 “触”景
“触”景主要通过手、足、肌肤以及身体等对周围环境感知而营造的意境景观,相比“视”、“听”、“嗅”都来得更真实。在园林景观的感知中,人们可以通过“触觉”感知有形的水体、植被、建筑等园林要素,也可感知无形的光、热、温度、湿度、微风等气候元素,自然而然的融入园林环境中。如钱塘十景中的“冷泉猿啸”,唐白居易为冷泉亭写记中有云:“夏之夜,吾爱其泉渟渟,风泠泠,可以蠲烦析酲,起人幽情。”夜晚清冷的空气拂过皮肤产生“泠风”,这种夏夜泉边独有的风速与流动,蠲除心中烦嚣,随风的流动而舒缓幽情,正有“清气觉来几席,凡尘顿远襟怀”的深远意境。
3 生态审美
3.1 “乐林泉”之美
山水林泉是现代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一种理想目标和追求,然自古以来人们便有着浓厚的山水情结。历代文人雅士身处凡俗,却“读尽儒书鬓皓然,身游城市意林泉”。林泉是其心中向往的精神境界,正如《林泉高致·山水训》有云:“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体现了对山水自然的一种诉求和回归。中国古典园林即为古人出于对自然的向往而创造的一种自然趣味的游憩玩赏的环境,是一种审美享受的对象。因此,园林素有“不出城郭而获山水之怡,身居闹市而得林泉之趣”的艺术境界。园林中的山水多模仿自然山水而建,“有真为假,做假成真”,把自然山林的“真”,做成咫尺山林的“假”,达到于壶中天地领略须弥山水的妙境,正如元代谭惟在《狮子林即景》中所写:“人道我在城市里,我疑身在万山中。”
中国古典园林具有林泉之美,不仅表现在对自然山水的缩移模仿上,也体现在筑园活动中,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对待园林中的山水、建筑、植被、生物等构成要素,使其保存自身生命节律的同时,互存互生,形成一个完整和谐的可持续生态系统,从而达到“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的“快人意,获我心”的审美意境。
3.2 “致虚静”之美
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等级序列主要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级别,可见,居于首位的“士”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以不同的身份和职业面貌出现,是社会上雅文化的领军者[3]。与此同时,士人们经营的园林成为了民间造园活动的主流,遂其将高雅的气质赋予到了园林当中。
道家“致虚极,守静笃”、“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返璞归真”等原始的美学思想,铸就了士人们宁静致远、淡泊自适、潇洒飘逸的心态。如《林泉高致·山水训》有云:“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邱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可见,园林具有自然山水之虚静,“清冷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可涵养淡泊名利、超然物外之心境。从园林的匾额楹联之中又可见“致虚静”的营造意韵,如苏州沧浪亭中的静吟亭匾额“静吟”,寓意“亭林流水地斯趣,室有幽兰人亦清”,虚亭、流水、月夜、兰香,以景物比德,传达了清净幽远的意境。又如“闻妙香室”,取意于杜甫的“灯影照无睡,心清闻妙香。”妙香特指佛寺所用令人脱俗的香料。此室为园主读书处,匾额暗指主人对妙香涤除心中凡念、进入遗世脱俗的空寂境界之向往,兼指环境之清幽虚静。
4 结论与展望
景感生态学思想体现了人们调动眼、耳、鼻、舌、身、意来感知自然、品悟自然,以实现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国外现代学者有提出过“一座教堂不仅应看上去像教堂,而且听上去也应像一座教堂。”可以说,中国古典园林就是如此,而且更善于利用感官感知“清风明月”与“近水远山”,营造集视、听、嗅、触四位于一体的园林环境。本文援引诗词文献、楹联匾额和实际案例,从园景营建、景感运营、生态审美三方面挖掘和阐述中国古典园林中景感生态学思想的体现,对当下人居环境建设和生态可持续发展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
[1] Zhao J Z, Liu X, Dong R C, Shao G F. Landsenses ecology and ecological planning towar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World Ecology, 2015, 23(4): 293-297.
[2] Dong R C, Liu X, Liu M L, Feng Q Y, Su X D, Wu G. Landsenses ecological planning for the Xianghe Segment of China's Grand Can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World Ecology, 2016, 23(4): 298-304.
[3] 周维权. 中国古典园林史(第三版).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10-22.
[4] 王鹏, 赵鸣. 中国古典园林生态思想刍议. 风景园林, 2014(3): 85-89.
[5] 曹林娣. 中国园林文化.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155-157.
[6] 张家骥. 园冶全释.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3:175-179.
[7] 金学智. 风景园林品题美学.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1: 40-53.
[8] 李飞, 王欣, 姜长稷, 朱海雄, 刘文军. “借景”概念再思考——以“风”的得景主题为例. 风景园林, 2016, (6): 16-23.
[9] 林玉莲, 胡正凡. 环境心理学(第二版). 北京: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2006: 1-14.
2016- 12- 12
10.5846/stxb201612122556
*通讯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E-mail: zm0940@ 126.com
张学玲, 闫荣, 赵鸣.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景感生态学思想刍议.生态学报,2017,37(6):2140- 2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