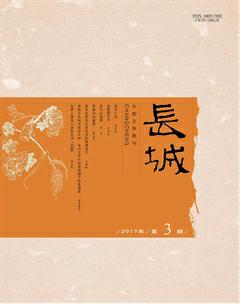世界上惟有小说家无法“空缺”
张学昕
一
格非是谁?小说家兼学者,或者是学者兼小说家。近三十年来,格非一直在叙述和讲授中游弋,在讲坛和文坛之间,难分主次。后来,格非曾被喧嚣的文坛誉为“中国的博尔赫斯”,这个称谓,让格非又被认为是一位最“接近”知识的小说家。因为对博尔赫斯叙述“迷宫”的精致模拟,也陡增了格非小说文本的神秘性色彩。但是,令人费解和疑惑的,可能是他在虚构自己的文本时,时常在经意或不经意间,颠覆他在课堂上向学生谈论、讲授的“小说叙事学”,演绎出颇具行为艺术的现实版“迷舟”。多年以来,我感到,格非似乎始终在叙述的深处徘徊和徜徉,尽管,他略显疲惫的神情,掩饰不住岁月的“青黄”带来的沉重,但是,像充满悬疑意味的《戒指花》,格非的写作,同样让我们猜不到他的未来。
1987年,这位二十三岁就发表了小说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的格非,很快,在1988年,又迅速地写出了具有浓郁抒情风格的小说成名作《迷舟》。不同凡响的是,这个小说所讲述的故事,在叙述的最关键性的“节点”,竟然出现了逻辑性的“空缺”,极其霸道的“中断”,使得阅读发生了令人难以忍耐的迷茫。从叙事学的角度讲,可以说,这简直就是中国小说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革命”和“起义”。一个原本极其写实、老实地讲述故事的小说,人物及其活动,在叙述的关键环节上突然消失了,故事,虽然没有“死亡”,可是,因为这个“空缺”的出现,叙述所本该抵达的目的无法实现,小说完成了一次自我性的虚无。一切,在苍茫云海间变得空空荡荡。
那么,在1980年代末,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篇小说呢?就像《迷舟》这个小说的名字一样,年轻的格非,为什么执意要将我们引入不可思议的“迷舟”?此后,格非的一系列短篇小说的叙述,继续沿着这个惯性不断地向前推进,使得他的“先锋”气质,即使在“先锋群落”里也独具一格,而且,近三十余年经久不衰。骨子里的先锋精神,不断地在大量的中、短篇以及长篇小说文本里悠然重现,精致、优雅的叙述,宿命般地伴随着这位学者型小说家,滋生出舒缓、起伏的汉字的风韵,在经常性的细节的休止符间隙,偶尔就会令人柔肠寸断。我们从格非几十年的小说创作中,深刻体悟到了吴亮那句经典之语“真正的先锋一如既往”。
从写作发生学的角度看,回想那时的历史语境,其实,1980年代的中后期,是最宜于文学的叙述的时代。那也是许多写作者和阅读者感慨系之的“黄金时代”。几十年来的文学“一体化”格局结束了,在一阵思想界对文学自觉的强力介入之后,在不可避免的浮躁和喧嚣消散后,文学开始渐渐以文学应有的发生、生产方式,用心地打量、思考和呈现这个世界,文学重新找到了出路。作家开始在冷静地思考世界的同时,也开始思考究竟要“写什么”和应該“怎么写”的问题。对于任何一位作家而言,作为写作主体,能真正地回到写作本身的审美轨道,都会欣喜若狂。所以,那个阶段的文学,出现了一大批“有意味的文本”,以极端形式主义的呈现方式,开始了一场叙事学的革命。实际上,这场看似文学本体层面的革命,蕴含着更内在的社会、精神和心理价值成因。包括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吕新、北村在内的一大批年轻的写作者,在1980年代中后期“汹涌”而来,虽有复杂的外部现实的影响和“催生”,但是,更为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这些写作者内心的文学诉求和冲动。真正的文学“潮流”和运动,从根本上都不是被“组织的”,而是作家独立、自由开拓出的叙述空间和方式,确切地说,应该是写作者内心的需要。可以说,余华、苏童和格非们,创造了在当时文学接受状况下一个几乎“读不懂的空间”,这无疑是挑战了当时读者的阅读惯性,令人一时无法适应。仔细想想,从“先锋小说”的内部看,格非是这其中在“先锋”性方面走的最远的作家。一开始,他就没有丝毫“迁就”读者的意思,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阅读“滞后”问题,而是叙述者实在是走得太远。《迷舟》《褐色鸟群》《唿哨》和《青黄》,一路云雾弥漫,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从容的叙述中隐匿着悬疑、紧张、冲动、期待,文本所演绎的存在世界,如同充满了感性生命的“如梦的行板”,其不乏清冷、神秘的“零度色调”中,生命和时间的理性,在人物模糊的意识形态里,虚无缥缈,绰约可见。作家通过这样的叙述,究竟想呈示什么,解决什么,其中“蛰伏”着怎样的精神寓意?它试图抵达一个什么样的幽深境地?说到底,格非想让自己的叙述,将自己带到何方?格非小说叙述的“出发地”在哪里?“回返地”又在何处?“先锋”的内在涵义,在当时的特殊语境,在奇崛的文本形态中若隐若现,险云山远,机关算尽,文字中不时地透射出叙事的玄妙和乖张。
现在,回顾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氛围,我们就会慢慢地清楚格非、余华等人的写作初衷,主要是,他们出于对“启蒙”使命的警觉和放弃,而回到生命本体,回到文学本身之魅,以纯粹“复魅”的、富于科学品质的美学立场,专注于对存在、世界、历史的重新勘查。实际上,这是一种“我思故我在”的思考维度和观察维度,在文学叙述的价值取向及其“原则”上,宣告了线性思维逻辑、叙述“因果链”及其存在世界“本质化”的终结,这是对所谓世界“本质性”怀疑的开始,这也就直接导致了文本形态的一次彻底革命,也导致了历史叙述之虚无品性的出现,它是反抗传统叙事规范的开始。这些,在几位“先锋作家”的写作追求中都普遍存在,但是格非较其他各位尤甚。而且,他以自己的文本建立起“先锋”性的合理性,重新建立了叙事的逻辑,发现存在世界及其历史的非理性状态和盲目性的一面,而重新界定文学虚构的哲学边界。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格非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我们理解和判断历史的结构图式,显然,他在努力地寻找历史与现实的隐秘关系。同时,他还借助文本发出了充满理性的追问:历史理性究竟在哪里?由谁掌控?历史如何书写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现实的问题,那么,究竟应该依靠什么理念或者依据来判断历史与存在的真实呢?依据个人经验判断事物、叙述历史,显然是可怕而愚蠢的选择,完全是自以为是的行为。从文学叙事学的角度看,存在世界和历史都具有很大的“审美间性”,为叙述提供了巨大的弹性和张力,但是也树立了一个难度或障碍。似乎,历史的意义和存在的重现,只能由这些似真似幻的故事来决定,而根本上的问题,却在于故事与历史之间造成的“误读”,这才是先锋文学叙述的内在追求。
“先锋写作”,构成一股文学潮流,让我想起余华关于1987年至1988年间他与《收获》之间联系的美好回忆。《收获》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元老级人物巴金创办、主编的文学杂志,数十年始终坚守着独特的人文和艺术的品质。正是这种坚守,才使得1980年代的后期,一大批年轻作家激进的文学探索,能够在当时较为复杂的政治、文化环境下得以呈现出来。1987年和1988年连续推出的几期“先锋文学”专号,宣告和催生了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和写作风格的开始。可以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收获》这样强力的倡导和力挺,就不会有“先锋写作”的创作实绩和经久不息的潮涌。从这个意义上讲,令余华、格非和苏童们所难忘的,不仅是自己写作过程中内心所感受的温暖,主要是写作的价值和意义,能够有可能被精英文化认可的机遇。
我之所以要努力厘清这样一个文学写作的语境,是因为这涉及一种新的叙事原则和形态的出现,以及存在的理由。惟有清楚这一点,我们也才会明白,“先锋写作”作为一股潮流在几年后为什么会终结,而它的“先锋精神”却可以持续几十年不衰。可以肯定,作家的内在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学及其精神的走向。因此,我们现在看,《迷舟》这样一篇小说在当时出现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打破了当代文学叙述的传统时空秩序,更重要的是,它在开启一场叙事学革命的同时,生发出了由叙事多元化所带来的新的历史审美观的变化。相比《迷舟》的写作更早些时候,也就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王蒙等作家有意地模仿西方的乔伊斯和伍尔夫,用“意识流”的写法,表现那个年代“忽如一夜春风来”的精神、心理感受,“旧瓶装新酒”式的艺术手法,对一个精神上正在复苏的民族心理给予了异样的呈现,着实也令人耳目一新。而格非的《迷舟》等一系列短篇小说,进一步突破了这个格局,将小说带进了叙述及其策略决定文本意义的文学时代。
二
从某种意义上讲,真正的写作,其实就是一种宿命。格非小说的叙事形态,来自于自身的宿命和诉求,更来自于文化的宿命和写作的愿景。已故评论家胡河清,对格非及其写作曾有过精到的分析和评价,我认为,这是迄今最为切近格非写作发生学意义的研究。胡河清借用《鬼谷子》和《鬼谷子命书》中关于“腾蛇”的比喻,来影射、揣摩和阐释格非的小说及其意象的生成。“腾蛇”為神蛇,“能兴云雨而游于其中,并能指示祸福。腾蛇所指,祸福立应,诚信不欺。蛇之明祸福者,鬼谋也;蛇之委曲屈伸者,人谋也。”{1}在胡河清看来,喜欢蛇的格非,恰恰就是这样一条观察、写作和叙述的“神蛇”。因为格非的小说里有大量关于蛇的隐喻,其中,“蛇在我的背上咬了一口”,构成了格非小说的基本意念。“格非的蛇会咬人,而且极其狡诈,这说明他感兴趣的是术数文化中的诡秘学成分。也许正因为深藏着这一种关于蛇的意念,格非眼中的世界是诡秘的。”{2}这当然不失为一种独到的解读。“诡秘”“诡谲”“水蛇般缠绕在一起”“因为生病每天都要吃一副蛇胆”,这些神秘的字眼,以及蛇的意象,密布于格非的小说之中,而且,我们在他的诡秘里感受到一种文化的神韵,至少,我们能够强烈地感知到格非努力洞悉世界和存在真相时,那双如同蛇一般的目光,包括这双眼睛对世界的探究欲望和解读策略。于是,胡河清将格非描述为“蛇精格非”。这虽是一种极具隐喻色彩的想象性概括和调侃,但我以为,这非常切近一个作家的本相,作家最渴望的,就是有一双与众不同的眼睛,不为已有的“框架”所束缚,就像所有人观察世界的时候,完全不受自己视网膜的影响,是一种直观,而不是反射。我们也由此体会到,像格非这样的小说家,宿命般地走上虚构的道路,而他却会为我们必然性地提供了关于这个世界真实的基本图像。
但是,即使有这样一双的“鬼斧神工”般的眼睛,格非也依然无法清晰地看见一切事物的机枢,这不是一个作家自身的能力问题,这是人类认知所面临的局限和关隘。也许,只有小说这样的虚构文本,才可能大胆地肩负起猜想世界的使命。因此,就有了大量所谓“空缺”的存在。仔细想想,之所以有“隐秘”世界的存在,是由于事物整体性的不可知。不可判断和预知,这是一个本源性的问题,因此,可以说,格非的小说《迷舟》,带领我们从另一个路径进入了历史、进入存在世界,这不仅是小说叙事的革命,而且涉及到美学、哲学和历史学与文学关系的深刻变革。它强调和重视的,是文学叙事,终将无法“篡改”历史命运。
若想深入阐释《迷舟》这个小说,我们依然需要从文本的几个重要元素入手:时间、历史、回忆、人物、叙述、“空缺”和隐喻。
在这里,时间,是使这个文本充满个性化的基本元素。空间是一个容器,而时间也是一个容器。所以,时间不是线性的,往往是多维的空间吞没了时间,令时间被假象所遮蔽、所忽视。叙述现实,叙述历史,讲述人在现实和历史世界中的存在形态,却是在对时间和空间的想象和回忆中完成的。记忆,同样是一个复杂的容器,其中杂陈、积淀了无数事物的因子和元素,但时间本身无法唤醒和发酵它的存在价值和能量,只有“回忆”,才有可能揭示“时间的伪形”和历史假象的虚伪,发现既有“事实”的根本性缺陷,这样,在精致、超凡脱俗的回忆过程中,发现现实、历史以致存在间隐秘的时间、空间联系。时间在叙述的关键处发生了“断裂”,这是叙述的“症结”所在。无法接续的时间链条,被抛掷进时间的深渊。于是,小说的结构,成为对历史的解构和消解,成为对历史和真实进行重构、“还原”的基本过程。这也是《迷舟》能成为“先锋小说”杰出的代表性文本的重要原因。也可以说,《迷舟》是以自己的策略和哲学,直奔历史而去的,也是间接反思现实的。
谁能拆解开时间这个容器,谁就能打开历史和现实的真正隐秘,因为这个容器里面装的就是历史。这个容器之于小说而言,就是对一个新的、属于它的叙述方法的出现。《迷舟》这个小说为什么要如此布局?为何一定要如此这般地结撰叙事文本?我想,最大的原因,还在于思想、精神或者心理容量的溢涨,已经令原有的形式无法容纳和承载存在可能性这个历史摇篮,惟有破茧而出,才能重建文本畅达的隧道。也许,这就是艺术的辩证思维。
短篇小说《迷舟》,选择的是一个开放性的叙述人“冷峻”的视角,时间,成为文本中一个明显的存在。无疑,这是马尔克斯式的时间意识引入,如同“多年以后”这样的时间状语,在几乎所有先锋作家的文本里,一开始就主宰了叙事的秩序和格局。这些年来,人们大多愿意聚焦在“形式”的层面谈论这个小说先锋品质,认为这个如谜一样的小说,这个叙事的“迷宫”,是作家营构的“形式的迷宫”,历史的迷宫。其实,在这里,格非的文本叙事,在引入特殊的叙事策略的同时,却始终牢牢地遵循着中国诗学的一个美学情境:超逸之逸,并且是“冷逸”。其中蕴藉着那种空灵清润的气息,覆盖着破败衰朽的悲凉之雾。这看上去像是一种文体色调,实际上弥散出叙事的语气、趣味和精神格调,旨意遥深。所以,在《迷舟》所裹挟的南方的氤氲之气中,始终渗透、弥漫着萧索、苍茫、荫翳,也不乏透出隐隐的杀气。这仿佛对逝去的历史有种莫名的恐惧。这种语境,暗合了文本对历史乖张的假设和构想。混沌之气,搅和着历史的烟云,徐徐升腾。
小说中的几个人物,在叙述中,也几乎都是处于虚无缥缈、朦胧、模糊的状态之中。有姓无名的“萧”,以及马三大婶、母亲、老道、杏、三顺,仔细感受和体悟,他们在这个故事里,仿佛都只是一个个符号而已。
那么,格非“如此”讲述“这样一个故事”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是发现历史和时间的幽暗,感知个人与历史之间永远存在的、无法沟通的关系?若从本质上说,在这个文本里,历史也只不过是一个弱不禁风的框架,是一块早已风化的顽石而已。而“借尸还魂”永远是作家的拿手好戏,那么,历史之魂又在何处呢?一个作家,既不能肆意“俯视”历史,也不能刻意去净化历史,历史在文学叙事中可能是一种多维性的存在,只有具有清晰的叙事伦理和美学的品质,才能接近历史本身或者触及事物的可能性。
三
其实,《迷舟》里的“空缺”,就是历史的盲点和断裂之处,它也是我们在现实中回望历史时的盲点,是历史局部在我们判断中的“本质性”缺失,也是历史叙事时逻辑起点的迷失。说到底,相对于“人”这个主体,这个“空缺”,也就是存在的盲点。那么,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只有这样叙述历史的时候,小说家的谦卑也许才会尽显无遗,“全知全能”的叙事,再也无法在历史和“存在”面前大行其道。而且,在叙述中,作家已经隐藏起一个文学中最至关重要的因素——情怀,像罗兰·巴特的“零度叙述”,这样“主体困顿、风格忧郁”的文本,根本就不需要作家对历史“往事”有过多的热情。因此,在小说里,“萧”是一个冰冷的、几乎没有温度的人物,这是格非的一种刻意的处理,他像某种意念、理念的影子,跟随着自己模糊的意识,在自己家乡的村落和小河里漫游,任由自己本然的欲望,信马由缰,狼奔豕突。我想,“迷舟”之意,就是迷失,是一只迷途之船,是“迷失了的水上之船”。像是迷失在迷宫之中。这个整体的意象,或许就是在隐喻历史本身的飘忽性、不确定性,如同失衡在一片复杂的水域,处处遇到玄机。到最后,甚至连人物、故事和语言也会迷失在叙述里。在描绘这个历史主体“迷失”的过程中,凸显出历史的苍凉和羸弱,而历史的“能动”的必然,因为一种偶然性,一个人的“偏狭”走入茫然无际的“黑洞”。
萧重新陷入了马三大婶早上突然来访所造成的迷惑中。他觉得马三大婶的话揭开了他心中隐藏多时的谜团,但它仿佛又成了另外一个更加深透的谜的谜面。他想象不出马三大婶怎会奇迹般地出现在鲜为人知的棋山指挥所里,她又是怎样猜出了他的心思。另外,杏是否去过那栋孤立的涟水河边的茅屋?在榆关的那个夏天的一幕又在他的意念深处重新困扰他。
这天,萧像是梦游一般地走到了杏的红屋里去。
三顺还没有回来。傍晚的时候,涟水河上突然刮起了大风。
萧的迷惑,既是格非叙述的迷惑,也是历史的迷惑。萧为现实所困惑,我们却为历史感到莫名的焦虑和惘然。历史前行的动力,在一个短篇小说的文本之中,遭受到了巨大的质疑。个人的欲望,竟会在不经意间替代了历史欲望的达成,抑或,个人的欲望,就是历史欲望的“原型”。而“空缺”到底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叙述的圈套,抑或两者的“合谋”?这的确又是一个最“本质性”的问题。显然,在这里,作家无力把握、决定这个人物的去向,不可能、也不想控制他的行动,这既是对历史的包容姿态,也是隐含悲观的对存在世界不可知的消解。“萧”在大战在即,部队采取重大行动之前,却突然遇到家事的变故,父亲意外身亡,他要去参加父亲的葬礼。而他的家乡,正是他们需要迅即占据的军事重镇,这个地域,也正是敌人蓄意占据、攻击的要塞。其实,“萧”的举动本身,就是一件极其荒谬和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常识告诉我们,一个领命正在执行军事行动的军官,根本不应该有这样肆意的选择。“萧”完全沉入了一个非军人的情感纠葛的境遇之中,沉浸在与战争毫无关联的、日常生活的情境里,他似乎已经生活在一种幻觉里,同时,整个情势也为其生死蒙上了一层迷惑的阴影,此时,对于生死,萧已经在冥冥之中觉察到了周遭腐朽的气息。旧情萌动,萧与杏的私通在败露之后,致使他继续沿着“错误”的方向向前滑行。“就在他站起身准备离开父亲书房的瞬间,他意念深处滑过的一个极其微弱的念头使他又一次改变了自己的初衷”,他执意要去榆关。此时的榆关,正是两军交战的要地,萧的哥哥所率领的北伐军刚刚在榆关不战而胜,那么,萧去榆关究竟是探望被三顺阉割了的“杏”,还是与北伐军营中的兄长会晤?叙述就在这里中断了,也被叙述者“阉割”掉了。也许,无论萧去榆关做其中的哪一件事情,即使真的仅仅只是去看望遭受“阉割”的杏,萧都逃脱不掉被警卫员杀掉的命运。可见,历史处于每一个相关者的猜测和武断中,师长给看似不谙世事的警卫员的密令,也是对可能性的一种预设,偶然性转瞬之间成为一种必然的归宿。
马三大婶的角色,也令人深感吊诡和匪夷所思,她的行为诡异,她总是在时间的关键处翩然而至,她在整个叙述中不可或缺,她穿针引线地连缀起时间和记忆的缝隙,推动着“萧”游弋前行。三顺“阉割”杏的行为,似乎是凭借一种直觉或第六感之类的暗示,产生的强烈的现实冲动,却铸成了萧的选择。而老道的箴语,也早早铺垫、预示出历史的残酷性和神秘色彩。从这个角度看,这篇《迷舟》从整体上讲也是一部精致、严谨和结构感极强的杰出文本。
陈晓明教授更愿意使用“阉割”一词,直接地描述格非的“空缺”对历史做出的“武断性”处理。而格非在小说中,选择让三顺对“杏”实施的“阉割”,似乎就是一个明显的暗示。小说家还能做什么?对历史和往事最大的宽容,就是在“回忆”的途中“无籍因循,宁拘自责,挺然秀出”。格非就是要呈现历史的断裂,关键是这个断裂,竟然源出于一个中级军官的极端个人的偶然性。简直不可思议,历史的盲目性,难道就始于个人的经历和经验的一意孤行?
现在看,小说《迷舟》所承載的内涵,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一个短篇小说的容量。诚然,它不仅充满对历史驾轻就熟的自信,而且,“迷舟”这个意象,构成了历史和存在世界变局的隐喻。我感到,这个小说的写作,还使格非的历史观及其审美视角的选择,或多或少地积淀了悲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因子。这一点,不但延续到《褐色鸟群》《青黄》《雨季的感觉》《唿哨》《戒指花》等一系列作品,还不断地在此后的一系列长篇小说《敌人》《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和《春尽江南》中若隐若现。
这些文本里,依然不断有“空缺”出现,唯独不会缺失的,是一个小说家,一个叙述者对历史这个“灵地”无尽的缅想。
2017年3月 波士顿——北卡·杜克大学
注释:
{1}{2}胡河清:《灵地的缅想》,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页。
责任编辑 李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