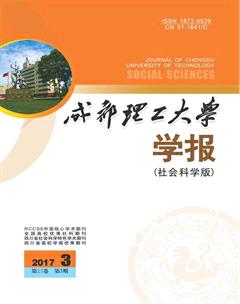“询唤”下的身份演变
周弋漪��
摘要:
主体身份的形成与意识形态息息相关,阿尔都塞意识理论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意识形态把个人询唤为主体”。他认为,人无法逃脱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影响着个体的行为,且意识形态将具体的个人建构为具体的主体。《浮世画家》的主人公小野曾是声名显赫的画家,弟子成群,然而当战争结束,人们开始质疑他的身份,认为他鼓吹军国主义酿成大错,而小野也在回忆中渐渐接受自己的身份演变。依据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从社会认可、他人关系以及建筑意象等方面分析意识形态如何将小野询唤为主体,并进一步探讨小野的主体身份问题,对《浮世画家》进行阿尔都塞式的解读。
关键词:《浮世画家》;阿尔都塞;询唤;主体;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 I106.4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7)03009504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1954- ),当代日裔英国作家,自20世纪80年代在文坛现身以来作品广受好评,是英国最杰出的当代小说家之一,他迄今共出版七部长篇小说和一些短篇小说、剧本。他的小说以“国际化”著称,写作往往清新细腻,作品囊括了英国文坛的几乎所有大奖。《浮世画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 1986)是石黑一雄的第二部小说,一经发表,它就获得了英国及爱尔兰图书协会颁发的“惠特布莱德”年度最佳小说奖和英国布克奖的提名。这部小说以日本二战为题材,从第一人称视角,在主人公小野增二慢节奏的回忆和叙述中,描绘了一位军国主义画家在战争前后的心路历程。正因为石黑一雄的日本移民作家身份,《浮世画家》的日本背景引起了批评家对日本历史和日本性的关注。然而,石黑一雄声称,自己对描写历史并没有兴趣,文本中的日本不是真实的日本,是他“为了满足写作需求而创造”[6]9的日本;他真正有兴趣的是全身心投入某件事的人,坚信自己做出很大贡献,最后却发现“社会的颠覆”让他们“曾引以为傲的事情变成一种羞耻”[6]7。
《浮世画家》中的小野正是石黑一雄所提到的那类人,而以日本二战前后那段历史为背景能为更好地体现小说主题奠定基础。从战前到战后,小野增二的身份从一个声名显赫的军国主义画家,转变为一个生活中屡屡受挫的老头,主体身份的巨变是小说表现的重大主题之一,体现了“社会的价值观永远在流动”[6]12,也与小说标题中的“浮世”相呼应。
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1971)中,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 ,1918-1990)曾提出“意识形态把个人询唤(interpellate)为主体(subject)”这一概念,也是他在这篇论文中的“中心论点”[1]253。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意识形态将具体的个人“呼唤”(hail)或“询唤”为具体的主体。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在他整个理论体系占有核心地位。用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分析这部小说,我们发现小野的主体身份之所以发生转变也可以归結为社会变迁所导致的意识形态的转变,因此本文试图围绕意识形态如何将小野询唤为主体这一概念,对《浮世画家》进行阿尔都塞式解读,以期为这部小说的研究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
一、意识形态下的想象性关系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 1943- )指出,每个意识形态理论家都有自己对意识形态的独特的定义,但“至今没有一个人提出一个完整又充分的对意识形态的定义”[3]1。尽管如此,阿尔都塞对于意识形态的研究被认为是“最具有穿透力的理论之一”[10]。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述”[1]256。这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使个人对现实产生了一种幻想,他所看到的现实只是意识形态作用下扭曲的现实,或者说,“意识形态扭曲了我们眼中真实的‘生存条件”[2]。在成为军国主义画家之前,小野一直在毛利先生门下学习“浮世绘”,历经七年,直至遇见冈田—武田协会——一个“致力于将艺术家与政治联系在一起”[9]的协会——松田智众,在他的影响下,小野离开了毛利先生,逐渐开始宣扬军国主义,“颂扬当今日本正在涌现的新的爱国精神”[8]77。很明显,“军国主义画家”是战败日本才为小野贴上的标签。意识形态的特点之一就在于不动声色地“把显而易见的事情当做显而易见的事情强加于人”[1]262。当时的小野没有也不会意识到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对外扩张”情绪或“军国主义”态势是错误的,对他来说,他只是一个纯粹的“爱国者”,只是在战后,人们才意识到他的军国主义画家身份,这就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对真实生存条件的扭曲。
意识形态无处不在,因为“人生来就是意识形态的动物”[1]262,并且“个体的每个行为都带有意识形态”[4]。于是,人们在意识形态作用下对幻觉(illusion)/暗示(allusion)的真实生存条件产生相应的行为。在日本国内对外扩张呼声正高的时候,在主流意识形态笼罩下,人们只看得到所谓的“爱国主义”,因此小野凭借鼓吹军国主义的画作取得不少名气,许多年轻人也慕名跟随他,可谓名利双收。“价值和理想在接受检验之后,人们会发现他们的价值和理想并不是他们所认为的那样”[6]36, 战后,小野也重新认识了自己过去的军国主义身份。
二、意识形态的询唤
在意识形态的不断询唤下,小野最终成为声名显赫的军国主义画家,从一个具体的个人被呼唤为具体的主体。那么,意识形态究竟是如何将个人询唤成主体的?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举了一些例子,他说道,“你我从来都是主体,并且就以这种方式不断地实践着意识形态承认的各种仪式;这些仪式可以向我们保证,我们的确是具体的、个别的、独特的、(当然也是)不可替代的主体。”[1]263我们平常常见的警察或其他人询唤:“嗨!叫你呢!”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双向确认过程,“在意识形态的询唤之下, 个体接受了意识形态为自己安排好的角色、位置, 同时也希望意识形态承认自己的存在和价值。”[11]这样一个互认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同样,在《浮世画家》中,小野的主体询唤过程无间断,方式多样,但说到底都是意识形态在发挥作用。本文试图从社会、他人和建筑意象等三个方面分析意识形态如何将小野询唤为军国主义画家。
第一个是社会认可方面,首先表现为小野获得的各种奖项和荣誉。1938年,小野获得重田基金奖,一个“在大部分人心目中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8]253的奖项,在这之前他还获得了诸多其他奖项和荣誉。这些奖项代表着他事业上取得的卓越成就,是主流意识形态对他所作出贡献的认可,因为奖项本身的设置就关乎是否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其次还表现为毛利和小野两人境遇的变化。小野本是因毛利的名气而师从于他,然而,数年后,当小野成为备受尊敬的画家,原本担心小野离开后会流落到为漫画书画插图的毛利“在城里的名望不断下降”,甚至“为了维持生计,已经开始给流行杂志画插图了”[8]254。毛利曾经致力于浮世绘的创作,绘画中的世界“充斥着娱乐、消遣和饮酒的夜晚世界”[8]179,这样的一个世界追求感情的瞬间性。而对于小野,正如石黑一雄在访谈中所提到的,“他觉得,通过隐含政治和宣传意味的画作,他可以将自己与一种不稍纵即逝,一种固化的价值相系”[6]31。毛利的落魄是主流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结果,而通过对反面意识形态的打压,意识形态实现了对小野主体身份的询唤。
第二个是与他人的关系方面,特别是小野与他的学生。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阿尔都塞指出存在两种国家机器,一种是镇压性国家机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 即RSAs),通过暴力发挥作用;另一种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即ISAs),包括家庭的、教育的、宗教的、传播的、文化的,等等。通过意识形态发挥作用,阿尔都塞认为其中最为重要的ISA是教育ISA,代替了以往的宗教ISA在现代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浮世画家》中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可以看作是一种追随与被追随的关系,德高望重的小野常常会“让那些其作品最能反映新精神的艺术家”聚集在一个酒馆谈话讨论,他说,“一旦我被问到一个有趣的问题,他们便都停住自己的话头,围成一圈,眼巴巴地等着我回答。”[8]89小野的学生给予他无限的崇拜,在他们看来,小野是不容置疑的时代先锋画家,自然而然,他们追随着小野的价值观。诚如小野自己所说,从老师那学来的“某些特征,就像当年那种影响的影子一样,一直陪伴着我们的一生”[8]169。于是,作为老师的小野发挥着教育ISA的作用;与此同时,作为军国主义画家他发挥着传播ISA和文化ISA的作用。也就是说,小野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进行实践活动,而通过日常生活中这些实践活动,意识形态将他询唤为主体。
最后一个是建筑意象方面,主要体现在小野从杉村明那买来的宅子上。在小说的开篇小野便交代清楚自己买进这座大大超出他支付范围的豪宅的经过。那么,作者为何要煞费苦心地描绘这一经过呢?这样一个宅子对于小野这个人物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在与Don Swaim的访谈中,石黑一雄曾提到,作为小说家,他对描写某个地点的表面细节并没有兴趣,他说,“对我来说,我创造的是想象的景观,是能够表达我诸多主题和情感的景观。”[6]96在文学作品中,空间往往是具有文化属性的一种隐喻。小野的豪宅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在买卖过程中,它的价值不以金钱为衡量,而是以买方的“品行和成就”[8]3为标准,小野之所以能在幾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正是因为,就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来说,他是一位品行和成就都极高的画家。这所豪宅成了小野军国主义画家身份的一种载体,意识形态通过这个载体询唤小野:他到底是不是一位符合标准的军国主义画家。就这样,意识形态通过建筑意象将小野询唤为主体。
“意识形态将个人询唤为主体”这一概念是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中心论点,强调“我们日常生活的实践都是意识形态的实践”[10],我们作为主体,实际上是意识形态不动声色地将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灌输给我们。这一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人的主体地位,“我们总是以为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在行动,实际上这是幻觉。”[10]《浮世画家》中的小野之所以成为军国主义画家,与其说是他的个人意愿,不如说,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下,鼓吹军国主义只是他针对扭曲的真实生存条件的一种实践。正如石黑一雄在这部小说中想表达的,“我充分意识到,人不受流行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控制简直不可能”[6]21-22, 《浮世画家》就是关于一个人“为了生活好而特意做一些事,然而事实上(他所做的)都是错误的”[6]208。
三、主体身份的演变
在小野的回忆性叙述中,他始终把重点放在军国主义画家身份给他带来的荣誉和满足上;而“日本战败后,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战争期间深受爱戴的政治家、军官、商人、艺术家转眼间沦为历史的罪人”[9],作为曾经的军国主义画家,小野在战后日本面临的是不断的质疑与挫折。弟子纷纷离开他,曾经最钟爱的学生黑田甚至与他反目成仇;昔日的同伴松田生活潦倒,疾病缠身,感慨“如果我们看问题更清楚一点……应该能做出真正有价值的事情”[8]249;象征着他声誉的豪宅、回荡着他豪言壮语的酒馆都被战争所破坏;女儿先前的婚事因为他被拒,一家人担心现今与大郎佐藤的婚事会重蹈历史,也让小野开始审视自己的过去,并渐渐接受自己主体身份的转变。
战争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小野依然沉浸在对过去的臆想中。当用自杀来弥补战时所犯的错误在社会上成为一种风气,当年轻一代的人质疑“有许多应该以死谢罪的人却贪生怕死,不敢面对自己的责任”[8]67时,小野却声称年轻人不能理性看待他们上一辈的牺牲,“那些在战争中为国家尽忠效力,战斗和工作过的人们,不能被称作战争罪犯。”[8]67-68然而,像这样的论断在当时是站不住脚的。意识形态具有一种承认(recognition)功能,阿尔都塞解释说:“我们不会认不出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情,而且在它们面前我们还免不了要产生一种自然的反应,(大声地或‘以良知的轻微之声)喊出:‘那很明显!对!那没错!”。[1]262-263与之相对的是意识形态的误认功能(misrecognition)。小野的论断是对过去的逃避,他内在的真实想法依然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左右,所以他才会为了仙子婚事的顺利进行探访松田和黑田,希望他们只说好的部分,因为不好的部分是不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承认的。最终,在与佐藤一家见面时,小野承认了错误,“我毫不讳言我犯过不少错误。我承认我做的许多事情对我们的民族极其有害,我承认在那种最后给我们人民带来数不清的痛苦的影响当中,也有我的一份。”[8]156从逃避到承认,小野接受了意识形态对他具体主体身份的询唤,“从阴影中走到阳光下,默默关注着被美国文化影响的年轻一代”[9]。
从战争到战后,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既是物理空间上的,也是心理空间上的。不同的主流意识形态询唤出不同的主体,小野的身份也由军国主义画家演变为有过错且不被社会认可的老头,而他从最初的逃避渐渐接受了自己身份的演变,正如小说的结尾所言,“我们的国家,不论之前犯过什么错,仍然有机会改过自新”[5]206,而已步入晚年的小野,只能寄希望于年轻人,“我们只能深深地祝福这些年轻人。”[8]258
四、结语
《浮世画家》延续了石黑一雄的第一人称叙述,也体现了他对回忆、怀旧等主题的关怀,小说中的主人公小野在缓慢的叙述中用压抑的语言向读者披露自己的过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小野的过去代表着他的辉煌,这是意识形态对真实生存条件的扭曲,也是意识形态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他的询唤。讽刺的是,当社会环境发生巨变,相应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改变,在新的主流意识形态下,小野成为新的主体,对过去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读者这才发现他过去曾是一位鼓吹军国主义的画家。在这整个过程中,意识形态扮演着太重要的作用。在谈论这部小说的创作时,石黑一雄说道,“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关于一个普通人无法超越自己周围环境的无力”[6]9。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部小说与日本性、日本历史有关,但人类无法逃脱主流意識形态的笼罩应该是它的更大主题,并和石黑一雄的其他小说一样,再次体现了他的一种整体关怀。
参考文献:
[1]Althusser, Louis.On the Reproduction of Capitalism: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Apparatuses(B. Brewster Trans.)[M].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14.
[2]Bertens H. Literary Theory: The Basics[M]. London: Routledge,2001.
[3]Eagleton, Terry.Ideology: An Introduction[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1991.
[4]Sadati, Seyyed Shahabeddin.The influence of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identity formation: Althusserian reading of Amiri Barakas “In Memory of Radio”[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lish and Literature,2013,(4):480-485.
[5]Ishiguro, Kazuo.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M].New York:Vintage International,1986.
[6]Shaffer, Brain W.Understanding Kazuo Ishiguro[M].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2004.
[7]陈越.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8]石黑一雄.浮世画家[M].马爱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9]郭欣.对话自我理论视角下的《浮世画家》解读[J].世界文学评论,2013,(1):160-163.
[10]王晓升.意识形态就是把人唤作主体——评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四个规定[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2):48-52.
[11]徐彦伟.结构与询唤——阿尔都塞后期意识形态思想的文本学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09,(11)3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