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绘画,百花灿烂
王吴军
唐朝是中国古代极其灿烂夺目的一个朝代,从“贞观之制”到“开元盛世”,唐朝发展到了一个极为隆盛的顶点,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强盛、最具有高度文明的国度。文化交流频繁,贸易交通发达,从丝绸之路引进的异国礼俗、音乐、美术以及多种宗教,使都城长安盛极一时,形成了空前的文化大交流和大融合,进入了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这时,绘画领域出现了一批非常杰出的人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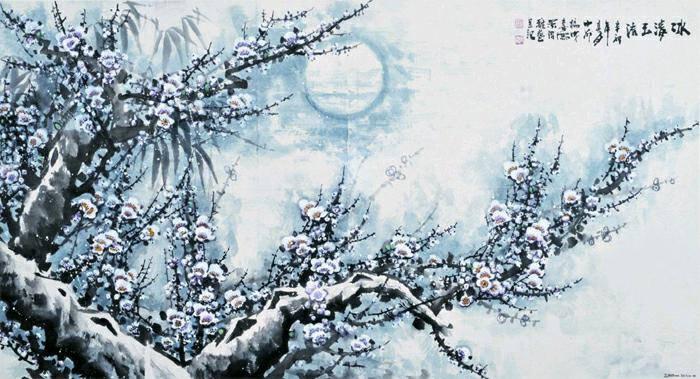
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至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的将近一百年间,六朝时延续下来的人物画仍然是唐朝画坛的主流。以绘画作为宣传工具的现象,在唐朝也未完全绝迹。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建文学馆,让画家阎立本画十八学士图像。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年),朝廷曾把功臣二十四人的像画在凌烟阁内,之后,凌烟阁内的功臣画像也先后绘过四次之多。这个时期,最著名的人像画家是阎立德、阎立本兄弟二人。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到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绘画出现了众花齐放、百舸争流、自由发展的灿烂局面。除了传统的人物、道释等题材之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山水画有了极大的进步,同时,因为当时的皇帝喜欢马,因此,朝廷常常命画家把心爱的骏马一一绘成图像,于是,画马也开始大为发达。人物道释画家以吴道子最为著名,鞍马画家曹霸、韩干、韦偃名闻天下。山水画家则以李思庆和王维二人的造诣最为深厚,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山水画的起源在唐以前,但是,山水画成为一个独立的绘画主题,则是在中唐时期。
李思训及其子李昭道,师承展子虔,又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创造出了青绿山水。画法上是先勾勒出山的形状,然后再用青绿重色进行填色,兼用泥金描出山脚,画法极为繁琐细密。后来,明朝的董其昌称这种画法是“钩斫之法”,其特征是画面繁复而华丽。唐朝大诗人王维,也是一名大画家,受了吴道子行笔纵放的影响,利用水墨的渲染,以浓淡的墨色画出的山水,很接近后世的写意画,耳目一新。王维与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的畫相比,一简一繁,一淡一浓,一疏一密,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后来,明朝的董其昌提出了中国山水画有南北二宗的说法,就是基于此。王维这派的画法属于南宗,李思训和李昭道父子一派的画法列为北宗。王维的画也有田园诗的气质,诗意弥漫。文学与绘画的结合的文人画就始自王维。此后,中国的绘画就开始逐渐脱离了宗教色彩,与诗词书法结下不解之缘。可以说,王维始创的所谓文人画一直占据着中国画史上的主要地位。在一幅画上题款、题诗、题跋甚至加盖图章,以及后来画家以书法笔力作画等等的演变,则是文人画的副产品,王维对后世的影响是极大的。
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至唐朝灭亡(907年)这个时期,著名的画家有周昉、戴嵩、边鸾和刁光胤等。周昉最初学的是张萱,长于人物画,尤其多绘贵妇人的那种雍容华贵的面貌和体态,与唐朝之前画家画的妇女那种清肌秀骨的瘦削形貌截然不同,这应该是唐朝人以丰肌为美的缘故。周昉画的人物的面貌对后世影响很大,从五代时期的周文矩,直到明朝唐寅的人物画,都有周昉的遗风。戴嵩则以画牛闻名,以牛为题材的绘画作品早在汉代就有了,六畜之中,牛的地位仅次于马。唐朝画牛的名家有三位,除了戴嵩之外,还有韩榥和戴峄。韩榥是戴嵩的老师,戴峄是戴嵩的弟弟。
晚唐时期的绘画中,花鸟画的兴起最为引人注目。以题材而论,人物画的发展最早,其次是山水画,花鸟画居第三。花鸟图形成为绘画的独立题材,始于中唐而盛于晚唐。当时的画家边鸾画的折枝花卉,只画一枝花,无根无干,风格非常新颖,很受当时人的欢迎。而且,边鸾还擅长画翎毛,于是,就奠定了花鸟画的地位。刁光胤更是将花鸟画发展到了完善的地步。唐朝末年,天下已经大乱,战火不断,刁光胤到四川去避难,把花鸟画也带进了四川。花鸟画因之得以发扬光大,在画坛上占有重要地位。
相对唐朝文化的博大精深,宋朝就显得要小家碧玉一些。在宋朝长达三百年的时期内,始终受着外族的骚扰之苦,这也是宋朝统治者的心腹之患,因此,使得宋朝文化的包容量远不及唐朝,但是,在宋朝这一时期内,绘画艺术也得到了空前发展,绘画题材非常广泛,几乎无所不包,绘画作品非常多,难以计数,为浩如烟海的中国艺术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宋朝在对外关系上是被动的,处理外事时总是谨慎细微,失去了唐朝的霸气,不过,宋朝工商业的繁荣兴盛带动了世俗文化的发展,而且,宋朝上至皇帝下至各级官绅,构成了一个比唐朝更加庞大和有文化教养的阶层或阶级。这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发展,绘画也不例外。在唐朝被认为是后妃、夫人一类上层妇女的仕女,在宋朝的含义已经有所转变,仕女图在宋朝更加世俗化了。
此外,宋朝还出现了李公麟的白描人物画和梁楷的简笔画,其绘画作品内容包含了禅宗人物和文人雅士参禅论道、读书谈天。宋朝的山水画种类繁多,北宋初年有郭熙、李成的雄伟山水,后来,又出现了更具有抒情意味的小景山水、燕家景致、米点山水、青绿山水及南宋四家的截景式山水。宋朝的时候,由于院体画的出现,皇帝自己也工于花鸟,花鸟画十分兴盛,其中以折枝花卉最为典型。而且,宋朝还出现了风俗画和历史故事画。这与当时社会环境有关系。宋朝工商业的繁荣则促进了市民生活的活跃,风俗画就应运而生了,但是,宋朝又是一个长受边疆骚扰之苦的朝代,一些画家希望以史讽今,于是,便创作出了许多历史故事画。
北宋对于封建割据造成的分裂和隔阂的统一与消除,使得社会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着相对安定的局面,商业和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城市布局打破坊和市的严格界限,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南宋虽然偏安于江南一隅,但是,由于江南的物产丰盛,大量南迁的北方人和南方人一起共同开发江南,使得经济、文化都得到继续发展并超过北方。北宋的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南宋的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等城市商业繁盛,除了贵族聚集外,还住有大量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城市文化生活空前活跃,绘画的需求量便明显增长,绘画的服务对象也迅速扩大,为绘画发展和繁荣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群众基础。
宋朝的绘画进入了手工业商业行列,与更多的群众建立较为密切的联系。一大批技艺精湛的职业画家,将他们的作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汴京及临安都有纸画行业。汴京的大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庙会,百货云集,其中就有售卖书籍和图画的摊位和店铺。南宋的临安夜市也有细画扇面、梅竹扇面出售。汴京、临安等地的酒楼也以悬挂字画美化店堂作为时尚,吸引顾客。市民遇到有喜庆宴会,需要的屏风、画帐、书画陈设等都可以租赁。适应年节的需要,宋朝的岁末时又有门神、钟馗等节令画售卖,甚为兴盛。
北宋时,汴京善画照盆孩儿的画家刘宗道,每有新画必然要画出几百幅,在市场一次售出,以防别人仿制。專画楼阁建筑的赵楼台和专画婴儿的杜孩儿,在汴京也享有盛名。吴兴籍的燕文贵常到汴京的州桥一带去卖画。山西绛州的杨威,善画村田乐题材的画,每有汴京贩画商人买画,他即嘱咐其如到画院的门前去卖,可得高价。对绘画的需求和民间职业画家创作的活跃,是推动宋朝绘画发展的重要因素。宋朝由于手工业的发达,促成了雕版印刷的发展与普及,出现了汴京、临安、平阳、成都、建阳等雕版中心,不少书籍及佛经都附有版画插图,绘刻非常精美。
大文豪苏东坡也是一名大画家,他画有《枯木怪石图》这幅画。米芾在《画史》中说:“子瞻(苏东坡)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枯木怪石图》的画风简洁明了,画面上怪石盘踞左下角,石后冒出几枝竹叶,而石右之枯木,屈曲盘折,气势雄强,怪怪奇奇,于笔意盘旋之中,凝聚成摇曳直上的不平之气,更有浩然之气在悄然弥漫,由石到树、由树干到树梢,扭曲而盘结,直冲天宇。苏东坡在绘画上不落前人窠臼,也不拘束于古人之绳墨,强调表现自我,大胆创新,批评学院派画家的匠气。而且,苏东坡在绘画上强调神韵,不拘泥于形似,他真诚抒发自己胸中的意趣,他的画与他的文、书、人,皆如是。
宋朝设立了翰林图画院,培养宫廷需要的绘画人才。北宋徽宗时,还曾一度设立画学。宋朝多数皇帝如宋仁宗、宋神宗、宋徽宗、宋高宗、宋光宗、宋宁宗等人,都对绘画有着不同程度的兴趣,都很重视画院的建设。特别是宋徽宗赵佶, 他自己在绘画上具有较高修养和技巧,注意发现画家并将画家聚集在一起,扩充和完善宫廷画院,并不断搜访名画充实内府收藏,推动了宫廷绘画的兴盛。当时的画院集中了社会上的优秀画家,体现了当时较高的水平,创作出了如郭熙的《早春图》《关山春雪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西湖争标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李唐的《采薇图》《万壑松风图》,马远的《踏歌图》《水图》等一大批成功的作品。
宋朝的文人士大夫在绘画理论上也颇有建树。欧阳修提出了表现萧条淡泊的情怀,陈与义则主张“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苏东坡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这一系列见解都具有代表性。宋朝的文人士大夫绘画影响到了辽、金地区,成为元明文人画发展的序幕。宋朝绘画的分类不如唐朝那么纯粹,也就是说,到了宋朝,画家的绘画能力范围扩大了。在绘画内容上,唐朝的绘画关注上层社会、宗教神话,宋朝的绘画则更为关注市井生活、文人雅行,内容的写实性增强了。
从唐宋时期的人物画笔法上来看,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绘画中线的运用很大程度上与书法有关。唐朝的书法处于中兴期,各家的书法争妍斗奇,还有魏碑、隶书遗风,但是,在人物画的线条上,唐朝的画家却用一种极富跳跃感的轻盈线条去表现对象。宋朝的书法以行草取胜,字体飘逸洒脱,舒缓自如,可是,宋朝的画家在绘画中却表现出了工整、厚实的线条。
应该说,唐宋时期是中国绘画史上非常灿烂的时期,是极具特色又创造了无数辉煌成就的时期,对于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