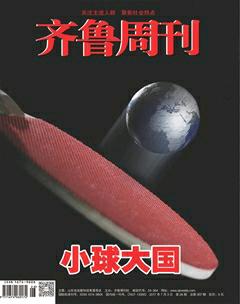放下手机,立地成佛
邓娟
互联网让世界天涯若比邻,但你选择将信息源锁定在封闭的朋友圈。你越来越无法忍受严肃的长篇阅读,渐渐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基于熟人社会的朋友圈,无法摆脱中国式社交关系的弊病和圈子文化的壁垒;网络生态的种种乱象,在这个微缩平台上放大,演化为焦虑、混乱的精神病场。
“熟人社会”延伸的线上朋友圈,无法改变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
有病的当然不只是微信朋友圈,溯本追源,病根在于圈子背后的中國式社交关系。同为本土化社交工具的微博和微信,最大区别在于微博偏向“陌生人社会”,而微信是把线下关系向线上移植的“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所以中国圈子文化的弊病林林总总都在朋友圈浮现。
美国记者布德瑞写过一本Guanxi:The Art of Relationships,以微软在华研究院的故事为主线,剖析在中国做公关的潜规则。布德瑞认为,要在中国获得社会资源,“关系”的作用至关重要,而要获得关系需要混圈子。但中国式关系之复杂和微妙,让布德瑞难以用纯粹的relationships去表示,而是大有深意地使用了中文音译的“guanxi”。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有更精准的论述:“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形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费孝通认为,在中国圈子文化中,亲疏远近以及经济水平、社会地位、知识水准,都可以导致“差序格局”。
基于“熟人社会”的朋友圈,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线下圈子那根深蒂固的壁垒和等级。长辈、领导、同学、同事的角色,依然制约着个体在朋友圈的言行。于是发表状态就变得不是真正自由了,提供沟通便利的朋友圈有时反带来误解。2014年4月,北京海淀区法院审理了一则朋友圈引发的离职纠纷。李女士因为家事困扰,写了一段“扪心自问,自认坚强,不知还能坚持多久,泪流满面,无愧良心和天地,此时窗外雷声不断,老天为我在流泪,人在做,天在看”发在朋友圈,老板看到后愤而评论:“如果一份工作让人如此悲伤,不做也罢”“你把我置于何地,周扒皮?刽子手?这是公众平台,请所有员工自律!”虽然李女士立即解释了双方语境不对等,但还是被动离职。
这并非个案。2015年,人大历史系硕士新生郝相赫在朋友圈点名称两位学界专家为“庸才”,这令他的导师孙家洲“极为震怒,怒斥狂徒”,出于“学界的规矩与尊严”,公开宣布断绝师徒关系。“言多必失”的中国式关系学,在看似“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朋友圈,依然灵验。
社交网络中的人格:每个人都是天生的演员
原来惹不起躲得起的同学会,都围堵朋友圈了。原本下班后可以抛开的办公室政治,都蔓延朋友圈了。这里有中医特色的养生,想象力一点不输《女医·明妃传》;有高贵冷艳的代购,比房产中介还无孔不入,比完美、安利更擅长营销。三观大战朋友圈,鸡汤与狗血齐飞,假新闻和伪科学PK。
冷门喜剧《波特兰迪亚》有一个片段,男主角带着新欢去意大利度假,虽然在酒店睡过了整个无聊的周末,但他们还是发布了许多秀恩爱的照片,收到来自朋友的恭喜。于是片中有了这个对话——“网上的所有人,他们过得并没有你觉得的那么爽。”“我想,人们只不过是把悲伤都裁剪掉了。”
被裁剪后的生活,难免成了局部的真相。但在社交网络上,我们判断别人过得好的依据不过是通过ta提供的信息——即便有记录的成分,发布之前必然经过挑选,这种记录也就参杂表演性质。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生活的年代还没有Twitter、Facebook、Instagram以及微博、微信,但他却先知般地洞见了一切社交网络中的人格。
戈夫曼认为,日常生活就像剧场,每个人都是天生的演员,只要站到前台,就会戴上假面具,进行合乎他人期待的表演;与前台对应的后台是观众看不到的地方,只有在这里演员才能卸妆,或者表演些前台不适宜展现的戏码。演员们还需要给彼此反馈,以融入共同的社交场景,有时他们组成剧班,相互配戏;有时又互为观众,进行互动——演员和观众,是一场完美表演的必备要素。
“拟剧理论”从1959年提出就招致批评,不过,隔了半个世纪后再看,戈夫曼简直为网络社交的种种病态提供了绝佳的注脚。
中国人爱面子的程度恐怕举世皆知。戈夫曼对人际交往表演模式的剖析,在我们的朋友圈里到处可以找到案例:理想化表演,譬如晒花、晒书、晒美食,晒经过包装的生活方式,塑造想成为的自己,在点赞和评论中获得满足;误解性表演,譬如富人哭穷、穷人摆阔、大智若愚、假装高冷;神秘化表演,譬如发文留悬念,发图马赛克,欲拒还迎,犹抱琵琶半遮面;补救性表演,譬如自称各种狗、“人丑就该多读书”,看似自我矮化,实则求表扬、求抚摸。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技不如人,难免失意。根据戈夫曼的理论,表演也存在被拆穿的风险,比如当观众闯进后台。然而在朋友圈,除了少数“装逼失败”事件,许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总是别人的前台,被嫉妒和自卑冲昏头脑,失去了辨别和思考的独立。
不必对技术因噎废食,但永远不要放弃对被圈养和绑架的警惕
20年前,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勾勒过一种“并行表达”的沟通场景:一群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唯一不会说法语的那个人显得很孤独,虽然所有的主、客体都处于同一时空,但他倘若想要接收其他人的信息,需要另外一种解码和编码的能力。
如今,互联网解决了编码、解码,虚拟空间的互动,代替了过去手势、眼神、会话等的面对面交流。所有社交媒体的初衷都是为促进沟通、消减孤独。“它是个快乐的地方,一个可以找乐子,提供消遣,一个和朋友聊天,让你感到愉快,受人认同的地方。”瑞士伯尔尼大学研究信息系统的汉娜·克拉斯诺娃说。Facebook起初让人们从交流中获得积极、快乐,但后来却出现了被称为“脸书抑郁”的社交综合症。
密歇根大学社会心理学家伊桑·克劳斯2013年的一项调查发现,人们汇报自己在某一时刻上Facebook越多,从这一时段他们的情绪就恶化得越多。
连续4年里,缅因州科尔比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索托对1.6万余人使用社交网络的幸福感进行追踪调查,结果显示,最初“外向、和蔼可亲、正直的人幸福感增强”,但当幸福指数升高以后,受调查者反而会开始变得内向。
交友过热,反而孤独。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越刷朋友圈真正的朋友反而越少。
廉价的点赞、虚伪的感动、没脸没皮的哗众取宠、不经思考的愤怒,异化的朋友圈带跑了生活,表演性质的“前台”无限扩大,属于自己的“后台”时间越来越少,人们仿佛成了被圈养其中、被牵着走的动物。
我们都是朋友圈的病人,但,有些病也不是关闭朋友圈就能痊愈的。
在中国式社交关系格局里,无论什么圈,都不要忘记对被绑架、被圈养、被同化、被规训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