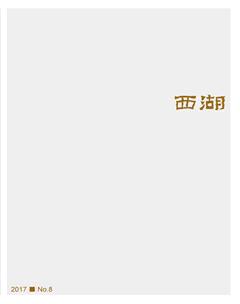“水浒叶子牌”及其他
水浒叶子牌
潘之恒有《叶子谱》,上面的标记是这样的:
万万贯宋江,千万贯武松,百万贯阮小二,九十阮小七,八十朱仝,七十孙立,六十呼延索,五十鲁智深,四十李进,三十杨志,二十扈三娘。九万贯张横,八万贯索超,七万秦明,六万史进,五万李俊,四万柴进,三万关胜,二万花荣,一万燕青。
将水浒人物制成纸牌,用来玩游戏,也是一种不错的创意。
据说,“叶子戏消夜图”始于宋太祖,后宫闲得无聊,漫漫长夜,不如玩牌,时间会流失得很快。
《青箱杂记》载:杨大年好与同辈打叶子。这个叶子,就是纸牌。
这些人物,在统治者眼里,都是反贼;老百姓也将他们当成反贼,好在已成勾栏瓦肆里的戏剧人物,将其标注在纸牌上,就有一种警示,你打我,我打你,你压我,我压你,各人抓得一手牌,就如同各人带了一支队伍,可以尽情厮杀。
但也有人不喜欢玩叶子,认为玩物丧志。叶子传到明代,有人就叫“马吊”,桐城张文端公深恶痛绝,他刻印了一颗章,上书“马吊众恶之门,习者非吾子孙”,他还将这颗印盖在他们家所有的藏书上,至今,张氏子孙也不敢玩马吊。
官位,也可以入叶子戏。
清代梁章钜的笔记《浪迹丛谈》卷六,有“升官图”,讲的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游戏:
他和同僚潘芸阁在林少穆家里,看到过升官图,有人也叫它“百官铎”,上面列有明朝的各级官职,用来玩游戏。玩的时候,以得到点子数的多少作为晋升官职的依据,点数多,官就大,反之,官则微,一局牌打下来,有的只得尉一类的小官,有的则贵为将相,有的开始就得到了很大的官,有的开始是小官,但突然就升了大官,这些变化,跟官本身没有关系,只是牌好牌差的机遇而已。
叶子戏发展到现在,并没有实质性的技术变化,但有些人玩的注,却远超古代,让古人感叹。
(清·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八“水浒叶子”、“马吊”)
比家庭出身
李隆基,曾经做潞州的副市长。
有一回,他请假回京城。正值暮春时节,他一身酷装,骑着马,军装,臂上还停着雄鹰,行进到京郊野外时,正好有十几个富豪子弟,在昆明湖边的帐篷内饮酒,他们一边饮酒,一边唱诗。嘿,嘿,嘿,一个招呼,小李就加入到了活跃的活动中。
饮酒时,一人要求:今天,我们是豪门聚会,喝酒前,大家都要将自己的出身报一下。
羡慕,暴笑,打趣,起哄,什么声音都有。
轮到小李时,他笑笑:曾祖是天子,祖父是天子,父亲是相王,我是临淄郡王李某。
话一讲完,这些人都吃惊地逃散了。小李郡王,却慢悠悠,将很多酒倒在一个大杯里,喝光,离开。
臂上停着鹰,很酷的。好多少年英雄,打扮都这样。汉代,茂陵少年李亨,他养的鹰都有名字:青翅、黄眸、青冥、金距。
这个版本,在刘斧的《青琐高议》中,又出现了一次,这时李隆基的身份是唐明皇,他是去打猎的,碰到一批人在喝酒,要报祖先的官爵,他也兴致勃勃地参加了,结局差不多。
都说工作生活中有小圈子,李隆基碰到的,应该就是典型的小圈子。
在小圈子内,大家知根知底,气味相投,有些还是死党,讲起话来无所顾忌。吹牛显摆,自然是小圈子交流比较重要的一环,尤其是,当有个别陌生人加入进来的时候。
有官的人比官,有钱的人比钱。
不要被表象所迷惑,所遮蔽,楼外有楼,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当然,李隆基也是去显摆的,他显摆的机会并不多,自然要好好把握。
(宋·钱易《南部新书》卷甲)
钱如蜜
仲殊和尚,初游吴中,自背着一只罐子,看见有卖糖饼的,就向他讨一文钱,钱到手,就用钱再买卖糖人的糖饼,吃了离开。
他曾到某古寺作客,有和尚朋友来看望,就问他们要钱,看望的人互相看了看,很难为情地摊手:身上钱不多,怎么办呢?仲殊笑答:钱如蜜,一滴也甜。
仲殊的两个简单行为,就可以看出他和别人不同的性格。
他也是北宋的詞人,与苏轼交情不浅,曾参加进士科考试。年轻时游荡不羁,差点被妻子毒死,后才弃家做和尚。他有个嗜好,就是喜欢甜食,常食蜜以解毒,人又称“蜜殊”。
一般的乞讨者,如果想吃甜食,索性直接乞讨。问题是,做小买卖的,总希望他的产品能多卖钱,而不是直接用来施舍。仲殊这是在替别人考虑,先讨一文钱,游方僧,吃百家饭,乞讨是他的权利。一文钱,起步价,施舍者给了钱,积了小德,德要日日累进。拿到钱后,迅速买糖,对施舍者来说,哈哈,既做了好事,又生意上门。而仲殊,在日常行为中,保持了一种尊严。
仲殊向朋友讨钱,更是理所当然,他倒没有更多要求,一文也是好的。在他眼里,只有蜜,太喜欢蜜了。
其实,不只是仲殊喜欢钱,普通人都喜欢钱,只是仲殊直说罢了。
钱如蜜,一滴也好。还有更多的题外话,这里不讨论了。
(宋·惠洪《冷斋夜话》卷八“钱如蜜”)
樊恼自取
韩侂胄打了败仗,头发胡须都白了,困闷不知怎么办。
皇帝还是派人来安慰他,并在宴会上安排喜剧表演,设法让他开心。
喜剧演员们表演的,自然是一场喜剧。台上有三个人,一个叫樊迟,一个叫樊哙,旁边还有一个叫樊恼。又有一个演员,只管作揖设问。
问樊迟:迟,谁给你取的名啊?
樊迟答:夫子所取。
作揖者拜了又拜:噢,是孔圣人的高徒啊!
问樊哙:哙,你的名字谁取的呀?
哙答:汉高祖取的。
作揖者拜了又拜:噢,真是汉朝的名将啊!
问樊恼:恼,你的名字,又是谁取的呀?
恼答:樊恼自取!
优,俳优,常指男。伶,乐工,也指女。伶优,往往泛指演员。伶优表演,一直可以追溯到汉朝的东方朔,他似乎是滑稽的祖宗。
再举一例笑一下。
汉武帝游上林苑,看见一棵好树,问东方朔树名,东方朔说:此树叫“善哉”。武帝暗中让人标记这棵树。数年后,再问东方朔此树名,东方朔答:此树叫“瞿所”。武帝立即反问:东方朔,你欺骗我好多年啊,此树的名字,为何不一样呢?东方朔答:大为马,小为驹;长为鸡,小为雏;大为牛,小为犊;人生幼为儿,长为老;昨日的善哉,今日已长成瞿所。生老病死,万物成败,哪里有定数?汉武帝于是大笑。
杜甫有四句名诗:“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个“君”,就是唐朝著名音乐人李龟年。大诗人和音乐人,都一起流落到江南,《江南逢李龟年》,讲的是安史之乱,说的也是伶优的生活。
所以,伶优,通常是以机智诙谐的面目出现,插科打诨,缓解气氛。烦恼自取,打一场败仗算什么呢?不是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吗?
(南宋·叶绍翁《四朝见闻录》卷五戊集之“伶优戏语”)
求闲适
某读书人极贫困,但心有不甘。每到夜晚,则在户外露天点香,虔诚向天祷告,坚持不懈。
某个晚上,刚点上香,突然听到空中有神人和他说话:上帝被你的诚心感动,派我来问问,你想要求什么呢?书生答:我的愿望很小,不敢有大的奢望,愿我此生能衣食粗足,在山间水滨逍遥终身,这就足够了。
神仙听完,大笑:这是天上神仙的生活,你怎么能求得到呢?如果你求富贵,那是可以的!
这显然是杜撰,但不无哲理。
求闲适极难,是因为闲适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是,衣食不愁,百事无忧,物质极大丰富,这种情况下的闲适,人人都想求。
但这是一对矛盾。
物质不丰裕的时候,千方百计争取,有的人还会不计手段,等有了几辈子也吃不完花不完的积累,他就会想到其他,想到人生的目的,人生就是为了挣钱吗?家财就是为子孙积吗?
因此,闲适属于精神层面。但我认为,好的闲适不是一般的游山玩水,那是一种看透世事的领悟,这种闲适,并不是无所事事,而是一种对自身灵魂充实的放松。
和山林同伴,和白云同游,需要一种情怀,有了这样的情怀,世事也就少了许多纷争,安静多了。
清代作家陆以湉的笔记《冷庐杂识》卷八有“道情”,录了一段著名中医徐灵胎的打油诗《邱园乐》,农家乐,闲安逸:
做闲人,身最安,无辱无荣,无恼无烦。朝来不怕晨鸡唤,直睡到红日三竿。直来时篱边草芟,花边土要翻,香疏鲜果寻常馔,鸟语关关,顽儿痴女跟随惯,绿蓑青笠随时扮。也有几个好相知,常来看看。挂一幅轻帆,直到我堂湾,带几句没紧要的闲谈细细扳。买碎鱼一碗,挑野菜几般,暖出三壶白酒,吃到夜静更阑。
但无论古今的现实都是,即便富贵是低层次的,芸芸众生仍然乐此不疲,不遗余力,真正的隐士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宋·费衮《梁溪漫志》卷八“士人祈闲适”)
云间酒太淡
云间酒淡,有作《行香子》云:浙右华亭,物价廉平。一道会买个三升。打开瓶后,滑辣光馨。教君霎时饮,霎时醉,霎时醒。听得渊明,说与刘伶,这一瓶约迭三斤。君还不信,把秤来秤,有一斤酒,一斤水,一斤瓶。
上海地方有家酒坊,价钱倒是不贵,物价廉平,但质量却不敢恭维,说是三斤酒,却都是水和瓶子,这样的酒,别说陶渊明、刘伶这样的酒专家了,常人都要吐嘈。
这哪里是酒,明明就是水嘛,假酒无疑。
但似乎也有夸张成分,这酒喝下去也会醉嘛,只不过是醉得不深,醒得快而已。
这样的词,以不同形式出现在陈世崇以后的各种笔记中。冯梦龙《古今谭概》、李宗孔《宋稗类钞》、褚人获《坚瓠集》中,都有传抄,只是,有的将朝代改为明代了。
《坚瓠集》中,将这一首讽刺词的量由“斤”改“斛”,结尾变成:有一斛酒,一斛水,一斛瓶。
酒水瓶,三斤或三斛分開,实在经典。
(宋·陈世崇《随隐漫录》卷二)
刻薄施肩吾
唐朝,元和十五年,施肩吾与赵嘏同年考上进士,但他们关系不好。赵嘏以前不知什么原因,一只眼睛瞎了,用珠子代替。施嘲笑他说:二十九人同及第,五十七只眼看花。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施肩吾考中进士,他一下子就成为我们那个地方的名人,他在老分水县的五云山苦读三年。我在好几篇文章中写过,我和他是校友,我们都在五云山上读过书,施读书时叫五云书院,我们读书时叫分水中学。
施肩吾是杭州地区第一个进士。以前的进士也可叫状元,所以,我们那里都叫他状元施肩吾。
这赵嘏同学,也算唐朝的著名诗人了,眼瞎不是他的毛病,假珠代替,说明唐朝的眼科还是比较发达的。一只眼对看花有影响吗?只要心情好,看什么都好,孟郊“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哈,看花只是一种形式和荣耀罢了。
施状元是不应该如此嘲笑同学的,对残疾人的不尊重不宽容,说明修养还不深,如果只是单单为了诗句的押韵,那更不妥当,诗才用错了地方。
其实,作者钱易搞错了,施说的不是赵嘏,而是崔嘏,有施自己的诗集为证《嘲崔嘏》,且有说明,时间都对,事件也对,只是钱易将讽刺对象搞错了。
当然,还可以为同乡这样狡辩:施状元只是客观地记录了唐朝眼科发达的医学成果,并无多大的坏意,不算刻薄的。
(宋·钱易《南部新书》卷甲)
生前福与死后福
有生前之福,有死后之福。生前之福者,寿、富、康宁是也;死后之福者,留名千载是也。生前之福何短,死后之福何长。然短者却有实在,长者都是空虚。故张翰有言: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持一杯酒。其言甚妙。
生前福与死后福,文字虽短,却是深奥的哲学问题。
长寿,富裕,健康,几乎是人生所有的追求了。
三者中,如果缺少长寿,即便你富甲一方,也是人在天堂,钱在银行,不长寿,谈不上健康;如果缺少富裕,那么,这样的长寿也是压抑的,不完美,太苦了,长命百岁,孤苦无依,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呢?如果缺少健康,那更痛苦,吃喝不香,寝食难安,长寿就是折磨,越长寿越折磨。
死后留名,千载留名,那也是许多人追求的梦想,让这个世界上的人都记着我,永远地记着我。
如果能两者结合,那就是完人、圣人,有吗?孔圣人是吗?不是,他生前不幸福,也不是最长寿。孔圣人自己知道死后会这么有名吗?哈哈。
所以,张翰直言了:他一定不要身后留名,这还不如一杯酒来得实在呢!
(清·钱泳《履园丛话》卷七“臆论·五福”)
伤泉脉
广济地方多云山,我(宋荦)曾经两过其下,都是晴天,但轻云笼罩峰顶,云山的称号不虚。
云山的岩石间,有细泉滴出,一天可以贮满一升多。山民们想将泉孔凿大一些,刚刚凿掉如铜钱大的石块,泉马上就枯竭。其间道理讲不清楚,有人说,可能是伤了泉脉。
山泉的形成,如果仔细探讨一下,确实很有趣。
一般的原理应该是,天空中的降水,大部分被土壤吸收,有些成为河流,有些就一直渗透到地底下岩缝中,再通过适当的条件渗出。
让人不能理解的是,高高的一座山顶,也会有一孔泉,且常年不枯,于是就生出许多传说。我家乡的天子岗,就传说是孙钟葬母的地方,山顶有泉,不枯。萧山湘湖,越王广场城山山顶,传说是越王勾践屯兵之地,也有大泉,吴兵围困两月毫无险情。
既有泉,就一定有泉脉,这泉脉,就是泉在岩石间的走向,本来就是细若游丝,是滴渗出来的,如果凿大孔,加大流量,那就会迅速干枯。
泉脉不能伤,这是一个很好的暗喻。
比如,古代征收粮税,有这样的谚语:少收几粒,多收几年。这其实是农民(或有良心的官员)向统治者发出的善意劝谏,粮税不要太重,给我们留下足够的吃食,我们有力气再种,你就可以年年收取了。
再有,人类对地球的各项开发,也要适度,过去若干年,已经有够多的事实证明,人类已经干了类似伤及泉脉的蠢事,应该警醒。
泉脉,另一个代名词就是,适度。
(清·宋荦《筠廊偶笔》卷下)
长途运鱼苗
江州(今江西九江)等地靠近水边,盛产鱼苗。到了夏天,人们都卖鱼苗赚钱。鱼苗贩子也一时聚集,他们会将鱼苗贩到福建、衢州、金华等地。
怎么运送呢?用细竹丝编织成像桶一样的形状,里面糊上漆纸,将鱼苗放到桶内。刚孵出的鱼苗细若针芒,一桶内可能装数百万条。在陆路上行走,水不能放太满,每遇到池塘,一定要换新鲜水,每天要换好几次。另外用一个小篮,做法和桶一样,是用来换水用的。换水时,要将鱼苗中稍大而有黑鳞的,拣出丢掉,如果不丢掉,它会伤害其他小鱼苗。
运送鱼苗,终日奔驰,晚上也不能休息,如果要稍作休息,也要讓人专门摇动竹桶。桶在动,水在晃,鱼以为还在江湖中,如果水不动了,鱼苗就会死去。
将这些鱼苗运到家,做一个大布兜放在水塘中,用绳子将布兜的四角都挂起来,布的四角离水面尺余,将鱼苗全部放入布兜中。风波微动,这些鱼苗,仍然以为身处江湖河海中,它们会顺着布兜,旋转,游戏。
鱼贩子们,将这些鱼苗养上一月半月,就可以按条出售了。
有人说,初养之际,用油炒糠喂它们,这样长起来的鱼,不会生子。
鱼贩子们要赚点钱,也不容易。
这似乎是鲶鱼效应的萌芽版。
稍大而有黑鳞的,必须丢掉,因为它极有可能吃掉小鱼苗。短途运送,估计问题不大,有黑鳞们在,小鱼苗会活蹦乱跳,它们要时刻防止自己被吃掉。
对针一样的小鱼苗来说,小小的竹桶,就是微型的江河湖海。它们并不清楚,自己即将从海滨城市到犄角旮旯的平原或山区去生活和发展。模糊并仿拟小鱼苗们的生活环境,是运送成功的关键,当然,还要不时换新鲜水,它们太弱小了,经不起任何风浪。
现代运送鱼苗,就没有这样的风险,弄个氧泵,不停在运转,就如人们家里的鱼缸,如果没有十分特别的原因,那些小金鱼们,都会自在得很,有氧呢。
(南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鱼苗”)
贼马
王春亭刺史说了一件马的事。
某人非常喜欢骑马。他曾经买了一匹马,骑着它出了广渠门。刚一出城,前方来了一辆大车,这马看见了,长嘶一声,就横在马车前。马车的群马见了它,都不敢前进。这马屹然而立,某人虽识马颇多,也不知所措,不知道什么原因。仆人却心里有数,就将衣物解下来,远远地抛给他的主人,主人接着衣物,更加莫名其妙。
那马见骑者已得到东西,迅速向前飞奔而去,深沟短壁,一跃而过,遇见推着小车的,也从他们头上跃过,一直飞跑,跑到旷野无人处,此马才停下,前蹄跪着,趴着不动,温驯无比,某人才得以从马上下来。
某人问了仆从,才知道他买的是一匹响马,就是盗贼用来劫人财物的,这马已经养成习惯了。
我在《笔记中的动物》中写过《舞马的悲剧》。
唐玄宗时代,那些马是因为训练久了,会跳漂亮整齐的舞蹈,跳舞表演就是它们的职业。这些只会跳舞的马流落到民间,被征招进军队,军乐响起的时候,舞马习惯性地起舞,士兵们没见过,吓得不轻,视为异端,用棍打。越打,舞马就认为是自己没表演好,跳得越起劲,一直打,一直跳,最终被乱棍打死。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虽说的是遗传,却也说明习惯的重要,跟着老鼠,只能练习打洞,打洞是它们的生存法则。
动物训练久了,自然会养成习惯。
同书卷二写到象的礼节:
岁丁酉秋,入朝站班之象,行至西长安街,一象生病倒地,过了会,此象尽全力撑着起身,跪着,向北方叩首三下,又转向西方,叩首三下,倒地死去。向北面拜,是谢恩;向西面拜,是不忘它的出生之地。
替朝廷站班的象,也是有级别的。级别不一样,享受的待遇也不一样。病象死去前,不忘礼节,除了说明象的聪明外,也是习惯训练成的。
(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八)
者者居
我(钱泳)游历过的地方,不过七八个省,每每见到好的古碑、石刻、匾额、楹帖之类,我都要随手记下来。
如酒店匾额叫“二两居”,楹联是:“刘伶问道谁家好,李白回言此处高。”
河南水城、睢州一带,有酒店联:“入座三杯醉者也,出门一拱歪之乎。”
山东济南府省城,有酒店叫“者者居”,我不懂。
一日,在孙渊如观察席上谈及此条,有一当地人在座,他说这出自《论语》。我问《论语》哪一章?他答:近者悦,远者来。
大家一听,都认为这个店名妙绝。
让人铭记于心的,无非是这样几个条件:新鲜,好玩,有意思。
不新鲜,肯定不好玩,即使有意思,人家也记不牢。
“二两居”的妙处在于,对联犹如一个极有意思的场景,两个不同时代的酒量极大的千古文人,跨时空对话,此地,有二两足够了。质量好,品位高,省钱又过瘾。
者者居,由冷僻到拍案。近者悦,来过的人高兴;远者来,这种情绪会影响远方的客人,犹如淘宝网上门店的星钻,颗数越多越好,天南海北,再远的人,都不影响网购。
而且,“者者居”,还来自《论语》,中国最有文化的一本书,连喝酒,也要喝出文化。
产品的竞争,就是文化的竞争,古今概然。者者居,就是一个很好的古代案例。
(清·钱泳《履园丛话》卷二十一“笑柄·者者居”)
诗人“胡钉铰”
有个胡生,不知道姓名,平时以洗镜、补锅、锔碗为业。他居住在霅溪边,靠近白蘋洲的地方。他家边上,有座古坟,胡生每次喝茶时,一定会用茶祭奠一下。
有一天晚上,胡生做了个梦。
有人对他说:我姓柳,平时喜欢喝茶写诗。我死后,就葬在你居住的边上。你常常给我茶喝,我无以回报,想教你写诗。
胡生回答:我怎么会写诗呢,我只是一个混混日子打打零工的普通百姓而已。
柳生很执着:这个你不用管,到时候你说出的话就是诗了。
胡生醒来后,试着构思,果然感觉有神来帮助。一段时间后,他写的诗就像模像样了。
人们都叫他诗人“胡钉铰”。
这里,作者钱易忘记姓名的“胡钉铰”,其实文学史上有名的,他叫胡令能,是唐朝贞元、元和间人,一辈子以钉铰为业,能写诗。
陆地上小学的时候,我教过他读《小儿垂钓》就是他写的:
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
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扎着蓬头的小孩,側身坐在莓苔上,身子掩映在草丛中,举着长竿子,学着大人在钓鱼,路边有人在问路,小孩子连忙招招手,别吵别吵,小心我的鱼跑了!
活灵活现,一幅小儿垂钓图!
诗人和补锅锔碗,有什么关系吗?没有关系,又有关系。没有关系的是身份,作家应该是没有身份的,只要对生活有感受,有良好的文字觉悟,谁都可以写;有关系的是生活,正因为他的职业,他随时随地都在体验生活,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和各种人打交道,细致真实,不做作。
普通劳动者成为一个有名的诗人,在古代社会,实在让人不好理解,于是就要加很多的附会:上面是柳诗人的帮助。还有个版本,是在梦中,仙人来到“胡钉铰”的家,割开他的肚子,把一卷书放进去,一觉醒来,什么诗都会作了。
杭州运河边,著名作家黄亚洲,有个亚洲书院,他在那里,经常举行民工诗人论坛,若干年来,有一大批民工诗人脱颖而出。
我也去参加过民工诗人的诗会。我对民工说,作家是不分职业的,清代著名作家袁枚的《随园诗话》,应该是清代著名的诗选刊,他就选有好几首以弹棉花为职业的劳动者的诗,甚至连他司机写的诗都收入。
现如今,钉铰的职业已经消失殆尽,但“胡钉铰”的《小儿垂钓》却永垂千古。
(宋·钱易《南部新书》卷壬)
背小虎渡水
有谚语说:虎生三子,必有一彪。彪最犷恶,会吃虎子。
我听猎人这样讲:老虎要率领三只小虎渡水,一定会考虑,如果先背一只小虎过河,那么其中的另一只会有被彪吃掉的可能。所以,老虎采用的办法是:先背着彪到达对岸,回来再背一只小虎到对岸,然后,虎会再次将彪背回原地,将彪放下,又将另一只小虎背到对岸,最后,才背着彪到达对岸。
彪这么厉害,老虎母亲也要防着它。
动物的智慧,也是现实生活中逼出来的。因为爱,因为惧,因为生存,因为各种原因,所以,动物们的智慧也千姿百态。
我的《笔记中的动物》,写到了《鼠狼和鸦救子》,写到了“猎鹰奉命捉玩猴”,也写到了“训练有素的猴小偷”、“千里送家信的聪明狗”、“会跳舞的马”,都是普通动物,在生活中显露出来的高级智慧,有些连人也未必想得出来。
虎背彪渡水,颇有点田忌赛马的智慧,但田忌是人,是人中的官员,似乎不可比,可原理却相同。
不知道猎人是不是夸张了,我宁愿相信是真的。
后汉的贾彪,兄弟三人,都有很高的名声,但贾彪名气最大,天下人都说:贾氏三虎,阿彪最优!
睢景臣的《哨遍·高祖还乡》:“见一彪人马到庄门”,彪,虽作量词,但也是一队厉害的人马呀!
(南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虎引彪渡水”)
冬舂米
吴中老百姓家里,算好一年要吃多少米,到了冬天,全部舂好,并将它储存起来,大家都叫它“冬舂米”。
我(陆容)当初的理解是,春天来了,农事繁忙,百姓没有功夫做这种闲杂碎事,就在冬天将其准备好。
最近,我和一位老农民闲聊起此事,老农告诉我:不仅仅是这样的。春天舂米,春气动,谷芽开始浮起,米粒就不坚硬,这时舂米,米容易碎,损耗很大的,冬天舂米,米粒坚硬,损耗少!
生活中的许多小常识,都是人们经年累月的经验总结。
按季节言,冬天有冬天要干的事,夏月也有夏月该做的事,将冬天做的事放到夏月做,有时就会很不合适,上面的冬舂米,大约就是典型的例子。
闲冬腊月,村里开始打年糕,每户都要打不少,晾几日后,浸到水缸或木桶里,要吃捞几条,滑嫩柔软。立春过后,那浸年糕的清水,就要勤换,即便勤换,年糕吃起来的口感,也远远不如立春前。我的习惯,除去冬季,其他季节的年糕,我基本不吃,因为没有那种特有的柔软感。
我(陆春祥)也喜欢吃黄瓜、茄子之类的时蔬,但是,六月的黄瓜、九月的秋茄,我最爱;特别是六月的黄瓜,切成薄片,经阳光简单曝晒,那卷卷的疲软的瓜片,微盐略渍,加上切细的青椒,妈妈的拿手菜,想着就流口水。
机械化,现代化,流水线,将季节、时令,统统打乱。
不能想象,一个专门生产米的食品加工厂,只有冬季才舂米。
我无知,也许,春天舂米易碎,科学早解决了。
但我还是怀念那个“冬舂米”。
(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二)
律师培训班
陈石涧、李声伯告诉我说:江西人喜欢打官司,人们讽刺为“簪笔”。他们往往开有教人打官司的培训班,上百人来学,培训班的主要课程,是教学员们如何对答,如何从别人的话语中找到破绽,攻击他人。
又听说丽水的松阳,有所谓的“业嘴社”,也是专门教人怎么吃嘴巴饭,这个社团中,还出了个张名嘴,张槐应。
“簪笔”,可以理解成口才的厉害,像针一样,这样的口才,纵横捭阖,和人辩论,无往而不胜,绍兴人叫师爷,香港电视剧中称“讼棍”。
要在话语中将人置于死地,需要极为扎实的各种能力。
记忆的能力,大量枯燥的条文记忆,且是理解基础上的记忆,如此,才能引经据典,让人佩服;演说的能力,能将死的说成活的,反之亦然;思辨的能力,层次清晰,逻辑推导力强,常诱敌深入,陷别人于泥淖中不能自拔,即便处于劣势,也能在细微处发现蛛丝马迹,反败为胜。
上面的各项能力,虽有天生悟性,但也有很多技巧可以琢磨,更要经久练习。于是,讼学培训班和业觜社,就有了天然的市场。
至于张名嘴,没有细节,但不妨碍让人充分想象,他一定是打过数场知名的官司,常常将不可能变成可能,险中取胜。
我去松阳,听到松阳人这样形容能说的:甲厉害,能将树上的鸟儿骗下来。还要再加一句:乙胜甲,他能将骗下的鸟儿,再骗上树去!
(南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讼学业嘴社”)
三教都围着利字转
儒家以仁义为宗,释家以虚无为宗,道家以清静为宗。
今秀才何尝讲仁义,和尚何尝说虚无,道士何尝爱清静,惟利之一字,实是三教同源。
秀才以时文而骗科第,僧道以经忏而骗衣食,皆利也。科第一得,则千态万状,无所不为;衣食一丰,则穷奢极欲,亦无所不为矣。而究问其所谓仁义、虚无、清静者,皆茫然不知也。
从此,秀才骂僧道,僧道亦骂秀才,毕竟谁是谁非,要皆俱无是处。
然其中亦有稍知理法,而能以圣贤、仙、佛为心者,不过亿千万人中之一两人耳。
这实在是一篇极好的向儒释道挑战的杂文。
这个时代(作者所处的时代),什么教义,都变味了。秀才不讲仁义,和尚也不说虚无,道家更不谈清静,都干什么去了?都奔着“利”字去了。
秀才将文凭拿到手,名有了,官也有了,他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呢?他在一心想着如何确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他在一心思着如何编织好官场的关系网,他在一心谋着怎样才能拍好上级的马屁。仁义呢?先放放再说,需要时再拿出来。
僧道将大殿大堂修好,引来香客无数,香火旺盛,扩张,继续扩张,组建公司,扩大集團。南方某著名寺庙,人流天天如织,功德箱常常爆满,香火钱要一日点存两回。头香,烧头香,天价,仍然抢着烧。虚无吗?清静吗?不可能的,人流如潮,就是钱流如潮,僧衣道袍一脱,都是俗人。
仁义骂虚无,虚无责仁义,清静也抱怨。
这个世界,究竟是被谁弄乱的?不怪名,不怪利,怪你,怪我,怪他,怪我们大家,是我们自己搞乱了自己。
(清·钱泳《履园丛话》卷七“臆论·三教同源”)
(责任编辑:钱益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