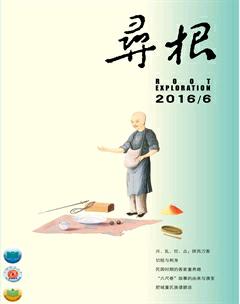切脍与刺身
周朝晖
说起日本菜,人们就想到被叫作“刺身”的生鱼片。日本人嗜生,举世皆知,读音“sashimi”也被收入英语字典。韩国人不服,说日本的“刺身”源自他们高丽王朝时代的“脍”(hoe),一副欲与日本刺身比高,争专利申报文化遗产的架势。其实,“刺身”也罢,“脍”也罢,都与中国古代食俗脱不了干系。
人类在掌握用火技术之前,都经历过茹毛饮血、活剥生吞的历史阶段。地球上很多民族和地区都有过生食鱼贝、肉类的历史,有的地区至今古风犹存,如北欧一些海洋国家,还有我国东北阿穆尔河流域乃至闽西某些村落,仍有吃鱼生的习俗。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饮食文化史上有关生吃的食俗也是可圈可点的,不仅源远流长,还深刻影响了周边的国家。
一部日本古代史,几乎大半是中日交流史。曾在北京留学数年的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为刺身寻根溯源,将食鱼生的历史推到周朝,见《诗经》中的《小雅·六月》:“饮御诸友,焦鳖脍鲤。”公元前823年,周宣王肱股尹吉甫北征胜利归来,大开盛宴,用炖甲鱼和鲤脍与朋友痛饮欢庆,脍在周朝是一种高端佳肴。何谓脍?杜诗邵注:“脍,即今之鱼生,肉生。”脍鲤就是切得非常薄的鲤鱼肉。怎么吃呢?《礼记》说:“鱼脍用芥酱,春用葱,秋用芥。”淡水鱼有土腥味,配以姜、葱、芥可以去腥味。不过这里的“芥”,并不是今天日本料理常用的芥末泥(山葵),而是用芥菜籽晒干研磨而成,气息和辛辣度更近于柔和的洋芥末。我国古代王朝大多定都中原,黄河流域的鲤鱼是最常见的食用淡水鱼类,或生吃,或腌渍,都是首选食材,延续了数千年。在孔子生活的时代,食脍应该比较常见,《论语·乡党》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一说,“食”与“脍”相提并论,可见其日常性,又说“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把食脍上升到礼仪的文化高度。北魏农政学家贾思勰《齐民要术》里收了很多古代流传在中原的食谱,其中“切脍”与“鱼鲊”分别是今天日本菜中刺身与寿司的雏形。唐宋时代切脍风俗似乎更加普遍,频频出现在李白、杜甫、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等诗人骚客的酬唱宴饮食单上,清新优雅,如诗如画。13世纪,游牧民族蒙古族入主中原,带来饮食风气的变化,但由于习俗具有一定延续性,所以并没有马上随民族征服带来的食俗变迁而消亡。元初关汉卿杂剧有一出《望江亭中秋切绘旦》,就是以切脍谱写的传奇故事:权贵杨衙内垂涎寡妇谭记儿的美貌,在她改嫁白士中后,百般构陷,并挟皇上势剑金牌之威欲置白于死地。谭寡妇假扮渔妇,在望江亭上荐杨衙内以美味切脍,用美貌美味作诱饵把他灌醉,骗得金牌,最终将其扳倒,挽救夫君和爱情于险境。这说明切脍在元代还未消失。
日本美食家北大路鲁山人说:中国菜在明朝达到了最高潮。但切脍食俗似乎难得一见,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个个生猛,大口喝酒大块吃肉,但他们的酒桌上似乎不见生鱼生肉。而到清朝,切脍就从中国人餐桌和酒肆里消失得干干净净了,有我国封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之称的《红楼梦》,不厌其烦写了一场又一场盛宴食事,就是不见切脍的影子。1877年,晚清诗界领袖黄遵宪到日本,得以近距离观察甚至体验大和食俗,将生食鱼脍之俗当作新鲜事记入《日本国志》:“以生鱼聂而切之,以初出水泼刺者,去其皮剑,洗其血鯉,细刽之为片,红肌白理,轻可吹起,薄如蝉翼,两两相比,姜芥之外具染而已,人口冰融至甘旨矣。”在黄参赞眼中,脍已是不折不扣的异域食风了。
日本的食脍起源于何时已不可考,从列岛四处都有绳文时代留下的鱼骨贝类残骸推想,生鱼生肉无疑也曾长期是大和民族的家常便饭,原始而古朴,犹如天地混沌初开。漫长年代之后,终于有一天仿佛得到某种启示似的突然觉醒,而且进步神速,自成一家格局,令世人惊艳,其中一大奥秘来自中国文化的启蒙和点化之功。
日本首屈一指的“中国通”内藤湖南曾以做豆腐为例,生動阐释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启蒙和点化作用。按照他的说法:日本文化由来已久,很多事物的种子已经存在,好比做豆腐,用豆磨成液体的素材一直存在,经过中国文化卤水的点化,一锅混沌初开的豆乳才凝聚成块。像切脍之类的食俗也是这样,古已有之,但经过中国文化的启示,使日本从原本混沌、模糊、庸常的既存事物找到一种规范、表达和升华的门道。作为饮食文化一环的切脍,在日本发扬光大即是中国文化影响日本文化的一个范例。
按照《后汉书·东夷列传》的记载,公元57年,倭奴国遣使来汉都洛阳称臣入贡,此后千年延绵不绝,迄唐为盛。对此,东洋最早国史《日本书纪》直言不讳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远渡汪洋前来大唐的初衷,“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从7世纪到9世纪的两百余年,日本先后向中国派遣近二十批次遣隋使、遣唐使,大量学者、僧人居住长安求学问道,甚至在长安做官,包括切脍在内的大唐食尚东传扶桑是可以想见的,至今不少日本人都深信刺身即由海归遣唐使从长安带回的。切脍在日本食文化史上的影像开始清晰起来的平安时代(8-12世纪)基本与唐宋重合,显示了某种意味深长的渊源关系。
切脍第一次见诸日本文献,是编撰于8世纪的正史《日本书纪》中,写成“脍”或“绘”,分别指的是细切的动物肉类和鱼类肉片,与醋等调味作料拌着食用,训读成“生醋”,不难看出与中原食风的相近性。8世纪一首和歌“酱醋捣蒜合鲜鲷”,歌咏大和王朝宫廷宴席上的佳肴。两百年后,律令书《延喜式》里出现了生鲤和鲷鱼切丝与姜葱同食的记载,已是一种饮馔制度了。
“物”的影响方面,豆豉、酱油等的引入引起调味料的巨大革新,提升了切脍的美味。8世纪,日本从中国学习做豆酱的技术,豆豉成为一大生活调味料。工匠做酱时无意中从积存桶底的液体中发现了酱油。这一发现使得日本菜肴开始有了独特的味道,切脍从此在鲜美一途一以贯之发展下来。
由于酱油的食用,切脍从薄片切成丝缕,变成大厚片如轩,“切身”之名即由此而来。但室町时代武家登场,忌讳“切身”与“切腹”“切首”的“切”,改为“刺身”,叫法因循至今。
从切脍到刺身,在日本得以一枝独秀地发展,还与日本岛国独特的食语传统密切相关。人类从生食到熟食,在烹饪上是一种进步。切脍在华夏中原源远流长,但最后式微,乃至从中国人餐桌上消失,异民族征服带来食尚变迁是一大因素,最主要的恐怕还是在卫生防疫条件落后的古代,生食尤其是以淡水鱼为主的中原切脍带来的寄生虫疾病,使人们最终远离这种鲜美的吃法,专在煎、炒、炖、煮、炸上下功夫,形成调和鼎鼐、五味共融的饮馔风貌。与中国不同,日本四岛环海,海洋鱼类十分丰富,比起淡水鱼,海鲜大多生息在水温极低的深水海域,寄生虫和细菌相对较少。此外,某些调味作料被开发利用,如山葵芥末、萝卜、紫苏被作为刺身搭配,不仅增加其风味而且因为具备强大的消毒、杀菌功效,有效解决了由生食引起的食物中毒和寄生虫危害,也使得这一传统食尚一直被保留下来。
吃刺身不可或缺的芥末泥,日语叫山葵(wasabi),原产于日本,与西洋芥末气息相近但辛辣刺鼻得多,具有强大的杀菌消毒之效,最早在日本是作为药用,被供奉在皇家宫苑里。奈良明日村大和朝廷宫城遗址出土的一块木简,上面用墨笔写着草药名称,其中有“倭佐俾二升”字样清晰可见,据考证“倭佐俾”就是wasabi的万叶假名读音。日本最古草药事典《本草和名》也是作为药用草本,写作“山葵”,至今通用。山葵有洁癖,对空气、水、土壤都有很高要求,人工培植相当困难,被当作贵重草药。17世纪初期,武士出身的望月六郎右卫门在静冈安倍川上游人工栽培山葵获得成功,山葵由贵重药成为吃刺身的作料。一般的餐馆上刺身会附带一块芥末粉和成的芥末泥,高级餐厅则上一段指根粗细的生鲜山葵,在金属凸起板上研磨。大宫车站前的百年寿司老店“東鮨”,用鲨鱼皮贴在小木板上,细细研磨,是山葵的最考究吃法。和山葵一起作为刺身搭配和作料的还有萝卜和紫苏叶子。萝卜用柳叶刀削成片,细切成粉丝浸泡去除辛辣味沥干,团成蓬松状,垫上苍翠的紫苏叶,专业术语叫“妻”,就是专门和生鱼片搭配,红白翠绿相间格外养眼,不仅是审美,最主要的还是解毒杀菌。日本举国大吃生鱼,却很少出现食物中毒事件,功劳恐怕要记在这些被当作陪衬的“妻”上。
鱼类肉柔软,切成片最见刀上功夫。杜甫诗里常见切脍的生动描写,“无声细下飞碎雪”意即刀工卓绝。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里就写了善切脍、刀工一流的南孝廉能将生鱼片切得“谷薄丝缕,轻可吹起”,神技近乎道,但在日本厨师行业,至今也不难见到。日本制刀技术源自大唐,但日本出产优质钢材,加上奇巧精炼的工匠气质,经过精心锻造研磨,削铁如泥,无论制刀或用刀,都后来居上,到北宋时竟返销中国,连欧阳修都啧啧称道,写入《日本刀歌》里。历史上,武士曾长期居于社会主流,江户时代,每日到将军居城或大名藩府上通勤的就有“庖丁武士”,专门负责主君的膳食,身上插的两把刀只是身份象征,但案板上的刀工更胜一筹。也许是这一传统,至今日本料理职人在对待刀具的虔诚与专一上也颇有武士之风。笔者曾在大宫一家百年老字号工作数年,对这种职人气质印象深刻,店里每个厨师都有自己一个精致的“庖丁箱”,切生鱼用二尺长的“柳刃庖丁”,宰杀鱼贝用刀背宽厚的“出刃庖丁”,切菜用“菜庖丁”,雕刻竹叶用“花庖丁”,分得清清楚楚,自己选购,自己养护,连磨刀石也各有专用,每天打烊离店前,就在各自的操作台前一丝不苟地磨刀,同时也是磨心,很有一种仪式感。笔者曾在日本料理达人神田川俊朗开在大阪梅田的河豚老铺里见识过他切河豚肉片,一片片薄如蝉翼,快如雪花飘落,一片片贴在青瓷盘里,透出盘子的纹路,“运肘生风看斫脍,雪随刀落惊飞缕”,简直就是苏轼笔下北宋“脍匠”神技再现,令人感叹华夏饮食之道在扶桑传承不衰。
在选取切脍用食材的喜好上,日本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在遥远的古代,中国王朝大多定都于黄河流域中下游的中原,哪里是王都,哪里就是中心,远离中心的海边只能是边鄙,是化外蛮荒,因此,鱼类以河鱼为贵,海鱼为贱。黄河鲤鱼是鱼中之王,这一观念也影响到日本。长期以来,作为刺身原料的鱼类就是鯉鱼。京都曾长期作为日本首都,离大海较远,附近滋贺县琵琶湖盛产鲋鱼,也就是鲫鱼,肥大鲜美,长期供应王宫和贵胄,切脍或做成鲊,分别是今天日本刺身和寿司的雏形。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城开设幕府,原本荒芜的小渔村成为另立中央的行政中枢,迅速发展成为人口超百万的大都市。与京都不同,江户人崇尚新鲜口味,讲究“旬物”,即当季食材。江户时代,现今皇居前的日本桥沿河岸一带,有个日本乃至亚洲最大的“鱼河岸”(海鲜批发市场),来自纪州湾、伊势湾、濑户内海的新鲜鱼介都在这里集散,食用海鱼成为市民食桌主流。武士是日本社会中坚,本来无人过问的鲣鱼因为读音类同“胜男武士”,用其做成的刺身大受追捧,奇货可居。鲣鱼汛期未到,就有按捺不住的武士立在岸边数着银子痴痴地等,甚至有人典当宅邸去大快朵颐。今天刺身食材中不可或缺的金枪鱼,也是江户时代才开始进入切脍案板的。18世纪后,日本深海捕鱼技术大进,鲸鱼、金枪鱼大丰收,开始进入江户市民餐桌。不过当初只吃金枪鱼身上清淡的“赤身”部位,脂肪堆积如雪花的肚腩没人要,买鱼时,店家附送带回去喂猫喂狗,干粗活的人用它加酱油煮汤补充油水。二战后,美军占领日本,吃惯油腻的山姆大叔不欣赏自身赤身的淡泊清雅之美,到寿司店专点没人问津的肥腻的金枪鱼肚腩,世风跟着转向,令金枪鱼肚腩价格扶摇直上,成了高岭之花。
饮食文化的流播与传承,既有普遍性也有偶然性。“脍”“炙”人口的华夏食俗,被周边国家的接受和传承也各有偏向,可谓——花开五叶。日本得其“脍”,即刺身,因缘际会发扬光大成为大和“国菜”;朝鲜得其“炙”也就是烧烤,如今也是满世界烟熏火燎大行其道。韩国历史上也盛行过脍,今天韩菜里的“hoe”,即是“脍”的汉字音读。据考证,脍在三国时代传到朝鲜半岛,生鱼写作“脍”,生肉作“鲙”,高丽王朝时代因为佛教被立为国教,“鲙”被废止,剩下“脍”,原料主要来自自身鱼类,如鲤鱼、鲷鱼,又叫“生鲜脍”,蘸料则是豆瓣酱、辣椒酱、大蒜片,口味浑浊泼辣,与淡泊清雅的日本刺身大相径庭,色相也黯然无光。花叶同根,如果要争专利,先得寻根,那就穿越到两三千年前的华夏中原来吧。
华夏饮食文化后来转型,专在煎、炒、炖、煮、炸上下功夫,形成调和鼎鼐、五味共融的饮馔风貌。堂皇始大,从人类文明进程来说是一种进步,脍、炙被远远甩在后头。无论和脍还是韩炙,各自将中原食俗某一特点发扬光大乃至趋于极致,但就是学不来中华饮馔之道兼容并包、有容乃大的气派和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