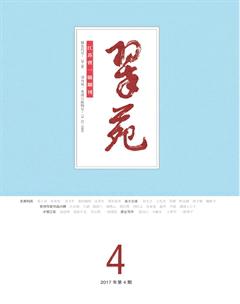隐遁的村庄
姜刚
炊 烟
我不知道村庄里的炊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减少的,但始终守候村庄的人知道,村庄知道,只是,所有的人、村庄里所有的事物都在我内心布满疑惑的时候缄口不语,仿佛这一切并不需要我这个走出村庄的人去见证。毕竟,对于一个村庄,我又能见证什么呢?我只是在这里出生,然后走向远方,带着属于我自己的炊烟。
一柱炊烟对应着一个家,一家有几个人,这柱炊烟就有几缕,那几缕纠缠捆结在一起,就是一家人,哪家人不和睦,这家的炊烟也会貌合神离。一个人离开了,一柱炊烟就会少掉一缕,炊烟也就没有了这个人的颜色和气味。离开的人带着自己的炊烟到达另一个村庄,更多的是去了城市,到另一个村庄的炊烟会找到另一柱炊烟融合进去,到城市的那个人很快就会在比大地还要苍凉的城市中散失掉炊烟,成为没有炊烟的人。
这个村庄的炊烟正在逐渐变细、变淡。不断地有人带着自己的炊烟从这个村庄走出去,也不断地有炊烟融入这个村庄,只是走出去的越来越多,融进来的越来越少。走出去的人还会短暂地回到村庄,但即使回来,很多的人炊烟已经融不进自己家的那一柱里,就像是一个客居异乡的人。而失去炊烟的人即使回来了,村庄也以为他依旧漂泊在外。
在我离开的时候,村庄的炊烟繁密茂盛,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稻草或者树枝的焦香。这种香味往往比饭香更先到达我们的鼻端,有点类似于母亲无声的呼唤,或者说是母亲呼唤的前奏——不久,我们就可以听见母亲悠长的呼唤,那声音穿透岁月厚重的尘埃,萦绕在逐渐老去的耳畔。
每回到村庄一次,感觉中这香味就变淡一次。最先消失的是稻草的焦香,接着是玉米秆的,再后来就是黄豆秆的、花生秧的。这些村庄上长出来的植物不再通过灶膛成为灰烬再回到村庄的土里,而是在冰冷的机器割碎,在田野里烂掉。
现在,每年中村庄炊烟最茂盛的时候是过年,飘离村庄的人暂时回到这里,一家人相聚在离自己的祖宗最近的地方。
或许有那么一天,村庄成为没有炊烟的村庄。可那,又是谁的村庄?
河 流
河流是村庄的血脉。
她比滋养更为深刻,比孕育更为厚重,她是比赐予更为久远的恩典,是比注视更为久远的凝望。
村庄曾经生活在河流柔软、潮湿的腹地,她的湿润如同乳汁,让村庄受孕、分娩,氤氲在生生不息的温暖之中,河流是村庄相伴终生的女子。不管朝着哪个方向从村庄里走出去,不久,就有一条河流横在面前,但她不是我们走出村庄的阻隔,它只是我们将自己从村庄里放逐出来,走向浩渺远方时一个停顿和回眸的契机,她让我知道我即将走出那温暖的腹地,告诉我异乡的寒与冷,只是,她不发一言,如同大地缄默千年。
河流里生长着莲、菱角、芦苇和水蒲草。嫩嫩的芦苇芽子顶破松软的湿土时,小荷露出尖尖的角绽放出赠予世界的第一朵微笑,河流与村庄顿生涟漪。菱角浮在水面,开出白色的小花。翠绿的翠鸟停驻在远处的柳树上,偶尔像一道翠绿的闪电快捷无比地掠过正午平静无风的河面。莲和菱寄居在柔软的水里,却日渐生长出坚硬的外壳,存放她们温柔的内心,小心地躲避开世界带来的伤害。而走出村庄的人在河流之外,日渐被异乡的风雨剥蚀去村庄的味道和气息。修长修长的似婉约的女子,随便一阵风吹过来,便多情地舞起纤弱的扶风之舞。
雨季来临的时候,河水逐渐丰盈到膨胀,淹没了水边的青青野草。等到河水退去的时候,河岸上会留下一条明显的界线,界线以下,曾经茂盛的草萎顿入淤泥,界线以上,还在生长的草也终将在深秋的寒露中逐渐枯去。随着寒露降临,风情万种的荷叶逐渐萎败到折断并融入水中,花白花白的苇花渐渐张扬成河流飘飘摇摇的旗帜。寒冬之后,河面被冰密密地封住,熟透的莲子和菱角早已钻进河底温暖的淤泥中,只有早已将蒲棒结得扎扎实实的水蒲草坚强地站立在冰面上,只是那腰杆已被冻伤,在冰面上奔跑的我们只要将脚轻轻一踢,那蒲茎便在一声脆响中颓然倾倒在冰面,飞絮四散,像极了春天的柳絮。
河岸边的草一岁一枯荣,河流里的水还是每到夏天就涨起,只是,那些水在我离开故乡的日月里逐渐变得浑浊、僵滞,不再灵动,莲和菱慢慢地忘记发芽开花的梦,清晨或黄昏里不再有水蒲草修长的身姿吸引我温情凝视的目光,冬天里不再结那么厚的冰,不再有花白花白的苇花编织成高高的木屐,或者垫在我们的老棉鞋里。那些在河里泡上整个夏天的时光,撑一只木桶采莲摘菱的时光,在冰面上奔跑玩耍的时光,真的就这样成了过往,永不再来的过往,任何回忆、任何时光也复制不了的过往。
河流黯淡,血脉梗塞,村庄逐渐虚脱。而我心里的愿望却日渐单纯而倔强:愿每个春天,河流还在我的身体和气息里汩汩作响,还在我的血脉和魂魄里拨动颤颤地弦。
桑 梓
村庄在我的字典里有两个名字,一个名字叫老家,这个名字朴实易懂,充满了世俗的温情,在我离开村庄的这么多年里被我反复提起,大约也像村庄对我隐约的呼唤。村庄的另一个名字叫桑梓,这个名字是诗化的名字,显示了汉语魅力的名字,从远古先民的吟唱中承传绵宕至今。桑,悠扬的后鼻音,梓,嘴角微微翘起的平舌音,连缀起来,是排遣不去、割舍不开、楔入心坎的回忆与现实的缠织,甜蜜与忧伤的交媾。
梓树,我没有见过,或许也见过,只是我因不知道她的名字而不记得她的身姿。而桑树,却植满了我记忆中的村庄。童年经验大概是我人生永远的根基、岁月秘密的起点和永远走不出去的宿命,而童年的经验,很多都和桑树连接纠缠在一起。
那时的村庄是养蚕的村庄,田地中多的是大片大片的桑田,有风吹过的时候,那窸窸窣窣的声响对于并不懂得音乐的我来说犹如天籁。待到年纪大了一点以后,便被父母叫着跟去捋桑叶。这样的劳作类似于玩耍:父母用的是藤条编的大篓子,我用的是竹编的提篮,捋了浅浅的一篮子便倒进大篓子。采完桑叶后,手上满是乳白色的桑汁受伤风干后留下黏糊糊的污渍。几天后,我手上的污渍就可以慢慢淡去,但父亲和母亲的手掌上却永远是纵横交错的伤疤和粗茧,指甲剪得再短,那些经年的劳碌还是会顽固地在他们的掌纹和指甲缝里留下剔除不掉的尘垢。又有哪一种水能洗去这些尘垢呢?除非,无情的时间消泯掉他们的肉身,也顺带着消泯去他们在这个短如一日的尘世上付出的所有劳作、划下的所有痕迹。即使我还记得这些痕迹,可我也将成为世界的尘埃啊。
父亲善嫁接。在村庄还养蚕的年代里,这是一门受人尊敬的手艺。这门手艺我虽勉强学过,可如何操作早已忘记。但父亲因为淘桑籽而变得愈发黑的双手却刻在了我的记忆里:在河边,父亲蹲下来,用手挤碎盛在细篾篮子里的桑葚,紫黑色的汁液不断地从篮子渗进池塘,最后,一篮子的桑葚只能淘出大概几两重的桑籽。晾干后,父親会很虔诚地把它们装进母亲用纱布缝的袋子里——所有的种子对村庄来说都是希望,更何况,父亲大概是希望地上种满了桑树的。
而对于幼年的我们来说,桑树最迷人的正是它每年结出的桑葚,那是从白到红的变奏,最终沉淀为黑紫。浅色衬衫上经常沾染上桑葚深色的汁液,那汁液会顽固地渗透进衣服纤维的深处,反复揉搓也洗濯不去。因此总被母亲责骂,毕竟,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里,桑葚是很能满足我们贫瘠的口舌之欲的。但后来,为父亲收集桑葚却成了我的主要功课,并因此成了我的荣耀。
原来,老屋的边上有一棵桑树,桑葚不大,但却异常的甜。这棵树大概在我还没有出世的时候就有了,父亲没有告诉我这棵树的来历,但记忆里,它年年长出嫩嫩的桑叶,结出甜美的桑葚。前几年,盖新房子的时候,父亲锯掉了这棵桑树以及和这棵桑树紧挨着的两棵榆树。这棵桑树活在世上的时间大概比我短不了多少,我不知道一辈子没有离开自己出生之地的它是否拥有比我更多的安宁与幸福。
9月的一天,我竟在寄居的小区里几乎无人打理的绿地上看到了几株小小的桑树,还不足一米高,翠绿的叶子迎风招展,像是孩子般的羞涩与纯粹。面对这些摇曳的曾经那么熟悉的优美植物,我刹那间不由恍惚起来,我所在的地方到底是异乡还是故乡?究竟是“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还是“生仍冀得兮归桑梓,死当埋骨兮长已矣”?不知道,一切都是不可解开的谜底。也许,我终将在那个村庄和未知的前方之间徘徊不定,犹疑不决。前方的诱惑总是更美,即使那最终被证明不过是虚幻,但却也能使我朝着未知开始又一场旅行。只是,在去往前方的路上时,我一再听见村庄远隔千里的呼唤穿越了寥廓平原和茫茫时空,一声比一声紧、一声比一声颤地提醒、催促我踏上精神的返乡之途。可我终究只是将易碎且日渐苍老的身体放逐向无尽的远方。
桑梓之地,父母之邦。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只是,桑和梓已在苍茫的岁月中渐渐远逝,我将在何处得以埋葬我卑微的躯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