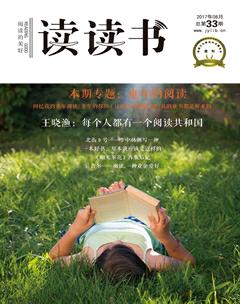“现在给孩子看的东西太幼稚了”
南方周末:与你的少年时光相比,现在的孩子有什么特别之处?
王安忆:现在的人阅读少,当年我们不管爱好不爱好文学,读书量都比现在大。图片、电视、电影还有动漫……现在直观的东西太多了,所以阅读量非常低。这肯定是不好的,文字很重要,需要更高的智慧。你先得识字,之后还要有一定想象力,能把文字转换成各种各样的声音、画面。读图一定是很直接的,相对来说简单和表面得多。
但年幼的孩子读绘本,是比较科学的。他们识字量少,看图画非常合适,尤其绘本有专门的风格,非常适合儿童阅读。我个人很喜欢绘本,觉得好的绘本像安徒生童话一样,小孩要读,大人也要读。它有些东西是孩子根本读不懂的。像《海的女儿》,写的不是残酷的故事,而是非常高尚的,那么纯洁、无我的爱情。
西方有些绘本非常深刻。我曾经看过一本叫《阁楼上的光》,好像是“新经典”出版的,真可以称为经典,大人孩子都可以读。它不是一个连贯的故事,只是生活当中小小的现象,配上图和文字。这些现象非常幽默、温馨或严厉,总之很有趣。
南方周末:为编选这些故事,你是否特意观察过当下孩子的趣味?
王安忆:我没有刻意去关心这些,只是覺得现在给孩子看的东西太幼稚了。好像一个人年龄很大,还是这种趣味,30来岁的人也非常幼稚。这是我从生活中观察到的,具体现象非常多。孩子读书少,动漫都那么简单,好像一个人发育非常晚,始终那么天真。从我们周围的文化环境看,现在的电影、电视等都趋向于低龄化,非常简单,整个标准在不断降低。影视作品我现在看得比较少,它们可能更加强调直觉和所谓的视觉冲击力。
以前过于强调孩子要阅读“低”的,其实不见得。大概四年级的时候,我看课外书,班主任过来说不应该看这样的书,意思大概是在你这个年龄看《红岩》已经到头了。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本书名叫《虾球传》(注:黄谷柳的长篇小说,以1940年代中后期的香港一带为背景,描写少年“虾球”在底层社会的流浪历程)。我四年级就看《红楼梦》了,《红岩》不能满足我。《铁道游击队》等“红色经典”我很多都没看过,个人取向不一样。
有些概念,把事情规定得越来越窄。我们现在好像分得非常严密,孩子该看的和大人该看的有分界线。幼儿看看绘本、图画,等到一定程度,就有了所谓“成人文学”。其实不是,文学就是文学,不应该分得那么清,文学本身就是青春的读物。
南方周末:你选择汪曾祺的《黄油烙饼》等写到死亡的作品,是希望帮助孩子形成正确的死亡观吗?
王安忆:这又关系到我们对孩子的认识:难道不给他看小说,他就不知道死吗?这是时时刻刻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有些孩子很就早经历爷爷、奶奶去世,回避没有太大意义。我倒没有考虑死是不是能让孩子阅读。
南方周末:书里的故事还涉及很多重大主题,比如亲情、友谊、成长。这是你个人的偏好,还是文学就植根于这些最重要的词汇?
王安忆:严肃的文学当然要回答一些重要的问题:生命是什么,死亡又是什么,世界是怎么样的,我们应该怎么度过光阴……都是很严肃的问题。我觉得孩子也应该慢慢学习,尤其是我们对孩子的定义,就像我在序里面写的,我大概把孩子、读者的年龄上限放在15岁。15岁的人应该读正常的文学作品了,不要读那些为他们特制的。
南方周末:一些作品有具体的历史背景,比如东西的《你不知道她有多美》以及王璞的《捉迷藏》。但孩子未必了解得那么清楚,你预期这些故事将产生什么效果?
王安忆:《你不知道她有多美》里的大地震完全是隐喻性的,景象很灿烂,是一个男孩子对女性初生的崇拜。大地震给了他一个环境,身上插满玻璃片,玻璃片亮闪闪的,不能拔,一拔就出血。它有隐喻,意象又非常美,非常璀璨;《捉迷藏》写得很好,一个晚上发生的事情非常丰富,可能值得我们不断地挖掘出来,了解不了解背景无所谓。每个孩子都会捉迷藏,她在外面躲一晚上,回到家以后,显然发生了一件比一晚没回家还要重要的事情,这就行了。你让孩子知道了,这个世界可能发生很多比他的事更加严重的事情。他现在可以明白一点,不断地再详细地明白。读书最重要的是让孩子感情丰富,让孩子更聪明,让孩子了解:世界上可能发生的事情,比实际发生的还要多。
南方周末:让孩子读令人难过的故事,是要打“预防针”,告诉他们人生会发生这些吗?
王安忆:不是人生,我们读小说,是要将感情变得丰富一点,得到一些充实。难过是感情的一种表达,如果一个人连难过都不会,还有什么感情可以享受?
南方周末:但大家通常认为该让孩子多看点世界的温存,而少让他们接触残酷的事情。
王安忆:我对残酷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有些东西是不能看的,比如说比较暴力的,我选的小说没有一篇是暴力的。暴力是外部的东西,内里感觉不舒服,感觉到难过,正好说明你的感情还没有麻木,还敏感。我觉得不能给孩子看太直接、太暴力、太血腥的东西。像电影分级一样,有些东西就是不该看的,连大人都最好不要看。我个人抵触暴力,还有比较庸俗的、鄙俗的东西。我其实是从美和丑来分辨的,特别暴力的东西首先不适合美学,我不太赞成美暴力美学。美学和道德在一起,又和我们对世界的真实认识在一起,但“真善美”这个词被大家用烂了。
南方周末:你希望这些故事能“澄澈地映照世界,明辨是非”,这里的“是非”指什么?
王安忆:其实是非不需要我来解释。有一些事情是我们绝对不能去做的,还有一些事情的对错是比较微妙的。比如苏童的《小偷》,里面的是非就很微妙,但又和感情联系在一起,有些事情不是理性告诉你不对的,而是感性告诉的。应该让孩子面临一个比较丰富的环境,再抉择。
本文节选自“南方周末”(5月25日)C21版“王安忆和《给孩子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