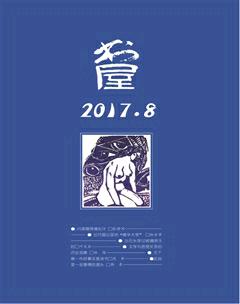道并行而不相悖
2015年2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原诗》第一辑,副题是“汉语诗学融通的可能性”。同年6月,由同济大学诗学中心编选的《中华新诗档案》第一辑,也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两部书,无心插柳地成为当年度汉语诗坛的一个事件,忝列《非非》、《非非评论》联合评选的“2015年中国诗歌界十大新闻”之一。作为一部学院派的诗学集刊,《原诗》的努力被誉为“开辟汉诗学术和研究新模式”;而旨在为全球华语诗人立此存照的《中华新诗档案》,则被称作“一部诗学视野广阔和开放的汉诗选本”。这些不虞之誉,我们从来不敢自诩,只是觉得路还很长,不能就此止步。
一晃两年过去,2017年,《原诗》第二辑将由岳麓书社推出。颇有纪念意义的是,2017年,距离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第一首新诗的1917年,正好一百年。所以,这一辑《原诗》的副题是——“古今与新旧的对话”。
说实话,在组稿中,我们并未刻意集中于某一视角和论域,而是依旧延续当初的办刊思路:辨异玄同,折衷弥缝,希望能在古今、新旧、中西之间,寻找汉语诗学的转圜余地与共生空间。尽管,这样一种看似暧昧或骑墙的诗学姿态,或为执着己见的诗人学者们所不取,但我们立意已定,且已在诗坛和学界看到了某种从容商量、平情讨论的端倪,故甚望沿着既定方向走下去,至于能否曲径通幽,柳暗花明,则只好听天由命。
众所周知,自新诗诞生以来,围绕新诗与旧诗的争论甚至争吵,就一直没有消停过,至今依然不绝于耳。对此,我们不愿意、也未必有资格充当仲裁者,更不想“意必固我”地为任何一方背书,我们想做的只是一种类似“搭桥”的工作。正如三国时的天才哲学家王弼在诠释“言意之辨”时,别出心裁地添加一“象”的范畴,遂在“言”、“意”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彼我的桥梁一样,我们愿意在“新诗”与“旧诗”的二元对立中植入一个“古诗”的视角,以求缓冲前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揆诸中国诗歌的形式发展史,恐怕谁都不会否认,在“新旧”诗泾渭分明的体式对立背后,其实还隐含着一个作为大背景的“古今”分野,拈出这一个“古”字,真可谓境界全出!你会发现,中国诗歌史完全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且相应地形成了三个传统:自上古以迄六朝是第一阶段,形成了近两千年的古诗传统;自隋、唐降及清末、民初是第二阶段,形成了一千五百年的近体诗或曰旧诗传统;而自1917年以来的整整一百年,则是第三阶段——无论你承认与否,也已形成了百年新诗的小传统。我曾在拙著《古诗写意》的自序中说:
新诗—旧诗—古诗,这是一条上行的线索。古体诗—近体诗—新体诗,这是一条下行的长河。……溯源,不是为了截流,而是为了引水——下游正是枯水期。鉴古,不是为了泥古,而是為了察今——当下不缺古样板。你会发现,古诗和新诗,其实有着某种基因的相似性,而真正的诗性,诗意,诗境从来没有古今之分。有的古诗,不分行,还是诗;有的新诗,分了行,也未必是诗。〔1〕
仔细打量汉语诗歌的这三个传统,我们会发现,这好比是一个不易觉察的“洋流循环”,新诗在近体格律诗那里找不到的“同质性”,反倒可以在古体诗中寻觅到形式或者语言上的“基因”。所不同的是,古体诗和近体诗的共同传统——音乐性——正在被新诗当作“包袱”而彻底扬弃,仅此而已。
有趣的是,本辑的好几篇文章如臧棣、董辑、李国华等人的论文,在论及新诗发展中的重要诗人和作品时,都不约而同地涉及了新诗相对于传统诗、词,其性质、前途、合法性乃至特殊性等问题。而著名旧体诗人杨启宇先生和新旧诗兼善的青年诗人朱钦运(茱萸)的两篇文章,则被放在“诗人观点”一栏中“示众”,以便突显新旧与古今对话这一议题的现实张力。类似的争论对关注诗歌的读者而言也许并不陌生,但相信本刊的视角和立场,还是能够提供一种“静观”和“圆照”的可能性。
顺便说一句,今年春节期间引发收视热潮的《中国诗词大会》,通过国家媒体的强势宣导,引起坊间热议势所必然。然而,如果以为全民诵读诗词就必然能够迎来传统诗词的春天,则显然属于高烧不退的胡话了。事实上,个别评委在本该曲终奏雅时的“荒”不择言、捉襟见肘,恰恰证明了《礼记·学记》“记问之学,不可以为人师”这一古训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性。换言之,如果传统诗词仅仅停留在口头的记诵上,而疏于教育的普及、技法的操练和现实的感怀,则终究不过是一场脂粉气浓厚的多媒体娱乐表演,只能堕入“被消费”的尴尬命运而不自知罢了。不过,这都是题外话,不宜在此展开。
关于新旧、古今的诗学博弈,我们看到的情况往往超出既定的成见。比如,新诗派因为已经占据诗坛或者当代诗歌史书写的泰半江山,故对传统诗词派并无太大偏见,只是执着于阐释新诗的合法性与现代性。在为新诗辩护的文章中,董辑的《他山有玉》一文值得注意。作者借助两位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和洛夫对于新诗的不同理解,阐明了即便在新诗人中,对于古典诗歌传统的态度也是多元的,并非千人一面,冰炭不容。如余光中在《先我而飞:诗歌选集自序》中就说:
从我笔尖潺潺泻出的蓝墨水,远以汨罗江为其上游。在民族诗歌的接力赛中,我手里这一棒是远从李白和苏轼的那头传过来的,上面似乎还留有他们的掌温,可不能在我手中落地。不过另一方面,无论在主题、诗体或是句法上,我的诗艺之中又贯串着一股外来的支流,时起时伏,交错于主流之间,或推波助澜,或反客为主。我出身于外文系,又教了二十多年英诗,从莎士比亚到丁尼生,从叶芝到佛洛斯特,那“抑扬五步格”的节奏,那倒装或穿插的句法,弥尔顿的功架,华兹华斯的旷远,济兹的精致,惠特曼的浩然,早已渗入了我的感性尤其是听觉的深处。同时我又译过将近两百首英美作品,那锻炼的功夫,说得文些,好像是在临帖,说得武些,简直就是用中文作兵器,天天跟那些西方武士近身搏斗一般,总会学来几招管用的吧。〔2〕
余光中认为:“古典的影响是承继,但必须夺胎换骨。西洋的影响是观摩,但必须取舍有方。”
相比于余光中的左右逢源、古今都不得罪,洛夫则认为,新诗难以格律化,但是新诗自有其形式,这种形式就是“一诗一形式”,新诗是形式和内容不可分割的一次性艺术创作,其形式因素很难被反复使用和上升、定型为“格律”。他说:
我一向钟情于自由诗,我以为一个作品的偶然性是决定其艺术性的重大因素之一,而自由诗的偶然性远远大过格律诗。格律当然也有他的优点,否则不可能流传数千年,但不可否认的是每种诗体用久了势必趋于僵化,不但内在情感变得陈腐,对事物感受的方式也日渐机械化。抒情语言更是带有浓烈的樟脑味。一般人仍留恋旧诗,是出于心理的固定反应,读起来和写起来都很方便,就像买鞋子,因有固定的型号,穿上合脚就行了。韵文时代已一去不返,用散文体写格律诗,读起来怪别扭的。语体诗还要押韵,感觉十分做作,很不自然。
不可否认,任何一首诗都有它的形式,它被创作出来的那个样子就是它的形式,每首诗本身就是一种形式,它并不排斥中国韵味,它同样可以具有汉语诗歌的优良品质。格律本身是一个机械性的载体,而一首诗的存在是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割的有机体。我赞成诗应有形式感,但那不是格律,我也承认典律的重要性,但并不意味典律必须依附于某种固定的形式。〔3〕
应该说,洛夫的“一诗一形式”和“诗歌偶然性”的论说,非常具有理论上的革命意义。其革命性并非在于反对传统的格律和既定的程式化,而在于,他为每一首诗赋予了新的生命和独特意义。洛夫甚至说,“诗,永远是一种语言的破坏与重建,一重新形式的发现”。相比于旧体诗只有依赖于格律和形式才能存活并获得尊严这一事实,洛夫的观点不仅在空间维度上直面当下,而且也在时间维度上拥抱了未来。
无独有偶,在废名的《谈新诗》一文中,也提到了“偶然的”問题:
让我说一句公平话,而且替中国的新诗作一个总评判,像郭沫若的《夕暮》,是新诗的杰作,如果中国的新诗只准我选一首,我只好选它,因为它是天然的,是偶然的,是整个的不是零星的,比我的诗却又容易与人人接近,故我取它而不取我自己的诗,我的诗也因为是天然的,是偶然的,是整个的不是零星的,故又较卞之琳、林庚、冯至的任何诗为完全了。〔4〕
请注意,废名说新诗“是天然的,是偶然的,是整个的不是零星的”,无意中道出了新诗乍一出世,带给世人的新鲜感和错愕感。废名还把新诗的创作喻为“生命的偶尔的冲击”,这颇类似于陆游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相比之下,旧诗因为必须“习得”,即便“偶得”之后也必须经过格律的严格检验,不得漫漶于传统的河床之外,自然就成了“应然的,必须的,是全体的一部分而非整个的”了。
可见,至少在新诗人看来,新诗之所谓“新”,本来就是要摆脱某种既定的模式,比如句式、格律等的束缚,尽情地、自由地展开生命和语言的偶然之舞。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诗”之“新”,并非仅仅是时间上或诗歌体式上的一个概念,更多的恐怕还是文化精神上或者说诗歌生命上的一种“新变”追求。这在中外文学史和诗歌史的宏观视野注视下,似乎是一个十分常见而无须自证其合法性的现象。
然而,新诗是否就应该罔顾母语的千年传统,一如脱缰的野马一样狂顾顿缨、一往无前了呢?百年新诗的实验现场到底如何?如果不是借助中小学语文课本以及现代大学中文系教科书的强势渗透,新诗的所谓经典作品,又有多少真正堪称经典而无愧色?特别是,新诗占据学术的庙堂之高,却在江湖之远上应者寥寥,新诗的各种活动、刊物、诗人等也越来越成为一种不以职业为诉求的特殊“专业”,特别是,新诗人们在精英品格和自我期许上,倒是和旧体诗词的作者们同样“曲高和寡”。这些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无疑值得深入探讨。
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现代史上作为政治人物被聚焦的汪精卫,其实也是一位十分重要的旧体诗人。他1923年写给胡适的一封信,涉及新旧诗之争的段落,读之令人眼前一亮。汪精卫说:
适之先生:
接到了你的信和几首诗,读了几遍,觉得极有趣味。
到底是我没有读新体诗的习惯呢,还是新体诗另是一种好玩的东西呢,抑或是两样都有呢,这些疑问,还是梗在我的心头。
只是我还有一个见解,我以为花样是层出不穷的,新花样出来,旧花样仍然存在,谁也替不了谁,例如曲替不了词,词替不了诗,故此我和那绝对主张旧诗体仇视新体诗的人,固然不对,但是对于那些绝对主张新体诗抹杀旧体诗的人,也觉得太过……
作为编者,我不能不说,汪精卫的话与我心有戚戚焉。让人略感遗憾的是,时过将近百年,今天的诗人们依然没有走出“新旧古今”的形式陷阱和话语魔障。孔子说:“过犹不及。”《礼记·中庸》亦有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无论是新诗诗人还是传统诗词作者,于此皆当有所反思。新诗也好,旧诗也罢,虽同为语言的艺术,却各有其写作宗旨、审美标准与受众期待,正如流行歌曲之与京剧昆曲,各行其道、各遵其理可也,如果各自强分轩轾,甚至以己所长轻人所短,甚至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恕我直言,此皆非诗人应该有的大心量与大情怀。
还是用余光中的话结束这篇小文吧!他说:
古典的影响是承继,但必须夺胎换骨。西洋的影响是观摩,但必须取舍有方。多个十多年前我早就醒悟,株守传统最多成为孝子,一味西化必然沦为浪子,不过浪子若能回头,就有希望调和古今,贯串中外,做一个真有出息的子孙。学了西方的冶金术,还得回来开自己的金矿。〔5〕
“调和古今,贯串中外,做一个真有出息的子孙。”诚哉是言也!
编完这本集刊,再次感叹光阴的无情。两年光阴倏忽而逝,忙忙碌碌的我,只能交出这么一份微薄的答卷。感谢同济大学诗学研究中心的顾问团队,感谢《原诗》的新老作者,更感谢因为种种缘分而阅读过《原诗》的读者朋友们,没有你们的支持,我们无法走到今天。
(刘强主编:《原诗》第二辑,岳麓书社即出)
注释:
〔1〕刘强:《古诗写意》,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3页。
〔2〕余光中:《先我而飞:诗歌选集自序》,转引自《余光中诗歌选集》第一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三页。
〔3〕《洛夫谈诗:有关诗美学暨人文哲思之访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61页。
〔4〕废名:《谈新诗》,转引自《废名集》第四卷,第1822页。
〔5〕《先我而飞:诗歌选集自序》,《余光中诗歌选集》第一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旧诗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