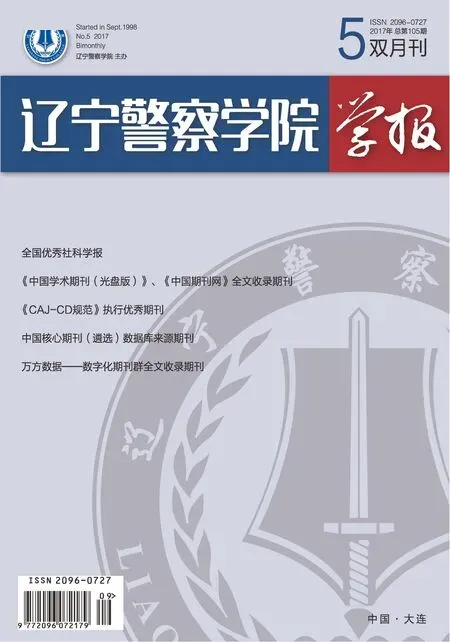我国扒窃犯罪的现状及精细化治理
方海涛
(重庆 江北区人民检察院, 重庆 400025)
我国扒窃犯罪的现状及精细化治理
方海涛
(重庆 江北区人民检察院, 重庆 400025)
通过对京津沪渝四地 112件扒窃犯罪案例的分析,发现目前我国扒窃犯罪呈现出犯罪地点稳定、犯罪职业化倾向严重、犯罪成本偏低等特征和问题,在国家短期内无法通过修改刑事政策、提供就业等宏观措施治理扒窃犯罪的情况下,通过对犯罪热点的准确预测、公开犯罪地图、开展地点警务、制造犯罪障碍等措施进行扒窃犯罪的精细化治理,从而将扒窃犯罪控制在人们所能容忍的范围之内,应是扒窃犯罪治理的必然选择。
精细化治理;犯罪热点地图;环境预防;地点警务
犯罪的精细化治理,是相对于整顿市场秩序、完善社会法制等宏观治理而言的微观治理。精细化治理从社会局部微观层面设计操作性、针对性较强的治理措施,比如对特定人员、场所开展针对性的防控,对重点区域加强警察巡逻、视频监控等,实现对特定单位、特定区域犯罪的快速、有效治理。精细化治理虽然属于微观治理层面,但并不等同于微观治理,微观治理是相对于宏观治理的治理模式,其范围更宽更广。目前扒窃犯罪在全国各地都呈现高发趋势,并且表现出犯罪职业化倾向,在国家短期内无法通过修改刑事政策、创造就业、完善监狱改造制度等有效治理的情况下,如何通过精细化治理,解决当前扒窃犯罪的高发现状,让扒窃犯罪控制在人们所能容忍的范围之内,不仅是专家、学者,更是基层司法实务人员所应思考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京津沪渝四市112件扒窃案例的分析,发现目前我国扒窃犯罪呈现的特征和问题,借鉴西方犯罪精细化治理理论,提出我国扒窃犯罪精细化治理的疏浅建议。
一、我国目前扒窃犯罪的主要特征和问题
扒窃犯罪主要集中在人流量较大的市区,因此本文所选研究对象来源于京津沪渝四市在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上公开的扒窃案例。笔者通过查询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从京津沪渝四市共计找到扒窃犯罪案件起诉书 113份(件)、115人,①其中两份起诉书为一案两人,为便于计算,笔者选取其中 112份(件)、112人作为研究样本,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地点、前科情况、文化程度、工作单位等方面进行统计和分析,以期发现我国目前扒窃犯罪的主要特征和问题。
(一)司法案例反映出的基本情况
1.从扒窃犯罪的发生地点来看,发生在城市街面、路口的案件有 30件,占比 27%;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案件有 25件,占比 22%;发生在公共交通设施的案件有 20件,占比 18%;发生在网吧、医院的案件有 7件,占比 6%;发生在农贸市场的案件有 13件,占比 12%;发生在商场内部的案件有 12件,占比 11%;发生在其他地方的案件有5件,占比4%。(具体见表1所示)
2.从犯罪嫌疑人的前科情况来看,无前科人员有22人;具有行政处罚前科的人员有6人;具有犯罪前科的人员有 84人,其中,只具有盗窃前科的人员有 72人(具有 1次盗窃前科的人员有22人,具有2次盗窃前科的人员有16人,具有 3-5次盗窃前科的人员有 24人,具有 6-9次盗窃前科的人员有 9人,具有10次及以上盗窃前科的人员有 1人),具有盗窃和其他犯罪前科的人员有12人(前科总数合计5次以下的有7人,5次及以上的有5人)。(具体见表2所示)

表1 犯罪地点情况统计

表2 犯罪前科情况统计
3.从文化程度和就业情况来看,文盲半文盲 人员有20人;小学文化程度人员有54人;初中文化程度人员有 28人;高中、中专文化程度人员有9人;大学文化程度人员有1人。再从就业情况来看,农业人员有 44人;城市无业人员有66人;具有工作单位的人员有2人。(具体见表3所示)
4.从前科与本次犯罪的时间间隔来看,本次犯罪属于漏罪的有5人;间隔时间在6个月以下的有 24人;7个月以上 1年以下(不含 1年)的有 10人;1年以上 5年以下(含 5年)的有41人;5年以上的有4人。(具体见表4所示)

表3 文化程度和就业情况统计

表4 前科情况统计
(二)司法案例所反映的扒窃犯罪之特点和问题
第一,犯罪地点、热点地区较为稳定。首先,起诉书反映出了扒窃犯罪的一般发生地点,即人流量较大的街面、路口、公共交通工具上。这很容易理解,人流量较大的区域,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内,被害人的注意力被集中到其他地方,对自身财物保管的注意力反而降低,为犯罪分子的扒窃制造了条件,同时人流量较大也便于犯罪分子转移赃物、找到更多受害人等等。
其次,起诉书还反映出一个城市扒窃犯罪的热点地区,甚至反映出同一犯罪人员作案区域的稳定性特征。本文虽然只有112份起诉书作为研究对象,但这些起诉书也反映出了京津沪渝的部分扒窃犯罪热点地区,比如通过多份起诉书可以看到重庆市某区的 S公交站就是经常发生扒窃犯罪的热点地区。虽然从前科材料中无法得知犯罪嫌疑人之前的犯罪地点,但多次被同一法院判刑的事实,以及五名在火车站实施扒窃的犯罪嫌疑人都具有多次被铁路运输法院判刑的事实,证明了同一犯罪人员扒窃犯罪区域的稳定性特征,为何会出现这种看似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在于犯罪分子从一个自己熟悉的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地点不仅需要十分努力,还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另一方面在于犯罪分子并不认为所有地方都拥有同样的作案机会。[1]
第二,扒窃犯罪存在职业化倾向。扒窃犯罪人员大多具有犯罪前科,这点不难理解,毕竟扒窃犯罪属于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犯罪,没有长期的犯罪历练很难实施该种犯罪。因此,在112人中发现 84人具有盗窃犯罪前科不足为奇,但这84人中54.8%的人具有3次以上犯罪前科,11.9%的人具有6次以上犯罪前科却有些出人意料,并且34.5%的人员是在刑罚执行完毕后六个月内实施的本次犯罪,最短的时间间隔不足一个月,这些数据综合起来表明很多犯罪嫌疑人常年以扒窃犯罪为业,扒窃犯罪出现了职业化的发展趋势。造成扒窃犯罪职业化的原因,可能有扒窃犯罪收益大代价小的因素,也跟一些犯罪人员好逸恶劳,自甘堕落有关。扒窃犯罪的职业化倾向及其原因说明了国家通过提供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修改刑事政策等宏观措施治理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第三,扒窃犯罪的犯罪成本较低。扒窃犯罪成本较低一方面表现在扒窃犯罪不易被抓获,比如案例中的犯罪嫌疑人李某某(无业),具有 9次盗窃犯罪前科,最近一次前科发生在一年前,很难想象李某某在本案发生前的一年内没有实施任何扒窃犯罪,可能更合理的解释是在这一年内李某某从未失手被抓,对李某某而言扒窃被抓与成功相比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扒窃犯罪成本较低的另一方面表现为判刑较轻,司法实践中扒窃犯罪的刑期基本上集中在六个月至一年六个月之间,即便具有多次犯罪前科,也很难获得重刑。目前盗窃犯罪在我国整体上呈现出轻刑化现象,最高人民法院 2014年发布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不仅总体上规定“被告人如实供述有助于定案的,可以减轻基准刑的20%”,针对盗窃罪时还具体规定,犯罪数额达到“数额较大”起点的,两年内三次盗窃的,或者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可以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重庆市将这一起点确定在“三个月拘役至六个月有期徒刑”之间),而对于前科罪犯的加重处罚,量刑指导意见则要求“综合考虑前科的性质、时间间隔长短、次数、处罚轻重等情况,可以增加基准刑的10%”。
此外,司法案例还反映出犯罪嫌疑人大都没有固定工作、文化程度较低等特点,司法案例虽未反映但事实上这些犯罪嫌疑人还普遍存在着好逸恶劳、不务正业、夫妻离异、吸毒、嗜赌、患有艾滋病、被家人嫌弃、自甘堕落等问题。如果犯罪嫌疑人具有稳定的工作、完整的家庭,必然会大大降低他们再次犯罪的可能,但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犯罪嫌疑人的自身问题,是国家、社会不能解决或者很难帮助(短期内)解决的问题,这属于犯罪治理的宏观范畴,本文不作阐述,本文的重点是如何根据扒窃犯罪反映出的特点和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精细化治理。
二、犯罪精细化治理的主要内容
国内关于犯罪精细化治理的文献较少,本文对犯罪精细化治理的介绍主要基于国外的理论和实践。犯罪精细化治理的内容包括哪些?有学者认为主要包括环境预防、地点警务、犯罪预测和第三方警务四个方面。[2]这四个方面都强调对犯罪的事前预防,但犯罪精细化治理不能只有事前预防,还应包括事后的刑事制裁,特别是在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刑事制裁可能会是犯罪精细化治理的重中之重。就犯罪事前预防的四个方面而言,不论是环境预防还是地点警务,都需要基于对犯罪的准确预测,因此,笔者认为将犯罪预测放在环境预防和地点警务中一并阐述即可。刑事制裁在任何法治国家都存在,而第三方警务并不十分适合扒窃犯罪的治理,因此本文着重对环境预防和地点警务给予介绍。
(一)环境预防
环境预防的基本理念是,既然不能消灭犯罪,不如通过环境的改变来减少犯罪的发生。大量日常经验证明,外部环境与某些犯罪的发生有着密切联系,比如在人多的场所容易发生扒窃,在脏乱差的地方容易滋生毁坏财物犯罪。美国犯罪学家、建筑师奥斯卡·纽曼在 60年代通过观察发现,华盛顿两个临近街区的建筑因设计不同而造成两个街区居住环境的截然不同,进而提出了防御空间理论。防御空间就是一种本身具有控制犯罪的自然属性的建筑设计模式,通过特定的建设设计,对潜在的犯罪人的心理产生抑制作用,从而使其不敢在这一区域犯罪。[3]具体措施包括对小区设置围墙、配置保安、出入口安装监控等等,目的是创造犯罪障碍,让潜在的犯罪人员望而却步。除了奥斯卡·纽曼之外,美国 20年代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帕克(Robert park)、4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学者什奥(Clifford Shaw)和麦凯(Henry McKay)、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伍德(Elizabeth Wood)、70年代的布兰汀汉姆(Brantingham)夫妇都对街区和犯罪的关系进行过实证研究,这些研究成果直接促使 70年代以来美国在公共安全领域“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的实施。[4]
环境预防不仅适用于住宅小区,同样适用于街道、楼市、重点机关单位、学校等等,比如在人流量较大的区域增加监控摄像头,在晚上加大路灯的亮度和密度等,都能让潜在犯罪人员意识到犯罪成本和风险的加大,进而放弃犯罪意图。
(二)地点警务
地点警务顾名思义就是警察的犯罪治理工作围绕地点而非人展开,具体措施包括对特定地点或单位加大警力执勤、加强巡逻等等。支持地点警务的依据是对犯罪热点的统计。20世纪 80年代谢尔曼审查了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的报警地址,发现一年内该市50%的犯罪报警电话集中在约 3.5%的地方。2004年威斯勃德(David Weisburd)和同事布什伟等人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且发现犯罪集中在一些特定地区能够保持长达 14年的稳定。[5]单勇博士对我国 H市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在该市S区10%的路段上集中了全区67.35%的犯罪;在该市X区的5%网格区域内集中了56.31%的犯罪,10%的网格区域内集中了 78.84%的犯罪(一个网格区域的面积约为 1.36平方公里)。就犯罪热点的稳定性而言,单勇博士通过GIS(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对犯罪密度进行了分析,得出盗窃犯罪热点在省会城市中心区四年中保持相对稳定,在地级市沿海郊区十年中保持相对稳定的结论。[6]实证研究揭示了犯罪热点的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一地方会一直成为犯罪热点,特别是随着人们意识到犯罪热点并加强戒备后,犯罪热点会呈现一定程度的弱化甚至消失,但这并不否定针对犯罪热点地区开展地点警务的意义,因为在外部环境很难改变的情况下,犯罪热点可能会长期存在,比如人流量较大的商业区,可能一直会是扒窃犯罪的热点地区。
犯罪热点的存在为地点警务的开展创造了条件,根据犯罪热点有针对性地开展警务活动,可以改变以往警察与犯罪分子较量中的被动局面,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犯罪热点的确定除了个人的经验判断外,更依赖于对犯罪数据的统计分析,当前以信息技术为支持的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构建,应加强基于GIS的犯罪热点地图绘制,实现犯罪治理的信息化,为地点警务的开展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
三、我国扒窃犯罪精细化治理的路径
(一)扒窃犯罪的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就是对扒窃犯罪生成的各种社会因素的治理,通过犯罪预测和环境预防以减少扒窃犯罪发生的机会,从而实现扒窃犯罪的治理。扒窃犯罪的社会治理强调事前对扒窃犯罪的预测和社会因素的改造,从源头上堵住扒窃犯罪的发生,社会治理是一种对潜在被害人和犯罪人员都无害的治理模式。我国扒窃犯罪的社会治理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树立犯罪预防的治理理念。我国传统犯罪治理强调预防与打击并重,但司法实践中却又轻预防重打击,从扒窃犯罪嫌疑人的归案情况可见一斑。扒窃犯罪嫌疑人的归案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由被害人扭送归案,另一种是被反扒民警当场抓获归案。就后者而言,反扒民警是在目睹整个扒窃犯罪后将犯罪嫌疑人抓获,而非在犯罪伊始就及时制止犯罪的发生。刑事打击固然能够威慑犯罪,特别是在社会治安状况较差的时期,通过严刑峻法能够快速遏制犯罪高发势头,但犯罪的发生除了犯罪人的生理因素外,还跟很多外在因素有关,比如脏乱差或者无序状态都会对人的违法、犯罪产生莫大的诱惑,国外学者针对“破窗理论”的试验充分证明了外部环境与犯罪的关系。因此,树立犯罪预防理念,通过事前预防来降低扒窃犯罪的发生,也应是我国扒窃犯罪治理的重要途径。对处于办案考核压力之下的一线民警来说,树立扒窃犯罪预防理念可能并不容易,但作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策者应当树立扒窃犯罪预防的理念,这不仅因为犯罪预防是从源头上减少犯罪的生成,更是扒窃犯罪长期有效治理的根本途径。
2.开展扒窃犯罪的精准化预测。犯罪预测包括个人经验预测和数据分析预测,比如反扒民警有目的地选择反扒地点,就是个人对扒窃犯罪的经验预测;公安机关定期对辖区内犯罪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评判某一时期高发犯罪的种类以及原因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就是对犯罪数据分析预测的运用。尽管犯罪预测在我国存在已久,但犯罪预测的价值目前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比如对犯罪数据分析的主要目的是供领导了解辖区治安状况,而非为了指导犯罪治理,同时犯罪预测的精细化、专业化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开展扒窃犯罪精细化治理,必须重视扒窃犯罪的预测工作,只有准确预测扒窃犯罪,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展犯罪预防工作。犯罪预测的内容包括扒窃犯罪的热点地区、高发时段、引发扒窃犯罪的因素等等,开展扒窃犯罪预测并非简单的数据统计,而是通过对犯罪数据的专业化分析发现扒窃犯罪的一般特征,找出扒窃犯罪高发的原因并提出解决的对策,为决策者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为一线民警的反扒工作提供指导。
3.灵活公开扒窃犯罪热点地图。制作犯罪热点地图是犯罪预测的结果,通过犯罪地图能够更加清晰地反映犯罪的具体情况,不少法治较为发达的国家已经实现犯罪地图的社会公开,普通民众可以直接查询了解自己所在社区的治安状况。比如美国民众通过 Crime Reports 网站可以直接在线查询各区域、各时段的犯罪信息,韩国民众也可以通过“国民生活安全地图”了解自己社区及周边的治安情况。[7]是否需要公开犯罪地图,存在较大的争议。公开犯罪地图,能够提高民众对犯罪的警惕,但也可能造成民众对犯罪的恐慌,甚至可能会不利于当地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比如犯罪地图显示重庆市观音桥商圈属于扒窃犯罪的高发区,势必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去观音桥商圈消费的信心。但如果一味地讳疾忌医又必然不利于对犯罪的治理,比如国外一些轰动一时的连环犯罪,都是因为政府没有及时公开犯罪信息而使后来的受害者未能采取足够的防范措施所致。因此,公开扒窃犯罪热点地图具有绝对的必要性,它可以提醒进入这些区域的民众提高警惕,从而降低扒窃犯罪的发生。考虑到我国的文化传统、民众的法律意识,不宜直接赤裸裸地给某地贴身扒窃犯罪热点地区的标签,但可以在这些地区通过公益广告的形式,间接发布扒窃热点地图,比如可以在扒窃犯罪热点地区的显著位置张贴反扒公益广告、宣传标语、卡通图片来提醒民众对扒窃犯罪的警惕。
4.制造扒窃犯罪障碍。扒窃犯罪预防工作主要是制造犯罪障碍,让潜在的犯罪分子意识到犯罪的难度和风险,进而放弃犯罪。制造扒窃犯罪障碍,一是可以通过加强犯罪热点区域的视频监控,尽量不留死角,并且在显著位置标明“视频监控中”,让潜在的扒窃人员就象想在路边乱停车的驾驶员一样,忐忑之中理性选择自己的行为。二是加强相关区域警察和安保人员的定点执勤和巡逻力度,提高扒窃热点地区的见警率,②增加犯罪后被抓、被判刑的可能性,让潜在的犯罪分子找不到可以轻易实施犯罪的“僻静角落”。三是开展扒窃热点地区的环境整治,通过清理乱涂乱画、乱丢垃圾、占道经营等乱象,创造规矩有序的环境从而消除环境对潜在扒窃犯罪人员“在那里可以为所欲为”的心理暗示。
(二)扒窃犯罪的刑罚治理
扒窃犯罪的刑罚治理,是指国家司法机关通过刑罚对扒窃犯罪的治理。刑罚治理的优点在于它是最容易兑现的犯罪治理方式,因为各国大都具有完整的司法体系、专职的司法人员来执行刑罚。刑罚治理的不足在于刑罚的威慑作用只对有稳定工作、家庭或者事业有成的理性人有效,对他们来说,刑罚对他们带来的后果(比如工作的丧失、家庭破碎)是他们所无法承受的。而现实中触犯刑律的大都是些穷困潦倒、好逸恶劳、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的群体,对他们来说犯罪是自己获得成功和收获的捷径,刑罚只是为此付出的代价而已,如果他们认为犯罪的收获大于刑罚的代价时,刑罚对他们的威慑作用将荡然无存。因此,刑罚作为治理犯罪的杀手锏,一旦设置就应当体现出其应有的威慑作用,要让犯罪分子认识到犯罪永远不会成为他们人生的康庄大道。
我国扒窃犯罪的轻刑化,一方面与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关,另一方面是有限的司法资源与解决司法纠纷的社会需求之间的张力愈发明显,把有限的司法资源用在严重侵犯人民群众人身、财产的重大案件势在必行。但扒窃犯罪的高涨态势,以及扒窃犯罪职业化倾向,让我们意识到重拳治理扒窃犯罪的必要。如何治理惯犯,美国在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三振出局”的刑事政策,“三振出局”主要针对严重的刑事犯罪,但在美国很多州判处一年以上监禁的犯罪就被视为重罪,因此“三振出局”对我国扒窃犯罪的重拳治理也有借鉴之处。当然,我国对扒窃犯罪的处罚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可以判处 25年的监禁或者无期徒刑,但可以明显增加扒窃惯犯的量刑幅度,突显刑罚的威慑性。目前司法实践中,无论扒窃犯罪人员具有多少次前科,对其量刑具有影响意义的只有最近一次前科,因为这次前科将决定着被告人是否属于累犯,但即便属于累犯,只要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对其从轻处罚的幅度足以抵消累犯所增加的刑期,更有甚者有些省市为扒窃犯罪设置了入罪门槛,扒窃未达一定犯罪金额(比如500元)的不以犯罪论处,更加纵容了扒窃犯罪再次发生的可能。
鉴于此,在短期内刑法不易修改的情况下,笔者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应修订量刑指导意见中有关盗窃罪的规定,对于没有犯罪前科的扒窃罪犯可以判处缓刑,③避免短期监禁带来的诸如罪犯之间相互感染、犯罪人身份更加自我标签化等后果;对具有盗窃前科罪犯的起点刑可规定为一年,具有三次以上盗窃前科的起点刑可规定为二年,具有五次以上的盗窃前科的便可认为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在三年以上刑期量刑。虽然刑罚治理并非最佳的治理方式,但选择了刑罚治理就应当体现其效果性,让追求扒窃犯罪职业化的人在犯罪时“三思而行”。
四、结 语
扒窃犯罪的最终有效治理依赖于市场经济秩序、法治环境、教育改造措施、就业社会保障等等的完善,这是个宏大而艰巨的工程,短期内很难实现。在当前有限的司法资源与解决司法纠纷的社会需求之间的张力愈发明显的情况下,如何制定具体可行的扒窃治理措施,实现最小的司法成本换取最大的治理收益,应是我们思考的重点。扒窃犯罪的精细化治理注重对犯罪的预防,强调从源头上消除犯罪产生的条件,不仅降低了犯罪,而且减少甚至挽救了犯罪人员,应该成为我国扒窃犯罪长期治理的根本路径,同时在其他宏观治理措施短期内很难实现的情况下,精细化治理应成为目前扒窃犯罪治理的首要选择。
注 释:
①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http://www.ajxxgk.jc y.gov.cn/html/index.html,访问时间2017年1月8日至10日。该网站于2014年10月正式上线运行,目前还未能实现检察机关所有法律文书的公开,因此从京津沪渝四市只找到 113件扒窃案件。这 113个案件可能在所有扒窃类犯罪中的占比重并不是很大,但由于本文只限于对扒窃犯罪内部特征的统计分析,并不涉及与其他犯罪的数量比较,因此,笔者认为 113件扒窃案件足以能够全面反映京津沪渝四地(或者说是全国)目前扒窃犯罪的一般特征。
②本文写作期间正值 2017年春运,这段时间有关火车站民警便衣反扒的报道屡见报端。反扒民警的辛苦付出自然值得赞扬和肯定,但笔者认为在开展便衣反扒的同时,一并开展制服警察的巡逻排查,或许能够更好地威慑扒窃犯罪,更加周全地保护旅客的人身财产安全。
③司法实践中也确实存在一些犯罪分子属于首次犯罪,比如在网吧看见他人睡着,便临时起意将他人口袋里的苹果手机偷走,这些犯罪人员如果到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判处缓刑必然更加有利于他们改过自新。但笔者并不赞同作不予起诉或者免于刑事处罚处理,一方面我国目前并不具有成熟的社区矫正制度,对于犯罪人员除了刑罚并无其他更好的处罚措施;另一方面很多人走向犯罪的道路,主要原因就在于刚开始犯罪时没有被发现或者未得到应有的惩处,在这些犯罪人员心理上造成“一次成功便可次次成功”或者“只要认罪赔偿就没事”的假象,最终走向犯罪的深渊。
[1]大卫.威斯勃德.基于地点的警务(上)[J].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11(4):91.
[2]单 勇,阮丹微,李 欣.犯罪治理精细化:国外经验与理论启示[J].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16(3):75.
[3]刘广三.犯罪控制宏论[J].法学评论,2008(5):31.
[4]李本森.破窗理论与美国的犯罪控制[J].中国社会科学,2010(5):156.
[5]大卫.威斯勃德.基于地点的警务(上)[J].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11(4):89.
[6]单 勇.犯罪热点成因:基于空间相关性的解释[J].中国法学,2016(2):286-289.
[7]单 勇.犯罪地图的公开[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3):113.
(责任编辑:李 刚)
The State and Elaborating Governance of Pick-pocketing Crime in Our Country
FANG Hai-tao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Jiangbei District, Chongqing, Chongqing 400025, China)
Through the an alysis o f 1 12 pi ck-pocketing c rime cases occ urred in Be ijing, Tianjin, Shanghai and Chongq ing, we found features of pick-pocketing: fixed site,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lo w cost. Since we can’t take measures such as creating jobs, revising the c riminal policy to get an effective governance in short time, the way through the accurate prediction of crime, opening the hot spots map, carrying out site policing, creating barriers to crime to govern pick-pocketing crime, thus pick-pocketing crime will be controlled in the range of people can tolerate, will be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pick-pocketing crime control.
elaborating governance; Hotspots M ap o f crim e; environment p reventing; lo cation policing
D035.34
A
2096-0727(2017)05 -0098-08
2017-05-04
方海涛(1983-),男,河南确山人,主任科员,硕士。研究方向:刑事法学。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2016年度重点课题“适用‘两高’《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疑难问题研究”(CQJCY2016B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