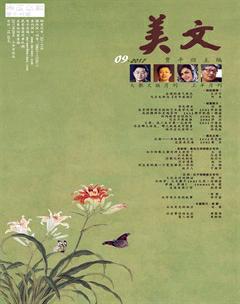北海
李光胜
传说,北海的珍珠是一位善良美丽的人鱼的眼泪。很久以前,人鱼公主在海上救了一位青年,后来两人产生了感情并结成了夫妻。县官渴望把夜明珠偷走,为此杀害了人鱼公主的丈夫。人鱼公主非常思念丈夫,她手捧夜明珠,泪如泉涌,涌出的泪水化作颗颗晶莹的珍珠回落大海。人鱼公主真挚的情感感动了海中的珠贝,此后每当人鱼公主滴下晶莹的泪滴,珠贝就吞下,使泪滴变成了珍珠。

“传说”是一切领地灵魂的永恒表象。若一个人不知道他所在地区的传说,那么他就不能理解自身所处脚下土地的唯一性,也就不知道自己的足迹下曾经还有属于其他人的足迹了,更不能知道这些足迹之下还有土地本身的深刻痕迹。这类人没能发现自身属于一个比自己更深奥更广大的境界,因此他们遗憾地丧失了最真挚的情感 —— 被自然所包围环绕的归属感。“传说”使我们与眼前的实体重新连接,就像那些在童年时代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经验知识可以让我们与前者更亲近。实际上,更令人惊讶的是有时候人能通过印刷在景色上——那些活着的“传说”与已被不断流动的忙碌生活而越甩越远的自我之根进行重新连接。
北海作为以前的海上丝绸之路,直到今天还保留这个命运,还能使人与全世界重连接,甚至与自身内在世界重连接。
然而,传说不是唯一能够转达某个地区精神的方法。传说只不过是对不可言的故事的一种间接的体现,所以不知道它的人还能够去理解它所包含的奥秘。当某个人到达一个新的地方,尽管都是沉默的处女地,但他可以感受到本地精神的存在,可以心照不宣陷入风景中无形痕迹的故事里。当人在陌生的景色面前时,对其的神秘感成为一种温和的吸引力,于是,不禁用自身本性的材料来补充对眼前事物的无知,不自觉地用自身回忆和感受给景色的模糊外形涂上颜色加以限定。这样,我们可以凭自己的传记重建眼前风景的传说。所以可以说,当面新鲜的景色,也是当面自身。由于此,我这里叙述的并不是历史中的事情,因为历史无法传达北海人的故事那深远含义,也不是一般地理学那样仔细精确的描述,因为前者无法传达北海生态环境独一无二的魅力和生命力。
从另一方面看,北海具有一种独特的地理特性,让我联想到一种对应的人生地理。这样,瞥见了北海后,我心里形成了一种关于人与地以及人與海混在一起的马赛克。
自从第一次踏上北海的土地,我就发现了这一点。那夜,天上落下轻柔的雨,我对面有一座桥,上边装饰着多种颜色的霓虹灯,桥下的水面上闪耀彩虹似的光,泊在岸边的小船安静地做着梦。夜渐深,城市里的所有街道越发显得明亮了,与此相反,所有人在黑暗的屋子里睡觉。
北海由水和土所成,不仅是作为海港被建起来,还是有着许多犹如养育身体的脉络般的河流所穿过的城市,你瞧,城市到处都介质在水土之间,若往内看就有桥梁,若向外望就有港口。北海的桥梁,有的是比较简朴,如躺着的梯子,有的设计较抽象很难形容,还有的是弯曲如过山车的。由此看,确实可以把北海看作一座巨大的桥。正如,生活就好比是人必须渡过的一座无形的桥,人总是在从此岸到彼岸的过程中,无法停留在其中。
所以,北海独有的特性部分在于使原来遥远的世界连接起来,大海跟大陆,火山与河流,西方和东方,古代同现代。这种连接,正好是人类的根本需求之一,虽然人人都寻找自由,但或许更渴望的是那种出于与别人关联而产生的归属感,哪怕为此可能会失去珍贵的自由。在北海人人都身处在被“连接”当中,要么与大自然连接,要么是与人类连接,似乎这种“连接”的能力是城市本身所拥有的特殊力量。
当然,每个领地都有其各自的独特魅力,比如浪漫的巴黎有埃菲尔铁塔,久远的北京有故宫,等等;但是,很少有像北海这般把如此多宝物聚集起来的宝地,甚至如此多样的因素协调地结合在了一起。这时候,我不禁想起来,在十八世纪,古巴的哈瓦那港口是作为美洲中所有西班牙属殖民地欲往西班牙航行的必要转折点,自然特别多的财物堆积在城市里,结果在那个时期中经常被海盗攻击。迄今,国家的财物远远不如那个时代,但还能看到那些用来抵抗海盗的古老又坚固的大炮。在涠洲岛的鳄鱼岭上,我竟然看到了一个很小的大炮,围绕着大炮有各种各样的高树和有色的花朵,甚至大炮的青铜变成植物似的绿装,似乎被大自然彻底打败的样子。可见,北海不吝啬地抵抗旅客的冒险精神,反而用自身拥有的别样自然来吸引他。难怪,当我离开北海时,以为自己得到了一点什么,或者说自己被充实了,犹如在精神上夺走宝贵财物的海盗。
第二天我们坐船向涠洲岛航行。上岸的时候,有柔柔细雨和柔风欢迎我们,灰色的天空犹如婚礼上盖新娘脸的面纱,羞怯地既掩饰着又展开着其壮丽的景象。那天涠洲岛显示出一种引诱游客去仰望的隐秘魅力。涠洲岛的美,似乎是创造者的杰作,具有一种微妙的无限特性,通过心灵上的亲密关联来静静地揭开自身,这样渐渐地被观察者发现。涠洲岛虽只有六公里的长度,但在岛上每一个角落中都藏着值得观赏一辈子的自然奇迹。
后来,我们到了一个小湖边,那里路比较狭窄,所以大部分人换车到酒店。我却决定走路,这样能够更好地观赏周围的风景。周边有些灌木以及其他热带水果树,如番木瓜,但我印象中没有特别高的树,主要有香蕉树蔓延于全岛各地,甚至在旅馆里随时都放着香蕉可以吃。估计涠洲岛的土壤不深,其下面该有火山石。令人惊讶的是,路边所看到的东西,朴素的房子,院子里的猪栏,到处跑着的鸡,遍布各地的草木,尤其是香蕉树,甚至潮湿的粉红土地,这一切都让我感觉到自己突然被瞬间移动到古巴的农村里。没想到,离得这么远的岛还可以显得这么相似,以至于脑子里明明知道自己依然在中国,但心里难免有回到老家的幻想。毕竟,所谓家不仅仅是迎接人诞生的那个地方。
很可惜,匆匆行程让我们没来得及与当地居民互动,但安慰的是能通过沿路的街市看到人们在买卖当中显露于表的那份开朗,似乎是岛上人生活的一种普遍表现。一般“岛”这个词涉及分离于世界,涉及处境孤立的事物;在英语和西语两门语言中,这个观念更为明显,即指“隔离”的词(isolation)来源于“岛”(island)这个词。但作为一个岛国的居住者,我可以说一件或许将令读者惊讶的看法:其实,岛上的生活是最为不隔离的,反而比大陆上的更为整合。endprint
在某种意义上,全球是个巨大的岛,周围只有海洋似的无限太空。但大陆和岛屿有些重要差别。大陆,由于土地广阔并且资源丰裕,居民生活相对独立,人与人之间有物质上的距离,从而人之间也有心理上的隔离。虽然,在拥挤的大城市里,各方面的距离被缩短了,但人们的疏外感则增强了。迄今,大城市处处有高楼,日升日落被彻底流放,生活被冷漠地机动化了,人生之路便形成迷宫,在同一街道行走的人或许永远碰不到。
在哈瓦那有个与整个城市不一样的地区,那是古巴高建筑最多的地方。这地区被称之为Alamar,意思是“向海边”,恰好这个地方也在海岸。这些建筑都是由前苏联建设的,迄今可能还有不少八十年代搬过来或移民的俄罗斯人以及由他们与古巴异族人通婚的后代人。后者其中一个是我的大学同伴,之后还成为我的好朋友,因此有时下课后去他家,果然他家正好在Alamar。那时候,我才发现那个地区的另一个特征,即基本上所有的建筑都很相似,难怪每次我一个人回家总会迷路。其实,对我来说这等于每次可以找到一条新的路,以至于后来想,有时候迷路可以成为做某种新发现的代价。在我体验“找一条新的路”的过程中,有了一个发现,住在Alamar的人彼此之间竟然距离大、很陌生。那里建筑物的房间都是相连的,不过房间里面的人却是相隔的。开朗的古巴人,特别爱开玩笑,可以说音乐和幽默已经成为面对困难的一种普遍方式,若研究古巴笑话的演变历史将发现其主要特性在于把悲伤经验和不复境地当成笑话的原材料。这种情况奇妙而又自然而然地扩展到幾乎任何显著的东西上了,Alamar不是例外的,人叫它的绰号是“Elpalomar”(鸽舍),讽刺那里的人住得很拥挤。于是,我到中国来以后,每次看到草房区的建筑,就不由得感觉我在Alamar了,即便我不那么爱开玩笑但难免想起“鸽舍”的恰当讽刺来,心里还以为那些万房之高楼仿佛是荒谬的群岛。
现代社会的高楼,很好地表明人们之间的垂直距离虽缩短了,水平距离却增加了,人处于不同的无连接阶层。似乎,在大陆的城市里人们被物品的富足与机会的不足所约束,而激烈竞争使人生范围“岛化”。当然,岛国的生活,尤其是在高速发展的首都,如日本的东京,有时候也是这样。与此相反,在像涠洲岛这样的地方,居然还能看见岛上原始的生活方式。在这里,生活的节奏与自然的节奏彼此相符,夜里渔夫在海里钓鱼,白天妻子在市场把丈夫钓的鱼卖出去。当人们相处时,没有犹豫,也没有转念一想,更没有看不见的障碍,反而是有一种心照不宣的依赖感,他们心里都知道在岛上完全独立生活是不可能的。通常,岛民都比较热情友好,轻而易举地向别人借东西,又自然而然地借给别人自己的东西。在古巴也是这样,似乎邻居之间存在一种自由贸易区,通过此几乎什么都可以借用,从一匙糖用来冲咖啡,到一件西装参加某个好朋友的婚礼。通常,这也意味着人家会把那一杯咖啡分享给你,也意味着那个人会邀请你去参加哪个朋友的婚礼。从另一方面讲,我记得有时候乘公交车与旁边的人开始聊天,结果当你到该下车的那一站时,基本上知道了那个人的生活,甚至一些比较隐私的事。这样,两个陌生人不知不觉间就成为彼此熟悉的人。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自认空间极缩小到似乎消失的程度,甚至,某些被看为隐私侵犯的行为就理所当然地失去这种一般的意义。至于北海的“疍家人”,作为生活在海上的民族,我猜想更应该是这样,因为其条件所允许的自认空间绝不大于其生存空间。总结起来,悖论在于大陆的生活更适合用“岛”这个词来描述,而这准确地反映了人的本性,即固有的依赖性与相对独立性的愿望这两者之间的永恒矛盾。
据上所述,北海和涠洲岛两者的特性在一些方面上,体现了人生的地理特性。其实,人都有岛似的孤立之地,也有陆地似的交融之地。
涠洲岛的最高处上有一座白灯塔。该灯塔的设计较独特,上部和下部都是八角形,两者之间的隔墙是圆柱形的。虽然,目前灯塔装备了自动装置,但其与初期的那些在地中海边上发光的大火堆的基本功能一点也没变,即用光亮来充当向导。对于涠洲岛,作为以商业捕鱼为主,这座灯塔至关重要。每天,明亮白光从白灯塔中散发出来,撕裂漆黑之帐而使得处于海中的渔夫能够找到回家的路。没有比这些渔夫更理解并敬畏大海之奥秘的人,他们自身体验过大海的愤怒和静默,亲眼看过强烈风暴和风平浪静,甚至他们生存的来源也可能有一天将成为自身下沉的大坟墓。难怪他们心理与大海存在一种爱与恨之情。因此,可以猜想对于渔夫,尤其是在广大的黑暗中干活的时候,白灯塔的白光表征地上有亲人的温暖在等待。对于一个从没下过海的人,灯塔只是既有点神秘又冷冷静静的地方。然而,对于那些时时刻刻面临死亡的渔夫则不一样,当他感到疲惫或灰心的时候只有转下身就立刻可以看见家人盼望般的那个闪光。对他们来说,即使有一天被海浪埋葬于海里,恐怕那一天的告别是最后的,但在那悲哀的瞬间还有一条由灯塔散发出光明而形成的路可走。所以可以说,鳄鱼岭上灯塔真正的意义就是涠洲岛渔夫心上的可靠锚。
灯塔之所以能发挥这么奇妙的作用,是因为它处于两种世界之间的裂缝中。也就是说,其脚踏在土地上而其臂向大海伸出,而且为了有效地发挥导向的作用,灯塔的高度应当以天与海的共同边缘为参照,也就是说,灯塔的归宿是由其至地平线的距离所决定的。在某种意义上,人生也是如此。若某人要真正地有作为,真正地产生好的影响,做出有真正的意义的事情,那么,他就必须勇敢地站在敌火下的战壕里,或陷于废墟之中,伸出手去抓那些有待拯救的人。有时候,为了做到像灯塔这样的高尚使命,我们首先需要放弃某些便利条件,需要放弃自私的追求,这时候就意味着要放弃逃避困难的行为,并且主动地为他人去面对原来不属于自己挑战,捍卫那些注定要失败的事业,探索那些可能永远找不到答案的难题。然而,这样的地方与我们距离不远,这样的地方甚至是随时随地都可能遇到,因为那是我们无法逃避的基本存在方式,即此时此地。另外,表面上灯塔是不动的,但事实上它的影响深远。同样,无论我们在什么条件下,都决不会把我们约束到完全失去穿越自身而影响别人的能力,无论周围有多黑,也绝不会把我们心灵的火焰完全熄灭掉。毕竟,没有绝对奴役,那约束我们的枷锁也有可能正是引发我们最大力量的根源。因为,我们不仅仅在于这个世界,也可以构造更好的世界。为此,也许权衡自身生活的方式应该要像界定灯塔高度一样,即通过对于地平线的参照。很可惜,视野就是人们总是视而未见的远处参考系,与此相同,崇高的理想经常是被置之不理的人生指南。缺乏心里地平线的人,犹如缺乏光明的灯塔。最后,涠洲岛上灯塔所发出的光线与世上任何别的灯塔都是不一样的。事实上,每一座灯塔的闪光间隔时间都不一样,甚至潜水艇雷达所收到的信号也都不一样。但是,原则上灯塔的机械都有一个共同的技术问题,那就是光线的色散,正因此都需要安装一个特殊透镜(以前叫作菲涅耳透镜)来纠正光线的轨迹。同样,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只不过都需要改善,有时候需要修复,又有时候需要复兴。要装满高尚信念,要制定高尚的目标,总得追求高过自身的东西。只有通过谦卑地接受纠正固有的毛病,人心中发出的独特白光才能无障碍地穿过无边无际的阴暗而到达目的地。endprint